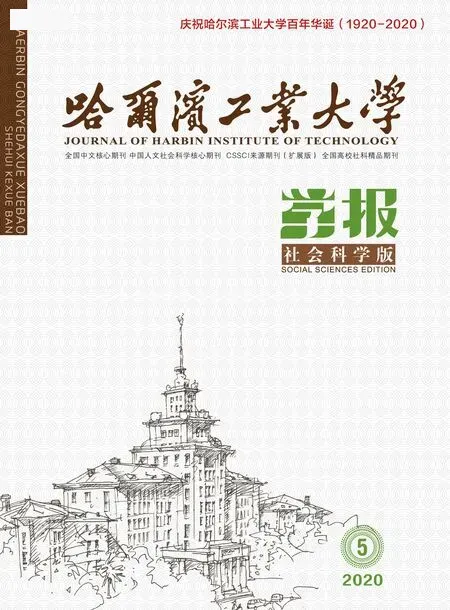宋代书判的散体化及其文体重构
王晓骊
(华东政法大学 文伯书院,上海201620)
书判①书判,又称判词或判,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都以“判”为独立文体。盛于唐宋,唐代多骈判,而宋代则以散判为主。唐代判词留存至今的有张鷟《龙筋凤髓判》、白居易《甲乙判》、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判词、《文苑英华》卷503—552等,均为骈判。宋代除北宋早期余靖等人散见于文集的判词为骈判外,基本都是散判,大多收录于南宋理宗年间成书的《名公书判清明集》②《名公书判清明集》共收录判词和其他公文475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在整理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亦简称《清明集》)时,又将刘克庄、黄榦、文天祥等人文集中未收入本书的判词一并作为附录出版,共计543篇,这样,南宋现存散体书判基本都收录于此书。。作为现存第一部散判集,《清明集》共收录南宋判词及其他相关文书将近500篇,除标注为“花判”的叶岩峰《占赁房》和《赁者析屋》两篇外,其余都是散判,且均为真实司法语境中的实判。唐宋之间书判的散体化带来了文体风格的重大转捩,但是后代文章学家对书判文体特征的认识并不准确,明代吴讷“以简当为贵”[1]的概括,实际上是对基于考试语境的骈判的总结,而无法涵盖宋代以后居于主流的散体实判的基本特征。宋代书判文体风格和文体规范的形成,与当时的司法实践和文化思想有密切关系。值得重视的是,这种时代特殊性造成的文体特征,在后代实判中基本被继承下来,成为书判的文体规范。因此,我们认为勾勒梳理宋代书判的散体化及其文体重构的过程,是全面考察书判作为独立文体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书判文体发展的语境演变
从表面来看,书判作为政务类实用文的文体定位并没有太大争议,刘勰所谓“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文心雕龙·书记》)[2]的论述,对这类文章早就作了整体性的规范。但具体到书判却并不那么简单,尤其是唐代骈判的盛行,使书判一度突破了“艺文之末品”的文体定位。从唐代骈判到宋代散判,书判经历的不仅是从骈文到散文的形式转变,更是一次文体重构的过程。而这种文体重构的关键因素在于书判的语境演变。
从现代意义而言,书判作为法律文书的语境是非常明确的,即司法机关的裁判文书。但在古代中国,如果不算文学作品中的书判,至少还存在两种语境:一种是现实的司法语境;另一种则是官员选拔和考核中的考试语境。明代文章家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因此将判词分为“断狱之词”和“选士之词”[3]127-128,也就是当代学者所谓实判和拟判。
从源头而言,书判的出现一定是司法实践的产物。“断狱之词”即实判出现的时间非常早,有的学者甚至上溯至舜,而西周晚期出现实判应该是可以确定的[4]25-26。判词的成熟则是汉代以后的事:“古者折狱,以五声听讼,致之于刑而已。秦人以吏为师,专尚刑法。汉承其后,虽儒吏并进,然断狱必贵引经,尚有近于先王议制及《春秋》诛意之微旨。其后乃有判词。”[3]127-128从周汉流传下来的判词来看,这些判词都有要言不烦的特点,用语极简洁,句式则短小精悍,三言、四言居多,铿锵有力,体现了“执法据理”的原则,自有居高临下、理直气壮的气势。如西周《匜铭文》[5]可以视为现存最早的判词.判词全文仅80字,用第二人称,是直接面对当事人的宣判,全文大多是二言、三言、四言、五言的短句,仅从字面来看,就可以感受到司法官伯扬父严峻的语气和不容置疑的威严。春秋时期的判词直接延续了这种风格,如《左传》“昭公元年”记载郑国子产的判词就与此类似:
国之大节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听其政,尊其贵,事其长,养其亲,五者所以为国也。今君在国,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国之纪,不听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贵也;幼而不忌,不事长也;兵其从兄,不养亲也。君曰:“余不女忍杀,宥女以远。”勉,速行乎,无重而罪。[6]
直到汉代,董仲舒《春秋决狱》留存下来的数篇判词,如《君猎得麑判》[7]也是简短的散文,具有相似的风格。由此可见,判词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居高临下的气势,在早期散体判词中就已经定型。
然而,书判的原初文体规范随着制判纳入科举考试而被打断。据唐人记载,“国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选,主者将视其人,覈之吏事。始取州、县、府、寺疑狱,课其断决,而观其能否。此判之始焉”[8]152;官吏铨选,亦需试判,《新唐书·选举志下》:“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9]唐代书判文体风格的形成,与科举考试有直接关系。一方面,从隋开始,科举考试中的通用文体即为骈文。隋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就曾云: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競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競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10]
可见,隋朝的科举考试,骈文已经是主流形式,而“朝廷据兹擢士”的考试语境,无疑是骈判形成的重要因素,唐代最负盛名的判词集张鷟《龙筋凤髓判》、白居易《甲乙判》就都是针对应试的骈文拟判。而“(唐前判文)在语言上与唐代的拟判讲究骈化文采的倾向性差异较大,但与真正案判的差异并不明显。总之,唐前判文与唐判的差异主要在于与拟判的比较”[11],可见拟判的骈文化是考试语境引导的结果。
另一方面,“选士”的考试语境,直接决定了唐代书判偏重于文辞的审美追求。应试而作的拟判,是以考官为读者进行设计的,格律的优美,对仗的精准,典故的深奥,都是让自己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的利器;换而言之,拟判的考试语境决定了审美追求高于实用目的。被奉为士子圭臬的张鷟《龙筋凤髓判》就因其“全类俳体,但知堆垛故事,而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殆是无一篇可读,一聊可味”[12]358而被南宋人所批评。汪世荣教授甚至认为《文苑英华》中的判词“大多注重词藻的华丽和用典的堆砌,有时竟然不顾律令条文规定或封建礼教的要求,囿于文字工整的范围。……仅具有文学欣赏的价值”[4]55。考场语境对书判的影响,不仅限于拟判,也会渗透到实判的创制中去。据唐人记载:
裴琰之弱冠为同州司户,但以行乐为事,略不视案牍……命每案后连纸十张,令五六人供研墨点笔。琰之不上厅,语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倾州官寮,观者如堵。[8]120
文案堆积但知行乐,倚柱断之而不上厅,只凭主案者略言其事意,不细梳其始末,不深究其情理,就手不停缀,落纸如飞,这种传奇式的记载虽有夸张之处,但其判文恐怕也只能是“词理纵横,文笔灿烂”的“花样文章”,而不是“执法据理,参以人情”的临政断狱之文。
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带来了书判语境的根本改变,整体而言,就是考试语境全面让位于司法语境。这种改变以王安石科举制度改革为界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科举考试文风的改变,促使拟判的制作中,散文取代骈文;第二阶段是制判退出科举考试,彻底回归司法实践,为新的文体风格和规范的确立提供现实基础。
先来看第一阶段。宋代书判的散体化首先出现在拟判之中。“唯宋儒王回之作,脱去四六,纯用古文,庶乎能起二代之衰,而后人不能用,愚不知其何说也。”[3]127-128而目前可见的王回判词,均为拟判,应该都是应试之判。王回于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这一年的科举欧阳修知贡举,立排怪诞的“太学体”文风,对于宋文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事实上,科场文风的改变在此之间就已经开始。张方平《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奏》:“自景祐元年有以变体而擢高第者,后进传效,因是以习。尔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13]37册,53张方平所谓“变体”指的是效习古文的“太学体”,也就是说,景祐元年(1034)的科举考试就已经不再是骈文一统天下的局面了。可见,在经历了自“景祐元年有以变体而擢高第”之后的“传效”之后,散体古文取代西昆体时文(即骈文)实际上是受到科举制度的保障和推动的。而从北宋现存不多的拟判来看,天圣二年(1024)中进士的余靖留下的拟判均为骈判,而皇祐五年(1053)榜的韦骧和嘉祐二年榜的王回留下的拟判,则均为散体。由此可见,景祐元年(1034)科场文风的改变在科场拟判中得到了回应。
再来看第二阶段。王安石变法改革选举制度、尤其是官员铨选法,对于书判创制风气的转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制判退出科举考试。“熙宁铨试法的实施,事实上废止了幕职州县官依固定年限参选的‘守选’制度及自唐代以来铨试中‘判’这一考试内容”[14],迫使书判回到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去。另一方面,官员铨选制度也加强了对官员实际司法能力的考察:
及铨曹合注官选人,自来例须试判三道,因循积弊,遂成虚文,皆未为允。今欲改更下项,应得替合守选幕职州县官,并许逐年春秋于流内铨投状乞试,或断公案二道,或律令大义,各听取便乞试。[15]4474
可见,是将作为写作能力考查的“虚文”替换成“断公案”的实际能力考查,以及对“律令大义”即法律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断公案”的材料,“并取旧断案内挑拣罪犯攒合为案”[16],即来自实际案件,而“断公案”的要求也明确必须依据具体法令法条:
其试公案……刑名须明具,理断归著及所引用条贯、断遣刑名,逐一开说。其律文大义,即须具引律令,分明条对,如不能文词直引,律令文义对答者亦听。[15]4474
简而言之,必须把具体的法令法条作为断案或者阐发法理的根据,杜绝了凿空虚构式的“纸上谈兵”和“家长式断案”的随意性。断案的最终文字呈现虽然与判词有一定区别,但包含了对案件判决的法律依据,“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判断的过程和结论”[4]2,具有书判的基本要素。在之后的官员铨选考试中,“断公案”被保留了下来,如宋室南渡之后,就恢复了“试刑法”考试,并以案例分析为主。①据《宋史·选举三》:“绍兴元年,复刑法科。凡问题,号为假案,其合格分数,以五十五通分作十分,以所通定分数,以分数定等级。”可见,是以断案为唯一考试内容。参见《宋史·选举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73页。毫无疑问,选举制度对司法实践的高度重视,最终推动书判创制成为司法实践的一部分,从而重构现实司法语境中的文体规范。
二、宋代司法实务与散体书判的文体要素
宋自立朝以来就重视司法实务,宋太宗曾对群臣说:“朕以庶政之中狱讼为切。钦恤之意,何尝暂忘”[15]6677;宋真宗则云:“法官之任,人命所悬。”[17]这也成为宋代士大夫集团的共识。欧阳修曾自述自己的经历:
大底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以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18]
欧阳修对案判存在问题的讶异和警醒,并不在于其文笔卑陋,而在于“枉直乖错”,即错判、乱判等原则性错误,他由此而发“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的感慨,也就是将判词看作“政事”而非“文学”。欧阳修的这一警示对宋代、尤其是南宋亲民官影响极深,刘克庄曾自述其临政断狱的心理:“数佐人幕府,历守宰庾漕,亦两陈臬事。每念欧公夷陵阅旧牍之言,于听讼折狱之际,必字字对越乃敢下笔,未尝以私喜怒参其间。”[19]632
刘克庄对狱讼的重视在南宋士大夫文人中是有代表性的,最显著的标志是出现了一批关注州县民事案件的政书,如《作邑自箴》《州县提纲》《昼帘绪论》等。其中署名陈襄的《州县提纲》①《州县提纲》,明代杨士奇《文渊阁书目》题名为北宋陈襄,但语涉南渡之后事,当为南宋人所作,《四库全书提要》辨之明矣。详见《州县提纲》所附《四库全书提要》,中华书局1985年版。共四卷,除第一卷谈为官之道,后面三卷对狱讼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易犯之错,一一陈说,极为详备。再比如真德秀出任地方官,下车伊始,即撰《咨目呈两通判及职曹官》,文中专列所谓“十害”[19]2-3,有六条是有关狱讼的,包括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等,超过一半,可见狱讼已经成为士大夫临政最关切的事务。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事诉讼不断增多。而民事纠纷多发生于亲属邻里之间,对这些案件的处理,又往往与中国古代治理理念中的教化职能有直接关系。《州县提纲》卷一即云:“为政先教化而后刑责,宽猛适中,循循不迫,俾民得以安居乐业”[20]2;胡太初则认为“愚民懵无知识,一时为人鼓诱,自谓有理,故来求诉。若令自据法理断遣,而不加晓谕,岂能服负者之心哉?故莫若呼理曲者来前,明加开说,使之自知亏理”[21],强调对百姓的说服和劝导工作,以达到教化目的。
对狱讼、尤其是民事诉讼的重视直接影响了判词的制作,《名公书判清明集》的结集就最大程度体现了司法实务对判词创制的引导。“它选录的标准,主要不在文章,而在是否‘清明’;刻印的目的,主要不是供士人应试之用,而是供为官者判案参考。如果当时社会没有这种需要,《名公书判清明集》应不会出版;即使出版,也不会在以后一再重刻。”[22]在司法实践的引导和推动下,南宋书判形成了由叙述、分析、引证、判断和议论等要素组成的新的文体结构。
首先,司法官作出判决的前提是要将纷乱如麻的案情原委梳理清楚,故叙述是书判的基础要素。而叙事虽以简要为主,但于关键处必须一一剖析,绝不能草草带过,否则是无法让当事人心服口服的。《清明集》所载判词的篇幅或长或短,从百余字到上千字,并无一定,完全视案情的复杂程度和实际需要而定。而制判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文字驾驭能力决定判词是否能简而不漏,详而不芜。如范应铃《罗棫乞将妻前夫田产没官》[19]107,牵涉人物关系非常复杂,表面看来是关于田产的争讼,但其中还隐藏着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一是立继绝子孙,二是夫死改嫁事。这两者是本案的前置事件,唯有先对这两个事件的合法性进行判定,才能对田产问题作出合法判决。所以判词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简单梳理涉案人的关系,并从中剥离关键事件,进行独立审议,最后综合判决。值得注意的是,判词对这一复杂过程的呈现,整体上仍然非常精要,是要言不烦与滴水不漏相结合的典范。
其次,基于逻辑和常理的分析。民事纠纷中不乏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欺诈行为,司法官需要非凡的洞察力,识别真伪,勘明是非,并体现在判词之中,从而起到主持公道的作用。如李文溪《利其田产自为尊长欲以亲孙为人后》[19]258-259,阿张夫死子亡,暮年疾忧交作,不得已归母家,夫族有吴辰者,以其孙强为其后,以图谋其田产。判词从三方面揭穿了这一欺诈行为:立嗣文书中作为关键证人的族长签名为吴辰自己所署,属于自证行为,不可采信;通过询问吴氏亲属尊长,证明阿张田产是其出嫁时的自随田,不属于吴家族产;阿张同意立嗣的文书是吴辰之子吴君文伪造。吴辰父子侵吞阿张田产的奸计由此昭然若揭。再如吴革《兄弟一贫一富拈阄立嗣》,叶容之、叶咏之争相以己子为堂叔叶秀发继嗣,却都不愿为亲兄瑞之立继,吴革一眼识破了他们不可明说的心思:“舍亲就疏,此其意为义乎?为利乎?盖秀发生理颇裕,瑞之家道侵微,容之、咏之徇利忘义……”[19]203单刀直入、一针见血的剖析使书判具有基于事实和逻辑的穿透力和说服力。
再次,引证和判断。对于当事人是非对错的判断是书判的最终结论,同时其判决必须有法律依据。胡颖曾自述:“本府之所处断,未尝敢容一毫私意己见,皆是按据条令”[19]281,对法律条文的引用是《清明集》判词的重要特征。据统计,《清明集》(含正文和附录)明确标明引用各种形式法律的有133篇,其中引用《宋刑统》条文60次,引用《刑统》以外的敕文130次、指挥7条、令文18次、格文2条、“看详”5条[23],基本体现了依法判决的原则。有的案件涉及法律条文较多,判词往往一引再引,如刘克庄《继绝子孙止得财产四分之一》先后引述三条法令:“在法:诸户绝人有所生母同居者,财产并听为主。”“考之令文:诸户绝财产尽给在室诸女。又云:诸已绝而立继绝子孙,于绝户财产,若止有在室诸女,即以全户四分之一给之。”[19]251为案件的判决提供了详尽的法律依据。当然,南宋书判的引证不仅限于法令法条,有时还涉及《春秋》《诗经》等儒家经典。
最后,说理议论。不可否认,宋代士大夫法律素养的习得是与儒家德治思想相始终的,官员断狱的根本目标是“息讼”,其实现必须同时依靠道德伦理的教化手段,这就决定了判词不仅承担判决的功能,也具有训诫、劝导和说服的功能,说理议论由此成为书判的核心组成部分。书判的说理往往融合在整个行文之中,或先叙后议,或夹叙夹议,而越是与人伦相关的民事纠纷,其书判说理的成分就越多。南宋翁甫书判《僧归俗承分》所涉民事纠纷中,出家还俗的侄子要求婶母归还亡叔遗产的一半,案情并不算复杂,而书判夹叙夹议,或责之以礼:“烈乃德懋亲叔父,壮年当家,所宜抚育犹子,教以诗书,置其家室,以续乃兄宗祀,岂不仁至义尽乎!”或动之以情:“以十四岁小儿,弃骨肉,礼僧为师,在故家七十余里外,零丁孤苦,至今念之,使人恻然。死者有知,岂不含恨茹痛于九泉之下,何烈之设谋用计,何其忍哉!”或晓以利害:“当职此判,非特为德懋计,亦所以为缪氏计。传不云乎:蝮蛇蛰手,壮士解腕。谓其所弃者小,所保者大也。德懋之归俗,其何烈身后之遗毒乎,缪氏子母何以御之?万一信唆教之言,不尊当职之判,越经上官,争讼不已,则何氏之业立见破荡尽净,此其事理之所必至也。”[19]138-139反反复复,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威胁利诱,说到底,就是为了规劝两家接受判决结果,“以绝两家之讼”,以全人伦之美。
三、以说理为核心的文体结构及其文体风格
从整体而言,书判要素的组合比较自由,并没有形成严格的公文格式和结构,但《清明集》所录书判的共同特征是有比较充分的说理。从结构而言,判词最常见的说理方式有三种:一是以伦理性的议论开篇,开宗明义,表明制判者的观点。如胡颖《妄诉田业》[19]123,全文不到300字,从判词一开始,就用了将近一半文字以论词讼之慎为;翁甫《僧归俗承分》开头即云“余观何氏之讼,有以见天道之不可欺,人伪之不可作也”[19]138,即为全文定下基调,后文或叙或议,不出天道人心之论。二是引述法条法令,开门见山,直接引入对案情的分析,然后再出之以人伦教化之义,进一步解释或批判。如翁甫《已立昭穆相当人而同宗妄诉》[19]247,先引三条法令,判决王华老为王霖继嗣有效,然后批评同族王宗权垂涎其财产,进而侵夺其财物的不义行为。三是先剖析案情,然后进行分析和议论。如刘克庄《继绝子孙止得财产四分之一》[19]251先简要叙述案情原委,分析争讼起由,揭露斥责一方当事人田通仕不顾兄弟人伦,欺凌幼孤的行为,然后从生活实际出发,抽丝剥茧,批评另一方当事人刘氏之谬,说明财产处分的依据和道理。这三种形式的共同特点是以说理为核心,以案情的叙述和法律条文的引证来支撑判决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其目的都是为了把观点阐述清晰,并让对方易于接受。由此可见,散体书判的结构虽然自由,但已经形成了以说理为核心的特点,散体书判文体风格的形成与此密切相关。
南宋胡颖曾云:“殊不知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循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19]311胡颖曾任平江府知府兼浙西提点刑狱,是一位有司法实务经历的亲民官,《清明集》就收录其判词76篇。他的这番意见,当然不是纸上谈兵或者书生之见。在南宋的现实司法语境中,法意和人情是必须同时考虑的两大因素。而出于教化和劝谕的目的,南宋亲民官也强调听讼断狱一定要耐心晓谕,使人心服。如胡颖临政断狱,“每事以理开晓,以法处断”[19]280,理法兼顾,而理在法前;《州县提纲》甚至主张对无理之人也应耐心解释,开导说服:“其人果无理矣,则和颜呼之近案,喻之以事理,晓之以利害,仍亲揭法帙以示之,且晰句为之解说”,反对“不先委曲示之以法,而骤刑之”[20]12的粗暴做法。不管是人情的现实,还是教化的目的,以逻辑性为主要特点、以严谨有力为主要风格特征的法律语言,自然无法完全让乡民理解并接受的,而骈体书判古奥典雅的风格无疑也不适用,散体书判由此形成了与一般公文或者政论文不同的风格特点。
从说理风格而言,详尽透彻、委曲近情取代了“简要”“含蓄”的传统文章规范。南宋楼钥曾盛赞一位地方官:“君资明而健决,两词至前,情伪立见。书判数百千言,反覆切当。每曰:久讼废业,实官司不决之过,惟详尽不可转移,则安居矣。”(《朝请大夫史君墓志铭》)[13]266册,101所谓“数百千言,反覆切当”“详尽不可转移”,都说明发展至南宋,“简要”原则已经实际上并非当时散体化实判的真实风格。《名公书判清明集》也支持了他的说法,上文所举翁甫《僧归俗承分》即是典型。再如胡颖《兄弟侵夺之争教之以和睦》[19]369开篇以宗族和睦则兴为立论基础,先从“叔伯兄弟,皆是祖先子孙”入手,论证叔伯兄弟之间和睦相处的情理基础;然后推导出“必爱兄弟如爱吾身,然后为尽奉先之孝”,把睦族和孝先联系在一起;再进一步论证“所谓爱者如何”:“出入相友,有无相资,缓急相倚,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持,锥刀小利,务相推逊,唇吻细故,务为涵容,此之谓爱”,以上是正面论证。接下来反面论证,如果兄弟相攻,其心何忍?何以奉祭祖先?何以见祖先于地下?又引故事,以清河之民兄弟先之以诉讼,终之以息争为例,激发当事人见贤思齐之心。整个判词,推理论证、举例论证、正反论证等各种手法综合使用,以达到说理的目的。《宋史》说胡颖:“书判下笔千言,援据经史,切当事情,仓卒之际,对偶皆精,读者惊叹”[24]。从《清明集》所收其判词来看,“对偶皆精”云云,纯属想象;“下笔千言,援据经史,切当事情”,还是恰如其分的。其余如范应铃《漕司送下互争田产》、胡颖《随母嫁之子图谋亲子之业》、韩竹坡《同宗争立》、无名氏所拟《立继有据不为户绝》《双立母命之子与同宗之子》等都是超过500字,甚至将近千言的长文。
从说理角度,书判常常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变换角度进行论述,一方面全面照顾当事人各方的利益,另一方面拉近当事人的心理距离,增强说服力。翁甫《僧归俗承分》[19]138-139,不仅从审判官的角度对当事人之一缪氏进行单向的宣判和教谕,而且还从缪氏的角度考虑:“万一信唆教之言,不尊当职之判,越经上官,争讼不已,则何氏之业立见破荡尽净,此其事理之所必至也”;吴革《生前抱养外姓殁后难以动摇》[19]201分别从当事人双方剖析案情,还原事件,既从抱养的外姓侄子邢坚角度,谴责对方当事人叔父邢柟对侄子未尽教训维持之责,又从叔父邢柟的角度,批判邢坚听信谗言,不能敬事叔父,从而抚慰双方的情绪,兼顾双方的利益。
从说理手段而言,《清明集》所收判词一般采用分析与说教相结合的办法。由于书判面对的多为乡民,相比于逻辑推理,诉之于情感和经验的感化和说服可能更有效果,所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是书判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间用类比、引用,偶有夸张和讽刺等手段,以达到条理性与情感性并存、说服力与感染力兼具的效果。用类比的有胡颖《母讼其子而终有爱子之心不欲遽断其罪》[19]363,民阿周讼其子马圭不孝,判词以汉代陈元因不孝为母所讼的案例进行类比;《叔教其嫂不愿立嗣意在吞并》以国立异姓与家立异姓相类比,“国立异姓曰灭,家立异姓为亡,《春秋》书莒人灭鄫,盖谓其以异姓为后也”[19]246,说明立异姓为嗣的危害。引用的经典除《春秋》外,还有《诗经》。天水《子与继母争业》:“自《柏舟》之诗不作,寡妇始不能守义以安其室;自《凯风》之什既废,人子始不能尽孝以事其母”[19]365,引《诗经》而申孝义之道;甚至还有用唐诗的,如叶岩峰《谋诈屋业》引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尝读杜甫诗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我天下寒士俱欢颜。’又曰:‘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19]192,以此对比、讥刺凃适道夺其师所居之屋,置其于受冻之地的卑劣行为。这也是引用、对比和讽刺综合使用的实例。这些积极修辞手法,都有助于增强判词的说服力。
在说理语言上,具有明显的生活化和情感化倾向。一方面,唐代拟判四六对仗的语言形式在南宋被视为不严肃的方式,甚至目之为“花判”:
(唐人)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数十语,今郑畋敕语、堂判犹存。世俗喜道琐细遗事,参以滑稽,目为花判,其实乃如此。[12]127
证之以《清明集》,其中叶岩峰《占赁房》和《赁者析屋》[19]196-197,均为四六文而并无所谓“滑稽”之语,却被标注为“花判”。由此可见,在南宋司法语境中,骈俪对偶的华美语言形式已经不再适用,从而被剔除出了实判的语言系统。朱熹曾批评当时的公文写作:“被几个秀才在这里翻弄那吏人,翻得来难看。吏文只合直说,某事是如何,条贯是如何,使人一看便见,方是。今只管弄闲言语,说到紧要处,又只恁地带将过去。”[25]南宋散判大多文字明晰浅显,口语化程度较高,有的书判甚至直接使用口语。如胡颖《乡里之争劝以和睦》:“且道打官司有甚得便宜处,使了盘缠,废了本业,公人面前赔了下情,着了钱物,官人厅下受了惊吓,吃了打捆。而或输或赢,又在官员笔下,何可必也”[19]394。完全抛弃了高高在上的官方用语,全是白话,通俗易懂,也贴近乡民日常生活,很容易让当事人接受。
另一方面,注重语言的感染力。在句式上,除了陈述句外,还杂用祈使句、疑问句和感叹句,以表现不同的语气,达到不同的效果。陈述句用来梳理和分析事理,祈使句用来宣布判决结果,前者理性冷静,后者威严坚定。而反问句和感叹句,则在加强语气、渲染气氛、增强感染力等方面有显著的效果。如方岳《寺僧争田之妄》[19]127凡用四反问句,针对妙缘院寺僧与吴姓百姓争田的诉求,批驳其妄有十,极言事理之荒谬,气势逼人,几不可挡;翁甫《已卖之田不应舍入县学》[19]133连用感叹,文势如水注地,如马蓦坡:“若如此而可以舍受,是以吾圣文宣王维兼并之媒,县学之田当连阡陌矣!其诬先圣,污学徒,孰胜焉!”“孔主簿、吴八强不义之可畏矣!世道至此,可叹也哉!”书判也使用了大量情感词,如翁甫《僧归俗承分》[19]138-139,既有明确否定性的贬义词如“悍妻”“不晓事理”“遗毒”“唆教”等,也包含具有情感色彩、能够引起情感共鸣的词汇,如“藐然孤儿”“茫无依归”“零丁孤苦”“恻然”“含恨茹痛”等,以诉诸情感,引发共鸣。书判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说理语言形成了有助于认同的情感体验基础。
结 语
在南宋的现实司法语境中,散体书判作为面向民众的法律文书放弃了传统文章学家对“简要”“含蓄”“典雅”“深邃”的追求,走向周详全面,细密平易,甚至通俗家常,形成了与宋代其他实用文、与骈判完全不同的文体特征。这一文体发展走向同时具有法学和文学的双重意义:从法学角度而言,后代书判大多延续了司法与教化兼具的双重功能。直到今天,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判决书是否应该借鉴中国古代书判的说理方式,以更亲民的方式进行说理论证,以增强判决书的感染力和认同度,并实现道德引导的问题,仍然为法学界广泛关注[26],甚至也不乏这样的实例[27],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南宋书判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文体发展史上,也留存在了司法实践之中。
从文学角度而言,虽然书判对实用性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过文学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散体实判没有任何文学性或审美性可言,诚如王水照先生所云:
从我国古代散文历史形成的具体特点出发,似不宜把散文艺术性理解得太狭窄。我国古代文论家强调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强调结构、剪裁、用笔、用字,强调间架、枢纽、脉络、眼目等等,对于述意、状物、表情都是极其重要的表现手段,理应属于艺术性的范围。[28]
散体书判的发展,一直处在法理与人情的制衡消长之中。从法理的角度,要求有理有据,逻辑严密,判断清晰,具有不容辩驳的权威性;从人情的角度,要求周密详尽,语气委婉,循循善诱,兼顾说服力和感染力。两者的结合决定了散体书判的特殊文体风格,并成为后代书判的写作规范。而平易不芜的语言表达、错落有致的句式变化、夹叙夹议的言说方式、强烈的情感和气势等,都赋予散体书判一定的美感,成为其文学性的表现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