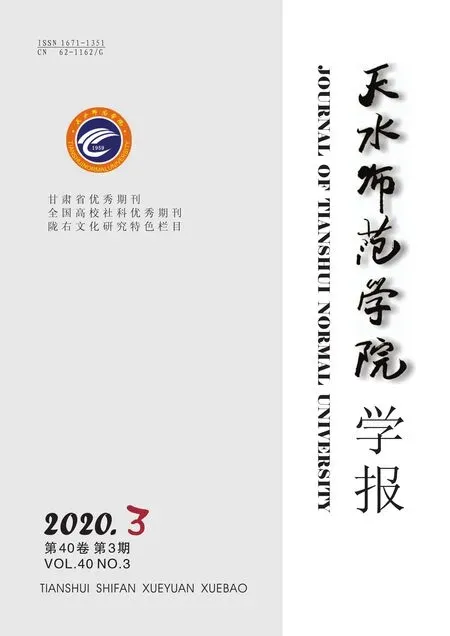论月兔意象的起源与发展
王东辉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论及同月亮有关的神话意象,除了盗药奔月的嫦娥之外,月兔应该最为大家所熟知,它同嫦娥一起,构成了中国月亮神话的核心元素。也正缘于此,我国首辆月球车就以“玉兔”命名。尽管月兔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是针对月兔形象的起源与发展演变,尚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既往的研究中,有些问题讨论得并不充分,需要补正之处尚多,因此有进一步分析说明的必要。
一、兔子与月亮
月亮中有兔子的说法不仅存在于中国神话,还见于其他许多民族的神话。《大唐西域记》就记载了一则月中有兔的印度神话。说的是兔子为帝释寻食而无所收获,遂举身赴火,以自己的肉身供食帝释。帝释感念兔子的诚心,遂将其置于月中,令后人世世得见。季羡林先生还由此判断中国月兔的说法起源于印度。[1]8南美印第安人传说太阳和月亮分别是纳纳渥瓦辛和德库西德卡尔所化,但最初月亮和太阳一样明亮,众神觉得这样不妥。于是,一个天神抓起一只兔子扔向德库西德卡尔,因此月亮失去了一部分光芒,脸上也因此留下了疤痕。[2]106除此之外,在英格兰、北美印第安人及非洲的神话中,都有兔子同月亮的神话。可见,月亮同兔子存在联系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文化现象。
兔子为什么会同月亮有这么紧密的联系呢?古人有种说法,即兔子可以“望月而孕”。张华《博物志》载:“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3]9《埤雅》曰:“兔,吐也,旧说兔者明月之精,视月而孕。”[4]49“望月而孕”当然是无稽之谈,但这种说法在古代却颇有市场,如《春渚纪闻》载:“东坡先生云,中秋月明,则是秋必多兔,野人或言,兔无雄者,望月而孕。”[5]83通过中秋圆月的明暗来判断兔子的多寡,不过是根据“望月而孕”的说法所作的主观臆测罢了。士大夫们未曾格物致知,轻信古书,所以会闹出这样的笑话。明人徐应秋就对此加以批驳,他在《玉芝堂谈荟》中说:“雌雄交感即孕,匝月而产四子,或三子,有至七子者。后每月辄如之,乃知前人所云兔‘望月而孕’与‘子自口吐’之说皆讹。”[6]823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古人之所以会有兔子“望月而孕”的说法,可能来自兔子假妊娠的现象。在母兔群养、仔兔断奶晚及受到不育公兔性刺激等情况下,母兔会出现乳腺膨胀,衔草做窝的现象,好似妊娠,却没有孕育胎儿,这就是兔子的假妊娠现象。[7]30古人认为兔子能“望月而孕”,当是受到了这一现象的误导。兔子多于夜间活动,其活动的时段多能见到月亮的隐现,古人对兔子假妊娠的现象无法解释,故而创造了“望月而孕”的说法。此外,“阴影说”也是一种解释月兔起源较为久远的说法。这一观点认为月中阴影的形状同兔子形似,因而附会出了月兔的说法。《灵宪》载:“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兽,像兔。”《苏鹗演义》说:“卯,兔也。其形入于月中,遂有是形。”[8]89月中阴影是否像兔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许多学者并不认同。
尹荣方在《神话求原》中认为月中有兔的神话当同兔子的生理特性有关。兔子交配之后,大约一个月即能产子,并且在生产之后马上能进行交配,一个月左右又能再次生育。兔子的生育周期同月亮的晦明周期极为接近,所以古人会把月亮同兔子联系起来。[9]119此说颇有道理。笔者认为,除此之外,月兔形象的形成还应同兔子的生活习性有关。兔子有一雅称,叫作“明视”。《礼记》载:“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刚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鸡曰翰音,犬曰羹献,雉曰疏趾,兔曰明视。”[10]207祭祀时,敬献给神的祭品都要换一个别致的名字,其目的是“异于人用也”,以示神人身份的不同以及对神的尊重。“明视”,颜师古注曰:“兔肥则目开而视明也。”此说较为牵强。李时珍解释为“言其目不瞬而瞭然也”。[11]2886即兔子较少眨眼,视域广阔,所以被称为“明视”。笔者认为,兔子之所以被称作“明视”,当同它们的生活习性有关。兔子为晨昏觅食的夜行性动物,野兔晚上较为活跃,在较暗的光线下也能看清东西,所以才被称作“明视”。正是因为兔子具有夜间活动的习性,才有可能发生“视月”的行为,并由此产生“视月”生子的说法及兔子拜月的民间传说,因而兔子才会同月亮联系在一起,成为月兔。月中白兔最早见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其一号墓帛画中绘有月牙形状的月亮,月中有白兔与蟾蜍。[12]57马王堆汉墓为西汉初年的墓葬,此时白兔与蟾蜍已经以成熟的神话形态出现在这种贵族墓葬里,揆度社会观念形成所需要的时间,我们有理由相信月兔的形象在先秦就已经形成。
二、月兔与捣药兔
在我们的普遍认知中,月兔是以捣药的姿态陪伴在嫦娥左右的,但是早期的月兔图像并非如此。汉代画像石、帛画、墓室壁画为我们认识月兔形象的变化提供了最早的图像。月兔图像最早出现在西汉初年的马王堆帛画中,从此时直到东汉一直是以奔跑的姿态存在;捣药兔的形象最早于西汉末年出现,直到东汉一直是作为西王母的固定搭配图像而存在。二者到东汉才开始发生混同,即月兔开始以捣药的姿态存在。那么月兔同捣药的兔子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原始形态里奔跑的月兔又是怎样变成一个捣药的月兔呢?
捣药兔较月兔晚出,探讨二者的联系与转变,我们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兔子为什么会以捣药工的形象出现。在偃师辛村出土的新莽时期的墓室壁画中,一只硕大的白色羽翼兔子半跪在西王母前,一手持臼,另一手当持杵,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捣药的图像。[13]137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捣药兔形象。进入东汉,艺术图像中的捣药兔开始大量出现,并基本构成了西王母图像的固定搭配,可以说有西王母图像的地方几乎都有捣药兔。相较于九尾狐、神鸟等图像,捣药白兔在西王母图像系统中出现的频次最高,比较稳定,所以李淞将它归为西王母图像志的核心图像。他说:“在一幅表现西王母的图像中,如果其中的图像组合减至最低因素,那么就是西王母配玉兔捣药;如果再减掉玉兔图像,则使西王母的可识别性受损。”[14]252
统观西王母图像系统中的兔子形象可知,捣药几乎是它在西王母图像系统中唯一的职能。白兔所捣之药为不死之药,乐府诗云:“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蝦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药可得即仙。”[15]612白兔能同西王母联系在一起,盖因不死之药的缘故,没有不死之药就没有西王母图像中的捣药兔,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理清西王母神话同不死之药的发展脉络,就能解决兔子为什么会以捣药工形象出现的问题了。
西王母形象的首次明确出现是在《山海经》中,不过此时她还只是一个“豹尾虎齿,蓬发戴胜”的神怪形象。经过不断的加工与发展,西王母的形象逐渐脱离粗鄙的形态而臻于成熟,并在汉代得到了极大的荣宠,几乎上升到至上神的地位。尽管不断丰满的西王母形象被人们寄托了多重诉求,诸如宜子孙、保富贵、求吉祥等,但长生不老始终是西王母这一形象的核心意义指向,从先秦到汉代从未改变。《庄子》言:“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16]199说西王母得“道”之后莫知始终,即她寿命变得绵延无期。《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同穆王唱和时说:“将子无死,还能复来。”[17]15如果穆王长生不死,还能复与王母相会,这就暗示了西王母可以长生不死。司马相如在《大人赋》中说:“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18]3060在西汉末年“行西王母诏筹”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中,其所传之语也是“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19]1476
西王母虽最早在《山海经》中已明确出现,但此时她还不是不死之药的拥有者。《山海经》所载可致长生的东西有多种,如不死树、甘木、不死药等,但这些不死之物主要为上帝及巫所控制。《海内西经》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20]301《大荒南经》载:“有云雨之山,有木名曰栾。禹攻云雨,有赤石焉生栾,黄本,赤枝,青叶,群帝焉取药。”[20]376《山海经》中同西王母有关的文献记载共有四处,但都没有将她同不死之药联系在一起。查阅其他先秦文献,亦是如此。
西王母同不死之药发生联系最早见于《淮南子》中的嫦娥奔月神话,《淮南子·览冥》载:“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何则?不知不死之药所由生也。”[21]217这是传世文献中关于嫦娥奔月神话的最早记录,也是西王母同不死之药产生交集的最早记录。当然,嫦娥神话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1993年王家台秦简《归藏·归妹》出土,其中两简的内容可将嫦娥神话的出现时间提前至战国。其307号简载:“昔者恒我窃毋死之□□”,201号简载:“奔月而攴占□□□。”[22]32这两则神话中没有提及西王母,西王母同嫦娥神话的关联或许是汉人的发明。但这一关联无论是发生在战国还是汉代,西王母同不死之药的联系都是自嫦娥奔月开始。
既然没有西王母掌管不死之药的神话就没有捣药兔的诞生,那么捣药兔出现肯定和嫦娥奔月神话有关,确切地说,捣药兔当同古老的月兔神话有关,捣药的白兔当是月中白兔形象的分化。这一现象,通过汉代画像石可以观察出来。李淞总结了汉代艺术中几个同西王母联系较为紧密的图像,有白兔、蟾蜍、三足乌、九尾狐等,其中三足乌、九尾狐、青鸟等早在《山海经》中就已经出现,如:“西王母梯几而戴胜仗,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海内北经》)[20]306“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大荒东经》)[20]347“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大荒东经》)[20]354它们都较早地同西王母一同出现在《山海经》这一大的神话系统中,有了被加工成西王母身边瑞兽的可能。然而,唯独白兔与蟾蜍没有在《山海经》中出现,而神话中的蟾、兔正是月亮的代表。搞清楚西王母与不死药的关系始于嫦娥奔月神话,以及捣药兔为月兔形象的分化,就能明白兔子是怎样和西王母联系起来的了。
月兔分化出捣药兔,除了不死之药神话的关系外,还应同其白色的体貌有关。白色是长寿的象征,在汉代文献及艺术图像中,长生的西王母就是白发满头。司马相如在《大人赋》中言:“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史记·司马相如列传》)[18]3060在西汉末“行西王母诏筹”的运动中,百姓亦“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正是因为信众意识中的西王母为白发的形象,所以人们才会将白发当作她传谕于众的信证。《抱朴子》曰:“虎及鹿兔,皆寿千岁,寿满五百岁者,其毛色白。”[23]41月兔通体雪白的外貌正符合人们对于长寿的认知,所以,在西王母同嫦娥奔月神话产生交集时,月兔开始同西王母联系起来,并以瑞兽的形象在她身边出现。
西汉初,兔子还仅是以月兔的形象存在,如马王堆帛画所绘的月中白兔,此时的兔子还没有同不死之药发生任何联系。这一状况在西汉中期开始发生变化。在西汉中期的卜千秋墓室壁画中,西王母图像前有一匍匐的白兔,口中衔着一株硕大的仙草。推其寓意,应当是白兔在向西王母敬献长生草药。这幅图像可以看作是月兔向捣药兔分化发展的过渡形态,兔子开始和西王母、不死药搭配出现。捣药兔的形象最终完成于西汉末年,并在洛阳辛村壁画中清晰地体现出来。此外,在大约同时期的郑州新通桥画像砖及始建国二年铜镜的图像中,都可以看到这一形象。
总之,捣药兔形象是由月兔形象分化而来,形成于两汉之交,并在东汉的艺术图像中大量出现。随着时间的推进及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逐渐将二者混同看待,最晚至东汉末年,月兔开始与捣药兔发生混合,[24]其表现就是月宫中开始出现捣药兔的形象。如山东安丘市董家庄出土的画像石中,[25]113就有兔子、蟾蜍执杵捣药的图像。同样的图像还有不少,如滕州市官桥镇大康留庄出土的画像石、泰安市大汶口出土的画像石等。汉代以降,月中捣药兔的形象日益强化,并逐渐替代了原有的月兔形象而固定下来。刘惠萍认为,月兔捣药形象的形成是月兔对西王母神话系统中捣药兔形象的借用,其实这只说出了月兔发展进程的后半段。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捣药兔形象首先应该是由月兔分化而来,然后才有了二者形象的混同,直至捣药兔完成对原始月兔形象的替代。
三、月兔与蟾蜍
随着月中捣药兔形象的强化,被逐渐置换掉的不仅是原始的月兔形象,还有作为月亮象征的蟾蜍的月中主体地位。虽然早在马王堆帛画中白兔与蟾蜍就已经共同出现在月亮之中,但在汉人意识中蟾蜍同月亮联系的紧密程度似乎更高一些,是月宫中的主角。在汉代艺术中的月亮图像里,除去蟾、兔共同出现的图像之外,还有许多只刻画二者之一的图像。其中,单独刻画蟾蜍的图像占多数,如洛阳卜千秋墓葬壁画里的月轮中就仅绘蟾蜍,[13]68而单独刻画月兔的则寥寥无几。另外,在蟾、兔同时出现的图像中,也往往是蟾蜍的体积明显大于月兔,马王堆一号墓帛画中的蟾兔即是如此,这明显同现实中二者的生物特征相反。据笔者统计,在《中国画像石全集》所录两汉画像石中,可明确判断月中出现蟾、兔的图像共计23幅,除去蟾、兔共同出现的11幅图像之外,剩余12幅图像全部为蟾蜍单独出现。在蟾、兔共同出现的11幅图像中,蟾、兔等大的图像有3幅,蟾体积大于兔的有6幅,而兔体积大于蟾的仅有2幅。由此可见,相较于月兔,蟾蜍作为月亮象征的主体地位更为明显。
蟾蜍月中主体地位的获得,当同古老的蟾蜍食月神话有关。《淮南子·说林》载:“月照天下,蚀于詹诸,腾蛇游雾,而殆于蝍蛆。”[21]556《史记》托孔子言曰:“日为德而君于天下,辱于三足之乌;月为刑而相佐,见食于蝦蟆。”[18]3237可见,蟾蜍同月亮的关系,源自蟾蜍食月的古老神话。《论衡》载:“儒者曰:‘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26]229对照《史记》所托孔子之言,月中蟾蜍正是对儒家所记录保存的食月神话的反映。在华夏文明早期,蟾蜍就是一种神圣的生物。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就发现了许多蟾蜍图像,如辽宁阜新查海遗址陶罐上的蟾蜍浮雕、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彩陶盆里的蟾蜍图像等。古人之所以会认为蟾蜍可以食月,应同这一生物的生理特征有关。我们知道许多雄性蛙类都有可以产生共鸣的声囊,这可以使它们鸣叫时的声音更为响亮。位于嘴部下方的声囊鼓起时成为一个泡状的圆形,正同满月的形状相似。此外,蟾蜍多于夜间活动,同月亮联系颇多。古人于月食时联想到蟾蜍声囊的消鼓,于是创造了蟾蜍食月的神话。《楚辞·天问》载:“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8]88“顾菟”为蟾蜍与兔,这在前文提及的汉代画像中就有体现。王逸说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8]85月中有蟾蜍的图像当在战国就已经出现,蟾蜍不利于月,画像中的月亮又为什么把它置于自己的肚腹之中呢?“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正是屈原面对这一图像所产生的疑问,无意之中为我们记录了一则古老的蟾蜍食月神话。
汉末魏晋之后,随着人们对月宫想象的增多,嫦娥开始被逐渐美化,与此相照应,有着美好形象的白兔在月宫中的地位逐渐提升,成为陪伴嫦娥的主要形象,逐渐取代了蟾蜍成为月宫中的主角,并在后世诗人的吟咏中不断强化。蟾蜍乃丑陋之物,早在先秦时期就有针对它的贬低之词,如:“鱼网之设,鸿①闻一多认为“鸿”即蟾蜍,在《〈诗·新台〉鸿字说》中有详细考证。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27]77在月中白兔被人反复歌颂的同时,曾经地位显要的蟾蜍却被提及的越来越少。
总之,兔子之所以能同月亮联系起来,盖缘于其匝月而孕的生理特征及夜行性的行为习惯。西王母图像系统中的捣药兔形象,实为月兔形象的分化。最晚至东汉末年,捣药兔逐渐同月兔相混合。捣药兔的形象不仅逐渐替代了原始的月兔形象,也替代了作为月亮主要象征的蟾蜍的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