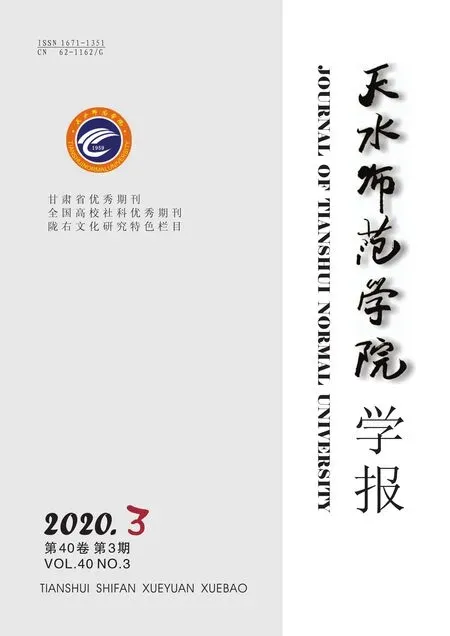“惟忠惟孝,各行其志”
——文天祥、文璧、文璋的人生选择之伦理意义
张小花
(甘肃中医药大学定西校区, 甘肃 定西 743000)
南宋时期的文化思潮和伦理道德观念随着理学思想的兴起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士人对“忠孝”“节义”等价值观的尊崇上。“忠”和“孝”都是儒家士人所推崇和遵守的价值取向,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如何抉择成为许多士人面临的难题。文天祥与他的两位兄弟文璧、文璋在南宋灭亡之际慷慨就义和屈身仕元的不同选择,显现了“为国尽忠”与“为亲尽孝”在宋代士人心目中的伦理价值。
一、文天祥为国尽忠的精神价值
南宋末年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宋蒙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中华文明的进程。蒙古帝国在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拉开了侵宋、灭宋的序幕,直到祥兴元年(1279)崖山海战失败,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随行皇族、忠臣、以及军民近十万人跳海殉国,南宋彻底灭亡。身处灭国战争中的南宋官员,不乏杀身成仁的悲壮义士,也有许多投敌的降臣。而同一个家族内部,兄弟几人因不同的人生选择得到后世截然相反的评价,则寥寥无几。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状元及第后进入仕途。文天祥生活的时代已经是南宋末年,内忧外患,国事飘摇,他为官期间正是元朝灭宋的最后阶段。咸淳八年(1272),襄樊失守后,南宋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之后元军顺长江东下,宋军节节败退。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文天祥应诏起兵勤王,后被任命为丞相。他为朝廷的存亡苦心孤诣,鞠躬尽瘁,兵败被俘后宁死不降,被囚禁元大都四年后慷慨就义,成为中国历史上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
文天祥在被俘北上途中,看到战后国破家亡、民生凋敝的场景,一次次在诗词中表明自己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决心。祥兴元年(1279),文天祥行至广东潮阳,写下了《沁园春·题潮阳张许二公庙》词: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
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留芳。古庙幽沈,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1]1569
文天祥在开篇就指出“为子死孝,为臣死忠”,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儒家伦理道德所提倡的做人根本。这在他的《忠孝提纲序》中也明确提到:“为臣忠,为子孝,出于夫人之内心,有不待学而知,勉而行者。”[2]227可见在文天祥的心目中,子对父孝,臣对君忠,是出于人的天性,而不是后天学习或人为要求的结果。这正是南宋理学思想的主张,认为孝悌、仁爱、忠信都是出自人的本性,是天理在人性中的自然流露,文天祥很明显受到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他后期的诗文中充满了对故国家乡的怀念和从容就义的决心,《正气歌》《乱离歌》《指南录》《集杜诗》都是这种精神和情感的真实写照。
自文天祥被俘之后,为国尽忠已不仅是他个人的人生选择,也成为南宋遗民的集体期待。与文天祥一同被押往元大都的邓剡(1232~1303,字光荐)因病不能北上,被滞留在建康时给文天祥写了《酹江月·驿中言别》词: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惜世间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
那信江海余生,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睨柱吞嬴,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1]1579
邓光荐赞扬文天祥宁死不降的气节,希望他能一直坚持这样的操守。文天祥当即和词一首《酹江月·驿中言别》,并在词中表明心迹:“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1]1578呼应了他在《过零丁洋》诗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825的誓言。
而在期盼文天祥以身殉国的人物中,最著名的当属他的同乡王炎午,在文天祥被俘后写下了流传千古的《生祭文丞相文》。对于这篇文章的写作初衷,王炎午在序言中交代的十分详细:“仆于国恩为已负,于丞相之德则未报,遂作《生祭文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2]513并“眷录十本,自赣至洪,于驿途、水步、山墙、店壁贴之。冀丞相经从一见,虽不自揣量,亦求不负此心耳。”[2]513同时写下生祭文的还有王幼孙,他的《生祭文丞相信国公文》虽不如王炎午的文章流传之广,但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却如出一辙,都是在文天祥尚在人世时写下祭文,期以必死。
呜呼!人皆贪生,公死如归。人为公悲,我为公祈。……公心烈烈,上陋千古。谓山可平,谓天可补。奋身直前,努力撑住。千周万折,千辛万苦。初何所为,以教臣忠,策名委质,视此高风。[3]265
这些同乡好友的态度代表了当时整个南宋遗民的意愿,他们都希望状元宰相文天祥作为公忠殉国的楷模活在后人心中,作为南宋文化精神的象征永垂史册。如果文天祥投降,那不仅是文天祥个人的耻辱,更是南宋朝廷和整个华夏文明的耻辱。因此,当文天祥最终慷慨赴死之后,他成为南宋遗民的精神领袖,其行为被赋予崇高的意义。南宋遗民为其写的祭祀诗文数量可观,他们在诗文中不仅讴歌文天祥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更是从中体会到华夏文明千载不灭的精神内涵。
在文天祥被杀后,南宋遗民中为其作传的就有刘岳申、胡广、邓光荐等人。刘岳申在《文丞相传》中称赞文天祥:“及得死所,卒以光明俊伟,暴之天下后世。迨天以丞相报宋三百年待士之厚,且以昌世教也。”[2]493很明显,刘岳申是把文天祥的死节归因于宋代三百年间厚待士大夫的国策,认为正是这样的时代风气培养了士人忠君体国、爱惜名节的道德观念。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胡广,他在《丞相传》中也认为:
观其从容伏锧,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2]504
当时的士人在评价文天祥时都将他凛然不屈的臣节与宋代文化精神联系在一起,与科举取士的国策联系在一起。文天祥就义的选择已不仅是个人荣誉,而是两宋三百年涵养士人的突出体现。而宋代是华夏文明发展的最高峰,文天祥作为华夏文明精神的代表,在宋亡后成为体现文明优越性的象征。
文天祥的诗文集被其弟文璧带回家乡后,开始在亲友圈中被人抄写、刊刻流传,他的诗文也成为南宋遗民的精神遗产。连文凤在《读文丞相宋瑞诗》中写道:“身后声名满世间,孤魂万里朔风寒。何年得见忠臣传,且把君诗当史看。”[1]1714彭秋宇在《读吟啸集》中也写道:“力支大厦炯孤忠,太息黄旗运不东。天若有情虹贯日,人谁不死气凌空。”[1]1714很显然,很多南宋遗民是将文天祥的诗文视为精神和情感的寄托,并在阅读中获得某种共鸣,或隐或现地表达对故国的怀念,和对华夏文明的自豪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天祥的慷慨就义已经成为南宋文化精神的一个符号象征,代表着当时理学家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
二、文璧、文璋为家尽孝的亲情伦理价值
文天祥在南宋末年为国尽忠的事迹留名青史,而他的两位弟弟文璧、文璋身为惠州守官,却在元军攻城后投降,后又服从元世祖忽必烈,在元朝为官。尽管后来文璋出家为道士,在某种程度上做了南宋遗民。但文璧却终身为元朝效力,安抚战后流民,恢复地方秩序,政绩显著,受到元朝嘉奖。
文天祥的二弟文璧(1238~1298),字宋珍,与文天祥同年进士及第。三弟文璋,生平事迹史料不载。文天祥与两位兄弟感情深厚,对弟弟的人品学问赞赏有加,他曾亲自写信为两位兄弟选择良师益友。在《与李复卿书》中,文天祥称赞文璧:
天资每与义理合,丧本心以求外物,则自保其决无也。惟是闳深博遂之学,汪洋演迤之文,日力方来,正将从事。执事与之处,公余得商略上下,交阐互发,他日此弟其殆非吴下蒙乎,某敢不知自。[2]102
文天祥将文璧比作吕蒙,足见对其期许之厚。在《别弟赴新昌》诗中,文天祥回忆了兄弟二人十几载同学共游的经历,并对弟弟的学业提出了要求,在诗歌的结尾,他写道:“对床小疏隔,恋恋弟兄情。”[2]14兄弟之间的手足深情令人动容。
文璧与文天祥进士及第后,同时供职于南宋末年风雨飘摇的朝廷。文天祥辗转流徙,竭力抗元;文璧扼守惠州,却在元军进攻时开城投降,接受元朝官职。第二年受元朝命令北上都城,顺便看望被囚的兄长。文天祥听闻弟弟的到来,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下了《闻季万至》一诗:
去年别我旋出岭,今年汝来亦至燕。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
可怜骨肉相聚散,人间不满五十年。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4]43075
文天祥在诗中感叹兄弟二人因战争造成的骨肉离散,以及不同的选择造成的命运差异。文氏家族在南宋末年抗元期间遭遇到毁灭性打击,文天祥起兵勤王,辗转各地与元军作战,不仅将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也将整个家族的命运置于危险境地。文天祥的两个儿子先后死于战乱,妻子、女儿被俘,年迈的母亲在饱受流离之苦和孙儿夭折的打击中悲痛离世,两个妹妹劝说各自丈夫跟随文天祥抗元,一家死于战乱,另一家被俘。文氏家族的巨大牺牲突显了文天祥为国尽忠的崇高,但作为儿子、父亲、丈夫、兄长,文天祥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悲痛和愧疚。他先后写下了许多诗篇表达内心的悲痛,如《邳州哭母小祥》《哭母大祥》《哭妻文》,《集杜诗》中有关家人的诗就达二十多首,有《坟墓》《宗族》《妻》《母》《二女》《妻子》《弟》《长子》《次子》《长妹》《次妹》《思故乡》等。这些诗歌不仅充满了文天祥对亲人离世和四散流离的哀痛,也表达了身为人子、人父却无法承担家庭义务的愧疚。这在他的《乱离歌六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仅选取其中一首如下:
有妹有妹家流离,良人去后携诸儿。北风吹沙塞草凄,穷猿惨淡将安归。
去年哭母南海湄,三男一女同嘘欷,惟汝不在割我肌。
汝家零落母不知,母知岂有暝目时。呜呼再歌兮歌孔悲,鹡鴒在原我何为。[2]364
文天祥在诗歌中甚至庆幸母亲不知道妹妹一家的惨剧。更有甚者,母亲在战乱中去世后,他被押解北上,无法办理丧事,这给文天祥的心灵带来极大的煎熬。在古人的心目中,为父母主持丧事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文天祥在《哭母大祥》诗中认为:“人间送死一大事”,[2]364朱熹在《近思录》中甚至说:“凡事死之礼,当厚于奉生者。”[5]107因此,文璧、文璋在战后将母亲灵柩护送回惠州安葬,缓解了文天祥因无法亲自料理母亲丧事的遗憾和愧疚。他在诗的结尾写道:
古来全忠不全孝,世事至此甘滂沱。夫人开国分齐魏,生荣死哀送天地。
悠悠国破与家亡,平生无憾惟此事。二郎已作门户谋,江南葬母麦满舟。
不知何日归兄骨,狐死犹应正首丘。[2]385
从诗中可见,文天祥不仅对两个弟弟安葬母亲之事心存感激,并且也将自己的身后事和延续家族宗嗣的任务交给了两个弟弟。在《与弟诀别书》中,文天祥平静地交代了身后之事,包括选择自己的坟墓、让侄子文升续嗣宗祧、选定墓志铭撰写者等事:
潭卢之西坑有一地,已印元渭阳所献月形下角穴,第浅露非其正,其右山上有穴,可买以藏我。如骨不可归,招魂以封之。升子嗣续,吾死奚憾!女弟一家流落在此,可为悲痛。吾弟同气取之,名正言顺,宜极力出之。自广达建康日,与中甫邓先生居,具知吾心事,吾铭当以属之。若时未可出,则姑藏之将来。文山宜作一寺,我庙于其中。[6]402
文天祥选择为国尽忠,而他写给嗣子文升的《狱中家书》则显示了文天祥对家族的巨大关怀,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文天祥对兄弟行为的态度:
父少保、枢密使、都督、信国公批付男升子:
汝祖革斋先生以诗礼起门户,吾与汝生父及汝叔同产三人。前辈云:“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吾与汝生父俱以科第通显,汝叔亦致簪缨。使家门无虞,骨肉相保,皆奉先人遗体以终于牖下,人生之常也。不幸宋遭阳九,庙社沦亡。吾以备位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汝生父与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
吾二子,长道生,次佛生。佛生失之于乱离,寻闻已矣。道生汝兄也,以病没于惠之郡治,汝所见也。呜呼,痛哉!吾在潮阳闻道生之祸,哭于庭,复哭于庙,即作家书报汝生父,以汝为吾嗣。兄弟之子曰犹子,吾子必汝,义之所出,心之所安,祖宗之所享,鬼神之所依也。及吾陷败,居北营中,汝生父书自惠阳来,曰:“升子宜为嗣,谨奉潮阳之命。”及来广州为死别,复申斯言。传云:“不孝,无后为大。”吾虽孤孑于世,然吾革斋之子,汝革斋之孙,吾得汝为嗣,不为无后矣。吾委身社稷,而复逭不孝之责,赖有此耳。[7]246
文天祥在家书中对文升解释自己和两兄弟的行为:“汝生父与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显示出他对两个弟弟仕元的态度。南宋朝廷已经覆灭,自己殉国是宰相职责,他的母亲、亲生儿子死于战乱,妻子、女儿、妹妹或被囚禁或下落不明。保全宗祀的责任只能寄托在兄弟身上,家族的延续通过侄儿作为他的继承人,将自己的血脉繁衍下去。他在信中交代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已然为国家和社稷付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于己了无遗憾。孝道有亏的痛楚只能通过侄子的过继来弥补,可见为国尽忠的理念和行为并没有抹杀为家尽孝的思想。从以上的分析中可见,“忠”与“孝”在文天祥的心目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三、宋代“忠”“孝”观念的变化
“孝”作为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核心内涵,是建立中国古代家国同构政治制度体系的基础,在本质上与“忠”并无矛盾。“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是历代统治者的共识,汉代“举孝廉”的选官制度就可以充分说明整个社会和国家对“孝”的重视。在古人的心目中,“孝”与“忠”是一体的。宋代以前,大多数人尽管对临难投敌背主的行为表示不齿。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氏族对于家族命运的关心远远超过对皇权和国家的关心,《颜氏家训》正是这一时代风气的产物。宋代之前的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士大夫和武将并不以身仕二主为耻,“五朝宰相”冯道因其渊博的学识,高尚的道德和身处乱世的为官之道颇受士人推崇,甚至得到辽国皇帝耶律德光的敬重。
宋代士大夫对待此事的态度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从立朝之初宋太宗对冯质的评论中已初露端倪,《宋史·冯质传》记载,宋太宗面对宋太祖对冯质的称赞时说道:“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者,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耳。”[8]8796从中可见宋朝的两位开国之君已经表现出对“忠君”这一为臣品质的绝对要求。同时,对冯道的评价由褒到贬的过程也揭示了这一思想的变化。在宋代立国之初,士大夫对冯道基本持褒奖赞赏的态度,但到北宋中期,对冯道的批评已基本成为定论。这其中以欧阳修和司马光为代表,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冯道传》中批评冯道:“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9]611之后又通过称赞断臂守贞的节妇李氏讥讽冯道:“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9]611司马光更是在《资治通鉴》中将冯道贬抑为“奸臣之尤”,认为冯道的政绩和学术成就皆为“小善”,不足为道。[10]9511
不仅如此,欧阳修在修《新五代史·忠义传》时,慨叹所收录的全节之士和死难之臣的数量之少,更加难过的是这些忠臣义士全部出身武夫,没有文臣的影子。他感叹道:“怪士之被儒服者以学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多矣。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9]611欧阳修的这种言论不仅代表了宋代儒家精英人士对武夫的轻视,甚至认为在“全节”“殉国”这件事情上没有文臣的身影,而把这一荣耀让给武将是一种耻辱,更代表了社会思潮的重大变化。从中可见,最迟到北宋中期,精英士大夫对“忠”与“孝”二者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忠君”已然高于“孝亲”之上,成为士人首选的道德价值观。
美国汉学家Richard L.Davis(戴仁柱)比较分析《魏书·忠义传》《唐书·忠义传》《新唐书·忠义传》以及《宋史·忠义传》的选择标准,及所收录人物数量的变化,指出宋代对于“忠义”标准的定义较之前代更加严苛,而被收入的人物却大大增加,“显示出宋代中国的道德结构发生了一次名副其实的革命。”[11]26在“忠”“孝”两种价值观发生矛盾的时候,宋代士大夫已然在内心深处首选尽忠。
这种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唐代灭亡的教训和五代十国的战乱给宋代士人心灵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如何避免唐末五代的悲剧再次重演是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寇准、包拯、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程颐、苏轼、蔡襄等一批砥砺名节的大臣登上政坛,他们强调纲常伦理,强调“父子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理想。经过以他们为代表的精英士大夫的不断努力,逐渐形成了新的士风。这一新的文化趋势促使北宋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改变旧有的道德涣散局面,重新塑造一个充满道德活力的新秩序。”[11]31元代脱脱在《宋史·忠义传》卷首指出:“及宋之亡,忠节相望,斑斑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8]13149也指出了宋代道德教化和理学思想在文人心目中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正因为如此,文璧的行为在亡宋遗民的眼中是为人所不齿的,也是不可原谅的。为国尽忠与为家尽孝是宋代士人所追求的高尚道德,文天祥和他的两位兄弟文璧、文璋在南宋灭亡之际不同的人生选择,显现了“为国尽忠”与“为亲尽孝”在宋代士人心目中的伦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