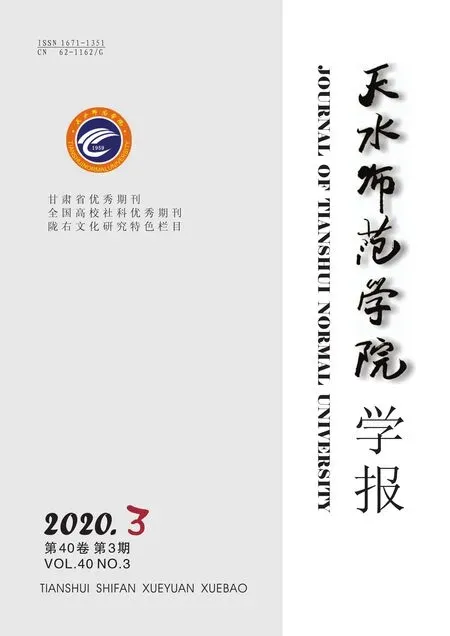乞巧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本体精神
余永红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民间艺术研究中心,甘肃 成县 742500)
七夕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七夕节最重要的民俗活动是“乞巧”。但自从完整的《牛郎织女》故事广泛流传以来,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中,爱情成为了七夕节的主题,许多人则将其称为中国的情人节。新中国成立以来,牛郎和织女更被作为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勇于追求自由爱情的典范而加以歌颂。但只要我们仔细考察七夕节的民俗活动,就会发现我们似乎偏离了七夕节的主题,乞巧才是七夕民俗活动的主体,就是向牵牛、织女祈求灵巧。这里的“巧”不仅仅局限于一般人理解的女红技术层面,也包含男人的耕作技术,后来还衍生出文才、武才智慧等,也就是广义上的巧思和智慧。但总体来看,此智慧是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紧密关联的“劳动智慧”。乞巧活动祈求劳动的智慧,与人类的基本生活息息相关。所以,这种智慧就是生产力。乞巧作为一种节日民俗,在一个国家的广大地区和漫长历史中长盛不衰,这在全世界的民俗史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七夕节的乞巧习俗,代表了中华民族对劳动智慧的不懈追求,这既是七夕节和乞巧文化的基本主题,也是其活态传承的核心价值和本体精神。
一、乞巧文化的发生源于对劳动智慧的崇拜
上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对牵牛织女故事和七夕民俗的研究,大多就事论事,很少有人关注牛女故事产生和形成的源头。赵逵夫先生在其系列研究中,将牛女故事的文化渊源上溯到更深远的历史时期,不仅明确了乞巧风俗源于秦人,而且指出织女应由擅织的秦人始祖“女修”演化而来,牛郎的原型为发明牛耕技术的周人始祖“叔均”。[1]其结论富有启迪意义。这两位始祖的历史功绩主要都不在于繁衍人类,而在于劳动智慧和发明创造,作为中华民族的杰出始祖,他们就是劳动智慧的化身。在史前时期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人类生产生活中的每一项发明创造,哪怕是点滴的进步,都对整个部族的繁衍生息产生重要影响。人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就是“衣食”,所以女修和叔均的劳动智慧和发明创造,其实就代表了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考古资料中发现的大量骨针、骨锥、陶纺轮、石纺轮、骨纺轮、印纹陶等证明,至少在距今7000年前,中华原始先民可能就掌握了纺织技术,为衣服的制作和美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墓葬中,人体骨架上发现有布纹痕迹,说明死者入葬时穿着衣服;另外在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墓葬中亦发现纺织品遗迹。[2]所以,《易·系词下》所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3]并非历史传说,而是史实。原始社会末期,服饰文明已发展到“以五彩彰施于五彩作服”[4]的历史高度。所以,《史记·秦本纪》中“女修织”的记载并非纯粹的神话和空穴来风。可以肯定,女修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女红文化已经形成。“女修织”不仅说明女修是善于织布的秦人始祖,其中也包含了后来“织女”之名。“修”的本义是修饰、装饰。《説文解字》:“修,饰也。从彡,攸声”。[5]远古氏族杰出人物之命名,都与其特长或经历有关。这里“女”为性别,“修”为其名。所以,“女修”之名同时证明,她不仅是一位织布的能手,而且也可能是一位能制作“五彩绣”的刺绣女红高手。
叔均之名中,同样包含了其名字的本质含义。其中“叔”为排行,即表示叔均非嫡长子;或因其非嫡长子的身份而未继承部落首领之位,[6]所以《史记·周本纪》周祖序列中未列叔均之名。“均”是其名,金文写作“”,是形声兼会意字,土为形,匀为声,意谓均匀;《説文解字》:“均,平徧也。从土从匀,匀亦声。”[5]其本体含义应表示使土地高低平整。这里面既包含了周人深厚的农耕传统,也说明叔均本为耕田能手,因此被人们尊为“田祖”。中华民族的农耕历史十分悠久,但这个漫长的农耕历史,基本可以概括为以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技术革命为标志的转折点:其一是从原始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向原始农业的转变,这一转变使人类从此可以自己耕种粮食,改变了人类的饮食结构;转变时间大约发生在距今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7]渭水和西汉水上游距今8000年左右的大地湾一期文化中的旱作农业,已是较为发达的原始农业文化。其二就是农耕技术从原始的刀耕火种方式向牛耕方式的转变,这是古代农业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真正的农耕文明由此形成;这一转变应发生在原始社会末期。其三则是现代机械化农业取代传统牛耕,这一飞跃在中国农村直到今天才逐渐完成。由此看来,牛耕的发明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体现了人类生产劳动的巧思和智慧。
按照《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周人始祖后稷的年代在唐尧虞舜之际,但后面又说“后稷卒,子不窋立。”而不窋末年已至夏末商初了,这期间跨度几百年,是不可能的。《索引》对此也提出疑问,指出“是失其代数也”。[8]按照《山海经》的记载,叔均为后稷之侄或后稷之孙,《大荒西经》云:“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海内经》云:“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9]由此可知,后稷至不窋之间应有数十代周祖,叔均应是早于不窋的周人始祖,其年代应在舜或禹夏之际。由此推断,叔均发明牛耕的时段应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原始社会末期。也许因为叔均发明了牛耕,其名后来演变为“牵牛”,就是牵引牛进行耕作之意,所以“牵牛”之名与牛耕密切相关。[6]虽然中国学术界对牛耕的发明时间尚有较大争议,多认为牛耕出现于春秋时期,但从一些考古资料可知,新石器时代中期已出现了石犁,末期已出现了人力牵拉的犁架,为牛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有学者就指出,从牛的驯养、犁架的形式和畜力用具三方面综合考虑,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代可能已经具备了牛耕的基本条件,商代则有较大可能开始使用牛耕,西周以降牛耕技术逐渐走向成熟。[10]这与叔均发明牛耕的时段并不矛盾,反而证明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极有可能就是牛耕的发明期,但不是推广期。
总之,“牵牛”和“织女”源于“叔均”和“女修”的观点,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早期人类对女修与叔均的崇拜,其实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始祖崇拜,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氏族繁衍之功,更因为他们对氏族生产生活的杰出贡献。女修之名与其对织绣技艺的独特贡献有关,她是那个时代女红文化的杰出代表;叔均之名则与其对农耕技术的发明创造有关,他也是那个时代农耕文化的杰出代表。后来演化为织女和牵牛,则更直接标志着他们在各自领域取得的技术成就。我们今天看传统牛耕显得那样落后,但在距今4000年前,却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巨大发明,不亚于现代的农业机械化。女修时代的织绣水平,不可能像汉唐时期那样成就辉煌,更无法与今天机器化织绣生产效率相提并论,但在原始社会末期,女修的智慧也可能使织绣技术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后来人们为表达对他们永久的崇拜与纪念,才将他们的名字与天上的星宿关联起来,由此产生了“牵牛星”和“织女星”。每当人们仰望星空,就会缅怀他们的历史功绩,对他们的智慧崇拜有加。所以叔均或牵牛、女修或织女,其实就是中华民族勤劳与智慧的象征,他们就是民族的“劳动智慧之神”。人们崇拜他们,其实就是祈求他们赐予劳动的智慧和灵巧。尽管对于女修、织女、巧娘娘以及叔均、牵牛、牛郎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后期研究以及大量证据的进一步确认,但他们的名字中所包含的文化深义是一脉相承的,也进一步证明,几千年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智慧的民族精神是贯穿始终的。
二、历代乞巧风俗的主题就是对劳动智慧的祈求
早期先民对两位劳动智慧之神的崇拜习俗,后来逐渐演变为婚姻爱情故事,这种演变应与周秦文化的融合有关。牛女故事的情节要素在先秦时期已基本具备了,而且在那时就有了男女婚姻的因素,所以秦简《日书》中才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之说。看来牛女故事很早就是婚姻悲剧了,这同样与不同部族之间的通婚关系有关,而造成婚姻悲剧的外部力量就是族群制度的约束力。由于出自不同部族,在形成传说故事的时候,由历史人物演变而来的故事主角也就具有了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史记·天官书》云:“织女,天女孙也。”意即织女是天帝的孙女,而其原型女修亦为帝颛顼之苗裔孙。[11]可见织女的地位高于牵牛,是有文化根源的。故事中的天帝也可能是黑帝颛顼,也可能是白帝少昊,总之他们都是秦人的始祖神。从而也进一步证明牛女传说的形成与秦人有密切关系,乞巧风俗源于秦文化。秦汉以后,随着封建礼法制度的建立和系统化,完整的牛女故事进一步演变为曲折动人的爱情悲剧,七夕节的主题似乎成为祈求婚姻和爱情,牛郎和织女也似乎成为爱神,也无怪乎许多人将其称为情人节。
笔者以为,这是民间传说和文学艺术的想象不断冲淡早期牵牛织女崇拜主题的结果,但无论如何,爱情因素与智慧主题之间并不矛盾,何况七夕节最核心的民俗活动还是乞巧。既然是乞巧活动,那么其主题依然是祈求劳动的智慧与灵巧。我们也不否定乞巧活动中存在女孩子祈求自己婚姻爱情美满之意,但其最核心的含义仍然是对劳动智慧的祈求,这恰恰是对早期劳动智慧之神崇拜的延续。
从有记载以来的乞巧民俗的仪式来看,七夕节乞巧活动的主题依然是祈求劳动智慧,而且乞巧也是男女共同的活动。目前大多数地区的乞巧虽然只是女孩子的活动,崇拜的神灵也只有“巧娘娘”,似乎乞巧就是女孩子向巧娘娘祈求灵巧的专门活动。但早期的乞巧活动,则是男女共同参与的祈求劳动智慧活动。乞巧活动中不仅崇拜织女,也崇拜牵牛;不仅是女孩子向织女祈求女红的灵巧,而且还包括男孩子向牵牛祈求农耕的智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乞巧活动中就用瓜果同时祭祀牵牛和织女。[12]唐代乞巧风俗中依然同时崇拜牵牛织女,据传唐玄宗曾于宫中建“乞巧楼”,陈列瓜果酒炙祭牵牛和织女二星。[13]宋代乞巧依然是男女共同参与,不仅要搭建“乞巧楼”或“乞巧棚”,而且要在上面刻画牵牛织女像进行祭拜;乞巧方式不仅有女郎呈巧,更有男童裁诗;摆设的物品既有女孩子的针线,更有男孩子的笔砚。[14]在这里,男孩子向牛郎祈求的不仅是农耕智慧,还扩展为文思与才华。明清时期依然是家家陈设瓜果、巧果,礼拜牵牛织女双星以乞巧,明代宫中的乞巧中还设兵仗。[15]可见男人乞巧的内容除农耕、文才之外,还增加了武才,人们对智慧的祈求进一步扩展了。男女共同参与的乞巧活动,也正是对早期牵牛织女两位不同劳动领域智慧之神崇拜的继承。
在近现代乞巧中,部分地区依然是男女共同参与。庆阳董志塬一带乞巧风俗中,姑娘们在七夕这一天用“巧芽”照花瓣卜巧,其中白巧芽代表织女,绿巧芽代表牛郎。与此同时,男孩子则把自己装扮成耕牛或者牛郎,在院子里模仿着耕种等农事活动,向牛郎祈求耕田种地的技能,他们相信通过这些活动会使牛郎和织女赐予自己聪明才智。[16]《广州岁时记》记载清末至辛亥革命期间当地的乞巧习俗:“初七日陈设之物,仍然不移动,至夜仍礼神如昨夕,曰拜牛郎。此则童子为主祭,而女子不与焉。”[17]在浙、闽、赣、台地区,也流传七夕拜魁星的风俗,拜魁星者自然也是男孩子。七夕之夜跟织女一道接受祭拜的不是牛郎,而是面目诡异的魁星神。魁星其实就是文曲星,主文章、文运,七月七日也是魁星的生日,尤为读书人所敬仰崇拜。[18]陕西凤翔糜杆桥镇曹家庄村的乞巧节庙会中,男性也参与其中,主要是担任会长进行收布施、请乐队、接待还愿等世俗的事务。[19]虽然没有了男人拜牛郎的习俗,但男性的参与应该还是过去拜牛郎的遗俗。
笔者认为,后期乞巧活动中设笔砚、拜魁星、设兵仗等习俗,是对崇拜牛郎的一种变异和拓展,拜魁星也是由拜牛郎演变而来,是随着封建社会后期男女社会地位的差距和劳动分工的固化所形成的。女人不仅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而且要缠足,身体被摧残,无法从事田间地头的重体力劳动,仅局限于织绣和茶饭。男人从事的劳动则相对广泛,不仅要耕种养家糊口,同时也要读书求取功名,即所谓“耕读传家”,而且在关键时刻还要参与保家卫国的战事。这与西方智慧女神雅典娜形成鲜明对比,雅典娜作为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她主导的智慧不仅在于纺织技术方面,也包括了冶金、驯马、造船等,相当于广义的物质文明智慧之神。[20]总之,虽然后期乞巧的内容有所拓展,但乞巧者、崇拜对象和乞巧时间未变,足以说明其本源精神依然是对牵牛织女劳动智慧的崇拜。
早期的乞巧活动倾向于庆祝牛郎织女的七夕相会,后来受封建礼教影响,才又以女红和乞巧为主题。[21]中国的传统民俗事象,一般都与特定的历史传说或神话传说有关,也可以说是后来的传说不断丰富着民俗的仪式和内容。例如端午节,最早其实与节气密切相关,相传五月为恶月,五日为恶日,此时毒气流行,所以人们用艾草、香料等祛毒怯邪。后来又与屈原、伍子胥、介子推等人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包粽子、赛龙舟、点高山等习俗。乞巧民俗也一样,由早期的人类智慧始祖崇拜,逐渐与牛女传说结合,发生了爱情婚姻内容。但随着封建礼教的深化,这种身份地位悬殊的爱情显然与其精神相违背,所以,乞巧的主题又回归于对劳动智慧的祈求。尽管封建社会强调男女有别,但男女共同参与乞巧活动的习俗却一直延续下来。这种维系力量正来自于中华民族“男耕女织”的社会结构特征以及历代中华儿女对劳动智慧的不懈追求,因为劳动技艺和聪明才智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三、乞巧文化活态传承的精神内核必然是劳动智慧
在全世界都关注非遗保护的今天,留住乡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之一,人们都普遍追忆过去淳朴的生活方式和多彩多姿的民俗,许多传统的民俗活动濒临消失,而大多数则依靠政府的非遗项目保护政策得以维系。一些具有民族文化责任心的专家学者呼吁,力求对传统民俗文化的原生态保护,但最终都无法达到原生态保护的效果。所谓原生态保护,其实也是一个伪命题。既然称为民俗,顾名思义就是民间风俗,就是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风俗和文化,也属于民间的上层建筑,取决于民间的经济基础。而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农村的经济结构、文化生态也发生了巨变,经济基础变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俗文化必然发生巨变。
民俗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活态文化,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只要我们认真考察一些传统民俗事象,就会发现不仅过去与当下不同,而且也存在区域差异。七夕节和乞巧风俗也不例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乞巧的仪式、内容也总是处于动态的演变之中,并体现出地域性差异。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乞巧方式较为单纯,多为穿“七孔针”乞巧;唐代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穿“九孔针”,搭乞巧楼;宋代乞巧不仅有乞巧楼、乞巧棚、巧竿、蜘蛛乞巧等,而且受异域文化影响,还出现了摩睺罗、种生、谷板等;[22]元明清以来在承袭宋代乞巧方式的同时,也有不同的变化。就西汉水上游的乞巧风俗而言,上世纪新中国成立前和70年代末期的乞巧方式主要是姑娘们手拉手唱乞巧歌;80年代,受《天仙配》《牛郎织女》《白蛇传》等戏剧电影的影响,乞巧活动中开始出现了古装戏曲特色的歌舞表演;90年代以后,姑娘们将现代流行歌舞也引入乞巧活动中。而且各个地域的乞巧仪式也各不相同,以西汉水上游和广州珠村乞巧习俗为例,西汉水上游以歌舞、生巧芽、供巧果、照花瓣等为主;而广东则主要为拜七姐、摆巧等。西汉水上游乞巧时间从六月三十日晚至七月七日晚历时七天八夜;广州珠村则从七月六日至八日仅有三天。[23]所谓移风易俗、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等,其实就是指由社会生活主导的民俗文化的演变。所以,“民俗”不只是以往本质主义理解框架中古老的、乃至必须经过几代传承的文化现象,而更多的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具体鲜活的生活文化。[24]因此,不仅民俗学必需朝向当下,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必需直面当下,才是民俗文化活态传承的唯一出路。
对于乞巧文化的当代传承,我们也应抱有包容开放的态度,紧扣其精神内核,适应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潮流,才能完成乞巧文化的活态传承。这种几千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的民间风俗,目前只在西汉水上游一带完整传承的事实足以证明,以“男耕女织”农耕文化为根基的传统乞巧民俗,同样面临现代化转型问题。当代农村妇女很少从事缝衣绣花的针线活,衣服大都是机械生产的现代服饰;已很少有人穿戴绣花的肚兜、绣花鞋、虎头帽等传统服饰;婚嫁习俗也受现代文化影响,不用绣花鞋、绣花枕头等陪嫁品了。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进城打工,很少从事农耕活动;随着旋耕机、收割机等现代化农耕机械的普及,过去用于耕作的牲畜在农村已基本消失,传统的牛耕文化已离我们远去。这些因素对乞巧文化的原生态传承影响巨大,现代化、城市化必将取代传统农耕社会文化,传统的田园牧歌式的慢节奏生活方式将一去不复返。乞巧文化也正处于这种社会变革的巨潮中,其生存必然要直面现代化转型问题。
那么,乞巧文化在当代能否实现活态传承?如能,其活态传承的关键因素又是什么?笔者以为,世界范围内的那些古老文明,唯有中华文明源源不断,传承至今,这正体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所以,乞巧文化能够活态传承,其活态传承的精神内核与核心价值仍在于“劳动智慧”。虽然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变化了,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样要求新的劳动智慧,而且对智慧的要求更高了。尤其是高科技时代的今天,国家之间的竞争,其实就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竞争的关键,就是勤劳与聪明智慧的比拼。当代中国妇女的聪明智慧再也不仅仅限于封建时代的女红方面了,随着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她们已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聪明才智,行政领导、军人、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教师、运动员等各行各业,都有卓越的女性代表。男人从事的劳动再也不限于封建社会的耕读传家,他们从事的劳动领域更加广泛。不论是哪一个劳动领域,不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不仅需要“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勤劳精神,更需要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聪明才智。
对于七夕节这个传统节日,我们也应抱有宽容开放的态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更应凸出和弘扬其核心的精神价值,恢复其蕴含的民族文化的精髓部分。七夕节与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密切相关,其中突破身份地位的局限,追求婚姻爱情自主自由的精神固然值得倡导,但我们更应注重其中以乞巧为载体的对劳动智慧的追求精神。特别是对于年青一代,应深入学习和勇于传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不应只看重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等西方节日,更不应该因为西方有情人节,就将中国的七夕节也当做情人节,这其实是对七夕节的一种片面认识和庸俗化理解。七夕节的核心民俗活动就是乞巧,所以七夕节其实就是乞巧节,是对劳动智慧的不懈追求。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国家富强的劳动智慧,才是其中更为可贵的精神价值。
四、结语
从传说中的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开始,就已经产生了追求智慧的民族精神,开天辟地的盘古、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发明巢居的有巢氏、创造八卦的伏羲、炼石补天的女娲、教民稼穑的神农、造字的仓颉等,可以说都是智慧的象征。后来的五帝,更是富有智慧且任人唯贤的明君和智慧之君,其部族中亦多智慧之才,其聪明才智使中华民族由原始石器时代步入文明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更是由历代先民以其聪明才智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强盛,其智慧精神延续至今。而其中的叔均和女修正是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关键转折点的两个代表性人物,他们在推动“男耕女织”型文明社会形成和农耕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的意义,由其演变而来的牵牛、织女,自然也成为农耕社会的智慧之神,是中华民族“衣食父母”的代名词,受到历代中华民族子孙的敬仰和崇拜。
乞巧文化的初始阶段其实就是人类对智慧始祖的崇拜,虽然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乞巧,还没有乞巧的具体仪式,但其崇拜智慧之神的精神其实就是一种乞巧行为。民俗化的乞巧文化,虽然伴随着后来形成的婚姻爱情因素,但也掩盖不了中华儿女祈求劳动智慧的本体意义。新时代的乞巧文化,也必将以中华民族对劳动智慧的不懈追求为精神纽带,才能使乞巧文化的精神永久传承,使其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发扬勤劳智慧的优秀民族文化,成为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