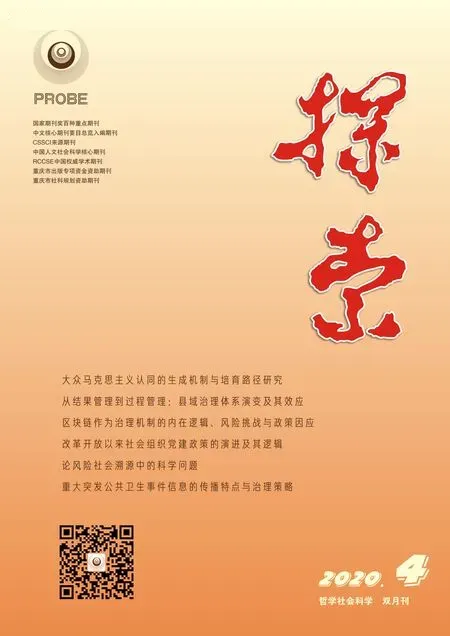新帝国主义的危机与新社会主义的使命
——兼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与应对
宋朝龙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二战之后旧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趋于解体,但金融资本在主权国家体系的基础上借助经济全球化、军事霸权、新自由主义和国际制度安排等建立了新帝国主义。在新帝国主义的庇护下,金融资本推动了世界市场和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但另一方面,金融资本也建立起以定价权、地产投机、证券投机、国债投机等为核心机制的寄生性积累机制,不仅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何深刻认识新帝国主义及其产生的重大消极影响,把人类社会从新帝国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更符合人类福利和自由的基础上推动全球化,这是新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
1 金融资本的新帝国主义及其本质
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是金融资本[1]347-433,而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有旧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两种形式。在旧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暴力不仅保护金融资本的国际积累条件,而且直接去建立超经济的剥削体系;在新帝国主义体系中,暴力转化为世界警察权,在形式上平等的主权国家体系中保护着金融资本的国际积累秩序。早在20世纪初,列宁就指出旧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下所蕴含的新帝国主义萌芽形式,即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的依附形式,各种形式的附属国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2]398。列宁的论述实际上涉及金融资本的新帝国主义形式,正是这种形式在二战之后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在新帝国主义的秩序下,金融资本积累得到了庇护,金融资本积累的规律及其内在矛盾也得到了充分的呈现。
1.1 新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建立的新型帝国主义
自希法亭[1]347-433和列宁[2]323-439以来,金融资本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帝国主义经济基础的核心概念。金融资本是在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垄断融合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大货币垄断资本,是统摄各职能资本的总资本。为了服务于自身积累,金融资本先后建立了殖民帝国和后殖民时代的新帝国。殖民帝国主义是在暴力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新帝国主义则是在主权国家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旧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与军事、官僚力量相结合,将世界市场分割为各帝国的不同势力范围。随着旧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取得了民族自决权,但大多数宗主国的金融资本基础被保存了下来。同时,二战后金融资本在生产全球化和主权国家体系的基础上,通过金融遏制、世界警察权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建立起了新形式的帝国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金融资本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即后来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推动下,强化了新帝国主义的统治。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使金融资本积累获得了更广泛的积累空间和更自由的行动条件。
1.2 新帝国主义为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开辟了空间
新帝国主义通过一系列全球合作机制的建立,例如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积极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和经济合作,为金融资本的全球投资保驾护航。金融资本作为一种不断自我实现的主体力量,使生产、流通全面加速,使世界市场不断深化、扩张,使人类对大自然的支配不断深化。金融资本支配着产业链、商业链、信用链;就像一切主体都试图通过变革手段来实现目的一样,金融资本也通过产业革命、商业革命和信用技术革命来积累。二战后,金融资本推动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推动了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一系列深度的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通过产业革命、商业革命和信用技术革命来积累,这是金融资本推动社会进步的方面,是金融资本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推动人类进步的表现,这可以看作是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
1.3 新帝国主义放纵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
阿锐基把资本积累分为实物扩张和金融扩张两个方面[3]1-4,有助于我们理解金融资本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的区分。新帝国主义为金融资本积累保驾护航,既推动了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也放纵了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金融资本通过生产革命、流通革命来进行的积累,是生产性积累,但金融资本积累还有另外一面,即寄生性、投机性、剥夺性积累的一面。金融资本借助各种形式的经营垄断,借助定价权而直接剥夺消费者。金融资本通过股票、证券投机,通过各种金融创新从中小投资者中圈钱。正如马克思所说,财产以股票形式的运动和转移“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并且也取代了直接的暴力”[4]541。金融资本控制着石油、矿山、地产等,凭借不动产的经营垄断和所有权垄断,以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形式从消费者征收货币税。金融资本经营国债,把税收、公共财政、公共工程等变成自己的积累对象,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成为金融资本的债务人。金融资本还支配货币发行权和国家的货币政策。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在金融资本的绑架下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印发货币来稳定金融秩序,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使工薪阶层遭受剥夺。因此,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所造成的种种消极影响阻碍着经济社会进步。
1.4 新帝国主义放大了金融资本积累的结构性危机
金融资本积累包含着自我否定的悖论逻辑,也即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时,金融资本试图通过刺激非生产性的积累手段,结果非但解决不了危机,反而带来新的危机。金融资本试图通过信用消费来扩大资本积累条件的努力,最终造成了大面积的社会负债。金融资本以刺激金融地产来缓解危机,结果导致地租提高,工薪阶层生活成本以及制造业成本增加,使产业竞争优势丧失。在新自由主义的制度下,货币发行权也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联合的大金融资本家。为了救助金融资本自身造成的金融危机,金融资本就印发更多的货币借给国家,国家为了救助金融机构,结果使自身背上了更沉重的债务负担。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缓解或解决危机,不可避免地造成通货膨胀,使本已贫困化的工薪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金融资本解决危机的办法反而使危机叠加起来,造成更大的危机。这就是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新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是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而新自由主义认为“最小的”国家就是最好的国家,自由放任的政策就是最好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使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放纵地发展起来,使危机暂时隐蔽起来,但解决危机的手段带来了更大的危机,使金融资本自我否定的逻辑加速表现出来。
1.5 新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积累危机加剧了对外扩张
在新帝国主义的庇护下,金融资本支配了产业链、商业连和信用链,支配了地产、银行和国债,支配了国家政策、世界市场和国际关系,支配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由于新帝国主义放纵了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由此所造成的一系列危机又进一步放纵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在这个恶性循环下金融资本的寄生性、投机性越来越强,而国家因救助金融危机变得越来越虚弱,国家在解决国内危机方面所拥有的手段越来越少,这就推动着金融资本联合国家力量到国际关系中去冒险,试图通过对外转嫁矛盾来解决国内矛盾。列宁曾分析过因为发达国家内部矛盾尖锐而对外加剧帝国主义扩张的趋势[2]391-392。列宁揭示的这种逻辑,在美国金融危机以后的西方政治局势变迁中再一次表现出来。2008年金融危机没有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那样很快过去,而是顺次蔓延、逐步展开、逐步深化,表现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国际关系危机的顺次转移和叠加。在各种局部性的缓解政策都用尽的条件下,西方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开始崛起,掀起逆全球化的潮流。这是新帝国主义在危机面前日益趋于对外冒险的表现。
2 新帝国主义在体系性危机时代的政策逆动
新帝国主义庇护了金融资本的全球积累,而金融资本的全球积累又造成了结构性的危机,使新帝国主义从全球化的推动者转变为逆全球化的急先锋。正如福斯特所言:处于衰落时期的帝国主义恰恰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岌岌可危的帝国主义恰恰是在为全球灾难开辟道路[5]。在新帝国主义的危机面前,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正走上西方的政治舞台,新自由主义也正向右翼民粹主义转化。右翼民粹主义是新帝国主义危机时代冒险政策的集中体现,其政治势力的崛起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政治气候,启动了反全球化的议程。如果任由其发展,那么右翼民粹主义会将把全球化带入以邻为壑的囚徒困境之中。
2.1 右翼民粹主义使新帝国主义从贸易自由转向贸易战
二战之后在美欧主导之下建构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为金融资本的全球积累创造了条件。金融资本的全球积累是一把双刃剑,它推动了全球生产和流通的革命,也给后发国家带来了连绵不断的危机。2008年以前的危机,或者是局部性的危机,或者是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例如在拉美、东南亚、俄罗斯等地方爆发的。2008年的危机转移到国际金融资本的核心地带,转到曾经发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核心国家。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带头推行新自由主义,推行全球化,推行贸易自由,但是现在美英两国领导人带头反对全球化,反对自由贸易。英国首相约翰逊继续推动脱欧运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从多个国际组织退出,带头反对全球自由贸易秩序。这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转折点。特朗普总统在国内继续推行对金融垄断资本有利的政策,例如减税、减少对金融资本的管制等,而在国际上通过挤压其他国家市场、通过贸易战的方式来为美国金融资本争夺积累空间[6]。
2.2 右翼民粹主义使新帝国主义更赤裸裸地抵制社会民主政策
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寄生性、剥夺性积累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新自由主义曾经许诺的橄榄型社会再度变成金字塔型的社会。丹尼尔·塞瑞拉教授对此指出:资本主义的矛盾之处在于,财富越多,贫穷也越来越多,由此造成了社会危机(1)引自丹尼尔·塞瑞拉教授在2019年10月12—13日于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面对工薪阶层的贫困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金融资本并没有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法,而是导向了右翼民粹主义倾向。特朗普总统反对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反对增加工人最低工资,主张减少国家的福利支出。塞耶斯教授也指出:英国约翰逊政府所力推的脱欧运动无助于解决工人的权益问题。英国脱欧一个隐秘的目的可能是摆脱欧洲大陆对工人比较有利的社会民主政策。欧洲大陆在劳动时间、劳动待遇方面的规定,要比英国进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推动脱欧运动,也是试图通过恢复自由放任,打压工会,解除对工人权益的保障,试图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来推动资本积累(2)这是笔者2019年8月20日在英国坎特伯雷大学对塞耶斯教授的访谈。。
2.3 右翼民粹主义使新帝国主义加紧蛊惑民众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已无助于西方国家克服内在危机,反而加剧了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7]。面对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失业、贫困、债务,没有人关心他们,民众处于焦虑之中。中产阶级面对债务压力、失业压力时,在移民、种族等问题上不再像资本主义顺利发展时期那么宽容,这是一种自发反应,是民众对社会矛盾和生活压力的本能的、直觉的、直观的、情绪性的反应。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利用人们的这种本能反应,把民众陷于困境的原因归咎于其他国家、其他族群,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对金融资本的批判中转移开来,在金融资本的积累机制之外去找原因,寻求替罪羊,向外输出矛盾。而西方左翼政党对民众运动缺乏有力领导和正确引导,也是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能够蛊惑民众的一个重要条件。左翼政党衰落,对民众运动的领导乏力,致使其民众运动没有统一的纲领、规划,而表现为一种凭靠热情的、短暂的、无序的、自我冲突的运动形式,这是民众运动受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支配的重要原因。
2.4 右翼民粹主义使新帝国主义抛弃“温情的”意识形态面纱
右翼民粹主义为了寻求其他国家作为替罪羊,不得不强化国内国民身份认同,来掩盖国内的阶级分化,来凸显本国国民身份和他国的对立。右翼民粹主义在金融资本已经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之下来讨论问题,认为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是自然的、不容置疑的前提,认为金融资本做大了,工薪阶层才能有好的经济处境,而实际上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及其对社会的剥夺,才是工薪阶层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右翼民粹主义为了强调金融资本和工人之间的绝对统一性,就在国民身份认同的意识形态下把金融资本和工人阶级的对立调和了起来。为了强调国民身份的统一性,右翼民粹主义又把本国国民和其他族群、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对立提到首位。而为了达到制造本国国民和他国国民或其他族群对立的目的,右翼民粹主义就夸大一些矛盾,把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炒作移民问题,把移民看成是导致西方经济社会危机的原因。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社会危机的真实原因。在右翼民粹主义的鼓噪下,个别国家将国内危机转嫁为国际危机,严重危害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直接抛弃了西方长期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价值观的“温情的”意识形态面纱。
2.5 右翼民粹主义使新帝国主义走向以邻为壑的囚徒困境
新帝国主义以右翼民粹主义的面目出现,以转嫁危机的办法来解决危机,这是不可能解决危机的,而只是使危机在新的形式上发展,在新的范围内扩散,在新的程度上加剧。麦克莱伦教授指出:英国的脱欧运动耗尽了英国的政治能量,政治分裂日益明显,使各种实际的问题不能得到应有的讨论和解决(3)这是笔者于2019年8月19日在英国坎特伯雷大学对麦克莱伦教授的访谈。。美国的政策困境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以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的方式解决危机,不可能不遇到其他国家的抵挡。现在,右翼民粹主义不仅在美国和英国,而且在德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法国、西班牙都能找到它的身影。如果各国都寻求替罪羊,那么这种替罪羊的角色最终会落到自己身上,对别人的惩罚会转变为对自身的惩罚。如果各国的出发点都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损失最小化,而实际上导致了各自利益的最小化、损失的最大化,最终的结果是使世界市场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失序。这就是右翼民粹主义所导致的新帝国主义以邻为壑的囚徒困境。
3 新社会主义扬弃新帝国主义的探索和使命
在新帝国主义的上升时期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西方提供了人类社会的终极秩序。但是,新帝国主义秩序下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所造成的一系列危机,是不可能在新帝国主义自身的基础上加以解决的。因此,批判、反思和替代新帝国主义道路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新社会主义是与新帝国主义相对应的,是从新帝国主义的时代条件中引申出来的。英美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欧洲大陆的民主社会主义、拉美的21世纪社会主义、苏东地区对社会主义的再探索,以及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社会主义,这些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起,形成全球新社会主义的图景。我们不妨把新社会主义界定为“与新帝国主义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新社会主义运动的各个支系有不同的起源,活动于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秉持着互有差异的理念,但是在批判和替代新帝国主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3.1 欧美世界的市场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西方的问题是如何限制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都无法解决西方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危机,凯恩斯主义也因国家已经高度负债而无法复归。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欧美世界又成为重要的议题。20多年以前,在英美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曾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麦克莱伦教授认为:为了公共利益而以强有力的方式控制和调节市场,这就是市场社会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既然没有直接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那么市场社会主义可以作为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起点和过渡。在美国民主党内部,伯尼·桑德斯已经公开举起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参与新一届的总统大选,这在美国这样一个新自由主义国家是重要的政治突破。美国民主党另一位总统参选人伊丽莎白·沃伦也保证将在政策方向上以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来应对美国的问题。在英国,杰里米·科尔宾当选为工党领导人之后,使工党进一步摆脱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把工党向左翼方向引领。固然,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曾经和改良主义相联系,但是金融帝国主义核心地带的结构性矛盾使改良主义难以达到目标,这也会催逼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向新的方向去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
3.2 拉美国家的21世纪社会主义
拉丁美洲曾是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结果,因此拉丁美洲也成为反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产生过一些重要的有世界影响的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领导人。在左翼政府的领导下,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开始改进收入分配,减少社会不平等,减少饥饿、贫困和社会排斥等问题。拉美的21世纪社会主义曾以委内瑞拉为代表出现了左翼群体性崛起的高潮,一直延续到2015年。此后,拉美左翼运动遭遇了挫折。过去两年,委内瑞拉也是举步维艰。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发生了左翼政权被右翼替代的变化。但是,拉丁美洲国家目前右翼政权也难以稳定住局势,为国家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拉美左翼的再度复兴也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在拉美社会主义运动中,古巴共产党领导的古巴革命和古巴社会主义建设,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主义探索的经验[8]。
3.3 俄罗斯东欧地带的社会主义再探索
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一直在对社会主义进行反思和再探索。俄共旗下有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组织,有广泛的分支机构。在当今俄罗斯,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等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讨论主题。这些思潮结合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反思,结合着当今俄罗斯社会阶级分化和社会不公的现实,使社会主义的研究呈现出了新的活力[9]。在中东欧国家,自1989年以来“在30年的发展过程中,左翼政党经历了组织危机、制度适应、左右轮换与总体低迷的阶段,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与政策主张”[10]。除这些地区之外,非洲、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具有社会主义取向的政党,例如摩洛哥社会民主党、纳赛尔民主党、印度共产党等都结合着自身的历史特点,一直在社会主义方向上进行着探索。
3.4 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探索
在新社会主义各种探索中最特殊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之外的各种新社会主义探索的影响目前都还比较有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实现形式,开辟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也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率先探索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表明,在落后国家率先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不能与世界市场隔绝,而要在与内外资本主义的并存和竞争中通过自身的经济建设来吸收世界体系中已经取得的生产力成果以巩固自身的经济基础。如何利用内外资本主义、把内外资本主义的必要经济成分结合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当中来,这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探索的重要的基本内容。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再到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经过曲折的过程探索到了公有制主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既能克服金融资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又能充分利用一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的积极职能,成为新帝国主义逆全球化时期继续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制度引擎。
3.5 新社会主义扬弃新帝国主义的世界历史使命
当代西方的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的局部性危机,而是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所导致的结构性危机。大卫·科兹教授指出:当下的世界资本主义,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停滞不前的时期,当时资本主义的停滞导致了三个方向的变化:走向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的渐进式改革、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转变(4)引自大卫·科兹教授在2019年10月12—13日于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右翼民粹主义不但解决不了危机,反而还会强化危机。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可能也难以挡住这个浪潮,世界历史陷入新的危险时期。在这样的时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金融资本的积累危机,才能克服新帝国主义的冒险政策。规训金融资本,以公有制主导的市场经济取代金融寡头所主导的市场经济,扬弃金融资本的新帝国主义,克服新帝国主义逆全球化的囚徒困境,在更符合人类福利和自由的基础上推动全球化,这是新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4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与应对
推动新社会主义对新帝国主义的替代,克服右翼民粹主义的逆流,在更符合人类福利和自由的基础上推动全球化,这是新社会主义的使命,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核心问题。为推动新社会主义对新帝国主义的替代,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应对如下一系列相关联的问题。
4.1 需要批判新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
新帝国主义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其意识形态外衣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就需要对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前提、逻辑结构、制度安排、政策体系及其与金融资本积累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全面的说明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私有产权、契约自由、“最小国家”、三权分立等观念,是适应金融资本的积累秩序和金融资本的统治的。新自由主义认为契约自由就是自由的实现,但实际上契约自由背后是金融资本的实际统治,金融资本的统治正是在遵循契约自由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契约自由这一形式上的自由,不能阻止当代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阻止不了货币、资本、金融资本、金融帝国的权力扩张。新自由主义演绎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神话,但在现实中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造成了中产阶级的衰落。在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理念中,只允许“最小国家”“极小国家”的存在,而被这样设计的公共权力实际上是无力解决资本积累所造成的经济社会问题的。不仅如此,国家还只能按照金融资本的要求和在金融资本所规定的政策逻辑下应对金融资本的积累危机,也即只能通过货币扩张、减税、削减福利等政策来解决危机,而这种解决危机的办法,不但解决不了危机反而使危机向纵深发展了。新自由主义所描述的形式自由,并非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形式。因此,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批判。
4.2 需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左翼政党结合以引领民众运动
西方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表明民众已经被激动起来、被发动起来了,但是民粹主义也表明民众运动还处在自发的阶段,表明运动还受右翼政治势力的支配,表明左翼政治和左翼政党还不够壮大、不够坚强、不够有力。右翼民粹主义盛行正是因为左翼运动的乏力。在资本主义的矛盾深入发展的条件之下,民众被右翼势力所利用、所蛊惑,民众运动被引向破坏性极强的方向,这也是历史发展中一个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正是在这样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必要性才更加凸显。马克思主义要通过自己的纲领、策略、组织工作,通过自己耐心的说服和组织工作,把群众从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蛊惑之下解放出来,使之变成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与右翼政治势力争夺民众,这正是历史上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为应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人员准备、组织准备、纲领准备和策略准备。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不够坚强,不能吸引民众,不能把民众组织起来,那么民众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就是必然的。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和左翼力量要虚弱得多,这是造成目前右翼民粹主义逆流的重要原因。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要应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要通过这一挑战而走向现实、走向实践、走向历史的潮头。
4.3 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逻辑中说明金融资本的规律
新帝国主义的危机、新帝国主义逆全球化的囚徒困境,不是由金融资本之外的其他偶然因素,例如,不是由监管不力、监管不严、经济伦理遭受违背等因素导致的,而是由金融资本的本质自身导致的,是由金融资本在生产性积累的基础上必然会发展起非生产性积累、非生产性积累必然日益膨胀、虚弱的国家救助金融寡头必然会加剧社会矛盾等一系列内在必然性所导致的。为了分析新帝国主义的危机,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上对金融资本的积累规律及其内在矛盾作出科学的说明。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和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有了很多变化,但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我们分析当代的金融资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希法亭和列宁在此基础上说明了金融资本的形成逻辑。金融资本支配着整个社会再生产,或者至少是支配着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核心环节,支配着价值运动中增值能力最强的环节。势力极大的金融资本内部,发生了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离,金融家转变为在社会生产过程之外支配着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寄生者,而各级管理职能则交给各级雇员来执行。在金融资本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化大生产扬弃寡头私有制的必要性和条件。
4.4 需要加强对新帝国主义的制度替代道路的研究
金融资本的新帝国主义如何进行制度替代,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面对的一个硬核问题。二战后随着金融资本新帝国主义的发展,随着全球化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获得了新一轮的扩张。在金融资本的上升时期,新自由主义曾一度风靡全球,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观念也曾一度流行。但即便是在金融资本积累的上升时期,世界上不同地带的社会主义也在艰难地探索着对新帝国主义的替代道路。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表明,公有制主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替代金融帝国主义道路的现实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另外一方面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垄断性的生产资料,对大的战略产业,对土地、石油、矿山、银行等,实行社会联合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是其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具体形式),而非实行私人寡头所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能克服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投机性、剥夺性积累,又能利用一般中小资本的生产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种制度能力,使社会主义能够成为取代金融寡头制度、继续推动人类发展的现实道路。
4.5 需要加强与全球化顶层设计的结合以克服新帝国主义逆全球化的趋势
全球化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合作。解决贫困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移民难民问题等,都需要全球性的合作,需要全球性的方案。但是金融帝国主义的核心国家只是想利用全球化,一旦全球化对自身不利则又想着向全球化输出矛盾。右翼民粹主义主导了金融帝国主义核心地带的政局,这加剧全球紧张局势,把全球化引向新帝国主义的囚徒困境之中。那么,社会主义有没有能力引领全球化?回答是肯定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从世界历史的运动中产生的。社会主义曾推动了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引领了民族解放运动,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格局。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同样能够适应、参与、推动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推动全球化的继续深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与方案。
5 结语
金融资本是帝国主义的灵魂和支柱。二战之前,金融资本建立了殖民主义的旧帝国主义;二战之后尤其是旧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解体以来,金融资本在主权国家体系的基础上,借助金融遏制、世界警察的军事霸权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建立起了新帝国主义。在新帝国主义的庇护之下,金融资本获得了自由的发展。金融资本的积累中包含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的双重逻辑,建立起一套投机性、寄生性、剥夺性的积累机制。这就使得金融资本积累包含着深刻的悖论逻辑:金融资本解决由其制造的危机的方法却造成了更深刻、更长远、更系统的危机。在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支配下,新帝国主义核心国家的金融资本越来越向非生产性积累偏移,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导致右翼民粹主义崛起,右翼民粹主义又引发全球化逆转和世界陷入以邻为壑的囚徒困境。新帝国主义的危机为新社会主义提出了挑战,反思、批判和替代新帝国主义的新社会主义运动也由此在世界各地得到了新的推动,形成了全球新社会主义的新图景。
走出新帝国主义的逆全球化的囚徒困境,在更符合人类福利和自由的基础上推动全球化,这是新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解答新社会主义运动所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批判新帝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左翼政党的结合从而把民众运动从右翼民粹主义中解放出来,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明金融资本积累和新帝国主义自我否定的运动规律,探索取代金融资本和新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形式,为全球化新阶段提供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顶层设计理念和方案,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应对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与发展。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以金融资本的殖民帝国主义和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基础来观察时代和时代变迁。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与旧帝国主义转化为新帝国主义,以金融资本的新帝国主义和多种形式的新社会主义为基础来观察时代本质和时代变迁,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说明资本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背后金融资本奠定的经济基础,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说明金融资本自我否定的历史必然性,在社会主义实践逻辑的基础上探索取代金融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同样需要在21世纪获得长足发展,以便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出现的新变化作出科学的合理的解释。正如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经验所揭示的那样,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将在对时代问题的解答中、在对其他各社会思潮的借鉴和相互博弈中获得日益明确的自我意识和实践能力,从而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局的背景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具有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引力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