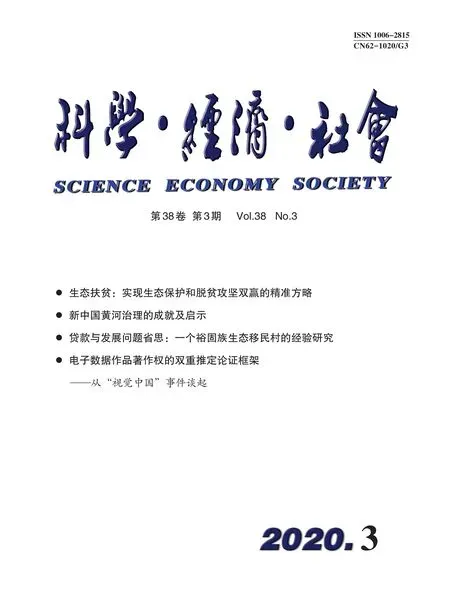基于想象力图型结构的“虚幻共同体”批判
徐 娜
(浙江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3)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实质是绝对观念的想象(imaginäre)活动,并进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指认为虚幻的共同体(illusorische Gemeinschaft)。但马克思也指出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使普鲁士德国在思想中达到了欧洲现代各政治国家的水平,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是欧洲现代国家之思想的完成。因此,对作为现代政治之完成形态的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就成为理解马克思批判现代欧洲政治的关键,而对这一批判的深入探究需要着力去思考马克思所指认的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实质——“想象性”或“虚幻性”的涵义。
当然,在西方近代哲学的传统范围内,想象性本身就带有虚幻性,想象活动本身所具有的纯粹主观臆想性,使其无法在心灵与物之连接中建构起真正、可靠而科学的实在性关系。然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却一反西方近代哲学的传统,给予想象力以极高的地位,想象力导向先验图型(Schema)作为桥梁(19)在《纯粹理性批判》两个版本中,康德对想象力的地位给予了不同的表述。在第一版中,想象力是与感性力、知性力并列的一种先验能力,在第二版中,想象力从属于先验知性能力。但不论在哪一个版本中,想象力都不是经验的,而是一种先验能力,并承担桥梁连接的作用。以联接感性直观与知性范畴。同样,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中,想象力属于理论精神中的表象阶段,并通过思维向实践精神过渡。可见,经过康德和黑格尔的论述,想象力(Einbildungskraft/facultas imaginandi)已经不再是人的一种简单的主观性经验心理活动,而是具有了更深层的、更复杂的内涵。因此,深入阐述马克思所指出的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想象性实质,就必须重视康德和黑格尔对想象力的重新思考。对马克思所批判的黑格尔虚幻共同体的理解若不深入到这一领域,就容易使这一批判又回到康德、黑格尔之前的哲学传统。如此,既无法透析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实质,也无法抓住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国家哲学之为虚幻性的命脉,更无法切中现代欧洲政治症结之所在。
一、康德对想象力的先验拯救与实践退缩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时,有一个著名的类比:“正像古代各民族是在想象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1]205这个类比表明——未来之于普鲁士德国与过去之于古代民族有着某种相似性,其历史都表现为同样的非现实性,一个依据想象中的神话考察自己的过去,一个依据思想中的哲学考察自己的未来。如果历史的非现实性在作为想象的神话和作为思想的哲学中有着同样的经历,那么历史现实性的回复是否意味着同样的路径,即对作为想象的神话的扬弃是否能够同时扬弃作为思想的哲学?或者说,当黑格尔哲学成为德国哲学最全面、最彻底的表述之后,对其国家哲学的想象性和虚幻性的批判能否通过对神话的想象性的批判而得以完成?
启蒙运动以理性祛魅了神话,以哲学驱逐了幻想。通过启蒙理性的祛魅,神话想象不仅在哲学中失去了地位,也在社会中失去了作用。通过启蒙哲学的教化,理性战胜了想象力,神话想象被认为是人类理智的不成熟状态,而理智的成熟运用就意味着要摆脱想象力的统治。然而,与传统启蒙哲学对想象力的完全排斥不同,康德的启蒙哲学不认同启蒙运动对想象力的一味否定。康德认为摆脱想象力的统治并不等于丢弃想象力,而是要限制想象力,是要将想象力置于一定的规则之下,这一规则就是理性。必须用理性来规范和约束想象力,才能确保想象力成为适宜的人类认识能力。如若想象力脱离任何规则,“毫无规则地乱冲乱撞和东游西荡”,就“不会是典范性的”[2]219。无规则的想象力是鲁莽的,非典范的想象力是愚昧的,它容易使一个民族陷于任性的自由。神话想象就是这样一种任性的自由,它游荡于理性规则的约束之外,“这些想象是粗野的、怪诞的和奇异的”,“对于未开化的人来说”,“能够对他的自然生活和内在生活提供一种解释”[3] 56。然而,这种解释对于已开化的人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来说,却是一种狂热的、致命的危险。狂欢的宗教祭祀、神秘的巫术仪式仅仅给一个民族提供了狂乱的、想象的、任意的预告或预示,而这种预告或预示不具有任何示范性、典范性或规范性。“对这种命运作出预报的一切预示”,不仅“对它来说毫无用处”,而且“自身就有荒唐之处,亦即在这种无条件的厄运(decretum absolutum[绝对的裁定])中去设想某种自由机制”[2]181。神话预言将巫师想象力预感中的主观的、任性的自由确认为绝对的裁定或判定,这使其陷于自相矛盾之中,并因而是未开化的和愚昧的。人类的开化状态和明智状态就是通过启蒙推翻神话想象,将主观、任性的想象置于理性规则的约束之下。
康德用理性限制了想象力,也拯救了想象力,想象力的理性运用避免了想象力的主观运用。虽然想象力确实不需要对象在场就可以主观地想象某种东西,但是在康德看来,想象力必须一方面“是根据范畴的”[4]114,另一方面“必须从感官那里汲取自己创作的素材。”[2]161于前者而言,它避免了想象力成为一种盲目的构想;于后者而言,它避免了想象力成为一种随兴的臆想。想象力必须依于范畴规则,确保了想象力是合规则的,想象力必须汲取感性素材,确保了想象力是合自然的。由此,康德将想象力从传统哲学中拯救了出来,它不再是一种无限制的、无规则的(由此想象力易成为愚昧的)以及任性的、随意的(由此想象力易成为狂乱的)心灵能力,而是一种脱离了愚昧和狂乱的,人类可以信任和依靠的心灵能力。
康德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要将想象力从传统哲学中拯救出来的原因,在于其所面临的形而上学难题,即感性的综合直观与范畴的先验统觉由于二者的不同质,如何能够统一起来。康德对此难题的解决之道就是借助于想象力的先验综合。想象力一方面是感性的,可以对知性范畴提供直观,另一方面是根据范畴的,可以按照先天形式规定感官。凭借想象力的先验综合,“我们把直观的杂多一方与纯粹统觉的必然统一性的条件另一方结合起来。两个终端,亦即感性和知性,必须借助想象力的这种先验功能而必然地相互联系”[5]85。可见,与传统哲学对想象力的贬低和排斥不同,康德通过限制想象力提高了想象力的地位,并赋予了想象力以极其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想象力作为一种纯粹的、先天的(20)康德并不否认想象力的经验性应用,但他认为想象力的先验性应用更为根本且更为重要。“感官、想象力和统觉;它们的每一种都可以被视为经验性的……但它们也都是本身使这些经验性的应用成为可能的先天要素或者基础。”参见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80.人的能力的强调,并借由想象力的先验综合,康德企图为人类知识提供确实而可靠的基础,来避免独断论者对知识的专断以及怀疑论者对知识的拆台。然而在实践理性领域,康德却又转而限制了想象力。他认为想象力既使作为一种先验的能力,也不能进入为实践理性确立纯粹法则的领域,“德性法则除了知性(而不是想象力)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居间促成其在自然对象上的应用的认识能力了”[6]94。想象力在先验知识论中的居间或桥梁作用,在德性法则的确立中不再适用,甚至康德格外强调要杜绝想象力进入这一领域。这一杜绝的目的在于,康德一方面要驳斥怀疑论所认为的德性法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主观幻想,另一方面要防止神秘主义借由想象力将德性法则过度应用到超感性领域(即彼岸的上帝之国)。
想象力不仅在纯粹的德性法则中被杜绝,亦在道德的经验性部分—实用人类学中被抑制。想象力在纯粹知性领域可以保障人类知识的共同性,但是在实践理性领域却妨碍了人类道德法则的公共性和实践活动的共通性。想象力的过度发挥和无原则运用所导致的“精神错乱的唯一普遍标志就是丧失共通感(sensus communis)”[2]212,停留在自己的世界里。因此,当人们在实践方面采取行动时,应极力避免个人由于过度的想象力而沉溺于自己的法则,无法适应别人的法则,无法与他人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里。公共生活应该极力避免想象力,如果“一个政治的艺术家……用想象来领导和治理世界”,他只是“懂得把这些想象冒充成现实,例如人民的自由,这种自由(如在英国国会中)或者等级和平等的自由(如在法国国会中)仅仅存在于形式中(mundus vult decipi世界愿意被欺骗)”[2]174。英国国会和法国国会表现出来的自由并不是康德心中理想的自由模型。国会中的自由只是政治家进行政治艺术表演的舞台,只是把政治家想象中的自由形式化为一种议会制度,而非理性的人们却愿意在这样一种形式化的想象的自由中被欺骗。
在康德看来,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真正自由,必须依据纯粹法则所建立起的自由的概念,并作为纯然的世界公民,履行法则所规定的义务,拒绝由于过度的想象而产生一种狂热的偏好,进而忽视纯粹法则,忽视公共法则。“人格性的纯粹理性特质就这样越来越多地自身展现出来”,“只有这样,道德性才可以被把握为纯粹的”,而不是“由实际经验中的人进行限制、甚至创造出来的东西”[7]159。康德无法全然信任经验中的人通过想象力而具有的创造力,这种想象的创造力稍不加以限制就会变为狂热。想象力和激情相连导致的狂热进入实践领域,就会造成道德的、伦理的、政治的狂热,这于公共生活而言是危险的。如果说纯粹理论理性多少可以按照逻辑规则限制想象力以“根据范畴”,然而实践理性却无法在实践活动中限制想象力的经验性行动,无法确保其按法则行事。因此与上述将想象力作为纯粹理论理性走出其形而上学困境的手段不同,康德拒绝想象力作为纯粹实践理性走出其形而上学困境(即纯粹实践理性法则在经验性行动中的具体运用)的手段,而是为纯粹实践理性悬设了“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对此,马克思指出,康德“喜欢在太空遨游,寻找一个遥远的未知国度;而我只求能真正领悟在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8]736康德对实践理性的思考,对公共福祉自由的判断最终滑入了遥远的彼岸,而拒绝了对具体个人经验性日常生活的思考,拒绝了将实践把握为一种感性的、现实性的活动。这一拒绝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康德在面对人类想象力时的退缩。
二、想象力在绝对观念结构性扩展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不可否认,康德在纯粹理论理性领域将想象力视为一种先验的能力,拯救了想象力,对于批判传统心理学和传统人类学将想象力贬斥为一种消极的人类臆想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康德在纯粹实践理性领域对想象力的退缩,也正表明了他无力面对想象力中的感性成分,也无法应对这种感性成分之不可避免的狂热和幻想对于德性法则扩展的阻碍。康德“在超越论想象力面前的退缩,就是旨在拯救纯粹理性,即坚守本己根基的哲思活动的行进路程,而这一行进路程就将根基的坍塌以及随之而来的形而上学的深渊敞开了出来。”[7]204为了拯救纯粹理性,康德选择了想象力的退缩,而这一退缩最终导致了纯粹理性作为根基的坍塌,当一切被排除出纯粹理性时,纯粹理性也就仅仅是纯粹的和空虚的。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纯粹理性根基的坍塌使形而上学的深渊完全暴露了出来,这一深渊最终面临的是对人的发问,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康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通过他对想象力的态度而得以窥见:康德对想象力的拯救仅限于政治天才们(天才即想象力依于理性规则的运用)想象中的自由,国会的自由、形式的自由总比这种自由“被强行夺去更好一些”[2]174;而康德面对想象力的退缩也仅限于一个有着“彬彬有礼外表”“庄重、无私外表”[2]144的,文明化了的资产阶级总比鲁莽的、狂热的、街头巷尾的幻想家要好一些。
马克思亦将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的根本性归于人的解放,然而人的解放并非如康德那般对国会公民(尽管是政治天才们的想象)和文明化了的市民(尽管是徒有道德外表的伪装)总是更好一些的肯定。恰恰相反,马克思要对政治解放所诞生的公民和市民提出双重批判,因为不论是市民还是公民都不是“真正的人”的存在状态,而是“非人”的存在状态。真正的人的状态绝不是像康德那样“消灭有限性,而是相反,恰恰是要让这一有限性变成为确定的,从而可以在这一有限性中保持自己。”[7]206康德无法正视人的有限性,只能对其加以限制,使其依附于人格性的纯粹理性,然而,纯粹的人格向来不是真正的、原初意义的人自身。马克思要求人向人自身的复归,而这种复归就是对人的经验性、有限性的确认。这一确认使人的现实性表现为人的有限的、经验的生活,而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经验生活中又使自身有限的个体活动凝结为一种社会的力量。“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中,“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的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189。社会力量是人自身的原初力量,是人固有的本质力量。只有当人意识到自身原初的、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之时,人才不会因其自我的有限性而处于与他人的敌对状态,并且这种敌对状态也不需要外在力量的约束,如先验范畴的限制或上帝的悬设,才解除其敌对状态。
然而,马克思也意识到,在普鲁士德国,“社会的力量”更为严重地被遮蔽在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之中。“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1]10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中,市民社会作为绝对观念的一个环节,成为绝对观念内在的想象活动,而政治国家作为扬弃市民社会的环节,也是绝对观念内在想象活动的结果。作为绝对观念的想象活动,政治国家无法真正消解市民社会利己的、私人的社会现实,因而只能是一种虚幻的、虚构的、虚假的共同体。而绝对观念成为主体化的实体,也并非仅仅是出于哲学推演的考量,还有出于政治意义的考量。“观念不再被看作是抽象的观念,它们被锻造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3]214绝对观念并不停留于其抽象的实体性,而是成为主体,并在其想象活动中展开,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为政治斗争提供锐利的武器。
当然,与康德用先验哲学进行政治斗争的方式不同,黑格尔是用思辨哲学进行政治斗争的。“黑格尔善于用巧妙的诡辩把哲学家利用感性直观和表象从一实物推移到另一实物时所经历的过程,说成想象的理智本质本身即绝对主体本身所完成的过程。”[9]76理念作为绝对的主体,其想象的活动,即其展开自身的运动过程,取代了康德哲学运用直观和表象对感性材料和知性范畴进行综合的方式。从一个特殊实物到另一个特殊实物的推演,以及从特殊实物到普遍、一般概念的推演,是依靠理念本身成为绝对的主体来完成的。将实体理解为主体及其运动过程,并展开为各个环节,是黑格尔思辨哲学方法总的根本特征。
按照黑格尔的体系哲学,表象(Vorstellung)的联结能力是理智自身设定的一个环节,以完成内在普遍性与外在具体性的统一。“表象是理智提升的推论中的中项”,能够实现“存在和普遍性的连结”[10]240。表象作为理智提升自身过程中的一项中介,作为直观与思维的中间环节,能够提供一些综合,以连接直观到的外部材料与思维的内在规定。借由表象的中介,直观到的外部材料获得了普遍性,内在思维亦获得了外部的存在意义。而想象力作为表象的中项,能够联系诸多意象(Bild)形成普遍性的表象。想象力促使特殊意象出场,并形成普遍的表象要经过三个阶段:再生阶段使特殊意象成为定在;联想阶段使特殊意象相互联系为普遍表象,并使联系起来的普遍表象具有主动性和主观性;第三个阶段使特殊意象与普遍表象同一,并产生象征、创造符号(符号的定在即语言)。记忆则保持符号,并过渡为思维,思维由此不仅是自我的、自主的,还是客观的和实在的。
对于黑格尔借助表象来联结个别和普遍、殊性和共性,并使思维具有客观性和实在性,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了这一思辨结构的本质:“如果我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再进一步想像我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实’〔
同样,黑格尔的法哲学,作为绝对理念展开为客观精神的环节,亦“一般地关系到表象的普遍性”,因为,不管具体的内容“是来自外部事物还是来自理性的东西,即法的、伦理的和宗教的东西”[10]243,都涉及到概念的外在表象。法哲学是自由意志由其内在规定性向外部客观性的过渡。自由意志在其外部客观性上,首先遇到的就是特殊意志,是人类学个体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作为个别意志总是有与自己不相同的、他人的、特殊的意志。每一个个别的自我意识都是特殊意志。特殊意志是自由意志内在规定的外部材料,是人类学中各种特殊的、具体的需要。法哲学作为自由意志内在目的性与外在客观性的统一,就必然要求自我意识扬弃其特殊性,上升为一种普遍意志。在自我意识从特殊意志上升为普遍意志,从个别意志上升为总体意志的过程中,作为个体需要得以满足的市民社会只能将他人的特殊意志作为手段,达到有限的、形式的普遍性。只有作为绝对观念之完全展现的政治国家才真正达到了最终的普遍性。但是,“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1]37黑格尔无法现实地解决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只能虚幻地解决此矛盾。虚幻的本性就在于矛盾的解决是绝对观念想象的目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和解是通过绝对观念的想象来完成的,即绝对观念借助想象力的中介,通过结构性环节的扩展来消解矛盾。由此,实际利益的冲突就被绝对观念的想象活动虚假地中介掉了,但实际利益的冲突并不因此而消失。可见,黑格尔的政治国家作为一种共同体仅仅是虚假的、形式的共同体。
三、想象力图型结构未来导向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
如果仅就纯粹人类学而言,那么,不论是康德对想象力的拯救,还是黑格尔对想象力的重释,都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努力。因为他们都捕捉到了想象力作为纯粹人类学的一项分支所独有的功能,即其意象能力或表象能力。尽管传统启蒙哲学为保证人类理智的成熟状态而对想象力大加贬斥,但康德还是从经验心理学那里把想象力拯救了出来。康德之所以无法抛弃想象力,就在于他认为对想象力的研究,不能只停留于它是人的一种经验性臆想或幻想,想象力更为重要的能力在于它能够提供图像(Figur)。想象力形成图像的意象性能力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种能力,它一方面“使直观的杂多形成一个图像”[5]83;另一方面使知性概念下降为普遍表象,“想象力为一个概念提供其图像的普遍做法的表象,我称为该概念的图型”,“图型自身在任何时候都是想象力的产物。”[5]94想象力通过其逐级成像的能力,最终构建为图型(Schema)(21)康德明确区分了图像和图型,“图像是生产的想象力的经验性能力的一个产物”,而“图型无非就是按照规则的先天时间规定”,“关涉到一切可能对象而言的时间序列、时间内容、时间顺序,最后还有时间总和。”参见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95,97. 可见,图像涉及的是经验性的、即时性的时间,而图型则涉及的则是先天的、联合起来的时间。。只有凭借图型,感性直观才能与知性概念相结合,感性图像才能与知性表象同一。
那么,需要进一步去追问的是,为何同一性必须建立在图像的基础之上,并借助想象力联结以形成图型?康德认为,除了感性和知性的不同质这一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感性和知性都处于时间之中,但处于不同类型的时间之中。理性处于普遍的、先验性的时间之中,而感性处于特殊的、经验性的时间之中,由此,就必须借助想象力来表象现在的时间、过去的时间和将来的时间,并联结时间之中的图像,产成超越特殊时间的图型。“‘想象’活动,事先就假设了心灵具有重新将那先前所表象过的存在物,再次表象性地提供出来的可能性,这样就可以将时时刻刻恰好感觉到的存在物,在更加实在的(seiender)整体性中表象出来。”[7]171可见,想象力的成像功能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联结作用,它能够将先前的表象再次表象出来,通过整合时间,使存在物时时刻刻以图像的形式向我们呈现。我们也由此获得了存在物在时间之中的整体性表象。想象力确实不需要对象在场,就可以将其表象出来,这对于传统启蒙哲学来说,是人类容易产生臆想或幻想的不成熟状态,然而,康德却将其拯救为人类对过去、现在、未来之时间序列进行整体性把捉和体认的一项重要能力。
黑格尔也正是在此时间意义上,将想象力重释为人类对时间的一种中介能力。直观“是一个时间中的定在,——定在在其存在瞬间的一种消逝”[10]247,“诸意象的最切近的联系是其一起被保存起来的外部直接空间和时间的联系”,想象力的再生功能“则有一个普遍的表象充当诸意象的……联想性的联系”[10]239。当人类面对感性直观的瞬间性,以及这种瞬间性所具有的易逝性之时,想象力则为人类提供了一种中介能力,它将瞬间消逝的直观在时间中联系起来,并保存起来。由此,经验性的、易逝的、特殊的意象被保存为普遍的、稳固的、概念性的表象。想象力在其第三个阶段使经验性的意象转为形象化的符号。声音容易在时间中消失,而想象力产生象征,创造符号,声音通过想象力被保存为符号和语言。想象力通过其成像功能,将暂时的声音,保存为持久的语言。相对于声音而言,语言具有了精神的意义。在语言中,自我意识与他者意识相遇,并使个体意识产生现实性。“我,它既然表述它自己,它就是作为我而被听到、被领会了的;它是一种传染,通过这种传染它就直接过渡到与那些认识到有我之存在的人归于统一,成为普遍的自我意识。”[12]63可见,语言作为想象力成像功能的一个结果,使个体意识对经验世界暂时性的直观,过渡为延续性的意识,并通过个体对语言的表述和聆听,而与他者产生交互传递。通过语言的传递,个体与他者归于统一,产生普遍意识。个体意识的产生,以及个体意识向集体意识和社会意识的过渡,都离不开想象力的成像功能,以及想象力对时间序列的联结功能。
然而,康德在实践理性领域还是剔除了想象力,使知性的力量成为人在道德、法、国家等领域的唯一力量。黑格尔亦将语言的本质理解为“知性把它的范畴灌注到语言里”,以及“逻辑的本能”[10]248。想象力作为人在时间序列之中的感性的力量,又被遮蔽在了知性范畴和绝对观念的深渊之中。同样,当时间序列被固化在绝对观念的想象活动中,未来也被遮蔽在绝对观念的想象活动中。思辨的唯心主义在时间序列结构中“反对提前关于概念未来发展的意识,反对一切关于未来的知识”,“因此也就没有政治科学,没有关于现在现象的未来结果的知识”[13]103。如果说政治科学以关于未来的知识为前提,那么,被知性范畴和绝对观念所遮蔽的想象力是无法穿透未来的,无法给予未来以知识。这也是为何当想象力从纯粹人类学扩展到实践科学时,丧失了其在法、国家等政治领域中的功能和意义的原因。而想象力在实践领域功效的缺失,使得法、国家等政治领域在时间序列中无法认知未来,并对现实采取一种无批判的态度。康德面对想象力的实践退缩,表现为他对一个知性化了的市民社会的无批判接受。而黑格尔对语言之为绝对观念之灌注的理解,亦表现为他对市民社会之为绝对观念之必然性环节的理解。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唯心主义的思辨结构“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11]35意识脱离了实践,被构造为某种纯粹的、单独的意识,以及以此纯粹意识为基础的关于法、国家等政治学说的建构,都是脱离了“某种真实的东西”的“真实的想象”。“真实的想象”无法获取“想象的真实”,个体意识及其借助语言而向普遍意识、集体意识、社会意识的过渡,都因缺乏现实性而沦为某种虚构的想象。而马克思则为思辨的唯心主义“真实的想象”找到了现实的基础:“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1]34马克思对意识的现实性及语言的实践性的揭示,使得以语言为媒介的为别人的存在和为我自己的存在所产生的交往,以及随着人们交往而来的群体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得到了说明。当马克思将人的力量复归于社会的力量,将人的原初的、本质的、固有的力量理解为社会的力量之时,意识、语言作为人的力量,才找到了其真正的、现实的基础。只有将知性的哲学语言变为现实的生活语言,人们在知性范畴和理性观念中所建构的知性化了的、理性化了的、孤立的联系才能变为真正的、现实的联系。由此,“对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来说,那构成法、政治、国家、道德等等之基础的唯一的现实,就是社会现实,”并且“这一现实同时还是历史性的。”[14]正是基于社会-历史现实,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对于历史时间的考量,击穿了绝对观念或神圣观念的超历史性,使得未来基于真正的社会现实而同我们照面。
思辨唯心主义通过将普遍的理性视为人的唯一力量,将范畴、观念作为永恒的范畴和绝对的观念,最终将人塑造为非人的,将国家塑造为神话学的,将历史塑造为超历史的。在绝对观念中被僵化了的过去,在市民社会中被物化了的意识,在政治国家中被虚构出来的神话,都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新的未来之可见、可经验的批判之中纷纷瓦解。同样,“人的‘想象力’(Phantasie)的充溢连同世界上的一切相互关系(想象力马上变成一种具体的、内行的想象力)”,如果“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它就无法得到检验。”[15]17想象力作为人的固有的力量,其在时间序列中的联结功能,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时间观的基础之上,才能在实践经验中得以检验。只有在实践经验中得以检验,想象力才能恢复其具体的、内在的、固有力量。基于马克思对人的力量的社会固有属性的强调,对人的感性的、经验性的力量的肯定,想象力脱离了其虚幻的外壳(绝对观念作为想象力的主体)。想象力的成像功能所描绘的图像终于冲破其先验的、单纯的、幻想的藩篱,而在感性经验和现实实践中得到了检验。一旦想象力在现实实践中得到了检验,想象力对于时间序列的联结功能也立马得到了检验和确证,“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僵硬区分归于崩溃,尚未形成的东西在过去之中变得可见了。”[15]9正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人们对于未来的幻想,才有可能转变为可见的希望。
由于思辨唯心主义以绝对观念作为想象力的主体,想象力在时间序列之中建构的关于过去、现在、未来之表象的图型,以及人们对于图像、符号、语言的集体的、共同的记忆和思维,都因此而成为虚假的,而非真实的。思辨观念关于法的、国家的理论,亦使这些理论成为幻想的理论,使国家成为虚幻的共同体。任何仍停留于此机制之中的学说,“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的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的人意志的规律。”[16]56“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各式各样的德国社会主义学说,正是由于将纯粹意志理解为真正的人的意志,将资产阶级的实践理性理解为人固有的理性,才始终停留于对资本主义政治国家的非真实的批判,以及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无批判的保留。这些学说对纯粹意志的服膺,使其始终无法从空虚的思想下降为现实的运动,无法为革命找到德国的现实基础和生活条件,因此就只能待在其纯粹理论的空疏楼阁之中。更遑论以纯粹意志为前提的资产阶级知性科学,以“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17]45,更是无法突破对资本主义印刷语言的贫瘠的想象。此种想象的共同体,甚至还达不到马克思所批判的“犹太人的想象中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一般地说,是财迷的民族”[1]195这样一种水平。从后者出发,已经可以着手对市民社会进行批判,而从前者出发,仍然处于需要对黑格尔“虚幻的共同体”进行批判的范围之内。可见,对于人类社会新的共同体理论的思考,必须建立在马克思已然完成的对知性范畴、对思辨科学的批判的基础之上。任何对各民族之间以知性范畴、以思辨科学为基础展开的共通性,都是幻想的共通性,而非现实的共通性。我们必须超越此种非批判的、非现实的想象,以使我们对于未来人类共同体的建构,建立在稳固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