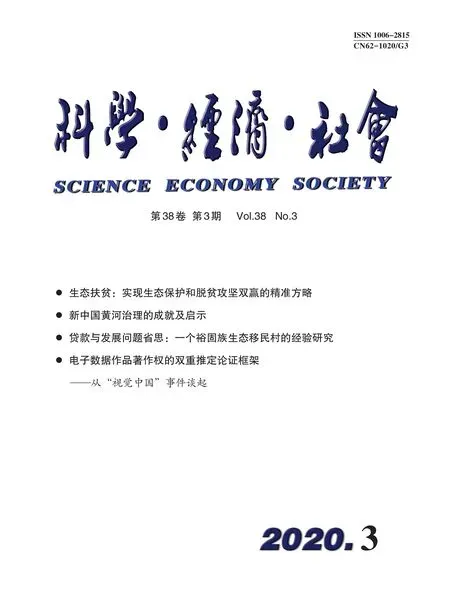核心区视角下的城市体系构建
——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中心
周 辰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和依托[1]。辽会同元年(938),辽太宗将幽州升为南京,北京始为影响力突出的中心城市,是为今京津冀城市群(32)本文研究的京津冀城市群在空间范围上,以今日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行政区划为标准。形成的开端。目前,学术界对京津冀城市群颇为关注,但是关于其长时段的考察相对不足,尤其缺乏对城市层级、功能、分布变化的研究。本文试以“核心区”理论梳理京津冀城市群形成及发展的历程,并分析不同时期城市层级嬗变的原因,以期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提供可行性借鉴。
一、“核心区”概念的梳理及影响因素
中国城市体系包括两种不同的层次,一种是出于地方行政管理目的而区划和控制的层次,一种是由于交易活动而形成,并反映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层次。当然,其间不少城市表现为两种层次的重叠[2]。关于中国城市体系的理论框架,施坚雅模型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中国学者鲁西奇在其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对“核心区”概念进行重新界定。
(一)“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借鉴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各区域市场均存在“核心—边缘”结构。横向而言,各区域根据资源集聚能力的强弱分为核心区与边缘区。纵向而言,各市场存在自上而下的八个层级[3]序言1-11。施氏认为,中国城市经济等级与行政等级基本对应,在经济层级中列为地方城市或更高级城市的多数中国中心地,同时也是行政治所。根据施坚雅的理论,核心区首要功能是经济,依次为政治、文化,军事功能被排除在外。一方面,经济功能能够强化文化、政治功能。税收潜力大的地方有力量大量投资,以便培养年轻人,使其获得学术上的成就,从而造就有功名的士大夫,而这些人又依赖于官僚,特别容易就范于官僚的规范控制。另一方面,经济区与军事区在多数情况下难以并存。税收和防卫在地区空间上的关系是对立的,在地区核心的中心区域,地方政府所孜孜以求的是税收,实际上排除了军事事务,而在地区边界上,地方政府所关心的是防卫和安全,实际上排除了财政事务[3]327-417。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情况各异,施坚雅根据市场构建城市体系的理论与国情不符,其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质疑。王卫平认为该模式的结论不符合江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江南地区,经济中心地等级与行政中心地等级的对应,只是极少的情况。在多数地区,情况可能正好相反。”[4]许檀亦认为该结论不适用于华北地区,“从明代中后期到清代中叶,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华北已有不少行政级别较低的城镇在市场层级中处于较高的位置,这些商业城镇的崛起反映的正是发展中的市场体系对原有行政体系的突破……在华北三省(直隶、山东、河南)中,除京城的商业规模基本符合其行政地位外,其他省城、府城的经济功能和商业规模大多与它们的行政级别不相匹配。”[5]
有鉴于此,中国学者鲁西奇根据冀朝鼎的“基本经济区”(33)冀朝鼎提出“基本经济区”概念,分析经济区与封建王朝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6]与施坚雅的“核心区”概念,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核心区”概念重新加以诠释。他认为,“施坚雅模式”的根本缺陷乃在于:中国历史的政治核心区并不必然就是经济核心区,经济格局简单地决定或制约政治格局的阐释体系,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所谓核心区,即兵甲所出、财赋所聚、人才所萃、正统所寄的地区。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分为不同层级的“核心区”,即王朝(国家)、大区、高层政区、中层政区、低层政区五个层级(34)清王朝灭亡后,王朝统治下的核心区改称为国家的核心区。[7]。根据鲁西奇的研究,核心区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是区域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项资源的综合体,不能仅以局部资源譬如经济区、文化区等概念进行界定。部分地区在局部领域的资源禀赋尤为明显,其余资源不足,只能称为经济、军事或文化中心,不能称为核心区。在本文研究的范畴中,首都属于王朝或国家的核心区;部分区域中心城市的综合辐射力强于路治、省会等高层政区,为大区核心区;三级行政区域的治所通常是各层核心区。
(二)“核心区”的影响要素
核心区是综合性的概念,涵盖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要素。在不同时期,各要素对城市体系演变的推动作用各异,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
1. 古代时期,政治、军事是决定核心区等级的主要因素。近代以前,政治、军事是推动城市体系演变的根本要素,经济要素从属于政治军事,文化功能与政治功能具有共生性(35)“正统所寄”与“人才所萃”兼具政治、文化双重功能属性。正统所寄,彰显的是一种文化权力,统治者通过宣扬“正统性”,阐释其政权的合法性,是对其既有权力的文化构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学而优则仕,人才构成了官僚集团的基础,是政权进行统治的主要力量。与之同时,国家权力控制体系中,行政力量与人才集聚能力呈正相关的关系。因此,文化功能与政治功能具有共存性。就本文研究的区域而言,文化区的发展以政治区功能的强化为前提。。兵甲、人才资源是封建王朝政权建立军队与官僚系统的基础,最为关键。由于财赋可以依靠武力和官僚征敛的手段获致,所以财赋系统在帝国统治体系中,处于从属于武力和官僚系统的地位。“正统之所寄”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权力”,决定着王朝统治的合法性[7]。
2. 近代时期,经济是推动核心区变化的主要因素,工商业城市、工矿型城市、新式交通枢纽城市成长迅速,传统的军事政治城市日渐衰落。
3. 现代时期,政治与经济是核心区确立的根本要素,其中政治属性具有第一性,军事因素被淡化。以我国七个大区(36)我国地理学专家根据自然地理特征,将全国划分为七个区域,即华东、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东北,即本文所研究的大区核心区,中心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武汉、广州、成都与重庆、西安、沈阳,其中西南地区拥有成都、重庆两座中心城市,上述8城均为直辖市或副省级城市,行政地位高于一般省会城市,是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中心。的中心城市为例,华南、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分别是广州和沈阳,但是其经济总量(国内生产总值)并不及同省的深圳和大连,政治是当代核心区城市确立的首要因素。
二、核心区视角下京津冀城市体系的演变
从辽代至今,京津冀(37)今京津冀行政区划的雏形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设立北京直辖市、天津直辖市以及河北省。笔者将建国前该区域称为河北地区,建国后称为京津冀地区。城市群的演变历经宋辽、金元、明和清前期、近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等时期,形成了南北二元对峙、北京中心地位的确立、城市功能分化、京津二元体系、京津冀三级阶梯等城市格局。
(一)宋辽对峙时期的二元城市格局
五代后晋年间,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中原王朝丧失长城屏障,今京津冀地区成为南北政权拉锯之地。北宋建立后,宋辽以白沟河为界,河北境内形成了二元对峙的城市体系,大名府和析津府为中心城市。
1. 辽境以南京析津府为中心城市。辽国行政区分为南北两面,汉人居住区仿效中原王朝制度,地方建置分为道、府与州、县三级政区,以五京为中心分置五京道。其统治的南京道全境与西京道、中京道部分地区位于河北境内,以析津府(今北京地区)为中心城市。辽太宗耶律德光取得幽州后,升为南京,又曰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8]494。南京因备御宋国[8]747而设置,是辽国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城市。南京的军事指挥机构等级在诸京中是最高的,是辽朝五京中商业贸易最繁荣的城市[9],是辽赋税的主要来源地,南京、中京多财赋官[8]801,从经济上看也是契丹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契丹草原地区在某些方面仰仗这个地区的供给[10]。根据核心区理论分析城市层级,南京是辽国陪都,为大区核心区的中心城市。辽五京为道治所之地,实为高层政区核心区,府和州、县分别是中层政区、低层政区的中心城市。
2. 宋境以北京大名府为中心城市。北宋行政区划分为路、州、县三级体系,河北行政建制屡有变化,通常以河北东、西二路见诸于史册。宋辽对峙格局形成后,宋境河北地区形成了以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为中心的城市体系。根据核心区层级划分,河北城市分为四层:第一层是大名府,大名府是北宋四京之一的北京,为大区核心区。第二层是定州(中山府)、真定府和瀛州(河间府),是河北安抚使治所在地,视为高层政区核心区(38) 宋代路级由四种长官组成,提点刑狱使负责司法和监察,安抚使负责军事,转运使专理财赋和民政,提举常平司和提茶盐司掌管赈灾事宜。彼此互不统领,没有统一的长官,管辖区域也不同。真定府、瀛州、定州是安抚使驻地,且经济繁荣,实为高层政区的中心城市。。第三层为中层政区核心区,是其他府、州、军治所之地;第四层为低层政区核心区,为各县治所。
大名府是都城开封府的北面门户,号称北门锁钥。庆历二年(1042),为应对辽军南下,北宋政府升大名府为北京,“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乃建北京。”[11]10209大名府是北宋在黄河北岸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河北路(河北东路)治所之地,也是河北转运使、大名路安抚使驻地,“(庆历)八年(1048),始置大名府路安抚使,统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通利、保顺军。”[11]2121设有市易司,熙宁年间年税超过3.86万贯。
真定府、定州、瀛州是第二层城市,商业发达,军事功能尤为突出,为高层政区核心区。第一,三地是安抚使驻地,是河北境内最重要的军事中心。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廷在河北置安抚使,命知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领之,“天下十八道,惟河北最重。河北三十六州军,就其中又析大名府、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为四路。”[12]第二,三城是境内商业最繁华的区域,商税额较高,设有市易司。据熙宁十年商税统计,真定府年税为3.9万贯以上,瀛州1.91万贯、定州1.97万贯[13]6303-6306,税额在今河北地区均位列前五。王安石推行新法时,率先在商业发达的城市设置市易司,三城均位列其中,“凤翔、大名、真定府、永兴、安肃军、秦、瀛、定、越、真州,并置市易司。”[11]455此外,部分军、州的经济、政治功能因战局演变而得以强化。宋辽议和后,北宋政府开放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为榷场,各军州遂为边境商贸中心。雄州是宋辽使者过境之地,政治属性增强,以雄州为国之北门,有宋一代,国信使皆自雄州出入[14]。保定原为清苑县,宋初置保塞军,又为宋皇族祖陵所在地,升为保州,为其以后的辉煌奠定基础。
宋辽时期,军事是推动河北城市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全境高层政区及以上的中心城市共计5座,其中4座为唐末藩镇要地,军事对峙强化其原有的军事、政治功能。析津府原为唐范阳节度使驻地,安禄山、史思明、李怀仙、朱滔、刘怦、刘济相继割据,刘总归唐。至张仲武、张允仲,以正得民。刘仁恭父子僭争,遂入五代[8]493。定州、恒州(真定府)、魏州(大名府)是唐末易定、恒冀、魏博节度使的治所之地,为华北地区北部最主要的区域中心城市[15]。五代时期,后唐李存勖曾于魏州建东京于镇州(恒州,即真定),辽耶律德光也升镇州为中京[16]。瀛州的崛起与宋辽交战密不可分,发展为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大观二年(1108)升为河间府。根据富弼的建议,瀛州与定州、大名府是河北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定为右臂,沧为左臂,瀛为腹心,北京为头角,此四城者,河朔之所望也。”[17]北宋政府采取其建议,始置高阳关路安抚使[11]2123,瀛州成为区域性的军事中心。此外,瀛州还是河北沿边军州的储量之地,“保州、广信、安肃、北平等军在定州之北,系极边要切储蓄之地;真定府、祁州、永宁军亦系次边。合行计置军储处,与都仓相去皆近,便缓急般取,克日可到,或容本司计置兑移,即可以并归都仓瀛州。”[13]6872
值得指出的是,河北境内多核心城市格局是一种非正常现象。根据中心地理论,两个相邻同级中心地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中心地的等级越低,其间的距离就越短[18]。河北部分中心城市距离过近,经济腹地高度重合,只是战时特殊状态,违背了城市分层原则。比如定州与真定府同时作为高层政区核心区的中心城市,彼此距离不足60余里,析津府与大名府作为陪都,同处于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平原区域,实际辐射空间颇为狭窄,这种双中心城市格局并不合理。多核心城市体系因战争需要而形成,随着河北地区重新统一,部分城市的中心层级让位于另外一座城市,河北城市体系发生重构。
(二)金元时期以北京为中心的城市体系初步形成
金灭宋辽之际,河北重新统一,幽燕地区先归北宋所有,旋即被金朝占据。金元两朝,我国政治重心北移,河北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城市体系。
金延续了北宋路、府、县三级行政区划体系,府分为京府、总管府、散府,州分为节镇、防御、州军。京府分为上、下两等,其余府、州分为上、中、下三等[19]。河北地区被划分为中都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大名府路以及北京路、西京路,前四路治所位于境内。城市层次如下:第一层是上等京府大兴府(今北京),先为南京,海陵年间迁都于此,改名中都,由大区核心区升为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同期,大名府战略地位下降,为大名路治所之地,降为高层政区核心区。第二层是总管府所在地,大名、真定、河间分别是大名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的治所,是高层政区核心区。定州降为节镇,归真定府节制。第三层是散府各州,为中层政区核心区,河北境内无散府,定、沧、冀、邢是上等节镇,雄、保为中等节镇。第四层是县、镇,是低层政区核心区。
元代调整行政区划,北京首次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城市,保定因毗邻京师而崛起,始为境内的主要城市。河北地区隶属于中书省,包括大都、上都、兴和、永平、保定、真定、顺德、广平、河间、大名等路。元代地方行政区划颇为混乱,“元则有路、府、州、县四等。大率以路领州、领县,而腹里或有以路领府、府领州、州领县者,其府与州又有不隶路而直隶省者。”[20]1346省下有路、州、府、县,路归省管,州、府、县隶属不定,故以路级行政单位作为分层的终点。河北城市体系如下:第一层是大都和上都(39)治所开平府,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路所辖部分区域位于今河北境内。。大都是元朝的法定国都,上都是皇帝避暑之地,世祖以上都为清暑之地,车驾行幸,岁以为常[20]4242,同为王朝的核心区。元武宗曾在兴和路(今张家口张北县)“敕城中都”[20]530。武宗死后,仁宗“罢城中都”[20]537,中都不是大区核心区。第二层视真定路为高层政区核心区,元朝腹里未设立省会,真定是河北境内大都外经济文化最繁华的地区。元代的税务提领,五千锭之上的,全国有八处,真定城就是其中之一[21]272,元朝的科举考试,乡试分散在全国各地举行,直隶省部路分则设真定、大都、上都、东平四个考点[21]291。第三层是各路,为中层政区核心区,包括河间、大名、保定等路。元代河北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基本保持一致,大名、河间等地延续了宋代以来商业繁荣的情况,仍为境内主要的中心城市。根据《元史·食货二》记载,大都宣课提举司商税额高达113006锭,是河北地区甚至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真定路(17408锭)、大名路(10795锭)、河间路(10466锭)、保定路(6507锭)[20]2398-2399是大都之后河北境内商业税额较高的区域。保定因行政区划调整而成为冀中地区的主要城市,辖一司、八县、七州,州领十一县,成为燕南一大都市。“保定路的设置,大抵是元廷照顾汉世候张柔和增加路数量,缩小路辖区等政策所造成的。”[22]行政区划的调整使河间、大名等原高层政区中心城市地位相对下降,保定因辖区扩大地位上升,取代定州成为太行山东麓新的区域中心城市[15]。
(三)明与清前中期城市功能的分化
明清之际,军事、政治、经济等因素的交织互动,使各城市主要功能初步分化,形成了政治型与经济型城市共同发展的格局。从核心区的主要功能来看,政治型城市在城市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经济型城市尚处于从属地位,区域性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趋势加剧。
明代城市包括地方行政与军事卫所两种体系。传统行政体系与元代相比有所调整,特点如下:第一,北京被确立为王朝统治的核心区。与金元时期相比,北京是全国政权的唯一首都,资源集聚能力空前增强。第二,府、直隶州为中层政区核心区。明代北直隶未设立省会,辖八府二直隶州,除京师顺天府,尤以保定、河间、大名、真定最为重要,保定军事功能最强,河间商业最繁华。军事领域,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将大宁都司迁至保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明长城以南的防守力量,尤其是军事重镇保定的防御力量[23]。经济领域,根据《续文献通考》对明代北直隶八府课税的统计,顺天府(66.5万贯)税额高于其余各府之和,保定(11.7万贯)、真定(11.7万贯)、河间(11.5万贯)、大名(10.7万贯)课税额度较多,广平、永平、顺德课税数较低,总额与大名府相当[24]。另据《万历会计录》对直隶七府(除京师外)商税的统计,以河间府居首(22.1万贯),保定(10.6万贯)、真定(11.7万贯)、大名(11.5万贯)居中,广平、永平、顺德最少,总额不及10万贯。河间是京师外河北商业最繁华的区域,彰显我国北方城市功能分离趋势。自元定都大都后,北京的赋税、物资主要来自南方,运河城市因商业而兴起,河北境内运河主要途径河间府境内,如沧州、天津等。沧州运河流经今辖境 253 公里,是京杭大运河全线流程最长的市[25],天津原为“海滨荒地”,主要是由于元代海运,其次是河运的缘故,“舟车攸会,聚落始繁”[26]。
明代还存在以卫所为中心的地方军事管理体系。明初,元朝残部逃往蒙古草原,对北京构成巨大威胁,故京畿之地卫所遍布。河北地区是大宁都司(北平都司)、万全都司管辖之地,卫所多分布在长城以北的口外地区,部分卫所发展为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行政建制提升,比如天津、宣府、张家口等。万全都司设置于明宣德年间,驻地位于宣府(今张家口宣化区),清代升为府城。“居庸者京师之门。户宣府又居庸之藩卫,也其地山川纠纷,号为险塞,且分屯置军倍于他镇,气势完固庶几易……”[27]天津在明代初为军事性质的卫所,因漕运、海运交汇而兴盛。到明末,天津远远超过一般市镇,成为北京周围首要经济辅助城市和东部军事门户[28],张家口是宣府镇下的军城,隆庆议和之后,是汉蒙贸易和中俄贸易交通要道上长城内的重要节点[29],雍正二年升级为厅。
清代河北地区被称为直隶,城市功能分化趋势更加明显,不过在近代以前,政治城市仍然在城市体系居于主导地位,如北京、承德、保定。清代城市体系较明代调整如下:第一,承德发展为国家政治副中心。为维护满蒙关系,康熙帝在原属内蒙古喀喇沁旗、翁牛特族的牧场内划地为界,设置了以“习武绥远”为目的的“木兰围场”,作为清皇室的禁苑、猎场和令蒙古贵族陪同皇帝射猎的练兵场[30]。康熙四十年(1701)修避暑山庄,长期驻跸于此,雍正元年(1723)设热和厅,十一年置热河直隶州,乾隆四十三年改为府。第二,保定被确定为省会,是高层政区核心区的中心城市。“(顺治)五年,置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驻大名。(顺治)十六年,改为直隶巡抚。明年移驻真定。康熙八年,复移驻保定。”[31]保定是直隶总督驻地,建有莲池书院,是直隶省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其经济功能相对薄弱,商业规模远不及天津、张家口等新兴经济城市。许檀曾经对华北商业城镇的市场层级进行划分,直隶境内的“崇文门、天津、张家口的税收额都超过临清,三者合计当可达2400万~3000万两;多伦、山海关、通州三者以平均200万两计,祁州可能也相差不多;其他如保定、辛集等7处,各以30万两计。”[5]在行政等级中,北京为首都,天津为府城,张家口、多伦诺尔为厅,通州、祁州为散州,山海关仅为镇,保定的商业地位与行政地位并不匹配。第三,部分卫所行政建制提升,如天津、宣化升为府、张家口升为厅,成为中层政区,改变了传统的城市体系。
(四)近代京津二元中心格局的形成
近代以降,中国城市体系在西方的冲击下被迫重构,经济成为推动城市地位演变的关键因素,河北境内形成了天津与北京形成了二元中心的城市格局,北京区域中心地位遭到天津前所未有的挑战。河北城市存在三种发展路径,一是经济城市的崛起,以天津、张家口、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为标志;二是传统政治城市相对衰落,不失为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包括北京、保定、承德等;三是传统政治中心的没落,如大名、正定、河间、宣化等。
第一,新兴经济城市的崛起。西方入侵使中国被动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沿海开埠口、铁路交通枢纽以及工矿型城市得到了优先发展的机遇。天津是漕运和海运交汇之地,1860年开埠后迅速成为北方地区的经济中心,取代保定成为直隶的政治中心。唐山、秦皇岛因天津的崛起而发展,唐胥铁路在唐山设站,带动了其他工业的发展,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厂等新式工厂的成立,使唐山成为冀东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心[32]。秦皇岛因运输开平生产的煤矿,由小渔村发展为新兴港口城市。近代以来俄、英、美、法等商人陆续在张家口经商,张家口为陆路商埠,毛皮加工业极为繁荣,被称为皮都[16]。石家庄原为获鹿县一农村,因京汉、正太铁路交汇而发展为商业集散中心。“石家庄为京汉铁路与正太铁路联络之枢纽……迄光绪二十九年,京汉铁路通车,始渐有商民来往。迨光绪三十三年秋间,正太铁路通车,石家庄之地位益形重要。自是以后,商贾云集,行栈林立,铸建繁兴。昔日寂寞荒僻之农村,遂一变而为繁荣之市场矣。”[33]
第二,传统政治中心的相对衰落。传统政治城市近代转型相对缓慢,凭借强有力的行政权力维持了区域中心的地位,比如北京、承德、保定等。北京在近代经济地位被天津取代,政治地位日渐式微,不失为区域性的特大城市。北京城市地位由传统时代的帝都,转身为中华民国时期的国都、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又由此复升中央直辖市,日伪政权时期演变为临时“国都”,1945年8月光复后一度被确定为中华民国陪都[34]。承德原为清帝避暑之地,自1861年咸丰帝驾崩后,清帝再未驾临,政治地位名存实亡,民国十七年(1928),南京国民政府改热河特别区为热河省,以承德为省会。保定是直隶省城,自1870年直隶总督轮驻天津、保定两地后,直隶中心地位被天津所取代,北洋政府时期为直隶军阀大本营所在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两度成为河北省会,仍为河北最主要的城市之一。
第三,绝对衰落的传统政治中心城市。民国初年,北洋政府调整行政区划,废府置县,部分府城沦为县城,原有区域中心地位被新兴城市所取代,如河间、正定(真定)、大名、宣化、永平原为府城,原中心地位被沧州、石家庄、邯郸、张家口、唐山等经济型城市所取代,行政建制降为低层政区甚至更低的级别。
近代河北城市体系形成了京津双核体系,以北京为行政中心,天津为经济中心。1928年国府南迁以后,北京由王朝(政权)核心区降为大区核心区。天津发展为北方经济中心,相继成为直隶省会、中央直辖市、省辖市,与北京同为华北地区的超大城市,升为大区核心区。京津之后,保定、承德、张家口是第二层城市(40)民国北洋时期行政区划为省、道、县三级,直隶省分为渤海道、范阳道、冀南道、口北道,以天津、保定、大名、宣化为治所,天津于1913年取得保定成为省会,保定、大名、张北为中层政区核心区,其中大名、宣化的区域中心地位已经逐步被新兴城市所取代。1928年,直隶省划分河北、察哈尔、热河等行政区,以保定(先为天津、北京)、张家口、承德为省会,这三地均为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为高层政区核心区。,其作为直隶(河北)、热河、察哈尔省会,是高层政区核心区。第三层为中层政区核心区,清代为府、直隶州、直隶厅等地。民国时期中国行政区划大体遵循二级体系,故各县均位列该等级。唐山、石家庄等新兴城市的建制低下,初期仅为区域性的商业中心。1938年建市以前,唐山一直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市政管理机关,其地方行政事务分属丰润县和滦县[35]。石家庄于1939年设市,设市以前的石门行政中心,就区域行政权限而言,依然归属获鹿县管辖[36]。
(五)三级结构:京津冀城市群的形成及演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以天津为直辖市,京津冀城市群正式形成,北京再度成为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天津区域地位被弱化。改革开放以后,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失衡,人均GDP差距过大,形成了三级阶梯格局。以2019年为例,北京人均GDP是16.29万,天津是9.06万,河北仅为4.67万[37],城市体系分布如下:
第一层是北京——国家核心区。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定位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和全国工业基地[38]。改革开放后,北京不再强调经济中心的功能定位,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所示,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39]。2014年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提出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重新界定北京的城市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40]。从建国至今,北京城市定位随着时代不断调整,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定位始终没有发生转变。尽管北京正在淡化经济中心的战略功能,其经济影响力反而日渐强化。从1978年至2019年,北京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居上海之后排名全国第二名,两地GDP比重日渐缩小,由上海的39.71%上升至92.7%。
第二层是天津,天津在建国后为直辖市,一度是河北省会,经济功能被急剧削弱,北方经济中心被北京取代,核心区地位介于大区核心区与高层政区之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天津经济发展资源受到制约,区域资源向北方倾斜。同时,根据“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城市”政策方针,部分工业向内地转移,天津工业实力进一步遭到削弱[41]。改革开放以后,天津被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2020年)》确定天津的城市性质为: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要逐步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42]。可是,天津在全国排名呈下降趋势,GDP从1978年的全国第三下降至2019年的全国第十。与北京相比,天津的GDP比重由76.6%下降至39.9%,京津经济差距拉大。
第三层为河北境内各市,中心城市由保定变为石家庄、唐山两地。计划经济时期,保定是河北省会、文化中心,是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同期的石家庄、唐山、邯郸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工业城市,石家庄、唐山的工业基础极为雄厚。石家庄是“一五计划”中全国重点建设的18座工业城市之一,是电力工业、纺织工业以及医药工业城市[43]。石家庄拥有苏联援建的全国最大的化学药品生产厂——华北制药厂,成为全国抗菌素生产基地[44]。唐山是河北省最大的重工业城市,素称中国“北方煤都”,1975年原煤产量2690万吨,约占总产量的1/20[45]295-296,邯郸铁、煤、棉矿资源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以能源和原材料为主,轻重工业并举的综合性工业城市[45]340。1968年,河北省会由保定搬迁至石家庄,全省中心城市发生调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河北省政策向沿海地区倾斜以及工业结构的调整,保定与钢铁城市邯郸发展日趋缓慢,逐步沦为全省的二流经济城市。以GDP为例,保定、邯郸在2019年分别是3902亿元、3881亿元,列全省三、四名,总量与排名前两名的唐山(6890)、石家庄(5809)差距明显。唐山是河北境内最大的沿海城市,矿产资源丰富,与北京、天津形成了京津唐工业区,承接两地工业,是河北省北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石家庄作为河北省会,还是华北地区最主要的交通枢纽,是河北省南部地区的中心城市。
2014年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提出与2017年雄安新区的成立,是对京津冀城市职能的一次重大调整。从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现状来看,其核心城市是首都北京,副核心是直辖市天津,再次是石家庄、唐山两个区域性中心城市。雄安新区选址在保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河北省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一次北移和归位[46]。京津冀城市群的结构性差异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改善,雄安新区的建设将使保定成为主要的受益者,在强化城市节点、改善交通等方面作用突出[47]。根据《河北省城镇体系规划(2016年-2030年)》所示,2030年石家庄将成为河北省内唯一的特大城市,保定、唐山、邯郸为Ⅰ型城市[48],石家庄的节点作用将超越唐山。
三、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分布及其原因
从辽代至今,京津冀重点城市(高层政区及以上城市)布局遵循了“由南向北”“由内陆向沿海”的空间分布,各城市在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历经兴衰起伏,社会环境、交通区位、经济基础等因素对城市体系的演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分布
京津冀城市格局演变历经五个阶段,笔者以图表的形式梳理各阶段主要城市的分布,进而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形成原因,参见表1。

表1 京津冀城市群层级分布
根据空间方位以及行政级别分布,京津冀地区可分为六个区域,分别是北京、天津、冀中、冀南、冀北、冀东。冀中地区包括今保定、石家庄、衡水、沧州、廊坊市,历史上的真定(今石家庄正定区)、定州(县级市,曾由保定代管)、河间(今河间市,县级市,沧州辖)位于境内;冀南地区包括今邯郸、邢台市,大名府(今大名县,邯郸辖)位于该区域;冀东包括唐山、秦皇岛二市;冀北地区包括张家口、承德二市,该区域位于长城以北,又被称为口外地区。其中,天津、秦皇岛、唐山、沧州临海。
自辽占据幽州伊始,今京津冀城市群重心经历了由南向北、由内陆向沿海的空间布局,部分时期略有反复,历经五个阶段。一是宋辽时期,城市群重心位于今河北省南部内陆地区,主要城市包括大名府、中山府(定州)、真定府、河间府(瀛州)与析津府(今北京),皆为内陆城市。二是金元时期,城市群重心向北移动。北京取代大名府成为中心城市,保定取代定州发展为冀中地区的核心城市。三是明代与清前中期,口外与东部沿海城市迅速成长,城市群重心向北部、东部转移。宣府、张家口分别因军事、经济而兴起,承德因清帝处理满蒙关系的需要而成为全国政治副中心,天津、沧州、通州等沿海、运河城市迅速发展,传统行政城市中唯有保定行政地位上升,成为清直隶省会。四是近代,城市群重心东移,东部沿海城市因经济而崛起,中南部内陆城市相继衰落。天津发展为北方地区的经济中心,强烈冲击了以北京为中心的传统城市格局。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京津冀城市群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天津为次中心的格局,城市群重心历经由内陆向沿海转移的过程。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确立了工业内迁的基本国策,北京、石家庄、保定、邯郸等内陆城市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工业重镇,天津经济作用被弱化,城市格局由沿海向内陆迁移。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城市优先发展,内陆城市除省会石家庄外,均发展相对缓慢。2017年,雄安新区在保定境内成立,京津冀中部区域迎来发展机遇。
(二)京津冀城市的发展路径
列宁指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49]政治(军事)与经济在各时期对城市地位变迁起到了关键作用,“不同的制度安排也演化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路径,并在经济表现和绩效方面产生巨大的反差。”[50]根据其发展路径,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 因军而兴,因政治功能而显赫。隗瀛涛将传统城市分为三种类型:即传统的行政中心城市、工矿业城市和工商业城市。行政中心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充分反映了行政地位与传统城市发展的密切关系[51]。近代以前河北城市体系以行政中心城市为主,“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52]城市的兴衰与行政地位紧密一致,受国家政局演变影响深远,典型城市包括北京、保定、真定(正定)、大名、河间、定州、承德、宣府(宣化)等。
2. 因军而兴,因商而兴。部分城市因军事需要而产生,此后其经济功能日益凸显,逐步转型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进而提升行政等级,典型城市是天津、张家口,近代天津从附属于首都的商业城市逐渐转变为沟通中外、南北商品交流的外贸型工商业城市和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53]。
3. 因经济功能而兴起商贸中心,比如石家庄、唐山、秦皇岛、邯郸等地,其中唐山、邯郸属于工矿型城市,石家庄、秦皇岛为交通枢纽型城市。
(三)京津冀城市体系演变的原因
1. 社会环境的变化是京津冀城市体系演变的根本原因。“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是农业时代中国城市的一个重要发展规律,近代以来进入工业时代,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虽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则成为城市一个主要的规律。”[54]
各历史时期,推动城市系统变革的主要因素存在区别。近代以前,政治、军事是主要动力,宋辽对峙、河北统一、政治中心北移、明清中原王朝与蒙古部落的交战与和解等众多历史事件,使河北城市群重心由南部向北部转移。近代以降,经济因素是推动城市体系变革的主要力量,经济城市蓬勃发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行政因素在推动社会资源整合过程中作用显著,导致京津冀阶梯性差异的形成。受行政干预等因素的影响,河北和京津之间,长期以来没有形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平竞争、互利互助的良好机制,其三者的经济关系没有很好地按照经济运行规律的轨迹运行,导致了一些不利于三者经济发展的后果,其中造成损失最多的是河北省[55]。
2. 地理位置与交通方式的改变。近代以前的河北主要城市分布在驿路与河流沿线,陆路是最主要的交通方式,核心城市大多居于内陆。近代以降,中国社会交通方式发生变化,即随着铁路的修筑、新的轮船航线的开辟,铁路沿线和轮船码头开始形成和初步发展起来一批商业城市[56]。沿海及内陆铁路枢纽区域是商品贸易交流的中心地区,城市重心经历了“由内陆向沿海”“由公路枢纽向铁路枢纽、开埠口岸”的移动过程。
天津开埠后,华北地区形成了以天津为中心的交通网络枢纽,继而发展为北方地区的经济中心。唐山、秦皇岛、石家庄、邯郸等城市因新式交通的产生而繁荣,邯郸因铁路实现了复兴,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取代大名而成为冀南经济中心,得益于京汉铁路的通车和邯郸站的建成[57]。与之同时,部分内陆城市亦因交通路线的变化而衰落。中东铁路与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完全改变了中俄贸易路线,张家口因未能抓住历史机遇而走向衰落[58]。正定的区域中心位置被石家庄所取代,“正定府(原真定府)自石家庄立为车站后,商业大受影响……商务日渐萧条,各处商家因时局不定,往往裹足不前。”[59]保定地处交通要地,转运业下滑进而导致工商业不振,特别是大量工商业者南移石家庄,保定因此失去冀中工商业的中心地位[60]。
3. 经济基础与经济结构的影响。马克思曾经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结构的演变,是推动城市格局体系变革的重要因素。
从辽代至今,河北地区经济格局发生了三次变革。一是近代以前,城市分布于农业区。河北地区以长城为界,分为农耕区和畜牧区,农业是城市形成、发展的基础,畜牧区逐水草而居,难以形成城市。北京及其南部区域长期为河北的经济中心,主要城市坐落于此。尽管元代以后口外地区得到开发,但多因军事需要而产生,经济功能较为薄弱,如元兴和路、明代永平府的课税额度皆处于全省较低水平。二是近代至改革开放,城市格局以工商业为基础,对外贸易、工业化水平成为衡量城市发展程度的标志。河北境内的新兴城市,多以工矿型为主,铁路的兴建使资源禀赋得以发挥,发展为区域性的商业中心。除天津外,石家庄、唐山、秦皇岛皆属于该类型。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唐山车站附近矿井日产原煤2000吨左右,秦皇岛车站附近有华商承办的柳江煤矿,日产原煤600余吨……正太铁路南河头车站附近有著名的井陉煤矿(先为中德官商合办,后收归河北省办),使用机器采煤,年产煤在民国元年(1912),达192000吨[61]。三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城市经济结构多元化发展,对外贸易、金融业、科技创新型城市相继引领中国经济发展,重工业城市进入21世纪以后发展日趋缓慢。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偏重于重工业,除北京外,各主要城市GDP排名持续下降,以邯郸最为典型。邯郸是一座资源型城市,钢铁、煤炭在工业总产值占有较高比值,曾在1983至1985年连续3年国内生产总值位列全国前20,居河北首位。伴随着我国工业能源结构的调整,邯郸经济转型转型不顺,GDP排名降至全国60名以后。
四、结语
京津冀城市圈的形成及演变是社会环境与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社会环境的变迁对城市分布及层级演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国家政局、经济基础、交通和地理区位等因素的作用下,京津冀城市群历经了由南向北、由内陆向沿海的空间分布过程,军事与政治、经济、政治与经济等因素推动了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期城市层级与功能的变迁。就长时段发展趋势而言,政治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演变起到了关键作用,城市经济受行政干预影响较为明显,军事因素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日渐淡化。伴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以及雄安新区的成立,京津冀城市群面临新的分工。打破人为设定的行政等级,使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域相统一,是解决区域城市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