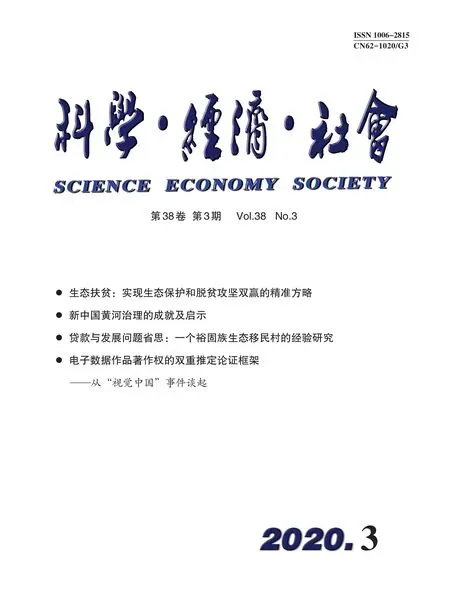“身”的“介入”:关于郭熙山水画学的环境美学考察
蔡志伟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350)
以“远”的图绘与欣赏为中心,郭熙对于山水画学意境理论的阐述,既包括画家在“身即山川而取之”的基础上营构的自然之境,也涉及观者在“行、望、游、居”的想象中体验的乐居之境。这种围绕“身”展开的审美活动,涉及自然环境的观照、自然景观向图像构成的转换,以及自然环境与日常生活环境的互动等问题,恰可成为环境美学的考察对象。本文尝试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范畴为切入点,以现代环境美学相关理论为参照,揭示郭熙山水画学中的环境美学观念,兼论其对当下环境美学研究与实践的价值意义。
一、“身”:主体与环境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身”绝非仅与肉体相等同,而是一个包含“心”的主导作用,强调以“心”统摄感官、四肢的“身—心”一体化范畴,这种意义的“身”指向主体。同时,“身”又绝非仅与主体相等同,而是一个包含天道自然、社会伦理作用于主体,指示个体进行非个体化扩展的“主—客”一体化范畴,这种意义的“身”指向个体与外部世界的交互。以上两种意义的“身”,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身”的维度。
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身”包括“心”,所谓“心……在身之中。”[1]这种“身—心”一体的观念,与西方传统文化语境之中“身/心”二元对立的观念存在显著不同。中国先哲主张发挥“心”在“身”中的主导与统摄作用,如《管子·心术》谓之:“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2]再如董仲舒谓之:“身以心为本。”[3]又如王阳明谓之:“身之主宰便是心。”[4]通过这些表述可见,由于“心”的存在与涉辖,“身”不仅是形体与感官媒介,而且是综合感性经验的理性机体。易而言之,“身”在肉体维度之外,同时附着一层精神属性。正是在这种“身—心”一体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哲人将“身”与主体相等同,将之视为进行自我建构、自我保存的对象,例如儒家有着“三省吾身”“修身”之说,道家有着“贵身”“保身”之说。
中国先哲对于“身”的主体意义的阐述,并不意味着将主体与外部世界相互割裂,反而着重强调主体是在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之中,方才能够获得自身的充实与定性。在如何实现主、客交融的问题上,不同哲学流派的论述不尽相同,譬如庄子认为应当通过“心斋”的方式,使得主体进入虚静状态,以直觉化的体悟来实现主体与外部世界的交互[5];而荀子则认为应当是通过“心”利用、综合感官与形体的功能,所谓“心有征知”,将万物纳入“身”之中,从而使得主体与外部世界形成通路[6]。尽管相互之间有所区别,但是最终意旨近乎一致,皆在强调基于“身—心”一体进行主客联通,以使主体获得天道自然或社会伦理的充实。由此,主体与外部世界形成了交互关系,完成了自身的非个体化扩展,实现了“主—客”一体。抑或言之,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标识着主体与外部世界存在一种可然且必然的互动。
“身”在“身—心”与“主—客”两种一体化中表现出的四个维度,既包含立足感官媒介的感性认知,又突出对于这些感性经验的理性综合;既将主体的意义凸显出来,又将主体融化于天道自然、社会伦理之中。这种对于自我构成的体认,以及对于自我与外部世界彼此交互的认识,建构了一种以“身”为中心,涉及主体与环境的思想传统。
二、“身即山川而取之”:“介入”自然之境
山水画学发轫之初,“身”在观照自然、营构画作中的基础地位已被揭示出来。宗炳《画山水序》有谓:“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7]583这里的“身”乃是“应目会心”的“身—心”一体之“身”,意在指出以“心”的能动,突破“迫以目寸,则其形莫观,迥以数里,则围于寸眸”[7]583的局限。同时,宗炳还曾提出“澄怀味象”[7]583的命题,凸显审美活动之中“主—客”一体的必要意义,强调处于虚静状态的主体与自然山水的充分交互。结合上节所论可见,宗炳山水画学对于“身”的论述,可以视为对于中国古代哲学“身”范畴进行的审美继承与美学演绎。
隋唐五代时期的山水画学,虽然未曾明确提及“身”,但是诸如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8]121的论述,以及荆浩“度物象而取其真”[7]605的说法,都可看做是对“身—心”一体、“主—客”一体的审美法则的表述,延续了山水画学中的“身”观念。时至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的“身即山川而取之”[9]575的命题,充分阐述、发挥了晋唐以来山水画学中“身”的美学内涵。
从当代环境美学的视野来看,“身即山川而取之”是主体身心对于自然环境的“审美介入”(aesthetic engagement)。“介入”是美国哲学家阿诺德·贝林特(Arnold Berleant)用以阐发环境美学的核心概念,其认为“美学欣赏,和所有的体验一样是一种身体的参与,一种试图去扩展并认识感知和意义可能性的身体审美。”[10]这里的“身体”,在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美国哲学对于西方传统哲学“身/心”“主/客”二元对立进行批判的理论背景中,实则乃是“身—心”一体、“主—客”一体之意,即“审美的身体化”(aesthetic embodiment),其与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身”相互暗合(9)实用主义美学、身体美学代表人物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认为:“汉语术语‘身体’则似乎非常适合用来传达我身体观念:一种活生生的、感觉灵敏的、积极活跃并且有意图的身体……中国古典哲学使用那么多词语来表示身体,表明身体是这个哲学传统的中心。”参见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M].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0-11.。这种美学思想重视身体与心灵一体关系的达成,强调主体与环境交互关系的建立。
郭熙“身即山川而取之”的命题,一方面承袭了山水画学历史脉络之中以“心”主导、统摄“目”的传统观念,强调“心”不为“目”所困,力图摒除感官经验的琐碎与局限,从而把握自然山水的整体面貌,所谓“真山水之云气……画见其大象,而不为斩刻之形。”“真山水之烟岚……画见其大意,而不为刻画之迹。”[9]575另一方面,较之此前的山水画学,郭熙在注重“心”对于“目”的主导、统摄之外,同时注重以身体的移动来补充“目”的不足,所谓“步步移”“面面看”等等,以期达到“饱游饫看”的目标[9]576。值得注意的是,“心”虽然可以帮助“目”实现局限性的突破,但是并不构成这种突破的充分必要条件;同时,过分重视精神而轻视肉体,将可能造成“身—心”一体的倾覆,构成“身/心”二元的对立,有悖于“身”的应有之意。相反,作为形式的“心”,其所进行综合的质料,无疑源自“目”之所见,而身体的移动则将为“目”之所见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与丰富性,亦即能为“心”的综合提供更多可以利用的资源。由此可见,“身即山川而取之”表述了充分发挥精神、肉体两种因素在观照自然景观之时的意义,是主体身心对于自然的全方位投入——“介入”。这既促成了以郭熙为代表的宋代山水画家对于“川谷”“云气”“烟岚”“风雨”在“远近”“四时”“朝暮”“阴晴”等各种环境下不同情状的细致观察,也对于将自然景观转换为富有自然主义色彩的图像——营构“如将真即其处”[9]576的画作提供必要准备。
同样出于山水画学的传统,郭熙以“远”来表述山水画作的营构。“远”何以能够成为表现“身”对于自然环境“介入”所得的恰当方式?山水画学之中“远”的基础意义是“张绡素以远映”[7]583“咫尺之图,写百千里之景”[7]592,是将“目”的感官体验,与“心”对于“目”之局限性的突破,融合为一的过程,亦即对于“身—心”一体的图像表现。当然,“远”绝非这样一种近似于机械性的累加。如前所述,“身”的外向实践乃是“主—客”一体的建立,其在处理感官经验与理性综合的过程中,已然伴随着主体与外部世界的交互。张璪曾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来表述审美观照与绘画创作中的这种外向实践,并以“绘境”来称之[8]121。这种对于画家与自然山水交互关系的强调,是“远”的应有之义,是“远”越出图像构成意义之上的文化精神层面。
郭熙在《林泉高致》中不仅细化了“远”的图像构成意义,也将画家与自然山水交互而孕生的“境”作为“远”不可分割的部分加以表述:
2695-2998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Waters公司;SB-5200DT超声波清洗机 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QP电子天平 北京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Milli-Q超纯水仪 美国密理博公司;酚标准品 Sigma公司;其他试剂均为HPLC级别;实验用水均为超纯水。
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其人物之在三远也,高远者明了,深远者细碎,平远者冲淡。明了者不短,细碎者不长,冲淡者不大,此三远也。[9]578
这里的“高”“深”“平”是对于“远”的图像营构之法的细化,而所谓“势突兀”“意重叠”“意冲融而缥缥缈缈”,则是对于画家与自然山水交互之际所把握到的“境”的细腻说明。如果说,在郭熙之前的山水画学中,“远”与“境”虽然相互为一,但是各有特指或侧重,那么在郭熙这里,“远”与“境”则全然融合为一,将“身—心”一体、“主—客”一体的成果与意蕴完全纳入“远”的范畴中,以表现“身即山川而取之”的“介入”所得。贝林特在《艺术与介入》中如是写道:
公元5世纪的郭熙写出了受距离和静观的审美所控制的西方人的眼睛所不可能达到的一种经验。在远东艺术中,看不到西方静观性距离的传统。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鼓励参与的技巧。[11]96-97
不妨说,中国山水画作中的“远”虽然是一种距离,但是一种可以“介入”的距离。在郭熙乃至宋代的绝大部分山水画作中,我们既能够看到对于“目”之所见的如实刻画,又能看到对于通过发挥“心”的主导、统摄作用突破“目”的局限,对于“目”之所不可及的展现;既能够观看到对于自然环境幻如真实的描绘,又能在这种描绘中看到附着在其上的情思与意趣。正是这样一种山水画学思想与实践,成就了画作中的自然之境。
三、“行、望、游、居”:“介入”乐居之境
宗炳曾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游,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8]78“卧游”是文士在无法游历自然山水时,以观赏山水画作的方式模拟游履情境,以完成生理、心理补偿的一种审美活动。郭熙《林泉高致》所谓“行、望、游、居”[9]574之实与“卧游”同义,其以特定身体动作的细致表述,提示观者“介入”山水画作营构的“身—心”一体、“主—客”一体的自然之境,体验、想象这种以图像为媒介、存于日常生活环境中的乐居之境。
“行、望、游、居”是以过往游历自然的感官知觉为基础,借以山水画作对于自然环境的模拟,通过精神能动再次催生出此前审美经验的体验、想象活动。这种勾连“过去—当下”知觉的审美活动乃是一种“介入”。贝林特认为:“介入当然依赖于感觉的投入,但是知觉总是有记忆的成分,因为过去的知觉和期待进入了有意识的现在。”[11]133郭熙之子郭思对于宋神宗观赏其父山水画作的记载,即可视为对于这种“介入”现象的一次描述:
睿思殿,宋用臣修所谓凉殿者也。前后修竹,茂林阴森,当暑而寒,其殿中皆凿青石作海兽鱼龙,玲珑通透,潜引流水,漱鸣其下,而上设御榻,真所谓凉殿也。上曰:“非郭熙画不足以称。”于是命宋用臣传旨,令先子作四面屏风,盖绕殿之屏皆是。闻其景皆松石平远,山水秀丽之景,见之令人森竦。有中贵王绅好吟咏,有宫词百首,曰“绕殿峰峦合匝青,画中多见郭熙名。”盖为此也阙。[9]587
这幅以屏风形式放置在睿思殿中的郭熙画作,不仅“见之令人森竦”,又与这座“凉殿”中的其他装潢构成了一种呼应关系,围绕“凉”“寒”这样一种感官经验进行配合,构成了以消除暑气燥热为目的的居室环境。正如贝林特所指出的:“在这种环境媒介(建筑)的内部,出现了心、眼、手、气候以及其他自然过程的激发力量,同时还有使用这些力量,并引起反作用力的知觉特征和结构性条件。”[11]139可见,郭熙不仅着意对于自然之境的意象化模拟,也会对于如何以画作为媒介,构成自然环境向日常生活环境的移入,使之成为能够提供审美愉悦的居住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以考量。
事实上,中国古人欣赏画作之时,从未将其作为与日常生活相隔绝的纯粹艺术品,而是将其作为构成日常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从未将生理体验从绘画审美中剔除出去,而是将这种体验作为构成日常生活与审美经验之连续性的重要环节之一。即使是在看似极为强调审美超越的士大夫那里,他们也并不拒绝画作引发的生理享受,也未曾切断日常生活与审美经验的连续性。苏轼在《书蒲永升画后》曾经如是写道:“(蒲永升)尝与予临寿宁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阴风袭人,毛发为立。”[7]628
当然,中国古人对于山水画作的欣赏绝非仅限于此,以“身”之“介入”体验、享受的乐居之境尚有更高意旨。郭熙《林泉高致》的开篇如是写道:
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直以太平盛日,为离世绝俗之行,岂必高蹈远引,而与箕颖埒素,黄绮同芳哉?[9]573
这里虽然提及“常处”“常乐”“常适”“常亲”的感性经验,但是仅仅将其作为破除“尘嚣缰锁”实现“离世绝俗”的精神解放的基础依托。换言之,在“身”对于画作的“介入”中,精神价值不可或缺。同样,山水画作也非仅是作为居室装饰,而是在现实生活之中豁开的另一空间场域,用以容纳所念而不可得的理想生活状态,亦即在超越却又日常的情境中获得一处文化精神的乐居之境。这种“身”的“介入”与乐居之境,是为当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山水画作欣赏之中更为主要的审美面向。这里,“环境美学成为一种文化美学……是独具特色的感官、概念和理念模型,它构成了一种文化的知觉环境。”[11]140
这种审美向度在苏轼对于郭熙山水画作的欣赏中鲜明地表现出来。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苏轼被召回朝并且屡次升迁,以翰林学士知制诏的身份往来玉堂之中。是时,郭熙绘制的《春江晓景》屏风已经伫立在玉堂三年有余。眼前的这幅画作勾起了苏轼对于友人文彦博手中所藏郭熙《秋山平远》的记忆:
玉堂昼掩春日闲,中有郭熙画春山,鸣鸠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闲。离离短幅开平远,漠漠疎林寄秋晩,却似江南送客时,中流回头望云巘。伊川佚老鬓如霜,卧看秋山思洛阳,为君纸尾作行草,炯如嵩洛浮秋光。我从公游如一日,不觉青山映黄髪,为画龙门八节滩,待向伊川买泉石。[12]254
借以由此画及彼画的神游,苏轼进行了当下时空向昔日时空的回溯。他希望回到往时“离世绝俗”的生活状态,不为现在“尘嚣缰锁”的朝堂生涯所困。随后,黄庭坚在唱和之作中点明了苏轼所想:“玉堂卧对郭熙画,发兴已在青林间”[12]254。对于帝王而言,郭熙《春江晓景》对于草木兴荣的气氛渲染,以及对于“如君臣上下也”的经营位置,呼应了玉堂的政治空间属性,象征着国运昌达与君臣伦理。但是对于苏轼而言,这幅画作并非是与玉堂建筑环境相得益彰的一件装潢,而是打破玉堂建筑环境的一处缺口,玉堂并非是一处乐居之境,画作才是一处乐居之境。尽管这处乐居之境不在现实世界之中,仅在精神世界之内。苏轼对于画作的审美体验,或与郭熙的作画本意更为贴近——希望画作能够为观者在备受困扰的现实中营构文化精神的乐居之境:
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之本意也。[9]573
综上观之,以“身”的“介入”为发生机制的山水画作审美欣赏,其中最为重要的旨趣之一,就是享受、追寻主体向往的乐居之境。在此,“环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力的王国,一个将感知者和被感知的对象纳入一个经验的统一体,把我们居住的世界变成一个真正的人的栖居地的力场。”[11]141
四、余论:郭熙山水画学中环境美学观念的当代价值
在《艺术与介入》中,贝林特将西方风景画分为:居于主流风景视觉观念的全景式风景画(panoramic landscape),以及更为个人化的参与式风景画(participatory landscape)。前者“强调物理距离和视野的宽度,提供了一种既建立于观者和风景之间的分离感之上,又在绘画形式中传达这种分离感的以视觉为主的经验。”后者“需要一种介入的美学,当身体在时空中移动时,关于身体的经验创造了一种功能性的知觉秩序,它使参与者与环境融为一体。”[11]85-103正如上文所提及的,贝林特将郭熙的画学思想作为这种“介入”的东方例证,而与西方参与式风景画相比类、甚至等同。
然而,这种判断失之对郭熙山水画学的整体考量与全面理解,无法真正揭示郭熙山水画学中的环境美学观念的意义。以郭熙为代表之一的中国山水画学,不能作为全景式风景画或参与式风景画的子集,而是兼有两者部分性质。与全景式风景画相较,郭熙山水画学虽然同有展现全景的美学理想,但是这种全景——“远”不仅超越了物理上的视觉阀域,更加由于摈除主体与环境的“分离”“静观”,从而拥有在“身—心”一体基础上、借以主客交互孕生的意蕴充满期间。与参与式风景画相较,其虽然同有“介入”的审美活动,但是在“介入”的内容上并不相同,即使注意到了身体的参与,仍然将心灵的主导与统摄摆在观照、营构首位,将精神解放与安适摆在体验与想象的首位。由此,郭熙山水画学可以为当代环境美学的“介入”理论提供一种新的绘画类型集合——意象体悟式。
在《审美欣赏与自然景观》一文中,另一位当代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基于科学认知主义,对于受到艺术观念影响的自然审美进行批判,反对“对象模式”(the object model)——仅仅着眼某个自然对象,以及“景观模式”(the scenery or landscape model)——仅仅观照某些景观,推崇“环境模式”(the environmental model)——立足自然本身对于自然环境进行全方位欣赏[13]。事实上,卡尔松这种激进的环境美学观念不仅违背了自然审美的实际——即使观照整体自然,也要起于注意其中的某一对象或片段,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文历史在自然审美中的价值。相较之下,一方面郭熙对于观照、营构自然之境的论述,虽然着眼于部分对象,但是并不为其所困,而是由对象、片段走向整体。这说明,“对象模式”“景观模式”与“环境模式”之间并不相互排斥,相反是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14]。另一方面郭熙有关体验、想象乐居之境的观点,将自然与人文充分地勾连起来,赋予自然以人性、人性以自然。这说明,自然与人文之间并非不可兼得。由此,郭熙山水画学中的环境美学观念可以矫正卡尔松的激进意见。
这里并非对于当代西方的环境美学成果存在微词,而是意在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美学资源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从思想根源来看,当代环境美学存有对于西方传统思想中“主/客”二分观念的一种反辄或补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主/客”二分导致了人与环境的根本性对立,而对于这种对立关系的化解则是环境美学的方向之一。然而,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存有“主”“客”意识,但是从未致使二者走向对立,反而是将“主—客”一体化作为基本主线。或言之,是在未经过“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想进程之中,实现一种朴素的“主—客”一体化。正是这种思想背景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古典文化语境中的环境美学观念的自身特点:虽然未有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理论所展现的颠覆性力度,但是呈现着朴素、和缓、切实可行的态度与观念。
在郭熙山水画学中可以见之,基于中国哲学与先前画学中的“身”观念,其通过强调“身即山川而取之”,力图使主体全身心地投入自然环境的怀抱,对于如何进行自然审美观照有着价值意义;以“远”来展现自然全貌与人性寄托,对于如何处理自然环境的图像表现、自然与人文的价值辩证关系有着启发意义;以图像为媒介将自然环境引入居室环境,借以“行、望、游、居”的体验与想象,实现日常生活的宜居与自我精神的救赎,对于受到生活环境与精神环境困扰的现代人有着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