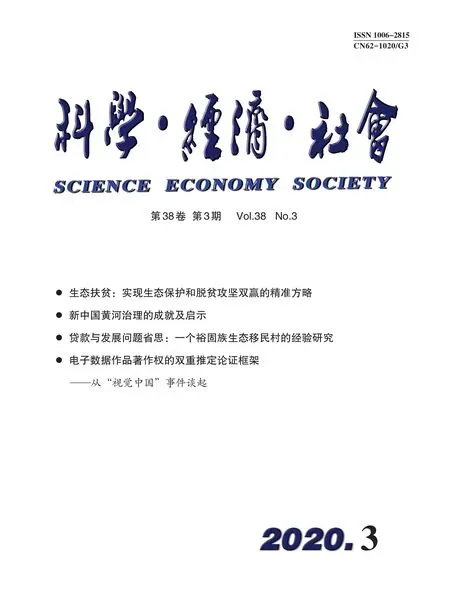论康德“纯粹实践理性的优先性”
——以加德纳和维拉山科的讨论为焦点
柳 康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实践理性的优先性问题,或许不只是《实践理性批判》中的重要论题,而是康德哲学本身的“动机”,具体而言,是批判哲学的道德-实践的动机[1]。而这种动机是通过前两大批判中的“辩证论”部分得以显明的。此外,这个议题还涉及康德对科学的形而上学的设想和建构、涉及理性本身的结构问题。在这种宏大的背景下,“实践理性的优先性”就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上是就康德哲学作为整体而言,该命题昭示着理性的本性和结构,标明了康德哲学的统一性;但在狭义上,作为一条“原则”,表明与理论理性的关系。但在后一种意义上,确立“实践理性的优先性”这一原则是无意义的,因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是不同的原则的能力,尽管它们可以运用相同的范畴通过类比来加以解释。
一、论证结构
“纯粹实践理性在与思辨理性结合时的优先地位”一节是在康德解决了“至善”概念的辨证论之后引入的。从表面上看来,这一节对辨证论的消除似乎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有一点,它是康德对理性在实践上的超验的运用——即对引入公设所作的辩护(2)这一观点来自孙小玲老师的《实践理性批判》课程,在此感谢。。这种辩护恰恰在于说明理性设定“公设”“权利”的问题,而这种权利似乎不能仅仅通过实践理性的“希望”(hope)和“需要”(need)获得,而只能通过对纯粹实践理性(不同于一般实践理性)的优先性的证明才能获得。
(一)文本梳理
这一节总共分为四段,但这四段却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康德首先定义了一般意义上的“优先”的含义:“对于在两个或多个由理性结合起来的事物之间的优先地位,我理解为其中之一是与所有其他事物相结合的最初规定根据的这种优先权”[2]。那么,如若我们暂时不论被理性所结合起来的事物的数目是多少,而暂时假定被结合项只有“纯粹实践理性”和“思辨理性”的话,加之,如果某个对于另一个具有优先性的话,其中之一就应当是与另一个相结合的规定根据。而这种结合时的优先性首先表现为兴趣的优先,即其他的兴趣都要服从这种具有优先权的兴趣。而兴趣是“一条原则,它包含着唯有在其下这能力的实施才得到促进的条件。”[2]164因此,这种优先权就表现为“服从”(subordination)的合法性和兴趣的优先性。除此之外,理性能够为每一种内心能力赋予一种兴趣,但理性自身的兴趣却是自我所规定的。那么,在作为规定根据上的优先性和兴趣上的优先性是不是严格对应的?如果不是,那么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难道兴趣最终就是在结合时作为规定根据的兴趣?但如此一来,如何解释,服从纯粹实践理性的优先性规则,就能使得该能力得到促进(3)我们将在第三部分集中探讨在此部分提出的诸多问题。?因为,“它的思辨运用的兴趣在于认识客体,直到那些最高的先天原则,而实践运用的兴趣则在于就最后的完整的目的而言规定意志。”[2]164那么,初看起来,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不同划分并不在于兴趣的不同而是由“质料的本性”所规定之下的划分?此外,理性的兴趣不在于与自身相一致(它充其量只能算作真理的形式条件),而在于“扩展”(Erweiterung)。但是,理性的“扩展”应在什么意义上来理解?尤其是在“实践的知识”这一条目下就更令人费解。因为对于理论理性而言,诸理念作为幻相是形成知识时需要避免的。但是,这种幻相却是理性自身的兴趣或本性所导致的,那么对于理论理性而言的“认识客体”的兴趣就需要避免这种幻相,因此对理性本身而言,处于这种状况无疑是悲剧性的(4)这或许不是理性的“悲剧”,而是理性自身包含的张力。[3]172。因此,理性的两种不同兴趣之间的不和谐就导致了理性自身的统一性问题。
总之,在第一段,无论是“作为结合时的规定根据”还是作为“兴趣”,纯粹实践理性的优先性并没有表现出来,反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集中表现在与理论理性结合时作为根据的纯粹实践理性,与作为兴趣而优先的纯粹实践理性之间的关系还不甚明朗。理性作为有理性存在者的自然倾向,它就在于追求“无条件的条件”,而这些最终的条件就表现为“理性的理念”——灵魂、自由和上帝。然而,在理论理性的意图中,它们只具有范导性的作用,但在实践理性的意图中,它们却是“构成性”的,“因为它们是使纯粹实践理性的那个必要客体(至善)成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的根据”[2]185。或许,康德正是要突出这种张力,以便于彰显区分“优先性”的必要性(5)如果康德能够将“兴趣”作为一贯的原则的话,有些批评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为什么只有“实践理性”和“思辨理性”的区分?最简单的理由,康德认为是理性“使用、意图和兴趣”的不同,如果“兴趣”在于包含该种能力被促进的条件的话,那么,实践理性优先于思辨理性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只能在于它更能促进理性,更能“满足”理性的需求,或更能成就理性成其为理性,避免理念的“空洞性”。因此,从逻辑分析的层面来讲,如果只有两项的话,那么它们的关系就有四种:要么实践理性优先于思辨理性;要么思辨理性优先于实践理性;要么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平行(并列);要么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无关。
(二)论证重构
第二段中,康德对于“优先性”问题做出了论证。对于此问题,Gardner重构了康德的论证:
1. 首先,1a:“纯粹理性自身能够是并确实是实践的”;1b:“毕竟只有同一个理性,不论是出于理论的还是实践的意图,在按照先天原则做判断”;因此,1c:理论理性“必须接受”“不可分割的从属于实践兴趣的命题”。
2. 其次,如果理论理性不被提议归属到实践理性的话,则2a:理论理性将“封锁自己的边界”,并且不承认任何得自实践理性的东西;2b:实践理性“会把自己的边界扩展到一切之上,并且在自己需要的要求下就会力图把前者一起包括到自己的边界之内来”;所以“理性与自身的冲突就会出现”。而隐含的前提就是2c:“理性不能与自己相冲突”;那么,就会推出理论理性应当归属于实践理性。
3. 最后,3a:“所有的兴趣最终是实践的”;3b:“甚至思辨理性的兴趣也只是有条件的,唯有在实践的运用中才是完整的”;3c:“人们不能指望纯粹实践理性从属于思辨理性”;由于3d:一项必须归属于另一项,因此3e:理论理性必须从属于实践理性[4]265。
同样,维拉山科认为,康德对上述“优先性”的三种论证依据康德的《逻辑学讲义》可以归结为一个选言推理,如下:
1)要么思辨理性较之实践理性具有优先性(A),要么实践理性较之思辨理性具有优先性(B),要么两者都不具有优先性(non-B);
2)或者思辨理性或者实践理性必须(笔者加)具有优先性(not non-B);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GM模型组HEK293细胞内GSH含量和SOD活性显著降低(P<0.01),LDH释放量及MDA含量明显升高(P<0.01)。与GM模型组相比,SVPr 4 g·L-1组GSH含量和SOD活性分别升高了49.03%和60.98%(P<0.01),LDH释放量及MDA含量显著降低(P<0.01),与GM模型组相比,分别降低45.57%和54.71%(图3)。
3)思辨理性不具有优先性(not A);
4)这样,实践理性具有优先性(B)[3]178。
维拉山科的的论证比加德纳的论证更为清晰。但是,二者对康德的论证能否成功却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
二、可能的困难
加德纳认为该论证最终不成立是因为康德并没有很成功地论证“理性的统一性”,而这一断言在康德的论证中是根本性和奠基性的。此外,笔者认为,如果ppr不成立,如果无法解释理性的统一性,那么至善的概念无法成立,更遑论作为构成至善的德性和幸福之间的两种要素之间的先后关系能够成立了。因为我们发现,理性及其不同“兴趣”之间的关系与至善及其要素之间的关系具有同构性,如果作为“基底”的理性统一性无法自圆其说,那么其他的论述将是没有根基的、外在的。如果推到极致,就连理性本身或许都会遭到怀疑,但这不是我们在此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当前问题的解决。我们将集中在加德纳和维拉山科关于ppr的相关说明,并基于对文本的解读一一评述他们的论证。
(一)系统性的缺失
要么思辨理性较之实践理性具有优先性(A),要么实践理性较之思辨理性具有优先性(B),要么两者都不具有优先性(non-B)。
康德认为,不管是理性的“兴趣”“意图”还是“使用”,均可分为两种: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从而在逻辑上除过它们不相关论题之外,就只具有上述的三种可能,但第三种可能性会导致理性自身的破裂,留下斑驳不堪的理性。因此,康德是无法接受这一论断的,因为这会导致理性自身的不可能,从而连思维的基本形式(如同一律、不矛盾律等)也将随之消亡。
维拉山科是在对公设的“接受-拒绝”(acception-rejection)的对子中展开这三种可能性:如果思辨理性具有优先性,则思辨理性会拒绝公设,实践理性也会拒绝公设;如果实践理性具有优先性,则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都会接受公设;如果两者都没有优先性,那么,实践理性会接受公设,而思辨理性则会拒绝公设[3]179。维拉山科认为,这种解释模式潜在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引入在遵循“命令”时的“本体论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来很好地解释实践理性的优先性。
维拉山科所举出的例子就是“请把窗户打开”,它在理论上并不与“这儿不存在窗子”矛盾,但如果这一理论命题作为命令需要人来遵守的话,那么就预设了“窗子存在”;与之可类比的“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作为“至善”可能实现的条件,亦即作为道德主体,若想保证至善的话,那就必须以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为前提[3]180。但是,从理论上的预设,到实践上的公设,再到信仰的对象,实践理性的优先性命题似乎在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作用。其中,维拉山科认为公设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理论上未规定”(theoretically undecidable)和“实践上的必要性”(practically necessary),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如果说可以通过所谓的“本体论承诺”得到解决的话,那么,从实践的必要性到信仰或者从“希望”(hope)到信念(belief)则需要“认其为真”(Fürwahrhalten)这一环节。
在关于理性如何是“一个”的问题上,加德纳认为,康德根据“兴趣”的不同无法区分出孰高孰低。在笔者看来,如果兴趣在于包含该能力的促进的条件,那么无疑,思辨理性只有在“认识对象”时才能促进自身;而实践理性只有在“规定意志”时促进自身。如果说康德的兴趣(不如说意图)划分成立的话,正如加德纳所说,除过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各自兴趣除外,理性作为整体还应该有自己的兴趣。因此,如果实践理性优先于思辨理性,那么理性的整体性只能在被理解为“系统性”(systematicity)的前提下才能成立(6)这种区分是荒谬的,它只是一种逻辑上划分的结果,亦即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等同于种和属的关系。。但维拉山科认为,可以在不顾及理性自身能力的划分的情况下,只专注于理性的使用,但这种使用是在“同一个认知系统中”进行的,换句话说,这种认知是同一种认知,但却是以实践为导向的(7)如果维拉山科的论断成立的话,同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功能(Ergon)的论述相类比,康德对“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的区分只是展开论述的引子。但是,这种说法对康德来说显然是不充分的,因为康德的论证明显要比亚里士多德更加倚重对理性的划分。。但是,这种“系统性的认识论”解读有可能会导致黑格尔式的哲学,即理性在认识中展开自身,亦即从理论理性出发,并最终认识到自己是实践理性。此外,对理性自身的结构漠不关心而只专注于使用,会给人留下“两张皮”的印象,从而将康德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本体论)区分开来。当然,这是除了将“至善”解读为“道德世界”的现象学解读之外的可供选择的作为另一种形态的目的论[5]。康德之后的德国观念论也正是在此观念上发展起来的。康德确实意识到了这点,但他并不愿意走这条路,而是在此后的《判断力批判》中区分出三种并行的“理性”能力。加德纳试图通过“种属”关系来描述实践理性和思辨理性之间的关系,从而把思辨理性看成是“实践理性”的一个阶段,但这种企图显然不会成功,因为完全从属于纯粹实践理性并不符合理论理性的兴趣。
(二)扩展的不可能
或者思辨理性或者实践理性必须具有优先性(not non-B)。
问题(2)与问题“为什么二者之一必须具有优先性而不可以相互并列?”是一体两面的。思辨理性为什么要“接受”这份外来的财产?为什么思辨理性不能“据其自身”而成为一个“他者”紧守住自己的认识领地?这一“必须”的根据到底是什么?这种必须大概来源于康德对形式逻辑的倚重,即“不矛盾”性作为任何“真”的条件(不论是理论上的“真”还是实践上的“真”)的铁律显然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如果理性的结构缺乏“一致性”,那么理性自身也会随之解体,前后一致的“理性的描述”也不会出现[3]182,因而最终会导致理性的解体。
就理论(思辨)理性而言,如果不接受任何来自实践理性的东西,并不会给自身造成多大的损失,因为它在经验性的运用中会得到相应的充实,因而只要它满足于认识对象,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自足的。但实践理性却有所不同,在其自身的需求的驱使下,它会逐渐吞并思辨理性。这种思想确实很难与康德在辨证论部分作出的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的方式兼容,因为德性从属于本体界,而幸福从属于现象界,“意向的道德性作为原因,而与作为感官世界的结果的幸福拥有一种即便不是直接的,但也毕竟是间接的(以自然的一个理智的创造者为中介)而且是必然的联系,这种结合在一个仅仅是感官客体的自然中永远只是偶然的发生,而且不能达到至善”[2]157。那么,问题在于:实践理性对应于本体界,思辨理性对应于现象界?那么,二者之间的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表现在道德判断上应该会是什么样子?它就是道德法则吗?它与自然法则是什么关系?难道自然的法则最终可以还原为道德法则。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在本体界具有优先性的实践理性会统治整个现象界,最终会变成精神,所谓的自然的和自由的因果律将会无任何的用武之地,可是,这样就会违背康德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初衷。因此,思辨理性接受了公设,并没有增加任何经验性的知识,而只是从单纯的设想的可能性为理性的概念赋予对象,在此意义上,从而成为“概念”,便已然是一种扩展[3]191。换句话说,概念的形成在于它和它指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但维拉山科对“扩展”的解释似乎在实践理性是构成性的这一点上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只要是构成性的,那么便会运用到范畴,这种运用即使不存在经验性的对象与之对应,但会存在所谓的“先验对象=x”,因此本身是“概念”。因此,不存在认识时,概念与其对象是间接的,唯有直观才与其对象直接相关的情况。但从理念转变为概念究竟是不是一种扩展呢?理念本身如果具有对象性的话,那么它通过实践理性的优先性确实会得到充实,在此意义上,似乎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扩展。但这与康德对“概念”的定义有冲突,概念必须是综合的结果,这种综合必须与经验性直观相关。依照笔者浅见,实践的构成性的意义在于依照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由理念”并依照公设来行动,是行动者之道德性的体现,没有了公设,道德性和神圣性将得不到彰显,而它们恰好体现在有限理性存在者的行为之中。
(三)循环的不可避免
思辨理性不具有优先性(not A)。
加德纳认为康德断言“一切兴趣都是实践的”,这一推论似乎“太快”了[4]267;他集中探讨了这一命题。与之相反,维拉山科却探究了思辨理性为什么是有条件的?在何种意义上是有条件的?他通过援引“假设”(hypotheses)和“公设”(postulate)之间的区分来论证了思辨理性运用的有条件性。他认为,思辨理性的假设只是被允许的,此外“思辨理性只能颁布假言命令”,在遵循此一命令的时候,我们是有选择的余地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被强制的;但是,公设作为信念无法被强制,只能是实践理性自我抉择、自我意愿的结果,或者说应该如此。换句话说,作为思辨理性的假设依据的是有条件的假言命令,而实践理性依据的是无条件的道德法则。因此,思辨理性是有条件的,与无条件的实践理性相比,是不具有优先性的。
在维拉山科的论述中,思辨理性的兴趣如果在没有任何高于其自身的兴趣的情况下,是可以自存的。因此,似乎在实践理性的兴趣未被给予理论兴趣之前,理论理性没有必要着眼于实践理性的兴趣,也就是在理论理性的兴趣中尚未包含着能够为实践理性所规定的可能。这样,就可以避免所谓的“循环”,即它们互相限制和规定的循环,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在“不同意图”之间的转换会获得独立的意义。因此,实践理性的优先性只是同一理性的不同种类的意图之间的优先性。这也就能够解释同一理性的第三种意图的出现,即审美的意图的出现了。但是,如之前所讲,如果理性本身的结构与至善的结构具有同构性的话,那么在法则建构成功之后所证明的自由意志以及自律就从根本上先于上帝和灵魂,因为后面两者是法则要求的作为义务的至善可能实现的条件。因此,似乎存在着某种次序(order)上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表现在“自由”所扮演的角色上则十分明显,亦即自由到底是预设(presupposition)还是公设(postulate)?
三、自由与否定
在第一批判中,在宇宙论的图景下,康德提出了自由的理念。与知性所具有的相对的自发性相较,理性具有绝对的自发性。同时,自发性表现在它们都具有综合的功能。但与知性作为规则的能力不同,理性作为原则的能力,它“使知性概念摆脱某个可能经验的那些不可避免的限制”[6],因此,在提供限制知性的规范的同时,理性总是以超越的姿态呈现自身。在非常微妙的意义上,这种绝对自发性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具有后世所谓实践的意义。但它并非康德所要确立的实践理性,而是在理论理性的范围内,所表现出的综合统一的功能。
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与道德法则的确立有关,具体而言,一旦确立起道德法则在实践上的必然性,理性也就同时彰显了自身的实践性。在《奠基》中,康德通过诉诸现象界和本体界的区分,试图跳出所谓的在自由和道德法则之间的“循环”。很多学者认为定言命令以失败告终[7],但他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自由的理念”所具有的功能与自由在本质上的“超越性”关联。这也表明“道德形而上学”中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意义并不是在“后物理”意义上谈论的,而是在“超越”(meta-)的意义上讲的(8)这一洞见实际上来自海德格尔“莱布尼茨讲座”中对“meta-”的解读。。
道德法则作为纯粹实践理性法则,其“超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先验的自由”超越了知性的综合统一功能;第二,“实践的自由”的超越性体现为对于欲求、偏好等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首先体现为对于欲求等的否定性。前者在于对“无条件的绝对总体性”[6]的追求,后者试图体现出“善良意志”的无限制性。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将“实践”完全限定在“道德”的含义上,因此,道德意义上的实践可以看做是康德对实践的最终的界定。
从上面的论述中,在康德哲学内部,若存在着“优先性”问题,也不存在于“理论理性”和“思辨理性”之间,因为康德在该节否定了这样的优先关系。因此,理性就其自身来讲被一分为二,尽管在思辨理性中起着综合的功能,但在实践理性中起着主宰欲求、偏好等的功能。前面提及,从兴趣(或关切)方面来讲,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各自紧守住自己的疆域即可。相反,真正的优先性问题存在于对一般实践理性的划分,即“纯粹实践理性”和不纯粹的实践理性之间,它们大致相当于罗尔斯对合理性(reasonableness)和理性(rationality)之间的区分,因为,前者具有绝对性、具有对欲求和偏好的拒斥性以及对道德法则的奠基。
因此,在与理论理性相较的具有优先性的实践理性是无意义的,只要我们暂时不去考虑康德复杂的目的论。康德并不是做出某种论证,而只是在做出相应的解释。尽管在“至善”概念所包含的道德与幸福的两重要素中,理性对于整体和绝对的追求并没有停止。
四、结语
纯粹实践理性的优先性试图为至善理论提供前提,但从康德整个哲学来看,这一优先性并不体现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相反,这一优先性关系体现在广义上的康德实践哲学之中,即存在于纯粹的实践理性和一般的实践理性之间。当然,这一论证的依据主要仰赖康德的“兴趣”(关切)理论。如若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至善论作为某种类型的道德目的论,似乎仅仅规定着实践理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存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优先性的问题。因此,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这一节的提出的优先性命题只是在解释的意义上来讲的,而不是在论证。由此,可以看出康德并不愿意走上所谓“德国观念论”(康德被称为“先验观念论”)的道路,但令人感兴趣的是,康德为什么没有走上“费希特-黑格尔式”的道路,尽管康德也特别看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