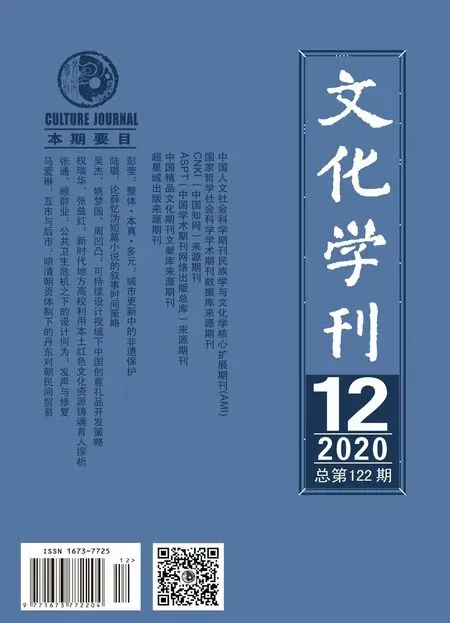东北工业文明视野中的“新人”形塑
——以“新东北作家群”作品为例
武兆雨
“新人”似乎是一个无法彻底厘清的术语,其内涵与外延处在不断丰富、延展的过程中。每一个历史时期、甚至每一个历史时刻都会产生新人,其形象及意义也随之产生变化。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人”区别于马克思所说的“新人”,也区别于梁启超的“新民”,它是根植于共和国文化土壤之上的,是共和国的文化根基。如果说,“‘新人’和国家都是现实中的政治性存在,都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创造历史”[1]15,那么,“新东北作家群”笔下的诸种形象,都是共和国的“新人”。当然,如果是简单地如此对等照应,无疑是将“新人”泛化了。“新人”需要有一种区别于其他人物形象的特质,是“自由的观念,人的尊严和平等,民主的观念,创造和对幸福的追求”[1]16。将之投射在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的作品之中,我们能够在其中捕捉到,曾经共和国工业建设的生力军、构建国家现代化历史的一代工人阶级,以个体/群体的牺牲,配合共和国的发展和转向。他们在东北工业由盛转衰、渐为废墟的历史进程中,坚韧地创造新的生活,追求个体的尊严。而这些追求的外部动作和内在动力则是工人阶级所特有的当代工业精神的产物。
一、“新人”的历史承担
无疑,东北地区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经历了群体性的高光时刻。工人阶级对自我及所属群体有一种深刻的身份自觉,阶级属性为他们的精神注入了历史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因此,我们发现,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转向,工人阶级默默承担了身份与生活的位移,尤其是在“子一代”的视角下,这种书写便被赋予了更大的真实性。下岗工人的牺牲是自觉的,他们的历史承担与责任感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阶级精神。当然,在牺牲奉献之中,这一代工人阶级有面对新生活的惶惑不安和举步维艰。但是,阶级和群体属性,共和国建设者的使命使得他们迸发出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和“自助者天助”的豪迈。下岗之后,工人们为自己找到了新的职业,摆摊、拉车、卖古董、跳大神,他们失却了荣光,却以这种自我牺牲的形式,为整个工人群体获得了新的社会价值所在,以退潮的形式为现代化建设继续贡献些微的力量。牺牲奉献等诸多集体性精神的呈现,或可以说是东北工业文明视野中“新人”的重要质素。在更深远的意义上,这些精神内涵、性格质素,不仅对照的是20世纪90年代一代人的历史,它更多指涉的是未来。正如班宇所言:“我觉得一个作品在此刻能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怀旧,而是它其中一定展现了某种未来性”[2]。正是因为“未来性”,才使得经济转轨时期的东北工人阶级获得了“新人”的意义。
在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家的笔下,工人阶级的自我牺牲和奉献是一种默然的悲壮,很难在他们的叙写中看到工人们阻挠历史发展的群体性动作,也没有过多关切面对生活错动时,那些片刻的痛彻、凌厉的体验。“子一代”视角所提供的是,父辈们默默地、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变化。那些轻描淡写的“下岗”经验,包含着未被“子一代”所注意到的内在体验,是一个极为漫长的、痛苦的、压抑的自我消化的过程,折射出工人阶级群体的隐忍和承担。可以说,“大厂”的落幕,分解为一个个以人为单位的小因子,落幕的痛感也分化到每一个人身上,最终被个人所消化。这意味着,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北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变革所带来的“阵痛”,是由工人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所缓释和分解的。其中的责任感、历史感、伟大感和悲壮感,是这些“新人”的精神内面,也是当代人所苦苦追寻的能够超越历史而前行的力量。
二、“新人”的精神自觉
“新东北作家群”笔下的下岗工人群体是时代的落水者、困厄者,社会位置和生存境遇的改变,这些人在自我牺牲、自我消化的基础上,苦苦挣扎求存。但是,对个体发展的渴望、对个体尊严的追求,时而在压抑的空间中迸发而出,折射出工人群体超越了社会和阶级的内在的精神自觉。这种自觉,是“新人”之所以为新的另一种精神内涵。
我认为,东北工业地域视野中的“新人”,其个体发展的渴望、尊严的追求转化到实践中,表现为学习力、想象力和创造力。通常情况下,“工人”这个概念所对应的词语是力量、劳动,是勇武、粗蛮。但是,在“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中,我们经常能够发现热爱读书的工人形象,他们努力地实现文化的更新、技术的更新。正如前文所言,“子一代”视角所自带的优势性叙述距离,使其书写具有极大真实性。因此,这些作品及其中的工人形象,为我们重新想象东北及东北的工业文明,提供了一种可能,这既对应过去也观照未来。东北是共和国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地区,工业化进程要依靠科学、技术、文化,这些因素也随之成为东北文明根基,尽管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被日益遮蔽。具有自觉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工业“新人”,作为东北文明的一分子被发现的同时,也意味着,东北工业和东北文明找到了一种复兴的路径。
在“新东北作家群”的书写中,东北的工人具有继续钻研和学习的能力与精神。《盘锦豹子》中孙旭亭所在的印刷厂,“进口”了一台机器,他和工友们“几乎每天住在厂里,四五个人废寝忘食地钻研,一起琢磨该如何组装这台庞然大物……后来又自费去了趟北京,住在地下室里,每天去北京印刷学院请教机电工程教授。”[3]14这里所展现和强调的,已经不只是这些工人的主人翁意识,而是面对未知的领域,这个群体积极的探索和求知精神。在此视域中,从“工人”到“教授”的联结,甚至是“东北”与“北京”的联结,是由知识、文化和共同创造的愿望实现的。《空中道路》的李承杰看“武侠”、看“历史”,看“《日瓦戈医生》”[3]122,设计“空中道路”;《飞行家》里的二姑夫制造降落伞;《走出格勒》中的父亲“晚上喜欢读武侠小说,还参加过厂里的征文比赛。”[4]这些动作,是学习、是发展自我、是创造新生活,是一代工人阶级通过科学、文化来展开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同时,他们又把这种精神自觉传递给“子一代”,即便是“无赖”般的人物,也有为了下一代读书而愤然自戕的行动,更不必说“新东北作家群”作品中那频繁出现的东拼西凑的9000元学费。因此,“父一代”与“子一代”在彼此的代际牵连中共同构成了东北文明的历史。
三、“新人”的同理共情
下岗的东北工人社会身份发生转换,其阶级身份所具有的彼此之间的共鸣,随之迁移至日常生活中,投射至道德情感层面。也就是说,工人下岗之后的相互关怀,不只来源于我们曾经同属一个集体的阶级情感,还来自这个离散的群体在广阔社会生活中的情感映射,这种惺惺相惜、彼此扶助,是人类共同命运视域下的情感伦理。“新人”能够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崇高的道德观念”[5],在“社会生活变化”中的东北工人群体,其中包含的是深切的悲悯感、道德感、崇高感,表现为同理与共情,这些质素也是“新人”为当代东北文化与文明延续的内在动力。
《逍遥游》中,“我”身患重病,父亲的老同学在路上偶遇父女二人,“掏出一张五十的,非要塞给许福明”[6]93,这个“条件一般”“给人打更”的老同学,直接又真诚地表达他的心意,还要“大家回头一起想想办法,帮助帮助你”[6]93。自身也处在困境中的个体,仍然要试图去帮助和拯救他人,这是人类情感中令人震颤的部分、最可宝贵的部分。《肃杀》中肖树彬用五十元钱“骗”走“我”父亲的摩托车,“我”和父亲许久之后“再次见到了肖树彬”,“他的面目复杂,衣着单薄,叼着烟的嘴不住地哆嗦着,而我爸的那辆摩托车停在一旁”,“我相信我和我爸都看见了这一幕,但谁都没有说话,也没有回望。”[3]69事实上,“我”和父亲的沉默以对,这种并不外现的、隐藏于父子二人内心世界的同情、悲悯或者惺惺相惜,是“父一代”与“子一代”的道德传承,是来自精神和灵魂的良善。或者,我们把这些困境中仍存有的关怀视为一面旗帜,它召唤的是一个由无数“父亲”和“我”构成的群体,这个群体在彼此共情和呼应中产生强大的力量,奔向前方。正如《肃杀》所书,“所有的沈阳人都是兄弟姐妹,肩并肩手拉手站在你的身旁。”[3]70一群陌生人唱起同一首歌,其中包含的已不仅是对于一个球队胜利的向往,他们唱出的更是具有共同文明背景、生活经验的无数个体彼此扶助、共向未来的信念。这些书写意味着对于沈阳,甚至对于东北而言,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共同的情感联系,它既是基于社会的、伦理的,更是基于人情的、人性的。在这个意义上,东北的文明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存在的,那些在阶级意义上自我消化、自我承担的个体,又以一种内在联系的方式统合在一起,构成了东北文明的另一重根基。
王德威说,“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们带来奇妙的启悟契机。走出无物之阵,他们是‘报信者’。”[7]或许,对于东北而言,“新东北作家群”所书写的20世纪90年代的“父一代”是一种再生的“信号”,这些下岗的工人形象中所包含的历史承担、精神自觉和同理共情能力,是共和国“新人”所应具备的意涵。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工人群体便是东北工业和东北文明的复兴的“报信者”。
——以广西高校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