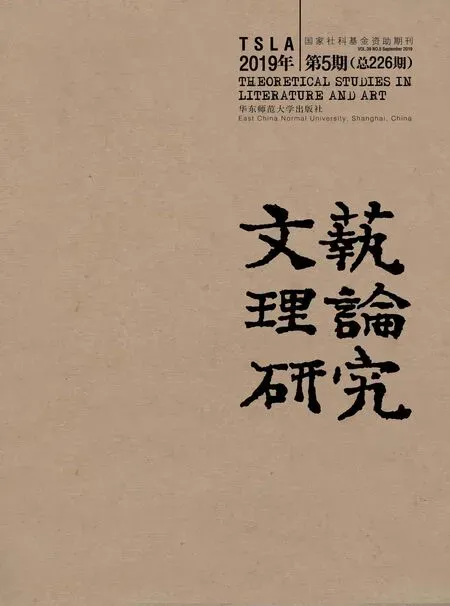“生态正义”何以可能: 两种形而上学辩护
赵 卿
引 言
随着环境美学、生态美学以及生态哲学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对自然本身问题的研究价值也愈发重视。自日裔美籍环境美学家齐藤百合子提出“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的命题以来,这一研究旨趣更加得以凸显与强化。然而,如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以接近自然、贴近自然,对这一问题进行认识论上的思考却显得相对薄弱。这无疑导致了生态美学的学理基础不够稳固。鉴于此,本文选取以阿多诺和石涛为代表的两种典型自然观,分别呈现西方反思形而上学与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论思路径。前者从社会意义上来思考形而上学,欲使形而上学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框架内得以复兴,从而实现主体和对象、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和解。后者基于中国传统自然环境审美体验中深厚的“道”“玄”成分,在本体意义上展现人与自然的相合。
“生态正义”的核心在于如何破除人类中心主义,这直接影响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具体过程与程序,也就是说,在人与自然的交流过程中,重点在于如何突破主体论立场。因此,为了确保对自然进行“如其本然地欣赏”,对主客体关系进行一番“生态正义”地讨论成为一种必然。因此,本文选择“生态正义”这一观念作为切入点,通过阐发中西上述两种典型的自然观,尝试为生态美学奠定一个认识论基础。
一、 “生态正义”观念的引入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生态正义”(ecological justice)与“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并未得到海内外学人的区别对待。“生态正义”被普遍理解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实现“生态正义”,就意味着追求这样一个理念: 即社会各阶层公平地享受环境资源、公平承担环境责任和义务的理念。但近些年来,随着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研究的深入,学界对相关话语的适用范围与概念界定有了更具精确性的要求。“生态正义”以一定特殊性的立场指向了对非人类世界的正义问题的关注。可以看到,它相较“环境正义”呈现出的内在差异:“生态正义”从“环境正义”内部分化出来,其意义在于超越后者关注差异性主体对于环境权利的分配正义的实质,将视点从聚焦人类共同体内部的社会正义扩展到对非人类世界的生态正义。显然,二者基于正义理念呈现出对不同视域的论说:“一个是在人类之间分配环境的正义,另一个是人类与自然界其他物质关系上的正义。”(Law2)在这方面,加拿大环境政治学家戴维·施洛斯贝格(David Schlosberg)清晰地认识到“生态正义”超逸出“环境正义”的论域范围,他认为,虽然“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对“正义”的理解有相似之处,但二者研究对象各有侧重:“环境正义”指向人类社群内的环境问题,比如资源的分配、食物安全等;“生态正义”指向非人类世界,关注人类社群与人类之外自然界的关系。根据施洛斯贝格的理解,界定“生态正义”应该注意两方面内容: 首先,它的正义对象包含了非人类世界的自然,将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生命的生态系统,人类应该对自然持有尊重态度;其次,它的立论基于人与自然二者的关系,体现为一种关系性思维,也就是弃除人类中心主义的、人与自然互为主体的关系性思考。显然,关系性思维,是生态学、生态哲学的主导性思维方式,与生态美学所倡导的“生态审美方式”也完全吻合一致。本文采纳施洛斯贝格对生态正义涵义的界定,认为它的论域范围涵纳对于地球生物圈所有成员的公正。
但是,如果生态正义指涉的是地球所有的生命体,也就是包括并无自由意志和言语能力的动物甚至植物,那么实现生态正义何以可能?在施洛斯贝格看来,只有代自然立言,才能够实践生态正义。施洛斯贝格列举了环境政治学家布赖恩·巴克斯特(Brian Baxter)、罗依·埃克斯利(Robyn Eckersley)等人对于“做自然之代理者”的实践设想,并得出结论说:“像代理者一样为自然言说,已成为环境运动中日益发展起来的一个手段。为非人类自然做代表,能够以科学、故事讲述或者传统知识为基础。人们能够‘代表’动物或者非人类自然,想象和故事讲述能够起一定作用,以及传统的或者民族知识也能被利用——它们都是通过对来自自然界的信号的敞开而使用的知识形式。代理已然成为自由决策制定中所普遍适用的,就像那些为幼童或囚犯的权利做代表一样。”(194—95)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来可泓,《论语直解》493)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今注今译》650)。万物以静默如斯的方式在言说,但是我们听而不闻。我们似乎很难把握非人类自然的客观意图,我们没有合适的渠道了解到非人类自然在与人类互动的时候,它究竟是悲是喜,是赞成还是反对。施洛斯贝格提出的自然之代理,乃是我们假想自己可以代替自然传递信息。但是,以科学、故事讲述或者传统知识的形式来为自然代言,其为非人类自然代言的合法性或者正当性从何而来呢?因为如上所述,非人类自然看起来是没有表征能力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能够成为它的如其所是的代言人呢?
生态正义的理想只能从消极的方面来想象自然之代理的可能性,正如巴克斯特直言不讳地说,为非人类世界代言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愿望,它在构想上是可行的,但何以具体发挥实际效用则有不可避免的困难:“原则上,承认一些人类具有为非人类世界代言的资格和诚意,至少是没有困难的。但以任何特殊立场使一个既定个人或群体明确满足这些要求则是困难的[……]”(Baxter83)。原因很明显,即现实一直都明白为自然代言的敌人就是作为有自我利益观念的人类自身,于是,要对付这个局面,最引人注目的方法,就是试图走通一条“必由之路”:“理想的情况是,在争论的特别结果中,作为代言人那些关切自身本质的利益应该是离场的。”(Baxter83)也就是去主体化,即在代言自然过程中,最大限度地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换言之,如果我们试图真的去聆听自然之音,我们就必须澄怀观道,摒弃人类自己的主观意志。从表面上看,人类在替自然代言,实际上人类要非常谦卑地让自然的精神能够照耀到我们身上。我们的代言可能是错误的,我们的理解也可能是不够准确的,但是我们需要克服人类躁动盲目的欲望和意志,经过多次实践,经过坚忍不拔的长期努力,才能或多或少逐渐理解一点自然之音、自然形象向我们呈现出来的真理之光。

二、 阿多诺的生态神学观

阿多诺意识到要试图实现对存在之物本身的理解,就要认清这个困扰所有现代本体论思想的基本矛盾:“用以获取超主观性存在的手段无外还是那个主观理性,即早先确立了批判的唯心主义结构的主观理性。”(Adorno,“The Idea”254)他认为,若要实现对存在者的真正所是进行追问,其可能的方式是转变传统观察问题的方式,即“存在者不是呈现为有意义,而是无意义。”(255)而无意义,实质上是对主观理性的挣脱,因为按照阿多诺的说法“意义本身其实已经被主观性所设定了。”(254)因此,他必须要借助一个超越主体理性的路径,实现对存在之物的真正救赎。那么,我们就可以感到,为何神学成为阿多诺思想体系中重要的构成部分: 他以神的超越性,救赎工具理性所呈现出的那个僵化的、被主体理性同一化的自然,以表现自然的“非同一性”特质。这个特质的经验获得不能依靠理性,因为理性是为人类自己的存在秩序提供保障。显而易见,若依赖这种理性的认识方式去理解自然是不合理的。相比之下,神的介入,使人类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以及自然具有的无限超越性。按照神学教义,人类与自然本就是上帝或上帝之灵的创造物,神学思想家卡尔·巴特就此作了说明:“不论在旧约中,还是在新约中,上帝的灵,即圣灵,通常就是上帝自身,以致不可理解,在这方面丝毫不逊于上帝,他可以临到万物,并且由于他的这一临在,能影响到被造万物同他自身的关系,而且由于同他自身的这一关系,他给被造万物以生命。被造物需要创造主,以便能够生存。”(莫尔特曼19)这意味着,上帝不仅创造了人类,也创造了自然。在这一神圣创造的行为中,人类与自然都来自上帝所赋予的“神圣的荣耀”。阿多诺利用神学对自然的“圣化”,是要实现对自然存在本身的深意的追问。
那么,阿多诺如何借助神学抑制人的主体理性,如何变相达到“去主体化”境界?答案是,他将自然存在提升到上帝存在的高度,由于神是不可知的、超越的,因此自然也具有同样的特征。然而,人的主体理性,即同一性思维是无法认识“不可知”的神的,因此在阿多诺看来,只有对自然的非同一性的体验才是对自然的体验,而非同一性思维的形成也是突破人的主体理性的过程。
阿多诺借助神学特质,使自然脱离主体理性把握之物,成为了具有超越主观性的上帝之物,即一个犹如上帝一般的无条件之物。这样,自然与人类的疏离感获得弥合。可以感到,在与神学的相互反应中,自然散发出自身的“光晕”,也就是一种谜状特质,同时人类舍弃自身的“固执”与“偏见”走入自然之光,与自然发生“平等”的互通交流。借用当代西方新教神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莫尔特曼所用的“团契”概念可以形容这种“交融”状态: 将自然恢复到上帝创造物的这一原始传统,上帝创造的自然与人类不再是被支配与支配关系,而成为参与性的“团契”关系。“团契”源自《圣经》中的“相交”一词,是指伙伴关系,意思为相互交往和建立关系,指向上帝与人之间的相交和基督徒之间相交的亲密关系。对此而言,“团契”不单指向上帝与人的交流性、参与性,同时将自然扩展为交往对象,赋予它与人类相交的亲密关系。因此,“团契”使世界与上帝具有了彼此圆融的价值基础: 由于上帝之灵的灌入,它使上帝存在于世界中,世界也存在于上帝中。从而,自然被提升到上帝存在的地位。这样,自然与人类具有了亲密的关系,为向彼此开放提供了前提。

阿多诺大致上将神学的宗教信仰等同于神话,而神话又被他理解为“试图使自然事件合理化和理解的原始例子”(Brittain23)。那么,人类若要获得与世界的交流,就要借助神的超越性向自然开放。并且,向世界的开放性要以上帝中心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理解人向世界开放的意义。原因是,若脱离对上帝问题的探讨,人超越世界的使命便无法理解。这就是说,对世界的无限开放性只产生于人超越世界的使命中,这一使命却来自于上帝赋予我们的能力: 人类要超越每一种体验,对一种既定的境遇,不断地向外开放;同时,人类的开放最终要超越世界,实现上帝代言人的形而上追求。因此,人类既是上帝的创造物也是他的形象,又像上帝一样拥有面向世界的开放性:“作为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和全权代表,人类对作为生物的全部环境的完美典型的世界开放。”(莫尔特曼210)在开放的过程中,人类的感官体验一直与世界、自然进行互动,使人类能够不断地获得新体验。而对现实做出确切回答的可能性,也几乎是在无限制的变化着。在这样一种自然美的体验中,我们无法以有限的语言去描述,它逃离了理性的管束,无法被有限的规定与概念所获取。在阿多诺的观念语境中,他意识到自然美的超越性,我们只能在自然美面前保持沉默,然而活泼的交往体验依然还在继续。
否定辩证法作为能够接近自然本身的分析模式,打击的是主体理性施加于自然的暴力,从而使自然的真理之光显现出来,所以阿多诺坚定地认为,“等候在客体本身中的东西需要这种介入来说话。”(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29)实际上,否定辩证法指向的正是神学的超越性,引导我们进入与自然相通的“同一”境界,去聆听自然的声音。可以说,当我们以神学视角体验自然时,发生的是与世界不断交流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人类世界向自然世界开放的过程,即一种向“去主体化”的进程: 在这种交流与开放过程中,人类与世界形成了“寄居”“参与”“持续”“陪伴”“交融”等生态的共生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阿多诺神学思想具有生态属性。但这并不等于说,阿多诺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具有同一性身份的不同存在去体验与认识,相反,他认为这是一种“类神秘主义”(Cook123)。尽管阿多诺也阐释自然的生态问题,但与其他生态哲学家美学家不同的是,他认为“人类与非人自然之间的和解不需要‘所有的身份都被归入一个整体,一个概念,一个完整的社会’。相反,真正实现的身份需要‘非同一性意识’,以及‘和解的非同一性的创造’。”(Cook131-32)这就使阿多诺对自然的论述更具有现实主义意味。显然,这意味着一场意义深远的主客观念的认知革命。
因此,借助于上述共生关系,在神学中自然与人达到了交流的平等性。可以推论,阿多诺在神学中论证新的主客关系达到了某种“去主体化”的效果。神学家克里斯托弗·克雷格·布里坦写到:“用当代的话讲,否定辩证法的核心是对一种被称为去主体化问题的突出关注。传统上经常强调这样一种观念: 通过与神的交遇,自我对自己重要性与权利的主张将受到猛烈的动摇,随之其知识精确地捕捉到神的充分的真理。否定神学尤其主张: 通过一种否定的路径,主体可以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精神变革。”(Brittain92)于是,对阿多诺来说,“证明否定神学最终是要证实: 在一个具有绝对同一性的神圣存在中主体与客体最终的同一性”(Brittain93)。显然,神作为一种公正化和正义化的思想信念才被阿多诺拉拢过来。换言之,神作为一面象征旗帜,它的出场首先具有反对主体化暴力的功能性意义,至于其本身的实体性内容至少一开始不是阿多诺所关心的。
三、 石涛:“我为山川代言”
“我为山川代言”命题是以何种思路彰显“去主体化”立场的呢?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石涛的有关论述。石涛曾经在《苦瓜和尚画语录》中揭示了“我”与“山川”的“代言”关系。他说:“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俞剑华63)。从行动本身看,山川是“被代言者”,“画家”作为代言者与山川形成了“代言”关系。何为“代言”之意?可以参照《现代汉语词典》对“代理”与“代言人”两个词条给出的解释: 前者指“受当事人委托,代表他进行某种活动。”(240)后者指的是“代表某方面(阶级、集团等)发表言论的人。”(241)不难感到,这两个词的“代”字,其意思是一样的,皆指主体不出场的情况下的替代性行动。由此,可以这样说,因为“代”理,所以山川势必会丧失其主体性地位。显然,如果停留在“代理”字面意义,强调“代理”二字,这个说法会被施予浓厚的人类主体论色彩:“我”的主体维度得到突出,意味着“我”作为被强调的主体,对方的事情由“我”来代理,由“我”来负责,但对方出场的必要性却被“我”消解了。不容否认,这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即自然的退场。但这完全不符合石涛的本意。石涛之意是让作为代言人的人类山川化,自然化,使山川的主体性地位得以重返。
由此,可以论述这样一个问题: 我作为人类,如何可以使自己山川化?石涛给出了独特的解答。从望文生义的角度看,“代言”命题的确表达了“我替山川做主”的“代言”关系,但是,作为对这一命题的理论解读,它所强调的主体则是相反:“山川”。在“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中,山川才是被强调的真正的主体,我代山川而言,是受山川之命,而忠于山川之事。当石涛说到“予”的时候,已经是自然化与山川化的“予”。可以说,“代言”命题其实表达的是“山川即我”思想。我即山川,意味着我就是山川,这与“我为山川代言”字面之意是不同的。“我就是山川”,反映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思想,庄子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今注今译》88),表明中国古代思想认为万物与人本为一体,因此不难理解在天人合一思想中,“物我两忘”也成为可能:“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今注今译》366)在忘己的境界中,作为主体的人已经超越了自身有限的存在,融入到天地流转的大化运行中,这时人与万物为一体,所以宋代苏轼在讨论画家身处山水之间的状态时讲到:“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苏轼59)因此,在古人眼中,自然并不是我的对象和客体,而是能够与我“物我为一”的存在: 物我为一,不存在主客体的差异,同一性暴力也自然会消失。此外,“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还有另一层意思: 山川役使我描摹它,山川甚至是主体。当然,山川不可能是真正的主体,但这里面排除人类主体性的立场昭然若揭。显然,在排除主体性问题上,石涛开出的路径是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立场。也就是说,“代言”命题论述的重点并非是“我替山川代言”,而是“予即山川”,这正是天人合一的理论视野在画论上的落实。
与阿多诺解决去主体化的路径类似,石涛的论述首先还是彰显一种思想的形而上学性,即上文提到的那些反映“物我为一”“齐物论”等天人合一性质的思想。显然,石涛视野所呈现的,是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一贯的立场与意识,是一种直指本源、本体的认识方式。然而,与阿多诺不同,石涛对“人”这个主体意识并不“反感”,但却巧妙地产生了“去”主体化的效果。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石涛是如何解决的?
这里援引巫鸿的相关思考。巫鸿以石涛的《黄山八盛》图册为例讨论了这位画家眼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文殊院》这页能够深入石涛思想最本质东西,通过分析画中景致安排与题字,巫鸿指出:“石涛把自己表现成一个微缩版的‘黄山之主’。”(261)画面是这样表现的: 在中心部位,有形如侧面的山石巨人,在其脚下又绘有一位微小的现实旅者。但在这里,他与山石巨人的角度与姿势完全相同。并且,在石人旁边写有一诗:“玉骨冰心,铁石为人。黄山之主,轩辕之臣。”(巫鸿261)巫鸿将之视为石涛所设的“画谜”。他认为,“画谜”的谜底是“这次登黄山对石涛来说绝非简单的旅游观光,而是一个寻访历史、精神升华的过程。当他在岩石之间看到‘黄山之主,轩辕之臣’的遗迹,他所感到的是一种深刻的古、今相遇,也就成为了这幅画的主题”(261—62)。这一解答是合理的。一方面,石涛如此安排主题,呈现人对自然“有意为之”的“模仿姿态”,并非是张扬形态上的“模仿与被模仿”,而是彰显彼此内在精神的“相合齐一”。另一方面,根据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思想,天人合一观念在中国艺术,特别是山水画艺术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即通过山水的描摹,呈现点景人物与天地交合的精神气质。其深意是,人已经超越有限的自身,实现了与天地自然之无限宇宙的相互感通。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石涛甚至可以以自然的合法代言人的身份自我期许,以此将“我”视为自然的“缩小版”。可以说,此时的“我”已不再是自我意义上有限的“我”了,而是具有某种超越个体精神、与天地相遇的“大我”。石涛言语中“自然化的“予”便是如此。这种“自然化的“予”实则是中国艺术表述“去主体化”意涵的别称。
在石涛看来,自然化的“予”是这样的一个主体:“予”来自于“天地生产”,而非“社会生产”。它来自于本源力量的生成,故石涛以“脱胎”来形容它,意指人本身就孕育于天地母体之中,由自然孕化而成。人生于自然,由此,在某些程度上与自然心性相通。这就意味着,在终极的存在场域中,物我本为一,并不存在主客体的差异。他讲到:“此予五十年前未脱胎于山川也;亦非糟粕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俞剑华63)。石涛列出“予”与自然在相处中所出现的两种关系的对峙: 一种是自然与“我”被认为有主客体差异并处于二分状态,这主要受制于“未脱胎”状态;一种是自然与“我”被认为主客体无分并处于合一状态,这主要来自于“脱胎”状态。两种关系的对峙典型地表现为主客体之割裂与差异之取消与否,亦即人“自私”与“无私”的区隔;或理解为对主观维度的强调与否。前者坚持人类自身的主体立场,与之相对,后者采用的是接近自然本身的去主体化立场。
这种区隔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独特的论述模式,并有较为统一的价值导向。接近自然、成为自然的“予”被视为“圣人”“贤者”,反之,则需要以“涤除玄鉴”方式或澄明的心境去修炼之、体验之。两条思想主线大致无他。具体来说,从主体角度立论,提倡“人与天地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人生境界(《庄子今注今译》88);从自然角度立论,秉承“自然为体,人事为用”(俞剑华292)的行动原则;而对山水画艺术来说,则要达到“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唐岱105)的画境。显而易见,“人”作为一种主体,在中国传统思想语境中,其存在与天地自然在本然上是不可分割的,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哲人或艺术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由此,不难看出,在中国形而上思想预设中,人被赋予了为自然“代言”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与阿多诺所批判的主体理性不同,前者提出“代言”思想,真正的意义在于它认为人自身就是“自然”身份,这时的“予”不是与世界区隔化的独立存在,而是深嵌于整个世界生命图景中的一部分,彼此“生生相息”: 山川即我,我就是山川。
基于此,“我”具有了“如其本然”地认识与欣赏自然的可能。由此,为了真正的展开“代言”行动,自然成为“我”聆听的主体,我成为自然忠实的“聆听者”。可以想见,尽管自然是无音的,但我们可以辨识出它的声音,理解它的声音,让它呈现出来,让它进入我这里,然后理解它自身,品味它自身。这就为人类“公正”地理解自然提供了可能。困扰当代环境理论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去排除人的主体性,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而解决人与非人类的自然事物之间的“主体间性”也成为哲学美学的难题。鉴于此,石涛的“代言”命题的价值在于它直接取消了自然与人二者之间的断裂状态,使自然与人从本源上相合为“一”。
结 语
以阿多诺与石涛为代表的中西方认识自然的观念,呈现出彼此处理主客关系问题时两种不同的思考路径。也许可以得出结论: 尽管思考路径不同,但是为生态正义所进行的认识论辩护在这样的意义上却殊途同归: 人类不是唯一的主体,自然也具有“主体性”,然而为了认识自然,人类要突破自身中心主义视域。这样,自然作为一个“主体”,其本然的样态才能被人类洞察与把捉。由此,这为实现生态民主、生态平等提供了可能。从而,在另一方面我也可以初步指出,两种自然观反映了对人类精神的两种不同要求,即两种观察世界的独特观点。
以石涛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形而上学认为,自然源自天地宇宙的“自化”:“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庄子今注今译》492—93)“自化”即表明万物的天然自发之状态。这一观念隐含了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万物都是独立平等的思想,它从一开始就规避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优越感,“涤除玄鉴”“以道观之”等古代思想无不教导人类要从世俗化的一己小我成为宇宙大我,徐复观先生说:“个人精神的自由解放,同时即涵盖宇宙万物的自由解放。此一要求,乃贯穿于《庄子》全书之中。虽然只是精神的,但若对现实的奴性世界而言,当然能发生批判、提撕的作用。”(徐复观356)因此,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与人类对自然本身的认识活动并不矛盾。相反,随着人类精神的升华,自然认识也更加深刻。可以说,人与自然始终保持在一种“亲和”状态中,而“无”便是人与自然亲和关系达到的终极状态:“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今注今译》20)“无我”并不是我在自然中的离场,而是在场的一种终极表达,恰如“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一般。如此,在“无我”状态中,人类与自然实现了天人合一,自然也能够以如其所在,如其所是的方式被人类所接近。那么,便可顺理成章地说,“无我”成为中国古人看待自身、观察世界的一种人生态度与人生理想。
相反,阿多诺的自然观更多充斥着对人这一主体精神的批判与否定。在他看来,人类的主体理性毁掉了自然的独特性,自然与精神始终处于一种对峙与紧张的状态。这导致他的思辨理路和石涛主动与自然弥合的态势不同。为了表明自然并不是人类主体理性可以随意施暴的对象,阿多诺将自然观基建于神学之上,赋予自然以神性的光辉,目的是让人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以及对自然神性的“僭越”: 自然不是人类能够掌控的物质世界,而是具有神性的“存在的永恒之物的结构。”(Hullot-Kentor236)这就可以解释,为何阿多诺对尤利西斯之旅充满着否定与讽刺,尽管尤利西斯以“无人”之诡计逃脱了独眼兽的猎杀,但他却取消了象征自身独特性的第一自然,进入了具有同一性特质的第二自然。“无人”意味着自然存在特异性的最终丧失,由此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亲和性”便成了讽刺。阿多诺主张要取消它:“在启蒙辩证法中,尤利西斯之旅,是第二自然内在性的生产。尤利西斯的自我在此航程中得到发展,是通过变成它所掌控的(东西),而同时它又消解自己与对象之间的亲和。”(Hullot-Kentor236)然而,在化解亲和关系后,精神与自然不再同一,自然才成为自然自身: 主体理性撤离,自然得以显现自身。神作为至高的存在,人类只能信仰它却不能认识它,只有人类直面神的不可超越性,人类中心主义的优越感才有可能得到抑制,换之以谦恭地姿态去拥抱自然,使自然获得救赎。
可以看出,尽管二人的思想有着相同的“去主体化”倾向,但是他们之间的内在理路的确存在不同,甚至有些冲突与矛盾。那么,如何化解这些冲突和矛盾,文章认为应该对此有一个本体论上的深刻认识。比较起来,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所体现的本体论,侧重的是万物一体,并指向主体与万物在根本上具有“同一”的可能性;而阿多诺言及本体论,其实质仍是为了处理自然存在与主体存在的“非同一性”,他认为万物在本质上就是斑杂多样的。阿多诺的本体论被称为新本体论,是为了捍卫自然存在本身,以“彻底地阐明自然要素与历史要素之间不可超越的相互交错性。”(Adorno,“The Idea”260)神学、神话都是阿多诺挪用来以压制理性的思想武器。正如斯塔莱·芬克所说:“阿多诺对认识论的元批判,既不能在经典的本体论意义上也不能在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意义上来理解,因为它的目标在于避免同一性,贴近特殊性。”(Finke107)
最后,需注意的是,本文指出的这两种认识路径仅仅作为生态正义可能实现的两种参考方案,并未抹杀其它认识路径的可能性。
注释[Notes]
① 美籍日裔环境美学家齐藤百合子在《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一文中,首先明确提出了“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这一思想,指出环境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把自然当作自然自身来欣赏。她的研究主要基建于美国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立场,但仍未完全解决如何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这个核心问题。参见Yuriko Saito, “Appreciating Nature on its Own Terms,”Environmental
Ethics
20.2(1998): 135-49.② 施洛斯贝格敏锐地观察到生态正义与环境正义二者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他认为并不能完全以环境正义中的相关话语去研究人类影响之外的自然世界: 包括动物个体、群落以及自然系统等。他试图突破仅仅对环境正义有效的理论话语去探索生态正义理论的潜在可能,比如超越环境正义既有的理论话语,去探索能够包含个体动物、群落与自然体系的各种话语、概念与框架模式。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之间具有的关联性。David Schlosberg.Defin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ories
,Movements
,and
N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6.③ 中国古代山水画论最精深、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它那丰富的技法学说,而是它的如下艺术美学原理: 以笔墨描绘山水的方式去体认中国古代天地意识。清人唐岱在《绘事发微》中提出的“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命题,正是对笔墨与天地二者关系的集中概括。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dorno, Theodor W.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B. Asht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3.
- - -. “The Idea of Natural-History.”Things
Beyond
Resemblance
:on
Theodor
W
.Adorno
. Ed. Rorbet Hullot-kent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Adorno, Theodor W., and Walter Benjamin.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1928-1940
. Ed. Henri Lonitz. Trans. Nicholas Walk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Baxter, Brian.A
Theory
of
Ecological
Justice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Brittain, Christopher Craig.Adorno
and
Theology
. London: T&T Clark International, 2010.陈鼓应注译: 《庄子今注今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年。
[Chen, Guying, ed.Annot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Chuang-Tz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7.]Cook, Deborah.Adorno
on
Nature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Finke, Stale. “Between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Theodor
Adorno
:Key
Concepts
. Ed. Deborah Coo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77-97.Hullot-kentor, Rorbet.Things
Beyond
Resemble
on
Theodor
W
.Adorno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年。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d.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来可泓编: 《论语直解》。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Lai, Kehong, ed.Analysi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1996.]Low, Nicholas, and Brendan Gleeson.Justice
,Society
and
Nature
:An
Exploration
of
Political
Ecology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于尔根·莫尔特曼: 《创造中的上帝: 生态创造论》,隗仁莲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Moltmann, Jurgen.God
in
Creation
. Trans. Kui Renlian,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Schlosberg, David.Defin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ories
,Movements
,and
Nature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苏轼: 《书李伯时山庄图后》,《东坡论画》,王其和校注。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
[Su, Shi. “Annotation toImage
of
Villa
of Li Boshi.”Theory
of
Dongpo
on
Painting
. Ed. Wang Qihe. Jinan: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2012.]唐岱: 《绘事发微》,周远斌注释。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
[Tang, Dai.Insight
on
Painting
. Ed. Zhou Yuanbin. Jinan: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2011.]巫鸿: 《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Wu, Hong.The
Art
of
Ancient
China
in
the
Global
Perspective
.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7.]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Xu, Fuguan.History
of
Chinese
Perception
of
Human
Nature
.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1.]俞剑华: 《中国古代画论精读》。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
[Yu, Jianhua.Theories
of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
. Beiji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