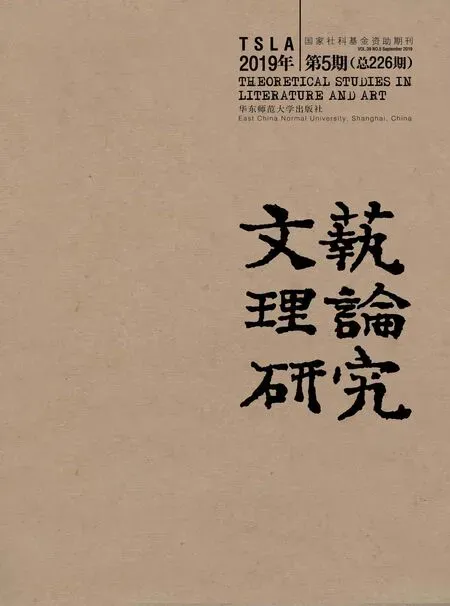中医、西医与病人
——中西医论战下的疫病书写
邓小燕
一、 陈大悲的“倒戈”
1923年3月陈大悲染上猩红热,辗转首善医院、同仁医院,经历死生危机。待熬过难关后,他在《晨报副刊》上发泄了一腔不满,并为拒绝采用冰枕降温而庆幸:“冰枕头可真是可怕,或者比猩红热本身更危险呢!我幸而没有用”(陈大悲3)。但这文章显然不合时宜,因为“科玄论战”已拉开帷幕。这场论战无关“科玄”孰是孰非,而关乎科学的适用范围,可以说“科学”才是论战各方的共识。陈大悲显然触犯了这“共识”。首先是遭到了孙伏园的批判,孙敏锐地将“冰枕头”纳入中西医论战背景下:
[……]我并不知道医学,我也决不配为“冰枕头”辩护,不过大悲先生所谓必不可用,一定是犯了太粗率的毛病,我希望有医学知识的学者应该来一个简单的说明。不仅冰枕头一项,其他西医方面的有些设备,每每能引起没有医学常识的病人的怀疑,似乎也该在通俗的出版上当有这一类的解释。
[……]
反对“冰枕头”的一类论调,如果确经证明为没有根据,那么也是迷信中医的意见的一种余毒了。(孙伏园4)
中医是反对冰枕的,章太炎说“冰囊却热,犯水潠之戒”(《章太炎全集·医论集》363),这也就是孙伏园所谓的中医“余毒”。孙伏园之后是西医朱企洛的批判,并且给出“忠告”:
大悲君不用冰而治愈,我已说过觉得很危险,他反当做庆幸,我觉得这个庆幸心尤其危险呢![……]那不是同大悲君改良社会的宗旨违背吗?(企洛4)

这件以陈大悲的沉默作结的争论,是中西医争战中不起眼的一段插曲,因为笼罩在“科玄之争”下,它很微妙地将一场形而上的学术论战简化为一场形而下的知识之争。在后来不少新知识分子笔下,中医或是与“新医”对立的“旧医”,或是与“科学医”对立的“玄学医”。作为一种身体技术,医学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但这种等级制度在近代却尤甚。如梁邵勤的文章题目就是《科学医与玄学医》,开头道:“现在医学界,凡属文明国,均由‘玄学’方面而进乎‘科学’方面,换言之,即由空理而演为实验矣,惟我中华,‘玄学医’之腕力,尚极坚固”(梁邵勤124)。周作人根据肯斯敦的《医学史》,也将中医归入“玄学医”(《周作人散文》卷五492)
在“中西医论战”与“科玄论战”的双重背景下,陈大悲的牢骚,显示出立场上的摇摆,成为新文化阵营中向“中医”倒戈的人物,因而遭遇了新文化阵营内部的整肃。
“中西医论战”是近代以来文化领域“新旧之争”的重要组成,而且波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久。1916年余云岫以《灵素商兑》挑起“医学革命”,1922年恽铁樵方以《群经见智录》作为回应,拉开了论战大幕。同年3月北洋政府颁布《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试图将中医纳入政府管理,直接激起中医界的反抗。之后围绕孙中山服用中药,梁启超“失肾案”,汪精卫推动废医等一系列公众事件,使各界对医学论战保持持续关注。到1929年“废止中医案”通过后,中医面临被废除的危险,中医界团结一致开展大规模救亡运动,中西医论战也进入一个新阶段。本文时间主要集中在新文学革命之后的几年,并以1926年为下限。
应该交代的是,本文集中于疫病书写,这与疫病问题进入公众视野也密切相关。西方殖民扩张极大地加速了世界范围的人口流通,也带来传染病的大流行。明代万历、崇祯以降,中国的疫病发生频次不断增长,至民国达于顶峰(余新忠等24—25)。民国时期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灾害疫灾占25%,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疫病高发期(余新忠等280)。民元以后,京、津等大城市一直有白喉、猩红热、伤寒等疫病,尤其是1918年世界范围的流感大流行造成约5000万人死亡的惨象。这些都引起公众对疫病的长期关注,并且促成兴起不久的细菌学的广泛传播。这严重的社会事实也被新文学家捕捉到,并造就了具有共同话语模式的一组文学创作,这些作品是考察新文学创作中启蒙主义与科学主义微妙张力的重要文本,这张力集中体现在“病人”身上。
在批评陈大悲的文章中,孙伏园承认“我并不知道医学”,且“从前有几次不由我自己做主,倒都被中医医好的”,但他仍断定陈为“没有医学常识的病人”,因为陈怀疑“西医方面的有些设备”(孙伏园4)。孙伏园似乎自相矛盾,却提出一个重要命题:“没有医学常识的病人”,算不得“合格”的病人。
如果陈大悲不是合格的“病人”,那么如何获得“病人合格证”就很值得讨论。在此便有必要重读菊英的故事。
二、 菊英的“顽抗”
发表于1925年的《菊英的出嫁》采用倒叙结构,末尾才叙及菊英生前的事,菊英吃喜酒回来,便觉得喉咙不适且起了白点,娘带她去看医生:
娘连忙喊了一只划船,带她到四里远的一个喉科医生那里去。医生的话,骇死了娘,他说这是白喉[……]医生要把一根明晃晃的东西拿到她的喉咙里去搽药,她怕,她闭着嘴不肯[……]最后,娘急得哭了[……]她依了娘的话,让医生搽了一次药。回来时,医生又给了一包吃的和漱的药。
第二天,她更加厉害了[……]一个邻居的来说,昨天的医生不大好,他是中医,这种病应该早点请西医。西医最好的办法是打药水针,只要病人在二十四点钟内不至于窒息,药水针便可保好。(王鲁彦139—40)
菊英到中医处治病,反倒“更加厉害了”,这时突然出现“一个邻居”,后来西医也回天乏术时,“邻居”又来了。“邻居”两次都是来推荐西医的,但他的身份却非常可疑——一方面,乡村愚昧之风盛行,乡民信仰土方、中医,还信仰香灰、灶君和高王经;另一方面,乡中却有明辨中西医优劣的“邻居”。并且这“邻居”在医疗行为中没有发挥实际效用,只是前来点出乡民的愚昧和中医的无能——这其实是流窜到舞台的“上帝视角”,也即王鲁彦本人——既然“中医”不行,“这种病应该早点请西医”,母亲不得不带着孩子去看西医,但菊英顽强地抗拒治疗,几天后菊英病入膏肓,“邻居又来了”,劝菊英娘去请西医来:
(医生)说不应该这样迟才去请他,现在须看今夜的十二点钟了,过了这一关便可放心。[……]她怕打针,几个人硬按住了她,医生便在她的屁股上打了一针,灌了一瓶药水进去。——但是,命运注定了,还有什么用处呢!咳,娘是该要这样可怜的!下半天,她的呼吸渐渐透不转来,就在夜间十一点钟[……]天呀!(王鲁彦144—45)
这无疑是现代小说中最为有力也最为沉痛的结尾了,联系小说中的“冥婚”,一句“天呀!”真有摧肝裂肺的力量——而毁灭的原因正是菊英的“顽抗”。
自鲁迅开始,王鲁彦便被视为“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然而作为王鲁彦代表作品的《菊英的出嫁》,其现代话语远多于乡土话语,乡土性仅存在于题材层面,且两种话语等级森严,带有强烈的“反乡土”色彩。菊英就诊地为首善医院,这与陈大悲就诊地同名,可见虽在写乡土,挥之不去的是作为参照系的大都市——“都市”“男性”“现代”“西医”具有先天正义性,“乡村”“女性”“传统”“中医”则有原罪——乡村虽好却疫病缠身,因而急需救治;中医虽名为医,治病时往往速其死亡;母亲、祖母的爱虽深切,但必须是愚昧无知的;菊英活泼可爱而且病弱,但其抗拒西医却异乎寻常地强而有力。对王鲁彦来说,菊英是非死不可的。
正如胡适在医学史家西格里斯(Henry E. Sigerist)《人与医学》的中译本序中所说:
我们至今还保存着的许多传统的信仰和习惯[……]到了危急的时候,我们也许勉强去进一个新式医院;然而我们的愚昧往往使我们不了解医生,不了解看护,不了解医院的规矩。老实说,多数的中国人至今还不配做病人!不配生病的人,一旦有了病,可就危险了!(胡适9)
菊英便是“愚昧”的“不配做病人”,“不配生病的人”。同样感染时疫,陈大悲以“侥幸”而得生,菊英以“顽抗”而夭亡,从新文学阵营的立场来看,都不是“合格”病人。
但要深入理解王鲁彦笔下的中西医论战,却有必要对“中医诊疗”作细致辨析。母亲“带她到四里远的一个喉科医生那里去”,医生“把一根明晃晃的东西拿到她的喉咙里去搽药”,回时“医生又给了一包吃的和漱的药”。造成病情“更加厉害了”的中医诊疗细节就是这些。然而这却极为可疑。
首先,传统医疗行为,以家庭为中心,有所谓“请大夫”,即请医生到家为病人诊疗,“家”和“诊所”融为一体,家人参与到医疗活动中,诊疗空间中“渗透着家庭感觉”(杨念群243)。而西医以医院为中心,有所谓“上医院”,即病人前往陌生空间寻求诊疗。菊英去寻“中医”治病倒更像“上医院”。
其次,这“中医”是“喉科医生”。建立在现代解剖学基础之上由局部定位的疾病模式促成的现代医学才将分科制度化,传统中医虽也分科,但极少分科执业。制度化的中医分科是迟至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后,个体中医转为集体,中医医院建立后才逐渐形成的(武伶俐53—54)。王鲁彦笔下的“喉科”更像陈大悲笔下的“耳鼻喉科”。
最后,小说里“中医”的治疗步骤,先是“把一根明晃晃的东西拿到她的喉咙里去搽药”,这和陈大悲的疗法相同,所搽不外碘水之类的消毒剂。又给了“一包吃的漱的药”。民初西医治疗喉病药物多为外科消毒、外伤溃疡和漱口水,杀菌的内服药很少使用(皮国立178)。恽铁樵说:“西医治此病,先用消毒棉花,去喉头白腐,继用血清以杀血中之喉菌,继用冰枕后脑,以防热甚而见延髓发炎之险症。”(210)恽铁樵为民国名中医,他眼中西医治疗白喉的手段正与王鲁彦笔下“中医”的手段相同。小说中“搽药”与“漱的药”,无疑是“杀菌”“消毒”用的,而这一医疗手段建立在细菌学基础上,这与中医理论中的喉痧病理很不相同。
王鲁彦试图以“庸医”害命的情节结束小说,但他显然并不了解中医治疗白喉的情形,以至把西医技术“嫁接”到中医身上。
然而医疗死亡本极正常,何况喉疫致死率也很高,恽铁樵说:“据西医籍言,血清为此症特效药,愈期约六日,治愈成分,得百分之七十五,然吾曾实地调查,实不能有如此成效”(皮国立210)。这还是一般情况,儿童的死亡率又远出成人。且霍乱、白喉、猩红热这类致死率极高的疫病,当时无论西医、中医,都没有特效药,“要到1935年磺胺剂以及40年代抗生素(青霉素。Penicillin,译为‘盘尼西林’)出现并确立疗效之后,西医才能确实有效的治疗许多传染性疾病”(皮国立40—41)。在历史条件下,菊英的死本应视为技术的限制而需要得到理解,但因与“中医”有关,就成为指认其为庸医的“血证”。
朱企洛对陈大悲的批评采用的是科学话语,“并不知道医学”的孙伏园对陈大悲的批评只需要站对立场即可,就有效性看孙伏园却不会比朱企洛更弱。正如林毓生所说:“现代中国的‘科学主义’(scientism)是指一项意识形态的立场”(林毓生252)。这也正是王鲁彦并不知道所批判的“中医”为何物,但只要选对立场就不会妨碍这种“政治正确”。
历史地看,在治愈时疫的效率上,此时西医并无绝对优势,何况西医人数极为有限。以1935年为例,全国西医仅5390人(含外籍752人),其中江苏(2010人)广东(606人)两省约占半数(朱席儒 赖斗岩147—48),全国绝大区域仍赖中医、草药,乃至于巫医。在这样的现实下,中医仍受到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强烈批判,就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问题了。
三、 可怖的“细菌”成为敏感问题
赵洪钧在《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中说,“细菌病因说,是在近代西医传入中国后才发展起来的重要理论,在近代中西医论争中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赵洪钧235)。知识之争变得“敏感”,意味这绝非纯粹的知识问题,它更联系着近代中国人特有的那种恐惧感。
1924年章太炎作《猩红热论》专门讨论猩红热,并暗中与西医较劲,章氏认为猩红热病因主在肠次在肺,西医只强调病菌入肠的观点不及中医全面。《猩红热论》文后还附了随无咎盛赞章太炎的评语,并嘲讽西医“视西医谈虎色变,固夐然尚矣”(“猩红热论”1)。章、随二人显然未将细菌学说当回事,因而嘲笑西医在这种观念下的“谈虎色变”。那么令中医觉得可笑的“谈虎色变”究竟是什么呢?余云岫对此作了解释:
以喉痧灭门者,吾见之矣;以肺病夷族者,吾见之矣;以鼠疫、霍乱屠村者,吾见之矣;以伤寒绝嗣者,吾见之矣。…其未染病者,人皆忽之…及其菌毒传染,仓皇就医,已不及矣。(余云岫79)
“菌毒”可怕的传染性是西医“谈虎色变”的原因。在疫病成因上中西医有着巨大分歧。中医称疫病为“热病”“温病”,明清以来,江南就形成了独特的温病学派。明清医生已认识到“疫疠秽邪,从口鼻吸受”(叶天士260),这与西方的疫病与环境有关的理论十分相似。但中西环境却有微妙差异,西方环境为城市环境,而中国的环境则是素被视为瘴疠之地的南方,所以西欧医学认为致病因素在于人口稠密的城市,改良都市环境便成为重要的应对策略,明清医家则未能产生改良环境的思想(梁其姿388—89),对于疫病的认识,“基本没有突破疫气传染的认识框架”(《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155),即便接受细菌学说,也视同毒、虫、疠气等物。章太炎就认为:“瘴气也,微菌也,虫也”(《章太炎全集·医论集》470),细菌不过是中医早已意识到的“瘴气”之类。
西方在传染病理论形成前,瘟疫被理解为“上帝不悦的征象”,十九世纪末细菌学时代的到来,“带来的希望包括发现传染病的病因、诊断的改良以及透过治疗来控制疾病”,“其结果是公共卫生的努力从具有包容性的预防医学措施,转变为更具排斥性而把焦点放在致病因子上,进而创造出新的干预意识形态”(克尔·瓦丁顿33)。当无处不在的“细菌”替换了无处不在的“上帝”,成为传染病的“世俗化”了的病因之际,寻求庇护的信仰便从上帝降为现代国家的卫生体系。治疗传染病成为在医生指挥下,由国家发起的针对细菌的战争(苏珊·桑塔格60),而服从这种战争动员的心理基础,正是中医所嘲笑的那种“谈虎色变”:
野蛮人怕猛兽,文明人怕微菌;猛兽伤人有限,微菌伤人无限,只看去年西班牙风邪大流行的时候,世界上死的人数,据说比死于欧洲大战还要多,便是一个最近的证据。(刘士永 皮国立编124)
这种造成野蛮与文明之别的“怕微菌”的情绪,是再形象不过的隐喻了,周作人在文章中将不惧细菌的中国人视同疯子,他说,“中国人是怯懦不过的,然而也很大胆,有两种最可怕的东西他独不怕,这便是霉菌与疯子”(《周作人散文》卷四704)。中医不怕细菌,理所当然是“野蛮”的。在有着深刻危机,渴求迈入“文明”的近代中国,中医成为具有耻辱性的标志,褚民谊说的十分清楚:
假令旧医从兹得势,新医从此消灭,科学无事乎研求,病菌一任其蔓延,而死亡日众,人口日减,纯任其自然,则若干年后,无需外人之任何侵略,吾族人必日即于澌灭矣。(褚民谊33)
褚民谊的话透露出近代知识分子所共享的一种普遍的受迫害妄想狂症,这一点像极了鲁迅笔下的“狂人”: 狂人意识到周围环伺要吃他的人,而喊出“我怕得有理”(鲁迅,卷三20),“文明人”意识到“微菌”环伺,自然也“怕得有理”。在新文化知识分子那里,对细菌的恐惧与近代中国的现实困境巧妙地结合起来。列强环伺,造一种大恐怖,“细菌”环伺,同样造成一种大恐怖,在以保种强国为目标的现代主题下,以治疗个人疾病为目标的中医,先天就丧失了政治正当性。个体的存亡与群体的存亡,在中西医关于疫病的论争上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得新文学家的“文学革命”有着强烈的“医学革命”色彩,无论新医学家还是新文学家,治病救人的传统医学不仅全然失去了救人的资格,甚至于它就是疾病本身。
在列强与细菌双重环伺之下,由细菌学所引发的军事隐喻只会更加强烈,在“战胜疾病”“消灭病菌”成为人处理与疾病关系的新法则下,干预的、改造的,甚至于破坏的、革命的观念在意识形态上取得了合法性,中医对“冰枕头”的反对就不合时宜了。无论是陈大悲的“倒戈”,还是菊英的“顽抗”,都会让现代卫生防御通过细菌的恐怖感展开社会动员的意图受挫,在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那里,这种不合格的“病人”,直接威胁到中国是否能够突破细菌与列强的重重封锁,摆脱“亡国灭种”的威胁。
传统的以仁术仁心自命的医者,斥无德无术者为庸医,当其遭遇“可怖”的“细菌”竟不觉“恐怖”时,自身也难逃被斥为庸医的命运,这也是为什么在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笔下——中医即庸医。
四、 “公益局”职员的恐惧
甚至包括鲁迅本人在内,讨论“幻灯片事件”影响的时候,也只谈到列强环伺的危机感,而忽略了细菌学作为一种全新的科学意识的影响。可以这么认为,“幻灯片事件”中,“列强”与“细菌”这两种威胁是同时出现的,这让鲁迅认识到救治个体病患之无效,并转而将“新生”寄托于“群体”,但鲁迅的说法却是“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卷四650),这样的有着强烈启蒙色彩的表述。
在讨论鲁迅思想中“个”与“群”的关系时,引用最多的,无疑是《文化偏至论》中的“任个人而排众数”(鲁迅,卷一288),这种推崇个性解放的启蒙主义,也被认为是鲁迅精神的核心。但从科学主义的一面来看,同样是处理“个”与“群”的关系,在生理学教科书《人生相敩》中,就很不一样,鲁迅写到:
关于预防传染病者,为公众卫生首要,凡最险之疾,如霍乱,赤痢,黑疫,痘疮,时或流行,则当急施遏止扑灭之术[……]顾其基本,在于个人,若譬国家于个人,则个人正如一幺,幺而不健,体奚能壮?故政家立制而善,个人所当遵行,同一心力,俾群安善[……](鲁迅,卷一493)
这里“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被修辞性地用一个细胞(一幺)与身体的关系置换了,在这修辞话语下,“个人”与“国家”间的“政家”却被省略了,“个”“群”关系成为“政家立制而善”之下,“个人”遵守“善制”,“同一心力,俾群安善”。在鲁迅精神中,《人生相敩》中“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无疑对《文化偏至论》等篇章中“个性”与“众数”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挑战。这种矛盾有点类似《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中曹操与孔融间的矛盾,“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鲁迅,卷八360)。但《人生相敩》中的“公共卫生秩序”绝不仅仅是一套物质性的施政方针,而意味着一套全新的意识形态,其合法性来自于科学,具体说来就是细菌学。这矛盾暴露了新文学知识分子启蒙主义与科学主义间的微妙的张力。
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家身上,启蒙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微妙的张力,构成了新文学创作中未能弥合的一道裂缝。前文中,无论是孙伏园等人对于陈大悲的批判,还是叶圣陶、王鲁彦的创作,都暴露出被新文化知识分子视为启蒙主义重要内容的科学主义对启蒙本身的挑战。
倘若陈大悲与菊英因为没有遵行“新文明的秩序”而被认为是不合格的“病人”,那么,下文中我将以鲁迅的《弟兄》和许钦文的《传染病》为例,来看看“合格的病人”的情形。
《弟兄》中有个未曾引起研究者注意的“公益局”,民国时它不仅有公益职能,也常兼及卫生事务。《弟兄》以“公益局一向无公可办”(鲁迅,卷六411)开头,结尾却讲抬埋安葬“无名男尸”的“卫生”公益。联系报上的猩红热流行,那么“速行拨棺抬埋”(420),暗示“无名男尸”极可能染疫而死。“公益局”就是现代医学卫生防疫的产物。主人公沛君是“公益局”职员,自然相信西医,文中提到沛君向中医白问山“说过好几回攻击中医的话”(414),是合乎身份的。沛君对猩红热的恐惧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理解《弟兄》的背景与动机,不应忽略这个“公益局”。
在一番关于兄弟之情的争论之后,小说转入同事间讨论猩红热的流行,并立刻引发了沛君的恐惧情绪,因为他原是以为兄弟所患只是“受寒”,而整篇作品便围绕这种恐惧感来展开。
沛君的恐惧最终是由西医祛除的,但在这之前,临时请来确定病名的中医白问山的“误诊”,却让沛君的恐惧感达到最高点:
“问山兄,舍弟究竟是[……]”他忍不住发问了。
“红斑痧。你看他已经‘见点’了。”
“那么,不是猩红热?”沛君有些高兴起来。
“他们西医叫猩红热,我们中医叫红斑痧。”
这立刻使他手脚觉得发冷。
“可以医么?”他愁苦地问。
“可以。不过这也要看你们府上的家运。”(鲁迅,卷六414)
白问山算不得重要角色,但小说的情感动力却源于他的“误诊”。
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到留日学医时,鲁迅已不再相信中医,但这种不信任的形成,从私下表达,到公开表达,却有个过程。1916年致信许寿裳时便说:“朱渭侠忽于约十日前逝矣,大约是伤寒后衰弱,不得复元,遂尔奄忽,然大半亦庸医速之矣。”(鲁迅,卷一464)1918年给许的信中又说:“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药方则无以下笔。故仆敢告不敏,希别问何廉臣先生耳。”(鲁迅,卷三4)这里也是讽刺中医,但这还是私下表达,与《弟兄》面向公众是不一样的。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先生比较《我的父亲》(1919年)与《父亲的病》(1926年)后感觉十分诧异,因为后者“文量要多出六倍以上”,且“大半是对中医的冷嘲热讽”(645)。倘放在中西医论战的背景下,会看到这种比较还有另外的意义。《狂人日记》(1918年4月)《药》(1919年4月)《明天》(1919年7月)《〈呐喊〉自叙》(1922年12月3日)《忽然想到(一)》(1925年1月17日)《从胡须说到牙齿》(1925年10月30日)《弟兄》(1925年11月3日)《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1926年3月10日)《马上日记》(1926年6月25日)《父亲的病》(1926年10月7日),都是批判中医的重要文本,对比可知,从1922年《〈呐喊〉自叙》开始的批判文章有一共性,即对中医的批判是在中西医并举下展开的: 《〈呐喊〉自叙》、《父亲的病》写因父亲的病而厌恶中医,选择西医;《忽然想到(一)》、《从胡须说到牙齿》讲身患牙病,中医久治无效,“西法的牙医一到,这才根本解决了”(鲁迅,卷六24);《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涉及孙中山临殁前,中西医就治法展开论争,而孙中山不为所动;《马上日记(一)》涉及梁启超“失肾案”引发的中西医论争;《弟兄》一篇则涉及中西医围绕传染病的论争。1922年之前的《狂人日记》《药》《明天》三篇里的中医,是代表传统的具体符号,而不意味着整个古代的身体技术手段。如前文所述,二十年代的中西医论战,也在鲁迅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考虑到这一背景,鲁迅笔下那种中医“荒唐无稽”,西医“根本解决”的激烈而偏执的态度才能被充分理解。
“科玄之争”中鲁迅似乎缺席,但正如刘禾说:“假如我们在时间关系上把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和《祝福》摆在一起来读,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祝福》里面发现鲁迅对那场论战的有力回答”(刘禾9)。同样的,中西医论战中鲁迅似乎也不在场,但若把这背景同《弟兄》等篇章摆在一起来读,也可以发现鲁迅并未缺席,并具体呈现为白问山与普悌思之争,“红斑痧”与“Measles”之争。
除此之外,小说在整体情节上与同时期的疫病书写的互动也值得关注。
五、 两个沉默的“兄弟”
《弟兄》中靖甫的病从“受寒”,到“猩红热”,到“红斑痧”,最后由西医确诊为“Measles”(疹子),在确认病名的波折中,怀疑“猩红热”是源自报上的新闻,并因中医误诊而加强,确定为疹子则出自西医,——那么“受寒”是由谁诊断的呢?——这看似无意义的质问,却暴露出鲁迅“虚构”小说的一处漏洞,藉此却能窥测到与前文王鲁彦相同的问题。
“受寒”由谁诊?在小说中是没有答案的,但这篇小说历来被认为是以周作人染病为本事的,并且“靖甫”的原型周作人也留下了值得注意的文字。《周作人日记》1917年5月有:
十二日晴上午往首善医院,俄国医生苏达科甫出诊,云感冒。
十三日晴[……]下午请德国ドクトルGrinm来诊,云是瘄子(疹子),齐寿山君来为翻译。
[……]
十六日晴下午请德ドクトルDiper来诊,仍齐君译。(《周作人日记》669—70)
先后三位外国医生参与诊断,确实费了不少波折,即便德国医生(Grinm)诊为疹子后,也不像小说中听了普悌思的“Measles”就全放心了,而是又请了一位(Diper)来诊。但如果德国医生没有误诊,首善医院俄国医生诊为“受寒”,就与白问山一样属于误诊了。——事实或许还更复杂,关于请中医周作人在《彷徨衍义·弟兄》中也有说明:
请中医来看的事,大概也是有的,但日记上未写,有点记不清了…医生说是疹子,以及检查小便,都是事实,虽然后来想起来,有时也怀疑这恐怕还是猩红热吧。枉长白大到三十几岁,没有生过疹子,事情也少有,而且那红疹也厉害的很,连舌头都脱了皮,是很特别的事。(《周作人散文》卷十二402—403)
裘吉生就曾在文中提醒说:
近来绍兴发生一种极厉害的小儿传染病,初起恶寒发热,咳嗽头痛,宛然伤风的样子,当即舌红苔黄,偶有苔不黄的,唇舌必红,眼泪汪汪,二三日面颊上手足臂里,发见红晕,渐即成疹,大概都当瘄子医治[……]因为这是一种时毒病,新医学所谓猩红热[……](裘吉生2—3)
裘吉生对猩红热的描述,与周作人的记录非常相似,猩红热可能误诊的“伤寒”“疹子”(绍兴谓之瘄子)都提到了,这足以证实周作人“也怀疑这恐怕还是猩红热”的合理性。如果周作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靖甫”的原型,并且周作人的回忆还值得取信,那么周作人的声音,无疑整个地解构了《弟兄》中那场中西医之争。当然这种“考据”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应该明白的是,无论是误诊还是医疗中的死亡,完全是医疗实践中应该被接受的事实(因此周作人看了三个医生以防误诊),但为何在新文学作品中,与中医关系的死亡和误诊就不被接受呢?
笔者使用这样的分析策略,并非利用周作人的回忆坐实鲁迅的小说,而是想指出: 新文化知识分子在评价中西医时,出现了标准的分裂: 无论是前文菊英的死亡,还是后文靖甫的误诊,倘与西医相关,误诊与死亡会被认为属于医学的局限而被接受,若与中医相关,则足以构成中医之为庸医的铁证。甚至不妨将现代化自身的问题归诸传统(常具体化为乡村和中医),这体现在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中,也体现在许钦文的小说《传染病》中。
1922年许钦文寓居绍兴县馆,根据真实经历创作了《传染病》,《钦文自传》写道:
拜言固然是我的胞弟,曾在“北京”同时患过白喉和红热症。我于万分的危险中救护他,自己也弄得非常吃苦。这种情形,在收入我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故乡》中的《传染病》上写过一回。(《钦文自传》1)
在时疫流行的背景下,“兄弟”来到城市,同时染上猩红热和白喉,“我”承担照顾“兄弟”的责任,在传染与死亡的威胁下,“我”陷入很深的精神困境。这篇小说仍留有中西医论战的印记。小说开头写到:
我在乡间碰着的医生们,凡有病的人去请他们诊治,他们总是有种种理论[……]:
“医生医病不医命,只要他的命数还有,这服药吃后一定能够见效的。”

“这病要看你们的家运了。”(“传染病”[27日]3)
“乡间”的“医生们”自然是中医了,这开头与《弟兄》中白问山的“这也要看你们府上的家运”正是相同意思。小说以批判“乡间”和“中医”开头,接着便歌颂起“大都会”和“西医”:
这次我的兄弟患传染病,幸而在北京的大都会,得由第一医院和传染病医院治愈。他是第一次到北京,并且到了还不过三天,好像预先已经知道,特地赶来医治似的。(“传染病”[27日]4)
小说一开头就给“病人”一个“弃暗投明”的开头,这不仅指向地理空间上的从“乡间”到“大都会”,也指逃离中医投入西医,与王鲁彦笔下的菊英不同处在于,一者“顽抗”一者却很“顺从”。正如王鲁彦为批判中医而让虚构沦为虚假,许钦文的“实录”也不例外。小说开头便写道:
他来到北京第一天的下午还是跟着我踱过马路,第二天早晨觉得头有点晕[……]三天以后的早晨,他觉得嗓子有点异样[……](“传染病”[27日]4)
这发病的情形与陈大悲、菊英很类似,即先到过人群聚集处,染上时疫后很快便发病了。现代大都市人口众多,疫病多发,是伴随现代化、城市化产生的新问题,但许钦文将现代化自身的问题,巧妙地转化成“城市”与“乡村”,“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对立,都市的问题被归诸“传统”,具体到乡村和中医,并且顺理成章地演化成具有文化自残倾向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
“科学”完胜“玄学”带来的是一种新的一元化文化权威,这种新的权威也在促成病人角色的变迁,传统病人与现代病人分野了,在传统医疗行为中,病人从能够参与医疗,与医生做有效互动,甚至批判、质疑医生,但现代医学抑制了病人的主体性,病人只能被动接受医疗。正如陈大悲步入医院时便意识到:
我进同仁医院时尚不肯自认为弱者。但是渐渐觉得勉强支持底不自然了。(陈大悲4)
面对中医时病人可以发声(现代一般是批判),在西医面前病人则要保持沉默,这构成了疫病书启蒙意图的复杂面向。
《传染病》中“兄弟”很怕打针:
[……]突然被“打针是不是很痛?”这问题打断了。“不见得罢。我曾经陪过我们的八妹去拔双比牙,牙床上连打三四针,她一声也不叫,可见是不痛的。”[……]我又和他说:“你进去以后第一胆要放大。[……]千万不要恨他们,却要感激他们才好。[……]凡事宁可听他们的号令[……]”(“传染病”[28日]3)
这里规定了“合格”病人的要求: 他要接受陌生空间,忍受侵入式的治疗方式,“凡事要听他们的号令”,要忍耐要沉默。现代医学兴起的过程中,“病人经常是沉默的,只是被控制或接受医疗步骤的客体”(瓦尔顿120),这也就是所谓“病人的消失”(李尚仁142)。病人必须放弃自己的自主性,同时必须认同居于客体位置的新关系,这显然与启蒙精神背道而驰,同时也构成了启蒙主义与科学主义间不可弥合的裂痕。
《弟兄》中沛君听到“Measles”后,兄弟间的对话极耐寻味:
“你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他遇到了什么奇迹似的,惊奇地问。
[……]
“你自己是不会记得的。须得问母亲才知道。”
[……]
“母亲又不在这里。竟没有出过疹子。哈哈哈!”(鲁迅,卷六417)
靖甫的“回答”两次以省略号填补文本空间,意味着靖甫的沉默,正如《传染病》中“兄弟”被要求“一声也不叫”,正是这“沉默”,同陈大悲的“倒戈”,同菊英的“顽抗”区别开来。这两个沉默的“兄弟”才是“合格”的病人。然而新文学家却试图“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鲁迅,卷八43),因为他们认为是传统造成了无声,因而要反传统,但启蒙者却没有意识到,“现代”同样会造成“无声的中国”。
注释[Notes]
① 这类批评,也见于西医,如余云岫在《箴病人》中就有:“国人畏疑之心犹未除也,非极有智识之人不就也,非重笃之病不就也,非疑难之症不就也,非沉珂宿疾,遍访名医讫无成效,无门可问者不就也”(《医学革命论集》78)。
② 这种认识,在杨念群《再造“病人”: 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年—1985年)》第七章也有论述。
③ 1926年之后,鲁迅涉及中医的文章明显减少了,直到1929年中西医论争白热化时,鲁迅又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是杂文《“皇汉医学”》,二是翻译《药用植物》,尤其是后者,反映了鲁迅“废医存药”的思想。详见笔者《鲁迅中医批判策略的形成与演变》,刊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1(2018): 78—107。
④ 《传染病》一文分期发表在1922年11月27日、28日《晨报副刊》上,此处以[27日]、[28日],以示区别。另,值得一提的是,许钦文《传染病》开头批判中医的一节,在鲁迅编定的《故乡》里被删除了,此处引用报刊所载原文。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大悲:“腥威将军的威味”,《晨报副刊》1923年4月2日第三版、第四版。
[Chen, Dabei. “The Power of the Scarlet Fever.”Morning
News
Supplement
2 April 1923.]褚民谊:“附褚民谊对新旧医药纷争之意见”,《医界春秋》34(1929): 33。
[Chu, Minyi. “The Attachment to Chu Minyi’s Views on the Disputes between New and Old Medicine.”The
Spring
and
Autumn
of
Medicine
34(1929): 33.]藤井省三:“鲁迅《父亲的病》再考——作为新起点的中国传统医学批判”,《中日学者中国学论文集——中岛敏夫教授汉学研究五十年志念文集》,刘柏林、胡令远编。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43—55。
[Fujii, Shozo. “Re-examination of Lu Xun’s ‘Father’s Disease’: Criticis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a New Starting Point.”Essays
on
Chinese
Studies
by
Chinese
and
Japanese
Scholars
:In
Memory
of
Professor
Nakashima
Toshio
’s
Fifty
-Years
’Chinese
Studies
. Eds. Liu Bolin and Hu Lingyuan.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6.643-55.]胡适:“《人与医学》中译本序”,《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183(1936): 7—9。
[Hu, Shi. “Preface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Man
and
Medicine
.”Publishing
Weekly
183(1936): 7-9.]李尚仁:“从病人的故事到个案病历——西洋医学在十八世纪中到十九世纪末的转折”,《古今论衡》5(2000): 139—46。
[Li, Shangren. “From the Stories of Patients to the Cases of Individuals: the Transi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from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Disquisitions
on
the
Past
&Present
5(2000): 139-46.]梁邵勤:“科学医与玄学医”,《生命与健康》41(1926): 3—4。
[Liang, Shaoqin. “Scientific Medicine and Metaphysical Medicine.”Life
and
Health
41(1926): 3-4.]梁其姿:“疾病与方土之关系: 元至清间医界的看法”,《生命与医疗》。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357—89。
[Liang, Qiz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ease and Local Conditions: Views of the Medical Field from the Yuan to the Qing Dynasty.”Life
and
Medicine
.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5.357-89.]林毓生: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Lin, Yusheng.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
.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8.]刘禾:“鲁迅生命观中的科学与宗教(下)——从《造人术》到《祝福》的思想轨迹”,《鲁迅研究月刊》4(2011): 4—14。
[Liu, He.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Lu Xun’s View of Life (2): The Trajectory of Thought from ‘Creating Human’ to ‘New Year Sacrifice’.”Lu
Xun
Research
Monthly
4(2011): 4-14.]刘士永 皮国立主编: 《卫生史新视野——华人社会的身体、疾病与历史论述》。新北: 华艺学术出版社,2016年。
[Liu, Shiyong, and Pi Guoli, eds.A
New
Perspective
on
Health
History
:Body
,Disease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in
Chinese
Society
. New Taipei: Airiti Press, 2016.]鲁迅: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20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
[Lu, Xun.The
Complete
Works
and
Translations
of
Lu
Xun
.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皮国立: 《“气”与“细菌”的近代中国医疗史: 外感热病的知识转型与日常生活》。台北: 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2013年。
[Pi, Guoli.The
Moder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of
Qi
(Pathogenic
Qi
)and
Bacteria
:The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of
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
and
Daily
Life
. Taipei: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企洛:“对陈大悲君之‘腥威将军的威味’的批评和忠告”,《晨报副刊》1923年4月18日,3—4。
[Qi, Luo. “Criticism of and Advice on Chen Dabei’s ‘The Power of the Scarlet Fever’.”Morning
News
Supplement
18 April 1923.]裘吉生:“绍兴时病发生”,《绍兴医药学报星期增刊》5(1920): 2—3。
[Qiu, Jisheng. “Epidemic Occurs in Shaoxing.”Shaoxing
Medical
Journal
Weekly
Supplement
5(1920): 2-3.]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Sontag, Susan.Illness
as
Metaphor
. Trans. Cheng We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孙伏园:“冰枕头”,《晨报副刊》1923年4月7日,4。
[Sun, Fuyuan. “Ice Pillow.”Morning
News
Supplement
7 April 1923.]克尔·瓦丁顿: 《欧洲医疗五百年》(第二卷),李尚仁译。新北: 左岸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4年。
[Waddington, Keir.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Europe
Since
1500
.Vol.2. Trans. Li Shangren. New Taipei: Left Bank Cultural Services Co. LTD, 2014.]王鲁彦: 《柚子》。上海: 北新书局,1926年。
[Wang, Luyan.Pomelo
. Shanghai: Beixin Publishing Company, 1926.]武伶俐:“中医分科的演变”,《中国医院管理》11(1986): 53—54.
[Wu, Lingli. “The Evolution of Branch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hinese
Hospital
Management
11(1986): 53-54.]许钦文:“传染病”,《故乡》。上海: 北新书局,1926年。47—54。
[Xu, Qinwen. “Infectious Disease.”Hometown
. Shanghai: Beixin Bookshop, 1926.47-54.]——: 《钦文自传》。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 - -.The
Autobiography
of
Qinwen
.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6.]杨念群: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年—1985年)》。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Yang, Nianqun.Remaking
“Patients
”:Spatial
Politics
under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1832-1985
).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6.]叶绍钧:“祖母的心”,《小说月报》13.7(1922): 20—26。
[Ye, Shaojun. “Grandmother’s Heart.”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13.7(1922): 20-26.]叶天士: 《叶天士医学全书》。山西: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
[Ye, Tianshi.The
Complete
Medical
Book
of
Ye
Tianshi
. Shanxi: Shan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2.]余新忠等: 《瘟疫下的社会拯救: 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北京: 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年。
[Yu, Xinzhong, et al..Social
Salvation
from
the
Plague
:Research
on
Major
Epidemics
and
Social
Responses
in
Modern
China
. Beijing: China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4.]——: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 - -.The
Plague
and
Society
in
the
Jiangnan
Region
in
the
Qing
Dynasty
:A
Research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3.]——: 《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 - -.Diseases
,Medical
Treatment
and
Health
since
the
Qing
Dynasty
:An
Expl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
-Cultural
History
.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余云岫: 《医学革命论集》。上海: 社会医报馆,1932年。
[Yu, Yunxiu.The
Collection
of
Debates
about
the
Medical
Revolution
. Shanghai: Social Medicine Press Office, 1932.]余云岫 恽铁樵: 《灵素商兑、群经见智录》。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7年。
[Yu, Yunxiu, and Yun Tieqiao.A
Critique
of
The
Divine
Pivot
and
Basic
Questions
;The
Wisdom
of
Various
Medical
Classics
. Beijing: Academy Press, 2007.]章太炎:“猩红热论”,《神州医药学报》2.5(1924): 1。
[Zhang, Taiyan. “On Scarlet Fever.”Shenzhou
Medical
Journal
2.5(1924): 1.]——: 《章太炎全集·医论集》,潘文奎等点校注。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 -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Taiyan
(Comments
on
Medicine
). Eds. Pan Wenkui,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赵洪钧: 《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北京: 学苑出版社,2012年。
[Zhao, Hongjun.History
of
Controversy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
. Beijing: Academy Press, 2012.]周作人: 《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郑州: 大象出版社,1996年。
[Zhou, Zuoren:Photocopy
of
Zhou
Zuoren
’s
Diary
. Vol.1. Zhengzhou: Elephant Press, 1996.]——: 《周作人散文全集》。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 - -.The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Zhou
Zuoren
.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9.]朱席儒 赖斗岩:“吾国新医人才分布之概观”,《中华医学杂志》21.2(1935): 145—53。
[Zhu, Xiru, and Lai Douyan. “General Situation of Modern Medical Talents in China.”Modern
Chinese
Medicine
21.2(1935): 14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