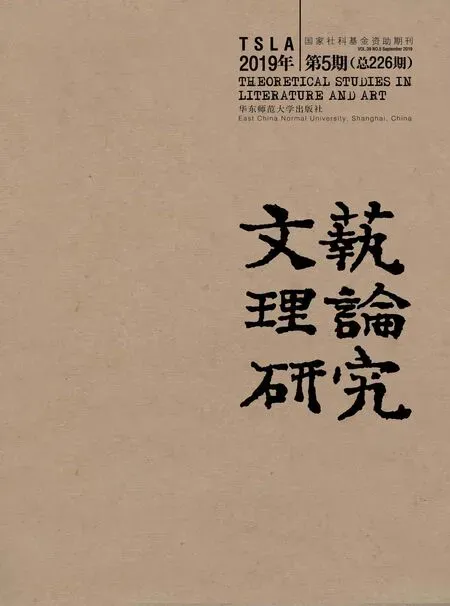南宋艾轩学派文道观及其文化意义
郑天熙
艾轩学派是南宋中后期活跃在福建莆田一带(兴化军和福州府东南)的理学流派。主要传承脉络为林光朝(艾轩)——林亦之——陈藻——林希逸,创始人林光朝虽有程颐一系的伊洛渊源,但心学倾向也很明显。艾轩学派自创始时就有综合融会的包容态度,对南宋中后期以朱陆为代表的两宗最大的理学流派的思想均有吸收。传至第四代林希逸,则不仅在理学内部倡导融合,更是试图融通儒道释三教,理论姿态更加宏通。艾轩学派还以“重文”闻名于当时,学问与文章并重是艾轩学派的重要特色,他们没有如伊洛学人那样排斥文章,反而进行了广泛的诗文创作实践。这在林光朝、林亦之、陈藻、林希逸四代传承中,均被贯彻与弘扬。四代艾轩学人虽均标举文道并重,但也呈现出富有深意的变化。可以说,这种变化反映了南宋中后期文学的自性规律越来越被理学家正视的发展趋势以及南宋末年理学家“流而为文”的总体特点。南宋末年的理学家在“文”之害与“文”之惑的张力中不断将文学纳入理学整体的思想体系,以理学规范文学,压制文学的审美自律。正是在南宋末年理学与文学的交汇场域中,艾轩学派文道并重、坚持探讨文学自性特点的意义得以显现。而四代艾轩学人的文道观变化,则典型地代表了南宋末年理学家对文学认识的发展。本文着重探讨艾轩学派的文道观及其相关问题,揭示出四代艾轩学人文道观的变化,并在南宋末年的思想语境中审视其文化意义。
一、 林光朝的文道观
自中唐韩愈建立“道统”以来,道与文的关系问题即为儒者关注的重点。宋代周敦颐明确提出“文以载道”(周敦颐432),程颐则发展为著名的“作文害道”说(程颢 程颐239)。程颐批评当时为文者仅在雕琢章句上用功,类似俳优,妨害对圣学的践行。他极端鄙视诗文,视诗歌为“闲言语”,将诗文视为悦人耳目的小技,与理学的作圣之功对立。对于六经以文传的文献现实,程颐认为那是圣人在修养功夫纯熟后的自然吐露。后来朱熹亦有文从道中流出的观点,这种认识取消了文学创作的自性规律,不承认(或轻视)文学创作技法。

若曰圣贤之学不在于无用之空言,则千百载之下,无六经无诸子,无百家传记,而能得古圣贤之用心者又不知其何事也。幸详言之,以观诸君子之所学问。古者以弧矢一事而合之以声歌登降之节。于是乎贤不肖无所逃矣。樸日以消,伪日以滋,谓弧矢有所不足,尚也。乃从而书其道艺,书其德行。(林光朝590)
由于理学提倡的“道”在林光朝精神世界中具有无上权威性,而“文”又是载道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媒介,因此他肯定“文”的记载作用,表明其对“道”的推崇。这是重视“载道之文”。而林光朝对文章自身的审美特性也有认识。他论及三代至于宋代以来的文章发展史时,说道:
问道之亏隆存乎其人,文章之高下存乎其时。唐虞三代至周而治极矣。故其文为独盛也。战国之诡激,魏晋之浮夸,南北朝五季之颓败,彫弱其间。[……]自元和以后渐复古雅,虽贾谊陈子昂之徒一时特起,初若有意于发挥古文,润色当代,而其风流蕴藉亦无传焉者,以其独立而未盛故也。班固赋西都,具述公卿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刘向、董仲舒、萧望之之徒皆以文章称之。[……]及欧阳子以古学为倡,而文章始一变矣。熙宁元丰之后学者皆祖于王氏,又其后苏氏出焉。今之学者,不出于二家。(林光朝588)
这段文章发展史较少理学教化色彩,“诡激”“浮夸”“彫弱”等都是对文章自身风格的评判,没有理学的心性道德等旨趣,而林光朝所提及的诸如班固、司马相如乃至宋代王安石、苏轼等人,也只是称赞其文章,无涉其道德修养。可见林光朝已经明确区分两种“文”,一种是载圣贤之学的文(载道之文),一种是“文章”之文(文学之文)。他重视前者,也不忽略后者,而且对于后者的发展和自身的内在规律等多有关注。他甚至对文学史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如“三百篇之诗一变而为离骚再变为词人之赋”,再如“文体之变,其风俗之所系邪。是故读虞夏之书则有浑浑之气,商书灏灏,周书噩噩,内外相形,虚实相应,不可以为伪也。战国尚纵横,其文也巧而善辩;西汉尚经术,其文也质而有理,晋尚清谈,唐尚辞章而文亦随之”(林光朝589)。
林光朝认为《诗经》《楚辞》与赋三者有流变的承传关系,同时文体的流变与风俗密切相关,这都是对文体自身发展规律的深刻体知,并没有带上理学的有色眼镜。更重要的是,林光朝没有将“文章”之文(文学之文)这一系统定义为“害道”,指出对“文章”之文创作技法的通达与实践,有助于对“圣贤之文”的学习。他认为“谈经者”与“能赋者”的优点不可偏废,应兼而有之:“谈经者或至于穿凿,能赋者或至于破碎,亦其势然耳。科目所以待天下,于斯二者不可以偏废。然罕能兼通之。求相如以经义,则疏矣;责仲舒以辞章则泥矣。[……]自贞观以还,其亦有通经博古而兼得夫雕篆之艺能者凡有几?愿详闻之。”(林光朝590)“通经博古”指学习“圣贤之文”进而修道体道,践履“圣学”;而“雕篆之艺”则指向文章创作技法。
林光朝重视载道之文,认为圣贤之学诸如六经、诸子百家之说需要文字记载才能传世,同时又肯定“文章”之文的存在价值。在前者以“载道”为全部目的的“文统”中,由于坚信圣贤“有德必有言”,创作主体的重点会落在道德践行与心性修养。当修习到“天理”完满充沛,私欲荡涤后,文章即从胸臆中自然流出。而在林光朝的表述中,“文章”之文与此不同,它对主体的要求更多偏重于形式层面上的文辞技法的学习,并且“文章”之文自身有独特的发展历史与规律。林光朝认为两个系统的“文”都要重视,前者固然是修学重点,对后者的掌握并不全然就会“害道”,反而是对学习“圣贤之文”的有益助因。
可以说,林光朝文(“文章”之文)道(圣贤之文)兼重的文道观为整个艾轩学派面对文与道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态度,林亦之、陈藻、林希逸等艾轩学人在此基础上则进一步深化林光朝两个系统的观点,形成艾轩学派一以贯之的文道观: 因重道而重道之文(圣贤之文);因不忽视文章自身的审美特性而重文学之文(“文章”之文)。对文学的重视,使四代艾轩学人均在诗文创作实践与批评活动上有所发挥,联系到南宋末年理学大肆入侵文学、取消文学审美自律的现实语境,作为理学流派的艾轩学派在“重文”这点上,具有特殊意义。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林光朝、林亦之、陈藻、林希逸四代艾轩学人在“重文”上的言论,则可发现,艾轩学派在“重文”上亦有不同。对于林光朝来说,文学自性的确被他正面肯定,但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在他肯定的有文采的文章中,有如《书》等儒家经典,这属于“载道之文”;二是,他提倡学习文章写作,是因为文学对修道有促进作用。前者说明文学的合法性离不开儒家经典的文本支持,后者则说明林光朝对文学的肯定,仍有理学家一贯的对文学的工具性、他者性认识。不过,相对于一般理学家,林光朝对“文”的认识与态度,无疑显得包容,他开始正面论及文学问题。
由于承认文学有自身发展规律,林光朝不仅在理论上探讨“文章”自身特点,还对历代文学家作出批评并注意到不同作家的独特风格:
苏黄之别犹丈夫女子之应接。丈夫见宾客,信步出将去,如女子则非涂泽不可。韩柳之别犹作室。子厚则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别人田地,退之则惟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也。(林光朝607)
如果不是大量深入阅读苏黄韩柳的诗文并有丰富的审美体验,难有如此形象生动的批评。他评论百家诗:“百家诗抹一过,只有孟浩然脚踏着实地。谢玄晖、陶元亮辈人名不虚得也。毋怪乎杜子美每每起敬,子美岂下人者。如孟东野、刘宾客、韩柳数家,又如韦苏州、刘长卿等辈,皆不在百家数中,却别有说。”(林光朝623)除文学批评外,他还致力于诗文创作。杨万里曾赞:“自隆兴以来,以诗名者,林谦之(光朝)、范致能、陆务观、尤延之、萧东夫。”(杨万里4359)刘克庄赞其文:“下笔简严,高处逼《檀弓》、《谷梁》,平处犹与韩并驱”(林光朝553)。

此问题可在林光朝对《诗经》的评论中见到答案。林光朝相当重视《诗经》,并对此有精深的体悟与研究。他批评欧阳修《诗本义》“若论本义何尝如此费辞说”,认为《诗本义》“欲作数段注脚”的做法只是说了许多“枝蔓语”(林光朝614),“断然非本义”(615)。他以“麟之趾”为例说道:
麟之趾只是周南之人目之所见,如公子者乃人中麟趾,乃以比公子,于嗟麟兮,此叹美之辞,二章三章只是说麟已,说趾又须说一件,乃谓角大序。所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所以一篇而三致意焉。今乃云以蹄角自卫如我国君以仁德为国,尤须公族相辅卫尔。如此说诗,谓之本义可乎?(林光朝615)
他不满欧阳修将麟角与君臣相辅相对应的解释,认为麟之趾是对公子的比喻与赞美,而二章三章则属于“一篇三致意”的咏歌之辞。林光朝对《诗经》“一篇三致意”的歌咏性特别强调,他甚至以此评论《离骚》:“《离骚》去风雅近,一篇三致意,此正为古诗体”(613),将吟咏性视为古诗正体,曾说“《诗》不歌,《易》不画,无悟入处。”(曾枣庄、刘琳341)由于重视诗的吟咏性,林光朝还主张不泥于文字笔墨解诗,通过吟咏而心悟,达到“不费辞说”的效果:“某尝向人说读风诗不解芣苢,读雅诗不解鹤鸣,此为无得于诗者,才见二诗的然如是,则三百篇之义不费辞说。然吾人如此说诗却恐门外草深三尺也”;通过吟咏而心悟诗义,竟与“不立文字”的参禅有相通之处:“一朝读《周颂》,不觉到天明,将笺注去掉,诵一遭方得解脱”,足见“吟咏”之于《诗经》的重要意义(617)。
既然是“吟咏”,而且还要“去掉笺注”,那“一篇三致意”的“吟咏”对象是什么呢?林光朝说是“性情”:“文中子以为诗者民之性情,孟子云诗亡而春秋作,人之性情不应亡。”(615)广泛地说,不仅诗歌,所有文学都应“吟咏性情”,这在艾轩后学林亦之、陈藻、林希逸等人的文道观中均有提及。回到刚才的问题,林光朝承认文学自律,且文学创作必须具备“性情”,即创作主体要有充沛丰富的情感,再通过一定的文辞技巧表现于文字。如果脱离“情性”,毫无真情实感,片面走向玩弄华辞的文字游戏,这也是林光朝所反对的。
可见,虽然都反对浮华文辞,程颐是从理学修习的角度,认为自然感发,不受任何约束的情感属于“情欲”,是修学需要荡涤的。与自然生发的丰富情感相应的文学藻汇属于“闲言语”,会妨碍修道,故应屏除,专务道学。林光朝则不然,他肯定自然情感的存在,进而肯定经由自然情感吐露而来的文学,但如果脱离真实的情感内蕴,只在文字堆砌中用力,就不能创作出优美而感人的文章。所谓“吟咏情性”则指出写好文章的前提是必须要有丰富的“情性”,因此他反对脱离“情性”的雕饰,并非反对一切文字技艺。
林光朝文道兼重使其言说潜在地具备两个系统,一是“道—文”系统,一是“性情—文”系统,前者是对理学家文道观的继承,后者则是林光朝的新创。在林光朝看来,两个系统并非水火不容,而是相互增益,又有各自的独立性。如果把林光朝的文道观分为这两个系统来理解,看似矛盾的言说便可迎刃而解: 在“道—文”系统中,林光朝心学色彩明显,他虽然强调文以载道,但不喜著书,认为“道之全体存乎六虚,六经注疏固已支离,若复增加,道愈远矣,故不注疏”(668)。林希逸曾有其师祖文章不传之憾。林光朝批评汉儒于经典泥而不通,主张大道至理不由绳墨见闻而得,强调心悟,不要泥于章句注疏,刘克庄评曰:“以语言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589)而在“性情—文”的系统中,林光朝不仅大谈文章发展规律以及历代诗文风格,还指出《诗经》“一篇三致意”的吟咏特点,强调“情性”(亦即“性情”,此处指文学活动中的自然情感)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也有大量的创作实践,对诗文创作技法有深刻体会。陈宓赞“其文森严奥美,精深简古,上参骚词,[……]数语雍容有余。”(林光朝553)刘克庄说:“乾淳间,艾轩先生始为精湛之思加煅炼之功,有经岁累月缮一章未就者。”(曾枣庄 刘琳341)两个系统的相对独立,使林光朝既可以在“道—文”系统中强调心悟而不喜著书,也可以在“性情—文”的系统中论及文学自律并进行文学实践。
然而前文还说到,两个系统在林光朝处虽然是相对独立的,却不代表二者地位是平等的。林光朝虽对文学给予一定的肯认,但仍把重心放在理学家修道体道上,强调的是在学习文章写作的过程中,把“通经博古”的修道之业与“雕篆之艺”文辞之技统一起来,最终目的是对“圣学”的践履。林光朝还不能完全离开理学而专言文学,尽管如此,他对于文学自性特点的认识仍较一般理学家深刻。
二、 林亦之、陈藻的文道观
林光朝文道观中的两个系统,使其可以突破周敦颐、程颐等人以理学观文的局限,发现并探讨了文学的创作、批评以及文学史发展等各方面问题,艾轩学派二传林亦之则继承师说,进一步深化、发挥其师的文道观,推进艾轩学派对“文”的重视。刘克庄曾称赞“网山论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意,得少陵之髓矣。其律诗高妙者绝类唐人,疑老师当避其锋,它文称是。”(林亦之854)说明林亦之也有丰富的文学创作实践经验,艾轩学派更是有自为一家的诗法规范与诗歌风格。这是对文学自性的肯定。
然而林亦之丝毫未忽略理学的权威。在“道—文”系统中,林亦之坚持并深化林光朝的观点,认为真正的大道不在文字上,但他也说“夫子之道不绝,则数圣人之道有所托”,仍然承认“文”的载道功用,这是对文学工具性、他者性存在的自觉认知(877)。不仅如此,他更是在理论上说明了“道—文”系统中学习圣贤文章对于体道修道的重要性。这是林亦之在艾轩学派文道观中最大的理论贡献,表明林亦之也不能完全脱离“道—文”系统而言文。他在《伊川子程子》中说: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道,吾于程子不敢有毫厘异同之论。然伊川之门谓学文害道,似其说未必然也。盖自有天地以来,文章学问并行而不相悖,周公仲尼其兼而有之者乎?自是而后,分为两途,谈道者以子思、孟轲为宗,论文者以屈原、宋玉为本,此周公仲尼之道所以晦而不明,阙而不全者也。请以六经言之。六经之道,穷情性极天地,无一毫可恨者。六经之文则舂容蔚媚,简古险怪,何者为耳目易到之语?是古之知道者未尝不精于文也。苟工于文章而不知学问,则大道根源必闇然无所识;通于学问而不知文章,则古人句读亦不能无窒碍,是皆未可以谈六经也。[……]程子以学文为害道,则于六经渊源虽极其至,而鼓吹天地,讴吟情性又将何所托也?是安得谓之集大成者乎?[……]则学问固为大本,而文章亦不得为末技也。(林亦之878)
林亦之赞同程颐的“道”论,但对他的“作文害道”论却有微议。他认为学问与文章并非二事,即使圣贤之文如六经,同样有“舂容蔚媚”“简古险怪”之文采。林亦之在“道—文”的系统中,肯定了载道之文可具备文学的审美要素,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予文学一定的合法性。但需要特别注意,林亦之这段论述视角实有两个层面: 一是见道者的圣贤层面;一是学道者即一般人层面,对于圣贤,他通达天地之道,可创作出既载道又有文采的文章,“未尝不精于文”,这有一定的理想色彩,但却是持“有德者必有言”“道根文枝”的理学家们普遍信奉的圣人之能。从这个层面上说,文学之文与载道之文本是一体,同根同源,其中,载道之文侧重文章的内容,而文学之文既是指文辞洋溢的审美价值,又是圣贤见道后的情性即“圣贤气象”的朗然呈现。因此对于圣贤,前文所述的“道—文”系统与“性情—文”系统是合二为一的状态。
但在学道者的修习层面上,林亦之认为面对学问与文章合一的诸如六经等文本,则不应人为割裂,因为如果只学习文章,固然于大道无所见;而如果只注重学习其中的“道”,完全忽视文辞,不学习其章法技巧,则不仅不能体会圣人在六经中“鼓吹天地,吟咏性情”的“圣贤气象”,甚至不能在句读等形式层面上通达六经。故他提出学问文章不可偏废,文章更不可为末技。但很明显,文章之所以重要,还是因为通过文章能见到“圣贤气象”。
林亦之主要是在“道—文”系统中,肯定见道的圣贤所作的载道之文有审美性,同时提倡修道与学文对于修学者同样重要。前者固不待言,至于后者,林亦之认为学习载道之文的创作技法以及注重其审美价值,则可体会到“圣贤气象”,只有这样,对于六经的学习才是全面的,否则于六经“晦而不明”。他也因此批评程颐于六经事业“阙而未备”。可见,林亦之对文学的肯定,落实在文学服务于修道体道的工具性作用上。他对文学的合法性论证,离不开儒家经典文本的支持,如认为六经“舂容蔚媚”“简古险怪”,是学习文章写作的典范。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对文章的学习有助于体悟“圣贤气象”,这说明林亦之一方面看到了文学兴发情感的妙用,一方面仍始终将文学视为他者性存在,认为文学是服务于理学家修道见道的工具、媒介。
与林光朝类似,林亦之的论证也还未完全脱离“道—文”系统,他是在重视道之文的基础上肯定性情之文的价值的。这种价值要在经由文章进而体悟得道之人的气象这个过程中才得以体现,体悟“圣贤气象”才是最终极的目的。林亦之固然重视文章,但他亦是在重道的基础上重文的。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不看到,艾轩学人一贯的重文传统相对于程颐“作文害道”论的差异。实际上林亦之也谈论、写作律诗,他甚至在诗法锤炼方面下过苦工,曾写过“雕肝篆肺得一句”“沉吟堪脍炙,涂抹更精神”的诗句(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28991,28994)。
特别指出,在“道—文”系统中,“圣贤气象”是圣贤的“情性”,是理学体系中天理流行、私欲荡涤后的“情性”,也是理学家唯一肯定的“中和”“温柔敦厚”等情感。其他自然感发的情感如喜怒、哀乐、悲欢等,都需要荡涤清净的。而“性情—文”中的“性情”侧重一般人在天地自然、社会人事中感荡的各种情感,丰富的情感积蓄可转化为强烈的审美体验进而发为文辞华丽的文章(文学)。当“情性”在“道—文”系统中作为“圣贤气象”时,在理学家那里其实是修学欲达到的理想状态,它需要对一般的情感作理性的涵养功夫,使之中和敦厚,符合理学要求,不能任由情绪推动产生出逾越规矩的情感。而“情性”在“性情—文”系统中作为一般人面对自然事物及社会人事感荡而起的喜怒哀乐各种情绪,恰恰要求其丰富、多面乃至复杂。这似乎是真正信仰理学并躬身践履“圣学”的理学家们始终对文学怀有最低限度的戒备的根本原因。文学活动中的创作、接受、批评等各方面环节都离不开人的丰富情感的参与,而理学家恰恰需要将这些情感都转为“中和”,即“思无邪”。于是他们不得不对“溺于文辞”而邪思泛滥的可能性有所警惕。但是,理学家们又看到了文学对于兴发情感、陶冶性灵的妙用,故而对“圣学”有信仰的理学家,他们不至走向程颐“作文害道”的极端,在有助于见道体道的前提下,他们可以对文学给予一定的合法地位,在“不妨大道”的范围内肯定文章写作与鉴赏对于修道的促进作用。林光朝、林亦之对文学的态度,正可作如是观。
因此,艾轩学派虽然以“重文”而“别为源流”,但在林光朝、林亦之等艾轩前人处,“道—文”与“性情—文”两个言说系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文学的自性虽被他们发现并重视,但二人始终未能完全脱离“道”而言文学,文学仍不能完全敞开自性。我们既要看到艾轩学人较一般理学家对文学的宽容、正视以及他们对文学的批评与实践这一面,又要分析出林光朝、林亦之等人对文学有限度的肯定以及在有助于见道体道的前提下重视文章的一面。
陈藻文道观也在上述两个系统中展开。在“道—文”系统中,陈藻强调“诗三百,思无邪。思无邪者诚,诚者中,中者仁。此诗之至也”(80)。这在理学家《诗经》功用观中不是新见,只表明陈藻对理学思想传统的继承。同时他还说过“诗,情性也。情性,古今一也。说诗者以今之情性求古之情性,则奚有诸家之异同哉?”(83)暗中表达诸家泥于文字训诂,不通诗歌情性而致解诗互异。联系到陈藻《阅世》诗:“道理初从纸上求,因而处世得优游,于今但阅人间世,自有文章笔下流。”(64)文章是通过阅尽人间世态,感荡情性,下笔而成,这里的“情性”更多指向一般人的各种丰富的情感,在这一点上,陈藻认为古今人相同,只要以我们的自然情性与古人的情性相感通,就能获取诗之真义。这显然是在“性情—文”的系统中谈论文学欣赏的问题,但因为谈的是如何解《诗经》,实际上也就有了解构经典神圣性的意味,即将诗三百看成在古人“性情—文”系统中创作处的表现一般人喜怒哀乐情绪之作,而不是在“道—文”系统中反映“圣贤气象”的载道之文。
这种强调人在诗文创作时的自然情感古今无异的观点并非陈藻独见,刘克庄也说:“余谓诗之体格有古律之变,人之情性无今昔之异。”(李壮鹰、李春青124)即使诗歌体式有古律之变,但作为创作主体必须具备丰富的情感,不能埋头于书本章句,这是古今一致的。可以说与陈藻一样,刘克庄也注意到“性情—文”系统中丰富的性情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他说:“或古诗出于情性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李壮鹰、李春青123)。也在强调诗歌创作的“情性”的重要性,批评时下写诗脱离真情实感,玩弄理学词汇,使诗歌变成理学思想的韵语化面目。
陈藻对古今性情相通的解读,表明他对文学活动自身规律有深刻认识。他继承林光朝对于《诗经》吟咏“性情”的观点,看到了丰富的情感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认为《诗经》是反映古人情感的文学作品,而陈藻较林光朝却极少谈及文学对于体道修道的工具性作用,他的“重文”相对于林光朝、林亦之,对文学的自性更为正视。也就是说,在“性情—文”系统中,他特别强调丰富真实的情感对于创作的重要性,甚至把理学家视为经典的《诗经》的创作视为与今人诗文创作无二的“情性”的发抒,充分认识到文学活动的自身规律,使“性情—文”系统相对于“道—文”系统的重要性得以上升。艾轩学派传至林希逸处,文学便真正实现独立,完全摆脱理学束缚。可见,“道—文”与“性情—文”两个系统虽然在艾轩前辈那里形成,但真正将两个系统完全平等地并立,且能互不干扰地言说,文学活动的规律与特点得以在脱离理学的视阈中进行探讨,在陈藻处已初见变化,在林希逸处则得以完成。
三、 林希逸的文道观
林光朝、林亦之在“道—文”与“性情—文”两个系统中,虽然对文学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正视与兴趣,但仍然保持对前一系统的主导性、基础性地位丝毫不动摇,文学的工具性、他者性存在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这是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即使林光朝、林亦之等人重视文学,也多是不离理学之“道”来谈文学,传至陈藻则初见变化,文学的地位得以上升,不需靠儒家经典获取合法性。直到林希逸,才真正做到道之文与文学之文的齐头并举,文学逐渐摆脱理学的束缚笼罩。林希逸还将文章学习的范围扩大,不光是儒学经典中的载道之文有文采,也不光是文学之文有文采,就是其他的学术著作,同样可以欣赏其间的富有文学性的篇章,更可以学习其文章设计、文辞技法等写作技巧。林希逸在《庄子口义》《列子口义》《老子口义》三部注解道家著作的书中,大量点评其文章写作技巧,鉴赏其文学性。林希逸文道观特点有以下数端:
首先,林希逸继承传统文以载道的文道观,同时也不忽略文自身的重要性。“士莫难于知道,文直寄焉尔。因其所寄,而后知道者存焉,然则文亦不可忽也。”(曾枣庄 刘琳325)他对文章的重视来自于学派传承:“初疑汉儒不达性命,洛学不好文辞,使知性与天道不在文章外者,自福清两夫子始,学者不可不知信从也。”(李清馥137)福清两夫子,即林亦之和陈藻。林希逸文道并重,他称赞郑安晚“有道有文”:“知公学穷古今,出入经史,胸中所有浩如也。镕炼而出,俄顷千言,形之声歌,兴味尤远。”(曾枣庄 刘琳313)评论方次云:“乃若其诗,则或长或短,可兴可观,是谓学问之鼓吹也。其飘洒即谪仙,其浑重即子美,得遗音于《风》《雅》,寄逸思于《庄》《骚》,虽元、白、郊、岛,亦当北面,余子何数焉”(325),明显继承林亦之圣人“鼓吹天地,吟咏情性”的观点。但如果林亦之还只是在“道—文”系统中针对程颐完全鄙视文辞而强调圣贤文章也有“情性”和文采的话,那么从林希逸所列举的诗文、作家看,他主要是在“性情—文”的系统中,肯定诗文的审美属性,没有摆出理学家的道德面孔。文学的独立性被进一步认可。
其次,林希逸也没有忽略载道之文,他甚至对圣人创作经典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圣经之终始,盖与造化参焉,非人力所能与也。夫圣人作经,非以自求名也。古今天下有不容无者,圣人亦不得而自已也。造物者发其机于千百年之前,圣人者成其书于千百年之后,圣人与造化相为期也,是机既息,虽圣人复生,亦无所措其笔矣,况区区言语文墨之士哉!”(曾枣庄 刘琳401)他认为圣人作经非以自名,而是与造化相期的过程中“得其机”后不得不作。这种神秘色彩的解释大概与他受道家思想影响有关。重要的是他还区分了圣人和“言语文墨之士”,这表明了林希逸理学家的身份意识,恰恰也说明林希逸能自由地在“道—文”与“性情—文”两个系统中无碍言说。
再次,林希逸继承艾轩之说《诗经》:“《诗》于人学,自为一宗,笔墨蹊径,或不可寻逐,非若他经。[……]然其流既为《骚》、为《选》、为唐古律,[……]艾轩先生尝曰:‘郑康成以三《礼》之学笺传古诗,难与论言外之旨矣。’”(曾枣庄 刘琳337)《诗》自为一宗,不由笔墨蹊径,而是要通过“吟咏”,才能得其“言外之旨”。因为“吟咏”最能体会诗歌的审美价值,“独与翁守乐轩之书,呻吟竟日。”(344)这是在“性情—文”系统中继承林光朝“吟咏”的文学鉴赏方式。
最后,林希逸重视文章审美风格及创作技法。他所论的文学并不止于诗文,还包括奏篇讲卷、传檄、帛书等各种文体。他不认为诗文四六与科举时文对立,主张“文字无古今,机键则一。”(曾枣庄 刘琳359)只要用功,都能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他学习文章技法的文本较前三代艾轩学人更加广泛,他公开注解《庄子》《列子》《老子》(合称《三子》),认为《庄子》“大纲领、大宗旨未尝与吾圣人异”并大量学习其章法结构、文辞运用等文章技法,形成自己的《三子》文章观。他说:“希逸少尝因乐轩而闻艾轩之说,文字血脉稍知梗概”,“文字血脉”,即指艾轩学派自林光朝以来重视的文章结构,创作技法等文章形式要素(林希逸2)。林希逸将艾轩学派重视文章的观点大量实践于《三子》文章分析,既注重引导学者赏析其间的文学性段落,又时时不忘提醒读者关注文章的笔法文势、关锁机轴等结构、句式以及“鼓舞处”“归结处”等文辞运用技巧。如:“天地间无形无影之风,可闻而不可见之声,却就笔头上画得出,非南华老仙,安得这般手段!每读之,真使人手舞足蹈而不知自已也”(15),这是对《庄子》文段进行审美鉴赏;“文字最看归结处,如上七篇,篇篇结得别。[……]到七篇都尽,却粧撰倏忽混沌一段,乃结之曰: 七日而混沌死。看它如此机轴,岂不奇特!”(137),这是分析《庄子》文本结构安排。
林希逸在“道—文”系统中强调圣人作经的“得其机”而不得不作的神秘性;在“性情—文”中则大量评论诗文,强调诗文技法,曾云“句中有眼容参取,肯靳涪翁古印章”(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37292)学习江西诗法。同时,他对文章创作技法的学习并未局限在诗文领域,而是扩大至思想义理著作,在“文字机键则一”的认识下,广泛从《庄子》《列子》《老子》等道家文本中吸收文章写作技巧,在更广泛的文章范围(包括实用性问题)内欣赏其文学性。可以说,对于艾轩学派文道观中的“道—文”与“性情—文”两个系统,林希逸都有弘扬与创新的一面。
林希逸较前辈更加重视文学的自性规律,没有像艾轩前辈那样在“道—文”系统中肯定文学,在有助于修道体道的前提下学习文章,而是将文学与理学区分开,使二者成为相对独立的精神活动,并对文学自身规律进行相当深入的探索。文学在林希逸处真正实现自性存在,不再是理学家用以“践履圣学”的工具。两个系统在林希逸处终于地位相当,他可以在文言文,在道言道,自由无碍。他的诗学创作、批评实践尤其是通过在《三子口义》中对《三子》文章的文学性评赏及其文章结构、文辞等方面的学习倡导,使艾轩学派“重文”的传统为时人所知。
四、 艾轩学派文道观的文化意义
艾轩学派的文道观分别在“道—文”系统与“性情—文”系统中展开,前者视文学为“载道”“贯道”的他者性存在,文学的价值在有助于主体的践履功夫中得以实现;后者则是文学活动自身的特点与规律,“性情”指文学活动中涉及到的一切自然感发的情感。艾轩学派的“重文”有重视“道之文”与“性情之文”(文学)两面,同时四代艾轩学人的文道观也发生着富有深意的变化。艾轩学派的文道观及其变化特点在南宋末年的思想语境中有独特的文化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是四代艾轩学人的文道观变化与南宋中后期理学世俗化呈现反向对应关系;二是艾轩学派的“重文”在南宋末年理学压制文学的文化语境中守卫了文学自性。
先看第一点。从前文论述可知,从林光朝、林亦之、陈藻到林希逸,四代艾轩学人都能正视文学,有丰富的文学创作、批评实践,表现出“重文”的倾向,但他们的文道并重又是在不断发展的。具体来说,在林希逸以前的艾轩学人中,虽然也重视文章写作、批评与实践,但仍离不开理学思维框架,文学在他们眼中仍不能完全摆脱工具性、他者性的存在,他们始终在文学有助于体道修道的功用性认识上来肯定文学。“道—文”与“性情—文”两个系统在他们身上虽然独立但不平衡,前者权重远大于后者,甚至后者的合法性需要前者赋予。这在林光朝“通经博古”与“雕篆之艺”兼得、林亦之学习文章有助于体悟“圣贤气象”中有明确表现。到陈藻,则可以跳出理学,视《诗经》为文学作品,强调文学创作中的丰富情感,对文学自性的探讨大进一步,而到林希逸,两个系统真正地位相当,他既没有以经典之文作为文学的合法性论证,也没有提及文学有益于理学的修养功夫,而是完全直面文学活动本身,深入探讨文学创作规律,并进行大量文学批评。
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艾轩学派四代学人的文道观均“重文”,为何他们对文学自性的认识呈现出逐渐摆脱理学束缚而直面文学本身的变化趋势?本文认为,这与南宋末年理学世俗化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当理学在士人心中不具有神圣性,由文观道、体道,对理学终极境界的躬身践履便不再是唯一的人生追求,文学也不再仅仅作为“载道”、“贯道”的他者性存在,文学的自性规律便得以被理学家正视并深入探讨。反之,对于真正信仰理学的士人,他始终会对文学存有最低限度的戒备,担心沉溺诗文妨害对“圣学”的实践,警惕文学掀起的丰富情感对于“温柔敦厚”之中和心境的扰乱。即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文学的功用,也要限定在有利于理学修习功夫上,不能完全离开理学专言文学。而一旦理学不再是士人精神世界中的权威主导,谈论文学就不会有任何危险,文学自性的探讨得以在理学家中毫无心理压力地进行。
我们看到,从林光朝到林希逸四代艾轩学人,他们对文学认识的变化,恰好是不断摆脱理学束缚,正视文学自性存在的过程。他们文道观中文学地位的上升,正与南宋中后期理学神圣性不断下降,士人对理学逐渐由信仰性接受转为知识性接受形成反向对应关系。南宋中后期的理学由朱熹的集大成后,开始向现实政治以及社会民众渗透。随着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与科举必考内容,理学的实践性要求在士人对现实功名利益的追逐中迅速抽空,理学的神圣性“祛魅”后,蜕变为对士人精神世界不具指导力量的知识概念。当理学围绕着“道”展开的实践与理论逐渐沦为知识概念体系,当“道”不再是士人的唯一追求,文学也就不再仅具“载道”之用,其自身规律与特点得以出场。南宋末年理学家“流而为文”的变化在元代一直持续。
具体到四代艾轩学人的理学观,我们同样能看出这种变化趋势。林光朝、林亦之安贫乐道,专心圣学,林光朝不事科举,致力讲学;林亦之、陈藻更是终身布衣,以道自乐。理学对于林光朝、林亦之仍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使二人淡泊名利,一心向道。但相对于林光朝“辟佛甚严”,陈藻已经显示出三教开通的立场,理学不再具备唯一性,地位下降。而到了林希逸,则公开注解道家著作,宣扬三教融合。他自身则不顾道德名节,多次给权奸贾似道写贺启献媚,表明理学在林希逸的精神世界中不再是终极的信仰依靠,而是一套不必躬行践履的知识概念体系。他也就能在道言道、在文言文,并完全正视文学,毫无压力地谈论文学了。
艾轩学派文道观的第二个文化意义是,他们坚守了文学自身的特点,强调文学创作必须具备丰富的情感。真德秀以理学过滤文学,规定了“新文统”,导致南宋末年诗文创作堕入理学思想的韵体化表达的圈套。当时文人刘克庄批评这种理学对文学的统治:“近世贵理学而贱诗赋,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李壮鹰 李春青126)正是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艾轩学派自林光朝到林希逸的四代传人以“道—文”与“性情—文”两个系统共存并举,对文学采取正面审视姿态,重视文学的审美自律,改变理学家面对文艺时而反对,时而肯定的摇摆态度。他们讨论了诗文创作技法并进行诗歌实践,形成严谨的诗法。四库馆臣曾评价“艾轩流派当时实自成一家,其诗法尤为严谨。”(林亦之853)
在“性情—文”系统中,艾轩学人提倡的文章“吟咏性情”是基于一般人面对自然或人事的感荡而激发的各种丰富的情感,他们认为“性情”(或“情性”)是古今一致的,这既说明他们对创作主体的心理特点与文学的情感蕴藉有深刻的认识,也说明他们对《诗经》等儒家经典的理解有跳出理学框架,将之完全视为文学作品来解读的对于经典神圣性的解构倾向。这种“情性”与真德秀在《文章正宗纲目》提出的“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谓义理也”(真德秀7)有别,后者的“情性”完全是理学思想规范过的或是理学所设定的圣人“情性”。与前者自然感发的情感不同,这种“情性”要荡涤私欲,体认天理,不仅要求对一般的自然情感进行处理,而且理想色彩浓厚。不排除表现这种“情性”的文章有上乘之作,但南宋末年的文坛现实却是理学辞藻的堆砌,艾轩学派重视自然情感在文学中的抒发,恰恰是对这种毫无情感的“假诗”的矫正。
艾轩学派四代传人都标举文道并重,他们的文道观在“道—文”与“性情—文”两个系统中展开,并呈现出后者地位不断上升,最终与前者地位相当的发展趋势,文学自性规律与特点越来越被正视与肯定。这与南宋中后期理学神圣性下降、不断走向世俗化的发展形成反向对应关系。随着理学不断世俗化,士人不再对理学开出的境界躬身实践,文学也就逐渐摆脱“载道”“贯道”的媒介性、工具性存在,解放出自性。同时,艾轩学派重视文学,在南宋末年理学极力压制文学的文化语境中,能坚持对文学自身的思考,并进行大量诗文创作、批评实践,广泛积极地探讨文章创作技法。这在理学家中尤为独特。全祖望曾评价艾轩学派“终宋之世,别为源流”(黄宗羲 全祖望1470),从“重文”这一点上看,诚哉斯言。
注释[Notes]
① 参见石明庆: 《理学文化与南宋诗学》,第284页。
② 参见常德荣: 《宋代理学与诗学的内在矛盾与调节》,第551—62页;王培友: 《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第159页。
③ 这里的“情性”主要指主体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丰沛的真情实感,而不是理学范畴内的“性情”,前者则是主体面对外在环境自然感荡而生,后者则是由理学的修养功夫达到的中和之圣贤心境。
④ 这里指出的林光朝文道观中的两个系统,只是相对独立,并非绝对毫无联系。实际上这两个系统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在“道—文”系统中,并不完全拒绝审美性因素,比如对“吟风弄月以归”的气象的描绘,程颢观竹草生意,朱熹的理趣诗由万物观理等均有审美质素;在“性情—文”系统中,虽然“性情”(真情实感)是创作文学的前提,但不能说在体道修道的理学践行活动中,一定没有审美情感,因此也有可能创作出“美文”;再如“性情—文”系统中较为重视的文章创作技法,在“道—文”系统中,也为创作载道之文所需(至于理学家眼中的圣人,则无需创作技法,自然流出。但这充满理想色彩,现实中的理学家即使如何强调“有德必有言”,也无法完全回避创作技法问题)。本文以两个系统论述林光朝乃至整个艾轩学派的文道观,旨在表明艾轩学派,对文学的充分自觉与实践。同时,更试图揭示,“性情—文”系统(即文学活动)在四代艾轩学人的文道观中逐渐取得与“道—文”系统相当的地位。在林光朝处,两个系统只是相对独立,而“道—文”系统无疑有压倒“性情—文”的重要性,他重视文学,却丝毫未忘记理学家修道体道的根本任务。两个系统的地位在林光朝处是不平衡的。直到第四代林希逸处,才真正做到两个系统的平衡。
⑤ 参见曾枣庄、刘琳主编: 《全宋文》卷七七三二,第341页。“先生(林光朝)平生不著书,遗文仅数卷耳,殁五十年,未有全稿。余同舍方君严仲,先生外诸孙也,每相与振腕此事。”林希逸还敦促方严仲搜集艾轩遗文:“兄老艾外诸孙也,先生遗文散落殆尽,兄之责也。”(林希逸: 《老艾遗文跋》。见《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5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90页。
⑥ 林亦之此段话中的“鼓吹天地,讴吟情性”是儒家温柔敦厚的中和“情性”,非本节使用的“性情—文”系统中的“性情”,前者是儒家追求的唯一合法的人格境界与精神气象,后者则是指文学活动中创作、欣赏等环节产生的自然感发的情感,如喜怒、哀乐、悲欢等一切能转化为审美体验的情感。为避免重复与误解,本文使用“圣贤气象”代替林亦之此处的“情性”。而“性情—文”系统的“性情”则指文学活动中的一切自然情感,特此说明。林希逸曾大量用“自然无容心”“迫而后应”“不得不为”等句解释《庄子》《列子》《老子》。林希逸的《三子》文章学理论,笔者有另文探讨,此不赘言。
⑦ 这是从文学活动在理学家林希逸那里获得真正独立的地位因而其自身规律得以被探索的积极意义而言。从消极方面来看,这是理学家林希逸解构自宗理学思想的神圣性并将理学看作知识概念体系而非信仰来接受为代价的。换言之,如果林希逸将理学作为信仰接受并躬身践履理学之道,他必然对文学之“害”有最低限度的警惕,即使谈论文学,也有对理学信仰性的本位自觉。但林希逸是将理学作为知识来接受的,故在他的精神世界里,“道—文”与“性情—文”两个系统可以做到真正独立地存在,且地位相当,他也可以大谈文学而毫无理学家身份带来的心理压力。笔者于此有另文详加论述。
⑧ 参见查洪德: 《元代理学“流而为文”与理学文学的两相浸润》,《文学评论》5(2002): 35—39。
⑨ 参见祝尚书: 《论宋代理学家的“新文统”》,《宋代文学探讨集》(郑州: 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82页。
⑩ 参见许总: 《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上册,第101页。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常德荣:“宋代理学与诗学的内在矛盾与调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八届年会论文集》,2013年。
[Chang, Derong. “The Intrinsic Contradiction and Adjustment of Neo-Confucianism and Poetics in the Song Dynasty.”Proceedings
of
the
18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y
for
the
The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 2013.]陈藻: 《乐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2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Chen, Zao.Lexuan
Collections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yuan’ge Edition). Vol.1152.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86.]程颢 程颐: 《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
[Cheng, Hao, and Cheng Yi.Collected
Works
of
Cheng
Hao
and
Cheng
Yi
. Ed. Wang Xiaoy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黄宗羲 全祖望: 《宋元学案》。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
[Huang, Zongxi, and Quan Zuwang.Scholarly
Annals
of
the
Song
and
Yuan
Periods
.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李清馥: 《闽中理学渊源考》,徐公喜编,管正平、周明华校。南京: 凤凰出版社,2011年。
[Li, Qingfu.Examination
of
the
Origin
of
Neo
-Confucianism
in
Fujian
. Eds. Xu Gongxi, Guan Zhengping, and Zhou Minghua.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2011.]李壮鹰 李春青: 《中华古文论释林》,南宋金元卷。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Li, Zhuangying, and Li Chunqing.Explanations
of
Pre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Southern Song, Jin and Yuan Period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林光朝: 《艾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2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Lin, Guangzhao.Aixuan
Collections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yuan’ge Edition). Vol.1142.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86.]林希逸: 《庄子鬳斋口义校注》,周启成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1997年。
[Lin, Xiyi.Oral
Interpretations
of
Zhuangzi
by
Yanzhai
. Ed. Zhou Qiche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林亦之: 《网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9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Lin, Yizhi.Wangshan
Collections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yuan’ge Edition). Vol.1149.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86.]刘克庄: 《后村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0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Liu, Kezhuang.Houcun
Collections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yuan’ge Edition). Vol.1180.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86.]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Ancient Literature, ed.Complete
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1.]石明庆: 《理学文化与南宋诗学》。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Shi, Mingqing.Neo
-Confucian
Culture
and
the
Poetic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6.]王培友: 《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Wang, Peiyou.A
Study
of
the
Song
Neo
-Confucian
Scholars
’Idea
about
Wen
and
Dao
,and
Their
Practice
of
Poetics
.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许总: 《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
[Xu, Zong.Neo
-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and
Ming
Period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 Nanchang: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0.]杨万里:“诗话”,《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一四,辛更儒笺校。北京: 中华书局,2007年。
[Yang, Wanli. “Poetry.”An
Edited
Collection
of
Yang
Wanli
. Ed. Xin Gengru. Vol.114.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Zeng, Zaozhuang, and Liu Lin, eds.Complete
Song
Prose
.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6.]真德秀: 《文章正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5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Zhen, Dexiu.Orthodoxy
for
Writing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yuan’ge Edition). No.1355.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86.]周敦颐: 《周元公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Zhou, Dunyi.Collection
of
Zhou
Yuangong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yuan’ge Edition). No.1101.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