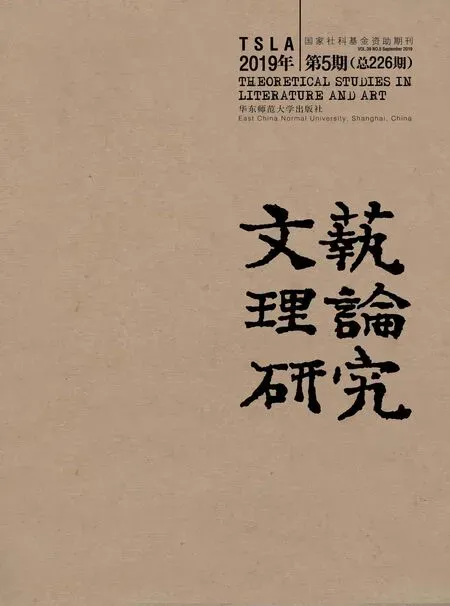试论朗西埃的现代虚构观
曹丹红
虚构问题是文学研究无法避开的问题,同时还因其涉及现实、语言、思维与真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始终在人文学科诸多领域占据着重要位置。法国知名学者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对虚构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近年来更是出版了《消失的线——论现代虚构》(Le
fil
perdu
.Essais
sur
la
fiction
moderne
2014年)《虚构的边界》(Les
bords
de
la
fiction
2017年)等专论,对现代虚构的本质进行了思考。朗西埃在其中提出的现代虚构观颇为独特,我们认为,对这一独特虚构观做出一番考察不仅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朗西埃的思想,也有助于反思虚构观念本身。一、 什么是传统虚构理性?
在《消失的线——论现代虚构》的引言中,朗西埃开门见山地指出:“在《情感教育》与《吉姆爷》的时代,虚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失去了秩序与比例,而秩序与比例是此前人们判断虚构作品是否优秀的标准。”(Le
fil
8)《情感教育》与《吉姆爷》的时代跨度很大,从《情感教育》第一版出版的1843—1845年直至1900年,横跨整个19世纪下半期。那么,在这翻天覆地、风起云涌的半个世纪里,西方的虚构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变化产生之前的虚构如何,变化之后的虚构又如何?朗西埃本人面对这种变化又持什么态度?对朗西埃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显而易见: 变化之前的西方虚构遵循亚里士多德确立的摹仿传统,变化之后的虚构则走上了相反的道路。《虚构的边界》一开篇,朗西埃即对亚里士多德《诗学》展开回顾,并为《诗学》所创立的虚构传统总结出以下几条核心原则。首先,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虚构摹仿的是行动。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摹仿者表现的是行动中的人”(38),或者“此类作品之所以被叫做‘戏剧’是因为它们摹仿行动中的人物”(42)。不过这番话并不意味着人物是摹仿的重心,因为亚里士多德随后指出,“悲剧是对行动的摹仿,它之摹仿行动中的人物,是出于行动的需要”(65)。另一方面,《诗学》结尾提到史诗时说,“史诗诗人也应该编制戏剧化的情节,即着意于一个完整划一、有起始、中段和结尾的行动”(163)。鉴于戏剧和史诗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意味着全部诗歌类型,因此也可以说,对亚氏而言,文学即意味着对行动的摹仿。“行动”一词在亚氏伦理学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暗含了行动主体、意愿与选择、目的性等丰富内涵,由此使传统虚构内在地具有了某些重要特征。
其次,虚构排除了偶然性,也就是说虚构是个有机整体,它的情节环环相扣,事件根据必然性或可然性原则得到组织,这里朗西埃想到的应该是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诗学》81)。对亚里士多德及其继承者来说,根据可然性或必然性来组织情节,这是诗歌区别于历史的最根本特征。在虚构作品中,必然性或可然性原则又体现为相互关联的两方面,一方面,情节的发展遵循因果逻辑,另一方面,虚构中的时间都与情节发展的某个环节有关,都是有效的行动时间。
最后,虚构强调行动的认知价值。亚里士多德对认知的重视由《尼各马可伦理学》可见一斑,亚氏在其中提到,行动的目的是对幸福的追寻,而终极的幸福是过上一种智性生活。在《诗学》中,亚氏指出,事件的发展不是神力干预的结果,而是行动者认知状态导致的结果,更确切的说是由行动者在无知状态下犯下某个错误所导致。例如《诗学》十三章中有言:“一个构思精良的情节必然是单线的[……]它应该表现人物从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而不是相反[……]人物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后果严重的错误”(98),《诗学》十四章又强调,诗人组织行动的最好方式,是将人物的行动描写成不知情情况下做出的举动,“如此处理不会使人产生反感,而人物的发现还会产生震惊人心的效果”(107)。认知错误引发蝴蝶效应,最后导向不幸结局,行动者面对悲剧结局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完成了认知过程。而认知达成的一刻也是真相披露、行动突转、命运变换的一刻,这一刻令悲剧观众对人物命运产生怜悯或恐惧,悲剧的净化功能就此产生。
以上由亚里士多德确立的虚构原则与精髓,朗西埃称其为传统虚构理性(rationalité或raison fictionnelle),后者概括来说就是“虚构知识组织了事件,活跃的人通过事件,从幸运走向了不幸,从无知走向了知识”(Les
bords
10)。朗西埃认为,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虚构确实被这种虚构理性左右,那么19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尤其是福楼拜、康拉德、左拉、伍尔夫、普鲁斯特等人的创作则逐渐摆脱了这种虚构理性,而传统虚构理性的颠覆既意味着文学观念与实践从再现体制(régime représentatif)进入到美学体制(régime esthétique),也意味着某种文学与政治新关联的诞生。二、 从行动的推进到感性的共存
由上文可见,对朗西埃来说,传统虚构理性最重要的原则是对行动的摹仿,而他的反拨也由此入手。通过两个步骤,他完成了对传统虚构理论的颠覆。
1. 从行动的主人公到不行动的大多数

Les
bords
9),但实际上,“行动主体的数量是有限的,因为大部分人严格来说并不行动: 他们只是制造物品和孩子、执行命令或提供服务,在第二天重复前一天的事。这一切之中没有任何期待,没有任何期待的落空,不会犯任何可能令人从一种条件过渡到其反面的错误。传统虚构理论因此只跟很少一部分人及人类活动有关,剩下的全部受制于无秩序、无缘故的经验现实”(Les
bords
9)。朗西埃在现代虚构作品中观察到的,正是这些融入日常生活的不行动的大多数,他们进入文学并成为了后者的表现对象。他指出:“在巴尔扎克和雨果的时代,文学也许最先对日常生活背景及形式所具备的承载历史的力量给予了肯定,不仅如此,对于这一内在于无名事物、存在及事件的力量,文学还把它变成了某种断裂的原则,来与过去从幸运到不幸、从无知到知识的重要转变模式拉开距离。”(Les
bords
11)这一观察并不是朗西埃一厢情愿的判断,因为它也符合某些理论家总结出的文学发展规律。在《写作的零度》和《什么是文学?》中,巴特与萨特就曾不约而同地指出,文学应表达社会上升阶级与新兴力量的诉求。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尤其在标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最终决裂的1848年革命以后,匿名的大多数逐渐成为法国社会中对抗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力量,理应成为新虚构的表现对象。2. 从行动的推进到感性的共存
然而,不行动的无名的大多数及其生活成为文学表现对象,这只是朗西埃意义上的现代虚构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为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朗西埃现代虚构观的其中一个理论来源,也就是奥尔巴赫及其在《摹仿论》中提出的文体混用原则。奥尔巴赫论证的出发点是古希腊罗马文学所确立的文体分用原则,朗西埃将其概括为文类性准则和得体性准则(朗西埃7—13),这两个准则又与虚构准则密切相关。一方面,不同的文类用以表现不同的对象,《诗学》即明确指出“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悲剧则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38)。对象的等级进而决定了文类的等级,因为悲剧摹仿对象在社会身份与地位上高于喜剧,悲剧在古希腊的地位与重要性便高于喜剧,这一点反过来又影响了西方文学史上“严肃”或“高雅”文学的主题与形式。另一方面,不同的风格用以表现不同的对象,体现了形式与主题的适应。奥尔巴赫通过考察西方文学史,发现由亚里士多德奠定的文体分用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有所不同,自19世纪初以来越来越明显地被作家僭越。奥尔巴赫本人对违背这一原则的作家或文学运动表示赞赏,在他看来,“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将日常生活中的随意性人物限制在当时的环境之中,把他们作为严肃的、问题型的、甚至是悲剧性描述的对象,由此突破了文体有高低之分的古典文学规则”(652),他们的创作“为现代写实主义开辟了道路,自此,现代写实主义顺应了我们不断变化和更加宽广的生活现实,拓展了越来越多的表现形式”(653)。
朗西埃的现代虚构观无疑深受奥尔巴赫影响,但他比奥尔巴赫走得更远。谈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伍尔夫的《到灯塔去》,奥尔巴赫认为包法利夫妇吃一顿晚饭的事件尽管日常,拉姆齐太太量袜子长度的举动尽管平凡,这些微不足道的事件却在叙述中获得了某种象征力量,“人们相信,信手拈来的生活事件中,任何时候都包含着命运的全部内容,也是可以表述的”(645),对奥尔巴赫来说,这两个例子是用高文体来严肃对待“低等”主题的范本。但朗西埃并不满足于此,他发展了“奥尔巴赫发现却没有明确提出”(Les
bords
13)的东西,在他看来,发掘普罗大众身上的高贵之处,揭示吃晚饭、量袜子这样的日常举动所包含的悲剧性,令寻常物嬗变成艺术品,这种逻辑仍然是重构行动的尝试,因而还没有摆脱传统虚构逻辑。真正的新虚构应试图打破的,是整个再现逻辑。这从他对《包法利夫人》的解读可见一斑。在他看来,农民的女儿爱玛爱看骑士小说,这件事本身不但无可非议,还意味着匿名大众从此也可自由获取知识,而知识不再专属某个阶级的事实反映出19世纪法国社会民主程度的加深。爱玛的问题在于,她那爱幻想的头脑总是试图按照她所读过的旧小说的模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也就是总试图回到与再现逻辑相适应的旧制度中去。朗西埃认为,福楼拜正是出于对等级分明的旧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产物——再现式文学的深恶痛绝,而不是觉得“放任了爱玛一段时间之后,断定这种民主过度了”(郑海婷90),才会在《包法利夫人》中为爱玛安排了死亡的结局。朗西埃进而借福楼拜的观点,拓展了奥尔巴赫的理论,同时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现代虚构观。在一封写给露易丝·柯莱的著名信件中,福楼拜曾说:“主题没有美丑之分,而且我们几乎可以依据纯艺术流派的观点确立一条准则,即根本不存在主题,唯有风格才是看待事物的绝对方式。”(Correspondance
345—46)这便是现代虚构所产生的变化,现代虚构“并不仅仅意味着[……]普通人的情感与‘伟大灵魂’一样,也能成为激发诗歌创作的灵感,它还意味着某种更为彻底的局面,从此以后,再无主题(sujet)存在”(Politique
19)。主题暗示了统一性与一贯性,意味着主次、布局与比例,“再无主题存在”则意味着这一切的消失。但是,无主题的写作似乎难以想象,它究竟是怎样一种写作?朗西埃认为现代虚构“执行了两个操作,第一个操作将匿名能力的表现分解为无数无人称的感性微型事件(micro-événements sensibles),第二个操作将写作的运动等同于这一感性组织的呼吸本身”(Rancière,Le
fil
32)。这段话还需结合朗西埃一贯的美学思想加以理解: 首先,个体具备审美能力,任何人都能感受到任何情感,这种能力是实现个体平等的基础。其次,个体感受力是一种类似济慈所说的“消极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个体并不像传统虚构中的主人公那样去行动,而是任由事件与感觉降临到自己身上。因而个体的感性体验遵循的不是有始有终的英雄模式,而是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模式。个体在梦游般的遐思之中与来自外界的纷扰事件相遇又分离,在环境、情感与思想共同作用下,获得对事件的短暂的、碎片式的感受。最后,这些碎片式感受彼此平等,“都被整体的力量赋予了生命”(Rancière,Le
fil
89),这“整体的力量”及上文提到的“匿名能力”“内在于无名事物、存在及事件的力量”都是一回事,都是“大写的生活,穿过并超越每个个体生活的普遍的生活”(118),朗西埃的美学思想是对“生活范式(paradigme de la vie)”(127)的推崇。因此现代虚构尽管书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它并不意味着普通人与日常生活成为文学的“选民”,就此获得高贵的地位;日常生活在现代虚构中分裂成无数感性微型事件,后者是碎片化的感觉,被虚构作品表达后,它们是无主的话语,可以是任何人的感受与表达,体现出一种无人称性,仿佛“无限微粒的永恒运动,在某种永恒的颤动的中央,时而聚拢,时而分散,或者重新聚拢。正是这个运动构成了新虚构的质地”(Le
fil
34)。福楼拜、左拉、康拉德、伍尔夫、普鲁斯特等作家的作品中体现的正是这种无人称的微粒运动。以伍尔夫《到灯塔去》第二部分为例,这一部分的内容大多在描写更迭的四季、交替的昼夜、静止或变化的自然环境,以及在这一切包围影响下逐渐毁损的拉姆齐家海滨别墅。这些描写很难找到叙事学意义上的视点与叙述主体,即无法确定是谁在观察谁在说话。奥尔巴赫评论《到灯塔去》时,把文中无法确定说话人的自由间接引语看成对“多个人的意识描述”(633)或“多元意识镜像”(647),此时他考虑的“多个人”主要还是书中的人物,无人称性则意味着作品中的观察、感受与表达再也找不到主人,任何读者都可以将其据为己有。文中也涉及人物行动,但主语常常是“人们”“一个身躯”“一只手”……也有有名有姓的人出现,也就是别墅管家婆麦克奈布太太,面对岁月流逝感叹忧愁的长久、生活的单调,自问还能活多久。但伍尔夫对麦克奈布太太的描写无疑是抽象的、诗意的,甚至有些失真,描写她只因她也在环境之中,也是熙熙攘攘的感性微型事件中的一件,她的叹息与思考融入环境,失去了个人色彩,她的名字完全失去了“以名举实”的作用,她可以叫任何一个名字,她可以是任何人的代言人,她与周围环境一起,被生活的气息与洪流裹挟而走。因此,现代虚构看似没有放弃对人物命运的讲述,实际上是将原子一般的无人称状态组合在一起,它不再是某个英雄或悲剧人物的故事,而是所有“无名事物、存在及事件”的状态组合,是“伟大的无人称生活(grande Vie impersonnelle)”(Le
fil
33)的自行展现。当微粒的永恒结合与分离运动打乱行动,渗入虚构并改变后者的质地,传统虚构理性中与行动密切相关的另两个原则——虚构根据必然性或可然性安排情节,虚构重视认知价值——也被颠覆。在新虚构中凸显出来的是一种“感性状态并存的秩序”(Le
fil
33),也就是大量“感性微型事件的并置”(Malaise
13),面对这些事件,无论对人物、作者还是读者来说,比起运用智力进行分析,更为重要的似乎是发挥感受力,去充分“体验内在与外在的融合”(Politique
71)。三、 从叙述到描写
由内容的差异产生了现代虚构与传统虚构的另一个差异: 当行动不再是虚构关注的中心,虚构文的写作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描写——尤其是细节描写开始取得重要地位。描写与叙述的历史同样悠久,但与叙述相比,描写在虚构传统中始终处于较为尴尬的地位。对描写进行过深入研究的法国当代文论家哈蒙(Philippe Hamon)指出,在很多理论家眼中,描写具有无法控制的膨胀与扩张倾向,同时还会在文中引入古怪的或太过专业的词汇,损害表达的自然流畅及文学作品的统一性,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阻碍文学发挥自己的教化或娱乐功能。因为这些缺陷,所以在16至18世纪的法国修辞学与诗学理论中,“描写并没有真正的理论地位”(Hamon10)。另一方面,描写又受到严格的限制,它的主要功能是为行动提供时间、地点、背景等信息,或者为人物提供侧写,帮助读者理解其道德、情感与行为,总之,它必须对行动的叙述起到辅助的作用。从19世纪初开始,随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因为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尤其左拉等人的努力,描写的地位有所改善;20世纪的新小说更是赋予描写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重要性。但将描写视作手段而非目的的观念却始终存在,即便是福楼拜、左拉等作家在面对描写时都抱持一种暧昧的态度,而卢卡奇、雅克布森、瓦莱里等理论家也都曾从不同立场强调过描写的“危害”,并劝告写作者克制描写的冲动。
在这种描写观中,不难想象细节描写遭遇的抵制。朗西埃认为“描写所具备的过度‘现实主义’倾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阐释,从这一阐释中能够获得一种有关虚构诗学与虚构政治学关系的全新认识”(Le
fil
10),由此重新定位了现代虚构作品中的细节描写。其论证从反对巴特与萨特的描写观入手。在著名的《真实效应》(L’Effet de Réel)一文中,巴特就福楼拜中篇小说《淳朴的心》的描写展开了思考。福楼拜在《淳朴的心》开篇花不少笔墨描写了女主人公费莉西泰帮佣的欧班太太家的房子,触动巴特的是其中一句描写“正房”的话:“晴雨表下方的一架旧钢琴上,匣子、纸盒,堆得像一座金字塔。”(3)巴特认为晴雨表“这个物体不突兀却没有任何意义,初看之下并不属于可被‘记录’的东西范畴”(Barthes84-85),因而很难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得到解释,进而将晴雨表归入西方普通叙事作品中随处可见的“无用的细节”(Barthes85)行列,并思考了其“无用之用”: 细节通过自己具体、精确却无用的特征,令读者“感觉自己所看到话语的唯一法则就是对现实的严格摹写,以及在读者与现实世界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Todorov7),也就是说制造出了令人信服的“真实效应”。由此可见,巴特的分析还是没有脱离其符号学思想。在萨特看来,“福楼拜写作是为了摆脱人和物。他的句子围住客体,抓住它,使它动弹不得,然后砸断它的脊梁,然后句子封闭合拢,在变成石头的同时把自己关在里面”(萨特163)。萨特认为,作家精雕细琢描写文字,制造出一个与现实世界隔绝的抽象世界,似乎想通过这一举动表明对资产阶级当权的世界漠不关心,由此来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但实际上他们的能指游戏无法为新兴的无产阶级所理解,也无法对其产生任何作用,因而风格游戏体现的,其实是作家向社会保守势力的妥协。朗西埃指出,以上两种观点表面看来有些矛盾,实际上殊途同归: 巴特与萨特都将描写视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反映,他们的思路仍然没有摆脱旧的再现逻辑,因而都“错过了问题的核心”(Le
fil
20)。在他看来,福楼拜对外省生活的描写,伍尔夫对资产阶级生活起居的描写,左拉对工人生活的描写,康拉德对大海的描写等等,所有这些描写只为自身存在,被描写的细节是“感性微型事件的并置”,是经纬交错的知觉与情感,是它们编织出现代虚构文本的网络,而对行动的叙述转变成了网络中的网眼。《到灯塔去》第二部分明显体现出叙述与描写的地位变化。在占据全书不到十分之一的篇幅里,作者讲述了十年间发生的事。那些本该为传统虚构大书特书的事件——全家核心人物拉姆齐太太的死亡以及最美丽的女儿普鲁的婚姻与死亡都被压缩至短短几行,与人物行动与状态相关的简短文字全部被放置于括号内,仿佛只是无关紧要的背景介绍,除此之外的文本空间都被描写占据。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朗西埃尽管没有总结,却在论述中不断提及。第一点,描写增多并不仅仅意味着在作品中增加一些画面(tableaux)。现代文学中大量出现的描写受到19—20世纪保守批评家的批评,后者气恼地指责作家用画面取代了行动。但朗西埃认为,这些画面“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们是差异,是移动,是强度的累积,外部世界通过这些活动渗透入心灵中,而心灵制造了它们生活的世界。正是这个感知与思想、感觉与行动交融其中的肌理”(Le
fil
29)构成了现代虚构中人物的生活。也就是说,现代虚构作品中的描写并不意在精确描绘外部世界,它们是世界、心灵、思想、情感彼此影响、彼此交织的产物,因而往往笼罩着某种梦境色彩,《包法利夫人》中的外省风景描写,《到灯塔去》的房屋描写,《吉姆爷》中的大海描写等莫不如是,朗西埃也正是据此认为注重描写的“现实主义根本不是对相似性的价值的肯定,而是对相似性起作用的框架的摧毁”(Le
partage
34)。另一方面,尽管人们时常给现代虚构贴上“印象主义”的标签,但朗西埃认为不应受所谓“印象主义”的欺骗,因为作为现代虚构肌理的感性微型事件彼此之间是平等的地位,它们都试图脱离中心,或者说它们全部是中心,不可能将这些并置的感性事件拼凑成一个完整的画面。第二点,叙述与描写篇幅的增减只是新虚构质地变化的表象。从更为本质的角度说,叙述与描写篇幅的此消彼长首先当然源于现代虚构中行动重要性的减弱。其次也因为现代虚构“将事件分解为感受与情绪的单纯游戏”(Politique
68)。举例来看,《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人生观、价值观与鲁道尔夫截然不同,却可以说是突然之间对他产生了爱意。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农业评比会上,鲁道尔夫坐在爱玛身边,爱玛闻到鲁道尔夫头发的香味,回忆起昔日的舞会和难以忘怀的子爵,看到远处的“燕子车”,回想起旧情人莱昂,这些回忆彼此交织叠加,作用于她的情绪,使她最终无力抽回被鲁道尔夫握住的手。《吉姆爷》中,富有英雄主义情结的吉姆在帕特那号遇难进水之时突然弃船逃生。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吉姆在意识到船只必沉无疑并且自己无力拯救船上几百名乘客时,他看到墨黑的乌云吞噬了船只和星光,看到暴风雨来临的先兆,感到浪涌晃动了大船和他自己的大脑,看到有人死了,听到已经逃离的人不断呼唤死人的名字,在种种刺激下,他产生了可怕的幻觉,不由自主跳下帕特那号,逃到救生船上。《包法利夫人》与《吉姆爷》表明,如果说在传统虚构中,行动转变与人物认知有关,并且遵循因果逻辑,那么在现代虚构中,行动转变往往是一连串感性事件作用下的突变,而对行动的叙述也自然被对感性事件的描写所取代。总而言之,在现代虚构中,“描写的膨胀损害了构成现实主义小说特殊性的行动,但它不是对渴望确立自身永恒性的资产阶级世界财富的展露,也不是人们忙不迭指出的再现逻辑的胜利,相反,它标志着再现秩序的断裂,以及构成其核心的行动的优越地位的颠覆。”(Le
fil
20)四、 感性的分配与文学的政治
以上我们对朗西埃的现代虚构观进行了简要的评述,这一现代虚构观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是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确立的传统虚构理性的批判,其次是对席勒、济慈、福楼拜、伍尔夫、奥尔巴赫等作家学者思想的继承,它指出现代虚构不再以摹仿某个有机整一的行动为核心,而是着力表现并置的感性微型事件。内容的改变导致了现代虚构形式上的变化,传统虚构中被边缘化的描写获得了与叙述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虚构的质地。朗西埃所举的例子基本都是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前半期的作家及其作品,但很多当代虚构作品的特点都印证了他的现代虚构观的中肯性,例如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沙漠》《看不见的大陆》等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对朗西埃所说“伟大的无人称生活”的记录。与此同时,在读者戏称“小说不如生活精彩”的当今社会,旧有虚构模式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朗西埃的现代虚构观为反思今日文学虚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视角。
不过,作为哲学家、思想家,朗西埃在提出现代虚构观时瞄准的并不仅仅是文学领域,他对传统虚构理性本质的认识即表明了这一点:“自亚里士多德起人们就知道,虚构并不是对想象世界的创造,它首先是一种理性结构: 一种呈现模式(mode de présentation),令事物、处境或事件变得可以感知与理解;一种关联模式(mode de liaison),在事件之间构建起并存、先后、因果等种种形式,并赋予这些形式以可能性、现实性或必要性等特征。”(Le
fil
11)虚构是一种呈现与关联模式,这意味着虚构是我们在某种思维模式影响下,赋予世界以秩序进而认识世界的手段,不同的虚构理性因而体现的是对不同社会秩序的理解与把握,《克莱芙王妃》所展现的井然有序的空间与《包法利夫人》所展现的被物品挤满的空间是不同社会秩序、不同感受性的象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朗西埃提出虚构并非文学作品的特权,政治行动与社会科学遵循同样的虚构逻辑,而“虚构秩序的紊乱反过来促使我们思考词与物、感知与行动、重复过去与展望未来、现实感与可能感、必要感与逼真感之间的新关系,社会经验与政治主体性的形式恰恰由这些关系构成”(Le
fil
13)。在这一点上,朗西埃对现代虚构本质的认识自然地与他的美学观相对接。对朗西埃来说,美学是“对时间与空间,对可见与不可见,对话语与噪音的切分,这一切分同时决定了作为经验形式的政治的场所与关键”(Le
partage
13-14)。文学与其他艺术活动一样,背负着与政治行动、社会科学同样的任务,或者说对朗西埃来说,文学实践本身就是政治,以现代虚构为例,它重新切割布置时空,打破阶级与身份限制,利用匿名的大多数的感受力,将消极被动的人群引入舞台,令不可见变得可见,令无意义的噪音变成清晰的话语,总之,文学有能力借助对感性的重新分配,创造出一个人人平等的全新的“人世共同生活”(Les
bords
147),这是朗西埃赋予文学的解放力量。但是,彻底颠覆传统虚构理性是难以想象的,朗西埃也清楚意识到这一点。包法利夫人、吉姆爷、拉姆齐太太的死亡也许确实象征着传统虚构逻辑的失败,但它们作为故事的结局,却体现出情节也就是传统虚构理性的胜利,因此,尽管“新虚构的本质是一元论的,它的实践却只能是辩证的,只能是无人称生活的伟大抒情曲与情节安排之间的张力”(Le
fil
67),也就是说,两种虚构理性的并存是文学虚构作品的现实,文学的矛盾性由此而来。在朗西埃看来,这一新旧辩证法也许永远不会消失,而保持文学的这种辩证性或许就是最深刻的文学的政治。注释[Notes]
①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直接探讨“虚构”问题,不过德国学者汉伯格(Käte Hamburger 1957年)、法国学者热奈特(Gérard Genette 1991年)、谢弗(Jean-Marie Schaeffer 1999年)等人均建议将《诗学》的核心概念mimesis翻译成fiction。热奈特曾特别指出“亚里士多德,我重申一下,把我们称之为fiction的东西称作mimèsis”(Genette 227),谢弗也在其影响广泛的《为什么要有虚构?》(Pourquoi
la
fiction
? Paris: Seuil, 1999年)一书中不时将mimèsis与fiction混为一谈,朗西埃更是在新著《虚构的边界》的引言中先直接指出“诗,应该理解为对戏剧虚构或史诗虚构的创造”(Les
bords
7)。引用作品[Works Cited]
亚里士多德: 《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年。
[Aristotle.Poetics
. Trans. and Ed. Chen Zhongme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66.]——: 《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年。
[- - -.Nicomachean
Ethics
. Trans. and Ed. Liao Shenba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3.]奥尔巴赫: 《摹仿论》,吴麟绶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年。
[Auerbach, Erich.Mimesis
. Trans. Wu Linshou,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Barthes, Roland. “L’effet de réel.”Communications
11(1968): 84-89.居斯塔夫·福楼拜:“淳朴的心”,《福楼拜小说全集》(下卷),刘益庾、刘方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3—28。
[Flaubert, Gustave. “A Simple Heart.”The
Complete
Fictional
Works
of
Flaubert
. Trans. Liu Yiyu and Liu Fang. Vol.3.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2.3-38.]- - -.Correspondance
. Deuxième série (1847-1852). Paris: Louis Conard, 1926.Genette, Gérard.Fiction
et
diction
. Paris: Seuil, 2004.Hamon, Philippe.Du
descriptif
. Paris: Hachette, 1993.Rancière, Jacques.Le
partage
du
sensible
. Paris: Galilée, 2000.- - -.Le
fil
perdu
:Essais
sur
la
fiction
moderne
. Paris: La Fabrique, 2014.- - -.Les
bords
de
la
fiction
. Paris: Seuil, 2017.- - -.Malaise
dans
l
’esth
étique
. Paris: Galilée, 2004.- - -.Politique
de
la
litt
érature
. Paris: Galilée, 2007.雅克·朗西埃: 《沉默的言语》,臧小佳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Rancière, Jacques.Mute
Speech
. Trans. Zang Xiaojia.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6.]让-保罗·萨特:“什么是文学?”《萨特文学论文集》,施康强等译。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69—291。
[Sartre, Jean-Paul. “What Is Literature?”Sartre
’s
Critical
Essays
on
Literature
. Trans. Shi Kangqiang, et al. 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8.69-291.]Todorov, Tzvetan. “Présentation.”Litt
érature
et
r
éalit
é. Eds. Gérard Genette et Tzvetan Todorov. Paris: Seuil, 1982.7-10.郑海婷:“我们需要怎样的现实主义文学”,《文艺争鸣》12(2017): 89—94。
[Zheng, Haiting. “What Kind of Realistic Literature Do We Need.”Literature
and
Art
Forum
12(2017): 8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