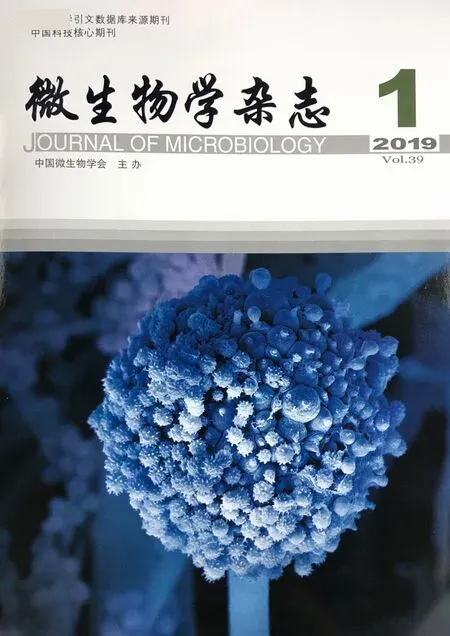疟疾疫苗研究进展及前景
尤 放, 王美莲
(中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教研室,辽宁 沈阳 110122)
疟疾是最常见的虫媒传染病之一,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了极大威胁,已成为严重的世界卫生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近91个国家和地区属于疟疾的高度和中度流行区,主要集中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包括非洲、东南亚、东地中海的多个国家和地区[1]。在非疟疾流行地区,疟疾依然是造成严重输入性感染的最常见原因[2]。2016年我国疟疾报告病例中99.9%为境外输入性病例,而本地疟疾传播主要在云南边境地区和西藏林芝地区。人类一直在与疟疾做着各种斗争,消除疟疾是人类共同的目标。使用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Insecticide-treated nets,ITNs)与室内残留喷洒(Indoor residual spraying,IRS)是最重要的两项病媒控制措施[3]。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是目前强有力的抗疟药物,以其为基础的联合用药策略(Artemisinin-based combination therapies,ACTs)是目前控制非复杂性疟疾的一线选择[4]。然而,多重耐药性疟原虫以及具有杀虫剂抗性按蚊的出现,对疟疾的控制与消除又构成了巨大的挑战[5]。安全、高效、价格低廉的疟疾疫苗作为现有抗疟手段的理想补充,显示出其重要作用。
疟疾之所以成为一个持续的全球疾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疟原虫复杂的生命周期[6]。引起疟疾的疟原虫生活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终宿主按蚊体内的有性生殖,红细胞内配子体的形成,为有性期的开始;第二阶段则是在中间宿主人体内的裂体增殖,感染后虫体在肝细胞内的发育和裂体增殖,形成成熟的红外期裂殖体(exo-erythrocytic schizont),在涨破被寄生的肝细胞后,以裂殖子(merozoite)形式释放,经血流侵入红细胞,随之开始红内期裂体增殖过程。
针对疟原虫发育的不同场所或时期,人们研制了以下三类疟疾疫苗:红前期(肝期)疟疾疫苗、红内期(血液阶段)疟疾疫苗以及蚊期的传播阻断疫苗。就疫苗的有效组成成分而言,可将其分为全虫减毒活(Whole, attenuated live parasites)疫苗和亚单位(Subunit)疫苗[7]。目前抗疟疫苗研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①疟原虫生活史较为复杂,在宿主体内经历多个发育阶段,且每一阶段表达的抗原不尽相同,多达数百种的独特抗原使得疫苗的研发相对困难。②疟疾感染后,机体的保护性免疫应答机制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未知的,针对某一阶段的免疫反应可能无法在以后的阶段提供保护。③作为生物制品的抗疟疫苗的安全性问题颇具争议。虽然大量的实验已经证明全虫疫苗可以对已识别的同种虫株提供持久的保护[8],但是减毒活全虫疫苗的性质并不十分稳定,因而在实际应用中亦受到限制[9]。④现有疫苗候选抗原的免疫原性较弱,抗原变异及存在的多种免疫逃避机制也增加了疫苗研发的难度。⑤缺乏合适的佐剂(adjuvant)或载体(vector),亚单位疫苗在流行区的表现低于预期,但若辅以强效的佐剂/载体将发挥极佳的抗疟潜力,极大地提高疫苗的有效性。
1 红细胞前期疟疾疫苗(Pre-erythrocytic malaria vaccines)
红前期抗疟疫苗,旨在临床症状(寒战、发热等)出现前对原虫的发育进行遏制,即对孢子虫侵袭易感机体肝细胞的过程进行阻断,抑制或杀灭已进入体内而尚未进入肝细胞前的子孢子,阻止肝期(红细胞前期)疟原虫感染,本类疫苗以降低疟原虫感染率为指标。
目前研究最为先进的是已进入IV期临床试验的RTS,S亚单位抗疟感染疫苗,该疫苗可对婴幼儿临床和严重疟疾提供部分的保护性效应,故而其研究目标在于降低临床疟疾的发病率以及减少年幼儿童中严重病例的发生[10]。RTS,S/AS01是由一种基于脂质体的佐剂(AS01)和乙肝病毒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病毒样的颗粒组成,核心是由源于恶性疟原虫(Plasmodiumfalciparum)的环孢子虫蛋白(Circumsporozoite protein,CSP)基因融合于Hepatitis B Virus(HBV)基因表面形成。有研究表明,6周龄至17月龄的婴幼儿可对恶性疟原虫及B型肝炎病毒产生主动免疫。基于RTS,S最初的研究表明其可保护流行区志愿者不受同源虫株的感染。相关研究中新生儿接种后可获得良好的耐受,不良反应主要为发热,但产生相对较低水平的免疫应答。新的研究证实RTS,S/AS01 在疫苗接种后的一年内均可产生有效的保护性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疫苗的效力逐渐减弱[11]。在一个包含223例5~17月龄儿童给予3剂疫苗后长达7 a的随访中,由负二项回归分析评估的疫苗效力仅为4.4%(95%置信区间[CI], -17.0 to 21.9; P=0.66)[12]。这一问题或可通过加强针(第4剂)的注射来弥补[13]。最新临床试验的数据表明,RTS,S/AS01 疫苗不论是在合并接种/不接种增强针的情况下,都可在3~4 a内预防低龄婴幼儿临床疟疾症状的发生[14]。此外,在接种增强针的两个年龄段患者中(34~41/39~50月龄),疫苗效力(Vaccine efficacy,VE)的提高均得到了证实,其中34~41月龄组为18.3%→25.9%,39~50月龄组为28.3%→36.3%[15]。除此之外,在5~17月龄组中,该疫苗的总体效力也取决于当地寄生虫种群中与之匹配的等位基因所占的比例,这对于今后的研究又提出了新的方向[16]。若在高危地区,将此疫苗与其他有效控制手段联合应用,将极大地发挥防控疟疾的潜力[17]。
基于恶性疟原虫子孢子的疟疾疫苗(PfSPZ-based malaria vaccines)研究广泛开展。目前,最早被研究的放射减毒活疫苗(radiation-attenuated sporozoites,RAS)已进入II期临床试验阶段。RAS通过一定剂量的辐射诱导保护使原虫转化为不具有感染性的裂殖体,从而阻止其感染。目前市场上暂无该类亚单位疫苗销售,也就是说,我们尚不能通过接种该疫苗而避免全球每年约2.16亿感染病例的产生。但是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RAS可呈现出剂量-阈值效应,即通过注射最大剂量获得最高的无菌保护效应[18]。可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基因减毒孢子虫(Genetically attenuated parasites,GAP)疫苗与药物减毒子孢子(Chemoprophylaxis and sporozoites/ Infection-treatment-vaccination,CPS/ITV)疫苗都处于I期临床研究阶段。CPS/ITV策略则是通过抗疟药物(氯喹CQ、青蒿琥酯AS等)化学预防,在一定覆盖范围内抑制或清除肝细胞内寄生(裂体增殖)阶段寄生虫而达到抗感染的目的[19]。它的优势在于,可通过与抗疟相关的化学药物的联合注射,强化疫苗的效力,故较之于RAS可以更为有效地降低疟疾的感染率[20]。新近的人体试验结果表明,联合CQ进行化学预防(PFSPZ-CVac)的新型疫苗在最后一次注射后的10周内,该疫苗仍能对受试者提供100%免疫保护[21]。目前研究人员又通过一种新的前临床鼠疟模型对CPS-CQ疫苗进行了相关实验,结果表明使用来自肝阶段的P.falciparum孢子虫(Pfspz)联合氯喹免疫DRAGA鼠可以诱导更强的抗体反应,继而产生更强有力的保护,未来有望在人体试验中达到更好的红前期(肝期)免疫保护效果[22]。GAP则是通过敲除或双敲除特定基因(如p36/p52等),使处于肝脏的晚期发育阶段的或一旦释放进入血液阶段的原虫立即被捕获而避免后续的感染发生,并且不需要注射抗疟药物。在P.berghei鼠疟模型试验中已经证实注射PbΔb9ΔslarpGAP后,不仅诱导了高水平的保护效应,并且未出现疫苗免疫失败[23]。由于在肝脏阶段被捕获的基因减毒疟原虫,可作为强有力的免疫原,进而对抵抗孢子体相关的疟疾感染提供完全的、持久的保护。新的研究通过在P.yoelii鼠疟模型中PlasMei2 和 LISP2(Liver-Specific Protein 2)两个基因的敲除,合成了一种致死的表型(即P.yoeliiplasmei2-/lisp2-),使得在原虫感染后的3 d内即可在肝脏晚期阶段被清除,从而避免了向红内期阶段的突破性感染[24]。这些发现为今后对引起人体疟疾感染的P.falciparum的探索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即创建一个完全的、恶性疟原虫相关的基因减毒孢子虫疫苗,这对于人疟的控制意义重大。
2 红细胞内期疟疾疫苗(Blood-stage malaria vaccines)
红内期抗疟疫苗发挥作用是通过抑制pRBC(parasitized red blood cell)内原虫的增殖发育以干扰感染RBC的黏附过程,可针对于预防感染的疫苗起到补充的作用。诸多流行病学研究为血液阶段疫苗的可行性提供了有效支持[25]。P.falciparum是一种致命的专性细胞内寄生虫,在宿主体内可通过一系列的寄生虫蛋白而加速红细胞的侵袭,其中裂殖子顶端膜抗原1(Apical membrane antigen-1,AMA1)作为存在于P.falciparum中的一种膜蛋白,是寄生虫裂殖子完成侵袭过程所必需的。人们对AMA1的疫苗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在一项试验中,使用来自P.falciparum的AMA1-3D7 蛋白与佐剂系统AS02A 进行重组 (即FMP2.1/AS02A),这一基于AMA1的疫苗增强了对疟原虫的生长抑制,然而这种作用与疟疾流行季节的等位基因特异性无关[26]。在实地研究中我们得到证实,仅单独应用AMA1疫苗虽可对部分同源寄生虫产生免疫应答,然而在同源性CHMI的实验中却未能提供保护性效应[27]。最近的一项动物免疫研究表明,联合注射AMA1和RON2(Rhoptry neck protein 2)肽复合体(即亚单位疫苗AMA1-RON2)可产生保护性作用,使小鼠虽感染P.yoelii但并不发病[28]。目前AMA1相关疫苗尚处于前临床研究阶段,但这些研究结果为以后实地对与临床疟疾相关免疫保护功能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并且有助于对下一代疫苗的研发进行相似的分析。
除此之外,P.falciparum中存在的网织红细胞结合类似同源蛋白5(Plasmodiumfalciparumreticulocyte-binding protein homologue 5,PfRH5)也是一种被广泛研究的亚单位候选疫苗。在原虫入侵RBC这一复杂过程中,PfRH5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寄生虫配体而与RBC受体结合。它具有有限的多态性,并可诱导产生一种强效的中和抗体。然而,缺乏跨膜结构域与GPI(Glycosyl phosphatidyl inositol)锚定[29],因此针对PfRH5疫苗的研究目前进展到Phase I阶段。先前的研究表明,该疫苗可诱导多克隆抗-PfRH5抗体的产生,从而抑制裂殖子与红细胞的紧密附着,并且具有干扰PfRH5与其受体蛋白之间相互作用的能力[30]。体外实验中抗-PfRH5血清抗体在功能上表现出对不同株系的生长发育抑制活性(Growth inhibition activity,GIA),并且该抗体靶向于RH5构象性抗原表位,在RH5侵袭复合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交互抑制作用[31],就P.falciparum而言,该疫苗具有不可预期的广阔前景。
抗红细胞内期原虫疫苗的优势在于不论是同源还是异源虫株均可诱导强有力的免疫。人们在美国和肯尼亚西部地区进行了一项试验,结果表明受试者的血清在生长抑制试验中产生了高滴度抗MSP1(Merozoite surface proteins 1)抗体,其对于血液阶段寄生虫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尤其是在美国的志愿者中,异源MSP1 等位基因与基于MSP1的疫苗(3D7等位基因)相比,产生的抗体表现出更好的交叉反应能力[32]。JAIVAC-1是针对恶性疟原虫而开发的一种候选疟疾疫苗,它是由PfMSP-1的C末端19 kD的保守区域与Pf受体以及F2功能区的EBA175结合而成,即PfMSP-1(19)。注射接种后,志愿者对JAIVAC-1 耐受良好并未观察到严重不良反应(Serious Adverse Drug Reaction,SADR)的发生。此外,从接种者血清中纯化出的IgG抗体,对P.falciparumCAMP株的生长有显著的抑制功效[33]。随着对有效的血液阶段抗疟疫苗研究的开展,发现了一种加速抗疟疫苗研究的方法,即在非流行区通过控制人类疟疾感染来尽早地对已筛选的疫苗进行有效性测试[34],这有助于及时剔除无效的候选疫苗,并发现更多的具有保护性免疫特征的疫苗。
3 传播阻断疫苗(Transmission-blocking vaccines,TBVs)
传播阻断疫苗是一种用于干扰疟疾传播的针对寄生虫有性阶段发育的疫苗,其首要目标是阻断中间宿主人-媒介按蚊-人之间的疟疾传播[35]。TBVs通过提高宿主群体免疫力,主要是针对蚊胃阶段细胞外疟原虫发育阶段,从而减少感染的发生,继而对传播形成有效控制。已经发现的具有传播阻断活性(Transmission blocking activity, TBA)的候选抗原主要有Pfs25、Pfs48/45、Pfs230、Pfs47、Pvs48/45、PfGAP50、AnAPN1(Alanyl aminopeptidase N)等[36-39]。研究较为成熟的两种主要的亚单位疫苗中Pfs25和Pfs230均处于I期临床研究阶段,而仅出现在雌配子表面的Pfs47则尚处于前临床研究阶段。其中Pfs25为配子受精前靶抗原,而Pfs230则为受精后靶抗原。这两种抗原候选疫苗的TBA都取决于原虫的暴露程度以及抗体的滴度,即在一定范围内,随着接触寄生虫的减少,抗体滴度的增加,它们的效力也随之提升,疟疾的传播随之减少[40]。Pfs47在自然的P.falciparum种群中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这种现象与通过蚊免疫系统进行的单体型自然选择有关[41]。它可介导疟原虫的免疫逃避,并可抑制在按蚊中肠进行的消化反应[42]。由于已发现的这些关键功能使得Pfs47有望成为阻断疟疾传播的又一靶点,对其研究将更加广泛深入。本实验室主要从事疟疾传播阻断疫苗(TBVs)的研究(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支持)及疟原虫有性阶段特异性基因的功能分析(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批准)。由于TBVs主要靶向原虫的有性阶段(即蚊体内阶段)进而发挥阻断效应,生活史中蚊胃内配子体(gametocyte)的发育以及由动合子(ookinete)形成卵囊(oocyst)的过程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相关蛋白质又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43]。基于生物信息学分析及鼠疟模型的构建与研究,我们识别到有性阶段中一个高度保守的蛋白Plasmodium PbPH (PBANKA_041720),其所包含的PH结构域(Pleckstrin homology domain)可对传播阻断活性产生重要影响。Pbph基因对于P.berghei有性阶段的发育十分必要,尤其是在体外实验中重组蛋白可显著影响雄配子的形成[44]。同时,动合子分泌蛋白(Putative secreted ookinete protein,PSOP)极具传播阻断潜能,尤其是PSOP7(PBANKA_135340)与PSOP25蛋白。其中PSOP7主要表达在原虫的合子及成熟动合子阶段,而PSOP25则在Retorts阶段也有表达(间接免疫荧光试验,IFA所证实)。本实验室通过对伯氏疟原虫ANKA株这两个基因截短片段(即rPbPSOP7与rPbPSOP25)的成功克隆与表达,发现重组rPbPSOP7蛋白具有较强的抗原性及免疫原性,在所建立的P.berghei感染小鼠模型中于实验鼠体内可诱导极强的体液免疫应答反应,并随之产生相关的特异性抗体。在直接蚊饲试验(Direct mosquito feeding assay,DFA)中,发现被动免疫即注射抗-rPSOP25单克隆抗体(anti-rPSOP25 mAb),可以降低感染率(31.2%→26.1%)并引起卵囊密度小幅减少(66.3%→63.3%)。PSOP25 基因敲除实验表明,该基因可显著影响动合子成熟及中肠卵囊的形成[45]。以上研究结果为PSOP7和PSOP25蛋白成为潜在的TBVs候选抗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我们对另外两个公认的动合子阶段蛋白(即PBANKA_111920和PBANKA_145770)的研究发现,使用该重组蛋白免疫小鼠后可显著降低卵囊密度(60.0%~70.7%)及适度抑制卵囊形成(10.7%~37.4%)[46]。尽管TBV在病媒传播疾病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目前候选TBVs抗原尚为有限,亟待识别新的抗原,未来仍需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47]。
4 多抗原、多表位重组疟疾疫苗(Multi-antigen/Multi-epitope recombinant malaria vaccines)
疟原虫进化中抗原的不断变异为其逃避宿主免疫捕获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也增加了相关疫苗研发的难度。由于虫体相关抗原多种多样,变异广泛,不同抗原又存在各异的抗原决定簇(Antigenic determinant,AD),即抗原表位。仅针对某一抗原或单一表位的抗疟疫苗有时并不能发挥预期的疗效,因此针对多种抗原、不同抗原表位进行的疟疾候选疫苗的研发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多抗原、多表位重组抗疟疫苗可对人体提供多阶段的保护性作用,具有绝对的优势。
重组B疫苗作为第一个具有等位基因特异性效应的血液阶段多抗原抗疟疫苗,它包含MSP1(K1等位基因)、 MSP2(3D7等位基因)及RESA (FCQ-27/PNG 等位基因) 抗原并且与油佐剂 Montanide ISA720 混合使用,在II期临床试验中,接种该疫苗的疟疾暴露儿童感染MSP2的3D7形式的疟原虫的几率小幅下降。
疟原虫随机重组抗原-1(Malaria Random Constructed Antigen-1, M.RCAg-1)包含了来自8种恶性疟原虫的11种抗原表位,作为评估流行区疟疾传播强度的一种新的血清学标记物[48],是公认的可在恶性疟原虫感染患者中自然获得的抗疟抗体,并且其与间日疟原虫感染的交叉反应非常有限。针对这一抗原所研制的候选疫苗(多表位重组蛋白疫苗)已在动物模型中得到证实,其具有较强的免疫原性,并且在体外试验(invitro)中可以抑制恶性疟原虫的生长增殖。但是如果以纳米乳单独作为该重组蛋白疫苗的佐剂,其效应较弱,需要添加其他免疫增强剂。
目前,本实验室基于联合免疫的理论,将已筛选出的具有良好传播阻断活性的候选抗原进行两两联合,即通过构建多抗原重组疫苗的方法以期获得更好的传播阻断效果。在现有P.berghei鼠疟模型的基础上展开研究,我们通过原核表达系统表达截短蛋白(截取优势抗原表位区),并对优质候选蛋白进行双组合,显著提升了传播阻断能力,后续研究正在进行中。
5 多阶段融合蛋白疟疾疫苗(Multistage fusion protein malaria vaccines)
多阶段融合蛋白疫苗的研发对于间日疟的控制具有重大意义,这是由于肝阶段中存在的休眠子孢子以及早期形成的配子体使得由P.vivax所致的疟疾在宿主临床症状出现前即可造成传播。靶向红前期和有性阶段疟原虫的多阶段疟疾疫苗可以有效保护个体,不仅可避免由蚊虫叮咬而引起的感染,同时针对有性阶段的疟原虫又可产生传播阻断活性。这一策略可能预防个体疟疾的感染,在更大规模上,也可阻断流行区疟疾在社区内的传播。新概念疫苗BDES-Pvs25-PvCSP兼具亚单位疫苗和DNA疫苗的功能,通过在体外实验中利用杆状病毒双表达系统(Baculovirus dual-expression system,BDES)转导入哺乳动物细胞中可高度表达,并可在病毒包膜上产生Pvs25-PvCSP融合蛋白,具有正确的空间构象,所诱导产生的高滴度抗体在鼠疟模型(实验所用疟原虫为可表达P.vivax相关抗原的转基因P.berghei)中可产生诱导性保护效应(43%)以及良好传播阻断活性(82%)[49]。
6 展 望
红前期抗疟疫苗可规避向红内期突破性感染的风险,相当于对原虫的体内感染进行了源头的控制,若能借助分子生物学技术进一步对亚单位疫苗RTS,S/AS01进行优化,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早投入临床使用,其必将成为疟疾控制的有力工具。此外,可在现有鼠疟模型的基础上对孢子虫相关疫苗(RAS、GAP、CPS等)在人疟相关研究上继续进行探索,如能开发出对耐药性恶性疟原虫行之有效的疫苗,将对于全球疾控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由于疟原虫对人体的致病作用主要是由红内期原虫裂体增殖所致,因此这一阶段的疫苗对于控制疟疾发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迄今为止,研究发现的无性血液阶段疫苗候选抗原十分有限,未来对潜在的候选抗原的识别是非常必要的。就红内期亚单位疫苗而言,未来仍需积极寻找合适佐剂提高疫苗的免疫保护效率和延长保护作用的持续时间。除此之外,或可通过提取红内期全虫疟疾疫苗的有效成分,将其纳入多阶段抗疟疫苗的研发之中,建立抗疟疫苗新的研究方略。
蚊途径的传播是疟原虫感染过程中一个主要的瓶颈,而这同时也是对疾病传播进行干扰的一个主要靶点[50]。传播阻断疫苗是目前最为理想、最具潜力的疟疾疫苗,较之于肝期、红内期疫苗而言,其可免受宿主机体免疫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作为预防性疫苗其前景广阔。然而目前的研究尚有局限,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倒如,保证重组蛋白异源正确、高效地表达(TBA产生的前提)[51],如何识别更多潜在的候选抗原等。理论上,血液阶段抗疟疫苗可降低疾病的发病率,减少死亡率[52],然而原虫减毒疫苗的安全性尚存在广泛争议,亚单位疫苗的效果也有待提高,如果能对重组蛋白所诱导产生的抗体的保护性效应进行提升,未来必将有所突破。
无论是多抗原、多表位重组疫苗,或者是多阶段抗疟疫苗,其本质都是基于联合免疫的理论,我们追求的是产生“1+1≥2”的效应,将不同疫苗间的相互干扰作用降到最低,继而降低疫苗有效性的风险比率,从而最大限度对人体提供保护性作用,这需要我们通过不断优化疫苗的配方、调整疫苗的有效成分等进行深入探索。除此之外,可以将转基因疟原虫与体内(invivo)前临床试验模型结合起来[53],用以评估候选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并发现关键的保护性免疫反应,从而提高疫苗的接种策略。未来的研究或可集中于识别跨阶段的保护性疟疾抗原,从而使多阶段抗疟疫苗的开发成为可能。
疟疾疫苗成功的另一关键限制因素是在免疫接种后机体难以维持长久的保护性,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归因于抗原免疫原性的缺乏,以及疟疾本身对宿主反应的抑制。尽管一种高效的针对疟原虫的疫苗的开发已经被证实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54],但是借助蛋白质组学技术将有助于发现潜在的新候选疫苗抗原[55], 基于扩增的深度测序技术有助于了解潜在的抗原异质性、疟疾寄生虫的种群遗传学因素以及影响复杂、多克隆疟疾感染的相关因素[56]。一个成功的疫苗既可强烈诱导持续的保护性免疫反应,又能降低免疫接种后严重不良反应(SARS)出现的风险。由于在临床研制和开发中,大多数候选疫苗都是高度纯化的蛋白质和多肽,它们依赖于佐剂来增强或直接免疫应答[57]。传统的铝佐剂因存在毒性而应用受限,可通过寻找新型佐剂(如纳米乳佐剂、微晶酪氨酸MCT等)并与之结合使用,在增强免疫原性的同时,使抗体活性的持续时间延长,继而研制出理想的抗疟疫苗。
——“零疟疾从我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