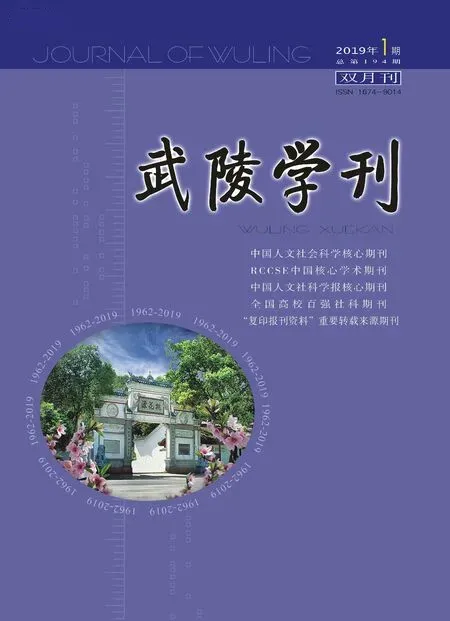“京派”诗歌与早期新诗抒情主义的修正
——以《水星》杂志中的作品为例
王辰龙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抒情主义:新诗现代性的一种维度
1932年,“九·一八”事变尚未久远,失去北方屏障的北平与战争前线的距离越来越近。这一年三四月间,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到私立北平辅仁大学做了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列讲座,后据记录整理出版,是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下简称《源流》)。与胡适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样,周作人也尝试以归纳旧文学的方式,找到新文学发生的历史源流,并为日后的白话文习作提供可凭借的古典圭臬。周作人认为,中国文学史上有两种潮流,言志派和载道派,他进而断言:“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1]22也就是说,周作人以一种二元循环的模式看待古典文学的发展,其中一派的衰落将为另一派的兴盛所接续,如此周而复始,生生不息。那么,以周作人的美学趣味去判断,哪一派的文学更卓越呢?答案是言志派。因为“言志派的文学,可以换一名称,叫做‘即兴的文学’,载道派的文学,也可以换一名称叫做‘赋得的文学’,古今来有名的文学作品,通是即兴文学”[1]45。体裁上,“即兴”往往与诗歌联系在一起,修辞上,“即兴”的典型呈现形式则是抒情,这样看来,“即兴”与感情更近一些。也就是说,在周作人的思想中,言志之“志”偏重于感情。言志之“志”的内涵,是很复杂的问题,至今有待持续的学术讨论,本文暂且不论周作人的判断是否准确,可以认定的是,这种对文学情感性的强调符合知堂先生的文学观念。对此,在《源流》中,他声称:“我的意见,说来无异于这几句话的。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若必谓为是有目的的,那么也单是以‘说出’为目的。”[1]17
周作人对感情的强调,所针对的是近代中国以来文学工具论的实用主义思潮。关于新文学的来源这一关键问题,周作人认为:“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1]36明末文学的代表是以袁氏兄弟为核心的性灵派,而他们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都是情感至上的,属于言志派的范畴。这无疑是在说,新文学也是言志的文学,周作人将情感提升到高于道德、理性的地位。仅就新诗的发生与发展而言,情感也始终处于被推崇的至高地位,常常被诗家与论者用以定义诗歌的本体。开新诗风气之先的郭沫若在致宗白华的信中写道:“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为诗。”[2]宗白华也与郭氏所见略同:“诗的‘形’就是诗中的音节和词句的构造;诗的‘质’就是诗人的感想情绪。所以要想写出好诗真诗,就不得不在这两方面注意。”[3]康白情同样将情感视为新诗的本质:“诗是主情的文学;诗人就是宇宙底情人。那么要作诗,就不可不善养情。”[4]成仿吾则认为理智将伤害新诗的写作:“象吃了智慧之果,人类便堕落了一般,中了理智的毒,诗歌便也要堕落了。我们要发挥感情的效果,要严防理智的叛逆。”[5]相似的说辞层出不穷,在此仅举1920年代的几个著名例子。对情感的重视与主张,作为一种时代潮流,令梁实秋不禁感叹:“现代中国文学,到处弥漫着抒情主义。”[6]2
对情感与抒情的重视,确有外来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更重要的生成因素则是中国古典文学自身的传统,这一点只要想想抒情诗在文学史上的塔尖位置就不难理解。新文学的主流长久以来被视为文学的功利主义,但事实的情况或许没有如此简单与一元,不难发现,“五四”以来,“作为单元观念的‘抒情’纵贯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剧情主线之中……在‘革命’和‘启蒙’之外,‘抒情’其实代表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主体建构——的另一面向”[6]2。纵观新诗前三十年的发展,主张“纯诗化”的象征派与现代派,与推崇“大众化”的左翼诗人群体,始终在对立与交锋,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对抒情主义的接受,进而呈现出了纯诗化的抒情主义与大众化的抒情主义两种形态。前者重视个人主体的情感,将其视为诗的本体;后者重视社会共同体的情感,将其视为政治变革的力量[6]13-20。讨论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不能绕开抒情主义这一重要的维度。因此,我们需要澄清抒情主义在中国新诗中所体现出来的内涵,本文采取当代学者张松建的观点:“它首先指的是诗学本体论上的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独尊情感乃至神化情感,有时漠视了深化生命体验或者开阔社会视野的必要性。有时执迷于神秘灵感、个人天才之类的古老信仰,对诗歌作为一门‘手艺’(craftsmanship)的认识不足,意识不到语言组织能力、技术历练以及知识积累的重要。在技术运用上,抒情主义忽视了节制内敛、艺术规范与形式约束,有出现感伤主义之虞。不仅如此,抒情主义者习惯于提升抒情诗在文类结构中的地位,缺乏文类多样性的意识,甚至压抑、贬斥和抹杀其他诗歌样式的合法性,而且即使对抒情诗自身也有狭窄和偏颇的理解:仅仅把抒发激情作为辨识抒情诗的身份标志,排斥了宁静的心境、恬淡的妙悟或者轻灵细微的感觉之转化为抒情诗内容的可能。抒情主义者有时夸大诗中哲理与情感的不相兼容。”[6]6
二、“京派”诗歌及其特征
之所以要花费上述篇幅来谈论抒情主义,是因为“京派”诗歌在追求现代性时必须要面对它。作为新诗的现代派,“京派”诗歌理应被纳入“追求‘纯诗’的文艺思潮”[7],进而带有“纯诗化的抒情主义”特征。但如果仔细辨析的话,不难发现,“京派”诗歌在认同抒情主义部分准则的同时,也试图对它的不足作出弥补或修正。“京派”诗歌并不反对抒情主义,“京派”文人论诗时也对情感极为看重,往往将其视为区分散文与诗歌的核心范畴之一。1930年代的北平也是一处适于抒情诗的文学生产场域。从20年代中后期开始,“五四”时期的文化领袖大规模南下,北平城失去了“五四”时期众声喧哗的热闹与激情,对留居旧都的知识分子而言,“一方面,军阀政治的腐败与暴力使得知识分子放弃了那些敏感的政治话题,进而使得这座城市逐渐远离流行于上海的有关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爆炸性争论。另一方面,西方技术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并没有像吞噬上海般地卷食北京”[8]200。相对于上海的高度资本主义化而言,北平类似一处前现代的时空,它的生产方式、存在形态都与乡土中国更近。简言之,1930年代的北平充满了与资本主义/物质主义不同的乡土情结,由此也塑造了“京派”文人批判现代都市、缅怀外省地方性的思维模式与情感结构,与这种模式、情感相配的正是一种“受约束的、简明的、空闲的、温和的、传统主义的和抒情诗体的非功利美学”[8]201。考察“京派”诗歌的现代性,确实不能忽视其抒情主义的维度,但需要指出的是,“京派”对抒情主义的弥补与修正,却更为值得关注,原因在于这种反思的诗学姿态结合着写作的实践,是“京派”诗歌对新诗现代性最有力的贡献。
滥觞于新诗写作中的抒情主义,究其内因,是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所谓诗意是这种传统的一个核心范畴,现代文人在论诗时也频繁地使用这一概念,是否具有诗意往往成为衡量诗歌价值高低的准则,古诗与新诗之间的文学政治关系也由此发生:古诗似乎天然地就具有诗意,而新诗总是诗意不足;新诗应该像古诗学习,朝有诗意的方向多多努力;古诗是高于新诗的美学范畴。可以说,诗意成为了一种话语,“它为诗歌假定了一个美学任务,即凡是诗就必须表达‘诗意’……它就有超时空的审美归化的能力,这种能力如此内在,如此本质,以致于它完全有能力磨平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的异质性。其次,它为诗歌预设了一个先验的本质。也就是说,可以不涉及任何前提,不顾及不同时代的诗歌实践的差异,不考量不同风格类型的诗歌美学的区别,‘诗意’就天然地判定为诗的本质了”[9]。古典诗歌美学的长期积累令诗意的内涵趋于单纯,它往往是作为优美的代名词而出现的,但现代诗的宿命是它需要处理现代生活中很不优美的部分,因此,抒情主义的文学政治地位有窄化新诗现代性的危险。
从文学理论层面上,“京派”文人们纷纷展开了对抒情主义的反思,这里仅举李健吾与叶公超的例子。在谈及徐志摩的诗歌时,李健吾认为:“他后期的诗章与其看作情感的涸竭,不如誉为情感的渐就平衡。他已经过了那热烈的内心的激荡的时期。他渐渐在凝定,在摆脱夸张的辞藻,走进(正如某先生所谓)一种克腊西克的节制。这几乎是每一个天才者必经的路程,从情感的过剩来到情感的约束。伟大的作品产生于灵魂的平静,不是产生于一时的激昂。后者是一种戟刺,不是一种持久的力量。”[10]在李健吾看来,抒情过度会使言辞夸张,诗歌会缺乏持久而深入的表现力量,诗人有必要节制个人情感的泛滥。这种约束情感的写作不禁会让人想起T·S·艾略特为现代诗定下的“逃避个性”的美学准则,而“京派”诗人对抒情主义的修正也确实借力于艾略特。1930年代,叶公超大力引介艾略特,正是在他的授意与鼓励下,卞之琳翻译了《传统与个人的才能》①,赵萝蕤翻译了《荒原》②。艾略特在诗学理论与诗歌写作方面的现代主义并蹄莲深刻影响了“京派”文人对诗歌现代性的理解。叶公超曾亲自撰文两篇,系统介绍艾略特的诗学。叶公超认为:“爱略特的方法,上面已提到,是要造成一种扩大错综的知觉,要表现整个文明的心灵,要理解过去的存在性。”[11]119显然,所谓“扩大错综的知觉”“整个文明的心灵”,它们的深广度是抒情主义难以企及的。此外,叶公超还强调了艾略特对历史即传统的思考:“爱略特的历史的意义(见《传统与个人的才能》)就是要使以往的传统文化能在我们各个人的思想与感觉中活着,所以他主张我们引用旧句,利用古人现成的工具来补充我们个人才能的不足。”[11]125艾略特主张学习传统,对个人的才能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这无疑是对抒情主义神化写作主体的个人天才的一种反驳。
通过对艾略特的译介,以卞之琳为代表的“京派”诗人形成了主智的整体风格,其诗作更为冷静,对情感与思想的呈现方式也趋于内向与复杂。具体而言,“京派”诗歌的特征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动荡的时代环境下,不以直陈的方式去抒发个体的体验、情绪或见解,而通过书写常与秋日、黄沙等意象联系在一起的荒凉的北平城映射内心对命运不确定与时局不稳的实感;第二,发展了早期新月派“抒情客观化”的诗学主张,提倡“诗的非个人化”,将西方文学中的戏剧性处境与传统文学中的意境相融合;第三,从白话的语言节奏与古典诗歌的形式特征中探究新诗的格律化。可以说,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京派”诗人对新诗的抒情主义作出了修正,丰富了新诗现代性内涵。
三、“京派”诗歌对早期新诗抒情主义的修正
探讨“京派”诗歌对早期新诗抒情主义的修正,为什么要选择《水星》中的诗歌呢?首先,《水星》是在“京派”文学上升期发行的一份重要的纯文学刊物,刊载了“京派”文学的许多名篇。“京派”文学上升期在1933—1937年间,其标志是《大公报》的三个由“京派”文人主持的纯文学副刊的相继出现,“1933年9月23日,由沈从文和杨振声主编的《文艺副刊》创刊。这个副刊的诞生预示着新文学在《大公报》的正式登场。1935年7月4日,萧乾接编《大公报》最有影响的一个通俗消闲副刊《小公园》,在沈从文、林徽因等京派作家的帮助之下,《小公园》经过萧乾大刀阔斧的改造成为又一个新的文学副刊。1935年9月1日,《文艺副刊》和《小公园》合并成《文艺》。无论是主编人选、编辑方针、作者队伍、作品内容,《文艺副刊》、《小公园》和《文艺》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连续性,它们作为京派文学的重要阵地,展示了京派作家群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活动。”[12]35《水星》创刊于1934年,终刊于1935年,存在时间正处于“京派”文学最为辉煌的上升期,而在它的主编人员中有“京派”主将沈从文,执“京派”诗歌牛耳的卞之琳以及“京派”文学理念的代言人李健吾,因此,《水星》是一处足以代表“京派”文学理想的聚集地。其次,选取《水星》中的诗歌作为讨论“京派”诗歌与新诗现代性之关系的分析对象,也旨在扩大研究视野,使目光不局限于卞之琳等已被文学史辨识出来的重要“京派”诗人;与此同时,《水星》总计刊载诗歌38首,其中不乏何其芳《箜篌引》、卞之琳《距离的组织》这样的名作,亦有诸如骆方《两世界底中间》、易椿年《夜女》、孙毓棠《河》等虽不知名但堪称杰作的篇什,这些作品借助一份刊物聚合于同一个时空,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的生态多样性,以此作为分析对象将使研究工作更为切合历史的真实,以防得出失之偏颇的结论。
典型的抒情主义新诗,往往会因对个体情感的专注而令文本的容量趋于褊狭,缺乏处理复杂的、外在的总体性景观的诗学向度,这一点也招致了诸如新诗与时代脱节一类的严苛指责。“京派”诗人的新诗,虽不以现实主义的内容说或再现论为宗旨,却以开放的诗学视野、复杂的修辞手段从事实上扩展了文本的容量。可以说,对新诗容纳空间的延展,是“京派”诗歌对新诗现代性的重要丰富,这一点也可从《水星》上的新诗见出。骆方的《两世界底中间》涉及到了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主题:工业化对乡土时空的冲击,现代性与古典中国的碰撞。所谓“两世界”,一个是指典型的中国乡村,在那里,“煤油火旁两个老农/指手划脚地谈讲千年前的故事,/侧着耳听听机械与蟋蟀底合奏/在心底跳着原始人舞”;另一个则是被工业占用的土地:“林立在天空里的/烟囱里的黑烟/冲散茅屋顶上晚炊底白烟,/在天边砌成一道高墙/紧围着被炎阳漂白了的田野。/上帝披着黑袈裟/站在蔚蓝的天心——/聋了耳,又瞎了眼。”[13]诗中多场景的切换,恍若电影蒙太奇,主体声音的发出者也随场景的变换而转移,从作为在场者与观察者的“我”,到倦行的工人行列,再到一位纺织女工,多种声音交织在一起,避免了主体情绪的独白。与此同时,每一种声音都表征着各自对处境的反应,以戏剧化的手法将现实体验以及批判的向度复杂化了:“我”厌恶工业文明对乡土文明的破坏,在工厂机器的轰鸣声中,“我”的内心满是被压榨、被索取的屈辱(“我不能忍受/蒸汽引擎地飞轮咆哮着/要突破铁的窗槛/威胁颤动在煤烟里的稻禾,青菜”);倦行的工人们为了生存,虽痛苦,但依然要走向那些已经侵入乡村的工厂(“他们向对面来的赶路的陈述:/你是谁?/你们从那儿来?/啊!啊!老乡啊!回去啊!/……/两队人各向各自的路前进——咬紧着牙齿,/咽下眼泪”);纺织女工则为工业化图景而陶醉(“纺织娘在矮林里/低咏着恋歌/循着工厂里的乏气/指挥机械的豪壮的旋律。/草叶底香,流水底香——/我吸着,心里充满感激:/朋友!来啊!/来瞧瞧这些线条底美丽的图案!/来听取这和谐的,优美的交响乐”)。
现代性在近现代以来对中国发起了突然袭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推动城市化的同时,也瓦解了农业文明长久以来的稳定秩序,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共存开始成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现实之一。乡村经济的大规模破产,使乡土充满了剩余劳动力,为了生存,这些劳动力必须前往城市。新文学始终在关注城里的农村人这一主题,其中,著名作品之一是老舍的《骆驼祥子》。在《水星》第1卷第3期上,也有一首作品写到了类似的主题,那就是易椿年的《夜女》。诗中的“夜女”即通常所说的站街女,诗人的这种命名方式,造成精致优美的所指效果,这与其残酷的能指之间形成了一种背反的张力关系。制造张力,也是贯穿整首诗作的修辞方式,一面是妓女讨生活的残酷生存经验(“有着乡土味的娇慵的病意/已被积重的生活压碎了:街头虽有揶揄的眼光和话语,/但你的耳目已密织了。/奈不幸者的最后的梯层上/也踏着法律的足印”[14]),一面是夜晚平静祥和的都市街景(“紫色的晚街上/又浮着你没有音符的步履了”[14])。诗中的都市因夜色的涂抹而显出恍惚的样态,如罩雾中,“夜女”与嫖客们都仿佛被遮蔽在了一道半透明的帐幕之后,只有身体的轮廓若隐若现,没有面孔和表情。在大都市,人们似乎渐渐成为没有姓名的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被拥挤的人群、快速的交通与高层的单元楼所分割,乡土中国中典型的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遭到了破坏,人与人彼此成为了陌生的他者。这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是一种新鲜的体验,而诗中恍惚的语气,也表征了新经验令人难以适从的感受。这首作品将内心的独白与外部的描绘糅合在了一起,随着诗行的推进,“夜女”的思绪从都市中跳脱到了对乡村生活的回忆之中(“你的含愁的脸,/虽织缀以欢笑的颜色,/但当你想起母亲和发霉的家时,/你的脂粉颤落了……而牧归的恋笛呢,/葡萄树下的年青人呢”[14]),而她实际所处的城市时空则构成了对回忆的威胁(“在风之萧索里,/雨之凄淋里,/这朦胧的往迹/会使你可望不可即吗?/但在陌生人的拥抱上/切莫触动你的心弦”),回忆的破灭意味着乡土中国的难以复原。诗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展开了对城乡二元对立的思考,并对都市糜烂的一面作出了反思与批判。此外,这首诗还有一个地方颇值得一提,诗中的一段:“你太忙的感觉里/镶着水兵的大领子的影,/垂着帽檐的人的徘徊,/插着裤袋的人的口哨,/和印度人的性感的笑脸……”[14]易椿年是在香港生活的文人,这首诗也写于香港,而香港作为英属殖民地,表征了现代中国需要应对的殖民化困境。很明显,这首诗中的城市是一个殖民地。《夜女》一诗不仅展示了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与此同时,也隐伏了中西之间的激烈冲突。
无论是工业化的图景展现,还是殖民化的局部传达,都是言说现代中国在现代性冲击下的灾变情形。对这种情形作出集中描述的,当属孙毓棠的《河》。孙毓棠试图以类似旧约的象征笔法,在新诗中写下现代中国人的“出埃及记”。诗中写到“两岸无边的荒沙夹住一条河”,河上挤满了出逃的船只,每一只船都杂乱、喧嚣,如同那末日过后的诺亚方舟:“舱里舱外堆着这多人,这多人,/看不出快乐,悲哀,也不露任何颜色,/只船头船尾挤作一团团斑点的,/乌黑的沉重。倚着箱笼,包裹,杂堆着/雨伞,钉耙,条帚,铁壶压着破砂锅;/女人们蓬了发,狠狠的骂着孩儿的哭;白发的弯了虾腰呆望着焦黄的浪;青年躬了腰,咸汗一滴滴点着长篙,紫铜的膀臂推动千斤的桨,勒住/帆头绳索上一股股钢丝样的力量。”[15]我们不知道这群惶惑的人为何要搬起整个家庭的根基作狼狈的出逃,但可知的是他们要去一个叫“古陵”的神秘地方,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我们到古陵去!到古陵去!”这首诗是对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处境、国人心境的整体性象征,诗人试图表明,在现代性的围攻之下,留给我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除了出逃别无他法。人们只好从没有粮食的地方出逃,从战事肆虐的家乡出逃,从旧中国出逃。摩西可以带着他的族人去约旦河的沿岸定居,进而成为某个民族的遥远源头,可对于出逃的中国人而言,那个被称为“古陵”的无比遥远、无比古老的乌托邦真的存在吗?诗人为此也是忧虑重重,正如诗中所追问的那样:“谁知道古陵是在什么所在?谁知道古陵/是山,是水,是乡城,是一个古老的国度,/是荒墟,还是个不知名的神秘的世界?”[15]没人能够回答,只有继续奋力地划船、前行。在这首诗中,不可知的终点与沿途的凶险,象征了现代中国的困境;而划船者的不懈努力,象征了我们民族的韧性与不屈,尤为重要的是,希望尚存于青年的肩头;那条联结起一切的河流则表征了充满现代性的时间。孙毓棠试图为民族塑像的野心,同样显示出了“京派”诗歌扩展自身容量的努力。
如果将上述诗歌放在一起来看待,我们会发现,“京派”诗歌与抒情主义并不对立,它们通过选取典型形象的方式将作为群体的现代中国人的体验与情绪抒发了出来,但这种抒发不是内向的、封闭的,而是基于对总体性社会图景的呈现,这种方式也正是“京派”诗歌对抒情主义的一种修正。可以说,在“京派”诗歌中,一个具体可感的、有立体时空秩序的现代中国终于出现了,这是它为丰富新诗现代性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对空间与主体关系的探讨本是叙述文学之能事,“京派”诗人将它引入了抒情文体。
总体性的社会图景中,都市是不可或缺的。《水星》上的新诗也不乏写都市的篇什,像上文中已谈及的《夜女》。此处仅以林庚的《都市的楼》、沈甲辰(即沈从文)的《北京》与沈启无的《牌楼》三诗为例。正如题目所示,林庚的诗将目光聚焦于城市时空中的核心景观——“楼”。“都市的楼中我看见对楼/女主人出现在凉台上”[16],对他人生活不经意的观看正在发生,居住在楼房中的居民甚至可以相互听闻,诗中就写到了温柔的琴声,只是主体无法确定琴声来自何处,正如他虽能看见出现的女主人,却对她的生活一无所知。楼宇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但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关联却未因此更近,楼宇实际上阻隔了人与人的接近。《都市的楼》一诗虽简短却触及了城市生活的奥秘。诗中的楼宇属于哪一座城市,这无从确知,但却不禁令人联想到上海(林庚也曾写过上海的雨天)。沈从文的《北京》与沈启无的《牌楼》都是写北京的诗。在沈从文的诗中,有一种由仰视到俯瞰的视角转换:先是写“天空中十万个翅膀接天飞,/庄严的长征不问晴和雨”,继而写“一列肮脏骆驼/负了煤块也负了忧愁,/含泪向长街尽处凝眸。/街头巷口有十万辆洋车,/十万户人口在圆轮转动下生和死”[17]。沈从文写北京是试图通过大景观的展现对北京生活作一种总结性的描述与思考,但诗人并不满足于此时此刻,主体的视角在诗的后半部突然转入历史和城外的远方,冥想起了城市如何建立、城市的生活如何被支撑的大问题,进而终究落入历史难以把捉的寂寞情绪中,诗歌题目不叫“北平”而叫“北京”,也是为了唤起一种超脱于当代的历史感。诗中的“风筝”“骆驼”与“洋车”,都构成了北京风俗的一部分,成为某段时期有关老北京生活的历史记忆。“牌楼”也是这种记忆的一部分。按照学者的定义,“牌楼又名牌坊,或简之曰‘坊’,是我国古代建筑中极为重要的一种类型,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发展到后期,其本身也集中了中国古建筑一些最具特征的构件——屋顶、梁枋、斗拱、雀替、柱、墙和须弥座,不啻如一座古典建筑的模型和标本,它们在异国他乡往往被视为中华文化的象征”[18]。作为一种装饰性的、能够起到街道分界作用的门面式建筑,牌楼曾聚立于北京城的街巷,至今仍有不少原址上的复建,最为著名的当属前门大街上的仿造“五牌楼”。沈启无的《牌楼》就呈现了这一旧京景观:“我爱看长街上的牌楼/风自萧条/人自纷纷/一朝而我看得我的牌楼偏有风尘相/于是我说我将不愿再看我的牌楼了/西方的远山远远的为我落一个颜色。”[19]
如上所述,都市时空的构建与城市生活的展示,也是“京派”诗歌对新诗现代性的一种丰富。在写都市的作品中,梦与回忆不时出现,像是对都市快节奏的时间的突然暂停。梦与回忆总是指向乡村生活所代表的简单的、平静的、充满了生命力的存在状态。将梦与回忆引入书写,一方面有批判都市文明的意味。梦或回忆中的场景往往是乡土,它们的气氛令乡村世界笼罩在温柔的轻雾中,生产着天然美好却又无法复返的乌托邦,这也是一种无奈乃至绝望的遁逃情绪。另一方面,梦的引入,还丰富了诗歌的时空层次,并为探究主体的潜意识提供了可能。梦与回忆在新诗中的运用及其效果,可被视为“京派”诗歌对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又一种丰富。《水星》诗歌中写梦的第一佳作当属何其芳早期代表作《箜篌引》。有论者指出,何其芳的早期作品中,“异性情结”与“异国情调”是两个重要特点,“它们经常混合在一起发生作用,对‘此地’、‘此身’的现实缺憾进行补偿,并构成他的‘梦’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深深影响到他的文学品质及语言风格”[12]151。当梦在何其芳诗中生成时,“抒情主人公当下的意识总是不由自主地滑向另一时空:不是古代中国的宫廷或闺阁、华筳或清斋,就是西洋中世纪的城堡或修道院,而尤以后面一种富于双重异质性的想象更能牵动他的心灵”[12]157。《箜篌引》一诗就是由“异性情结”与“异国情调”混杂而成的。诗中,梦开始于抒情主体“放下窗上的芦苇帘子”,梦中人已“在荒岛的岩洞间”不辨自我的身份与性别:“我到底是被逐入海的迷兰公/还是他的孤女,美鸾达?”[20]梦的一路发展,就是主体寻找自我的过程,从岩洞的茫然自失到困守于“十月伦敦的黄雾”之中,再到最终的梦醒:“卷起帘子来:看到底是黑夜了/还是一半天黄沙埋了巴比伦。”[20]有意将北平指认为巴比伦,这种修辞手段,既在传达梦醒后的恍惚感,又有将北平塑造为衰败历史的象征维度,可谓一言多义。
《箜篌引》中的一个重要修辞手段是用典。“箜篌引”这一题目,本就有典可依,诗人亲自作注以说明,此处不再敷述。但诗中的多处用典却没有给出说明,刻意地形成了一种李商隐无题诗式的晦涩与梦幻。如诗中提及的“美鸾达”与“米兰公”是父女关系,来自莎士比亚的早期传奇剧《暴风雨》;“裂帛声撕扇子声能使你笑吗”一句,明显指向了诸如妺喜、褒姒、妲己一类祸水红颜。用典的诗歌手法,为古典诗歌所常用,将它引入新诗的写作,是“京派”诗人对传统诗学的创造性转化,是“京派”诗歌对新诗现代性的又一种丰富。这种手法为卞之琳运用在了《距离的组织》一诗中,有趣的是,这首诗也写了城市中的一梦:“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报纸落。地图开,因想起远人的嘱咐。/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罢。)”[21]与何其芳不同,卞之琳每一处用典都有注,即便如此,关于这首名作,历来也是众说纷纭,专门的解说不计其数。在此,笔者只想单就卞之琳的用典作出解读。这首诗中的每一处典故都与另一个不同时空中的文本相关,由此看来,卞之琳对典故的解说是诗歌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不可删除的,正因为这些解说的存在,不同的时空才得以交织在同一个文本时空之中。卞之琳的这一梦,虽也是任由意识的跳跃,却具有那种晦涩而浓郁的潜意识情绪特征。卞之琳的梦显示出了整饬的设计感,通过场景嫁接的手法,诗人所思索的是有关时空关系、宇宙与人的哲学命题,同时,也以一种主体意识分化的手段表达了现代中国人惶惑不安、异常分裂的时代感。作为智性诗风的一首代表作,诗中的“灰色心境与智性化手法”[12]140会令人联想到艾略特的“荒原”,对此,穆旦的判断是准确的:“把同样的种子(指艾略特的《荒原》。引者注)移植到中国来,第一个值得提起的,自然是《鱼目集》的作者卞之琳。”[22]在《水星》上发表的几首诗,对卞之琳而言,具有个人写作史上划时代的意义,至此,他不再是受新月派影响至深的年轻写作者,而开始渐渐成为了开一代诗风的成熟诗人。
注 释:
①这篇重要的文章发表在1934年印行的“京派”刊物《学文》第一卷第一期上。
②赵萝蕤译《荒原》先是在《新诗》杂志上发表,后于1937年由上海新诗出版社出版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