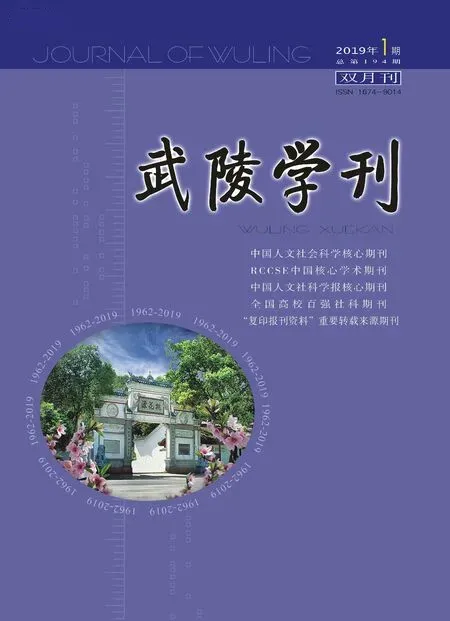另一种启蒙:1920年代张君劢新人文主义启蒙思想
欧阳询
(1.长沙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100;2.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院,湖南长沙 410081)
按照康德的经典说法,启蒙是指“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而成熟的标志就是人类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理智)。诚然,英法德等国的启蒙运动在时间上有着先后之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在特点上多样纷呈,但毋庸置疑的是,“欧洲近代的思想启蒙还表现出明显的统一性和世界意义”[2],即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倡扬科学理性精神和民主自由精神。正是以欧洲近代启蒙思想为标本,中国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欧洲已经流行各种与启蒙精神不同乃至对立的思潮,如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社会主义等,“囿于当时的思想学术水平,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不能将这些思潮与启蒙思潮严加辨析,而是在自己传统学养的背景下,在救亡图存和造就新人动机的驱使下,将自认为对中国有用的东西都介绍过来”[3]。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君劢选择了柏格森、奥伊肯的生命哲学,并使之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以作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武器。因此,相较于胡适、丁文江等人倡导的启蒙运动,张君劢更像是在进行启蒙反思,二者相反相成地推动着新文化运动的纵深发展。
一、1920年:张君劢转向思想启蒙的时间节点
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9月,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彼时,张君劢正在德国留学,致力于研究“一战”的进展,并亲赴战场进行实地考察,从而推测德国必将战败。所以,他回国后不久,便于1917年4月致函梁启超商议对德宣战问题,并四处游说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以争取他们的支持。而段祺瑞为了获得日本许诺的借款,达到扩充军备的目的,也意欲推行对德宣战政策。在这种情势下,以梁启超、张君劢为代表的研究系立即投靠了段祺瑞,竭诚为其内阁效力,先是在段祺瑞与总统黎元洪的权力斗争中为段祺瑞出谋划策、四处奔波,继而协助段祺瑞武力讨伐张勋,重新执政。嗣后,段祺瑞任命梁启超为财政总长、张君劢为总统府秘书,但在召集的“临时参议院”中,研究系却遭到了排斥,仅得少数席位。1917年11月,段祺瑞下台,张君劢跟着辞了职,转赴北京大学教授国际法。这一段经历,不仅使张君劢感到心灰意冷,意识到北洋军阀“不足有为”,而且也促使他对这一年来甚至是1911年以来所参加的政治活动进行深刻反省。他在日记中写道:“岁云阑矣!问此一年来,所为何事,则茫然不知所以。盖自来救国者,未有不先治己。方今海内鼎沸,已同瓦解,求所以下手之方,而不可得,惟有先尽其在我,此治己之谓也。”[4]16自此,张君劢开始了一段长达一年左右的严谨的律己生活:“第一,学书写《圣教序》;第二,读《汉书》每日二十页;第三,习法文;第四,编大学国际法讲义。”[4]16同时,他还于1918年初与唐规严、蒋百里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松社,希望在“政治固不可为”的情况下,借助讲学之业来提倡改良社会风气。
毋庸置疑,张君劢于1918年初开始提倡改良社会风气,确实蕴含了思想启蒙的因子;但平心而论,这种因子并没有迅速成长,而是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因为1919年初,他便陪同梁启超等人来到了欧洲,以个人身份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出谋划策,“初到之第一年,往来于伦敦、巴黎之间,所注意者,专在和会外交之内幕”[5]。4月30日,英、法、美三国为迁就日本,竟不顾中国代表团的强烈反对,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让与日本。这使张君劢深切地感到,国家无强大兵力,外交是空话,国际公法更是一纸空文。当时,他告诉同室的丁文江说,他要将自己所藏的国际法书籍付之一炬,不再读这些无用的书,而“决心探求一民族所以立国之最基本的力量,或者是道德力,或者是智识力,或者是经济力”[6]。但究竟何去何从,张君劢还举棋不定,也尚未打算要以哲学为自己“一生研究之目的物”[5]。所以,在1919年六七月间,当梁启超邀他同访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时,他竟谢绝之,认为“哲学乃一种空论,颠倒上下,可以主观为之,虽立言微妙,无裨实事”[5]。到了1921年与1922年之交,张君劢对此进行了深刻反省:“任公先生与柏氏(指梁启超与柏格森。引者注)谈而归,告我已所谈内容,及今回想,竟一字不记,我之淡焉漠焉之态度,可以想见。使在今日而有语我以柏氏口授之言,我且立刻记下,而当日乃见亦不愿去见,则吾此时束缚于现实生活,而忽视人类思潮之大动力,可想见矣。”[5]在这段话中,“现实生活”主要是指现实的政治生活,“人类思潮之大动力”则是指哲学。
那么,张君劢“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真正走上思想启蒙的道路,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据张君劢自己回忆,1920年1月1日,他陪同梁启超去慕名拜访奥伊肯,而奥伊肯对这些陌生客人异常亲切。当梁启超再三询问调和精神与物质的方法时,奥伊肯自知难以一二哲学概念表示,乃屡屡用两手捧其赤心,以表示将精神拿出来参透物质之意。奥伊肯的真挚态度,让张君劢产生这样一种感想:“觉平日涵养于哲学工夫者,其人生观自超人一等,视外交家之以权谋术数为惟一法门者,不啻光明、黑暗,天堂、地狱之别。吾于是弃其归国之念,定计就倭氏而学焉。”[5]显然,与奥伊肯的见面,是张君劢“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的一个关键节点,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下意识中“尚伏有种种暗潮”[6]。兹分两点来说:一是国内外政治的刺激。就国内政治而言,民国初年的国会贿选、政党倾轧、武人专政等乱象,使他“心上要求一种最基本的方法,对民族之智力、道德与其风俗升降之研究,时常感觉必要”[6];就国外政治而言,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使他认识到自己虽精通国际法,且以国际法尽窥外交秘奥,却于世界人类毫无裨益。二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刺激。从社会科学的性质上说,教育、经济与政治各自独立,自成一种学问,但从生活方面来看,一国政治的好坏,离不开国民财富的多少与国民教育程度的高低;同时,各门学问都有一个抽象的历程,譬如经济学有所谓“经济人”,政治学常以个人与国家相对立,这必将使科学家“遁于虚空”,以为学问可以解决一切实际问题。
随奥伊肯研究哲学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张君劢的启蒙思想迅速发展起来,且日趋成熟和完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张君劢在1920年的文章中开始出现“新文化运动”一词,他说:“再旅欧以来,默察思潮变迁之大势,常以学术界之大革命,已如晨曦之将达地平线上矣。……方今吾国新文化运动正在发端,应如何应此大势而急起直追,则吾以为凡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访求其主持新说之巨子,而罗致之于东方,则一切陈言可以摧陷廓清。”[7]这里主张用哲学与科学来解放国人的思想,不正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吗?其二,张君劢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反思国人“迷信物质万能”,指出:“欧洲经大战之后,鉴于物力之有尽而人欲之无穷,唯物主义已在衰落,吾东方学子,方迷信物质万能。此弟之所以来此,且欲以奥氏(指奥伊肯。引者注)之言药吾国人也。”[8]从这段话中,已能大致窥知张君劢在人生观论战中的基本立场。其三,张君劢把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问题看作是一种人生观问题,正如他所言:“若夫一国中有持个人主义者有持社会主义者,犹之哲学上之唯心唯物政治上之保守进取,本为一种人生观问题。”[9]而人生观,乃“意志之所命”“良心之所驱”,所以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最后须诉之于国人的良心或自由意志,“个人良心自由为真民主之命脉”[10];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现,亦是同样如此,“一切主义,苟其发于良心,起于意志者,未有不足以福社会而利人群者”[9]。其四,在倡扬良心或自由意志的前提下,张君劢极其重视国民的教育与民智的开化。他在《政治活动果足以救中国耶》一文中强调,旧形式的政治活动,如结政党、争选举,“万不容其留存于今后”[11],而须从头做起,即从国民教育入手。当然,与政治活动相比,国民教育的效果必定慢些,故他劝说道:“吾侪切勿求速效,切勿问他日之收获,待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再与此旧社会旧政体较短长度得失可焉。”[12]显然,这完全吻合了《新青年》同人的启蒙路向,“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13]。
既然1920—1921年张君劢的启蒙思想明显地成熟与完善起来了,那么,就有必要“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14],着力考察张君劢启蒙思想的内涵与特点。
二、新人文主义:张君劢启蒙思想的本质内涵
在考察张君劢启蒙思想的本质内涵之前,有必要了解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与内容,因为新文化运动构成了张君劢启蒙思想的历史语境。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发生,主要源于民国初年掀起的封建复古主义恶浪。1913年6月,袁世凯政府颁布《尊崇孔圣令》;1914年9月,发布《大总统亲临祀孔典礼令》;1915年1月,又明令恢复中小学读经教育。显而易见,封建复古主义思潮,是为帝制复辟运动做舆论准备;而帝制复辟运动,又推动封建复古主义思潮的发展。面对这种倒行逆施,新文化运动者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正如陈独秀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5]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新文化思潮在“五四”运动发生不久就出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化。这里所谓的科学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即“那种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即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方面)的观点”[16]。“五四”运动之后,尤其到人生观论战之时,胡适大力倡扬“科学的人生观”:一方面,关于人生是什么,他主张用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科学知识来做认识人生的基础,比如“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17]23;另一方面,关于人生应该怎样,他主张拿试验主义的态度、精神、方法来做人们生活的态度、精神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适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科学主义者。与胡适不同,陈独秀则在“五四”运动后经历了一个根本转变。1920年4月,陈独秀仍属于科学主义者,仍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自然科学方法:“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18]然而,到了1921年7月,陈独秀眼中的“科学方法”,突破科学主义的藩篱,明确地指向了“唯物的历史观”,正如他在《社会主义批评》中所说:“近代所讲的社会主义便不同了,其宗旨固然也是救济无产阶级的苦恼,但是他的方法却不是理想的、简单的均富论,乃是由科学的方法证明出来。现社会不安的原因,完全是社会经济制度——即生产和分配方法——发生了自然的危机。”[19]
在“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直高举人文主义旗帜的是以梁启超、张君劢为代表的研究系。1920年3月,梁启超的《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长文,同时连载于《晨报》与《时事新报》,文中指出:欧洲现代文明是一种物质文明,“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于科学之下,建立了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20],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反倒带来了许多灾难,叫人类“无限悽惶失望”。在这种情势下,倘若人们不能幡然悔悟,改弦更张,仍立在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上头,正在兴起的工团主义与社会革命,就会像从前的军阀一样专横。由是观之,梁启超反对工团主义与社会革命,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乃是基于他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想。胡适就曾经指出,自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发表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更有甚者,张君劢打着柏格森、奥伊肯等人的旗号“继续起来替梁先生推波助澜”[17]11,于1923年2月14日在清华学校作了一场《人生观》讲演。
严格说来,张君劢作《人生观》讲演,并非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而是受了柏格森与奥伊肯的影响。张君劢与梁启超是同时成为人文主义者的。因为,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虽然发表于1920年3月至6月,但却撰写于1919年10月至12月;同样,张君劢于1920年6月致函林宰平时,说自己“欲以奥氏(指奥伊肯。引者注)之言药吾国人”[8],其间不过半年时间。实际上,就在这封信函中,张君劢清楚地指出了奥伊肯哲学因反抗主智主义、自然主义而以人生为中心,它包含着三层要义:第一,世间实体不外心物二者,贯通心物厥在精神生活;第二,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皆以“思”为真理之源,而奥伊肯认为“徒思不足以尽真理,尽真理厥在精神生活上之体验”[8];第三,人心易为外物所束缚,故当以精神生活克制之,然后人生才能晶莹透彻。在此基础上,张君劢进一步指出,奥伊肯哲学与“吾国先哲极相类”,所不同的是“在吾为抽象之论,在彼则有科学根据耳”[8]。这里所谓的“科学根据”,并非指奥伊肯哲学以科学方法为根据,而是指奥伊肯哲学以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为根据。所以,对于孔孟的“求在我”学说在工业时代中的作用,张君劢保持着怀疑态度:“以今日之人类,在此三重网络之中,岂轻轻提倡‘内生活’三字所得而转移之者?故在锁国与农国时代,欲以‘求在我’之说厘正一国之风俗与政治,已不易矣;在今日之开国与工国时代,则此类学说,更不入耳。”[21]可见,此时的张君劢虽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但不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者。
如果说柏格森、奥伊肯的生命哲学,构成了张君劢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理论基础,那么,张君劢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倡导,便是应合了这种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现实要求。当然,政治与哲学的密切结合,正是“五四”之后新文化思潮的基本倾向,比如胡适将“好政府主义”建基于实验主义哲学之上,陈独秀则将共产主义建基于唯物史观之上。1920年,张君劢在《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一文中指出,中国须走德国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苏联的共产主义道路,因为“既言社会主义,自当承认社会主义之所谓幸福。……幸福云者,以一二人之意思为标准,不顾民意之从违而强之乎?抑必待民意之承认而后行之乎?幸福与杀人流血之惨祸,相随而俱至。以幸福为不敌惨祸而缓之乎?抑不顾惨祸而必强行之乎?如曰幸福决于民意,不决于一二人,则吾以为列宁之民意机关,不合于吾上举之二标准”[22]。显然,反对“杀人流血之惨祸”的人文主义精神,成为了张君劢“左德右俄”的根本依据。进一步说,他既用民主社会主义来排斥共产主义,也用民主社会主义来匡正资本主义的弊端。1922年,张君劢在《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一文中说道,欧洲文化危机“在现实之社会上、政治上”,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的兴起,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现社会之组织,是抑制本能,是戕贼生机,欲恢复心灵以调和理智”[23]。简言之,张君劢是把民主社会主义建基于抽象的人文主义之上,以作为他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在张君劢那里,人文主义是作为科学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但正如陈独秀所指出,丁文江的科学主义与张君劢的人文主义,实质上都是唯心主义,前者沿袭了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旧唯心主义,后者沿袭了柏格森、奥伊肯等人的新唯心主义。关于这两种唯心主义的区别,张君劢本人早在1920年初就已了然于胸。他曾明确指出,文艺复兴以来的旧唯心主义与19世纪末兴起的新唯心主义,主要有两点不同:其一,旧唯心主义以为世界一切事物之理,皆可于理性中求之;新唯心主义认为理性之外,有非理性存在。其二,旧唯心主义重理性,故认为可以思想尽之;新唯心主义以为人类历史进化,恃乎行为,非思想所能尽[24]。是故,张君劢又将旧唯心主义称为理性主义或主智主义,而将新唯心主义称为非理性主义或反主智主义。与之相应的是,在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人文主义”一词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涵义:第一种是蒋百里、胡哲保等人将文艺复兴的主流思想humanism译成“人文主义”;第二种是胡先骕、吴宓等人将19世纪末兴起的humanism译成“人文主义”。直至1930年,中国思想界才自觉区分humanism的两种译义,并开始使用“新人文主义”一词:“人文主义起于西洋文艺复兴时代,排斥宗教力量而主张以人力自由,研究真理,看重现实的人事,对于现世人类,抱乐观思想,继续希腊罗马的精神,而以文艺哲学科学为思想的产儿。……到了十九世纪末年,又有‘新人文主义’发生,主张文艺价值,不当偏重理性,而当兼重情感。”[25]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张君劢的启蒙思想是一种新人文主义,亦即非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
三、张君劢新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主要特点
张君劢的新人文主义启蒙思想,主要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强烈的唯意志主义倾向。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唯意志主义形成并流行于19世纪下半期的欧洲,主张意志高于理性(理智)、意志“创造”世界万物,从而歪曲、夸大意志的本质和作用。正是受了叔本华、尼采,特别是柏格森、奥伊肯的影响,张君劢的新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才表现出了唯意志主义的倾向。关于这一点,张君劢在《人生观之论战序》中曾说:“现世界之代表的思想家,若柏氏倭氏,本此义以发挥精神生活,以阐明人类之责任,推至其极而言之,则一人之意志与行为,可以影响于宇宙实在之变化,此正时代之新精神,而吾侪青年所当服膺者也!……呜呼,使即此之故,令我受千万人之谤毁,所不辞焉!”[26]诚然,与柏格森、奥伊肯一样,张君劢高扬自由意志,旨在反对主智主义,凸显人生价值,但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驳斥当时流行的“环境说”,为中国社会改造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1921年11月,当有人以民智低下为由对他提出的社会改造计划进行质疑时,张君劢这样回应道:“呜呼!吾知之矣,数十年来,环境说之入人心者,已深且久,一若天下事物,皆由自然因果支配,而人力无可得施。抑知人类进化之大动力,曰生命的奋进曰冲动曰意力,三者名虽异而实则一,总之则向上之心耳。惟其有此向上之心,故一切境界,皆由人造。”[27]更进一步说,其他新文化运动者虽然亦以“改造社会之说”相号召,但他们“以为西方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两大时间之先,尝经文艺复兴,以下思想解放之工夫,故吾国改造之路,亦不能脱此一级”[27];而与之相反,张君劢强调“时异地异已不容吾人拾级而登”[27],故思想解放、政权解放(民主政治)、生计解放(社会主义)必须同时并行。这何以可能呢?他如是说道:“吾闻西方学者之新说曰,人类之进化,生命的奋进而已,但知人生有不可不前进之冲动,而决无所谓一定之阶级,可以按图而索。”[27]显然,强烈的唯意志主义倾向,使张君劢忽视和否定了客观社会历史条件。
第二,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倭伊铿精神生活哲学大概》一文中,张君劢专门引述了柏格森为奥伊肯《生活意义及价值》一书所作的序文,该序文曰:“生活之意义安在乎?生活之价值安在乎?欲答此问题,则有应先决之一事,即实在之上是否更有一理想?如曰有理想也,然后以人类现在行为与此尺度相比较,而现实状况与夫应该达到之境之距离,可得而见;如曰无理想也,则安于所习见,不复有高下等次可言。”[28]1100这里所谓的“理想”,主要源于神秘的自由意志,亦即源于“人心之隐微处”,决非理智所能把捉。于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张君劢将人类世界划分为精神与物质两大部分:内曰精神,外曰物质;内在精神变动而不居,外在物质凝滞而不进。故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化,在于内在精神对外在物质(现实状况)“常求所以变革之,以达于至善至美之境”[21]。进而言之,在张君劢看来,民国初年最大的现实问题是政治乱象丛生,尤其是政党不讲主义,相互倾轧。所以,他极力推崇理想政治,主张建立理想政党。那么,何谓理想政治?张君劢认为,中国未来政制之抉择,应采取两种态度:一是比较英法德等国的政制异同,“共同者,则一般理想所在,不易更易者也;互异者,则为历史地理所限,不可以相学者也”[10]。二是“既比较矣,而后验之世界大势,审之中国国情,则舍小异取大同,而自有殊途合辙之日”[10]。由此可见,张君劢所谓的“理想”,并非真正源于神秘的意志或人心,只不过是运用综合比较法得出的结果,即主张走西方民主政治之路。就理想政党而言,它是一种政治教育机关,用于提高国民的政治知识,养成国民的政治习惯;当然,这反过来又可加强政党的巩固,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正如张君劢所言:“理想政党成,则理性政治之实现必矣。且所以断绝现实政治之念者,正所以使来者不存一毫名位之心,惟以一腔牺牲精神,献身于理想事业而已。”[10]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所谓的理想政党犹如镜花水月,是根本无法企及的。张君劢所领导的民主社会党,因参加伪国民大会而被中国民主同盟勒令退出,即是显例。
第三,鲜明的精英主义性格。一般而言,启蒙思想家应当而且必须具有平民精神,高度重视广大民众的主体性作用,张君劢也概莫能外。他说:“新文化之要件在解放,如人人当从自己解放起;新文化之要件在自立,故人人当不依赖他人做起;新文化之要件在劳动神圣,故人人当从自食其力做起。此寥寥数条,人人遵而行之,则民主精神、科学精神之新文化,自然实现于吾国。”[23]在这段话中,“人人”一词,尤其是“人人当从自食其力做起”,生动地体现了张君劢启蒙思想的平民特征。既然如此,何以又说张君劢的启蒙思想具有精英主义性格?因为,在张君劢看来,对国民的思想启蒙主要诉之于他们的良心自觉,而他们的良心又常被习俗所束缚,或被境遇所限制,于是自觉自动的精神,最后归于麻木;与此相反,精英分子“不甘于常人所好恶常人所云云,苦形劳神,以探求生活之新境界,毁誉不顾,生死不问,于是社会之进化,为之更上一层。非其人之有异于常人焉,其自觉性发达耳”[27]。在这种情势下,自然需要精英分子站出来,负起先知先觉者的责任,加之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必将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实际上,张君劢自己清楚地认识到,精英分子是珍贵而不可多得的,整个社会不过一二人而已,诚如他所说:“凡世界政治社会改革,无不始于一二人之心力,百折不回,以与旧社会斗,而终至于光辉灿烂之一日。有昔日之托尔斯泰,乃有今日之列宁,有昔日之马克思,乃有今日之爱勃脱(Ebert)。”[12]的确,马克思、列宁均拥有坚强的意志力,在与旧社会的斗争中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但他们坚决反对精英史观,而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第四,强调行为重于知识。张君劢指出,新文化运动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常以知识(或文化)运动为高洁,而以其他活动为卑污”[27]。究其原因,是由于“国人鉴于十年来政治之混乱,于是相戒不言行为”[27]。在这里,与知识运动相对的“其他活动”,广义上是指社会生活,狭义上是指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亦即建立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在张君劢看来,偏重知识运动与偏重社会生活,分别代表了当时两大哲学潮流——认识论哲学(思想哲学)与生活哲学。认识论哲学以“思”为出发点,以逻辑学的思想规则为研究方法,故重理性、重概念;生活哲学以“生活”为出发点,“以为思想不过生活之一部”,“故重本能、重直觉、重冲动、重行为”[28]1096。正是基于两大哲学潮流相反的立场,张君劢在《人生观》讲演中作了科学(知识)与人生观之比较,指出:人生观为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性的,故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知识所能为,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再进而言之,张君劢所谓的人生观问题,如“我与我之财产之关系”“我对于社会制度之激渐态度”“我与我所属之全体之关系”[29]等,几乎都属于政治、社会问题;他所谓的“行为”,便主要指向现实的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他一方面说:“然文化之根本,智识固不可轻,而所重尤在行为。”[23]另一方面又说:“所谓新文化者,不仅新知识已焉,应将此新知识实现于生活中,然后乃成为新文化。故吾国学术上固当有一种大改革,即社会上政治上之制度亦复如是,要之当自种种方面,造成一新时代。”[5]这清楚地表明,张君劢强调行为重于知识,是为了建立中国新文化,是为了造成一个新时代。
总的说来,以上四个特点是互相渗透、有机统一的。其中,最核心的是唯意志主义倾向,因为这种意志本身是至善的、重行为的,且内在地包含“先知觉后知”之义,“人心之动也亦然,始造端乎一二人,终则磅礴乎一世”[27]。这就集中体现了张君劢新人文主义思想的非理性主义性质。惟其如是,在科学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文化思潮中,张君劢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才显得比较另类和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