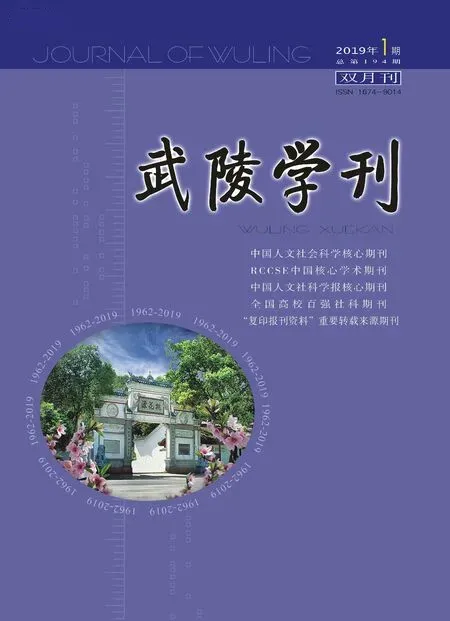“生生”之仁:理学之“仁”的本体化与境界论探微
吴 鹏
(廊坊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牟宗三认为,儒学的发展自孔子创立“仁”教以来,至今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先秦开始,到东汉末年结束;第二阶段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第三阶段自宋明开始并传至新儒家诸人。著名学者李泽厚则认为儒学发展历经四个时期:“孔、孟、荀为第一期,汉儒为第二期,宋明理学为第三期,现在或未来如要发展,则应为继承前代,但却颇有不同特色的第四期。”[1]无论“三期说”还是“四期说”,比较一致的是他们都认为宋明理学将传统的“内圣”与“外王”并重的思想变得更专注于“内圣”,其主要目的是“唤醒道德意识”“重视道德意识”[2]。与此对应,作为儒学内核的“仁”也由先秦儒学的“孝悌之本”(《论语·学而》)转变为宋明理学“仁”体的“超越的遥契”[3]37与“‘内在的’遥契”[3]38,将“仁”由伦理亲情概念改造为宇宙万物的存在论本体。为此,理学家主要通过借用《易传》中“生生”的概念,将《乾》《坤》两卦所演绎的天地之德诉诸“仁”的阐释中,建立起了“天理”的观念。与此同时,“仁”也具有了与天地之德相当的纯善无恶的圣人境界。
一、从“人德”到“天道”:“仁”的本体化过程
在先秦时期,“仁”的概念开始奠基,它是作为人伦亲情概念融合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的。因此,在提到“仁”时,孔子总是不轻易许以人,并随事指点仁,如称赞颜渊“三月不违仁”,称赞管仲“如其仁”。孟子则强调“尽性知天”,通过呈现仁义礼智之“四心”以“尽性”,体悟“仁”心,以此推至天下实现“不忍人之政”。由此可以看出,早期儒家之“仁”主要指称孝悌,讲的是人间之伦理道德,个体的伦理情感表现得比较活泼、比较自由,还没有“体”的意识。但在战国末年的文献中则出现了诠释“仁”的新倾向。在《易传》与《礼记·中庸》中,“仁”进一步被解释为“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4]1633。这时,“仁”尽管具有追求“合内外之道”的超越现实、通向宇宙的内涵,但是“仁”却被扩充为两个对立的方向:天道与人德。正如陈来先生指出的那样:“先秦儒学的仁学已经从多方面显现了仁体本有的广大维度,但还未真正树立仁体论,这必有待汉唐宇宙论、本体论的发展,直到宋明儒学始能完全确立。”[5]130如果将宇宙论、本体论的展开过程视为“仁”背后的“天道”逐渐彰显的过程,那么,实际上这个过程也是“仁”体不断理性化并脱离现实“人德”的过程。由此路径,“仁”经历了汉唐、宋明时期的发展,最终成为“仁”体,成为万事万物普遍变化的动力与存在论本体——“天理”。
在“仁”尚未具有“体”的地位之时,“仁”所具有的“人德”内涵即道德情感相对较多。但在这一时期,“仁”开始重视“天命”的有关内容,所以在超越层面上有较重的宇宙论色彩。因此,陈来先生指出:“在先秦时期没有把仁作为天心的说法出现。以仁为天心,也就是仁为宇宙之心,这个说法是仁体在宇宙论形态发展的重大一步,也反映了儒家面对汉代统一帝国的出现所采取的理论回应,即重新努力把普世理论作为宇宙原理,以从道德上制约、规范皇权。”[5]139应该说,陈来先生很敏锐地把握了汉代“仁”本内涵的变化。但在所谓“皇权理论”的背后,这个变化应该还与“仁”所包含的“天道”和“人德”的双层内涵此消彼长有关。虽然先秦时期还未出现“天地之心”的说法,但如前文所述,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文化体系中,“仁”的概念实际上内在地包含了“天道”与“人德”的内涵,“仁”在宇宙论上的扩展,实际上也是“天道”不断扩展其形而上成分的过程。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仁”的内涵被扩展,其外延也扩大了许多。
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仁,天心,故次之以天心。[6]161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6]164-165
由此不难看出,“仁”扩充了在宇宙论上的丰富内涵,并且正在趋向宋明时期的“体”,并以此裁定现实的人是否符合“天”意。就形而上层面而言,“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仁”是宇宙运行变化的规律,是万事万物的“本体”。而在“人德”层面,强调“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把“仁”作为人类实践行为的准则。从这点来看,这时的“仁”实际上是介于孝悌之“仁”与“天理”之“仁“的中间状态。“仁”既可以表现“天”的运行规律,也具有人的道德情感,具有了丰富的本体论和宇宙论内涵。
到了宋明时期,“仁”结合了《周易》“生生”的内涵,其“天道”的成分更为突出,而“人德”成为了配合“天道”的存在,二者互为形而上、形而下的体用关系。在“天道”的作用下,“仁”就成了宇宙运行的规律与万事万物的存在本体。在其制约下,留给感性的“人德”的成分逐渐消失,甚至人的许多正常的情感欲望被“仁”体斥为“私欲”而被驱逐出人之常情外。由此,“仁”被视作彼岸化的“体”而悬置于形而上的层面。这从程朱理学对“仁”的定义可见一斑。
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盖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之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几曾有孝弟来仁主于爱?爱孰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7]183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与者,疑辞,谦退不敢质言也。言凡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谓孝悌,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8]50程子和朱子都将《论语·学而》中的“孝悌者也,其为人之本与”解释成“仁体”,而人在现实中的孝悌之情实际上只是“为”仁之本,而不是“仁”。在他们看来,“仁”是形而上的本体,是“爱之理,心之德”,是“性”而不是形而下的情感或实践行为。至此,作为“人德”和“天道”统一的“仁”消解了作为“人德”的情感内涵,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理”。
二、“生生”之仁:“仁”的本体化方式
在程朱理学中,“仁”具有明确的内涵,不仅具备道德理性的内涵,同时也是万事万物的“生生之理”、存在之理。对此,朱子指出:
天地之心,只是个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叶条干,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穷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干枯杀了。这个是统论一个仁之体。其中又自有节目界限,如义礼智,又自有细分处也。[9]3163
在这里,朱子不仅指出“仁”是“爱之理,心之德”,而且也认为它是万事万物的存在之理,体现在有生之物上,它是运动变化发展的不竭动力;体现在人身上,它是仁义礼智的四种德性。在朱子看来,仁义礼智以“仁”为本体;万事万物之所以能发展变化,是因为“仁”的存在,即所谓“天地之心,只是个生”。所以,在朱子心中,“仁”是“生生之理”,既是人的道德理性来源,也是支持物质之性持续存在且生生不竭得以呈现的“天理”。这样,“仁”既被视作道德伦理的本体,成为制约人现实情欲的决定因素,同时“仁”也是现实中的道德情感,是人的实践理性的感性显现。所以,个人的合理的、能为“天理”所包容的情感不再是通过接触外物而产生的情感欲望,而是待事接物时由“仁”体直接呈现在“事”之中的道德伦理情感。同时,接触外物而产生的情感欲望则一律被视为“私情”或“私欲”。这是理学家以“仁”来展现最高伦理本体——“天理”的手段,也是理学家建构圣人境界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
以此,理学家们建立了一个由宇宙“生生”变化,使万事万物得以不断呈现、变化发展的存在论本体。“生生”是先秦就已经相对完善的一个哲学概念。《易传》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4]78“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4]86以“生生”作为“易”的本体,即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4]77“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可止,故神无方而《易》无体”[4]77。由此可以看出,“生生”作为宇宙万物生成变化发展的最终动力,它指的不是万事万物具体的形构之理,而是“生理”,它是维持万事万物之呈现于现实中的存在之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天道”都是围绕这个思维展开的。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论物质的自然之构成的理论不是没有,但它始终附属于“生生”的思维之下。正如邹华所说:“(中国古代)不注重人对物的认知思维,而是讲人在世界中的生存状态,讲人作为个体的人生体验和对生命的自由选择,因此存在论实际上也包含着明显的伦理学的内容和倾向。”[10]8由此,“生生”这个概念便有了不断变化、发展的哲学内涵,它不仅能够作为宇宙化生的原理,也有作为伦理学本体的潜质。
同时,“生生”的概念是通过《周易》的《乾》《坤》两卦来展开的。对此,《易传》强调:“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4]82也就是说,通过“太极”的运动,万物的“生生”之变化由阴阳两种对立又统一的事物呈现出来,这种阴阳对立通过《乾》《坤》之卦的卦象呈现出万事万物运动发展变化的原因与内在动力。对此《易传》认为:“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4]82乾坤的交替转化过程就是万事万物的生成过程。正因为如此,《易传》才会认为乾、坤是代表“生生”之变化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生与成:“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4]82“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4]78-79由此可见,“乾”之德在于创生万物。而“创生”之初,必有初始,初始必有具备“终成”之德的“坤”相对应。而对“坤”来说,它若要具备“终成”之德,就必须通过“乾”的“创生”之德来实现自身。由此,无论“乾”“坤”,它们处在一个对立统一体中,互为不断变化发展的“生生”之不息的动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所以,“易”通过乾坤之原则所呈现出来的“天道”之变化,涵盖了宇宙生成的方方面面。作为流行于万事万物的“天道”,也制约着人间的伦理道德。《易传》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4]78由此可见,人类的伦理原则也来自“生生”的阴阳变化,百姓在现实之中对实践理性的“日用而不知”,是因为不识“生生”之作用。“生生”作为“仁”与“智”的来源,是形而上的呈现,作为“日用之常”则是形而下的呈现。虽然人能在日用上体现“天道”,但是鲜有人能认识“天道”。这从侧面印证了先秦时期“天道”与“人德”处于不分彼此的混沌状态,个体能通过现实伦理而达到圣人境界,而现实中的情感也是“天道”的反映,不需要剥离感性以体现圣人境界。值得注意的是,《易传》虽然将“仁”作为“生生”之阴阳作用的产物,但它还没有将“仁”当做宇宙万物的本体,而是将“人德”视为“天道”在人间伦理的一个呈现,而“仁”的内涵还是指百姓日用层面的道德伦理情感,如孝悌之情,还未达到“本体”的层面。正是在这一点,宋儒将“仁”和“性与天道”结合在一起,将“仁”提升到本体的地位,而不只是局限于道德伦理情感。
应该说,以“生生”作为“仁”的本质是宋代理学的创造,在“仁”上升到宇宙本体地位后,就能对现实中的情感欲望加以排斥,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中正仁义”在宋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的哲学体系中,就是“天理”,不仅是圣人本有之德,更是宇宙的“生生”之本体。正如《太极通书》所说: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至易而行难。果而确,无难焉。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1]13-16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是《论语》中孔子予颜子的“求仁之方”。周敦颐引用于此,明显是将“仁”作为“天道”,将圣人境界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周敦颐的“诚”内在地包括了“仁”之四德即“元亨利贞”,并认为“元亨”为“诚之通”,“利贞”为“诚之复”,将宇宙生生不息的变化与圣人之“仁”德联系了起来,同时以《易传》中的“乾道”作为宇宙变化的本体,将“仁”视为人间与宇宙变化的共同的形而上之源。由此,“仁”实际上就以形而上世界的“本体”地位制约着形而下的感性世界,成了“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相应地,现实中的情感也必须纯净而透明,才能获得与“仁”体相应的地位。故现实中人的许多“私欲”必须被排斥在“仁”体之外。所以,在周敦颐眼中,“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只有具备“诚”之德,即具备“元亨利贞”四德的情感,才能符合“仁”体的要求。而现实的正常情欲则是“非诚,非也,邪暗,塞也”,应被视为“私情”加以排斥。这样,上升到宇宙本体的“仁”直接制约了现实中人的情感变化,也排斥了个体之欲望,并将“五常”等人之伦常视为“私欲”、在圣人境界中是必须去除的。由此,“仁”再也不是一个道德伦理的存在,而是一个控制个体欲望以达到圣人境界的“天道”。
三、“生生”之境:“仁”本体呈现的圣人境界
此后,宋明理学家沿着这条路径,不断将理学家视野中的“生生”理论予以深化,同时“生生”与“仁”结合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其中,张载对“仁”的讨论,确立了天道与人道的联系,并由此确立了“仁人”所应有的境界。他认为:
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则须索做,始则须勉勉,终则复自然。人须常存此心,及用得熟却恐忘了。若事有汩没,则此心旋失,失而复求之则才得如旧耳。若能常存而不失,则就上日进。立得此心方是学不错,然后要学此心之约到无去处也。立本以此心,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亦从此而辨,非亦从此而辨矣。以此存心,则无有不善。[12]266
由此可以看出,“天”之所以能“生成万物”并使万物生生不息,在于其具有“仁”之德。“仁”德是天地万物所共有的德性,完成“仁”德才能实现天赋予人的道德本性,并进入到圣人境界中。因此,人的实践行为也要符合“仁”的要求;内心只要常存此“仁”,由内心散发出来的气质情感就会符合“仁”的规范。所以,人的全部实践行为都不能超越“仁”的范围,甚至于思虑也要符合“仁”的要求,而与此不符的情感和气质是为“私心”,应当摒弃。值得注意的是,张载认为实现“仁”德不能“勉勉”,也就是不能勉强。这就是说要从人的思虑上彻底将“仁”体之要求贯彻下来,不得有丝毫违背“仁”的念想,否则就是“私意”“私欲”;摒弃“私欲”并呈现“乐”的状态,人才能真正达到圣人境界。对此张载认为:“盖心弘则是,不弘则不是,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病。悟后心常弘,触理皆在吾术内,睹一物又敲点着此心,临一事又记念着此心,常不为物所牵引去。视灯烛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长一智,只为持得术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12]269在张载看来,圣人能随时随地弘扬“仁”道,而且能在待事接物时不被外物所牵引,没有自己的“私欲”;圣人之所以有此境界,全在“大心”,就是通过现实的工夫,将个人的情怀提升到天地境界上去,并在实践中践行天地大德。对此,张载进一步指出:“盖尽人道,并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则是与天地参矣。但尽得人道,理自当而,不必受命。仲尼之道,岂不可以参天地!”[12]178在张载看来,天地人三才,其中“道”为一。作为个体,有按照“道”的要求展开自己实践行为的义务。只有自觉践行“道”,实现天赋予人的“仁”德,才能使现实的人进入圣人境界。
由此,张载提出了“气质之性”的问题。他认为“气质”是人外在的表现,若要想达到圣人之境界,就必须按照“仁”的要求,克制自己的私欲,通过变化气质的方式呈现与圣人相同的气象。对此,他认为:
变化气质。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居仁由义,自然心和而体正。更要约时,但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礼曰:“心广体胖。”心既宏大则自然舒泰而乐也。若心但能弘大,则入于隘,须宽而敬。大抵有诸中者必形于外,故君子心和则气和,心正则气正。其始也,固亦须矜持,古之为冠者以重其首,为履以重其足,至于盘盂几杖为铭,皆所以慎戒之。[12]265
在这段论述中,张载将“仁”作为人性之中的本有之性,是与天地同德的“性”,也是人与生俱来的善性。外在之情作为人性的个体呈现,可能被现实中的物欲所牵引,或被私欲所遮蔽,使人呈现出来的气质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所以应该从“心正”入手,以达“气正”。在这个环节中,应“居仁由义”,将义理作为现实实践活动与思维活动的出发点,并且“但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将义理付诸现实活动中,并合“礼”与“仁”的要求,才能变换气质即“气正”。由此,个体才能进入“心既宏大则自然舒泰而乐也”的境界。需要指出的是,进入这种境界应以“仁”为出发点,以克制人现实中的欲望为前提,“大抵有诸中者必形于外,故君子心和则气和,心正则气正”,而不允许有私意或者偏于仁义要求的行为,只有这样,人才能心平气和,成为谦谦君子。
宋明理学家以“仁”为本,视“仁”为“天理”,并将“仁”作为沟通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的手段,作为制约人的“气质之性”的力量。他们还纷纷将“仁”作为古代圣贤如孔、颜在道德境界上的追求,如果在现实中能实现“仁”并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不勉强而自由的状态,就实现了他们心目中的圣人境界。
综上所述,先秦儒家通过对《易传》的阐释,初步构建了一个沟通天地人而又圆融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以“生生”为核心,确立阐释万事万物存在之理的方向,为宋儒构建以“天理”为核心的“仁”本体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宋儒的理论体系中,“仁”不再只是人的道德情感的一部分,更是“天理”的呈现,它是万事万物的本体,也是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来源。此时,“仁”不再是道德实践中的内在的伦理情感,而是与其相对的道德伦理原则和规范,并同时被视为人类道德创生的原理,也是宇宙万事万物生成发展的最终动力之源。可以说,以“仁”为核心,宋明理学家通过其本体化的过程,将具备“孝悌之义”的具体的、情感性概念提升到了“天理”的地位。这时,“仁”既可以成为道德情感,也是人的道德理性,同时还是人在现实中所呈现的喜怒哀乐之情是否符合“天理”要求的评价标准,具备存在论上的价值。在宋明理学家的心目中,“仁”也是境界理论的终极追求,是宋明理学一切本体、工夫理论的最终归宿,是他们与古代圣人精神境界追求的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