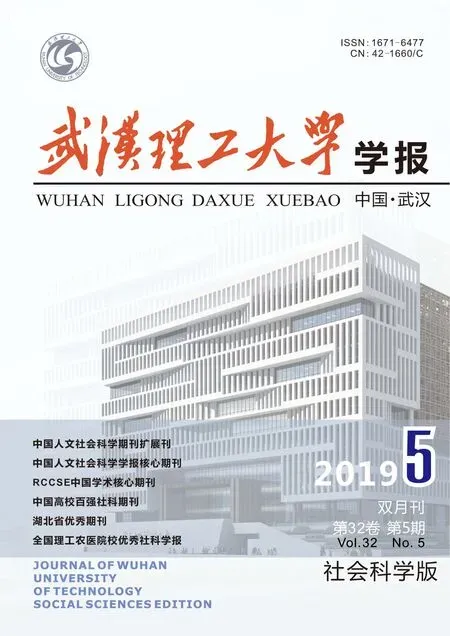关系心理学视域下的“自我”概念及其对青少年人格养成的意义
何 晶, 王炳煌, 黄 蓉
(1.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2.宾汉姆顿大学 心理系,美国 纽约 13902-6001;3.山东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关系心理学是西方后现代心理学特别是建设性后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后现代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科尼斯·格根、大卫·洛伊、约翰·布坎南、加拿大心理学家麦基卓、黄焕祥(Bennet Wong)等人。从关系的视域出发,关系心理学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在西方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对现代西方占统治地位的“自我”概念的挑战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关系自我”概念既构成了关系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内容,也是其重要成果之一。本文着重勾勒关系心理学视域下的自我概念的基本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探讨一下这一新的自我概念对于青少年人格养成的启迪意义。
一、 挑战现代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独立自我”概念
“自我”是现代心理学中的一个基石性的概念。按照我国学者的考证,自弗洛伊德建立起自我的概念以来,各种心理学流派都对自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詹姆斯的“经验我”、罗杰斯的“真实自我、理想自我”。不论各个流派关于自我的概念、自我的结构、自我的形成过程、自我的研究方法存在多大差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各心理学流派都认为自我是存在于某个地方的一个实体”[1]。所谓“实体”,按照笛卡尔的界定,就是某种独立不依的东西,它自己就可以存在,无需依靠别的什么东西。现代心理学家普遍将“自我”看作这样一个实体,看成是“一个独特的持久的同一身份的我”[2]。这样一个自我是绝对独立“自主的”、“自我创造的”、“首位一贯的”[3]。现代心理学中后来的自我实现,自我满足,自我成就等重要概念都是建立在这一概念基础上的。
而关系心理学则致力于挑战这样一个独立自足的“自我”的概念。作为关系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先驱,早在1977年,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在其著名的《不同的声音》一文中就开始了这一挑战。在文章中她向主流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等人的心理学理论发出挑战,质疑了自柏拉图到皮亚杰以来对男性主导的“分离的自我”概念的偏爱,并发现在以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皮亚杰和柯尔伯格为代表的西方发展心理学中,所谓“发展”被等同于“男性的”发展,所谓的“自我”被等同于男性的自我,亦即被等同于“个体化、分离、权利以及自主性”。在此基础上,女性的自我,依恋、关系和联系以及关怀与爱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受到遮蔽和排斥[4]。在新近出版的《关系性的存在》一书中,格根明确提出将自己批判的矛头指向(第一次)“启蒙运动的独立自我观”[5]。她很清楚,自己对西方占主流地位的现代自我概念的挑战将会“令人不舒服”(discomforting)[5]。因为心理学中的本质主义-执着于拥有特定精神过程和机制的个体概念,一直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一个中枢性的特征”(a pivotal feature)[6]。
尽管如此根深蒂固,但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作为单独的、分离的个体的自我概念,是人类一个最近的发明,它只有400年的历史,换句话说,它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5]。从现代早期的笛卡尔、洛克和康德到当代关于心灵与大脑的讨论,哲学家一直强烈支持封闭的存在概念。在许多方面,西方哲学的地标是它的二元论即“关于心与世界、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的假定”[5]。在麦克默里看来,标举二元论的现代哲学的奠基者笛卡尔的“我思”事先便预设了思想与行动的二元论、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预先排除了考虑任何“关系中的人”的可能性[3]。它给人们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人们可以并且应该能够离开他者的支撑而生活”[7]。这意味着,要成为自我,我必须成为某种分离的东西。
按照著名过程哲学家凯瑟琳·凯勒的分析,不论是我们的神话和宗教,还是我们的哲学和我们的文明都坚持这样一个假定,即个人是孤绝的存在:我是与我周围的人和世界分开的,我在本质上是每时每刻都保持同一的。我们的常识以“独立”和“自主”名义把分离等同于我们所珍惜的自由[8]。凯勒进一步从语源学的角度进行了考证,发现“自我需要分离”的假定已经深深根植于西方的语言中。拉丁文的“自我”(Se)意味着“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地”。成为一个人自己,必然意味着脱离关系。对我们的文化来说,“正是分离铺就了成为自我的路”[8]。当代的人类学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按照著名后现代人类学家吉尔兹的分析:这样一个西式的作为意识、情感、判断和行动中心的封闭的独一无二的自我概念,虽然在西方人眼里被看作是普世的,其实如果放在世界文化的版图上看,它似乎是一个特殊的甚至“古怪的理念”(peculiar idea)[9]。一些西方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与西方“实体”先于“关系不同”,东方思维是“关系在先的”[3]。按照著名比较哲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先生的分析,“整个中华文化有个共享的领域,无论儒家、佛家还是道家,作为它们出发点的价值观、意识倾向与行为,都是基于对关系至关重要——“关系为本”的认识”[10]。因此之故,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就“从没有这样一个实体性的自我(substantial self)概念”[7]。“关系”是中国人自我概念中至关重要的内涵。中国人的自我是最富有互动色彩的,“中国人的生命只有透过与他人的共存才能彰显其意义”[11]。
在格根看来,不仅如亚洲等非西方文化中没有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自我概念,就是在现代启蒙运动之前的西方,这样一个与共同体对立的“霸道”的自我也是不存在的[12]。可见,现代西式自我绝非什么永恒存在的普世理念。
在关系心理学家看来,虽然这样一个西式自我概念广受追捧,不仅被用来为自由主义经济制度辩护,而且也被用来“证明民主制度、公共教育和司法程序的合法性”[5],然而这个“虚构的”自我“已变成随时对人施展骗术的故事”。它不仅不是救治世界弊病的药方,而且恰是“使这种疾病本身加重、恶化的东西”[10]。
关系心理学家强调,伴随“关系转折”的发生和“全球相互依赖意识”的觉醒[12],所谓纯粹自主自足的“现代自我”观念正面临巨大的挑战,日益陷入危机。从理论上看,现代自我陷入如下三个误区:第一,现代自我由于过于强调分离往往导致社会异化或者孤独;第二,现代自我倾向于将社会析拆成孤绝的个体,从而毁灭了社会的团结,邻里关系和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第三,现代自我完全无法理解我们是如何被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文化和语言所创造的[3];第四,现代自我由于过分强调个体和自我的中心地位,极易走向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而现代个人主义最大的短板就是对关系有意无意的忽视,或者说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理解的错位。个人主义强调个体的自然权利,把社会看作是由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构成的。由于对个体的强调,社会被看作是第二位的、派生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或由个人形成的契约。而个人则是自然的、第一位的。这无疑撕裂了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对个人主义的高扬,关系、共同体和公共性失落了。社会共同体只具有外在价值,是外在的。其价值仅仅在于服务于个体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这种个人主义以及它的表现形式——自我中心主义忘记了内在关系的价值,忘记了人是在关系中滋养、成长和繁荣的。“正是在关系中人们寻找到生命的意义”[13]。
这种强调自主分离的现代自我不仅理论上存在短板,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后果。其最大的负面后果是产生大量“碎化的自我”,导致精神上的无根,产生心理上的孤独。对于当今社会普遍弥漫的孤独感,现代自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方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孤独感已成为现代人的通病。美国心理学家近年的一个调查为现代都市人的孤独感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在400名受访者中,百分之百的人自称常感孤独。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美国,已成为“地球上最孤独的地方”[14]。
这种孤独感与内在联系的缺失不无关系,而孤独感又与“情绪癌症”(emotional Cancer)的产生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劳伦斯·莱西就曾对一组癌症患者的生活史做过调查,他发现这些患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从童年时开始便留下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他们或早年丧母,或青年失恋,或中年丧偶,或老年失子。所有这些精神刺激,使他们变得沉默寡言、顾影自怜,对生活失去信心,对工作缺乏热忱,进而抑郁悲伤、情绪紧张、精神压力沉重,最终导致癌症的发生[15]。
在关系心理学家看来,虽然这样一个“自我”是一个现代西方人“集体的建构”,是集体创造的产物,但如果这一创造是束缚性的、压迫性的和毁灭性的,我们就该考虑放弃这一建构,创造出其他可替代性的方案。
二、 发展一种后现代的“关系自我”概念
“关系自我”(relational self)就是这种新的替代方案。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完全否弃”现代孤立自足的自我相反,关系心理学家试图“重建作为关系的和社会的自我”[7],发展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的“关系性自我”的概念。它用关系性的自我替代了独立自足的自我,用开放的“过程自我”替代了封闭静止的自我,用多元“创生的自我”取代了一元同一的自我。而将“关系”而非“自我”作为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的“基础”被当代西方社会称之为“心理学中的关系革命”[16]。格根则称之为哥白尼革命式的“文化转向”,亦即由把“自我”看作社会世界的中心转向将“关系”看作中心[6]。具体地说,与现代自我相比,建设性的后现代自我具有“关系的自我”、“过程的自我”和“创生的自我”三大特性。
(一) 关系的自我
所谓关系的自我,就是强调我们是关系性的存在。自我是关系性的,决定自我本性的是关系,正是关系构成了自我,离开关系没有自我可以存在。不过,关系心理学家特别强调:他们所说的“关系”不是指分离的自我之间的外在关系,而是内在关系或“有机关系”[12]。它是一个先于这个所谓自我概念的协同过程。格根对此写道:“我的希望是证明”,事实上一切可理解的行为“都寓居在生生不息的关系过程中”[5]。从这样一种立场出发,他认为“不存在孤绝的自我或完全私人的经验。”相反,“我们寄身于一个共同建构的世界。我们永远是从关系中涌现出来的。我们不可能逃离关系,即使在我们最私密的时刻,我们也从不是孤单的”[5]。著名《自我的根源》一书的作者查尔斯泰勒也强调,我们的自我是在共同体中,在与他人的对话中形成的[17]。在过程哲学家看来,大千世界的一切,从亲戚、朋友、同事,到山川大地、花草动物,都构成了我们自我的一部分,也可以说都是我们的“真我”[18]。这方面,关系心理学妙合了中国古人的天人合一理论。用怀特海的话说,自我是“整个宇宙的合生”[19]。
需要指出的是,“关系自我”概念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它是后现代思潮特别是建设性后现代思潮的产物,它的出现表征的是整个西方社会对个人主义的不满与对关系和联系的渴望。人们意识到,人是关系的存在。只有在对他人的关系中,我们才作为人而存在。“去存在不是去成为“孤立自主的”,而是“成为关系中的人”。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那里,“自我是彻底的社会的和关系的”[7]。“成为一个人也就是成为一个爱人者”[20]。按照著名后现代哲学家列维纳斯的分析,“发现我们面对另一个人,令我们觉醒,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感——一种对他者的无限责任……。通过委身他者,我践行这种责任感,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完全拒绝这种责任感,无异于谋杀。完全接受则等同于完美的爱”[20]。在列维纳斯那里,责任既是先于现象的,也是先于本体的。正是对他者的责任,构成了我们存在意义的来源。也正是站在这样一种关系的立场,列维纳斯拒绝笛卡尔的“我思”作为理解我们自己存在的出发点。对列维纳斯来说,他者不是个客体,不是一个在根本上可以与自我分开的东西。个人的主体性不是独立于他者的,相反,个人的意识是由他者的存在构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在根本上是对他者负有责任的。
正是从关系的立场出发,关系心理学家不满意现代的自我概念。认为它含有太浓厚的个人主义的色彩。而实际上,“个人的概念并不具有在先性,它只是“关系性的过程的一个副产品”(a byproduct of relational process)[5]。作为个体的自我仅仅是“关系的过程的衍生物。”真正具有在先性的是关系特别是内在关系。我们是关系性的存在。生态哲学的创始人奈斯则倾向使用“生态自我”概念以凸显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在他看来,由于人与自然的密不可分性,“自我本质上是生态的”[21]。法国人格主义心理学家伊曼纽尔·穆尼埃就曾强调:“我身上没有什么东西不是与地球和血液混合在一起的”[22]。著名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则质问道:如果“独立自主的自我”的神话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意识形态,“那么,除了深深的孤立感外,我们还能合理地期待什么结果呢?”[23]受这种现代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西方,人们错误地认为,“孤独的牛仔”可以独自存活。他与空气、水和事物不发生任何互动,“似乎他在分子水平上也与宇宙中的全部存在没有任何联系。”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正是这种立场导致了“现代儿童在凌驾于自然至上的‘玻璃盒’中长大成人”[23],成为无根之人。这种无根的教育,不仅削弱了“对地区周边联系、文化模式和生态系统的敏感性。”而且直接导致了我们与过去的决裂,与过去生命感的决裂,与周围共同体的疏离,与大自然的隔绝[24]。
(二) 过程的自我
所谓过程的自我就是强调自我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是变动不居的,而不是静止不变的,也就是说,“自我永远是处于变化之中的”[18]。它并非某种超越时间的东西,而是在时间中的,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之故,关系心理学家不满意现代西方语言中“自我”一词的名词性质,因为作为名词,它给人一种“静态的、恒久不变实体的意味。”而后现代的自我则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个动词,也就是说,自我永远在过程的在生成中。它的存在即是它的生成,它的生成即是它的存在。一个人此刻做什么,他/她的自我就是什么,一个人此刻在经历什么,他/她的自我就是什么。你此刻在做坏事你就是个坏人,你此刻在做好事你就是好人。在这个意义上,关系心理学家倾向于用“我做故我在”代替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
在关系心理学家那里,自我不是单一“固定的”,而是多元的,“灵活变化的”[25]。自我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不断生长的有巨大的可塑性、无限的可能性、无限的内在深度的过程。“自我”是“一个自童年以来通过本质性的关系而不断被形成的人”。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讲的是客观事物的动态性和过程性。而怀特海等当代过程哲学家则强调: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不是同一个人。这讲的是自我主体的动态性和过程性。这无疑进一步丰富了“一切皆流,万物皆变”的辩证法思想。你或许会争辩说,虽然经历了童年、青年、壮年,但“我张三还是我张三”。但你能在真正严格的意义上说,壮年的你和幼儿园的你是同一个人吗?且不说你的体格相貌,就是你的识见修养、精神风貌已迥然不同于那个幼儿的你。用关系心理学家的语言来说就是,如果我们镶嵌在多重(过去的、现在的、存在的、想象的)关系中的话,自我的一致性就是个神话。自我是“多元的”、“饱和的”、变化的[26],其所扮演的是一种在没完没了地改写中的角色[27]。其实就是你的身体每时每刻也在发生着变化。科学研究表明,人体胃细胞7天更新一次;皮肤细胞28天左右更新一次;肝脏细胞180天更换一次;红血球细胞120天更新一次;除了骨细胞更新需要7年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身体98%的细胞都会被重新更新一次[28]。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自我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西方现代主义的“静止的自我”是站不住脚的[7]。
(三) 创生的自我
与过程自我密切相关的是创生的自我。所谓“创生的自我”就是强调自我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在后现代的关系心理学那里,虽然拒绝“孤立自主”的自我,强调关系的重要习惯,但并不否认自我的自由与创造性。相反,它高扬创造性。强调作为主体,自我是“自我创造的”[25]。“自我在每一瞬间都经历了再创造——这就是自我的创造性,表现了自我成长和变化的巨大可能性”[1]。与机械论视人为机器不同,“自我”被关系心理学家看作是“活生生的人”。它与生命息息相关。而生命的一个重大特征就是它的高度独特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容易找到两个尺寸相同的零件,但却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用怀特海的话来说,在本真的意义上,生命是“原创性的代名词”[19]。创造性是人性的一个基本方面,用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大卫·格里芬的表述就是:“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的能量。我们从他人那里接受创造性的奉献,这种接受性同许多许多接受性价值(例如食物、水、空气、审美和性快感等)一起构成了我们本性的一个基本方面。但是,我们同时又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我们需要实现我们的潜能,依靠我们自己去获得某些东西。更进一步说,我们需要对他人做出贡献,这种动机和接受性需要及成就需要一样,也是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29]。
由于“创造”是人的本质属性,因此对于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来说,活着就是去创造,去奉献。因此,他们最推重的活动是创造性的活动,最推重的人生是富有创意的人生,最欣赏的英雄是从事创造的人而不是什么随波逐流的“消费英雄”或“购物狂”。同样,理查德·罗蒂所要“重塑”的人的“自我形象”也是一种创造的形象。他的原话是:“我们的自我形象就会是去创造而不是去发现的形象,这是曾经被浪漫主义用来赞美诗人的形象,而非被希腊人用来赞美数学家的形象”[30]。作为后现代主义圭臬的福柯对创造更是推崇备至。他曾经很奇怪,人们为什么将一张桌子,一棵树当作艺术对象,而却不把生活本身当作艺术对象。在福柯的心目中,生活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创造,因此是最好的艺术品。对创造性的迷恋深深地植根于福柯的思想中,在福柯看来,生活的真正乐趣就在于创造[24]。
如果说,“去创造”、“去寻找另一条路”,是后现代人最欣赏的一句话,那“告别封闭的老我,走向新的自我”则是关系心理学所推重的“创生的自我”的精髓。正是这种超越自我的精神造就和谱写了多彩的“创意的人生”[24]。
三、 “关系自我”概念对青少年人格养成的启迪意义
青少年是建设生态文明和振兴中华的主力军,他们的思想品德、精神信仰、价值追求和心理素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如何帮助青少年养成良好人格,塑造高尚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是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工作者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这方面关系心理学的“关系自我”概念对我们不无启迪意义。
(一) 有助于克服青少年的自我中心主义
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自我中心主义成为我国青少年中思想品德中的“最突出的问题”[31]。自我中心主义的一个最突出表征是“唯我独尊”。凡事都“以我为中心”,特别重视自我存在、自我感觉、自我价值,而漠视他人的存在与感受,轻视他人的生命价值,视自己为神圣,视别人为草芥,习惯于用自己的欲望统治他人,常让自我利益吞没他人利益。相应地,是同情心的极度匮乏。只关心自己的各种需要和利益,对与己无关的人和事达到了超乎寻常的冷漠程度,表现出毫无恻隐、同情、助人之心,因此而丧失了人性的善良,变得自私、封闭、麻木、脆弱、敏感、偏激,甚至残忍,呈现出“走我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特点和做法”[32]。近些年来,大学生“硫酸泼熊”、同窗相残、“虐猫事件”、药家鑫交通肇事杀人案以及“复旦学生投毒案”,无一不是这种自我中心主义泛滥的产物。因此,自我中心主义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按我国有学者的分析,自我中心主义“造成了人的价值追求的趋同化、人格的奴化、自我的物化、社会的‘散沙’化、社会关系的扭曲化或断裂化的问题或后果”[32]。青少年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振兴中华的重要依靠力量,其价值观的优劣“与祖国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所以,纠正青少年的自我中心主义价值取向“势在必行”[33]。
然而,在社会发展日益多元复杂的今天,把青少年的自我中心主义完全归结于“思想品德问题”,进而把匡正青少年的自我中心主义问题的重任一股脑儿地交给思想政治工作者是不够的,必须发挥心理学特别是广大心理工作者的作用,因为青少年的自我中心主义问题,既是一个“思想品德问题”,也是一个“心理问题”,因此破解此问题亟需广大德育工作者和心理工作者携手作战,亟需心理学的积极介入。这方面,关系心理学的自我概念可以起到一种独特的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解构和颠覆作为自我中心主义理论基石的“自我”概念。使青少年认识到现代“自我”概念理论上的虚妄性和现实中的危害性。意识到我们是关系性的存在。离开他者我们既无法存活,更别奢谈发展。我们的自我和他者之间互相依存,相互滋养。一个人的繁荣发展有赖于他人的繁荣发展。用苏哈克的话说,相互依存是我们的宿命。我们每一个人只是相对的中心,没人是绝对的中心。“我们不是偶然地相互依赖,而是必须如此”[34],否则我们一天都无法存活。
在解构“独立自足的自我”概念的基础上,自觉培育青少年的感恩意识,不失为医治青少年自我中心主义的一剂良方。在感恩教育中,循循善诱青少年思考如下问题:
是谁给了我生命?谁哺育我长大?
没有父母和亲人的关爱,我有没有今天?
是谁传授我知识?是谁一直在为我的成长做出无私的奉献?
是谁提供我的衣食住行?是谁给我创造了安全的生存和成长的环境?使我有了民族自豪感?
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是谁经常给我许多理解和鼓励?
没有他人的帮助,我有无可能拥有今天的一切[35]?
作为“绿叶”,我们如何报答“根”的情义?
这些追问和反省无疑有助于帮助青少年消解“唯我独尊”的执迷,从而步出自我中心主义的误区,生发出责任意识。因为自我从他者那里受益良多,不仅他/她的存在是由他者构成的,而且他/她的发展也是由他者支撑的。作为对他者和共同体的回馈,自我应该尽一切可能为他者和共同体贡献价值,用卢默的话说就是,真正的“关系自我”应该帮助他人,使他人能够对共处的关系,对所在的共同体“做出他最大的贡献”[36]。
在培育青少年的感恩意识过程中,可以考虑把“孝意识”的培养作为出发点和突破口。“因为孝不仅可以让我们找到生命的归属感,而且可以激发我们的责任感和崇敬感”[37]。这或许就是《论语》所说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二) 启发我们营造健康的生态环境和和谐的社会关系
与传统心理学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青少年个体心理发展,而较少考虑青少年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即其社会文化环境”不同[38],关系心理学对关系特别是内在关系的强调启发我们为青少年营造健康生态环境和和谐的社会关系,从而帮助青少年的人格养成。如果承认关系是人的本质性的构成,那就意味着你拥有什么样的关系,你就是什么样的人。正是与父母,与子女,与兄弟姐妹,与朋友,与同事,与他者,与自然,与大大小小共同体的关系构成了我们自己本身。这些关系是健康的,人也就是健康的。这些关系如果是不健康的,你就处于不健康的状态之中,你就是个“病”人。那么,通过建设一个健康的环境和和谐的社会关系,将直接有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要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因为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社会关系中的一环。要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就必须处理和保持好党员之间的纯洁关系。“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39]。同理,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有助于青少年的人格养成。因为每个青少年都是置身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亦即社会关系中的。这些关系的积极与否,健康与否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人格形成。这里所说的“环境”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家庭、学校和同伴,而且还包括虚拟世界。在互联网盛行的今天,虚拟世界对青少年的影响绝对不容小觑。因为今天,互联网已“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自我表达的机会”,人们往往第一时间利用互联网表达自己的“真实自我”。因此,互联网对于青少年“未来的和潜在的自我”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40]。有鉴于此,关系心理学家提示我们要充分占领虚拟世界的道德高地,确保其中充盈着正能量,避免其中的乌烟瘴气影响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
关系心理学如此强调关系会不会导致对自我发展的束缚呢?站在现代的视角看,它们二者是矛盾的,但站在建设性后现代的视角看,内在关系和自我的发展并不矛盾,它们彼此共存,相互促进。“我摄入的越多,我越感到联系,我个人的发展空间越大”[8]。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41]。以孔子为例,也正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孔子修养了自己,发展了自己。“在阅读《论语》时,我们面对的,是个以关系而构成的孔子,他一生的道路,都是在以最大努力,履行许许多多身份角色之中走过的:他是个充满呵护之心的家庭成员,他是个严格的先生、导师,他是个一丝不苟、拒腐蚀的士大夫,他是个热心的邻居和村社一员,他是个永久批评型的政治顾问,他是个感恩祖先的子孙,他是个特殊文化遗产的热忱继承者;其实,他也曾是个快乐少年以成人歌唱群的一员,在沂水畔嬉戏之余,唱着歌回家”[10]。可以说,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孔子的一生,丰富了孔子的一生,成就了孔子的一生。这正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言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自己”[42]。
事实上,当代成功学的研究也表明,成功是15%的专业知识+85%的人脉。这意味着人脉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成功者的一个必备的重要素质。根据哈佛大学就业指导小组调查结果表明,在数千名被解雇的雇员中,因人际关系不好而无法施展其长处的竟达90%之多。心理学家高尔顿和阿尔波特的研究也表明,人格健全的人,都同别人有良好的交往和融洽的关系。他们能够理解别人,容忍别人的不足和缺陷,能够对别人充满同情,给别人以温暖、关怀、亲密和爱的能力。
(三) 鼓励青少年告别昔日的旧我,创生新的自我
如果承认生命是个过程,那就要承认没有人是完美的。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要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走各种各样的弯路,甚至犯下各式各样的错误。这个时候是依然故我,破罐破摔,还是用一种过程的眼光、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些问题?对此,关系心理学的创生自我概念不无启迪作用。它可以帮助青少年走出昔日的旧我,通过建立新的关系而创生出新的自我,一个“更好,更丰富”的自我[27]。
传统的心理咨询师常常给人忠告是:“你需要爱你的自我”。此话听起来没错,但问题是:他/她需要爱那个自我呢?显然不该是那个不成熟的、闭锁的、狭隘自私的自我,而应该是那个我们尊重和敬佩的开放阳光的成熟自我。在关系心理学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这样一个成熟的自我不是给定的,而是慢慢培育出来的。在此过程中,个体的主动创造至关重要。因为在关系心理学那里,“自我的变化”是个常态[26],因为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无论你能否感受到,你都是一直在创造。你通过你所是的那个人,通过你的感受、你的有意识和无意识观点和信念的总和、通过决定你行为和反应的观念、通过你的目标和态度来进行创造”[43]。这意味着,创造贯穿在你的整个生命中。你是你生命之书的作者。如果你过去人生脚本写的不好,要学会改写。要勇于丢弃旧我,创造新我。“无论我们是否创造过一副画或一首诗,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创造者,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艺术。”[44]
需要指出的是,关系心理学虽然强调创生自我,但并非认为我的自我是自说自话凭空创造自己的,相反,它是“在回应世界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的”[18]。所谓自我创造,在关系心理学那里体现在自我用多重的方式回应世界。“自我创造意味着对于给定的环境做出新颖的回应。”1[8]
在关系心理学看来,要走出旧我,创造新我,就必须抛弃“完美主义的幻觉”[43]。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做起。认识到过去的那个自私的不成熟的旧我只是一种“低级的自我”,你现在的任务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将这个低级自我转变成高级自我。这是一种“英雄壮举”[44]。关系心理学认为,当我们抛弃了受害者的形象,不再认为自己是个“无助的孩子”,而是把自己当作生活的作者时,我们就会“体会到自身强大的创造潜力”[44],从而活出自己的最佳生命状态,活出优雅,活出美,活出自己“个性的舞动”[24]。
由于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我们所做、所说、所想都会对世界的其他部分发生影响,因此,我们自我的改变将直接影响着世界的改变。我们活出了美,世界也就会变得日益美好,我们活出了善,世界也就会变得日益善良,一如英国女作家爱略特在其小说《米德尔马契》中所写的那样:“世上善的增长,一部分也依赖于那些微不足道的行为,而你我遭遇之所以不止如此悲惨,一半也得力于那些不求闻达、忠诚度过自己的一生,然后安息在无人凭吊的坟墓中的人们”。这种用自己“微小的行为促进善的增长”的想法无疑将成为激励我们创生新我的巨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