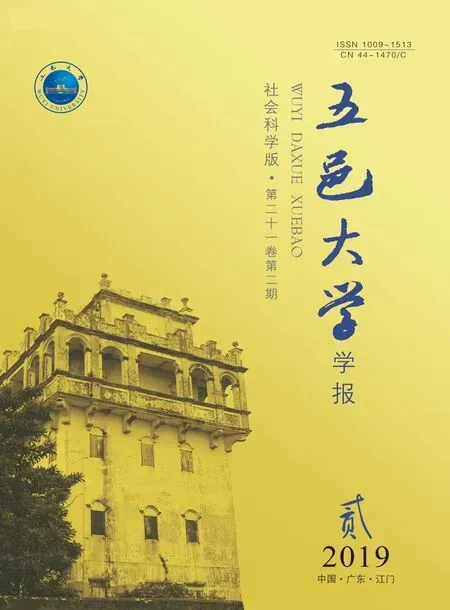“繁华落尽未成空”:梁启超逝世后之时评
雷 平,周 荣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梁启超作为维新变法的主要参与者,进步党的党魁、学术界的要人,于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56岁。梁启超逝世后,时人通过报刊杂志、日记、挽联等纷纷发表看法和阐明态度,评论其是非功过。此后,梁启超只作为历史人物进入研究者的视线,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基于各自时代主题和问题意识对梁启超学术及行事予以取向各异的评论,梁启超形象逐渐呈现出多面看山样态各异的情形。在既往梁氏研究、特别是相关各类传记著作中,在涉及梁启超评价时,研究者通常会引用个别梁启超逝世时的评论以佐证自己特定标准的评论。笔者所见,夏晓虹教授所编《追忆梁启超》(1991年)一书汇集了与梁启超有过交往者所写的各种追忆文章,侧重对梁氏学术生涯的评论;解玺章先生所著《梁启超传》(2009年)最后一章用“寂寞身后事”对梁启超逝世后时论的“沉寂”进行了解析。此外,迄今未见对梁启超逝世时评作细致梳理的研究。实际上,同时代人与后世研究者不同,其对梁启超的评论不仅是盖棺定论,也融入了同一生活境况下的复杂情感,而这种情感往往又不易为仅仅作为研究者的后来人察觉。因此,对梁启超的历史评价必须回到梁启超逝世时的时空场景中,关注各界人士不同取向的评论。
一、期刊杂志所见梁启超逝世之时评
梁启超逝世后,一些著名的报纸和有影响力的杂志都发布了其逝世的消息,或刊登相关的纪念性文章。作为全国性的大报,《申报》对梁启超逝世后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在梁启超逝世的第二天,即1929年1月20日,《申报》就以“梁启超昨在平病故”为标题发布了简短消息,称“梁启超今午后二时病故于协和医院、年五十六、遗骸运广慧寺、(十九日下午八钟)”。1月22日,《申报》又以“梁启超不起之原因”为题,论述了梁启超是“因体内Monelli末乃利菌蔓延致病乃至不起的”,而不是因肺病过世。①2月18日,再次发布了梁启超在北平举丧的相关情况,其文称:“今日梁启超开吊、中外学者及故旧到者数百人,梁著作未付印者,尚有三十八种,以《辛稼轩年谱》为绝笔。现由林宰平、丁文江、黄秋岳为之整理,梁将葬于西山卧佛寺东坡下(十七日下午八钟)”。3月2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也在其《时事日志》上发布了“梁启超因病在北平逝世”的简短消息。[1]
一些纪念性的文章、诗歌等相继在期刊杂志上出现。它们大多高度赞扬梁启超的贡献和为人。有些人赞赏梁任公是一个有特别影响力的思想家。比如抱一(黄炎培)的悼文称:“就文章论,戊戌讫今三十年来,自士夫以至妇人竖子,外薄四海。惟先生力能摄取其思想,而尽解其束缚,一其视听,此诚诱导国人迎吸世界新潮第一步最有价值之工作也……要之近世纪来,文章震力之大,应声之广。谁则如之?谁则如之?”[2]此文大力赞扬梁启超先生文章之影响力、思想解放之功。与此同调的还有发表在《长风》杂志上的悼文,其文说:“他本身性格本来不是一个政治家,并且也不是学者”[3]1,而是一个优秀的思想家,一个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对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再如郑振铎称赞道:“他在文艺上,鼓荡了一支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个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一种风气,引导了一大群的人同走。他在学问上,也有了很大的劳迹;他的劳迹未必由于深湛的研究,却是因为他的将学问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闻界上也创造了不少模式;至少他还是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与势力,却是普遍的,无远不届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的”[4]。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鼓吹其师康有为之今文经学,故论其学术影响,不可不论其对晚清今文经学发展之影响。梁启超尝自谓:“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则新会梁启超也”[5]。徐庆誉认为“梁氏既自认是今文学派的一个宣传者,我们现在要估定梁氏的思想在中国的地位,就当首先认清‘今文学派’”。[6]3署名为去夏的论者说:“他在今文学上的贡献,恐怕要比在国学考据上的贡献为大。”[7]这些论述都说明了时人对梁启超于今文经学所作贡献的肯定。
也有人称赞梁任公知识渊博,誉之为“通人”。张其昀说:“梁先生学问兴趣极广,自言对于文史哲地诸学,均所爱好,而于史学兴味犹浓,其用力最勤,著作亦最为宏富……实近代最富于修养之一通人也”[8]。
在对梁启超予以肯定性评价的同时,也有人颇有微词。比如著名作家苏雪林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某君仰慕梁任公先生的为人,想去参加他的葬礼,就邀请他的朋友(国民党员)一同去,他朋友的夫人不满地说:“梁启超是研究系的人,是腐化的分子,你若能担保我丈夫的名誉,不发生危险,便同他到追悼会!”[9]可见,此人对参加梁启超的追悼会存在顾虑,害怕自己的名誉受损,其实这与国民党对梁启超的态度相关。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长陈德征的悼文可为佐证,其文曰:“我们现在执笔来评论梁任公时,诚所谓‘盖棺定论’。我们觉得梁氏在从前一般人物中总算是有点成绩的人物。梁氏少年活动颇有声色,晚节亦甚好,惟中年颇多疵眚,一误于主义信仰,再误于投降军阀……辛亥光复以后,梁氏回国,从事政治运动,在熊希龄组织内阁时,一任司法总长,次年复改任币制局长;在段祺瑞任内阁总理时,梁亦被任财政总长,这些都是梁氏一生失节的污点”[10]。
二、时人日记所见梁启超逝世之评论
日记作为个人私密的记载,往往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心声,流露出对他人的真实看法。梁启超逝世之后,时人日记中的相关记载,表露出他们对梁启超不同的态度。
吴宓在1929年1月19日的日记中记到:“是日下午二时许,梁任公先生殁于北京协和医院。”[11]这短短20个字放在这一天内容丰富的日记中间,不显眼,似乎也不重要。梁启超是对吴宓有重要影响的人,他曾说:“儿时读《新民丛报》,即于梁任公先生倾佩甚至。梁先生之行事及文章,恒大影响我的思想精神”[12]。但在获悉梁启超逝世后,吴宓竟然只是简单的记录事实,如与杨树达的日记对比,则颇令人浮想。杨树达的日记十分简短,但其在同一天悲痛地写到“今日任公病逝于协和医院,中国学人凋零尽矣;痛哉!”[13]此后,杨树达又分别记其参加葬礼(一月二十日)和公祭(二月十七日)之事。杨的日记都十分简短,且不是每天都记,但是对于梁启超逝世有三天的记载,可见其重视的程度。由此可知,杨树达先生对梁启超的过世是很痛心的,且对梁氏的评价颇高。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与梁启超有过比较多的接触。胡适日记提及梁启超甚多。梁逝世之后,胡适对梁启超的评价可概括为三点。其一,为人和蔼可爱,全无城府。胡适在1929年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14]321其二,梁启超先生是旧学者。胡适举《墨经校释·序》一事为例来解释,他说:“以《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14]321第三,梁氏影响甚大,而自身成就甚微。胡适在2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了给梁任公作的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14]322然后又解释道“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统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故我的挽联指出他‘中国之新民’的志愿。”[14]323胡适的评价虽不无偏颇之处,实则代表了新派学者的看法。
胡适的高足顾颉刚和鲁迅兄弟都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知识分子,都曾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们都有日记,却都没有关于梁启超逝世的相关记载,这种“沉默”或许就是一种态度。鲁迅就对梁启超颇有微词。侯桂新研究《鲁迅全集》中的梁启超形象就发现,鲁迅对作为“政客”、“学者”、“文人”的梁启超几乎进行了全面否定。[15]鲁迅不喜梁启超或许有侯桂新认为的“傲慢的偏见和影响的焦虑”等原因。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1920年代的梁启超在部分人眼中已成了落后的象征,不再是时代潮流的引领者。
三、挽联中的梁启超评论
挽联是清末民初一种非常盛行的哀悼死者的文学形式,通常会对逝者的生平事迹、功过是非等作一总体评价,其中虽不乏溢美之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逝者的态度与评价。
梁启超逝世之后,在北平和上海两地同时在1929年2月17日举行公祭。期间许多与梁启超生前有过交往的人皆有挽联。
阎锡山、冯玉祥、何其巩为当时北方政界之闻人。他们皆送有挽联。内政部长阎锡山联云:“著作等身,试问当代英年,有几多私淑弟子;澄清揽辔,深慨同时群彦,更谁是继起人才。”军政部长冯玉祥联云:“矢志移山亦艰苦;大才如海更纵横。”北平特别市市长何其巩联云:“接清光在四载以前,说法维摩,我闻如是;稽政史溯卅年而上,危言同甫,士论如(云)何。”[16]364此三联均为应酬之作,阎锡山和冯玉祥的挽联实为他人代笔,何其巩则应为自己所作。从联中可知,他们皆对梁启超的才能、学术表示赞赏。
熊希龄与梁启超早年相识,交情极深。熊希龄的挽联情真意切,联云:“十余年患难交深(深交),有同骨肉,舍时去何先,著书未完难瞑目;数小时行程迟误,莫接声容,悲余来已晚,抚棺一痛更伤心。”[16]362-363此联除了惋惜梁任公“著书未完”之外,更多的是表现彼此之间的深情厚谊。从生平交谊出发的挽联还有丁文江,其联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星晨(日星)。”[16]364丁氏为任公好友,平生极崇敬任公。
除了表达情谊之外,挽联更多的是对任公一生政治活动、思想活动等的评价。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高梦旦联云:“不朽在立言,独有千秋追介甫;自任以天下,何辞五就比阿衡。”[16]365介甫是王安石的字,阿衡是伊尹的别称,这里把梁启超比作领导熙宁变法的王安石和辅佐商朝五代君主的伊尹。蔡元培的挽联云:“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16]365蔡氏的挽联虽和高氏之联似有相同,但其差别十分明显,高氏之联纯粹从政治上立意,蔡氏则兼顾了梁启超思想上之贡献,再者王安石颇多争议,而蔡锷(字松坡)在民国颇受赞誉。据此可见蔡元培对梁启超的评价比高梦旦要高很多。从政治和思想解放的角度评论梁启超的还有丁传绅、丁传琳二人,联云:“丙辰义不帝秦,丁巳力主参战,内安外攘,毕竟书生能救国;著论遍传九州,声名远腾四裔,功成身去,但开风气不为师。”[16]366他们对梁启超在民国时期反袁称帝、力主参加欧战以及思想解放的功绩表示肯定。
沈商耆则纯粹从思想上立意,联云:“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16]366上联称赞梁启超是近三十年新事业、新思想的发起和传播的先驱,下联“自有公评”则反映当时对梁启超的学术、文章、人品存在“不公评”的情况。
章太炎与梁启超相识于维新运动期间,戊戌政变后,章梁二人皆流亡日本。章太炎主张排满革命,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有过笔战经历,闹过许多不愉快。梁启超逝世后,章太炎挽联云:“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16]367章氏巧妙地说出梁启超和康有为之间的微妙关系,又赞扬梁氏再造共和之功。
杨度与梁启超早年相识,且都以中国青年自命,可说是莫逆之交,然而在袁世凯称帝的过程中,杨度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极力推动袁世凯称帝,乃至于袁世凯称帝失败,临死前发出“杨度误我”的怨言。梁启超则是袁氏称帝的反对者,写下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雄文。梁、杨二人自此为陌路。梁启超逝世后,杨度的挽联评论他“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16]368此时距离洪宪帝制已有十多年,从挽联中可以看出杨度并没有完全放下二人的恩怨,他认为梁启超的“事业本寻常”实为不公之论,实际上梁的事业就政治方面而言,维新变法和反袁称帝皆不同寻常。“文章久零落”是说当时梁启超的文章不受重视,“人皆欲杀”是指国民党方面嫉恨梁启超,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实情。最后一句“我独怜才”为梁启超辩解,对他的处境表示了同情。
四、梁启超逝世时评之特点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有重大影响之人物,其逝世后,由于亲疏有别、利害迥异,许多人或明或暗地表达各自不同的观点与看法,其特点有二:
其一,学界反响热烈,而政界则多有保留。学界对他的评价基本上以正面为主,都肯定他的思想解放之功、影响力之大,但也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时人特别喜欢将他和已故一年多的王国维相比。比如常乃德(字燕生)的文章说:“在一切未上轨道的国家里,社会需要思想家更甚于学者。一千个王国维的出现,抵不住一个梁启超的死亡的损失。”[3]3认为梁启超是思想家,王国维是学者,在飘荡中的中国,梁启超所起的作用比王国维大。又如,署名为舜生(原名左学训,左舜生亦为其笔名)的文章论到“假如我们说严又陵的努力算是近代中国人介绍西洋学术一部分较成片段的,王静菴算是在整理国故的成绩中一部分最为精湛的,那末,梁任公在学术上的贡献又刚刚是兼中与西而为一个常识的传播者,一个新思想的启发者。”[17]此论调与燕生的看法大同小异,都认为王国维是纯粹的学者,梁启超是思想的传播者和解放者。
与学界相对应,政界对梁启超逝世反应颇为冷淡,尤其是国民党嫡系人员更可谓是漠视。其原因正如国民党人徐庆誉所说:“梁氏最初与其师康有为都主张君主立宪,与同盟会立于相反的地位。入民国后,梁氏为研究系要人,不与国民党妥协。他死于青天白日旗帜下的北平不能引起党国重大的同情,是很自然的现象,毫不足怪!”[6]2实际上,梁启超逝世之后,蔡元培和蒋梦麟认为其对于中国学术大有贡献,曾提请国民政府下令褒奖,但遭到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他说:“梁启超不可不谓为反革命,生前不但反对本党,且反对国民革命,及其晚年,走入军阀段氏旗帜之下,其政治生命全以反革命为归宿,吾人不能恕其反革命之行为,而褒奖其学术也。”②胡汉民并不是个例,即使到了1943年,对梁启超的著作有了更多了解之后的蒋介石也曾说:“如梁专为学者,或终身从事于教育,而不热中(衷)政治,则其有益于国家民族必更多矣。惜乎,舍其所长而自用其短,至今犹不免为后人所不齿。”[18]在国民党人看来,即使梁启超在学术思想上对国家民族贡献巨大,但其政治上的错误也是不能忽视的。
其二,对梁启超之政治评价有异议,而对其学术则有较一致的肯定评价。从各方对梁启超之死的评价和态度来看,当时的舆论对梁启超之死主体上大多抱以同情。对于梁启超的学术成就及在思想上的启蒙之功,各界也大多表示肯定。但对梁启超在政治上的表现,因立场或个人恩怨而有不同意见。其时新派学者掌握了话语权,梁启超这样的旧派学者过世,新派学者及其影响下的广大青年,也不可能对其抱有特别的好感。在梁启超逝世前,就有人提出并发挥“梁启超魂附党国要人”之说。[19]在论者的潜意识里显然不以梁启超为然,即使是公开称赞梁启超的人,也往往略而不谈他在政治上的表现,或者简单地说一句“政治的思想与功罪,社会自有公论”[20]。
综合而言,梁启超逝世时,整个中国社会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国民大革命的洗礼,属于梁启超的繁华时代已经落幕,但梁并不凄凉,在其时的舆论文化场域中,人们仍然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梁启超之认知。对梁而言,可谓“繁华落尽”未成空。
注释:
①3月18日在《申报》上又有以“梁启超不起之原因的辩论”为题的文章反驳这种观点。梁启超的死因相当复杂,各方说法不一。
②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一七二次会议速记录》,转引自:黄克武:《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修订版)》,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第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