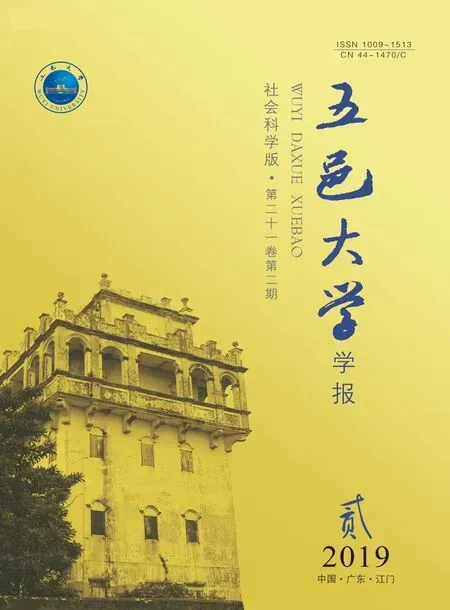论戴维·洛奇传记小说的自反性
蔡志全
(五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21世纪以来,英国文学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 1935- )创作了《作者,作者》(Author,Author, 2004)与《风流才子》(AManofParts, 2011)两部传记小说。洛奇的传记小说十分重视作为媒介和调节过程的写作本身,即“从认识论的角度,将生命写作本身问题化”[1],“作家在写作中反思,反思文类本身,反思传记家与写作项目及传主间的自我关系”[2]。洛奇的传记小说体现出一种元小说式的文本自省:“在故事情节进行中,洛奇频繁地对小说创作过程和方法加以讨论”[3]162,聚焦虚构的“真实”,同时又将其解构。这是一种自反行为:小说成了其自我叙事进程的隐喻,在书写自我的同时创立自我。可见,自反性(self-reflexivity)是洛奇传记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认为洛奇的传记小说是一种反思自身写作方式的元类型。
一、自反叙事
自反叙事通过提及其自身的生产条件,提醒读者注意其自身叙事身份。苏珊娜·奥涅加认为自反叙事可以被界定为一种写作方式,“一种自觉地操控小说结构,与小说游戏的方式。作为写作的元小说构成了一种特定副文类,其中自反性元素是其主要方面…… ‘自反性’一词提醒我们注意镜像结构(里衬、类比、框架、套层)以及与行动相伴的思想、意识和反思”[4]。
(一) 打破写实框架
在《作者,作者》中,自反叙事经常通过指射实际的作者来打破小说虚构的真实。比如在描写亨利·詹姆斯的生平创作时,洛奇明确地谈及创意写作过程。在小说的结尾,洛奇甚至以作者的身份直接进入文本,也就是欧文·戈夫曼所谓的“打破框架”[5]。这些内容用斜体文本形式与小说主要文本交替出现,旨在“把构建虚幻世界的所有细节一一暴露出来,以弃绝传统写实小说对于真实的天真信念”[6]13。
戏剧《居伊·多姆维尔》首演夜是小说的高潮,也是整部作品中自反叙事的高潮。首先,小说打破“真实幻象框架”,由叙述者向读者明确地说明了为何改换这种新的叙述模式:“正当这个故事,他的故事,这个视角极为有限的故事正在进行时,其他相关故事也在发生,其他的视角也在起作用,与此同时,与此平行,就像是在做着补充”[7]230。其次,来自不同人的叙事内容在小说文本中用方括号“[ ]”标识区分,犹如一张张来源不同的“剪报”,拼贴,并置在一起,它们之间各自独立,并无逻辑关联,顺序可以随意改换,需要读者去对比揣摩,是典型的后现代自反叙事。最后,在这部分,洛奇兼容并用了传记家与小说家常用的各种写作技巧:像传记家那样,尽可能多地收集与首演夜相关的不同报道、描述,“其中有亚历山大和其他演员的讲述,有坐在观众席中朋友的叙说,还有一些是当时他根本不认识、过了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才遇上的人说的,更有一些人关于当晚的回忆是通过他们之间共同的熟人转述的,或是事件发生后很久他偶然从一些人的回忆录和传记中读到的”[7]230-231。梁钫在谈到洛奇对首演夜的写作时这样评价:“洛奇在这一章中以自省的方式不仅评述了詹姆斯视角运用的合理性,同时也评价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经常采用的全知视角,暗示了这种视角给读者带来的不可信的感觉。这种自省在小说中运用得当,并没有割断情节主线,而是完成了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情节的形式更新”[3]162。也就是说,作者洛奇运用自反叙事手法,借小说人物之口分析评价了传统的全知叙事视角的局限性,在小说中评价分析小说的写作手法。
在《作者,作者》的结尾,洛奇运用“自我介入”的元小说手法直接进入小说文本,以作者身份评论詹姆斯的死后生活。这部分内容放弃了现实主义叙述,直接使用作者的语言,从当下视角评论亨利·詹姆斯:
就我而言,我在设想这一幕死亡场景时,好像是透过水晶球那透明的弧形表面看到的,也许,亨利·詹姆斯一生最痛苦的事实是,他先是在作家生涯的中期受到羞辱和拒绝,在《居伊·多姆维尔》崩溃时达到低谷,随即又成功地恢复了自己的创造力和信心,写出了后期的几部杰作,被称为现代心理小说奠基石的《奉使者》、《鸽翼》和《金碗》,然而,第一次痛苦经历后不到十年,他不得不又一次从头经历灾难性失败。这三部主要的长篇都是他在兰母舍写成的,并于1902至1904年间接踵出版,体现出他那令人惊讶的、持续涌动着的创作能力。然而,人们对这几部作品,不是在敬仰中搀着迷惑,就是完全漠不关心。[7]444-445
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作者一般不会“闯入”文本或者在文本中现身,正如福楼拜所言:“(艺术家)不该暴露自己,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自然中露面一样……至于泄露我本人对所造人物的意见,不,不,一千个不!我不承认我有这种权利”[8]。在此,洛奇作为叙述者试图以一种奇幻的临终安慰来满足亨利·詹姆斯成为名作家的渴望。这个场景“展现了虚构传记作者的任务是一种审美的奉献行为,而非一次不受欢迎的急切闯入”[9]。
作者自我介入构成了小说文本的一个元层面(metalayer),通过凸显作者的主体性展现了作品讲述历史故事的特征。在这个元小说层面,读者可以清楚地看见作者洛奇在行动:创作、解释、虚构另一位作者的生平与思想。读者完全明白这就是戴维·洛奇想要展现的亨利·詹姆斯。在小说框架中,洛奇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拥有主动权的作者形象,完全能够控制读者理解小说中詹姆斯的方式。这部分内容虽然篇幅不多,不过作用很重要:连接了洛奇与詹姆斯,“可是作者的手指还异常坚韧地扣着生命之线不肯放开。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松手……就我而言,我在设想这一幕死亡场景时,好像是透过水晶球那透明的弧形表面看到的……”[7]444。这小段文字包含了许多信息,不仅揭示了这部小说的本质,也反映了小说的目的。这小段文字彰显了一位固执且富有魔力的作者形象,他求生的意志坚定,藐视死亡。更重要的是还引入了一个元层面,让小说的作者进入小说的文本。叙述者也就是小说的作者洛奇的话语用斜体文本,旨在区别小说的主要文本。同时,这两部分用省略号链接。洛奇悄悄地把自己与亨利詹姆斯并置。省略号表明尽管詹姆斯已经去世,不过小说并未结束。既然詹姆斯已经无法继续叙述,洛奇就以讲述者的角色介入。在此洛奇描绘的作者有点像魔术师,可以透过“透过水晶球那透明的弧形表面”用魔法召唤过去的一幕幕场景。
(二) 斜体文本的“入侵”
读者在阐释文学文本时,总是“把它当作一个总的隐喻而与整个世界联系起来”,这种阐释“使文本和世界之间、艺术和生活之间形成了一道沟壑,把明显的事实和显而易见的虚构相结合,将作者和著述问题本身引入作品,在运用传统的过程中揭穿传统”[10],力图在这道沟壑之间造成“短路”,给读者以震动,使自己不归入传统文学范畴。卡普兰指出,传记与小说分属于两个文类,“区分这两种文类的特质中,或许有些顽固不融的东西,让二者无法不留缝隙、不留痕迹地对接融合,结合处总是显露无疑”[11]。
洛奇从未试图掩饰传记小说的虚构性,甚至还有意凸显卡普兰所谓的文类“缝隙”,这是他有别于当代其他传记小说家的重要方面。比如著名俄裔法国作家亨利·特罗亚(Henri Troyat)被称作20世纪三大传记文学家之一,其传记《托尔斯泰》(Tolstoy, 1965)因过于令人激动、技艺过于高超、太像一部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小说而备受诟病。当读者们开始好奇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艺术家的虚构时,常常会愈发惴惴不安。“优秀传记小说的优点是会刺激你去读传记、回忆录等一手资料,缺点是除非你读了一手资料,否则你不能确定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构”[12]。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指出,“当小说家使用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时,读者不知道有多少是取材于有记载的史实,有多少是他再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虚构出来的,这是历史或传记小说的主要危险之一”[13]。
在《作者,作者》《风流才子》两部传记小说中,为了不让读者“惴惴不安”,为了使传记小说“不归入传统文学范畴”,作者洛奇有意凸显了“明显的事实和显而易见的虚构相结合”的文本特征。他不仅大量引用了小说主人公詹姆斯与威尔斯等主要人物的书信、小说、文学评论等“事实”材料,并且用斜体文字标识这些引用内容,与小说的虚构文本形成强烈的对照,从而突出小说文本对其物质媒介的存在状态的关注。这是一种自反性叙事策略,“在传统小说那里,其物质媒介是透明隐身的。人们不会在意字体样式、纸张的装帧或印刷排版等方面,似乎它们自然而然、是其所是,与我们将要获取的小说意义毫无关联。然而在元小说中它们摇身一变成为阅读经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时刻提请读者注意其在生产意义方面发挥的作用”[14]。洛奇传记小说中斜体文字充分昭示了其“外部的、侵入性”特征,揭示了传记小说的虚构本质,反映了作者对小说文本的操纵和建构。
二、 传记素的自反性
戴维·洛奇在两部传记小说文本中引用、嵌入了大量斜体内容,这些实际上就是罗兰·巴特所谓的“传记素”(biographèmes)。洛奇通过使用“传记素”彰显传记小说的纪实与虚构的双重特征,同时也彰显了传记小说的自反性。
(一) 罗兰·巴特与传记素
罗兰·巴特在《萨德,傅里叶,罗育拉》中首次提出“传记素是由超然友好(没有偏见)的传记作家编撰的关于传主生命故事的细节”[15]9。巴特在《明室——摄影纵横谈》中再次谈到“传记素”:“我以同样的方式喜欢传记文章,在我的作家生涯中,这些传记文章如同某些照片一样,使我喜出望外;我把这样的文章称为‘传记素’;摄影和历史的关系,与传记素和传记的关系相同”[16]33。“传记素”是罗兰·巴特戛戛独造的一个新词,用于指细微的传记材料(一段细节,一段私人的迷恋——通常具有情感的或物质的特征),虽然细小,却能揭示出比装饰功能更多的信息。从构词法来看,“传记素”是一个“参照语言学的‘音素’(phoneme)概念造出来的新词”[17]。对于“传记素”的内涵,巴特概括为“浓缩了人物一生的核心事实或传记概要”[15]54。
“传记素”概念具有自反性内涵,体现了罗兰·巴特对传统传记写作的反思。巴特拒绝承认传记写作的传统愿望,即指称性幻想,这种幻想认为生平追随叙述,进而能够产生意义。与此观点一脉相承的是,怀疑以时间为序的线性关系,或怀疑把生平中一系列事件相应地表达为一种文本秩序。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想巴特杜撰“传记素”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表明生平的最小单位,经历的碎片,无拘无束的物体,轶事;同时,把写作本身这一媒介视为对栩栩如生地再现生平——这种过度被称为写作——可能性的一种自反性抵制。语言是生平留下的最后的碎屑”[18]。对于传记素的本质,巴特认为“传记素……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记忆而已”[19]109,因为传记素本身也是一种叙事性建构的产物;对于传记素的功能,巴特指出,“不只是源于传统目的论叙述的‘传记计时法’,传记素并不限制向他者的传递,也不限制向未来的、可能是虚构的接受或结合的传递”[19]278。巴特总结指出,“离开其所在的文本,进入到我们生活的作家没有统一性,仅仅是‘魅力’的复数,是几个贫乏细节汇聚之处,不过却是生动的小说微光的来源”[15]8。从这个意义上讲,传记素成就了传记小说,因为“传记小说依靠传记素获得人物生平故事的逼真性”[20]。
(二) 《风流才子》中自反性传记素
洛奇在两部传记小说文本中大量引用嵌入传记素,有时甚至是大段或成篇的斜体引文。这似乎是要向读者表明,在创作的过程中,作者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阅读了詹姆斯和威尔斯几乎所有的著作、传记、书信,书评以及相关的研究资料,从中提炼出传记素,编织镶嵌到小说的文本之中。比如在《风流才子》中洛奇以传记小说的形式,回顾、评论威尔斯的文学生涯与私人生活,把传记素与作者的想象虚构编织混成。因为“小说应具有复合性文体的特点,包括各种不同的文体和声音”[21]。传记素不仅提供了“事实”佐证,而且也是构成小说文本的重要内容。小说文本常常针对一些传记素展开,或是解读、或是评论,或是反驳,形成了巴赫金所谓的复调文本。洛奇使用传记素作为一手资料设定威尔斯的人物形象,然后根据自己的猜想和推断来表现威尔斯的所想所思。小说中的传记素主要包括主人公的作品(包括小说、传记、自传等),私人书信与日记,书评,等等。洛奇认为私人信件等传记素对于传记小说而言非常有用,“不仅可以展现人物的性格与动机,还可以向读者提供叙述的事实真实性的证据”[22]564。
穆拉(Moura Budberg)是威尔斯一生中真正爱过的三个女人之一(另外两个女人是两任妻子伊莎贝尔和简)。虽然穆拉拒绝与晚年的威尔斯结婚,也不愿意与他同居,不过在洛奇看来,在威尔斯心中,穆拉同样享有妻子的地位,或者把她当成事实上的妻子。在小说中洛奇引用了威尔斯写给穆拉的三封信的片段,这些传记素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也是洛奇分析威尔斯与穆拉之间关系,尤其是探查风烛残年的威尔斯所思、所感的重要参考资料。《风流才子》的文本中展现了洛奇对上述三篇书信片段进行文本分析、寻觅字里行间隐含的意义的过程。他继而给出了自己的结论:“(威尔斯在信中)反复提到穆拉叮嘱他用木板封住窗户,意在在家务事的安排上,赋予她一种妻子的角色。他害怕孤独,害怕没有女性伴侣关心他的健康,这种恐惧一直困扰着他。总有一天会说服穆拉搬到汉诺威排屋来住,他还没有完全放弃这样的希望”[22]33。在此,洛奇不仅给出了分析结论,而且把原始的参考资料以及分析研究过程展示给读者,因为“元小说的写作方式抬举恭维了读者,认为读者与作者在智力上是平等的”[6]247。洛奇把自己放在与读者几乎“平等”的位置,他的身份转而成为历史资料的分析者和研究者、小说文本的编辑者,同时邀请读者参与一同分析思考史料,引领、提示读者得出最终的结论。
从小说的物质媒介——文本的印刷字体来看,洛奇小说中引用的书信片段一律采用斜体编排,有的信件全文引用,独立成段,保留了完整的信头与信尾称谓,比如“亲爱的H·G先生,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感谢威尔斯太太的爱。……如果你能想到我多么喜欢收到您的来信,就别忘了再给我写信。你的永远的,安布尔·里弗斯”[22]278;“亲爱的朋友,今天早上我的小女孩诞生了……我们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对我妻子和儿子的爱。送上新年最好的祝福!H·G·威尔斯”[22]364。另外的一些书信片段,一般只有短短几行甚至一两行,这时文中总会有“书信”“便条”之类的提示字,表明所引内容为书信片段。换言之,书信片段这种传记素在洛奇小说文本中得到作者的提示、凸显。
洛奇在《风流才子》中杜撰了一些信件(片段)。这些虚构信件在形式上与“真实的”传记素无异,或者与“真实的”传记素出现在同一段文字中,因此一般读者很难识别区分,甚至会因其仿真形式信以为真,因为“一封虚构的信跟一封真实的信没什么两样”[6]27。不过,不同于拜厄特,洛奇在书末的致谢中不仅逐一“揭秘”了哪些是虚构的信件,甚至还标明了具体的页码。显然,洛奇通过引用传记素实现文本的自反性叙事,表明小说作者在工作、在编辑、在写作。
在洛奇的传记小说中,“传记素”实际上扮演着十分重要且看似矛盾对立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传记素”是将人物的生平与传记小说紧密联系的有效方式,从而增强传记小说的真实感,进入文本的“虚拟现在”[23]。“传记素”作为传记小说虚构的基础和出发点,不仅证明传记小说是“基于事实材料的虚构”,表明其“纪实”的文类特征,而且提请读者相信作品是真实可信的,有效地增加小说细节的真实感。另一方面,“传记素”是碎片化、不完整的信息,作家可以通过传记素,探查知识的碎片化、分裂的主体性等后结构主义观念。进一步而言,传记素还有伪造的可能,即使不是虚假的,传记素本身也是小说作者一种叙事性建构的产物。所以,“传记素”将叙事、尤其是历史叙事以及身份的建构本身问题化,揭示叙事是如何被建构的。因此,“传记素”沟通了传记小说中现实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在二者之间形成叙事张力。
三、结 语
戴维·洛奇的传记小说沟通了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小说与后现代主义历史编撰元小说,具有后现代小说的一些显著特征:“重在表现认识论的转向,即作品以自反指涉、模糊文类边界等方式凸显作品本身的存在”[24];同时又与二者有别,“19世纪的历史小说,为了说服读者虚构事件的‘真实性’,才引入或者提及‘真实的’人、地点与事件。不过,在历史编撰元小说中,其关注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不再用于证明虚构的真实性,而是指向历史知识的不确定性”[25]。洛奇的传记小说反映了当代英国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英国小说在坚持文字对客观世界指涉性的同时,也关注文本的虚构性和自反性”[26]。自反性揭示了洛奇传记小说虚实融合、虚实映衬的本质;自反性突显了文本中作者的在场,展现传记小说如何将“史实”演绎为文学真实的过程与本质,即使是非虚构文学,也是作者创作建构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