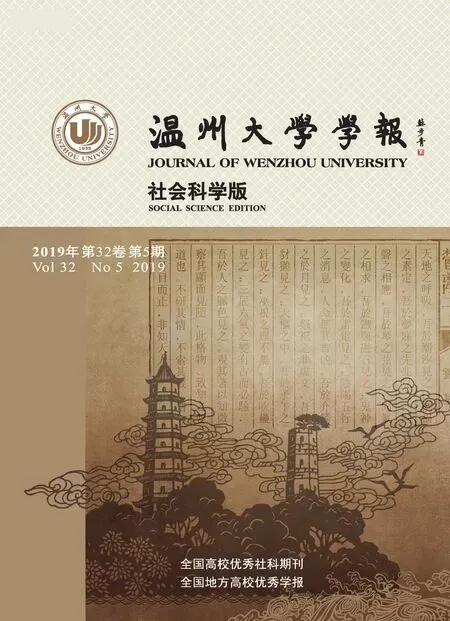论《劳燕》对“抗战书写”的突破与创新
韩宇瑄,伊艺飞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28)
作为张翎首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劳燕》,一经发表便备受关注。研究者或从主题意蕴、历史认知的方面读解《劳燕》主题,或从叙事学角度考察其书写向度,或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人物命运①参见:杨莎莎. 人性书写中的历史认知:论张翎长篇小说《劳燕》[J]. 名作欣赏,2018(23):104-106. 王玉琴. 耻辱、拯救与自由:张翎《劳燕》中的主题意蕴解读[J]. 学术评论,2017(5):101-106. 刘佳怡. 陌生化叙事下的人性书写:评《劳燕》[J]. 出版广角,2018(3):93-95. 宗波. 他乡视角下的人性书写:《劳燕》的叙事与美学[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6):114-118. 邓珊珊. 战争中的女性与女性的战争[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524-527. 孙良好. “疾风”知“劲草”:张翎新作《劳燕》之一解[J].2018(1):73-76.,但如果将《劳燕》放在更加宏阔的文学史流脉之中,便会发现与《劳燕》同题材的“抗战书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由来有自,形成了不断发展和流变的“抗战书写”谱系,而在这一谱系中,《劳燕》对“抗战书写”进行了突破与创新,展现出独异的美学价值与文学史地位。
一、“抗战书写”的发生与流变
如果将20 世纪的中国历史视为“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变奏”,那么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无疑是这支奇异的变奏曲中最为高亢悲壮的高潮。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在民族解放、维护和平方面的积极意义不可磨灭,但同时也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形成了民族危机阴影笼罩下“带有明显的危机压顶的特点”的危机文化[1]。
在这一文化心理的影响下,宏大叙事压倒个体灵性、激情炽热压倒平淡冲和、民族国家压倒文化启蒙、单纯坚实顽强的“我们”构成的“大合唱”压倒了苦痛孤独寂寞的“我”的浅吟低唱,形成一种“既单纯又狭窄,既朴实又单调”[2]260的思想情感方式,改写和塑造着“抗战叙事”。这样的“抗战叙事”不仅共时态影响着抗战时期七月派、战国策派、延安文艺等创作,共同构成了“或以悲慨高亢传达出广大人民的抗战心声,或者以拙朴浑厚呈现着中国民族的雄健气派”[2]261的发达的抗战文艺;并且历时地影响着当代文学阶段《青春之歌》《烈火金刚》《苦菜花》《风云初记》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叙述美学,并终于在《沙家浜》《红灯记》《平原作战》等抗战题材“样板戏”中达到最高潮,汇合进入无产阶级文艺激进派一元化的美学图景。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和文学艺术的新变,“抗战书写”开始呈现出多元竞构的全新格局,这其中,既有《黄河东流去》《历史的天空》《野葫芦引》这样试图接续17年现实主义“抗战叙事”传统,试图以人群断面反射波澜壮阔大时代的作品;也有《抗日战争》《南渡北归》这样通过大量史料剖析,全景、写实地呈现抗战时期军事、经济、文教等方面的史诗性作品;更有《温故1942》《红高粱》《吾血吾土》这样将叙事焦点放在普通人身上,通过他们在抗战中或抗争、或偷生、或悲壮、或凄婉的个人经历,关注战争对于人性的摧残与改变的作品。此外,在《圣天门口》《古船》《白鹿原》《丰乳肥臀》等旨在反映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变迁全景的史诗性作品之中,“抗战书写”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篇幅,并构成整个故事中人物沉浮变化的关键枢纽。
纵观这些新时期的“抗战书写”,往往具有某些共性。首先,在叙述视角方面,这些作品往往采取作者全知视角,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对于故事直接进行的讲述,这一方面体现出作者驾驭个人、群体命运后的宏大时代或直接进行宏大叙事建构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与这些作品中出现的纷繁人物,及其背后所牵涉的群体背景息息相关;其次,在形象塑造方面,这些作品往往倾向于通过一家、一地、一群体的代际选择,以小见大,塑造群像,并在纷繁复杂的关系交织中书写抗战这一事件对于原本就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易位与冲击;此外,在历史观方面,这些作品多承袭现代文学中“抗战文学”,选取民族反抗与民族解放的视角,但是,抗日战争结束后的70 余年间,伴随着新史料的挖掘与史观的更新,战争各方面各层面史料的发现使得这场战争的影响和形象更加具体和丰满,个体在战争中的命运以及战争结束后仍然难以抹平的创伤更加受到关注,思想界越来越多地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去反思战争,而历史学界则越来越多地将中国的抗战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背景下去评估这场战争的全球性意义。这样的新变,不能不促使文学界对于我们原有的“抗战书写”进行相应的调整——或至少是补充。在这样的视点之下,张翎的《劳燕》对于“抗战书写”的丰富与突破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众生喧哗的言论场:《劳燕》对“抗战书写”的突破与创新之一
《劳燕》对于“抗战书写”的突破首先体现在众声喧哗的言论场的构建①参见:张翎. 劳燕[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下引该书原文不再一一注出。。在传统的“抗战书写”中,作者的全能全知视角使其能如同上帝般俯瞰笔下的芸芸众生,通过第三人称的指示,对笔下人物进行调遣,编织其矛盾、安排其命运,而“抗战走向胜利”更像是一种先验性的历史预言,所有人物的命运、所有事件的结局不论过程中经历多少坎坷和磨难,都终将服膺于这一巨大的历史潮流,走向光明,走向永生。这样的书写方式当然有利于构筑史诗性的结构,使作品的逻辑线索鲜明异常,且更有利于作者主观意念的传达,却也在不经意间构筑着一种叙述人的话语霸权。在这一话语霸权下,主人公(在特殊历史阶段被提升为“主要英雄人物”)的一切行为有着天然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而其他次要人物的行为如果不与主人公保持一致,则必然是荒谬可笑、不合逻辑的。这样的“抗战书写”在构筑双方严厉对峙、主人公面临严峻战争环境的情节中,无疑是行之有效的,在一定的文学史时期内也形成了特定的“革命英雄传奇”类型,但伴随着“抗战书写”走向深入,开始触及战争中更为深层的、无问对错的人性以及复杂的、并非可完全归咎于战火的悲剧时,单一的直线性的叙述便显得粗暴而无力。
《劳燕》所遇到的正是这样的问题。小说没有直接描写战火纷飞的战争场面,故事主要的发生地——四十一步村、月湖,在战争中都因闭塞的环境而成为某种看似宁静的“世外桃源”,但一次空袭粗暴地将阿燕和刘兆虎一家卷入了战争之中,而机缘巧合的相遇又使他们与另外两位主人公——牧师比利和军官伊恩·弗格森的人生产生交集,在交集中演绎出各自或悲或喜的别样人生。战争无疑改变了三位男主人公的人生,但这并非是小说关注的重点。三位男主人公命运的交集点——阿燕及其悲剧的一生才是小说叙述的中心。在传统的“抗战书写”中,战争中女性的不幸毫无疑问是战争造成的,这样的揭示对于阿燕而言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却未必能够揭示悲剧成因的全部。正如牧师比利所说“战争把第一只恶手伸进你曾经饱满结实的生命之袋,我们跟在它之后也伸出了我们的手……‘我们’其实是每一个走进你生活的人,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罪孽”,“我们”中的所有人,都并非穷凶极恶的侵略者,相反,在阿燕生命的各个时刻,“我们”都曾以不同的方式或多或少地给以阿燕帮助,但也曾不同程度上给阿燕以不可挽回的伤害。爱与恨就这样难以剥离地黏连在一起,以至于作者无法使用锋利的手术刀将其中恩怨是非完全分割,因此在《劳燕》中,作者独具匠心地构造了众声喧哗的言论场,给三位与阿燕发生过纠葛却又命运攸关的男主人公平等的发言机会,让他们在对话和喧哗中,逐渐走向事实的明晰。
构筑言论场,令作品中人物分别发声,以各自的视角共同构筑起故事的全部的结构形式在新时期文学中并不罕见。早在1980年,“人道主义”作品《人啊,人》中,戴厚英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讲述了一群高校知识分子在几个历史转折关头由于各自选择所造成的悲欢喜剧①参见:戴厚英. 人啊,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而后来,李洱的《花腔》、莫言的《檀香刑》等作品纷纷采用这样的模式,借助不同人物视角和立场进行独白,在是非和观念的碰撞的碎片中,拼合出故事的全貌。而在《劳燕》中,张翎使用这样的手法,又有所发展,将故事的讲述时间预设在刘兆虎、伊恩、比利三人去世,三人的鬼魂践约相聚之时,这样的设定不仅使得三个历经沧桑的灵魂脱离了现实利益的纠葛,其立场更加真诚,省去了如同《花腔》之中三人因各自利益关切隐瞒部分实情使故事扑朔迷离之嫌②参见:李洱. 花腔[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敞开心扉,坦诚相待,使文本更加流畅,也使得三人在经历了历史风云变幻和充分的生活阅历后可以对自己的一生有较为明晰的认识,避免了对于《人啊,人》中人物思想语言脱离人物设定实际的指责,检阅一生,深入反思,使反思深度和广度达到最好效果。刘兆虎、伊恩、比利三人的陈述,并非是《人啊,人》中立场迥异的严厉控诉,也并非是《花腔》中处于特定情境下保护自身利益的斗智斗勇,亦非是《檀香刑》中立场身份各异的炫技讲述③参见:莫言. 檀香刑[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而是三个历经生命沧桑的灵魂,在经历了大悲大喜、大风大浪后归于平静的大彻大悟,是脱离了肉体皮囊和现实利益纠葛后风轻云淡、波澜不惊的智慧絮语,是站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距离外的深情凝望,是面对历史和上帝的理性反思和神性忏悔。在三人陈述外,还佐以部分信件、札记、报道乃至动物之间的对话,不仅使得故事更加立体,也使得对于战争的反思得以从不同路向分别开启。正如比利在末尾所说的“那是所有人的战争,也是每个人的战争,我们把战争庞大的身体肢解了,每个人手里都捏了小小的一块,于是,它就成了一个人的战争。这是我们做的自由抉择,我们都必须为手里的那小小的一块负上全部的责任和代价”。张翎肢解了宏伟磅礴、二元对立的“抗战叙事”,而将之打碎为一个个忏悔的灵魂碎片,这不仅触及了反思的痛感,也使得他们拼装起来,构筑成一段段更加立体而丰满的“抗战书写”下的际会与传奇,从而体现出“尊重、敬畏历史的真实存在,正视历史的残忍和暴力,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对个人命运的作用,关注被遮蔽的普通人的心灵史和国家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命运浮沉”[3]的“不解构”的历史还原与“非传奇”的历史建构。
三、极致美学中的人性逼视:《劳燕》对“抗战书写”的突破与创新之二
《劳燕》对于“抗战书写”的第二点拓展体现在极致美学中的人性逼视。长期以来,在左翼传统与现实主义一元化的烛照下,“抗战书写”往往或着力于残酷的战场描写,或注目于日常生活被战争搅扰后的颠沛人生,并以其人物悲惨情境的日常化、颠沛过程的长征化、人生跌宕与抗战进程的共时化形成了诸多“抗战书写”的经典叙述。作者往往将人物命运置于抗日民族战争的旋涡和洪流中,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一点点见证人物命运伴随抗战风云的跌宕起伏,人物性格伴随战争淬炼的发展,人性伴随着战争带来的悲惨命运的沉沦或奋起,以及在此之下不同人物的人生选择。这样的书写方式在使作品具有宏大的史诗风格和典型性意义,形成了慷慨沉郁、舒长浩荡的美学风格之外,也使得作品在漫长的战争进程铺陈与人物成长中,形成了一种“悲而不痛,哀而不伤”的阅读体验。一个最为直观的佐证便是,但凡“抗战书写”,大多数都是大部头:《历史的天空》《黄河东流去》都是五万字上下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分上下册,而《抗日战争》《南渡北归》《野葫芦引》更是长达三至四部的多卷本巨著。显然,以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和宏阔内涵,以煌煌万言大书特书自有其合理性,但史诗性著作漫长背景的铺垫、复杂的人物网络、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萃取往往使得对于人性和战争的反思无法深入,即使偶有精当之笔也被淹没在宏大结构的浩瀚文字之中。作为一位有着“痛感”追求的作家,张翎在《劳燕》毅然舍弃了对于抗战的史诗化书写,而是以极致美学长针直入,直戳战争撕裂的人性伤穴,在两万七千余字的篇幅中,便完成了对于人性的逼问。
极致美学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大刀阔斧地裁剪去漫长而琐细的日常生活,“小心翼翼地收藏并大开大合地演绎了所有动荡的、绝望的、窒息的段落”[4],将眼光驻足于百年中国特定历史事件中的极致情境,以接二连三的悲剧性时刻将人物置于绝境,将故事推向高潮,从人物绝境之中的选择与割舍观照人性,萃取出人性的形而上意义。面对浩瀚的14年抗战史,作者敏锐地从中抽取出三个人物——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学员刘兆虎、卫理公会传教士比利、美国海军军官伊恩,借抗战之力,将三人强行突入江南乡村小女孩阿燕的生活之中,数次沦入进退维谷的窘境。三位男性以各自对于阿燕的理解突入阿燕的生活,自信满满要给之以幸福,但最终他们发现自己对于阿燕的理解仅仅是自我命运在阿燕身上的投射,最终,刘兆虎病逝,在对阿燕造成伤害后与阿燕劳燕分飞;比利死在旅途之中,如星辰陨落,未能践行自己的誓言;伊恩回到正常生活轨道后见异思迁,留给了阿燕孩子后如风远走,最终使得阿燕的损失“那样彻底、那样惨重”。如果说刘兆虎使她面临的是亲情的窘境,比利使她面临的是伦理的窘境,伊恩使她面临的是爱情的窘境,那么这三重窘境的合力,又使她在面对整个世界的过程中面临着被误解乃至被践踏的窘境,使她在进退维谷之际发出了“你们为什么只知道欺负我,你们为什么不找日本人算账”的质问与呐喊。“战争把生命搅成肉泥和黄土,战争把爱情挤压成同情,把依恋挤压成信任,把肉体的欢娱挤压成抱团取暖的需求”,战争如一只巨手,将所有人的生活推出了既定的轨道,将人最美好和最自私的一面同时暴露出来,而战争中的人又以自己有意无意的爱或恨倾注在一个无辜的女孩身上,使她面临更加宽广的深渊。如果说极致美学的公式在于“日常生活-绝境=人性”,那么张翎在对于人性的剖析中得出了新的公式“人性+人性=进一步的绝境”。在绝境中,对男女爱情的反思、对男女社会性别的反思被升华为对战争的反思,对战争的反思又再次被升华为对人性的反思。正如作者所说“他知道人性是怎样一件千疮百孔的东西。战争是一个世界,和平是另一个世界,两个世界各有门,却不通往彼此”,通过极致情境挤压下的人性拷问,《劳燕》达到了以往“抗战书写”的未及之域,也使得“抗战书写”有了超越抗战本身的可能性。
四、以国际视野观照抗战的非冲突性史观:《劳燕》对“抗战书写”的突破与创新之三
《劳燕》对于抗战书写的突破和拓展还体现在以国际视野的历史观。一般而言,抗日战争被视为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而抗战的胜利被视为“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取得的,”“中国人民的巨大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和应用的民族抗争,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5]。这样的“战争文化心理”长期以来塑造着现当代文学的“抗战书写”的风貌。新时期以来,这种“战争文化心理”得到舒缓[6],抗日战争越来越多地被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伟视野中加以观照,越来越多在抗日战争中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战斗乃至牺牲的反法西斯战士的事迹得到弘扬,对于抗战的历史叙述开始超越民族矛盾的二元对立,升华为世界上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力量和法西斯势力的较量,但在文学叙述中,这样的声音仍然鲜见,直到《劳燕》的出现。
作为“抗战叙事”作品,《劳燕》的主人公不再是居于历史旋涡中心的国共抗战英雄和日本侵略者,也并非是抗战中颠沛流离的黎民百姓与知识分子。《劳燕》的三位男主人公分别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学员、来华传教牧师和美国海军军官,虽然深度地参与到抗战当中,但却无疑是传统抗战视野的“边缘人”。且不说在《红岩》中被塑造的为血债累累的反动魔窟的“中美合作所”和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排头兵的传教士,即使是作为援华海军军官的伊恩,其声名也大大逊于同时期的空军和陆军同僚。但是在故事中人们看到,尽管身处相当边缘的境地,但三人都为抗战竭心尽力,深度地卷入了这场改变他们人生的战争:刘兆虎作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学员之一,立志成为抗战中技术制敌的尖兵;伊恩作为援华海军军官,不仅将先进的军械技术倾囊相授,而且注重对于中国学员价值观的培养;牧师比利也被卷入这场战争,为战争冒死搜集情报。尽管书中对于直接的战斗场面着墨不多,有关这支队伍的实际战绩也并未做过多解读,但是在为数不多的战斗中,我们看到这支队伍的战斗是英勇的,而其中每个人焕发出的英雄主义光辉足以令习惯了另一套抗战叙事的我们耳目一新。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书写这曲可歌可泣的国际主义悲歌时,时时警惕过度浪漫的、乐观的英雄主义叙事,而是在他们可能成为“神”的情况下,随时将他们拉回到“人”的本位,于是我们看到:以一己之力掩护队友撤退而壮烈牺牲的“鼻涕虫”,在生活中不仅是个惹人嫌恶的家伙,而且曾对阿燕犯下强奸罪行;在战斗中英勇战斗的队长,在生活中曾多次欺凌刘兆虎,而即使是刘兆虎这样饱含理想的抗战青年,其从军目的也包含着太多的阴差阳错与事与愿违,对阿燕海誓山盟的伊恩,回国后轻易地忘记了阿燕,与旧爱结婚,而慈父一般照料阿燕的比利,其实对阿燕也有着忘年的感情,但这一切并没有消解他们为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相反使得他们更加有血有肉、生动具体,也更加真实地存在于文学的世界之中。
出于对包括“抗战书写”在内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失望,一些文学史家曾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文学”作品,认为“西方或苏联的军事文学,展现的大多是战争之残酷及反人性的一面……而中国作品中,主人公以投入战争为生存目的,作者也以歌颂战争为写作目的”,并指出“西方和苏联作品可刻意塑造的是一些受战争压抑、因而讨厌战争的人物形象,而这时期中国战争题材作品可以塑造的却全是战争英雄”[7]120-121。这样的评价固然有苛刻之嫌,却也戳中了原有“抗战书写”的痛处所在。因而,《劳燕》中所体现出的战争观便足称宝贵。整部作品贯穿着一以贯之的反战思想,战争对正常人性的戕害和正常生活的改变被三位主要叙述者一再提及。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无疑是英勇的战士,却也是极度厌倦战争、希望回到正常生活轨道的普通人。即使是在其它作品中的日军士兵,作者亦将之还原为死前呼唤母亲的普通人,体现了足量的人文关怀和战争文学视野。
以国际视野观照抗日战争的视角不仅在题材论上体现出巨大的突破,更使得作品在内涵方面体现出更为广阔的隐喻和可能。如果可以不计过度阐释的指责,则更可依据詹姆逊“民族寓言”理论来观照《劳燕》对于历史的理解别寄。在明显的身份寓言中,刘兆虎可视为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少年阶段,他们曾与中国的民众结成广泛意义上的同盟,并在西方新的思想(《天演论》)的鼓舞下试图对民众进行启蒙。面对外敌的入侵,他曾有浪漫的革命豪情,但最终终于难以克服自身的软弱性,而服膺了民族主义的“大义”结成同盟,虽高蹈于民众之上,但在暴风骤雨来临之际由于其先天的软弱性,仍然不能拒绝来自民众的庇护和养育,并给民众带来深重苦难,事与愿违。伊恩有着先进的武器和思想,也曾有着拯救与启蒙的雄心,对中国民众充满敬慕和好奇,甚至不惜为之一战,但这一切于其本体而言终归是他者,一旦形势发生变化,他也不得不抛弃当日的诺言而远走高飞。比利可视为近代以来进入中国的外国宗教势力,怀着传播福音的目的而来,但面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不得不采取医药和教育并重的手段,并通过一系列中国化的政策博取民众信任,当灾难袭来,外国宗教势力部分程度上充当了民众的庇护所,而为了达成庇护民众不得不自身也与政治达成同盟,却最终因民众的不理解无法实现本来目的而败走,成为孤独的幽灵。而阿燕则可视为近代以来中国民众的象征,近代以来,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中国民众自给自足的宁静生活,将中国民众推入了深重的苦难之中,各种国内外势力接踵而至,纷纷试图对之以自己的定义和判断进行救赎,却不同程度上造成了伤害。但在不断地伤害与离别中,中国民众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善良、隐忍和坚强,并始终怀着善意和感恩去看待这个世界。阿燕的品格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中国人民一直以来的民族性格,更体现了作者包容和实事求是的历史观念:尽管历经磨难,但阿燕对身边的所有人都饱含着感恩与悲悯,不论是对刘兆虎的营救与照料,还是对牧师比利的信任,亦或是对伊恩之“恩”的刻骨铭心,都体现了作者用爱和感恩对抗战争带来的伤痛的理念。如果说20 世纪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颠沛流离的劳燕分飞的历史,那么唯有正视历史,带着不变的宽容、爱和感恩,才有可能遥燕归来。
正如陈思和所说,“到1949年为止,20 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是由一连串的战争构成的,其中对现代中国意识结构直接发生影响的战争有两次,一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一次是1937年的抗日战争”,并指出“第二次战争的结果是民族积极性的高扬,并对中国当代文化规范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7]62-84,也正是从那时起,“抗战书写”成为几代中国文学工作者所致力探索并产生丰硕成果的领域。近些年来,伴随着历史观的新变与多元,“战争文化心理”逐渐被克服而远去,“抗战书写”呼唤着新的视角与新的突破。《劳燕》无疑是这样一部具有突破性与创新性的作品,它使我们在面对那段耳熟能详却又疏远陌生的历史时,在众声喧哗中倾听回声,在生命绝境中探索人性,在更加宏阔、也更加宽容的历史观的怀抱下正视历史、反思历史、面对历史,并在这样以人为本的历史观的观照下对“抗战书写”进行不断地突破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