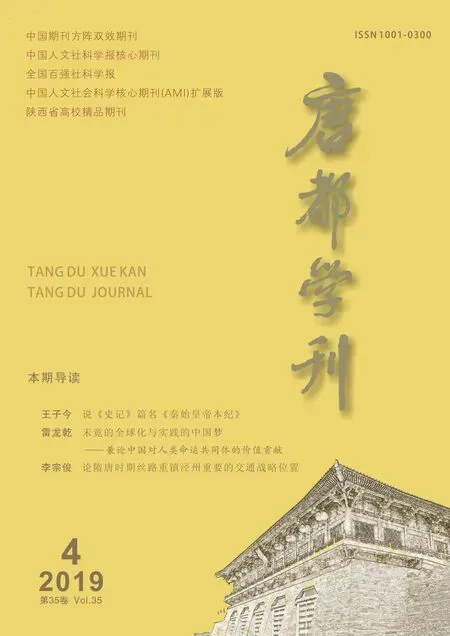唐太宗三教政策探析
李建国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武汉 430079)
一、唐太宗的儒家政策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许多新生的政权大都以武力取得。政权稳定后,统治者便思励精图治。为了王朝的兴盛,历代统治者大都选用儒生担负治国理家之任。唐朝建朔后,也借重儒生的力量。唐高祖虽然崇道,但在朝政运行方面还是以儒为重。对儒学的重视在太宗时期就愈益明显,而这也是唐太宗开创初唐盛世的关键之所在。
太宗即位后就着手设立专门的机构以备儒生讨论治国之术,史载:
太宗初践祚,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馆学生。[2]215
太宗皇帝如此行事是为了“通规正训,辅其阙如”[3]49,以听取不同的意见而能“引礼度而成典则,畅文词而咏风雅”[3]49。选贤任事,首先得听取不同的谏言,广而听取,细而审思,以为受用。贞观二年(628),太宗对侍臣又言:“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其非才,必难政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2]219而倡导儒学恰能发挥如此效用,太宗便开始颁发一系列兴儒之策。
太宗重视对儒家贤哲的礼敬和对后辈儒生的提携。史载:
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是岁大收天下儒生,赐帛给傅,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学生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2]216
于此可见太宗对后辈儒生的扶持。太宗还多次亲临国学,让祭酒、司业、博士讲论,给予不同的奖励。鉴于这样的崇儒政策,各地书生踊跃为儒,一时儒生数量大增,就连吐蕃、高昌、高丽、新罗等地的贵族都派子弟前来学儒,乃至有“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开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2]216。后又让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庙:“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王弼、杜元凯、范甯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自今有事太学,可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3]99尊崇儒家先哲也是重视儒学的反映,这也成为当时学术的一种风尚。太宗崇尚儒家伦理道德,想藉此培育有德之士来扶持自己的统治,这也便促成儒学兴盛的局面。由于儒家典籍传播久远,文字不免有窜误,贞观四年(630),太宗命颜师古于秘书省考订《五经》,史载:
因此,在电熔焊接PE管道施工中建议随机抽取5%的电熔连接件进行拉伸剥离试验,这样能有效地控制焊接质量,尽量避免虚焊的出现,从而保证管道达到设计使用寿命。
时诸儒传习师说,舛谬已久,皆共非之,异端蜂起。而师古辄引晋、宋已来本,随方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2]220
经义的厘定是为着教材的统一,这也极大地方便了取士及文化思想的一致。鉴于前朝皆有求访贤良之举,太宗也觉得“历选列辟,莫不贵此得人”[3]78,所以太宗极为重视这一选才之道,“可令天下诸州,搜扬所部,士庶之内,或识达公方,学综今古,廉洁正直;或孝悌淳笃,节义昭显;或儒术通明,学堪师范……并宜荐举……”[3]78太宗为了选取有用之才,广开进身之道,为许多饱学的儒生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同时也为朝政的治理延揽了优秀的人才。
太宗的另一个重儒之策,便是制定礼乐制度。古代就有“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传统,太宗对此也极其重视,与廷臣讨论“修文德、制礼乐”为朝之大事。对于礼乐的作用太宗也有陈述:
先王之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象天地以制法,通神明以施化,乐由内作,礼自外成,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风易俗,揖让而天下治者,其唯礼乐乎![3]70
太宗也因感于“大道”的衰弱,斯文的坠失,而深为忧心,于是“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典之废于今者,咸择善而修复;新声之乱于雅者,并随违而矫正。莫不本之人心,稽乎物理,正情性而节事宜,穷高深而归简易”[3]70。可见太宗对修制礼仪极为用心,礼制的修备也为社会的运行提供了一种规则,上行下效,社会才能有序地运转。
二、唐太宗的道教政策
太宗的道教政策承继高祖,以崇道为主。对于道教,太宗更以“尚用”的心态待之。对其所宣扬的神仙事宜,太宗则认为:“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2]196太宗时期,道教也时有发展,贞观十一年(637)“修老君庙于亳州,宣尼庙于兖州,各给二十户享祀焉”[4]48。后来太宗还颁布《令道士在僧前诏》:“老君垂范,义在清虚……况朕之本系,出于柱史。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章,阐兹元化。……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告报天下,主者施行。”[3]73这便使道教的地位大为提高。
至于太宗为何如此看重道教,寇养厚先生认为:“在李世民与其兄李建成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以王知远为首的道教徒支持李世民,以法琳为首的佛教徒支持李建成,这种情况决定了李世民在即位之初就有所偏护。”[5]其后太宗确对一些道士极为礼敬,如王志远、薛赜、成玄英。这也许只是太宗崇道的一个直接原因。对于更主要的原因,则与其出身及承统的天命性有关。贞观六年(632)时,太宗有感于门第轻重失宜,于是诏令修订《氏族志》。后修志者将山东崔姓和李氏并列,这使太宗极为反感,只因此举无法凸显李氏皇族的显贵之所在。太宗有此举动,便是想借助道教始祖李耳,重新划定士族、庶族的社会地位,以期打破固化的社会阶层。在太宗时期,魏晋以来的士族门风还有影响,他们占据社会资源,凭借门第,无所作为,这便严重阻碍了有为庶族的进身。而太宗就想以重新修订《氏族志》而打破已有的门第局面,以改良社会机制。其间要借重道教始祖,就必须得处理好与道教的关系。此外,佛教在隋朝发展迅速,极具势力,唐高祖虽有限制,其势力仍旧很大。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宗教势力,统治者不会希望它一支独大,所以太宗皇帝也想借助扶植道教来限制佛教的进一步强大。
三、唐太宗的佛教政策
太宗即位后,废止了高祖对佛教的沙汰政策。对佛教采取一些整治措施,以使其能更好地适应王朝统治的需要。太宗在位时期,对佛教有限制,但都比较理性,并依照具体需要而变化。
(一)信仰化的佛教政策
太宗在高祖皇帝起兵讨隋,建立王朔的过程中,征战各处,军功显赫。但战争发生之处必有生灵涂炭,必有军士殒命,这是无可避免的。太宗即位后,想起曾经的征战,想起战亡的手下兵将。就在战阵处广立寺庙,以为缅怀纪念,让那些游魂得以慰藉:
释教慈心,均异同于平等。……有隋失道,朕亲总元戎,致兹明罚,誓牧登,曾无宁岁。……衔须义愤,捐躯抗节,各徇所奉,咸有可嘉。……犹恐九泉之下,八难之闲,永缠冰炭。愀然疚怀,用忘兴寝,思所以树其福田,济其营魄。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陨身戎阵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侣。……称朕矜愍之意。[3]59
并先后在幽州立昭仁寺、台州立普济寺、晋州立慈云寺、汾州立弘济寺、芒山立昭觉寺、郑州立等慈寺、洺州立昭福寺。考虑到“释氏之教深尚慈仁,禁戒之科,杀害为最重,承言此理,弥增悔惧”[6]329。太宗也检讨自己“自征讨以来,手所诛翦前后之数将近一千”[6]329。为自己的行为深深忏悔,也想通过此举以解脱心中之苦。佛教一直关注人生的终极。人有前世今生,太宗就以广建佛寺、参与佛事活动来表示对亡者的缅怀,对自己的征战罪过进行忏悔。这时太宗所采取的佛教政策是基于一种内心的信仰,是想以此表示内心最大的缅怀之情。这种感受还表现在太宗为太穆皇后的追福手疏里:
圣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人之所爱者亲也,朕幼荷鞠育之恩,长蒙抚养之训,《蓼莪》之念,何日忘之?罔极之情,昊天匪报。朕每痛一月之中……欲报靡因,唯资冥助,敬以绢二百匹奉慈悲大道。傥至诚有感,冀销过去之愆,为善有因,庶获后缘之庆。[3]129
后太宗又在弘福寺施斋“追维抚育之恩,每念慈颜之远,泣血崩心……岁月不居,敬仰已晚,方恨不追,怨酷之深,百身何赎?唯以丹诚,皈依三宝,谨于宏福道场,奉施斋供,并施净财,以充檀舍。……疾证菩提,早登正觉,六道四生,并同斯愿”[3]124。在这里太宗通过施斋、手疏等佛教仪行表达对母亲的追念之情。在上面的记叙中,可以看到太宗不论在阵前立塔庙纪念阵亡的兵将,还是用佛教仪礼表达对母亲的怀念,他都把佛教当做一种精神信仰,想依靠佛教倡导的精神来抒发内心的寄怀。
(二)政治化的佛教政策
太宗通过玄武门之变而登上皇位,即位后他就终止了高祖的“废浮屠老子法”命令,从而出现一种佛道并重局面。对于太宗此时的佛道政策,顾自奋先生称:“由于贞观初年李世民有杀戮兄弟的非议,因此他‘抚民以静’的目的是注重于收取民心。”[7]在玄武门之变中,有部分佛教徒支持李建成,太宗虽有不满,但他毕竟已登上皇位,应通过更宽大的佛教政策来争取更多的支持,但这并不代表他会尊崇佛教。对于佛教的种种弊端太宗早有认知,贞观二年(628)太宗谓侍臣曰:
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唯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终日谈论苦空,未倡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帝被侯景幽通而死。……此事亦足为鉴戒。朕近所好者,唯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不可暂无耳。[2]195
所以太宗在佛教政策方面,注意与现实需要相结合。鉴于前朝的教训,太宗也注意佛教的不足之处,以图及早免除其带来的种种社会危害。太宗在位时期虽有度僧,更有限佛,但大都表现出一种理性的态度。基于佛法的教化精神,太宗也给予其一定的地位和重视,相继颁行度僧诏令。“三乘结辙,济度为先,八正归依,慈悲为主。”[3]66也因为当时经过战争后佛教的衰落,所以通过度僧以为复兴,“比因丧乱,僧徒减少,华台宝塔,窥户无人……眷言凋毁,良用怃然。其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其州有大小,地有华夷,当处所度多少,委有司量定。……务须精诚德业。”[3]66对于度僧还有记载:
昔隋委失御,天下分崩,……朕属当戟乱,躬履兵锋,亟犯风霜,宿于马上。比加药饵,犹未痊除,近日已来,方就平复,岂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徵耶。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宜度五十人。[3]104
太宗虽有度僧,也有规定。鉴于从前许多僧徒沉溺于流风余俗,而不思佛法;假托神通,谣言各处;以行道敛取不义之财。这些都违背了佛教倡导的精神,太宗为了净化佛门,制定一些律令,以为惩戒。“朕情深持护,必无宽舍,已令依附内律,参以金科,具陈条制,务使法门清整,所在官司,宜加检察。其部内有违法僧不举发者,所司录状奏闻,庶善者必采,恶者必斤。伽蓝净土,咸知法味;菩提觉路,绝诸意垢。”[3]66太宗还准许诸州寺观转经行道“神道设教,慈惠为先,元化潜通,亭育资始……敢藉圣时,介兹多祉,宜为普天亿兆,仰祈嘉佑。可于京城及天下诸州寺观,僧尼道士等七日七夜转经行道。每年正月七日,例皆准此”[3]107。太宗对佛像的制造也有限制,“佛道形象,事极尊严,伎巧之家,多有造铸。供养之人,竞来买购……买者不计因果,止求贱得;卖者本希利润,唯在价高。罪累特深,福报俱尽,违犯经教,并宜禁约。自今以后,工匠皆不得预造佛道形象卖鬻。其建成之像,亦不得销除,各令分送寺观,令寺观徒众,酬其价直。”[3]110太宗的这些举措,表明他会允许佛教的发展,但要其遵循基本的规则。这也便促使佛教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并有所改善而得到一种“常态”的发展,而不至于最后走向“楼台烟雨中”的局面。对于太宗重视佛教,寇养厚先生认为这和太宗想与天竺国保持友好来往也有关系。在唐朝之前,天竺国与中土虽有民间交流,但没有官方的文书往来。玄奘法师西行求法是他作为佛教徒的个人行为。贞观十五年(641),天竺国摩迦陀王尸罗逸多从玄奘处得知太宗的相关人事,便主动派遣使者来中土交流,太宗也派遣梁怀回访。寇养厚先生还说:“唐太宗才是中国历史上与天竺建立正式友好外交关系的第一人。”[5]此后,两国互有往来,而佛教就扮演了一个桥梁的作用,这也是太宗重视佛教的一个外在原因。
太宗对佛教时有支持,但终其一朝对佛教还是抑制居多。因佛教在前朝已经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虽有战争的影响,稍一扶植,便成力量。随着度僧人数的增多,便占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太宗就在政策上、经济上开始有所限制,如严格规定僧徒的授田,颁布僧道格来加强管理。一些朝臣也历陈佛教的弊害。傅奕在贞观六年再次上疏言:“佛法妖伪”[6]135,太宗临朝谓奕言:“‘佛道元妙,圣迹可师,卿独不悟何也?’奕对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老庄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上然之。”[8]836贞观九年(635)太宗就以“沙门道士,虧违教迹,留京师寺三所、观三所,选耆老高行以实之,余皆罢废。”[8]835但不久敕文,又规定僧尼道士依照从前的规定。可以看出太宗的佛教政策处于一种试探摸索中,忽而限制、忽而放开,总是依照需求而有所偏重。贞观八年,太宗对长孙无忌说:“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封事欲令我每日将十个大德,共达官同入,令我礼拜。观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8]835侍中魏徵就说:“佛道法本贵清净,以遏浮兢。……释慧琳非无才俊,宋文帝迎之升殿。”[8]836但颜延之就持反论云:“三台之位,岂可使刑余之人居之,今陛下纵欲崇信佛教,亦不须道人日到参议。”[8]836对于此事朝臣意见不一,观太宗所言,对佛教徒还是有所保留。另外,太宗还令僧道拜敬父母,把佛道拉入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之中,不至使其“无父无君”。太宗也通过对僧侣记诵、践行佛教遗经来考核其修成,“然僧尼出家,戒行须备。若纵情淫佚,既失如来元妙之旨,又亏国王受付之义。《遗教经》者,是佛临涅槃所说,诫劝弟子,甚为详要。……宜令所司,差书手十人,多写经本,务在试行。……其官宦五品已上,及诸州刺史,各付一卷。若见僧尼行业,与经文不同,宜公私劝勉,必使遵行。”[3]109还有后来颁布的《令道士在僧前诏》,通过政策来提升道教,压制佛教。
综上所述,在立国层面太宗重用儒生至为坚定。通过不断完善礼仪制度,广建学舍,征召儒生贤良,为后辈儒生提供更多出仕的机会。在佛道政策方面则本着“尚用”的精神,时有偏重。“在宗教问题上,他是宁信人而不信神的,但他不依好恶决取舍,而以功利断得失。”[7]太宗极为礼遇玄奘法师,是因为觉得玄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治国之才,想尽力劝说法师帮他治理国家。这就可以看出,太宗对三教的政策大都围绕他的政治统治,对于借助佛法来追念母亲以及通过建立寺塔祭奠阵亡兵将,这种因为精神上的关怀而崇奉佛教只是他宗教政策中很小的一部分。对于太宗一朝的三教地位,顾自奋先生总结道:“他始终坚持标榜皇权借重道,治国所学在于儒,归化民心必尊佛。他在动静矛盾中操纵平衡。”[7]可见,太宗对于“三教”还是依其社会情势所需各有侧重,而使“三教”在平衡发展中发挥出最大的社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