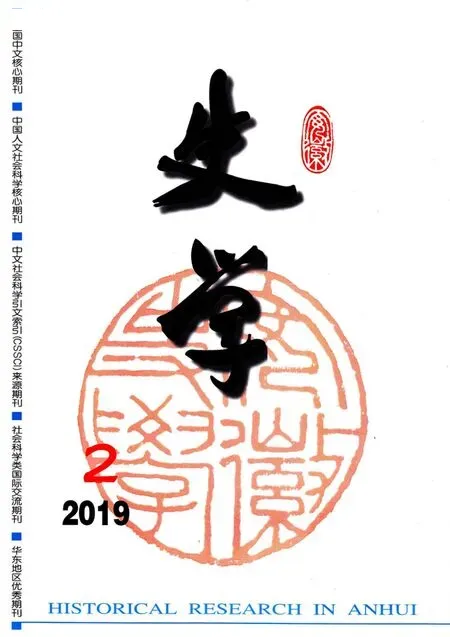严译《天演论》与叶尔恺、吴汝纶
马 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在近代中国知识界,严复是最善于炫耀学问的人,“严译名著”八种,跨越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诸多学科。现代中国人文学术的源头差不多都可以追溯到严复,但要论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毫无疑问,当属“天演”进化论。[注]“寻求富强”,就是严复译介《天演论》的主旨,也是时代对严复作为思想家、翻译家的要求,“在随着甲午战争失败而来的严重危机的气氛中,‘富强’的口号和一切有关的联想,赢得了统治阶级中大多数明智人士的默认,并且使讨论转向了新的话题。”(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这是严复转译《天演论》并获得巨大成功的时代背景。这个学说深刻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注]严译《天演论》还没有正式出版,就开始影响了“朋友圈”。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一代名流,无不受天演论之深刻影响。梁启超是读过严译《天演论》手稿的人,他曾坦率地承认:“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矣。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又思发明群义,则理奥例赜,苦不克达。近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悼天下有志之士,希得闻南海之绪论,见二君之宏著,或闻矣见矣,而莫之解莫之信,乃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见,证以实事,作《说群》十篇。”(《说群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页。),直至今日。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只是一本小册子,但其典雅的文字、明白易解的思想,使这本小书不胫而走,成为过去一百多年影响力最大的作品。这一方面是时代恩赐,是严复的机遇;另一方面与叶尔恺、吴汝纶等人密不可分。[注]注意吴汝纶与严译《天演论》关系的很多,俞政《严复著译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天根《天演论传播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动员》(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研究的最为细致;至于叶尔恺与《天演论》的关系,汤志钧先生《再论康有为与今文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一文最先提及。
一、译介《天演论》
说起梁启超的写作,人们最喜引梁氏这段话:“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注]朱维铮校注:《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其实,在转型时代,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中国知识人文字表达方式都在变化,只要关注时事,关注世界与中国关联的知识人,都不可能再像乾嘉诸老那样说话、作文,稍有情怀的知识人都在最大限度适应形势。不惟梁启超,黄遵宪、严复,以及稍后陈独秀、胡适等,都有各自不同的“尝试”。[注]胡适将自己的第一本白话诗集命名为“尝试集”,一再强调实验主义尝试的意义和价值。“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尝试集自序》,《胡适全集》卷10,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严复留学英国学海军,回国后一直在北洋水师学堂服务,由“洋文总教习”、“正教习”而“总办”、“总教习”[注]马自毅:《“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其前半生精力所在就是海军教育。如果不是甲午战争,严复必将教于斯,老于斯,以海军教育元老而留名青史。历史偶然性让严复的人生轨迹发生巨大改变。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也是严复生命历程的巨大转折。大东沟海战牺牲的将士,或为严复福州船政学堂、或英国海军皇家学院同学;或为严复的学生,来自福州船政学堂、或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因而严复对这场战争较其他中国人更加关心,更具情怀。“我近来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但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非深通其文字者,又欲知无由,所以莫复尚之也。且其学绝驯实,不可顿悟,必层累阶级,而后有以通其微。及其既通,则八面受敌,无施不可。以中国之糟粕方之,虽其间偶有所明,而散总之异、纯杂之分,真伪之判,真不可同日而语也。”读西书使严复觉得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知识人之知识结构及价值趋向:“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注]《与长子严璩第一书》,《严复全集》卷8,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37页。于是严复决意集中精力向国人介绍西学,并很快选定了《天演论》。
《天演论》原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为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严复将其简约为《天演论》,所翻译的内容也只是赫胥黎原作之“导言”和“进化论与伦理学”两个部分。
赫胥黎的思想来源为英国科学家达尔文。达尔文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生物界是几百万年发展演化的进程,并非一成不变。达尔文的名著为《物种起源》,这部书系统阐释了进化论的基本观点,强调世界上的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始终处于进化过程中;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连续的,不间断的;生物的进化、变化,所遵循的原则是自然选择的过程,普遍存在的变异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但其基本原则是优胜劣败。这就是严复归纳的道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二、叶尔恺与“味经本”
据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记载:“乙未(1895年),府君(严复)四十三岁。自去年夏间中东构衅,海军既衄,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次失守。至是年,和议始成,府君大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先从事于赫胥黎(T·Huxley)之《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未数月而脱稿。桐城吴丈汝纶,时为保定莲池书院掌教,过津来访,读而奇之。为序,劝付剞劂行世。”[注]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5页。严璩以为《天演论》翻译始自马关“和议始成”,即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之后。
对于严璩的说法,王蘧常并不认同。他将《天演论》翻译系在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二年丙午,“夏初,译英人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据《天演论》自序。案《严谱》四十三岁,误也),以课学子(据《天演论》原本译例言)。”[注]王蘧常:《民国严几道先生复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页。严复《天演论自序》这样说:“赫胥黎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为迻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注]《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1321页。王蘧常的直接依据就是这句“夏日如年,聊为迻译”,应该说是最直接的证据。
王栻主持编辑《严复集》时“曾看到封面题为光绪乙未年(1895年)三月非正式出版的陕西味经售书处的重刊本”,他们断定“可证此书至迟于1895年脱稿。以后译者屡加修订,才于1898年正式出版。”[注]《严复集》第1548页脚注。
陕西味经售书处有一个“乙未年版”是事实,但很难说这个版本就是什么“重刊本”,时间似乎也不对。“味经本”下卷“论三”有一段严复写的按语:“复案:释迦生卒年月,至今迄无定说。或谓生于周昭二十四年甲寅,终于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此摩腾对汉明帝说也。隋翻经学士费长房撰《开皇三宝录》,则云佛以周庄王十年……生,至匡王五年癸丑示灭,……又或云夏桀时、商武乙时、周平王时,蹖驳牴牾,莫衷一是。至贞观三年,勅刑部刘德威等与法琳详核真妄,乃定佛周昭丙寅岁生,周穆壬申示灭。然周昭在位仅十九年,无所谓二十四年,亦无丙寅。意是甲寅之误,乃周昭十四年也。去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共二千八百六十四年,先耶稣生九百六十八年矣。”[注]《天演论》味经本,《严复全集》卷1,第188页。严复在这里明确记载的时间节点为“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也就是1896年。据此,有研究者质疑,如果“味经本”系“光绪乙未春三月”“重刊”,怎么会有光绪二十二年丙申的记载呢?怎么会在严复未译出以前就已重印了呢?“事实上,光绪乙未三月,《天演论》还没有译出。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天演论》手稿,曾用各色笔多次修改过,并有许多题注。除自序注明‘丙申重九’外,其他有的注‘丁酉四月删节’,有的注‘丁酉六月初六删节’。丙申(1896年)、丁酉(1897年)还对《天演论》进行修改,怎么会在此以前就已‘重刊’?”[注]汤志钧:《再论康有为与今文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矛盾的记录让一些研究者对味经本《天演论》充满怀疑。其实,如果放在甲午后读书界知识饥渴背景中进行讨论,就可以明了味经本并非不可能。
我们知道,严复从开始到完成《天演论》定稿用了好几年时间,严璩说严复是受到《马关条约》刺激而发奋翻译这本书,不数月而完成初稿,之后在漫长的修改时间里,接触过、获得过此书译稿的并不少。在那知识饥渴、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极为淡薄时,好事的书商不论是为了经济利益,还是为了情怀,将正在修改中的《天演论》印刷出版,有什么不可能呢?也由于这样一层原因,陕西味经售书处的《天演论》就略显粗糙。这是研究《天演论》诸版本时应该注意的。
味经版《天演论》出版单位为“味经售书处”,而味经售书处隶属于“味经书院”,有的史料写作“味经书院刊书处”。“味经”的意思有吟诵、品味经典的含义。味经书院创办于1873年,是民间出资,官方认可的书院组织,与关中书院、宏道书院一样,其生源来自陕甘两省,其教学目标就是科举考试,教学内容就是儒家四书及其标准解释,以及扩充阅读的资料,特别是邀请名师讲述考试技巧。对书院水平的衡量,都是硬指标,就是科举考试的录取率。所以,过去很多人说,书院就是中国的教育机构,其实是不对的,书院是科举考试集中复习的地方,封闭式管理,名师云集,押题、解题,也各有办法。好的书院当然也生产出许多新思想、新学术,但这些思想学术主要的不是为了向社会提供,改变社会,而是要指导学生在规范化考试中不出格而又能出彩,赢得判题老师的认同、赏识,进而鲤鱼跳龙门,金榜题名。
1887年,味经书院山长柏景伟调任关中书院山长,刘古愚接任味经书院山长。刘古愚是关中学界泰斗,具有强烈的经世、救亡情怀。甲午战后,与京津沪、湖广维新同志互通消息,同气相求,味经书院一时间成为陕甘地区维新运动的中心。
味经书院在柏景伟时代原本设有“求友斋”,筹集有大量资金,用于刊刻有意义的书籍。刘古愚接收书院管理权前后,又与柏景伟一起筹划成立书院所属“售书局”。“由于陕西本地缺乏高质量的校勘、刻印书籍的机构,当时人们所读之书都是从四川、湖广等地购买而来,又有长途贩运,价格昂贵,一般人根本买不起。市场所见书籍大多是民间的私刻,有些书甚至连经文都删节不全,字句的讹误随处可见”;“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民间缺书的局面,在当时陕西学政柯逢时的支持下,味经书院于1891年8月成立了刊书处,这是求友斋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刊书处的初期资金一共一万两,陕西官方拨款一千两以示支持。柯逢时自己捐银一千两,从泾阳县绅商募集五千两,再加上其他人的捐集,共一万两。”[注]温芽清:《陕甘味经书院考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9期。雄厚的资本,灵活的运作,让味经书院有可能比较早地拿到好的稿子。
中日甲午战后的知识饥渴让《天演论》不胫而走,也就成了各地书商好意盗版的对象。研究那一时期流行作品不同版本,大概都有此种情形,这些不同版本并不单纯为了牟利,也有新知识传播的主观诉求。
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关于《天演论》的文字,可以发现严译《天演论》那时并没有定本,一方面严复自己还在斟酌修改,另一方面他的那些朋友即早期读者梁启超、康有为、卢靖、吴汝纶、夏曾佑、吕增祥、熊季廉、孙宝瑄等也通过各种方式反馈建议,这也是严译《天演论》早期版本格外复杂的一个原因。[注]汤志钧先生在《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4页)中也这样说过:“查《天演论》公开发表虽在1897年,见《国闻汇编》第二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正式出版则在1898年4月。但他在1895年所写的文章中就援引了‘天演说’,讲‘运会’,讲‘天择’、‘物竞’,观《原强》可知;他在翻译时,且曾出示友人,梁启超《说群自序》:‘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此文载《时务报》第二十六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出版,也早于《国闻汇编》,可知早经译出。”
陕西学政叶尔恺在致汪康年信中说:“弟前发味经刻《天演论》一书,所校各节,极可发噱。”[注]《汪康年师友书札》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6页。函又云:“刘古愚孝廉其人尚气节,颇有伉直之慨,惟服膺康学甚至,是其无识之处。”汤志钧先生据此分析,“信中明确记载《天演论》是叶尔恺到达陕西后交发味经印布的。此信末署‘十一月二十一日’,汪康年注‘己新正廿四收’。己是己亥,则信发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时在政变后不久,故信中诋刘古愚服膺康学为无识。由此可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前味经本尚在排刻中。案叶尔恺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接任陕西学政的,‘九月廿八日自京动身,初四日抵太原,初七接篆’。由此推断,他‘发味经刻《天演论》’,自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以后。所以,味经本应刻于光绪二十三年底或二十四年初,印出则在光绪二十四年,不是乙未。”[注]汤志钧:《再论康有为与今文经学》,《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自汤先生之论出,再也没有人敢肯定味经本刻于乙未了。
汤先生的讨论有理有据,本不宜继续讨论,我只是想提出另一种可能是,叶尔恺光绪二十三年秋从北京去太原赴任时,确实带了一本正式出版的《天演论》,就任后也确实交给了刘古愚主持的味经书院售书处翻印。叶尔恺之所以交印正本《天演论》,是因为他看到味经书院售书处的刻本极为糟糕。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在没有更多的直接证据呈现时,我比较倾向于相信,叶尔恺之前味经书院有一个《天演论》的本子,否则经叶尔恺如此认真校对,假如真有一个新刻本的话,为什么会将日期写成“乙未春三月”呢?这样的错误不是一般的小错,叶尔恺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其实,如果仔细重读叶尔恺这封信,叶说严译《天演论》味经本似乎并不是其交给刘古愚、出书处刊刻的,而是指刘古愚他们在叶来之前刻印的。叶尔恺的这封信主旨是说味经书院在他来之前很不堪,而且由于政变已经发生,官场开始清理康梁余毒,因而这封信就是渲染康梁的问题,渲染追随康梁的刘古愚如何不行,请看原文:“……时事奇幻,不可思议,诚如来书所云,新进少年举事率妄,遂致斯祸。康梁诸人本无阅历无见识,视天下事太易,加以学术乖僻,欲其不偾事也得乎?可痛者被累之人过多,无识之徒,反以新学为诟病,诸君之贻害其有穷耶?此间经弟提倡,风气颇开。其初将西学西教混而为一,已费剖白。近又以康学即西学,尤属可叹。康何幸而蒙西学之名哉?刘古愚孝廉其人尚气节,颇有伉直之慨,惟服膺康学甚至,是其无识之处。弟去年到后,即与之再三辩论,并捡朱蓉生集内与康数次辩驳书札示之,渠终右康而左朱。又此间最谫陋,通省无一人知小学门径者。味经书院所刻书可为捧腹者甚多,或字本古体必改从俗体,所刻《史书校勘记》援引《康熙字典》,弇陋至此。弟谓小学虽非今之所急,而中国制字源流,亦当略知一二。刘自安固陋,不以为然。弟以格致之学现虽无器具,亦当先涉其书,明其理。刘以为空谈格致,不如八股,其教人也,以《通鉴》为宗主,兼及西政各书,如是而已。夫言中学而不知小学,言西学而不知格致,则所学亦有限。又昧于知人,往往为人所愚,特其热肠处尚可取耳。日前此间大位自京中致书午帅,于刘竭力丑诋,目为康党。现刘已辞退,明岁味经延请何人,尚未定也。弟前发味经刻《天演论》一书,所校各节,极可发噱……句法之古奥近子者必以为有脱讹字,或径增改原句读,以求文理之平适,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所以味经每刻一书,其初校之笑话,必须逐一签出,甚是淘神,而刘及院中诸生或竟大惑不解,反不能无疑也。总之,此间人士除八股外,直不知有他书。”[注]《叶尔恺致汪康年函之十七》,《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476页。仔细理解这段文字,叶尔恺明显在批评味经本《天演论》编辑、校对不严谨,问题多多。这不应该是叶到任后交给味经书院的刻印,而应该是其到任前味经书院刻印的,叶尔恺举这个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之前的味经书院以及刘古愚不怎么行。当然,这样理解的一个关键点是如何理解信中“弟前发味经刻《天演论》一书”的“发”。这个“发”,究竟是发给味经书院一个从外地带来的《天演论》,还是将味经书院的《天演论》发给了汪康年呢?
至此,1895、1896、1897、1898,即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几个年份的证据都有。如此矛盾的记录,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如果从历史的观点看,从这个译本的特殊性看,单纯的文字记录可能还不足以理解其复杂性。换言之,如果尝试着从一个历史过程看,将历史与历史逻辑结合起来看,似乎比较容易理解这些矛盾的记录。
三、吴汝纶与定本
严复的英文水平在那时是第一流的,对西方的理解也是最深刻、准确的。但其早岁留学西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文字,应该说并不是那么特别优秀。这种情形在近代中国转型期并不少见。因而,严译《天演论》如果不能得到吴汝纶这样的文学大家指点,甚至修正,要想获得知识界认同,并不容易。
在翻译态度上,严复给出一个很高的标准:“信达雅”,因此他并不像许多译者那样只是简单地将英文对译成中文,而是反复斟酌,寻找最佳、更好,“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严复举例说,“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严复还举例说明他翻译《天演论》的难度与进度,“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卮言’,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父(汝纶)见之,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自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玄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以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注]《译例言》,《严复全集》卷1,第79页。
从这段话可以感到,严复翻译《天演论》确实下了大功夫,同时也并不是一蹴而就,一气呵成。大致情形应该是,在1895年春秋之交,《马关条约》签字前后,严复开始翻译这本书,由于充满义愤、激情,严复的效率很高,“未数月而脱稿”。稍后,莲池书院掌教吴汝纶过津来访,读而奇之,讨论了体例、文字,提出一些修改建议。与此同时,严复翻译出来的原稿也在朋友圈中流传,夏曾佑看过这部稿子,也提出过修改建议。梁启超此时也属于严复的朋友圈,不仅看过严复的译稿,而且也提出过修订意见。
吴汝纶、夏曾佑、梁启超等人看过严复的《天演论》译稿,一致认为意义重大,也分别给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而严复自己在初稿完成后也没有万事大吉,而是极为精心不时修改,这从现存《天演论》手稿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严复的字斟句酌,确实像他说的那样“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俞政先生通过对《天演论》底本、修改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今本”三个本子的比对研究,就发现严复《天演论》译稿至少有三次大的修改,而这三次大的修改基本上都与吴汝纶有关,或者就是按照吴汝纶的意见进行调整。[注]俞政:《严复著译研究》,第15页。
严复翻译《天演论》从开始至定稿是一个漫长过程,按照目前的研究,不少于三年。而在这三年中,严译《天演论》的消息随着吴汝纶、夏曾佑、梁启超等人因各种原因看过译稿的人越来越多,未定稿的译本也就在外面开始流传,有的甚至也被刻印出来。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1897年8月23日),严复致信五弟说:“《天演论》索观者有数处,副本被人久留不还,其原稿经吴莲池圈点者正取修饰增案,事毕拟即付梓。颇有人说其书于新学有大益也。中国甚属岌岌,过此何必兵战,只甲午兵费一端已足蒇事。洋债皆金,而金日贵无贱时,二万万即七万万可也。哀此穷黎,何以堪此!前此尚谓有能者出,庶几有鸠,今则谓虽有圣者,无救灭亡也。中国不治之疾尚是在学问上,民智既下,所以不足自立于物竞之际。”[注]《与五弟书》,《严复集》,第733页。这是严译《天演论》版本复杂的根本原因。基于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粗略介绍目前所知且所存各种版本的大致情况。
值得庆幸的是细心的严复留下了一个手稿本。将来有机会运用大数据的方法,一定能搞清楚各个版本之间的细微差别。这份手稿现在存放于国家博物馆,曾收入《严复集》以及后来的《严复合集》《严复全集》等不同汇编本中。据介绍,稿本分上下两卷,合订一册,毛笔草书,“手稿用各色笔多次修改,除自序注明‘丙申重九’外,其他有的注‘丁酉四月删节’,有的注‘丁酉六月初六日删改’”;“把它与通行本相较,可以看到严复思想的变化及《天演论》成书过程中的一些情况。”[注]《天演论》手稿本题注,《严复集》,第1410页。
手稿本之外,值得注意的为《国闻汇编》第二、四、五、六期连载的节略本,名《天演论悬疏》,又称《赫胥黎治功天演论》。[注]《国闻报馆章程》,《严复集》,第455页。
严译《天演论》从严复初译脱稿,至正式出版,一直在朋友圈传阅,吴汝纶、夏曾佑、梁启超等分别提出修改意见,严复也充分汲取这些意见进行修改。就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最后定稿的稿子可能有盗印,至少有传抄。读《忘山庐日记》,1897年闰十二月初二日,孙宝瑄通过《蒙学馆》叶浩吾“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归,即严复所译者。”[注]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孙宝瑄的这个版本据研究并不是《国闻汇编》登载的本子,因为孙的日记显示他差不多两个月之后,即1898年闰二月初四方才购得《国闻汇编》。[注]王天根:《天演论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动员》,第49页。
据严璩《严复年谱》,乙未(1895年),严译《天演论》未数月而脱稿,“桐城吴丈汝纶,时为保定莲池书院掌教,过津来访,读而奇之。为序,劝付剞劂行世。”[注]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1548页。由此可知,吴汝纶是最早一批看过严译手稿的人,一方面答应为之作序,另一方面敦促尽早问世。严复与吴汝纶之间为此书往返书信多封,吴汝纶之子吴闿生在编辑乃父日记时有摘录。其一谓:“男闿生谨案:先公与严又陵书,曰尊译《天演论》,名理络绎,笔势足穿九曲,而妙有抽刀断水之致,此海内奇作也。脱稿在迩,先睹为快。”这应该是译稿初稿尚未全部完工时的书信,吴汝纶看到过一部分,否则不会有如此评论。
接着又有致严复书信说:“尊译《天演论》计已脱稿,所示外国格致家谓顺乎天演则郅治终成,赫胥黎又谓不讲治功则人道不立,此其资益于自强之治者诚深诚远。”由此,“计已脱稿”,似乎吴汝纶还没有看到全部。又一封:“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自录副本,秘之枕中,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闳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钦佩何极!抑执事之译此书,盖伤吾土之不竞,惧炎黄数千年之种族将遂无以自存而惕惕焉,欲进之以人治也。本执事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注]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12页。吴汝纶看到了全稿,给予很高评价,并“经自录副本”。这个副本,就是《吴京卿节本天演论》,1903年闰五月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注]王天根:《〈天演论〉传播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动员》,第47页。其基本内容,就是吴汝纶在审读时摘抄在日记中那些文字。[注]详见《桐城吴先生日记》,第475—512页。
鉴于吴汝纶在那时代的巨大影响力,这个节录本不胫而走,风靡一时,甚至成为一些学堂的读本。据胡适回忆,他那时正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澄衷的教员之中,我受杨千里先生(天冀)的影响最大。我在东三斋时,他是西二斋的国文教员,人都说他思想很新。我去看他,他很鼓励我,在我的作文稿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后来我在东二斋和西一斋,他都做过国文教员。有一次,他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的很。他出的作文题目也很特别,有一次的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意’(我的一篇,前几年澄衷校长曹锡爵先生和现在的校长葛祖兰先生曾在旧课卷内寻出,至今还保存在校内)。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那个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术语,渐渐成了一般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我的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有一天的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作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1910年)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注]《四十自述》,《胡适文集》卷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从这个故事,可以直观感受到吴汝纶节本《天演论》的影响力。
还有一个“慎始基刻本”曾一度被认为是最早的刊本。[注]殷陆君:《严复〈天演论〉的最早刻本》,《中国哲学》第8辑,三联书店1982年。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这个本子。封面标明“沔阳庐氏慎始基斋刊行”,版心有“慎始基斋丛书”字样,卷末有“沔阳庐弼校字”几个字。庐弼,也作卢弼(1876—1967年),字慎之,号慎园,湖北沔阳(今仙桃)人,早年肄业湖北经心、两湖书院,追随杨守敬、邹代钧读书,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归国后曾任国务院秘书等,与傅增湘同在北洋任职,对《三国志》有很深的研究。卢弼之兄卢靖(1856—1948年),字勉之,号木斋,晚号知业老人,二十九岁中举,历任赞皇、南宫、定兴、丰润等县知县,后提调多伦诺尔厅同知、保定大学堂督学、北洋武备学堂算学总教习等。大约就在北洋武备学堂时,与水师学堂教习严复成为朋友,来往颇多。所以当《天演论》译稿完成后,卢靖近水楼台先得月,即请还在湖北沔阳书院读书的弟弟卢弼刻印。也因为与严复的特殊关系,所以这个刻本又被说成是经严复“亲校”,因而后来也被视为《天演论》最早最完善的版本。
其实,经研究者复查,情况并非如此。南开图书馆收藏的“慎始基斋刻本”并无吴汝纶的序言,“导言”仍然刻作“悬疏”,但在“悬疏”右侧并排,有朱笔补写的“导言”字样,各篇的篇首也均以朱笔写了后来严复采用的吴汝纶题的篇名。书中另纸添加译例言,用黑色墨笔加句读。全书其他部分皆红色笔迹,有句读。译例言后注有:“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四月二十二日严复识于天津尊疑学塾”。《天演论》下论三“教源篇”按语有“今年太岁在丁酉……”。据此,研究者判断南开藏本基于1897年修订手稿本。又由于南开藏本卷末有朱笔“光绪戊戌四月廿日校讫”,又因为朱笔补写了严复采用吴汝纶的篇目命名,“这就清楚地显示:南开藏本当在1898年(戊戌)2月之前,在严复采纳了夏曾佑的第一次意见修改《天演论》篇目之后。再查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国闻汇编》第二册刊载的《天演论悬疏》,译文与南开藏版一致。”[注]王天根:《〈天演论〉传播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动员》,第53页。
光绪二十四年4月天津“侯官嗜奇精舍”据慎始基斋版石印《天演论》,国家图书馆藏有“光绪戊戌十有一月侯官嗜奇精舍弟二次石印本”,扉页篆书“赫胥黎天演论”。这个版本与慎始基斋本相同,“但在‘译例言’末段中,删去了‘新会梁任公’五个字。这是因为戊戌政变已经发生,梁启超出逃日本,为避免政治迫害,不得不这样做。”[注]俞政:《严复著译研究》,第19页。嗜奇精舍本《天演论》,据说是国内印刷业第一次采用石印技术,校对精良,因而被学界、藏家推崇为《天演论》最好的版本,不时出现在拍卖市场。2014年北京中汉春季拍卖会图录编号891就是“光绪戊戌(1898年)侯官嗜奇精舍石印天演论”,估价一千元人民币,实际成交价为两千三百元,足见嗜奇精舍本确实受到藏家追捧。
此外,比较知名的《天演论》版本还有光绪二十七年上海富文书局石印本。卷末署有“后学庐江吴保初,门人南昌熊师复覆校上石”。与其他版本不同的是,富文书局将自序放在卷首,而其他版本均将吴汝纶的序言放在卷首。或以为这是目前所见《天演论》在商务印书馆1930年推出“严译名著”八种定本前最好的本子,字体工整清晰,布局合理,因而后来的许多书商差不多都以此本为底本翻刻翻印。
翻译《天演论》是严复给中国的巨大贡献,这件事情用了他几年精力,当然也给他赢来了巨大声誉,严复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主要的应该围绕着《天演论》的翻译展开。当然,在注意严复个人贡献的同时,还应该注意他的时代、他的师友,尤其应该注意桐城派大家吴汝纶。没有吴汝纶,严复肯定依然会因《天演论》而成名,但《天演论》的面貌肯定与现在的不一样。再者,因《天演论》和吴汝纶,严复与更多的皖籍学者建立了密切联系,这对于他后来的事业影响极大,比如严复受邀主持安徽高等学堂。又比如严复受命整顿北京大学,他不仅用皖籍学者充当主力,而且事实上让北大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成为皖籍学人,尤其是桐城派的重镇,进而在蔡元培掌教北大后,所进行的人事改革,如果仔细追究的话,都是因为严复和他所钟爱的桐城文学、桐城派。这是后话,就不再展开来。
——吴汝纶辞官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