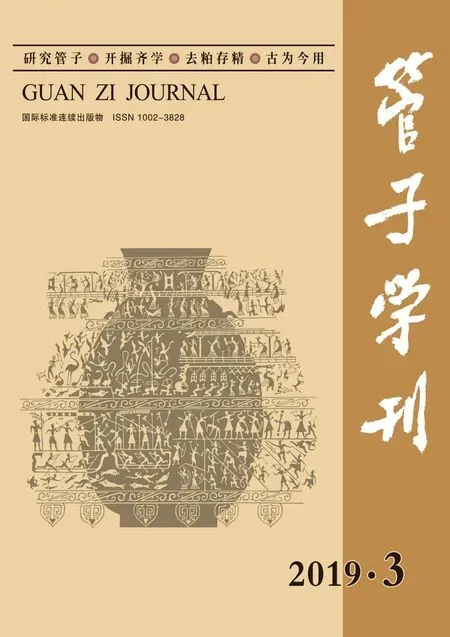《列子·黄帝》中的三种得道类型
李秋菊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100872)
《列子》一书自唐宋以来就陷入了真伪问题的泥潭之中。后世学者在柳宗元提出的怀疑基础上继续扩展,甚至得出《列子》完全是伪书的阶段结论,并且这一派在历史上一度占据主导地位(1)如高似孙《子略》、姚鼐《跋列子》、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皆收入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后引此书,不再一一出注,仅标注页码)附录三《辩伪文字辑略》),其中马叙伦著有《列子伪书考》,集伪书说之大成,详列二十余条证据以 证《列子》为伪书。,晚近则出现一批学者为《列子》平反鸣冤(2)许抗生:《列子考辨》,《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胡家聪:《从刘向的叙录看〈列子〉并非伪书》,《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1995年;陈广忠:《〈列子〉非伪书考》,《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马达:《列子真伪考辨》,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双方虽都言之凿凿,却都不乏推测之辞,因此双方都无法完全说服对方。不过即使如此,历代肯定《列子》一书的思想价值的也不乏其人,如柳宗元认为《列子》“尤质厚……好文者可废耶?”(3)杨伯峻:《列子集释》,第287页。可能受真伪问题的影响,《列子》一书一直不受重视,对其篇章、思想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我们认为《列子》思想极为丰富,学术价值也极高,如果因为真伪问题而弃之不顾,那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不如暂且搁置争议,先就其思想内涵本身做出充分讨论。鉴于《列子》一书在后世的巨大影响,即便我们暂时不管《列子》的成书过程和思想来源,《列子》作为后世道家道教的思想源头,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道家道教思想中,怎样的人、通过怎样的方式修炼成道,是非常重要的话题。而《列子》的《黄帝》正以修道工夫作为主题。《黄帝》篇由21章组成,其中20章都是涉及修道工夫的寓言。可以说《黄帝》是《列子》一书讨论修养得道问题最多的篇章,集中地体现出《列子》对于修道工夫的态度和看法,反映着《列子》的精神境界、理想人格、人生价值。此篇本应得到充分重视,但可能受到真伪问题的影响,过去学界对于《黄帝》篇及其修道工夫的研究,大多只是提及,很少能够看到专题的考察,而且很多还是拘泥于真伪问题。如肖登福的《列子探微》(4)见《列子的人生观》,原刊于《鹅湖》,第7卷11期,1982年5月,后收入肖登福:《列子探微》,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121页。一书在讨论《列子》的人生观问题时,从内情涵养的角度总结了《列子》中一些具体的修养方法,其中一部分涉及《黄帝》的思想。严灵峰在《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一书中有《辩诬》一章,专门对《黄帝》与《庄子》中的重出部分进行比对,认为是《庄子》因袭《黄帝》之说(5)严灵峰:《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第68-86页。。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一书的附录中,有《〈黄帝篇〉的内涵庄子学据以为思想资源》一文,将《黄帝》中的寓言按照主旨划分成六组,并分别与《庄子》重出的段落进行简单比较,最后得出是《庄子》收入了《黄帝》的内容、《黄帝》不伪的结论(6)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346页。。许抗生的《当代新道家》有《列子学派》一节,论及《列子》中心思想时,也涉及了《黄帝》提出的理想境界,并认为《黄帝》的人生境界开启了《庄子》思想(7)许抗生:《当代新道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6-71页。。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成果还是围绕辩伪居多,或是因为研究整本书的需要而旁及《黄帝》,对《黄帝》篇的关注严重不足。如上所言,本文不在文本问题上多作纠缠,而是通过《黄帝》篇的研究,一窥《列子》关于修道问题的看法。
《黄帝》篇以懂得养生治物之道的黄帝寓言开篇,然后描写了藐姑射之山的神人,树立起理想境界的典范(8)谭家健:《〈列子〉的理想世界》,《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但这些人物要么是传说中的帝王,要么是常人无法到达的仙境中的神人,虽然境界高超、功能神妙,却都是远离平常人日常生活的,他们得道对世俗中的普通人物是否具有借鉴意义?《黄帝》篇接下来便以大量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的寓言回答了这一点。此文将得道者划分成了三种类型:暂时性的得道者、先天的得道者和后天修养的得道者,通过这种划分,《黄帝》篇对于修养问题表明了自己鲜明的态度,突出了一个重点,那就是即使境界不高的普通人,通过适当的修养同样可以得道。
一、“得全于天”与“得全于酒”
《黄帝》开篇以黄帝、华胥之民、至人的得道者形象示人,直接展现出对得道的追求。不过这些得道者要么是传说中的帝王,要么远离世俗之地,似乎都离世俗中的普通人有一定距离。但接下来《黄帝》就以大量生活中的普通人的寓言来表明它对现实中的人,尤其是境界本不高的普通人之得道问题的关注。除了选择生活中常见的普通人为寓言主角外,《黄帝》通过区分得道类型,表明常人也可能最终得道,并表现出非常人的状态。《黄帝》首先区分的是两个大类:“神合于道”的“得全于天”者,是真得道者的典范;以及没有获得境界的实质性提升的“得全于酒”者。“得全于酒”者是“虚假”得道者,却为人们留下了一种可能,就是凭借一些后天的手段确实可能引人进入得道状态。
具体的区分见于“列子问关尹”段:
夫醉者之坠于车也,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坠亦弗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是故遌物而不慑。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列子·黄帝》)
醉者的形体构造与常人无异,所以他能坠车不死的根源必不在此。范致虚认为,应当在于人本身对乘与坠的区分:“人与接为构,则执物以为有,所见者诚车矣;认我以为实,所知者诚坠矣。知见立而乘坠分,讵能无伤乎?”(9)高守元:《冲虚至德真经四解》,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68-69页醉者之所以能坠车不死,是因为他在当时进入了一种不知不分、精神纯全的状态中,这是一种得道的状态。但向秀随之指出,“醉者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无心也”,是说醉者虽然确实处于这种状态中,但却不是自然而然就达到的。卢重玄也认为“醉人者,神非合于道也,但为酒所全者,忧惧不入于天府,死生不伤其形神”(10)杨伯峻:《列子集释》,第51页。,就是说醉者的精神并没有合于道,是酒使他精神纯全,因此恐惧不能扰乱他的内心,死生不能伤害他的形体。虽然“酒”直接将醉者带入了得道的状态中,但由于醉者本身并未得道,“酒”只是暂时遮掩掉了他本来的境界,而没有真实地提高他的境界,因此这种状态只是偶然的、暂时的,一旦所倚重的“酒”的作用消失,就又呈现出他本然的境界。所以“得全于酒”即使在当时确实处于一种得道的状态中,却并非真正的得道者。
除“得全于酒”之外,《黄帝》还展示了另一种类型,就是“得全于天”。与“得全于酒”者相对,向秀认为“得全于天”的至人“自然无心,委顺至理者也”,由于精神境界极高,所以自然就能无心、无知,一举一动无不顺应至理。他的精神完全与道相合,是超越于万物之上的;又已然打破了物我、主客的对立,与万物相与为一。虽然至人还有物的形体,却因精神与道相合,而能“潜行不空,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得全于天”者才是《黄帝》所追求的真正的得道者。
总结来看,《黄帝》划分出来的两种类型存在以下不同:首先,二者在神异程度上就存在较大差异:“得全于酒”者只能坠车不死,“得全于天”者则能完全不受水火之害。其次,虽然二者都确实表现出得道状态,但“得全于酒”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得道者,其状态是暂时的、不可重复的;而“得全于天”者则气性纯和、内合于道,是真正的得道者,无论在何时、何处,都不会为外物所伤。最后,二者并非都直接与天相通:“得全于酒”者是“酒”暂时的充当了中间环节,才勉强与天相通,得到保全;“得全于天”者则已经合于道,是直接与天相通,直接得到天的保全。
紧接着,《黄帝》又以商丘开的例子来强化这两种划分。商丘开不仅不怀疑两个投宿者的言论和子华之徒的戏弄之辞,还唯恐自己“诚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意外的是他投高台、入水火竟然毫发无损。和醉者一样,他能在危难中全身而退,也并不是因为形体上有特异之处,而是因为笃定但却盲目的“诚”,从而内心极度专一,即使面临悬崖烈火,也根本不会有忧虑和恐惧。正是暂时的进入了这种状态,才得以在水火中得到保全。商丘开展现出来的事迹是神奇的,但文章评价他的“诚”为“信伪物”,就是认为这种盲目的诚并不是引人真正入道的途径,却起到了与酒同样的作用,在其人精神境界并不高的情况下,直接将人带入了不知不分的境界之中。但由于这种“诚”不能在实质上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所以商丘开这种状态也只是暂时的,一旦他清醒过来,立刻就被打回原形。不过文章并没有完全否定“诚”,只是指出所信为“伪物”是不能得道的;而如果能够对道抱以极度的诚,就能够“动天地、感鬼神,横六合而无逆者,岂但覆危险,入水火而已哉”。
《黄帝》篇已经意识到,即使在当时确实表现出得道状态,也并不一定就是理想中的得道者,于是以精神境界是否真正达道为标准,将表现出得道状态的人区分为两种类型:以至人为代表的“得全于天”者;以醉者和商丘开为代表的“得全于酒”者。前者精神已然与道相合,表现出神异事迹是自然而然的,是真正的得道者;后者是凭借其他手段,才偶然、勉强的进入了得道状态,是“虚假”的得道者。通过对二者的划分与对比,一方面确立起了真正的得道典范,另一方面也借“得全于酒”者的存在说明即使境界本不高,也有通天的可能。只不过这里的“酒”与盲目的“诚”看似为得道提供了一条捷径,但实际上并不能真实地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所以在《黄帝》看来并不是可靠的得道途径。那么,什么才是可靠的途径呢,这正是下文要展开的内容。
二、“无道”与“有道”
《黄帝》在以上的区分中,“得全于酒”者依靠“酒”暂时进入得道状态是暂时的,那是否有可靠的途径能够真正引人通道呢?《黄帝》以“有道”“无道”之分表明,在真得道者中除了先天得道者之外,还存在一种通过后天修养最终得道的类型。这种后天修养得道的类型就是这种途径可靠、且存在的证明。
涉及“有道”“无道”问答的章节有三:
范氏之党以为有道,乃共谢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诞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聋我也,子其盲我也。敢问其道。” 商丘开曰:“吾亡道。虽吾之心,亦不知所以。虽然,有一于此,试与子言之。”(《列子·黄帝》)
孔子从而问之,曰:“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鼋鼍鱼鳖所不能游,向吾见子道之。请问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赍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同上)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若橜株驹;吾执臂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同上)
旁人见证了以上三人的神奇事迹之后,继续提出追问时,却得到他们或“有道”,或“无道”的回答。如果“有道”“无道”是对得道与否的回答,蹈水者与承蜩老者明显就是“得全于天”的真得道者,蹈水者却回答“无道”是否与前文相抵牾?即使不论以上三者究竟是否属于真得道者,但在他们呈现绝技的当时所达到的都是一种不知不分的、无我的状态,所以三人的回答彼此之间似乎相互矛盾。不过仔细揣摩之后会发现,产生这些疑问的根源在“有道”“无道”的“道”究竟指什么。本文认为,这里的“道”并不是指道家的最高概念,而是指具体的“术”,即方法、手段。
首先,“道”本身除了作为道家的最高概念之外,还有术、技艺的含义和用例。《说文》指出“道,所行道也”,许慎认为“道”本来就是指人走的路。《经义述闻·周易》“复自道”王引之按:“道者,路也。”(11)王引之:《经义述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礼记·缁衣》“是民之道也”孔颖达疏:“道,谓道路”等等,诸多例子皆说明“道”本义即为道路。而人们所走的路,实际也就是达到目的的途径和方法,这样看来,“道”本身便具有实践或者实践工具的意味(12)李壮鹰:《谈谈〈庄子〉的技进乎道》,《学术月刊》2003年第3期。。不仅如此,还有不少直接将之引申为方法、途径,并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用例,如: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司乐》“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为“道,多才艺者”(13)孙诒让:《周礼正义·春官宗伯·大司乐》,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20页。。《国语·吴语》“道将不行”韦昭注“道,术也”(14)左丘明:《国语集解·吴语》,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58页。等等。既然道本身便具有途径的意味,并且以“道”称技、术在早期文献也是广泛存在的,那么在这里以“道”指代具体的方法、手段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从询问者的问题来看,这些问题都是“惊叹 + 做此事有道/无道”的模式。范氏之党在忏悔、奉承一通之后直接提出,敢问是怎样做到入水火不伤的。吕梁上,孔子在一番惊叹之后,直接询问蹈水有什么方法。树林中,孔子也是对老者承蜩技术表现出兴趣,并且好奇是如何做到这么巧妙的。这些都是在见识了神奇事迹之后提出的疑问,针对的是如何能做到,是要求告知具体方式的问题。
由于后两段与《庄子》重出,所以或可借助《庄子》注疏做一定参考。成《疏》孔子问“蹈水有道乎”曰:
丈夫既不惮流波,行歌自若,尼父怪其如此,从而问之:“我谓汝为鬼神,审观察乃人也。汝能履深水,颇有道术不乎?”(15)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56页。
成疏认为,蹈水者在深潭急湍中还能镇定自若,孔子对此感到好奇,于是询问他是否有什么方法(16)之所以将“道术”翻译为方法是因为虽然成玄英在这里将“道”疏为道术,似乎没有明确道术究竟指超越的道还是具体的术,但其在《齐物论》中,他明确指出“道术”就是“术”:“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子游曰:‘敢问其方。……’成《疏》曰:“方,道术也。虽闻其名,未解其义,故请三籁,其术如何。”见郭庆藩:《庄子集释》,第45页。。
在佝偻承蜩的故事中,成玄英疏“子巧乎!有道邪?”曰:
贝类加工及副产品高效增值深加工技术体系也在那段时间开始形成,贝类热加工技术、贝类低温真空渗透调味及阶段式杀菌技术、贝类热加工食品的运用,使人们享受到了贝类食品“想吃就吃、随时能吃”的便捷。
怪其巧妙一至于斯,故问其方。(17)郭庆藩:《庄子集释》,第640页。
成疏认为,是孔子对老者承蜩巧妙到如此地步感到惊奇,于是询问他具体的方法。可以看到,以上两处成玄英都明确将“道”疏为具体的方法,认为询问者的问题是围绕方法手段展开的。就是说在《庄子》中,“有道邪”的问题询问的就是具体的术。
《黄帝》中的提问者都是对三者的神异事迹表现出极大兴趣,并且提问如何才能达到这一效果,如上所述,在《庄子》相应的重出章节中,成玄英将“道”疏解为“术”“方”。这就说明在提问者看来,三者究竟是否是得道者都是次要的,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三人表现出来的能力,以及达成这一点的具体方法。
再次,从回答者的回答看,其内容都是“有道/无道+如何做到”的模式,是对具体方法的回应。第一,问题并非关心三人是否得道,而是直接指向方法手段,因此作为回答者,一般也会顺着这一语境回答,所以回答的内容应当也是方法究竟为何。第二,三者做出了“无道” “有道”的回答之后,都直接围绕着方法展开了话题。商丘开不知其中的缘由,却提供了一种可能,就是“诚”。蹈水者则认为他并没有刻意做什么,这完全是他的“性命”使然,他只是放弃了自我的好恶,完全顺从于水之道而已。而佝偻者指出他是通过练习达到的,并具体到如何练习,等练习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能内心专一、不被任何外物扰乱。从内容来看,三者的回答都围绕着方法问题,而佝偻者更是直截了当地告知“有道”,以及这个“道”具体是什么。一般在总括性的回答之后,接续的内容是对前文的展开,二者是相一致的,所以看了总述就可以知道分述的内容,同样,了解分述的内容也可以反推总述。这里“有道”“无道”字面所指虽不明晰,但其后的内容确实是向着具体的术的方向去展开的,因此可以推知,这里所说“道”应当就指的是术。
综上所述,“道”除了作为道家的最高概念之外,还有术的含义与用例。由于问题与回答、总述与分述一般在内容和对象上都相一致,因此,询问者提问的对象和答案所指都是具体的术;“有道”“无道”的总述和分述也都是对具体之术的解释,这里“道”确实不是道家的最高概念和境界,而只是在对话中讨论了是否有术的问题。
不过,从文中对商丘开、蹈水者和承蜩老者的描写来看,三者也确实是得道者。商丘开因为“诚”不知利害、惊惧;蹈水者完全无我,已经将自己消融在水之中;承蜩老者心神凝聚在蝉翼上,肢体也完全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既然这里的“道”并不是指三者是否处于得道的状态,而是指具体的方法,那这里不同的回答又有何意义呢?
我们来看三人为何作出不同回答。通常我们有意识地使用某种方法,来达成某种目的时是有所自觉的,在达成了目的之后,是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相反,如果完全是无意识的达成了某种目的,则不知其所以然。这种所以然具体来说就是我们所使用的手段、方法,而知其所以然,其实就是我们对方法、手段的自觉。佝偻者明确地知道自己是通过练习达到的,他对此是有所自觉的,故回答“有道”,并继续对此“道”作继续说明。商丘开明言“虽吾之心,亦不知所以”,虽然他提供了一种可能,就是“诚”,但也只是他的猜测,也就是说他对具体的方法是不自觉的,因此回答“无道”。至于蹈水者,范致虚认为“无所因而自然,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18)高守元:《冲虚至德真经四解》,第81页。,他生长在水边,根本无需凭借什么就能于鱼鳖不可游之处自在蹈水,这是他的性,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所以也回答“无道”。虽然商丘开和蹈水者的境界不同,但单就他们不知其所以然而言却是一致的,并且他们不知所以然的根本原因是确实没有使用什么方法。因此他们都回答“无道”,知其所以然的承蜩老者则回答“有道”。
“得全于天”的真得道者在这里又可以被细分为二:一是以蹈水者为代表的天生的得道者,二是以承蜩老者为代表的,通过修养得道的后天得道者。胡家聪也做出了类似的划分:一种是通过“纯气之守”,排除物欲的干扰,从而神游物外的“至人”;一种是在精工妙技的实践中把握自然规律,直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劳动者(19)胡家聪:《稷下道家与黄老新学》,第346页。。不过对于“至人”为代表的得道者来说,他们天生就处于“纯气之守”的状态中,无需做什么就不受物欲的干扰,如华胥之民天生就处于不知不分的状态中;蹈水者只需顺性而为,在水中便能无私无我,完全与水融为一体;列姑射之山的神人本就没有偏爱和欲望;中山林中从石壁中出、随烟烬上下的人本就不知火、石等等。修养实践也不宜被简单概括为工、技,这是将具体的修养实践范围缩小化了,如黄帝通过斋心服形的修养,照样可以得养生治物之道;列御寇通过累年去除区分、是非之心的修养,最终也能御风而归,这些都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修养。而且在排除物欲的干扰这一点上,二者其实都是一致的,要排除的干扰也不止是物欲。所以我们不从胡家聪的划分,而是将“有道”“无道”讨论中涉及的得道者划分为先天得道者与后天得道者。前者只需顺性而为,甚至无需任何后天努力,就天然的“神合于道”;后者本来境界不高,需要通过长年累月的练习、修养才能达道。
因此,《黄帝》中的得道类型可以分为三种:“得全于酒”的“虚假”得道者,以及从“得全于天”中划分出来的先天得道者与后天得道者。商丘开与蹈水者的“无道”,前者无法借鉴,后者是偶然手段,二者对方法不自知,也就谈不上什么方法,对于修道者来说这两种经验是不可复制的,借鉴意义不大,被《黄帝》列入“无道”之列。承蜩老者境界并不高,但通过有意识的、对一定的“道”的练习,最终达到了“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境地,成为后天得道者的案例。他的“有道”对现实中大多数境界本不高的普通人来说,是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的。通过承蜩老者,《黄帝》向世人表明,通过一定的修养实践,境界不高的人最终也可能成为后天得道者。
三、理想境界:“心凝形释”
《黄帝》主张通过有意识的修养实践,境界不高的普通人最终也可能成为后天得道者。同时,也注意到并非所有的修养工夫都能使人通天达道。因为修养的本质不仅仅是获得方法、技术上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对心的修炼,追求的是达到“心凝形释”的境界。
“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的寓言彰显出了《黄帝》对这一点的关注:
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贯,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镝矢复沓,方矢复寓。当是时也,犹象人也。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当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若能射乎?”于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进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尔于中也殆矣夫!”
《黄帝》强调修养实践的重要性,同时也意识到仅仅停留在对方法、手段的磨练上不能达道,如这里的列御寇。射箭精准、动作流畅,看起来好似木偶,如此看来列御寇应当是得道者,但张湛认为他只穷尽了射箭之理,内心仍矜于外物(20)“虽尽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也。”见杨伯峻:《列子集释》,第52页。,因为内心有所矜,所以心神不一,高崖与深渊就足以给他带来恐惧,他在高山危石上的表现就在情理之中了。伯昏无人就不同于列御寇,他“气性纯和因而天守全”(21)林希逸:《列子鬳斋口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3页。,所以在危崖、深渊面前仍然风轻云淡,与列御寇的丑态形成强烈对比。
列御寇仅仅停留在对方法、形的磨练上,但这并不是修养的根本所在,修养的核心在心:
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 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为无为。齐智之所知,则浅矣。
张湛认为,“心动于内,形变于外,禽鸟犹觉”(22)杨伯峻:《列子集释》,第68页。,虽然人心在内,但只要内心一旦有一丝隐微的变化,即使人自身没有注意,也会从那种不知不分、浑然一体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对于外物而言就成了一个与之相异的存在,就一定会为禽鸟为代表的外物所觉察。历代注家也都持与张湛类似的看法,如宋徽宗以为沤鸟飞来与他游戏,是因为“去智忘机,纯白内备,故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群,鸟兽不恶盖本无机心,物自不疑故也”(23)高守元:《冲虚至德真经四解》,第84-85页。;范致虚“夫机心存于胸中,则海上之沤徒舞而不下”(24)高守元:《冲虚至德真经四解》,第84页。林希逸“‘舞而不下’疑之也。盖谓此心稍萌,则其机已露,岂能物我相忘哉?”(25)林希逸:《列子鬳斋口义》,第51页。好沤鸟者心动,内心就出现了主客对立、物我之分,此时我便远离了物,物也觉察到、远离了我,彻底堕入了有分的世界中。所以虽然形显于外,心隐于内,但《黄帝》认为“心”才是得道与否的根本,修养的对象应当是心。
《黄帝》倡导修养得道,各篇寓言都多少涉及到一些修养方法,肖登福据此总结出三种:去除自高心、机心;泯差别相、对待相,和同于物;用志不分,乃凝于神(26)萧登福:《列子探微》,第111-121页。。不过这些方法看似不同,本质都是一样的,都强调的是对“心”的修养。因为心比一切外在的形、方法都更加根本,所以常人欲修道就必须明白应当锻炼的是人心(27)卞晓鲁:《〈列子〉人生哲学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74页。。通过对心的修养,最终达到“心凝形释”的境界:
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耶?我乘风乎?
“心凝形释”是《列子》所追求的道的境界,也是道家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28)可参许抗生:《当代新道家》,第69页;郑开:《道家的心性论及其现代意义》,《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二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11页。。对于心神极度凝一、合于真道的人来说,因为已经同于大通,已经不再有区分耳目手足、外物与自身的知,不再有好恶、利害与偏见,这是一个我融入道、融入万物的过程。此时薄乎云霄与陨乎坎井之间就完全不再有差别,我就是风,风也是我(29)苏辙《栾城集》卷一八《御风辞题郑州列子祠》写“心凝形释”有“超然而上,薄乎云霄,而不以为喜也; 拉然而下,陨乎坎井,而不以为凶也”之语。。所以此时与其说是不再受到外物的干扰和伤害,不如说是已经没有了物我的差别、对立。“心凝形释”在这里所彰显的既是一种得道的状态,同时又是达到理想境界之人展现出神异色彩的根源。《黄帝》中大量的神异人物面目虽各不相同,但所达到的境界与展现神异功能的根源无不是如此。华胥之民、藐姑射之山的神人、御风而归的列子、坠车不死的醉者、入水火不伤不碍的商丘开、承蜩的老者等等,都是达到这一境界的典范。
不过,这种境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如佝偻者承蜩段:
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也,若橜株驹;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列子·黄帝》)
“心凝形释”段:
三年之后,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后,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七年之后,从心之所念,庚无是非;从口之所言,庚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九年之后,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夫子之为我师,若人之为我友:内外进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列子·仲尼》)
以上描写的是并非天生有道的普通人日积月累地锤炼内心后,最终精进入道的过程。这既是个体通过修养方法通向道的过程,又是个体精神摆脱方法束缚的过程。当个体修炼达到了“心凝形释”的境界时,由于精神的超越,人就不再为肉体所束缚,不再有任何阻碍,这是常人修道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也是《黄帝》追求的最终理想。《黄帝》以普通人的寓言彰显出,道的境界是常人累月地修炼内心,使之凝一不分达到的,这种修养路径对现实境界不高之人来说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结论
《黄帝》追求的最终目标是达到“心凝形释”的境界,一切的讨论都是围绕着它展开。《黄帝》开篇以得养生治物之道的黄帝、藐姑射之山的神人,以之树立起理想人格的典范。二者一个是传说中的帝王、一个是远离人世的仙境中的至人,虽足够神妙,却都离普通人的生活有距离。不过《黄帝》在后文中通过大量对普通人得道的描写,来表明了态度,就是普通人也可以得道,并且所达到的境界都是一致的,即“心凝形释”。
因此,围绕着这一点,可将《黄帝》中的得道者划分为三种类型:首先按照精神境界是否真实达道,划分出两大类,“得全于酒”的“虚假”得道者和“得全于天”的真得道者。虽然凭借“酒”等手段进入得道状态并不能真正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但“得全于酒”的类型的存在就已经昭示着,存在一些后天的手段,可以使境界本不高的普通人进入得道的状态。而后,可以再将“得全于天”的真得道者,细分为“无道”的先天得道者、“有道”的后天得道者。“虚假”得道者与先天得道者在真实的精神境界上有本质的不同,而且二者也都无法提供一个可靠的方法。而后天得道者直接证明,通过一定的方法的渐进修养,最终可以通天达道。这种方法的本质就是对心的修养,经过渐进的修心过程,即使境界本不高的普通人,最终也达到了“心凝形释”的境界。显然,这样的修道方式对于后世的道家道教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