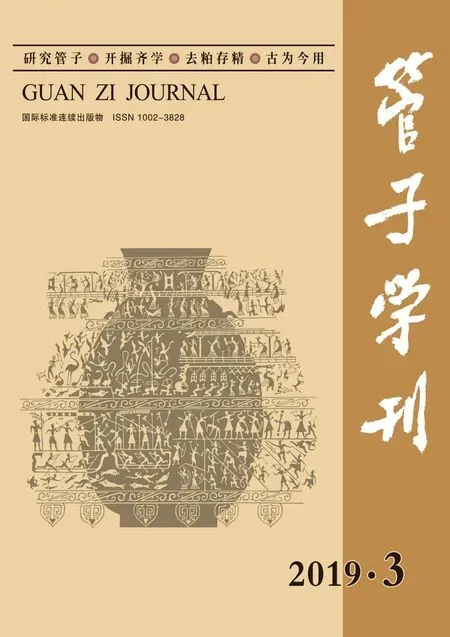文人隐逸精神的发展脉络探析
梁红燕
(华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6)
我国传统文人独特的审美生存方式,以及他们独特的“文人隐逸精神”,消解了肉身对封建主流价值难以割舍的无奈性,彰显了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力量。在密不透风的帝制专制中,文人阶层为世人打开了一个出口——一个比世俗世界更为开阔的精神场域。可以说,兴起于魏晋时期的中国山水艺术,是文人退隐山林的产物,也是文人找寻生命出口的主要途径和文人精神兴起的标志。
魏晋以后,道家艺术精神逐渐被融入文人感性生活体验,慢慢发展出了一套以“逸”为核心的独特审美生存方式,并在隋唐直到宋元乃至明清,随着文人地位的提高,“逸”作为文人超越自我的人格表征而大放异彩,成为中国传统美学史上的一朵奇葩。直至近代,在“救亡图存”和西方文化的双重挤压下,“逸”虽伴随传统文人的没落逐渐被边缘化,但仍在文化土壤中焕发着生命力。
一、文人隐逸精神的发端
在古代中国的一开始,自然、人都不是独立的审美对象:两者先是颂神文化的附属,再是比德文化的附属;一直到魏晋,时人才真实的发现了自然的美、被自然美所吸引,进而成就了心灵与自然的真正契合——现实的诗化人生与艺术创作。这样,在庄子那还是虚化的审美理想,到魏晋,尤其是“竹林七贤”那,转化为了活生生的现实人生,将纯粹的“自然”概念发展为人性的“自然”。
(一)“文”的自觉和自然美的发现
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有言:“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1)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用艺术洗净人世铅华,这种生命精神的外化就是魏晋时人的诗性艺术自觉,也是后世学者们认同的“文”的自觉的发端。
嵇康是魏晋时期“文”自觉期间的集大成者,他把“庄子的纯哲理的理想境界人间化,诗化了”(2)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4页。。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好一派玉树临风的翩翩君子貌!在性格上一方面“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晋书·嵇康》),但另一方面他又刚直认真,痛恨世俗名教的虚伪;他在为人处事中虽认同甚至向往阮籍的平和、宽容,而实际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晋书·嵇康》),与自己人生观相左的人便果断绝交。也正是这种表里如一,成就了他得到“万世景仰”的那种“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审美人生。
嵇康既发现了自然美,又创造了艺术美;他的崇尚自然和艺术创作都摆脱了功利实用的审美需求。他的真性情和正直不阿的品格,加上极高的艺术造诣,成就其鲜活的诗化人生:“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首》之十四)故此,在临刑之时,还能神气自若地弹一曲《广陵散》;发现自然美、创造艺术美、成就人格美,都是嵇康人生观的外在审美表现。
钱穆先生在论证魏晋“建安”时期为中国纯文学的自觉时期时言:“有文人,斯有文人之文。文人之文之特征,在其无意于施用。其甚者,则仅以个人自我作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情感,不复以世用扰忧。”(3)余英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66页。而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由老学、庄学所演变出来的魏晋玄学,它的真实内容与结果,乃是艺术性的生活和艺术上的成就。”(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页。也就是说,魏晋时人对山水的艺术化创造更带有艺术的自觉和纯粹。“在魏晋以前,山水与人的情绪相融,不一定是出于以山水为美地对象,也不一定是为满足美地要求。但到魏晋时代,则主要以山水为美地对象;追寻山水,主要是为了满足追寻者的美地要求。”(5)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第214页.在魏晋名士眼中、心里,山水林泉等自然环境非常符合清静自然的老、庄之学;归隐山林、卸甲田园成为了他们摆脱或超越世俗进入澄明之境的最佳选择。他们常有“登山临水,竟日不归”“每游山水,往辄忘归”的状态;觉得“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所在。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山林不可久居,那归来世俗社会怎么办呢?答案就是把那种“胸中丘壑幽映迴缭,郁郁勃勃,终不可遏”“性本爱丘山”的情感或表达于书画、或表达于诗文。就是“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返,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分飒飒,情往以赠,兴来以答”(《文心雕龙·物色》)的个体心性与自然本性的交融的诗性人生;在艺术上的表现就是将心灵空间与自然空间结合在一起的山水画和山水田园诗。
与之前时人总是把自然山水的美与人的道德品性相关联、自然美逐渐发展成独立的审美对象。
如宗炳,他“好山水爱远游”,归来又能将之图画,以便抚琴饮酒、独步画卷以“畅神”;发明了令后世文人学士竞相崇拜、效仿的“卧游”,还留下了名句:“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受其影响,后世文人中有人只画“卧游图”;有人把自己的画室命名为“澄怀观”(6)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8-12页.。宗炳主张“圣人含道暎物,贤者澄怀味像”(宗炳《画山水序》),他还把这种主张贯彻到了活生生的人生体验和艺术创作中:他跟庄子一样,拒绝食俸禄而主动选择了躬耕田垄;把身心的自由放在人生第一位,全心“澄怀观道”“体道”。
(二)隐逸人格美的升华
寄托了魏晋名士情感体验的山水田园诗,是他们试图在社会之外的大自然中寻求精神上的安宁闲适的另一产物,是他们欲求心灵上的轻松自在、清静淡泊的艺术实现。
如陶渊明,在他的眼中,“自然”并不仅仅是“赏心”的对象,更是一种归宿和安顿。在他的诗作中处处洋溢着一种家园之感,洋溢着一种平和之心。我们在“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诗句中看到了他忘怀于得失、返朴归真的田园生活;在“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皆有托,吾亦爱吾庐”“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中体悟着他自我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亲和。
朱熹曾结合时代特征如是评价陶渊明:“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是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7)谢天佑:《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梁启超说“自然”就是陶渊明本性,“他并不是因为隐逸高尚有什么好处才如此做,只是顺着本性的‘自然’”(8)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42页。。他自己也说自己“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陶潜《与子严等疏》)。这位“羲皇上人”就是一个彻彻底底信奉“道法自然”的“性情中人”。
年轻时候的陶渊明跟我国古代大多数读书人一样:面临着“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两种人生途径选择。虽“性本爱丘山”,但也有“猛志逸四海”的雄心壮志;所以,“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还能够及时折返,“觉今是而昨非”,于是过起了“采菊东篱下”的逸民生活。这一觉醒便为后世留下了一千古楷模——超尘脱俗的诗性人生典范。钟嵘在《诗品》中是这样评价陶渊明的:“(陶诗)文体省净,迨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叹其人,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陶渊明能享此殊荣的原因就是他的“质性自然”的淡定与从容的人生态度——“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神释》)——这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是极大的。如杜甫在年华老去、感叹春光不再时,就想起了陶渊明,“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杜甫《可惜》)又如白居易,提出“中隐”思想的他更是“常爱陶彭泽”(白居易《题浔阳楼》)。但“性质自然”的陶渊明不是后人可以轻易习得的,正如清朝沈德潜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维有其清腴,孟浩然有其闲远,储光羲有其朴实,韦应物有其冲和,柳宗元有其峻洁,皆学陶焉而其性之所近。”(沈德潜《说诗睟语》)再次证明了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那“清腴、闲远、朴实、冲和、峻洁”的隐逸人格在唐代兴盛的山水艺术中发扬光大。
伴随着以陶渊明为典范的文人选择“隐”的行动路线从“身隐”转向“心隐”,隐逸人格的审美形态也从人生体验转向艺术追求。他们在隐向山林时发现了自然的美,也发现了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同时,伴随这种转化,在欣赏自然美的过程中也有了“身游”向“神游”的转变,更有了从“比德”自然审美观向“畅神”自然审美观的转变。在这一系列的转变进程中,主体对“逸”的价值体认和审美追求的精神取向也越见清晰,即从最初逃向山林的有限具象行为逐渐转变为从有限趋向无限的超越精神追求;并在这种超越精神中体会到了比奢华物质满足的享乐更高级的精神自由带来的审美享乐。相较于许由的“幽忧之病”是众多隐士选择“隐”向有形山林之野时内心挥之不去的无奈愁绪纠结所致,而陶渊明的“心远地自偏”的自由则得益于主体选择“隐”时对“逸”的审美追求。
“隐”因为“逸”,才有了中国传统精神中特有的一枝——“隐逸精神”。“隐”和“逸”的这种独特关联性的建立在此后历代传统文人的人生体验中日益彰显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历史意义。
二、文人隐逸精神的高扬
隐逸文化的发展跟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一样都绕不开封建帝制的束缚,鲜有对帝制专制的有效反思。到了宋代,这一点仍没有本质变化,但人们对之认识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进步——人们认同了“天下不仅仅是帝王的,还更应是天下人的”观点,读书人在参政热情之外多了些理性思考;宋朝的开国帝王也深刻反思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意识到只有士人是可以依赖并能牢牢把控住的群体,做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选择”。
(一)文人对心灵安顿空间的探寻
这一政治文明的进步,并没有给士人带来自由而是相反。这种政治社会环境更关键的一点是:宋朝科举彻底废除了门第限制,同时废除了“公荐”制度,科举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这一方面体现了科举的公平性,有利于人们通过自身努力参与国家事务;另一方面,却是帝王加强了自身的权力,牢牢把握住了士人们的兴衰荣辱。在貌似公平的表象下,作为“天下之共治者”的士,相较于前朝的文人士大夫,他们的人身更加不自由了,精神更加压抑了,心灵安顿的空间愈加狭窄了!
对于宋代文人来说,一方面是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以及“科举制”的表面“公平”让他们对自身的社会责任和前途有了清醒的认识和希望;另一方面是他们对自身的不自由的认识也更加清醒,原有的精神压抑感也因了这清醒更加深重!体现在读书人身上的“仕、隐冲突”更加强烈!加之,宋朝三百年间,内有朋党、宦官之患,外有西夏、金、辽、蒙古的不断侵扰,而朝廷又轻武重文;建功立业以趋外辱显然希望渺茫。所以,两宋文人热衷于兴建私家园林,于庭园之间乐享山水春光——“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田,花竹秀而野。花香袭杖履,竹色侵盏斝。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苏轼《司马君实独乐园》)。
不过私家庭园、书斋毕竟空间有限,追求自由的心灵需要一个无限大的空间。
文人要向哪儿去找寻一个相对安全的出口?
魏晋时“文”的自觉,唤起了他们对“自我”的关注。唐以来稳定的帝制,加上儒家“天地君亲”的思想桎梏,文人感受到了精神压抑,他们要表达自己的对世界、人生乃至生命意义的追问。隐于庭园只是肉身暂得栖所,心灵所归只能在著书立说。诗词、曲赋当然是他们超越自我的出口,关键是无言的绘画对于文人来说,也是而且必须是思想的外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逸”为审美表征的文人画便是文人画家们变身为知识分子、张扬自我价值的思想表达;更是他们超越世俗社会追寻自我的出口。
他们不再隐入“云深不知处”,而是在儒家价值观的基础上以禅意悟道——用艺术表达思想,正所谓“逸笔草草,聊写胸中逸气”。如果说,魏晋时的文人隐于山水的“隐逸人格”还只是一种个人魅力的话,唐宋以后文人身处世俗社会、于艺术创作中找寻生命意义的精神支柱则彰显其作为一个群体人格的魅力。期间,社会思想领域儒道佛的融合趋势,更加夯实了文人或仕或隐的心理支持;完全化解了“隐”的心理矛盾——对人生意义的怀疑、对世俗的厌倦,又无法解脱的煎熬——从而催生了旷达、超然物外的审美境界。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是文人人格心理支持的最好注脚。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社会对文人艺术的追捧,使得文人思想在世俗社会中得到高扬。
(二)文人审美追求的现实途径
苏轼的人生可以说是传统文人审美追求发展的现实典范。他早期是崇儒而轻视佛、老的,遭贬后,才将佛、道与儒家“独善其身”的思想相结合。在世俗社会中,他尽力做个好官,造福一方子民;但在精神上却始终是超越世俗、坚守自我的,在其诗词、绘画中尽显自我价值的张扬。他的文人画理论助推了独具审美价值的中国文人艺术。他强调绘画在于表“意”,提倡离形“写意”——“文以达吾心,画以达吾意而已”;但他也重视“法度”、讲究“妙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强调创作在于“自娱”的自由随性——“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也重视“常理”的遵循研习——“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苏轼:《净因院画记》)又强调只有高人逸才之人才能识得“常理”,比如文与可画竹之所以高妙,就在于他知晓了竹之“常理”。在他看来,根本不需纠结与儒道佛三家的具体理念的同与异,正所谓:“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成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苏轼:《送参寥师》)其实,这些理论与实际创造归根结底还是道家的“顺应自然”的美学观,即顺乎自然本性,儒家的“理”、道家的“逸”、佛家的“空”;都可以融合于文人艺术创作中,即要重视“法度”,又要讲究“高远”“空寂”;诗、书、画皆“无意不可人,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顺乎“自然”就好!这些理念于苏东坡而言并不是空谈,他将之融会在了自己现实可感的审美实践之中,“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不嗔不骂喜有余,世间谁复如君者。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铓。剑在床头诗在手,不知谁作蛟龙吼。”(苏轼《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剑》)诗中反映出了他的创作极其随性,无所谓创作的材质;但又有法度,画的是“胸中成竹”。在他的创作中,有剑的豪情、有诗的浪漫、还有“不嗔不骂”的淡定;有自我但不孤独——朋友家雪白的墙壁上被作画写诗还很高兴;超越俗世但不鄙视——常被俗人责骂随地涂鸦而不影响自己创作兴趣。
中国传统文人的价值观一直就在儒道之间摇摆,到了唐宋之后,就更为明显。他们从小接受的是儒家经典的教诲,在自我觉醒时,面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现实专制的困扰,又接受道、禅思想的慰藉。他们在面对社会时常采用济世齐家,面对自身境遇时又向往生命的独立与自由。原本这两方面的追求并不具有必然的冲突,然封建帝制专制导致现实社会人人都受奴役观的影响,生命的独立与自由只能在“无何有之乡”找寻。
儒道佛三家在关于人文思想精神方面的观点有许多相通之处,如三者都主“静”:不论是儒家的修身养性,道家的纯任自然,还是佛家的入定修炼。即便是在“文”刚刚自觉地时期,在文艺批评领域已见出了三家融合的影响。如宗炳的“澄怀观道”,或刘勰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等观念。“逸品”审美理论中“最难其俦”的“意”,就是道家讲究的“神遇”而不可拟迹。唐代中期兴起的禅宗讲究的“顿悟”不就是道家“神遇”的不二法门吗!庄子的“无何有之乡”为文人的隐逸提供了哲学根基的理论支持,而禅宗的“竹密不妨流水过,山高岂碍白云飞”的“心性”智慧又为文人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持。以“逸”为审美追求的山水艺术成了唐宋乃至以后历代文人追求自身超越的最好途径,而儒道佛的融合又为这一途径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随着文人地位的降低,文人价值观面对现实所能借助的心理支持越来越狭窄——艺术成为了文人自我情绪的唯一宣泄口。元朝社会以等级世袭制代替了科举制,宋代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士与君王共治天下”的理念被元统治者的等级制践踏消弭。所以相比与前朝,元代的文人士子丧失了上升的通道和希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难以实现、弘道教化的理想也无途径,加上被“外族”统治的屈辱;内心自是更加苦闷、压抑,隐逸思想重又滥觚。相较于宋朝文人清醒的痛苦,元代文人则是用迷狂掩盖或表现苦闷。经历了大唐盛世、两宋开明,加之元朝统治者强大的统治力,元代知识人于心于外都不能简单的退避山林求取宁静了。元曲最典型的审美特征就是“自然”,这个“自然”指的是借艺术所宣泄情绪的真实——“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儿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一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劣,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9)王振铎:《王国维人间词话与人间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作为中国文学历史上“最自然”的作品,它的创作者只有一个目的——为困顿压抑的心灵找一个安顿之所;所以,元曲的创作者不在乎情节、思想、人物,只为讲故事、宣泄情绪“自娱娱人”;绘画对于文人来说跟戏曲创作一样,也彻底成了“自娱”以慰藉心灵的手段。就这样,元朝进入了文人艺术的鼎盛时代。此后,“有道有艺”的文人艺术就成为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代名词,其中以“逸”为表征的文人价值也一直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褒扬。由于对俗世生命的超越,使得他们有比现实更高的眼界,从而使“逸”能退去“隐”的消极外衣,化身为集儒道释于一身的更为积极的出口——“写意”就是对“逸”美人格的传达和表现。明清之际,随着帝制对思想控制愈来愈严重以及审美的世俗化倾向,文人对“逸”所蕴含的自由意志和人格独立品质的坚持显得更加可贵!
三、文人隐逸精神的没落及展望
当“世界历史”(10)这里“世界历史”的概念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多次提到的“世界历史”,而不是普通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通史。这一“世界历史”的概念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提出的,马克思后来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作了详细的论述。主要指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带来的世界“一体化”进程,人类社会自觉不自觉地都被裹挟进“交往”的“世界历史”之中。发展到今天,就是“全球化”。的步伐已经悄然启程——当我们的文人还在为“康乾盛世”又一次遭遇“明君”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以“工业文明”为发端的近现代史已喧嚣启程。当“自由、平等、博爱”伴随着现代科技大发展的浪潮而响彻寰宇的时候,我们却妄自尊大、蔑视科学、加强集权、禁锢思想。就这样,17、18世纪的世界把我们远远甩在了身后,此时的中国被马克思称为“奇异的悲歌”——“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页。于是,在密不透风的“铁皮屋”里麻木、陶醉着的传统文人是在列强的“炮声”中痛苦地醒来的,他们发现以“逸”为表征的人生的审美化和艺术的追求都变得不可能。现代化的启蒙还没来得及成长,传统却已开始落幕。
(一)文人境遇的进退失据
唐宋时期,文人阶层不论是在世俗社会的评价上,还是在精神价值的自我定位上,都有极高的地位。这种心理优越感在此后的时代一直在文人阶层中延续。但元代文人的失落感导致“隐逸”价值观的负面、消极情绪空前的浓厚;明清之际,又遭到了社会世俗化进程的冲击,“隐逸”被逐步边缘化;历史现实要无情地摧毁文人心理上的这种优越感。而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是新、旧文化“立”与“破”的两难处境;另一方面是“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和自我实现的个人诉求之间的两难选择;这种两难不再是以往进亦忧、退亦忧的个体压抑;而是时代洪流中进、退失据的整体命运。如果说李白、苏轼等传统文人是在自我价值追求中仕、隐之间矛盾煎熬,郁达夫、周作人等近代文人则是在时代洪流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煎熬。前者可以仰仗个体生命的强大得以消解,后者则完全是被时代洪流裹挟而无能为力!
中国传统文人价值观在面对时代巨变时,充满了无奈与无力。自鸦片战争以后,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现实是列强入侵、整个华夏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命运。尽管以往的中国历史总是在不断的朝代更迭中前行;但从来没有像这一时期那样直接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救国图存;所有知识分子都面临一个良心的拷问——全民救国的形势下,知识分子何以处世?也就是说,伴随着中国社会从封建性向现代性的过渡,传统文人社会功能和价值观都受到了空前的冲击,甚至毁灭性打击。
帝制虽被推翻,取而代之的不是共和,也不是民主;而是军阀混战割据、日寇入侵。新的思想、文化还没来得及好好发展,军阀混战不断、资本主义列强以各种手段欺凌中国的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又摆在知识分子面前。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理念,张伯苓的“有我在,中国就不会亡”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鲁迅的“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勇气都指向一个向度——“救亡图存”!相较于封建专制压抑住了人们的理性思考,这一“救亡图存”的现实问题再次压制住了所有人的理性思考——人人觉得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就是传统文化,似乎只要“打倒孔家店”,中国的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然而,社会现实却令人失望;正如鲁迅所言:“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12)鲁迅:《鲁迅自选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就这样,在文化和现实的双重压力之下,理性思考被一压再压,代之而起的是“否定传统”和“接受西化”的不确定性造成的焦虑;以及面对各股政治势力明争暗斗,一介书生救国无门的忧患意识带来的焦虑;是在文化“立”与“破”的两难处境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他们既做不成传统文人那样的隐士,又做不成直面新时代的勇士。
(二)文化遗珠的光芒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逸”是中国传统文人对现实不满,采取的不合作、逃离抽身甚至自我放逐的选择——隐向山林或隐于艺术的行为——在人格精神和审美艺术追求上的表现。这在当时乃至封建专制覆灭之前都是得到社会肯定甚至追捧的,因为“不与流俗合污”是他们对自我的心理暗示;“清高”是社会对他们的身份认证。然而,社会历史进程来到了20世纪;在这个时代,像传统文人那样隐逸、逃遁于山林,或专注于艺术、学术研究等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显然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
文人情结在这个时代都注定会是个悲剧。从客观上,在以往历次朝代更迭中,传统文人面临的只有顺服朝廷与否的问题,“仕”与“隐”都是一种个人基于“道同与不同”的选择而已;而且,文人的“隐”因“逸”还被赋予了“人格高尚”的美丽华衣,受到社会的价值肯定。然,近百年以来的中国在客观上是不允许知识分子有疏离感的,他要求知识分子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参与社会变革与发展,“逸”作为传统文人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追求被最大限度地挤压、甚至被强制从骨子里剔除。如周作人那样想要保身从世事中抽离的文人,不仅会遭到社会的摒弃,还会在历史评价体系中被置于毁灭性的价值评定;甚至一不小心就会被打入汉奸的行列。而像郁达夫那样自我放逐式的隐居,只能将自身置于个人与社会的两难选择之中,带来的只有郁闷、颓废而毫无传统文人旨趣的闲适之感。从主观上,他们置身于一个对传统文化爱之痛苦,破之更痛苦的境地。从客观上讲,他们又被置于对救国大业担之无力,弃之无门的尴尬境地。
就这样,明、清的闭关锁国令中国错过了资本主义生产大发展和近代启蒙思想;鸦片战争以来的“救亡图存”又使我们停留在了新文化的启蒙阶段而错过了发展新文化的最好时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又强行“洗去”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使得从形成到发展都极具现代性意味的“逸”理论生生丧失了与现代性接轨的大好时机,被无情地扔进了历史的黑洞。
虽说旧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应当“跳过去”,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时代。但,我们应该明白,文化是无法“跳过去”的,而且传统文化是根,这个根是该到重新发芽的时候了。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尘土。可是,精神将浮游于尘土之上。”(13)[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以“逸”为核心的文人隐逸精神,一方面作为人格美的表征,它是传统文人对独立自由人格的向往与追求。但在中国专制社会下,这种向往作为现实人生存在着极大的不可能,他们只好将之寄托、转移到自然山水以及艺术中。另一方面作为文人艺术的最高审美追求,“逸”是中国传统文人艺术化生活和审美创作相结合的艺术作品的艺术追求和风格表征,“逸”是文人艺术审美的核心范畴。从这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传统审美范式,“逸”蕴含的文人隐逸精神在今天看来虽有它的不足之处,更有很强的现代性意义——在带有虚伪、退避、颓废、个人主义的弱点之外,还有独立、自由、超迈率性、顺应自然的光环,在新时代的曙光已经闪耀之际,就让我们希翼这萦绕着文人隐逸精神的“尘土”培育出新芽并茁壮成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