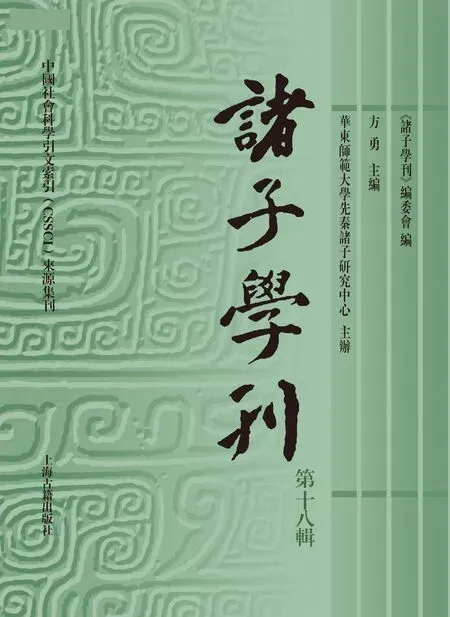孟、荀之“性”論是完善自足的嗎?
——從各自思想道路的内在矛盾性進行考察
史建成
内容提要 當代孟、荀“性”論的闡發者多從問題意識出發得出“應然”的理論重構,卻忽略了思想本身“已然”的内在衝突。從思想自身來看,問題不在於“性”論應該是什麽,而在於“性”論究竟是什麽以及爲何如此,這使得“性”論基於思想自身發展及其内在矛盾的闡發更具理論意義。在與告子的争論中,孟子從來源、内涵、面向三個層面對“性”論進行闡發。在層層區分中,“大體”、“小體”之别在孟子那裏成爲一個選擇難題,“性善”面臨着道德判斷是否成立的矛盾。荀子的“性”論有三重視角,即: 生理層面、心理層面、心知層面。他將批判的着力點置於心理層面的“情性”而非欲望上,並以“辨合符驗”作爲總原則,這使得“性”惡與“僞”善有着足够的理論張力。“性善”、“性惡”的闡發忽略了理論創建與實踐的道德判斷之間的差别,這造成了“性”論自身的斷裂。雖然具有理論缺憾,但“性”論的闡發策略卻爲進一步的理論架構與社會實踐提供了契機。
關鍵詞 性善 性惡 四端 情性 辨合符驗
一、 理論回顧與思路展開
先秦儒家“性”論思想的探討莫過於孟、荀之争。孟子主張“性善”,荀子主張“性惡”,兩種主張的餘緒衝突延續了上千年。即便是今日學術思想繁榮之際,對兩種思想的重新反思也從未停止,多樣性的闡發層出不窮。傅佩榮將孟子“性”論解讀爲“人性向善論”(1)參見傅佩榮《儒家哲學新論》,中華書局2010年版。,因爲他認爲孟子的“四端”之心只是一個傾向於善的開始,將仁、禮“存心”並且“思”才可得之。事實上,當代學者對於孟子“性”論思路基本達成一致,只是在闡發重點上有所不同而已。張鵬偉、郭齊勇對“性向善論”進行了批駁,並且從人的道德屬性的性質來判斷,確定了“性本善論”(2)參見張鵬偉、郭齊勇《孟子性善論新探》,《齊魯學刊》,2006年第4期。。他們從性之本體而不是從其發展與實現程度上來作判斷,最終的結論是: 性善不僅是應然的而且是實然的。張、郭二人事實上仍然基於孟子“四端之心”的發展來談性善,但他們試圖對“性善”做一種先驗的價值解讀。其對孟子之“性”與成人之間關係的討論並没在根本上區别於其他學者,只不過作出了“性”具有先驗性的判斷。楊少涵從孟子心、性、情的内在統一來闡發“性善”,認爲“‘性’是道德本性,心是良知之心,情是道德情感”(3)楊少涵《孟子性善論的思想進路與義理架構》,《哲學研究》,2015年第2期。,但忽略了“善”的解讀。
此外在當代,對荀子“性惡”觀進行重新解讀一時間成爲重要話題。當代新儒家代表牟宗三認爲:“此動物性之自然生命,克就其本身之所是而言之,亦無所謂惡,直自然而已矣。唯順之而無節,則惡亂生焉。是即荀子之所謂性惡也。”(4)牟宗三《名家與荀子》,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版,第150頁。這就是牟宗三的“順性爲惡論”。當代學者的討論基本延續了這一觀念,將荀子的“性”定義爲動物性的本能,將惡看作是順其發展的結果。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從“性”的外延出發對“性”本身進行重新區分。例如,梁濤提出了“性惡、心善説”(5)參見梁濤《荀子人性論辨證——論荀子的性惡、心善説》,《哲學研究》,2015年第5期。。他將荀子的“心”單獨拿出來進行討論,認爲它是“道德智慮心”,而不僅僅是認知之心,善就是從“心術”中得來。再例如,張炳尉認爲荀子對“性”的定義主要側重在“性”的生成之理上,所以它不是道德根源,從而徹底顛覆了天的道德根源性,將善歸爲後天人爲(6)參見張炳尉《荀子性惡説重估》,《孔子研究》,2011年第1期。。
任何孟、荀“性”論的重新解讀都面臨如何爲其確立理論合法性的問題。這種操作的危險在於諸解釋可能僅僅存在視角差異,而無益於增加思想語境以及思想本身的知識。這種危險在運用各種現代理論進行思想解讀的時候更加明顯。當代各種新穎的學説立論往往單獨拈出文本中“性”論已有的定語,並將其與現代倫理學加以糅合。它們從問題意識出發得出“應然”的理論重構,卻忽略了思想本身“已然”的内在衝突,這樣就使“性”本身及其“善”、“惡”被過度闡釋。思想的解讀應當建立於思想自身,從其自身的運行之中尋找解釋可能,即便思想存在斷裂和矛盾。我們認爲,無論是“性”向善還是順“性”生惡都忽略了原始文本中“性”論區分的複雜性以及在此基礎上所作善、惡判定的内在矛盾性。事實上,問題不在於“性”論應該是什麽,而在於“性”論究竟是什麽以及爲何如此,將文本自身的理論困境呈現出來才是一切解釋的基礎。這樣一種從思想自身出發的思考方式正是本文的核心闡發路徑。
二、 性善論: 大體、小體之惑
《孟子》通篇並不願意談“性”,更没有像荀子一樣對“性”作一個明確的界定。一方面原因是,孟子不從“性”字出發闡述理論,所以並不需要明確對其定義;另一方面,“性”論在孟子這裏産生了多重區分,“四端”之心才是孟子最爲强調的“性”。這種獨特性,引起了孟子、告子對“性”的争論,同時也顯現了“性善”在孟子思想結構中的矛盾。正如漢學家江文思(James Behuniak)評價葛瑞漢(A.C.Graham)的孟學研究所言:“葛瑞漢證明,只有當它(‘人性’問題)的使用被楊朱思想的擁護者們變成向儒家思想和實踐的合法性提出挑戰的工具時,‘性’這一概念才在儒家群體中變成一個‘哲學’論題”(7)江文思、安樂哲編《孟子心性之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頁。。由此可見,孟子的“性”論可能存在一種被動反駁的因素在裏面。也正因如此,學界往往忽視了孟子“性”論内在思想邏輯的複雜性而將其籠統描述爲“仁、義、禮、智”。
在《告子上》中有: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杯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杯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杯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杯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杯棬,則亦將戕賊人性而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杞柳爲木,杯棬爲器。告子認爲,人“性”就像杞柳之木一樣,等待人爲雕琢然後成爲杯棬。如果人“性”爲仁義的話,則相當於把杞柳等同杯棬。這句話之前的討論不得而知,但似乎孟子曾事先表達過“性”爲仁義的説法。孟子這裏的回答非常犀利,認爲通過殘害人“性”來獲得仁義簡直就是在禍害仁義。孟子之所以做出這種表述,原因在於告子在“性”的定義上走向了“已然之迹”,但此“已然之迹”的發展並非順其自然而是需經過一番改造。在葛瑞漢看來,告子思想中本來就不存在“生”之外的“性”,他提到“對他而言,除了‘生’没有‘性’,‘生’是生命過程本身、生命力、嗜好、激情以及感動,我們爲了一個道德目標通過自我約束來掌控它們。特别在這一點上,告子的學説對孟子形成了挑戰,因爲它不僅同道德與任意的、也就是天生的生命傾向之間調和問題的解決相衝突,它還否認這個問題本身的現實性”(8)A.C.Graham.The Background of the Mencian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6 /1,2 (1967).。告子的“性”本身既無關乎道德性,也無關乎非道德性,因而它在“性”論内核上是一種否定多元因素調和或衝突的“無定義”。這恰恰是孟子所要極力攻擊的標靶,同時也形成了孟子自身思路闡發的邏輯誘因。事實上,孟子的“性”論有着多重限定以及内在衝突,他從來源、内涵、面向以及善惡四個方面層層反駁了告子的“性”論思想,並爲“性”作了三重區分。
從來源上看,告子認爲“生之謂性”。告子的這一闡述可以理解爲“性”是生來具有的本能。孟子對於告子的批判不在“生來具有”上,而是在本能具體層次的所指上。在《離婁下》,孟子認爲:“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朱熹解釋道:“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9)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02頁。所以孟子的意思是,天下關於“性”的討論不過是就其已然之迹來談罷了(10)在孟子“性”的來源問題上,很多理論將其解釋爲“先驗”或“先天”。事實上在孟子時代,從已然之迹的現實出發來探討“性”是共同點,孟子也並没有擺脱這個歷史語境。所以,對孟子之“性”的“先驗”或“先天”解讀大有張冠李戴之嫌。,但此已然之迹必定是順“性”之自然的解讀。告子的主張符合天下言性從“故”出發的共同點,生來具有的本能也是從生活已有的經驗中得來。但後來告子對於“性”的闡發卻同以“利”爲本的“故”相異,這種差異突出體現於本能的具體層面不同。在告、孟的問答中,告子認爲“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並且“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在告子那裏,生來具有的本能被稱之爲“性”就像白色的東西我們稱其爲白色一樣。無論是白羽、白雪、白玉自然都是同樣的一種顔色屬性。可見,這種理論思路是從外在共性的視角來界定“性”。下文,告子在“仁内義外”的論述中印證了這一點:“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意思是: 對象之長並非我使之長,我只是以之爲長;就像物件之白是我以之爲白,是根據其外在的特徵來賦義,所以説是外在的。告子言“性”一方面承認其生來具有,另一方面則將“性”之本能界定爲外在的共有屬性。正因如此,孟子才極爲諷刺地反詰道:“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在“性”之來源上,事實上孟子首先肯定了“性”的生來具有的特徵,也就是天下言性的共識。孟子所謂“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仁、義、禮、智,我固有之”,均是强調“性”的天生所有。其次,他將“性”視爲同外在共性不同的内在屬性。這是孟子之所以猛烈批評告子理論的癥結所在,這同樣也是二者理論進一步在内涵、面向上不同的深層次原因。
從内涵上看,告子認爲“食色,性也”。順着外在呈現之共性的探討思路,告子將人同禽獸相同的食、色定義爲“性”。針對告子的論述,孟子一面批駁告子之“性”缺乏類意識,一面將“性”從外在呈現拉回到内在的心的層面,進一步深化了來源層面的反駁。孟子談道:
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唯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唯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告子上》)
這裏孟子突出强調了人作爲類存在的感官共性。所謂“天下之口相似”、“天下之耳相似”、“天下之目相似”是將人的口、耳、目感官特質區别於犬馬等牲畜,這一論述是對告子外在共性的模式的有力回擊。在經驗層面上,人同牲畜的官能差别是很容易判别的,但這是否意味着同牲畜構成差異的口、耳、目能够成爲人“性”的組成部分呢?或者説,人的感官官能是否可以被囊括進“性”概念之中呢?顯然,孟子面臨着如何爲“性”劃定理論邊界的難題。在類之“人”的理論視域下,孟子對人的感官官能和内在的心的官能作了進一步澄清。他將人“性”分爲“大體”之“性”和“小體”之“性”,“大體”爲“心之官”,“小體”爲“耳目之官”。孟子有言:“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告子上》)在孟子那裏,心官之中的仁、義、禮、智是人天生所有,它們分别代表了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心之官能思考人性本有的仁、義、禮、智四端,並在實踐中擴充發揚,但耳目之官如若不假以人的思考則會被外物所蒙蔽。確立“大體”之“性”的核心地位,並以其來統攝“小體”之“性”,這樣才不至於被外物所遮蔽以致混亂精神。顯然,孟子並没有將兩種不同類别之“性”對立起來或是否定其中之一。進一步來講,作爲兩種人天生就有的“性”,他們的相互關係才最受孟子重視,也就是以“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爲原則。孟子進一步談道:“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盡心下》)口、目、耳、鼻、四肢的感官官能是人“性”的一部分,由於有“天命”的規定,君子並不把它們歸爲“性”。仁、義、禮、智以及聖人對於天道,它們雖然由“天命”規定,但卻内含於人“性”之中,君子不把它們歸爲“天命”。由此而知,在孟子看來普遍理論視野下的天性、天命本身是交織在一起的,大體、小體之“性”本身也無所謂統合者和被統合者。性、命的區分以及對大體的重視是基於君子修養目的所采取的理論策略,這一策略對孟子的“養氣説”、“君子人格”理論有着極爲重要的奠基作用。孟子“性”之内涵並非是從普遍理論視野來界定而是特指君子視角,由此得出的“性”也自然迥異於天下言性的共識。
從面向上看,告子認爲“性”待改造。正如孟子、告子在來源、内涵上所顯示的差異那樣,孟子不可能贊同告子將“性”視爲外在呈現的共性,也不會將君子視角等同於普遍理論視野。這些不同使得兩者理論在“性”之發展方向上針鋒相對。告子用“杞柳”、“杯棬”的比喻形容人“性”的原初形態與接受塑造的必然性。孟子批駁告子説:“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杯棬,則亦將戕賊人性而以爲仁義與?”孟子認爲人“性”不應當受外在之力的殘害,而且“仁義”也不是被改造之後的結果。在“性”的面向上,孟子認爲應當“順性”而爲“仁義”。事實上,這也是孟子强調君子所認同的“四端”之“性”的必然結果,“四端”既然爲君子所選擇,那麽也必然是君子養成的充要條件。“四端”本之於“心”,是人生來就有的,它們屬於“赤子之心”(《離婁下》)以及“本心”(《告子上》)層面,是排斥“陷溺之心”、“動心”的。“四端”之“性”具有較爲明顯的排他性,這從根本上限定了人必須面向自身,而非外在規範。孟子在“性”的面向上走向了“自反”,他認爲“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自反而忠”(《離婁下》),通過“自反”實現人“性”的彰顯。
從善惡上看,告子認爲“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就人“性”來看,告子將之視爲人生來就有的“食色”,它需要改造,但没有善惡的道德價值;就“善”的界定來看,告子也是從社會意義上來做判斷,而非先天層面。所以告子反對對“性”做道德判斷。孟子提到另外兩種與“性善”不同的表述,即“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兩種理論明確了“性”具有善惡的判定,前者將善惡歸於爲或不爲,後者將善惡視爲“性”的天生差異。孟子否定了關於“性”惡的任何表述,並對善的判定進行了解讀。他認爲“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也就是説順“性之動”(朱熹語),“性”所自然呈現的也就可以判定爲是善的。事實上,孟子雖然贊同人“性”爲善,但很少直接提及“性善”。《孟子》文本中有兩處“性善”連用均爲旁人所説。分别爲《滕文公上》中的“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以及《告子上》中的“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此外,《告子上》中有“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這是孟子唯一直接對“性善”之義進行表述。那麽爲何孟子“性善”思想僅僅只有如此委婉地表達卻没有完全從理論上展開呢?
我們認爲,孟子的“性善”論並非是一個自洽的理論。正如其闡發源於對告子“無善無惡”理論的反駁,孟子的“性善”闡述也是進一步實現君子“仁義”之道的理論鋪墊,其内在思路的矛盾之處體現於普遍理論視野同君子視角的齟齬。孟子對“性”的界定雖然歸於“大體”(心官)之“性”,但没有完全否認“小體”(耳目之官)之“性”。“大體”對“小體”的統轄才是孟子真正要强調的,也即孟子所説的:“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11)唐君毅在《中國哲學原論: 原性篇》中認爲“即心言性”之説可以統攝“以生言性”之説,並分析了緣由。他從自心對自然生命的涵蓋、順承、踐履、超越四個方面出發,解讀爲何孟子選擇在“心性”的角度來討論“性”: 從涵蓋義上説,仁心能够肯定自然生命的欲望;從順承義上説,仁、義、禮、智順承了人生來就有的愛親敬長之心;從踐履上説,德性心最終通過自然生命的身體得以踐行;從超越義上説,心可以主宰自然生命的存亡。通過分析,唐認爲孟子“即心言性”是出於對“心性”統攝之力的理解,但他忽略了在孟子那裏這種統攝力也不是完全必然的,甚至有時在生存與仁義之間必然面臨抉擇。我們認爲,統攝並不代表可以完全地順承甚至取代,“大體”和“小體”的本質差異使孟子很難將“性”僅僅限定在“大體”範疇内的“四端”。所以儘量減少提及“性”並將“四端”作爲論述起點,這樣就可以避免陷入“大體”與“小體”之争。孟子用更加具體的四端之“心”來代替“性”的論述也是不得不作出的選擇。同時在《告子下》“禮與食孰重”、“色與禮孰重”的争論中,孟子也肯定了“小體”之“性”的意義。孟子説道:“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當食、色對人而言至爲關鍵,而禮節較爲次要的時候,怎麽能不説食、色更重要呢!孟子認爲只有當“大體”與“小體”處於同一層面的時候,才可説“大體”更重要,任意地否定“小體”是錯誤的。這種從辯證的角度來探討人性實際上基於一種普遍理論視野,即認同人“性”具有“大體”、“小體”的合理區分。但在性命之辨中,孟子以君子視角區分了性同天命的不同所指。《盡心上》中説“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將“性”完全限定在“四端”層面是君子之“性”的歸屬。這種限定構成了“性”善道德判斷的理論基石,而事實上孟子所言之“性”善也是從仁、義、禮、智出發而非感官官能。在此,基於君子視角的“大體”之“性”完全將普遍理論視野之“性”排擠在外。這種前後理論上的矛盾、“大體”對“小體”合法性的剥奪是兩種視角不斷轉换的結果。兩種不同視角下的“性”概念自然也無法統一於同一個價值判斷之中。
所以就孟子文本來看,目的不在於給予“性”論一個客觀縝密的理論論述,而在於從“性”的大視野下消弭“知”、“行”間的鴻溝,對於心之“四端”的理論認識正是基於外向擴充面向“行”的目的。阮元看待孟子的“性”論着重在節與治,在《性命古訓》他認爲仁、義、禮、智“此皆命禄,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禄,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行仁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 君子不謂命也”(12)阮元《揅經室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12頁。。這一看法從側面印證了孟子“性”論存在的外向實踐的傾向,君子之“性”不在於理論本身的完美而在於如何面對“小體”所涵蓋的諸多傾向以及如何從自身中發現必須“思”、“求”的善端。
三、 性惡論:“辨合符驗”原則下的“情”
同孟子以批判代論述不同,荀子在《正名》《性惡》中對人“性”做了非常明確的定義。儘管“性”惡思想主要針對孟子“性”善論,但荀子的闡發卻更加體系和正面。《正名》中説: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
《性惡》中説: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
梁啓雄認爲“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同“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是兩種不同的説法。在他看來,“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强調“性”是“生之然”的根據,“性”爲“生”的載體,所以“性”指的是包括了目、耳、口、鼻、身的形體器官。他認爲前者“指天賦的本質,生理學上的性”(13)梁啓雄《荀子簡釋》,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09頁。,後者“指天賦的本能,心理學上的性”(14)同上,第310頁。。廖名春繼承了梁啓雄對於荀子“性”字的分疏,將荀子前後的兩個“性”分别界定爲“生理的性”、“心理的性”。從“性”、“生”二字的源出關係來看,“性”發源於“生”,那麽“性”同人的器官官能關聯起來是可理解的。但將“性”等同於形體器官,則把器官與官能混爲一談。事實上,“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中的“所以”並非物理意義上憑藉的意思,因爲“生”本身不是憑藉“性”才得以實現,而是自然而生。“生之所以然”和“性”不是物理意義上的從屬,而是日常經驗屬性與對經驗屬性進行抽象定義的關聯。“不事而自然”之“性”也不可單單指涉爲心理意義上的“自然”,因爲陰陽合德所生的萬事萬物並不偏向於生理或是心理中的任何一層面,或者説“自然”本身就是統合生理、心理在内的哲學範疇。從荀子的論述中也可得見,荀子將“性”置於與其相關的概念群中進行解讀而非局限於推究單個概念。所以從其整體思路中把握而非單純探究語義學内涵才是研究荀子“性”論的更好方式。
荀子的“性”論首先是從“性”、“僞”之分合談起的。“僞”即人爲,它的目標是對於聖人制定的禮義進行學習。“僞”所效仿的禮義法度,必須從實踐的角度通過行動具體落實,是“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因而是有形有物的社會實踐。“性”所導向的“好利”、“疾惡”、“耳目之欲”等屬性是不需要任何事務的磨練就可以展現出來,也就是“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一方是“必且待事而後然”,一方是“不待事而後生之者”。“待事”同天生自然相對,唐人楊倞注“事”爲“任使”,梁啓雄依照久保愛的注解解釋爲“修飾”。“待事”與否就是“性”、“僞”區分的重要標誌。這種區分在於是否有外在規範介入到天生之性的展現過程當中。傳統天、人不是絶對理性意義上的概念,而是具體在經驗呈現層面的反思。與此同時,荀子的“性”、“僞”概念也並非具有先天、先驗成分與後天經驗的區别,兩者都是具體到實踐經驗層面(一爲‘待事’而然,一爲不“待事”而然)來談的。在差别之外,“性”、“僞”又不可分離,二者互爲前提,“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禮論》)。這種“性僞合”在理論闡發上體現了荀子所强調的“辨合符驗”(15)《性惡》篇説:“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楊倞注曰:“符以竹爲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議如别之合,如符之驗,然可施行也。”荀子從“辨合符驗”上看,“性惡”具有在理論上要求現實改造的必然性,“性惡”與“聖王”、“禮義”相互要求與印證,因而他説“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原則。這種原則認爲理論的判定一定要與現實有所呼應,是現實的驗證和補充,“坐言”與“起設”、“施行”構成互補才能成爲後兩者實現的依據。這種“合”與“驗”即可以是相互協調,也可以是相互衝突(16)在知行觀上,這種“辨合符驗”主要體現爲一種知、行的協同。在性僞論上,這一原則主要體現爲一種性、僞的衝突。葛榮晉在《先秦兩漢哲學論稿》的“知行論”部分,認爲荀子以辨合、符驗爲喻,説明凡是一種認識只有在“行”中得到驗證,證明它是與客觀實際相符合時,才是真知。他所提到的是這一原則在知行觀的體現。但在性論中,荀子則以雙方的衝突來實現“辨合符驗”。。孟子將“性”、“僞”看作是咬合在一起的兩個邏輯鏈環並使“性”論服務於更高的“出於治”、“合於道”。“性”、“僞”的結合建基於兩者的衝突,這爲“性惡”論的提出創造了理論條件(17)“性”與“僞”的辨合符驗,從來源上看一方爲“天之就”,一方爲“聖人之所生”;從内涵上看一方爲“好利”、“疾惡”、“耳目之欲”,一方爲“師法之化”、“禮義之道”;從結果上看一方爲“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一方爲“合於文理而歸於治”。兩兩相對,相互牽制與補充。。
從自身的邏輯内涵上來看,“性”爲陰陽二氣和合所生,即“性之和所生”。荀子從生理、心理、“心知”對“性”做了三重區分。
從生理上看,“性”體現在“目好色,耳好聽,口好味”、“骨體膚理好愉佚”,這種“食色”感官意義上的“性”同告子的論述相近似,可以説是對傳統意義的一種繼承。但不同點也非常明顯,荀子非常强調“群”與“類”,認爲“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勸學》),包含了人的口、耳、目、鼻、身的“天官”同樣也具備類特性。荀子認爲:“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正名》)人的不同官能發揮作用,對外在世界進行歸類並最終約定俗成事物之名。名、實連接關係的形成正是依賴於人感官的統一類特性。因此從生理意義上來看,荀子論説之“性”顯然不同於牲畜之性,同時區别於告子意義上的“外在呈現之共性”。荀子意義上的“性”概念首先是一種生理感官的類之性。
從心理上看,荀子着重解讀了“好、惡、喜、怒、哀、樂”之“性”,他將這六種元素稱之爲“情”,也就是文本中經常合用的“情性”。正如荀子所言“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正名》),“性”是一個總括性的定義,天生所然,“情”爲“性”之質體(楊倞語),“欲”爲“情”的外在對應者。顯然,代表質體的“情”居於“性”的中心,而“欲”則是“情”外在呈現的對應物。從“性惡”的判定上看,“情”也居於接受批判的核心位置。《性惡》中對“情性”的論述如下:
1. 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争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2. 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争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
3. 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
4. 縱情性,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
5. 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
6. 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兄弟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
人對於利、聲色之好,對於他人的嫉妒之情是繼“性”之後進一步發展爲争奪、犯分亂理的直接來源。所有對於“性惡”的判定,背後都有着“情性”的直接原因,所以荀子强調“六情甚不美”。從“情性”同“性”、“欲”差别義上來看,《荀子》文本爲三者所做論述是非常不同的。“性”的基本内涵是“本始材樸”,它同“師法”之“爲”相對,“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而師法者,所得乎積,非所受乎性”(《儒效》)。這是關於“性”本身的論述,其中並無過多的道德判斷,内涵義上也並非限定在“情性”之内。對“欲”本身而言,荀子認爲“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正名》),並且“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人“欲”(18)荀子所提到的食色以及各種官能的欲望,當它們圍繞着“情性”無節制之“好”的時候,才被“性惡”的論説所接受,單獨將感官欲望拈出,並没有被荀子定義爲“性惡”。並不可怕,它是區分人與其他動物,關乎人之生死的一件東西。它也不與社會治亂相關,而且一定意義上禮義就是爲了“養人之欲”。在這樣的理論差别之下,“情性”成爲一切悖亂不治的開端,而這一社會現狀的實現則是從縱、順“情性”而不對其加以矯飾開始的。由於人之情“窮年累世不知不足”,這導致“情性”在放任自流的情況下極易導向悖亂、壞理,造成惡的社會現狀。要實現社會之治,則必須對人之情性進行改造,也就是對其“正之”、“導之”。
從“心知”上看,荀子將“知仁義法正之質”視爲性的構成部分。荀子認爲“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心知”在荀子那裏很少用“性”來加以界定,這是由於“性”的論述更多地偏向了上文所説的心理層面。但毫無疑問,人生來並非没有“心知”,正如荀子所言“然而塗之人,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性惡》)。在荀子那裏,“心”是居於中虚以治五官的“天君”,通過“虚壹而静”來達到“定是非”、“決嫌疑”。“心知”歸屬於“性”的原因在於“人生而有知”,它同荀子“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的定義相契合。徐復觀認爲具有認知判斷能力的“心知”是由惡通向善的通路,並將是否具有道德性作爲孟、荀之心的重要分水嶺。雖然“心知”如此重要,但荀子並没有將其置於性論闡發的起點。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爲了區别於孟子的“四端”學説,避免走向同一理論思路而弱化禮義法度的規範性;另一方面,荀子所堅持的“辨合符驗”原則拒絶了無法同現實依據形成理論張力的出發點。後者是荀子“性”論更爲内在的結構性原因。
正如上文所述,荀子的“性”概念分爲生理、心理、心知三個層面。荀子做出“性惡”的判定也不是基於“性”本身的多層次内涵,這一判定來源於對孟子“性善”論的有意誤讀。荀子提道: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 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性惡》)
“性善”被荀子設定爲社會完成意義上的“正理平治”,顯然這並非孟子本義。而從荀子“辨合符驗”的原則來看,聖王之道、禮義法度的規範意義正是建立於“性”惡的基礎之上。只有確立了“性”爲惡的理論意義,才會爲“僞”善的施行提供確鑿的前提。從理論發展上來看,荀子的“性”概念是經過“情”、“慮”、“僞”和人的生活世界發生關聯。“情性”是“精合感應”所體現出的特質,假若没有人之“慮積”、“人爲”的矯飾,“情性”就會直接在現實中導向偏險悖亂。“情性”所扮演的角色是從“自然而然”的總特質到犯分亂理式的欲望呈現的中間環節。因而,從辨合符驗的原則出發,犯分亂理之惡就要直接同“情性”相契合而不是欲望本身(19)徐復觀認爲荀子的人“性”論有着兩層含義,一方側重於“生之所以然”的形上意義;另一方側重於經驗中的現象,而“性惡”的闡發是單就經驗層面官能所引發的欲望而言的。儘管他看到荀子對性、情、欲三者的分疏,但在解讀荀子理論時,徐復觀卻將三者認定爲一個東西的三個名稱,籠而統之爲“以欲爲性”,忽視了欲與情的差别。。人之欲望並不必然是犯分亂理式的欲望,“養人之欲”也是荀子非常重視的,但當人之情不合於理,那麽這種欲望呈現才會成爲破壞社會安定的因素。由此可見,荀子的“性”惡不針對天生的官能,同時也並不針對欲望本身、思慮心知。荀子對“情性”的論述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從董仲舒到《白虎通》以至於唐代李翱的“性善情惡”學説,但這種特指“情惡”的思想卻並没有在荀子的論述中得到具體澄清。
根據荀子的整體“性”論思想來看,對“性”所作“惡”的道德判定實屬牽强。最爲明顯的是,文本中所有得出犯分亂理、悖亂不治的現象均是從順、縱“情性”的角度來説的。但荀子又爲何在如此明顯的矛盾論證中選擇這一結論呢?從荀子整體的哲學思路來看,“性”、“僞”之分合作爲一切理論闡發的起點,最終導向“化性起僞”的教化偏向。通過“聖人之爲”制定的禮義、法度,具有無可辯駁的合理性和莊嚴感,並且它們對大衆的教化最終導向社會的完善。作爲“本始材樸”之“性”自然就成爲論證這一合法性的重要邏輯起點。根據荀子“辨合符驗”所要求的尋求理論與現實相印證的原則,“性”本身應當爲禮義法度之“僞”提供合法性與必然性依據。在這一前提下,“性”縮小了自身的理論所指,僅僅被劃歸爲以“情性”爲核心的“性”,並在此基礎上被賦予惡的内涵。
四、 兩種“性”論闡發的内在策略
從上文論述可知,孟、荀的“性”字解讀均開始於後天社會經驗而非先天的觀念預設,兩種理論均將“性”置於人存在的開端而非彼岸世界。孟子以“故”爲準的天下言性思路在荀子那裏同樣得到體現。但另一方面,“性”概念本身又極具社會内涵,它在戰國時期已經逐漸脱離“以生言性”的詞源學解讀而更加傾向於“人之爲人”的論説。在這種理論的言説過程中,孟、荀二人均有將理論認知與實踐的道德判斷相混同的弊病。因爲就善、惡的道德判斷而言,孟、荀均將其推到社會實踐意義上來探討,仁、義、禮、智的“反身而誠”、“强恕而行”與荀子意義上的“偏險悖亂”處於同一層面。兩人從未脱離具體社會語境來探討善、惡。但在理論認知上,兩人又同時將開端意義之“性”設定爲具有生理、心理等多維内涵的非定向概念。兩種不同所指混合於“性”之中,造成了理論自身的弊病。
正如上文所述,孟子的“性善”面臨“大體”、“小體”的選擇問題,荀子的“性惡”在“辨和符驗”的原則下排除了人的生理官能、欲望和心知。孟、荀的道德判斷均不是從性的整體概念出發,因而從根本上講,兩者的“性”論都是不完整和缺乏自洽的。在這種殘缺中,我們可以看到先秦兩大儒家代表在“性”論建構中的共同策略。
第一,集中的道德判斷與分散的概念界定。從文本的佈局來看,“性”之善、惡的論述篇目主要集中於《告子上》《性惡》,其餘各篇的零散表述也多爲後學所作的轉述。這一現狀一方面源於孟、荀有關“性”的道德判斷有着直接針對性,具體體現在孟子對以告子爲首的三種性論的反駁,以及荀子針對孟子理論的批判;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兩者並不將理論意義上的判斷作爲整個思路的論説核心,兩者都不固守於理論批判。而與之相反的是,兩者對於普遍意義上的“性”又有着較爲豐富的闡發。這些論述散見於各個章節,形成了特定歷史語境下較爲完善的理論總結並有所推進。孟子在《離婁下》《告子上》《告子下》《盡心上》《盡心下》中對普遍意義上的人“性”進行論説,並肯定了生理感官的類特性、着重强調了心官的道德内涵。荀子在《勸學》《禮論》《正名》《效儒》諸篇中對生理感官、欲望、心知等進行了圍繞“生之所以然”的探討。
第二,縮小概念範圍,實現道德事實的自證。無論是孟子將“性”善限定在心之“四端”,還是荀子將“性”惡限定在“情性”,兩者均從普遍意義上的概念整體進一步縮小其所指。成中英認爲:“兩者也有本體論上的互容性,因爲兩者均未對人性之爲人性的整體(一個開放的整體)作出全面的考察與反思。兩個學派的表面的矛盾及其解決也正好推向此一整體的發展的人性論的建立。”(20)龐朴編《儒林》(第四輯),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頁。所謂整體的發展的人性是對社會實踐意義上完成了的人的判定。孟、荀的“性”之善惡並不是從整體視角也不是從社會完成意義上來論述的,這種極爲狹小的概念界説實際上是一種道德事實的自證。這種道德事實在孟子那裏是彰顯君子修養的仁、義、禮、智,在荀子那裏是社會悖亂背景下人的犯分亂理。從已被定義的道德事實出發並將其置於人性的内核之中,得到的結論自然也就循環回到開始即有的判斷。
第三,以道德判斷引領理論闡發、實踐操作。正如前文所述,孟、荀的道德判斷並不局限於論斷層面而是有着建構理論體系、面向社會實踐和改造的用意。
由人“性”出發面向社會實踐,從君子修養的踐行以至於達到學爲聖王、實現堯舜之治爲兩者所共有。孟子的反身内求、“養氣論”,荀子的化性起僞、外學於聖王均是從“性”論延伸出來的理論架構。孟、荀强調普通人與聖人在“性”上的等同,其意義均體現在朝向未來的作爲。雙方所理解的堯舜之“性”雖然不同,但堯舜所達到的道德修養以及社會治理卻是共有的價值典範。荀子有言:“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修爲,待盡而後備者也。”(《榮辱》)孟子有言:“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盡心上》)堯舜的典範價值不在於“性”,而在於從“性”出發的聖人之“爲”。孟、荀認爲要達到堯舜的典範高度,必須從“爲”字着手,通過學習堯舜而成爲堯舜式的聖人,實現天下之治。“性”論的闡發引領了人之作爲,是人社會化的開端。
總之,孟、荀的“性”論在其概念界定與道德判斷之間存在斷裂。從理論自身角度來講,我們認爲這兩種理論均存在自相矛盾、缺乏自洽之處。忽略這一點並對兩種“性”論進行當代的善、惡闡釋並不是觀照思想本身的方法。從理論與其源出的時代語境來看,兩種理論又是先秦時代人性論意識覺醒的兩座高峰。從以生言“性”到“性”有善惡的發展體現了先秦儒家代表對於人之本質問題的深刻反思與推進。在兩者的整體理論叙述中,“性”善、“性”惡論都處於起點位置並爲各自理論内核提供合法性依據。當然,這種依據在理論變革的時代洪流中往往過於激進並造成多重視角内含於叙述話語中。這又是理論在歷史中必然經歷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