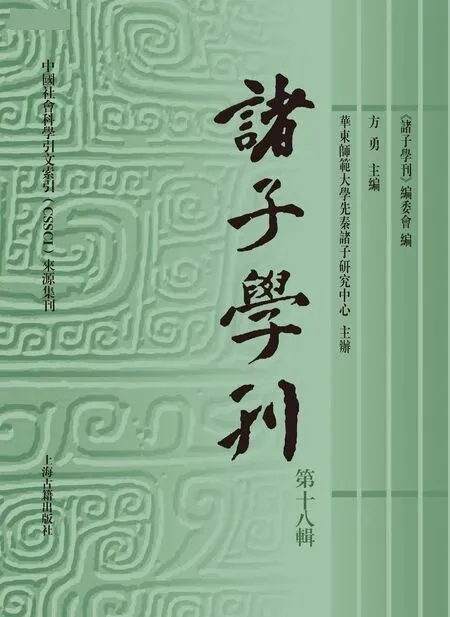陽明釋“盡心知性”章探析
唐東輝
内容提要 陽明對孟子“盡心知性”章的詮釋,是其“龍場悟道”之後的成熟見解。陽明之詮釋,以其“知行合一”的知行觀爲立場,受程子聖人“盡心知性不假存養”的啓發,以《中庸》“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爲比配框架,并注重學者之根器,且融合了他心性是一的心學思想以及深刻的生命體驗,故能言之有理而自成一家,但亦囿於其立場與比配,使此章失去了在成德實踐中的普遍意義。盡心知性、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三聯之間,並非自下而上、上可涵下的關係,而是開疆拓土、嬰城固守與磨刀石的關係。
關鍵詞 陽明 “盡心知性”章 成熟 成因 理路 檢討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這是理解孟子哲學思想的著名章句,歷代大儒對此皆有精闢論述,其中陽明的詮釋較爲特别:“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1)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頁。然而對於陽明此解,牟宗三先生卻頗不贊同,認爲“此種比配全無意義,此亦賢者一時之糊塗也(不知何故有此扭曲之想法)”(2)牟宗三《圓善論》,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版,第99頁。,又認爲“此種比配尤爲不類。陽明《傳習録》義理精熟圓透,很少有不順適處,惟於此處則極顯不類,滯之甚矣。不知何故。而且此義凡三見,此非偶爾之失”(3)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上),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3年版,第28頁。。陽明此解究竟是賢者一時之糊塗,還是絶非偶爾之失,其比配是否真是全然不類,竟至毫無意義,還是自有其深意在,以下詳論之。
一、 陽明此解乃成熟之見
如前所述,對陽明此解,牟宗三先生時而曰“此非偶爾之失”,時而又曰“此亦賢者一時之糊塗也”,所言竟至截然相反,故吾人何所適從,亟須辨明。就筆者所見,陽明此解,絶非“一時之糊塗”,乃是成熟之見。
一方面,就陽明此解之直接動因而言,乃爲對治朱子之詮釋,故不可能草率爲之,否則,根本無法實現其撥亂反正之目的。朱子之解此章,乃是以其知行觀(“知、行常相須”(4)黎靖德《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48頁。)爲立場,在仁(行)智(知)雙顯中凸顯聖者之能事(“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孟子·公孫丑上》),故是一成熟之見解。朱子解此章曰:“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49頁。又曰:“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6)同上。“造其理”屬“知”,“履其事”屬“行”,“知”不離“履”,“履”不離“知”,正是知、行常相須。朱子又曰:“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7)同上。此正是在仁、智雙顯中凸顯聖者之能事。但對朱子此解,陽明卻並不認同:
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修身,以“夭壽不貳,修身以俟”爲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8)王守仁《王陽明全集》,第49頁。
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尚未能不貳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9)同上,第50頁。
在陽明看來,朱子此解是將修身工夫倒做了,要初學之士便去做聖人之事,只會使學者徒費心力而一無所得。由此,陽明才提出了他對“盡心知性”章的新解,以救正朱子舊解之失。朱子之舊解,乃其成熟之見,陽明對治之新解,亦須深思熟慮,乃可撥亂反正。
另一方面,無論就陽明此解在《傳習録》中出現的頻次而言,還是就陽明此解本身的思想而言,陽明此解都是一成熟之見解。就出現頻次而言,據牟宗三先生考證,陽明此解在《傳習録》中凡三見,這足以説明此絶非偶爾之失。當然,牟先生所説的“凡三見”,是指詳細論述而言: 一見於《傳習録(上)》答徐愛所問;一見於《傳習録(中)》《答顧東橋書》所云;一見於《傳習録(中)》《答聶文蔚(二)》所論。實則仔細翻檢,《傳習録》中還有兩處論及孟子“盡心”一章,且均見於《傳習録(下)》: 一爲陳九川所記,一爲錢德洪所録(陽明所解,以下將隨文予以或詳或略之展開,此處不再具體羅列)。
就陽明思想發展的脈絡來看,陽明此解確係成熟之見。不管陽明在《傳習録》中對此問題討論了幾次,都只是一種量的説明;只有深入陽明此解思想之本身,才可作一番質的規定。陽明龍場悟道之後,始挺立自己的學問路向,雖屢有發展,但爲一種“同質的發展與完成”(10)蔡仁厚《王陽明哲學》,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頁。,黄宗羲在《明儒學案》中將其概括爲三階段: 一是龍場悟道之後,以默坐澄心爲學的;二是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三是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11)黄宗羲《明儒學案》,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80頁。。就時間先後而言,陽明首論“盡心”一章,乃爲徐愛在《傳習録(上)》所録一節,此爲徐愛在正德七、八年間(1512、1513)向陽明問學時所録,時陽明四十一、四十二歲,其解曰:“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12)王守仁《王陽明全集》,第6頁。其次爲陳九川在《傳習録(下)》所記。正德九年(1514)陳氏初見陽明,時陽明與甘泉論格物,陳氏甚喜舊説之是:“先生又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卻遂無疑。”(13)同上,第102頁。“卻”字表明,陳氏所無疑者,乃是與朱子舊説相對之陽明新説。雖然新説並未見記録,但與徐愛所記時隔僅一年,且從陽明以後對此章之論述看,陽明對此章的詮解是一以貫之的,因此可以説,陽明當時所論亦不出徐愛所記之範圍。這兩次記載是陽明龍場悟道後的見解。再次,爲《傳習録(中)》所載《答顧東橋書》。據《年譜》,是書作於嘉靖四年(1525),其言曰:“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14)王守仁《王陽明全集》,第49頁。最後,爲《傳習録(中)》所載《答聶文蔚(二)》。據《年譜》,是書作於嘉靖七年(1528),其言曰:“‘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説,頗已明白,無可疑者。”(15)同上,第97頁。這兩處記載均是陽明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期的見解,所答亦均不出答徐愛所問之範圍。此外,《傳習録(下)》還記載有錢德洪向陽明請教“夭壽不貳”的問題,其時陽明所答,亦是“困知勉行”之意(以下有詳論),與前此四條並不相違。陽明於正德十六年(1521)正月在南昌正式揭致良知之教,錢德洪於是年九月陽明歸餘姚時拜其爲師,明年二月,陽明父卒,居喪講學。故錢氏所録,極有可能也是陽明歸越之後的語録。可見,陽明對“盡心知性”一章的詮釋,乃是“龍場悟道”之後一以貫之的解讀,所以,此乃陽明成熟之見解,而非“賢者一時之糊塗”。
二、 陽明此解之成因分析
在此章的詮釋上,陽明之所以不滿朱子之舊解,乃是由其“知行合一”的知行觀決定的。如前所論,朱子之解此章,乃是以其“知、行常相須”(16)黎靖德《朱子語類》,第148頁。的知行觀爲立場: 以盡心知性知天爲“造其理”,屬之“知”;以存心養性事天爲“履其事”,屬之“行”;以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爲“智之盡”(知),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爲“仁之至”(行),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此即是“知、行常相須”,在仁智雙顯中凸顯聖人之能事。而在陽明看來,朱子如此解釋,實際是將知行分爲兩事,作兩截用功,已失去了“知行的本體”,故力主“知行合一”之論,要復“知行的本體”: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17)王守仁《王陽明全集》,第4頁。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聖學只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18)同上,第15頁。
某嘗説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説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説一個行,已自有知在。(19)同上,第5頁。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 知行工夫本不可離。(20)同上,第47~48頁。
在陽明看來,“知行的本體”即是“知行合一”,不可將知行分作兩事,作兩截用功。正是在“知行合一”的知行觀下,陽明才極力反對朱子將“盡心知性知天”分屬於“知”,而將“存心養性事天”分屬於“行”的解釋。在陽明看來,無論是“盡心知性知天”,還是“存心養性事天”,亦或“夭壽不貳,修身以俟”,其中都有個真知行在,區别就在於,“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中庸》)。正是在《中庸》這一論述的影響下,陽明將孟子此章的爲學工夫進行了比配,對應於三種不同的根器:“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21)王守仁《王陽明全集》,第49頁。
陽明所以如此比配,當是受《胡子知言疑義》中程子之言的直接啓發。朱子在《胡子知言疑義》中指出:“然程子‘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者,蓋惟聖人則合下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間更不須下存養充擴節次功夫。”(22)朱熹《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5~3556頁。觀陽明以盡心知性歸諸聖人,以存心養性歸諸賢人,與程子所論一般無二。而陽明早年亦嘗遍求考亭之書以讀之,《胡子知言疑義》如此重要之文獻,當在熟讀之列。且從陽明引述朱子解此章之言,亦明是從《胡子知言疑義》中轉述。朱子曰:“《大學》之序言之,則盡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誠意正心之事;而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修身以下之事也。”(23)同上,第3555頁。而陽明在引述朱子之觀點時指出,“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修身,以‘夭壽不貳,修身以俟’爲知至仁、盡聖人之事”(24)王守仁《王陽明全集》,第49頁。,顯係將朱子在《胡子知言疑義》與《孟子集注》中的説法融合爲一: 將“盡心知性”歸之於物格知至,將“存心養性”歸之於誠意正心修身,顯係《胡子知言疑義》之論(《孟子集注》中只有將“盡心知性”歸諸物格知至的論述,並没有將“存心養性”歸諸誠意正心修身的論述);而將“夭壽不貳”歸之於“知至仁、盡聖人之事”,則是朱子在《孟子集注》中所論。
此外,陽明此解所以如此比配,亦是其爲教注重學者根器的一貫立場的表現。當“天泉證道”之時,錢德洪持“四有説”,認爲:“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25)同上,第133頁。王龍溪則持“四無説”,認爲:“若説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26)同上。陽明則指出:
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 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27)同上。
就“盡心知性”一章而言,“盡心知性”一聯乃是接引利根之人的教法,“存心養性”、“夭壽不貳”乃是接引中下根之人的教法,故陽明曰:“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絶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能也。”(28)王守仁《王陽明全集》,第98頁。
三、 陽陽此解之理路分析
以下,詳論陽明解此章之理路:
陽明解“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一聯曰:
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29)同上,第6頁。
在《答顧東橋書》中又進一步詳細論述曰:
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30)同上,第49頁。
在心與性的關係上,陽明認爲“性是心之體”,但陽明所説的“心之體”,並不是朱子“心統性情”義理框架下,以性爲心之體、情爲心之用的體用之體,而是本心即性的本體層面的體,或者説心的本來面目就是性。“性一而已: 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31)同上,第17~18頁。所以,心與性原是同質的,只是因論述的角度不同而命以不同的名稱罷了。正是在這一理論背景下,才能理解陽明所説的“盡心即是盡性”,因爲在朱子,性是心所具之理,心是氣之靈,心與性是不能畫等號的;而在陽明,因爲心與性“一而已”,故“盡心即是盡性”。既然“盡心即是盡性”,關鍵是什麽人可以盡心或盡性,《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只有至誠的聖人才能“盡其性”,才能“知天地之化育”,才能“知天也”。這樣,陽明就將“盡心知性知天”一聯歸諸生知安行的聖人。
陽明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一聯曰:
海外投资项目中间层级公司架构的搭建由税务影响分析和法律可行性分析两部分共同完成。首先应由从事税务尽职调查的第三方机构从税务角度进行中间层级公司的搭建,要求在满足各国税务要求情况下尽可能实现税务最优,与此同时由专业从事国际投资业务的律师结合不同国家法律规定进行法律可行性的论证,最终得出最优海外投资架构设置。
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别。(32)王守仁《王陽明全集》,第6頁。
在《答顧東橋書》中又進一步詳細論述曰:
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己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33)同上,第49頁。
在陽明看來,聖人能盡心盡性,已與天爲一;賢人則未能盡心盡性,仍與天爲二。以《中庸》擬之,聖人乃是“發而皆中節”(《中庸》),故爲“盡心”;賢人則未能發而皆中節,時有所失,故未能爲“盡心”。而賢人若想達到盡心盡性以知天的圣人境界,就需要加以存養之功,“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待存之既久,養之益熟,才能漸入化境,不待於勉强而自無不存,最終達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中庸》)的聖人境界。
陽明解“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一聯曰:
至於“夭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夭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個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個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 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個困勉的意在。(34)同上,第6頁。
在《答顧東橋書》中又進一步詳細論述曰:
至於“夭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夭壽不貳”,是猶以夭壽貳其心者也。猶以夭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夭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夭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今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35)王守仁《王陽明全集》,第49~50頁。
在陽明看來,“夭壽不貳”又是比“存心養性”低一等的修養工夫。“存心養性”雖與天爲二,但已見得有個天在面前,真知天命之所在,所以能一心於爲善以“事天”;而“夭壽不貳”乃是學者“猶以夭壽貳其心”,所以不能一心於爲善,以致不能真知天命之所在,故此聯乃是教學者知道,窮通夭壽自有命在,不可因此便把爲善的心變動(貳)了,吾人所能做的,只是一心於爲善,修身以俟天命罷了(36)陽明如此解“夭壽不貳”,乃純從工夫角度入手;實則“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亦是極高之修身境界。工夫與境界,本不可分,有“夭壽不貳”之工夫,方有“夭壽不貳”之境界。。故陽明將其歸諸“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
關於“夭壽不貳”,《傳録習(下)》還有一段錢德洪向陽明請教的問答:
問“夭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脱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37)王守仁《王陽明全集》,第123頁。
陽明所答,實是對其整個生命體驗與學術活動的總結概括。陽明一生學問的進益都是以其鮮活的生命體驗作支撑,都是在“夭壽不貳”的艱難困境中實現學問的飛躍。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與謫居龍場有關:“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爲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灑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38)同上,第1354頁。正是在生死存亡之際,於默坐澄心之中,陽明乃得此心之静一灑脱,終於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致良知則與宸濠之亂、忠泰之變有關。陽明自謂:“某於此良知之説,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説盡。”(39)王守仁《王陽明全集》,第1412頁。所謂“百死千難”,即是指宸濠之亂、忠泰之變。陽明經此生死患難,於動心忍性中,學問愈加精進,“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40)同上,第1411頁。,於是正式揭出“致良知”之教。
詹阜民嘗問象山曰:“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象山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41)陸九淵《陸九淵集》,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71頁。若象山,真可謂“學知利行”也;若陽明,素夭壽行乎夭壽,無入而不自得,真可謂“困知勉行”也。故陽明一再强調:“吾儕用工,卻須專心致志在‘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功夫之始。”(42)王守仁《王陽明全集》,第98頁。
就此三聯的關係而言,陽明在《答聶文蔚書(二)》中指出:
蓋盡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説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説“夭壽不貳,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裏做個求到盡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説“夭壽不貳,修身以俟”,而“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43)同上,第97頁。
爲什么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以及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間是這樣一種關系,陽明以“行路”爲喻,進行了一番形象的類比説明。他指出,盡心知性知天者,譬如壯健之人奔走於數千里之間;存心養性事天者,就像童稚學步於庭除之間;夭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則似襁褓之孩學習起立移步。奔走千里、步趨庭除與起立移步之間:
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則不必更使之於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牆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44)王守仁《王陽明全集》,第97~98頁。
這一類比形象地表明,在陽明看來這三聯之間是一種自下而上、上可涵下的關係。就自下而上而言,是説通過夭壽不貳,修身以俟的學者工夫,可逐漸上達,向着存心養性以事天的賢者工夫以及盡心知性以知天的聖人工夫升進,就像人們學習走路,襁褓之孩通過對起立移步的學習,可逐漸學會童稚的步趨庭除以及壯健之人的奔走往來於千里之間。就上可涵下而言,是説高層次的工夫,涵蓋着低層次的工夫,能做到盡心知性以知天的聖人工夫,則存心養性以事天的賢人工夫與夭壽不貳,修身以俟的學者工夫自在其中,能做到存心養性以事天的賢人工夫,則夭壽不貳,修身以俟的學者工夫也自在其中,就像壯健之人能够奔走於千里之間,必是早已學會了童稚的步趨庭除與襁褓之孩的起立移步,童稚能够學步於庭除之間,也必是早已學會了襁褓之孩的起立移步。
四、 對陽明此解之檢討反思
相對於朱子舊説而言,陽明此解可謂别開生面,且有相當之理據,故能自圓其説自成一家,但陽明此解亦並非全無問題,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就陽明在“知行合一”的立場下,將“盡心”一章每一聯對應於一種根器,比配爲“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三個等次而言,雖看似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實則取消了孟子此章在成德實踐中的普遍意義。若依陽明以根器對應工夫的思路,則孟子此章每一聯均可以三種根器對應三種工夫。就“盡心知性”一聯言,聖人是在生知安行中盡心知性,賢人是在學知利行中盡心知性,學者則是在困知勉行中盡心知性。就“存心養性”一聯言,聖人是在生知安行中存心養性,賢人是在學知利行中存心養性,學者則在是困知勉行中存心養性。就“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一聯言,聖人是在生知安行中夭壽不貳,修身以俟,賢人是在學知利行中夭壽不貳,修身以俟,學者則是在困知勉行中夭壽不貳,修身以俟。陽明在其比配框架下,只注意到此三聯因根器不同而導致工夫不同,卻忽略了每一聯亦有根器與工夫的不同。實則無論是聖人、賢人還是學者,都須做盡心知性、存心養性的工夫,都須在窮通夭壽中做修身不貳的工夫。在此問題上,牟宗三先生的説法最爲透澈,盡心知性、存心養性,“都是實踐的事,而且每一人都當如此實踐,聖人亦須如此,此是原則性的話。這尚説不到根器的問題,故不能以生知學知來比配。……下聯‘立命’更是一普遍原則,更不能以困知來比配”(45)牟宗三《圓善論》,第99~100頁。。陽明的失誤就在於,陷於比配框架之中,而忽視了此章對每個個體成德實踐的普遍意義。這是牟宗三先生所以對陽明此解極爲不滿的根本所在,也是陽明此解雖有相當之理據卻仍啓後人疑竇的原因所在。
第二,就“夭壽不貳”一聯而言,陽明對此聯的解釋實是其全幅生命體驗與學術活動的概括,可説是其此章解釋中最精彩的部分,但其將“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中“之”字解作“天命”,卻值得商榷。將此句中“之”字解作“天命”,非自陽明始,東漢趙岐即作此解曰:“修正其身,以待天命。”(46)焦循《孟子正義》,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878頁。且從陽明“知天”、“事天”、“俟天”之層級看,亦能自圓其説,但此聯“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明是指修身以俟“夭壽”之命,故此命乃“氣命”而非“天命”,只有在夭壽窮通、吉凶禍福這些所謂的氣命面前,不爲心動,不改常度,才能“立命”。所謂“立命”即挺立正命之意,此通下章而言:“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嚴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盡心上》)“盡其道而死者”,即所謂“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正命也”,即所謂“所以立命也”。此外,孟子亦明言“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孟子·盡心下》)。“行法”即無論夭壽均不貳其修身,“俟命”即修身以俟夭壽窮通之命(氣命)之降臨。
第三,就此三聯之關係而言,如前所述,陽明認爲是一種自下而上、上可涵下的關係,這也是不妥的。因爲這三聯所示,是一種普遍的成德實踐工夫,困知勉行之學者,亦可以且必須做存心養性、盡心知性之工夫,而不是只能做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工夫,學知利行之賢人,亦可以且必須做盡心知性之工夫,而不是只能做存心養性,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工夫,所以所謂的自下而上、上可涵下之關係其實是説不通的。此三聯之關係,可譬之爲: 盡心知性是“開疆拓土”;存心養性是“嬰城固守”;“夭壽不二,修身以俟”是“磨刀石”。就盡心知性一聯而言,陳澧解此章曰:“盡其心者,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知其性者,知仁、義、禮、智之性也。此僞孫疏之説,甚明確,不可以其僞而忽之也。仁、義、禮、智,皆由於‘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知性則知天也。”(47)陳澧《東塾讀書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頁。陳解簡明扼要,實得此章之旨。孟子此處所言“盡心”,即是擴充心之善端之意。在孟子的義理框架下,雖然就本體層面而言,本心即性(仁義禮智之性),但就現實層面而言,現實心與本心是有差距的,所以才需要盡心(現實心)以實現本心。在現實層面,人所具有的,只是本心或性之端,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四善端,我們要做的乃是“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孟子·公孫丑上》)。因此,此聯可譬之爲“開疆拓土”。就存心養性一聯而言,“存”與“去”(48)《孟子·離婁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亡”(49)《孟子·告子上》載孟子引孔子之言曰:“操則存,舍則亡。”、“放”(50)《孟子·告子上》:“放其心而不知求。”、“失”(51)《孟子·告子上》:“求則得之,舍則失之。”、“陷溺”(52)《孟子·告子上》:“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相對,“養”與“害”(53)《孟子·盡心上》:“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伐”(54)《孟子·盡心上》:“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梏”(55)《孟子·盡心上》:“梏之反復,則其夜氣不足以存。”、“戕賊”(56)《孟子·告子上》:“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相對。在孟子看來,“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離婁下》),這“幾希”之處,即是人所固有的本心即仁義禮智之性,因此,就價值層面而言,人必須存養其本心真性: 若存心養性,則可躋於聖賢;若放心害性,則淪爲禽獸。故此聯可譬之爲“嬰城固守”。就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一聯而言,窮通夭壽、吉凶禍福,是每一個人都需要面對的,小人或許會窮斯濫矣,但修德之君子則應該是君子固窮,做到修身不貳,即在窮通夭壽、吉凶禍福的氣命中,不要把盡心知性、存心養性的爲善之心變動了,挺立起自己的正命來,這就是《中庸》所説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故此聯可譬之爲“磨刀石”。
結 語
綜上所述,陽明在知行觀上倡“知行合一”之論,故不滿朱子對“盡心知性”一章所作的分知分行的詮釋,他以“知行合一”爲學術立場,注重學者的根器,在程子“聖人盡心知性”的啓發下,以《中庸》“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爲比配框架,展開其對“盡心知性”章的闡釋。在具體的闡釋過程中,既有心學一貫的心性是一的思想,亦有其深刻的生命體驗作支撑。因此,陽明對此章的闡釋,絶非賢者一時之糊塗,此種比配亦非全無意義,而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
陽明此解最大的問題在於,陷於比配框架而使之失去了在成德實踐中的普遍意義:“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此絶非聖賢之事,乃是成德實踐中之普遍原則,是每個人都須依此而行之實踐工夫;“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亦非學者之事,而是每個人在成德實踐中都必須面對之氣命。此外“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三聯,並非是自下而上、上可涵下的關係,而是“開疆拓土”、“嬰城固守”與“磨刀石”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