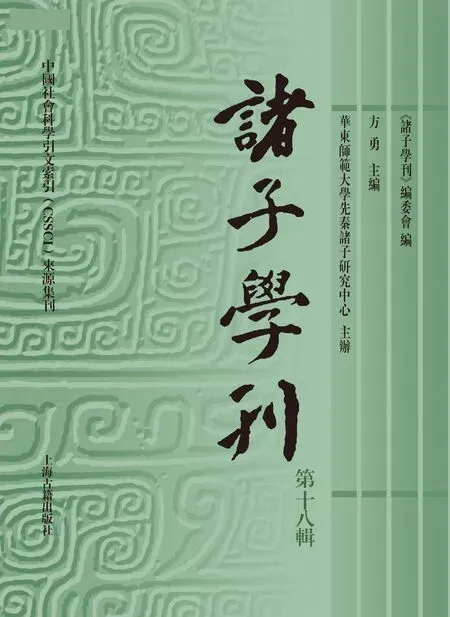梁啓超與章太炎論諸子流派之比較*
王 誠
内容提要 梁啓超和章太炎在民國諸子學研究中起了開創和引領的作用。梁、章對於諸子流派的論述吸收了近代學術的理念和方法,融入了對先秦思想的把握和理解。本文對梁、章早期和後期論諸子流派作了較爲細緻、全面的比較,從中梳理先秦諸子的源流,並由此探尋二人治學理路、學術觀點的異同,最後簡述了他們對其後諸子研究的示範和啓發。
關鍵詞 梁啓超 章太炎 諸子 流派 比較
清末社會政治、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諸子學在這樣的背景下復興。梁啓超和章太炎兩位學界巨擘引領了民國諸子學研究的開展,他們的諸子研究各具特色,均有開創意義,帶給後來的學者以深刻的影響。
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講論諸子,當先分疏諸子流别”(1)章太炎《諸子學略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頁。。諸子學的基礎,或者説先秦學術史研究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對諸子源流、派别的研究和考辨。《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韓非子·顯學》《淮南子·要略》、司馬談《論六家要指》等記録了古人對諸子流派的認識和分類,尤以本於劉歆《七略》的《漢書·藝文志》記載最詳,爲梁、章研究之所本。但梁啓超、章太炎論述諸子流派吸收了近代學術的理念和方法,融入了個人對先秦思想的理解,因此,比較梁、章之論不但有助於認識先秦諸子的源流,而且可以探尋兩位大師治學理路、學術觀點的異同。
一、 梁、章早期論諸子流派之比較
梁啓超與章太炎的學術觀點存在較大差異,甚至截然對峙,但兩人有個共同點,即思想都曾經歷較爲顯著的發展演變,至少可以明確劃分爲早期與後期兩個階段,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變動時代的影響。梁、章論述諸子流派,早期和後期也有明顯的區别。下面先分别介紹兩人早期對諸子流派的論述,然後比較兩人觀點的異同。
(一) 梁啓超早期論諸子流派
梁啓超早期對諸子流派的研究主要見於《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該書在分析了周末學術思想勃興的原因之後,專門論述先秦諸家的派别。梁氏的史學研究深受“地理環境論”的影響,這充分體現在他對先秦學派的劃分上,甚至可以説,他的諸家派别之論就是“地理環境論”的實踐。他明確提出“欲知先秦學派之真相,則南、北兩分潮,最當注意者也”,並根據“凡人群第一期之進化,必依河流而起”的通理,認爲“黄河、揚子江兩大流,其位置、性質各殊,故各自有其本來之文明,爲獨立發達之觀”(2)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頁。。由於地理環境的差别,南北的學術思想具有不同的特點。北方氣候寒冷,土地貧瘠,謀生不易,故其學術思想“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梁啓超將北學的精神概括爲:“則古昔,稱先王;内其國,外夷狄;重禮文,系親愛;守法律,畏天命。”南方氣候温和,土地豐饒,謀生較易,故其學術思想反之,南學的精神可概括爲:“探玄理,出世界;齊物我,平階級;輕私愛,厭繁文;明自然,順本性。”(3)同上,第25~26頁。
據此,先秦學派可分爲南北兩派,“北之開化先於南,故支派亦獨多”(4)同上,第29頁。,梁啓超又依地理位置析北派爲四: 以孔子、孟子、荀卿爲代表的鄒魯派,以管子、鄒衍爲代表的齊派,以申不害、商鞅、韓非爲代表的秦晉派和以墨翟、鄧析、惠施爲代表的宋鄭派。孔子和老子分别爲南北兩派之雄,而墨子生於宋,宋居南北要衝,所以梁啓超認爲墨子雖屬北派,有“務實際、貴力行”的精神,但同時受南學的影響,故“多言天鬼”,“力主兼愛,首倡平等”。他還具體分析了環境、地勢、民風及地理位置與其地學術思想的關係。例如,齊國接海,視界開闊,所以能産生《管子》中所反映的國家思想和鄒衍一派陰陽家閎大的世界觀。又如,秦地“控山谷之險”,而且“民族强悍”,所以國家主義最易發達。再如,名家之言“繁重博雜似北學”,“推理俶詭似南學”,所以必起於中樞之地如宋、鄭者。由此梁啓超慨歎道:“地理與文明之關係,其密切而不可易,有如此者,豈不奇哉!”(5)同上。可見“地理環境論”對其影響之深。
在空間分布的視角之外,梁啓超還運用時間的維度,把先秦學術全盛時代分爲四期: 第一期即南北分潮,兩派中分天下,孔、老各自爲魁;第二期孔、老、墨三分天下;第三期北派分支陰陽家、法家、名家蔚爲大觀,巍然獨立;第四期爲戰國之末的混合時代。
(二) 章太炎早期論諸子流派
章太炎早期對諸子的觀點集中反映於《諸子學略説》以及《訄書》《國故論衡》的若干篇章。《訄書》是章氏的第一部自選論文集,初刻本共收論文五十篇,最早的一篇作於1894年,最晚一篇完稿於1900年。《諸子學略説》是1906年章氏在東京爲國學講習會所編的講義,同年發表於《國粹學報》。《國故論衡》是章氏關於中國語言、文學和哲學的概論性著作,於1910年初刊行於日本。章太炎認爲“中國之學,其失不在支離,而在汗漫”,他推崇先秦諸子的學術,提出諸子學雖“非專限於周秦”,“而必以周秦爲主”,原因就在於“周秦諸子,推迹古初,承受師法,各爲獨立,無援引、攀援之事,雖同在一家者,猶且矜己自貴,不相通融”,“既立一宗,則必自堅其説”(6)章太炎《諸子學略説》,第1~2頁。。
章太炎論諸子十家,注重各派思想源流的梳理和同異、通别的比較,他認爲:“儒、道本同源而異流,與雜家、縱横家合爲一類,墨家、陰陽家爲一類,農家、小説家爲一類,法家、名家各自獨立,特有其相通者。”(7)同上,第24頁。在儒、道淵源上,章太炎持“孔學本出於老”的觀點,因爲“孔子問禮老聃,卒以删定六藝,而儒家亦自此萌芽”(8)同上,第3頁。,“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敗禍福之事悉在人謀,故能排斥鬼神”,而孔子也説“敬鬼神而遠之”,所以道家不崇信鬼神,“爲儒家之先導”(9)同上,第7~8頁。。他還認爲,老子多權術,並以其授之孔子,而孔子又詐取徵藏故書,所以“孔子之權術,乃有過於老子者”(10)同上,第9頁。。爲反對康有爲的尊孔,章太炎在《諸子學略説》中極力貶損孔子,稱“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禄爲心”(11)同上,第5頁。,甚至指其爲人忌刻,心術不良,這些顯然是借學術論政治的意氣之言。在《國故論衡·原道上》中,章氏依然持“儒家、法家皆出於道”的觀點,認爲“儒家、道家、法家異也,有其同”,“儒、法者流,削小老氏以爲省,終之其殊在量,非在質也”(12)同上,第96頁。。《檢論·道本》闡述老聃“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托天下”,依章太炎看來,“仲尼所謂忠恕,亦從是出也”(13)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0頁。。《檢論》是《訄書》的修訂本,改定於1915年,可見此時他還主張孔學出於老。包括1922年根據章氏上海國學講演記録的《國學概論》中也提到,儒、道兩家本是同源,後來才分離,兩家“政治主張略有異同”,但“其殊在量,非在質也”(14)章太炎《國學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頁。。但是,章太炎1935年在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講“諸子略説”,卻没有説儒、道的關係(只提及老子贈言孔子“毋以有己”),大概章氏晚年提倡尊孔讀經,重在提升儒家的地位,所以在《諸子略説》中儒家部分也論述得最爲詳細。因此,由早期提出儒源於道,到晚年不提儒道淵源,個中原委應該和章太炎由批孔到尊孔的思想變化有關,而這一變化又和政治形勢、社會思潮緊密相連。
章太炎早期將儒、道“與雜家、縱横家合爲一類”,特别指出“儒家者流,熱衷趨利,故未有不兼縱横者”,“儒家不兼縱横,則不能取富貴”,並認爲“孔子干七十二君,已開游説之端”(15)章太炎《諸子學略説》,第13、14、6頁。。墨家和陰陽家爲一類,墨家是古宗教家,而“陰陽家亦屬宗教”,不過“墨家言宗教,以善惡爲禍福之標準,陰陽家言宗教,以趨避爲禍福之標準,此其所以異也”(16)同上,第12頁。。章太炎認爲農家不單單是教授農耕、種植技術,“若農家止於如此,則不妨歸之方技”,他根據《漢書·藝文志》所述“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指出許行所謂神農之言,即“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是農家的一種主張,又認爲《韓非子·顯學》“與貧窮地,以實無資”相當於近世的均地主義(17)同上,第23頁。。可見,農家的立場基於勞動人民。而小説家的“街談巷議,所以有益於民俗”,故可看作“芻蕘之議”,也是站在普通民衆的立場,可能由於這個原因,章太炎將農家和小説家歸爲一類。
(三) 梁、章觀點異同之比較
將梁啓超與章太炎早期對諸子流派的論述作比較,可以發現兩人的觀點和主張有同有異。關於諸子學術的起源問題,梁、章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皆主“諸子出於王官”説。梁啓超認爲春秋以前的王官之學爲其後的學術發展奠定了基礎。章太炎則特别强調“仕”和“學”的關係,指出“仕”與“學”在當時是一而非二。在先秦學派和地理環境的關聯方面,章太炎雖然不像梁啓超那樣有專門、系統的論述,但也有同樣的認識和類似的觀點,例如他在《國故論衡·原學》中舉到,“山東多平原大壇,故鄒魯善頌禮。關中四塞便騎射,故秦隴多兵家;海上蜃氣象城闕樓櫓,怳變眩,五勝怪迂之變在齊稷下: 因也,地齊使然。”(18)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頁。可見,他認爲儒家出於山東,兵家盛於秦隴,陰陽家在齊國,都是由地理環境因素決定的。
梁、章對於諸子流派的獨立性有不同的看法。通過與希臘、印度學派的比較,梁啓超批評先秦學派的短處,其中一條就是“師法家數之界太嚴”,在他看來,先秦學者“守一先生之説,則兢兢焉不敢出入,不敢增損。稍有異議,近焉者則曰背師,遠焉者則曰非聖,行將不容於天下矣”(19)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39頁。。因此,中國學術的陵夷衰微實應歸咎於此。然而,章太炎卻以講究師法家數爲先秦學術的特色和優長,而對於後代之學則責其失在汗漫,他指出“漢武以後定一尊於孔子”,學者“强相援引,妄爲皮傅,愈調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會者愈違其解故”(20)章太炎《諸子學略説》,第1頁。。有意思的是,對《韓非子·顯學》所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的事實,梁啓超認爲弟子“得其師之一體,而又不敢有所異同增損”,所以其後不曾有“能青於藍而寒於水者”(21)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40頁。,而章太炎則從中看到“當時學者,惟以師説爲宗,小有異同,便不相附”,由此推崇“古學之獨立”。在論及雜家時,章太炎説其“彼此異論”,“言各異指”,“以一人爲之,則漫羨無所歸心”,“以一人之言而矛盾自陷,俛仰異趨,則學術自此衰矣”,他引章學誠《文史通義》的説法,謂“近人著作,無專門可歸者,率以儒家、雜家爲蛇龍之菹”,對學術的汗漫與思想的調和提出了批評(22)章太炎《諸子學略説》,第2、23頁。。
不過,守師法是一事,兼學他派又是一事。梁、章都注意到各派有異也有同,正如梁啓超所論述的,“諸派之初起,皆各樹一幟,不相雜廁;及其末流,則互相辯論,互相薰染,往往與其初祖之學説相出入,而旁采他派之所長以修補之。”他列舉了混合時代學界大勢的四種現象: 内分、外布、出入、旁羅。“所謂旁羅者,當時諸派大師,往往兼學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23)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26~27頁。如儒家的荀子兼治名家、法家言,道家的莊子兼治儒家言,法家的韓非兼治道家言。章太炎也説“孔子受業於徵藏史,韓非傳其書,儒家、道家、法家異也,有其同”(24)章太炎《國故論衡》,第107頁。,又認爲法家略有二種,“其一爲術,其一爲法”,“爲術者,則與道家相近;爲法者,則與道家相反”。在他看來,“儒家多兼縱横,法家多兼名,此表裏一體,互爲經緯者也”,而告子兼學儒、墨,“進退失據,兩無所容”,則被他當作“調和者之戒”(25)章太炎《諸子學略説》,第15、4頁。。
二、 梁、章後期論諸子流派之比較
梁啓超在1920年歐遊歸國後的十年時間對諸子學説作了更深入的研究,這一時期他對諸子流派的觀點也有進一步的發展。比如,他對先秦儒家思想的分化發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爲“孔子死後,門弟子析爲二派: 一派注重外觀的典章文物,以有若、子夏、子游、子張爲代表;一派注重内省的身心修養,以曾參、子思、孟子爲代表”(26)梁啓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百三》,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1頁。。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一書中他對先秦思想的四大主要流派儒、道、墨、法做了詳細論述和評價,其中對於四家發生及成立年代,他認爲“儒家爲傳統的學派,成立最早;道家……最早亦當在儒家後,遲或竟在墨家後;墨家成立,確在儒家後、法家前;法家發生甚早或竟在儒家前,而成立則在彼三家後”(27)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70頁。。
梁啓超指出先秦政治思想有四大潮流,“一無治主義,二人治主義,三禮治主義,四法治主義”,並把四潮流分配四家,從而對四大流派的政治思想作了比較: 無治主義,即無政府主義,是道家所獨倡,而農家許行一派爲道家支流;禮治主義,是儒家所獨有,但儒家實是人治、禮治並重;人治主義,是儒家、墨家共同的,但墨家的末流也趨到法治;法治主義最晚出、最進步,法家的學説可以説是將道、儒、墨三家之説鎔鑄而成。但在分析四家之異的同時,梁啓超也講了各家共通的幾點,包括“中國人深信宇宙間有一定的自然法則,把這些法則適用到政治,便是最圓滿的理想政治”,“君位神授,君權無限”,中國人對於國家性質和政治目的没有徹底的發明,“中國人説政治,總以天下爲最高目的”。由此可見,梁啓超是以人類全體文化、世界政治思想爲背景來考察先秦政治思想的,他致力於先秦學術的研究,是爲了回答“中國在全人類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置耶”的問題,他心目中的中國學術是“以研究人類現世生活之理法爲中心”的,所以無論何時代何宗派之著述都歸結於回答“人生哲學及政治哲學所包含之諸問題”(28)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211、215、3頁。。以此爲出發點,梁啓超不但對先秦各流派思想進行比較,而且還援引西方、印度的思想文化爲參照作中外的比較。
章太炎後期對諸子流派的論述主要見於《諸子略説》,這是1935年底至1936年初他在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講演諸子學的記録,比早年的《諸子學略説》要詳細、深入得多,可以説是其諸子學研究的總結。他首先將《莊子·天下》《漢書·藝文志》等四篇論諸子流别之文作了比較和説明,並主要依據《藝文志》論九流大旨。和梁啓超一樣,章太炎也注意到諸子的先後,這一問題司馬遷、劉向、班固都未曾論及,《淮南子》所述則先後倒置,“不足以考時代”,因此他對戰國諸家排了大致的先後:“儒家宗師仲尼,道家傳於老子,此爲最先”,墨子在孔子之後,“去孔子亦四五十年矣”,同時將《墨子·經説》視爲“别墨所傳,又出墨子之後”,“法家李悝,當魏文侯時;名家尹文,當齊宣王時;陰陽家鄒衍,當齊湣王、燕昭王時,皆稍稍晚出”,“縱横家蘇秦,當周顯王時;小説家淳于髡,當梁惠王時”,二者“與孟子並世”(29)章太炎《諸子學略説》,第29頁。。
關於諸子各家的先後,梁、章的意見不一致之處在於道家。梁啓超對道家成立年代存疑,認爲“最早不能在孔子以前,最晚不能在莊子以後”,但又説“莊子年代亦難確考”(30)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71頁。。章太炎則沿用傳統的觀點,即“老子生春秋之世”,孔子生春秋之末,故與老子大致同時。此外,章太炎重視學派的溯源,認爲諸子各派可“上徵於春秋之世”,即在春秋時期已具雛形,他將晏子歸爲儒家,管子歸爲道家,魯之臧氏近於墨家,又言“儒家著書在後,道墨著書在前”,“道家之出史官,墨家之出清廟之守,確爲事實”,認爲老子本於周之太史辛甲,墨子本於清廟之守尹佚。他還指出“師服之論名,即名家之發端”,“子産之鑄刑書,得法家之大本”,同時子産“存鄭於晉楚之間”,故又類縱横家,而“燭之武之退秦師,是純爲縱横家”,“梓慎、裨灶皆知天道,是純爲陰陽家”,“蔡墨之述畜龍,蓋近於小説矣”。只有農家和雜家“不見於春秋”(31)章太炎《諸子學略説》,第56、73、9頁。。梁啓超則僅提到法家的“法治思想”起源甚早,認爲“管仲、子産時確已萌芽”(32)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44頁。。
如果説梁啓超側重於政治主張,采用當時西方的政治觀念來比較先秦各派的思想,那麽章太炎在詳論儒、道、墨、法、名五家之時,則常以他所熟悉的佛學,特别是唯識學思想來比附和評判。這一點在早期的《諸子學略説》中已有體現,如論名家,舉荀子《正名》“緣天官”,他説“中土書籍少言緣者,故當徵之佛書”,從而用佛教的四緣、心所等概念來解説,又如論墨家,則用佛教的因明來解《墨經》。而在《諸子略説》中他進一步以佛學來評判儒家、道家諸派,將儒家的“克己”,孔子言“無知”、“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解釋爲破我執,認爲孔子“人我、法我俱盡”。他將子思比擬爲“中國之婆羅門”,將其學歸爲佛法中的“天趣”,即超出人格而不能斷滅,又認爲“孟子之學高於子思”,可歸數論派,因爲孟子“由色界而入無色界天”,但由於“有神我之見在”,故“較孔、顔爲不逮”。他還以佛教的阿賴耶識及四煩惱(我見、我癡、我愛、我慢)來評判孟子性善、荀子性惡之論。至於道家,章太炎認爲老子之道不但無我,而且能破所知障,而莊子則有近乎佛家輪回之説,此爲老子所無,同時又能够破除空間和時間的觀念,從而“證知不死不生”,而老子“但論攝生,而不及不死不生”(33)章太炎《諸子學略説》,第19、33、34、64頁。。章太炎於佛教法相宗深有研究,故能結合唯識學理論對儒、道兩家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境界作出評價,似爲牽合卻又頗有道理,很像南北朝、隋唐佛教的判教。
梁、章都論及孟子與荀子的異同。清末梁啓超與夏曾佑、譚嗣同曾發起“排荀運動”,推崇孔、孟,貶黜荀子,1898年他在《讀〈孟子〉界説》一文中提出,“孟子言性善,爲大同之極效”,而“荀子爲小康之學者,則必言性惡”,在“論諸子之派别”中他更是指斥荀子爲“儒家中最狹隘者”,“崇本師以拒外道”,“尊小宗而忘大宗”,甚至把李斯坑儒之禍也追究到荀子身上(34)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18頁。。但後期他對孟、荀的比較則較爲平實,指出二者“政治論之歸宿點全同,而出發點則小異”,“孟子信性善,故注重精神上之擴充;荀子信性惡,故注重物質上之調劑”(35)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00頁。。章太炎反對今文家,持“尊荀”立場,不過又能看到孟、荀二人各自所長,他既以孟子入天趣,能“超出人格”,甚至以爲思、孟五行之説近於陰陽家(此因不知五行謂何而誤解),又指出“荀子語語平實,但務修己治人,不求高遠”,“最反對言天”,故“不備超出人格,但有人趣”。在他看來,“以政治規模立論,荀子較孟子爲高”,“荀子明施政之術,孟子僅言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而已”,孟子“於五霸甚爲輕蔑”,荀子則能知其長處。此外,章太炎還分析了孟、荀性善、性惡之辨的原因,其一是“荀子隆禮樂而殺《詩》《書》,孟子則長於《詩》《書》,孟子由詩入,荀子由禮入,詩以道性情,故云人性本善,禮以立節制,故云人性本惡”;其二由於兩人生長、生活的環境不同,孟子生活於鄒魯,其地儒者習禮讓,多善人,而荀子長於燕趙,其地人習凶暴,多惡人,孟子受母之教,而荀子“幼時教育殆不如孟子”(36)章太炎《諸子學略説》,第34、38、37頁。。
對於法家的來源,梁、章都有具體論述。梁啓超認爲法家“學理上之根基,則儒道墨三家皆各有一部分爲之先導”: 儒家言正名定分,“勢必以禮數區别之”,故荀子言禮“幾與狹義之法無甚差别”,“韓非以荀子弟子而爲法家大師”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墨家“以尚同爲教”,務“壹同天下之義”,所以法是最必要的;名與法亦不可離,後世言法者亦號“刑名”。所以説法家是“儒、道、墨三家之末流嬗變匯合而成者”(37)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44、146頁。。章太炎則主張“法家者,道家之别子”,“韓非解老、喻老而成法家”,但又强調法家有兩派,一派以法爲主,一派以術爲主,前者出於理官,後者出於道家,二者絶異。在他看來,辛伯(辛甲之後)和管子都是由道家而入法家,而老子則是“道家、法家之樞轉”(38)章太炎《諸子學略説》,第79頁。。
三、 梁、章論諸子流派的影響
梁啓超和章太炎對於諸子流派的論述,一方面繼承了漢代以來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反映出近代學術的理念和方法,同時還融入了各自獨到的觀點和詮釋。其中有值得後人吸取的真知灼見,更有值得借鑒的研究思路。如梁啓超早期運用“地理環境論”劃分先秦學派,找出決定各派異同的環境因素,後期采用近代西方政治觀念來比較先秦各派思想,皆創出諸子學研究的新路,他對先秦學術全盛時代的分期也爲後來的研究奠定了基礎。而章太炎早期論諸子十家,比較各派思想源流的同異、通别,其中不乏頗具啓發性的精彩觀點,後期用佛學法相唯識思想來評判儒家、道家諸派,也爲諸子研究帶來新的視角。當然,由於時代思潮的影響和個人因素,梁、章關於諸子流派也有不盡客觀的認識和主張。如章太炎在儒、道淵源問題上,前後觀點不一致,以對孔子的不同態度而轉移,而梁啓超早期推崇孔孟、貶黜荀子也頗多意氣,有失公允。又如梁、章關於諸子各家先後的意見相對粗疏,缺乏確鑿的考證,尚待其後的研究者進一步探討。
總體來看,梁啓超、章太炎具有開創性的諸子學研究對後來的研究者有較大的影響。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曾説:“到章太炎才於校勘訓詁的諸子學之外,别出一種有條理系統的諸子學。”(39)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版,第30頁。同時,在《四十自述》中胡適又回憶了梁啓超對他的影響,特别是《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對他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啓發意義。梁、章對於諸子流派的觀點互有異同,皆爲後人作出示範、帶來啓示。例如,梁啓超闡發了學術思想受地理環境因素影響的觀點,並主要依據地理位置來劃分先秦學派,章太炎也注意到學派和地理環境的關聯。後來,傅斯年的《戰國諸子之地方性》繼承了這一觀點,但又有所修正和發展。他批評説,“近人有以南北混分諸子者,其説極不可通”(40)傅斯年《傅斯年“戰國子家”與〈史記〉講義》,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頁。,顯然是針對梁啓超的“先秦學派南北兩分潮”而言的,他提出“論諸子之地方性,但以國别爲限不以南北西東等泛詞爲别”,他例舉了齊(燕附)、魯、宋、三晉及周鄭、南國、秦國六個地方的學派及其思想,其實質和梁、章的主要觀點並無二致,不過他對齊國分析得尤爲細緻。又如,章太炎主張“諸子出於王官”説,梁啓超也並不反對《藝文志》關於諸子起源的推論,但值得注意的是,後者又説“《藝文志》亦非能知學派之真相者也”,隨後列舉了“諸子略”的四點瑕疵(41)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18頁。。後來胡適作《諸子不出於王官論》,一方面當然是讀了《諸子學略説》後針對章氏的觀點提出反駁,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認《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梁氏的意見對他的啓發。再如,儘管學術觀點有所不同,但錢穆治諸子學毫無疑問也深受梁、章的影響,他在《國學概論》“最近期之學術思想”一章中,就將章太炎、胡適和梁啓超視爲當時治先秦諸經與諸子的主要人物,而他1929年開始寫作《先秦諸子繫年》更是直接受他們的啓發,在這部著作中錢穆將先秦學術史分爲“初萌”、“醖釀”、“磅礴”、“歸宿”四期,很容易讓人想起梁啓超的先秦學術全盛時代四期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