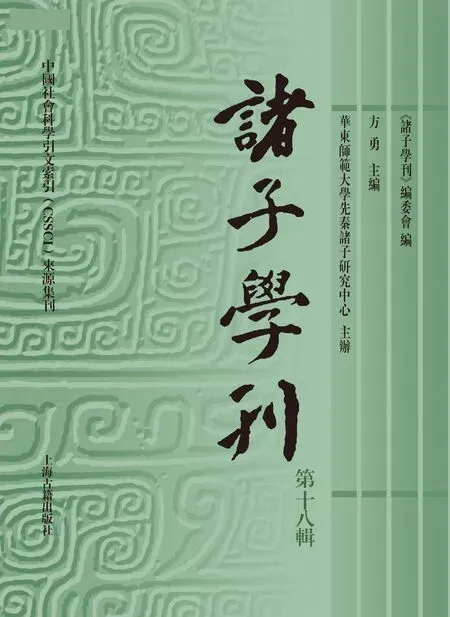論《劉子》對道家學説之承繼與取捨
(香港) 梁德華
内容提要 所謂“雜家”之學,就是把不同學派的學説作出綜合與取捨,以用於治道之中,從而形成其學説體系。成於魏晉時期的《劉子》,無論在結構或學説上都遠承《吕氏春秋》《淮南子》兩書,實爲《漢志》“雜家”的接續者,然而較諸《吕》《淮》兩書,鮮有學者討論《劉子》對諸子學説之取捨。考《劉子》一書以綜合儒、道兩家思想爲要,並在綜合的過程中,對儒、道學説作出篩選、轉化以形成其主張。本文擬仔細分析《劉子》如何承繼道家的思想,並指出《劉子》在吸收道家主張的同時,亦對其學説作出嚴格的取捨,並進而推論其取捨之原因,以見《劉子》兼融並包而無所牴牾的學術特點。
關鍵詞 劉子 道家 雜家 儒道互補
“雜家”之名首見於《漢書·藝文志》,其中除《吕氏春秋》《淮南子》外,均無全帙存世。過去有學者認爲“雜家”並無中心思想,而只是把不同的學説生硬地拼合,故多對“雜家”作出負面批評,以爲“雜家”不成一家,實不能與儒、道等學派並列(1)如蔣伯潛《諸子通考》云:“雜家兼采各家之説,故名之曰‘雜’。《漢志》所錄雜家之書,以《吕氏春秋》與《淮南子》爲最著。此二書皆成於門客之手,非吕不韋、劉安所自著,作者非一人,宜其雜矣。雖然,專門乃可名家,家而曰‘雜’,實爲不詞。”見蔣伯潛《諸子通考》,臺灣中正書局1948年版,第17頁。又如謝无量《中國哲學史》云:“《漢志》以爲兼儒、墨,合名、法謂之雜家,蓋其言雜取古説,不能自樹爲一宗也。”見謝无量《中國哲學史》第一編下,上海中華書局1928年版,第93頁。。這種見解,顯然與《漢志》對“雜家”的理解並不相同。《漢志》云:“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2)班固《漢書·藝文志》,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42頁。可見“雜家”之學,就是把不同學派的學説作出綜合與取捨,以用於王治之中,從而形成自身的學説體系。
現代不少學者都曾對《吕氏春秋》《淮南子》兩書如何吸收、轉化諸子學説作出研究,如傅武光《吕氏春秋與諸子之關係》仔細分析了《吕氏春秋》對儒、道等各家學説的取捨,以明《吕氏春秋》學説的結構(3)傅武光《吕氏春秋與諸子之關係》,臺灣私立東吴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93年版。。另外,孫紀文《淮南子研究》亦對《淮南子》整合諸子的具體情況作出深入的討論(4)孫紀文《淮南子研究》,學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220頁。。成於魏晉時期的《劉子》,無論在結構或學説上都遠承《吕》《淮》兩書,實爲《漢志》“雜家”的接續者,然而較諸《吕覽》《淮南》,鮮有學者討論其學説組織。相關的研究成果,如江建俊《從〈劉子〉看劉晝融合儒、道、法的思想》只概述《劉子》對儒、道、法三家之吸收(5)江建俊《從〈劉子〉看劉晝融合儒、道、法的思想》,《成大中文學報》,1997年第5期,第331~351頁。,又周振甫《〈劉子〉與〈文心雕龍〉思想的差異》認爲《劉子》學説前後矛盾之處甚多(6)周振甫《〈劉子〉與〈文心雕龍〉思想的差異》,《中華文史論叢》,1986年第40輯,第119~128頁。,而陳志平《劉子研究》亦指出《劉子》在融合儒、道思想時産生了矛盾(7)陳志平《劉子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頁。。可見以上三位學者均未有注意《劉子》對諸子學説之取捨。其實,《劉子》一書以綜合不同學派之思想爲要,在綜合的過程中,對不同的學説作出篩選、轉化以形成其系統。本文擬仔細分析《劉子》如何承繼道家的思想,並指出《劉子》在吸收道家主張的同時,亦對其學説作出取捨,並嘗試説明其取捨之原因,以見雜家兼融並包而無牴牾的學術特點。
一、 《劉子》對道家學説之承繼
(一) 《劉子》對道的認識
不少學者已指出《吕氏春秋》及《淮南》等“雜家”典籍均取道家之道論作爲其學説基礎(8)可參考牟鍾鑒《吕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齊魯書社1987年版,第33~34頁。。而《劉子》對道之描寫,亦一如《吕覽》《淮南》,有道家論道的特點。《劉子·崇學》云:“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形無以測其奥。道象之妙,非言不傳;傳言之妙,非學不精。”(9)傅亞庶《劉子校釋》,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36頁。孫楷第云:“‘大象無形’,即《詮言訓》所謂‘大道無形’。……是‘大象’即‘至道’,言象者,互文耳。”(10)王叔岷《劉子集證》,收入《王叔岷著作集》,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7頁。可知《劉子》以爲大道無言無形,與《老子》四十一章“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相應(11)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28頁。。而《妄瑕》云:“大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響求,不得以毁譽稱也。”(12)傅亞庶《劉子校釋》,第259頁。則指出了道無形、不可聞見之特點,這些都是道家論道的説法。考諸《吕覽》《淮南》亦有相類的描寫,如《吕氏春秋·大樂》:“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爲狀。”(13)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第一册,巴蜀書社2002年版,第506頁。《淮南·原道》亦云:“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14)陳廣忠《淮南子斠詮》,黄山書社2008年版,第31頁。可見《劉子》《吕氏》《淮南》三書均承繼道家對道之描述。
然《劉子》以爲道“非立言無以明其理”,“非立形無以測其奥”,與《老》《莊》之道論亦有差異,如《莊子·知北遊》云:“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15)王叔岷《莊子校詮》,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年版,第837頁。可見《莊子》以爲道不可言、不可形。故此,《劉子》雖吸收老莊之道無言、無形之特點,然而卻亦指出道可靠言、形傳達,以帶出崇學的主旨,這是《劉子》變化道家學説之處,並由此吸納儒家重學之主張,達至儒、道互補,此點將詳論於下文。而《劉子》對道有這樣的認識或是受到魏晉學者的影響(16)《劉子》對道有此認識或是受到魏晉學者的影響,魏晉時期玄學家經常討論“言意之辯”,其中一派以爲言可盡意,如歐陽建《言盡意論》云:“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言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則歐陽建認爲人必須通過言、名才能宣志、辯物,參考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2~506頁。故此,《劉子》之道論取於道家,以道爲體,而認爲可以透過言、象明道,亦承魏晉玄學思想而來。。
(二) 《劉子》對道家修養論之吸收
《劉子》首四篇爲《清神》《防慾》《去情》《韜光》皆發揮道家修養之説。《劉子》這樣的安排,一方面反映其作者對道家全性學説之重視;另一方面,可能是受到《吕氏春秋》的影響。《吕氏春秋》分爲《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一百六篇。而《十二紀》是全書思想的中心,《序意》云:“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17)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第二册,第1211頁。因《吕氏春秋》認爲春季乃萬物生長之始,故春紀三篇所録的篇章多重於貴生、養生之説,如《孟春紀》首二篇爲《本生》《重己》,而《仲春紀》首二篇爲《貴生》《情欲》,反映《吕氏春秋》非常重視養生全性之工夫。而《劉子》首四篇皆在論述養生之旨,且多吸收《吕覽》《淮南》修養學説的内容,反映前代雜家典籍對《劉子》之影響。
《劉子》首篇爲《清神》,旨在論述清静精神之要。《清神》云:“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指出了形、心、神三者互相依存的關係,而“神”爲心、形之本,故“神静而心和,心和而形全。……將全其形,先在理神。”(18)傅亞庶《劉子校釋》,第1頁。指出如能保持精神清明,則可令形體全足。整篇《清神》都强調内心必須清虚,並注重物欲對精神的負面影響,其云:“神照則垢滅,形静則神清。垢滅則内欲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19)傅亞庶《劉子校釋》,第1頁。以爲人若能清明精神,則能減低心中的欲念。而《清神》亦言:“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搴正性,況萬物之衆以拔擢而能清心神哉!故萬人彎弧,以嚮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20)同上。此語出於《吕氏春秋·本生》(21)《吕氏春秋·孟春紀·本生》:“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見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第一册,第63~65頁。,可知《劉子》承繼《吕覽》之主張,以爲外物對生命有其負面影響。且《劉子》以爲人要效法聖人才能全性,其云:“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静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德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忘貧,故厚利不能傾。”(22)傅亞庶《劉子校釋》,第2頁。此語見於《淮南子·精神》《詮言》以及《文子·九守》等篇(23)《淮南子·精神》:“清目而不以視,静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見陳廣忠《淮南子斠詮》,第334頁。《淮南子·詮言》云:“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見陳廣忠《淮南子斠詮》,第789頁。《文子·九守》:“清目不視,静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見李定生、徐慧君《文子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頁。,可見《劉子》取用道家修身之觀點,以爲人應保持性情的自然狀態,並放下世俗的牽動,令精神完足,才能不爲外物擾亂。準上可見,《劉子》對精神之重視,而講求精神全足亦是魏晉玄學的重點,如嵇康《養生論》云:“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24)《嵇中散集》,《四部叢刊》本,卷三,頁三下。可見嵇康亦以爲形神關係密切,主張養生當以養神爲主,並以呼吸吐納等法爲輔,與《劉子》純以清静精神之主張不同,然兩者皆以精神爲要,反映當時着重精神清明的風氣。
道家亦着重物欲與性情的關係,如《老子》六十四章云:“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25)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第309頁。《莊子·徐无鬼》則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26)王叔岷《莊子校詮》,第917頁。可見道家以爲貪欲能侵害性情。《劉子·防慾》承上述主張,進一步論述慾念對性情之影響,《防慾》云:“人之稟氣,必有性情。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27)傅亞庶《劉子校釋》,第10頁。《劉子》以爲“性情”是由人出生開始已經存在,傅亞庶認爲《劉子》此“性”是指“人先天稟賦所得之性”,而其“情”是指“性爲外物影響所生喜怒哀樂之情”(28)同上,第12頁。。若此,《劉子》對“性”之理解,與《荀子》有相似之處,《荀子·正名》云:“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29)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412頁。又下文云:“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30)同上,第428頁。《劉子》以爲“情”由“慾”而安,與《荀子》“欲”乃“情”之應的説法尤合。《荀子·性惡》云:“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争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争奪,合於犯(分)〔文〕亂理而歸於暴。”(31)同上,第434~435頁。俞樾以爲“犯分”當作“犯文”,今據改,詳見王先謙《荀子集解》,第435頁。可見《荀子》亦以爲若順人之性情而無節制,則社會易生混亂。而《荀子》視“欲”爲人天生已有,是由性、情而來,兩者没有矛盾關係,故荀子不主張消除所有欲念,而應從禮義去調節人的欲求,以免造成禍患。《劉子》則以爲“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慾之妨情,猶煙冰之與水火也”(32)傅亞庶《劉子校釋》,第10頁。,可見《劉子》把“性”、“情”、“慾”看成相對立的關係,“慾”影響“情”,“情”則影響“性”,故《劉子》此“情”其實與“慾”無别,均爲傷“性”之力量,因而主張“防慾”,與《荀子》“節慾”之主張有别。
《防慾》又云:“故林之性静,所以動者,風摇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33)同上。此語均見於《吕氏春秋·本生》及《淮南·俶真》兩篇,可見三書均注意慾貪對性的影響。《劉子》下文更云:“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綵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悦芳馨,命曰燻喉之煙;身安輿駟,命曰召蹶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所以傷生。”(34)同上。亦在推衍《吕氏春秋·本生》之旨(35)《吕氏春秋·本生》云:“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見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第一册,第70~77頁。,指出過分追求外物帶來的享受,反而對生命造成損害。而《劉子》認爲防慾之法在於“食足以充虚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虚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此全性之道也。”(36)傅亞庶《劉子校釋》,第10~11頁。則衣、食、住、行都以維持生命的限度爲準,而應抱有止足的心態。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性”、“情”、“欲”對立的主張亦見《老子河上公注》,如《老子》十一章:“三十輻共一轂。”《河上公注》:“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衆輻共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虚,神乃歸之。”(37)王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41頁。《老子》五十章:“出生入死。”《河上公注》:“出生謂情欲出〔於〕五内,魂定魄静,故生。入死謂情欲入於胸臆,精神勞惑,故死。”(38)王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91頁。反映《河上公注》以爲“情”、“欲”均能傷“性”,故欲保守精神,則先除情去欲。而《老子》六十四章:“其未兆易謀。”《河上公注》云:“情欲禍患未有形兆〔之〕時,易謀止也。”(39)同上,第248頁。又下文:“其脆易破。”《河上公注》:“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於色,如脆弱易破除〔也〕。”(40)同上。與上述《劉子》主張“將收情慾,必在脆微”相同。且《老子》七十二章:“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河上公注》:“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濯垢,恬泊無欲,則精神居之〔而〕不厭也。”(41)同上,第279頁。則《河上公注》把“欲”稱爲“垢”,而要“洗心濯垢”,又與《劉子·清神》“神照則垢滅”之説法相類。考《河上公注》蓋成書於東漢(42)《老子河上公注》的成書年至今仍未有一致的結論,其中多有分歧,鄭燦山從思想史及道教史的面向進一步作考察,亦贊成東漢末年這個説法,見鄭燦山《河上公注成書時代及其思想史、道教史之意義》,《漢學研究》,2000年第18卷第2期,第85~111頁。,其書當在《劉子》之前,由兩書主張、用字非常相似,或可證《劉子》曾吸收《河上公注》的學説。
《劉子·去情》以爲人應除情,因爲“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礙。……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43)傅亞庶《劉子校釋》,第20頁。可見《劉子》認爲“情”是引發是非利害的因素,如果用“情”以待人接物,則“觸應而成礙”,故主張“無情以接物”。《劉子》進一步指出“無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雖獲毁而無憾。”(44)同上。可知“情”影響人對於榮辱窮達的感覺,若能消除“情”對人的負面影響,則人不再執着於毁譽,故下文曰:“有心之於平,不若無心之於不平也;有慾之於廉,不若無慾之於不廉也。”(45)同上,第20—21頁。此用《文子·符言》之文,以帶出德行應自然而行,而非故意爲之。且《去情》舉出事例以引證情對人之判斷的干擾,其云:“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模刻其容,醜狀既露,則内慚而不怨。嚮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嚮怨今慚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故也。”(46)同上,第21頁。面對同一評價,因應外物有情與無情,卻得出埋怨與自慚的不同心態,可見主觀之“情”實爲人價值判斷的障礙,故《劉子》主張“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遣情以接物,不爲名尸,不爲謀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47)同上。。傅亞庶指出“‘真’猶身也,‘全真’即全身”(48)同上,第27頁。。而“不爲名尸,不爲謀府”見於《莊子·應帝王》中(49)《應帝王》云:“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眹;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見王叔岷《莊子校詮》,第300頁。。《莊子》以爲人應絶棄求名、智巧等思想,承着自然的本性,達到空明的心境,並主張用心如鏡,任物來去而不加送迎,如實反映外物的情狀而無所隱藏,則能勝物。《劉子》主張去情,無心接物,即除去干擾人判斷的阻力,是承繼《莊子·應帝王》這種去私存真的思想。
《劉子》第四篇爲《韜光》,亦是演繹道家處世修身的學説,其云:“物之寓世,未嘗不韜形滅影,隱質遐外,以全性棲命者也。夫含奇佩美,衒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毁命者也。”(50)傅亞庶《劉子校釋》,第28頁。指出人要全性保真,必須藏身收歛,若露才揚己,則招致毁性害身之惡果。《劉子》舉出不少例子以明其説,“是故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見害,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托性於山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患者,未能隱其形也。”(51)同上。翠、龜、丹、石皆因其材質而罹難,故人要全身,必須“韜光隱質”。《劉子》此篇乃發揮《莊子》“無用之用”的旨意。所謂“無用之用”,見於《人間世》:“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52)王叔岷《莊子校詮》,第167頁。在《莊子》書中不乏相類的論述,如《莊子·秋水》:“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内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見王叔岷《莊子校詮》,第631頁。指出商丘之木因不材而存,柏桑則因其材而見伐,則“無用之用”於己身實爲大用。《劉子》主張隱形滅質,就是避免人因才招害,與《莊子》以“無用之用”存身之旨相合,《劉子》總結云:“韜跡隱智,以密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内。”(53)傅亞庶《劉子校釋》,第29頁。則外不露材,内不存欲,才能全身保性,得其天年。
(三) 《劉子》對道家禍福觀之闡釋
《劉子》對禍福的看法是來源於道家學説。《劉子·慎隙》云:“禍之所生,必由積怨;過之所始,多因忽小。小過之來,出於意表;積怨之成,在於慮外。故其來也,不可防;其成也,不可悔。防怨不密,而禍害臻焉。”(54)同上,第336頁。以爲禍之成因在於怨恨,而禍之開始在於忽略小處,若不注意此兩者,禍則甚大。故其又云:“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害與利同鄰,若非至精,莫能分矣。是以智慮者,禍福之門户;動静者,利害之樞機,不可不慎也。”(55)同上,第337頁。其中指出“禍與福同門”,來源於《老子》五十八章:“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56)陳鼓應《老子註釋及評介》,第289頁。但《劉子》並非强調禍福對立轉化的情形,而是要指出人若不審於微小之處,則禍害來臨。
另外,《劉子·貪愛》亦云:“小利,大利之殬;小隙,大禍之津。苟貪小利則大利必亡,不遺小隙則大禍必至。”(57)傅亞庶《劉子校釋》,第465頁。亦指出禍患之來在於貪吝小利及不察小隙,並以蜀侯欲得秦惠王之貨而國亡、楚白公勝性貪而被葉公所滅爲事例論證其説。下文更云:“是以達人睹禍福之機,鑒成敗之原,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隙自害。《老子》曰‘多藏必厚亡。’《禮》云‘積而能散。’皆明止足之分,袪貪隙之萌也。”(58)同上,第466頁。則以爲人若要趨吉避禍,必須體察形勢,深入分析禍福的因素,其引用《老子》見於今本四十四章(59)案: 今本《老子》四十四章與《郭店楚墓竹簡·老子甲本·第十七章》相應。,意謂豐厚之藏必定招致慘失,即演繹“物極必反”的道理。而所引《禮記》則見於《禮記·曲禮上》,《劉子》並引《老子》及《禮記》以指出人應懂得滿足,不可過分追求外物。《禮記》雖爲儒家經典,然自《劉子》觀之,其中義理實可與《老子》相通,反映《劉子》兼容儒、道的特點。
而《禍福》篇更進一步演繹老子禍福轉化之思想,其云:“禍福同根,祅祥共域。禍之所倚,反而爲福;福之所伏,還以成禍;祅之所見,或能爲吉;祥之所降,亦迴成凶。”(60)傅亞庶《劉子校釋》,第456頁。篇中《劉子》列舉不少事例以明其説,而“陳駢出奔,以爲禍也,終有厚遇之福”,及“北叟有胡馬之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而至保身之福”數事均取諸《淮南子》。《劉子》以爲防範禍福轉化在於着重自身的修養,其云:“人有禍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是以君子祥至不深喜,逾敬慎以儉身;祅見不爲慼,逾修德以爲務。”(61)同上,第457頁。指出遇禍以敬,遇福以慎,注重己德,則無禍患之憂,此亦承繼《老子》修身之説。
(四) 《劉子》對道家誡盈、明謙思想之發揮
《劉子》在《誡盈》《明謙》兩篇推演《老子》謙讓誡滿的學説。《劉子·誡盈》云:“四時之序,節滿即謝;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陽極而陰降,陰極而陽升。日中則昊,月盈則虧,此天之常道也。”(62)同上,第346頁。指出四時更替,陰陽互迭,反映事物發展至盛處,必然會衰落,因而人若能“功成必退”,則可避免從盛處滑落,而保持不敗,可見所謂“日中則昊,月盈則虧”,乃在闡釋《老子》盈虚的思想。下文云:“勢積則損,財聚必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理之恒情。”(63)同上。則在推演《老子》“物極必反”的原理,此爲《劉子》論述“誡盈”學説的前提。《誡盈》篇中,《劉子》反復地提出必須知退守下,才可體察盈滿之危,其云:“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滿之危;處存而不忘危,必履泰山之安。”(64)傅亞庶《劉子校釋》,第346頁。而《劉子》此篇並以《周易》推展《老子》退下的思想,反映儒、道融合的特點,如篇中云:“故雷在天上曰大壯,山在地中曰謙。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勿履。處壯而能用禮,居謙而能益寡。”即化用《易·大壯·象》“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65)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頁。、《謙·彖》“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之文句(66)同上,第80頁。。又本篇最後云:“《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以君子高而能卑,富而能儉,貴而能賤,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窮也。”(67)傅亞庶《劉子校釋》,第347頁。可見《劉子》所述的聖人則包含高卑、富儉、貴賤等對立面,故能“損而不窮”。而所引《易》見於《屯·象》,而“君子高而能卑”數句則見於《説苑·敬慎》(68)《説苑·敬慎》云:“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虚,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見向宗魯《説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43頁。,蓋《劉子》以爲《易傳》《説苑》等儒家文獻與《老子》思想相通,皆在闡釋老子之説。
《劉子》另一篇《明謙》亦重在論述謙退之要,發揮《老子》三十九章“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之思想(69)陳鼓應《老子註釋及評介》,第218頁。,《明謙》云:“天道下濟而光明,江湖善下而爲王。故山在地中成謙,王侯以孤寡爲損。謙則榮而逾高,損則顯而彌貴。高必以下爲基,貴則以賤爲本。在貴而忘貴,故能以貴下民;處高而遺高,故能以高就卑。”(70)傅亞庶《劉子校釋》,第353~354頁。可知《劉子》由守下之道出發,説明謙下能卑的重要性,其中更明引《老子》三十九章之文字。其後又云:“是以大壯往則復,天地之謙也;極昇必降,陰陽之謙也;滿終則虧,日月之謙也;道盈體沖,聖人之謙也。《易》稱‘謙尊而彌光。’《老子》云‘不伐故有功。’謙者在於降己,以高從卑,以聖從鄙。”(71)同上,第354頁。亦一如《誡盈》篇,以《易·大壯》《謙》兩卦,並結合《老子》二十二章“不自伐,故有功”之文字(72)陳鼓應《老子註釋及評介》,第154頁。,論證人應體中不盈,亦反映《劉子》儒、道互通的特點。而《明謙》以謙退爲基礎,指出:“君子則不然,在榮以挹損爲基,有功而不矜,有善而不伐,遺其功而功常存,忘其善而善自全。情常忘善,故能以善下物,情恒存善,故欲以善勝人。”(73)傅亞庶《劉子校釋》,第354頁。可見《明謙》主張“忘善”,認爲若有心爲善,其目的只在“勝人”,而失去“善”的本質。可見《劉子》把《老子》謙退的思想運用到人生處世之上,希望以這種主張減少自矜自伐的惡習。
以上爲《劉子》所取道家思想的概況。
二、 從《九流》篇看《劉子》“儒道互補”之
結構及其對道家思想之取捨
《九流》爲《劉子》最後一篇,其中曾評價九流諸子,反映《劉子》作者對諸子之態度,此亦是了解《劉子》對諸子學説取捨之重要材料。《九流》中依次評價道、儒、陰陽、名、法、墨、縱横、雜、農等家,其後提出“觀此九家之學,雖旨有深淺,辭有詳略,偕僪形反,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會治道,迹雖有殊,歸趣無異”(74)傅亞庶《劉子校釋》,第521頁。。可見《劉子》以爲九家之説皆可用於治道,與《漢志》所言“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旨趣相同,故《劉子》亦綜合百家之學以成其説。
值得注意的是,《劉子》對“雜家”之認識,其云:“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夷之類也。明陰陽,本道德,兼儒墨,合名法,苞縱横,納農植,觸類取與不拘一緒。然而薄者,則蕪穢蔓衍,無所係心也。”(75)同上。楊明照云:“程榮本、王謨本、畿輔本‘夷’作‘南’,是。”(76)同上,第534頁。即“淮夷”當是“淮南”之訛,而《九流》所引孔甲、尉繚、尸佼、淮南等四種雜家典籍,均見於《漢書·藝文志》,然《漢志》只言“兼儒、墨,合名、法”,《劉子》則作出了擴充,指出雜家是“明陰陽,本道德,兼儒墨,合名法,苞縱横,納農植”,即九流並包,較諸《漢志》更爲明確。《漢志》未有言明雜家以道家爲本,而《劉子》則明言“本道德”,道出了“雜家”學説之結構,與上文《劉子》以道家之道論作基礎之情況相合,而江瑔《讀子卮言》卷二《論道家爲百家所從出》亦云:“唯其學雖本於道家,而亦旁通博綜,更兼采儒、墨、名、法之説,故世名之曰雜家。”(77)江瑔《讀子卮言》,臺灣廣文書局1982年版,第88頁。可見《劉子》對“雜家”了解甚深,而其組織框架亦同《吕覽》《淮南》,是典型的“雜家”著作,承續了先秦以來“雜家”以道爲本而對百家之學作出整合的特點。
於九家學説之中,《劉子》以儒、道爲要,《九流》云:“道者,玄化爲本;儒者,德化爲宗。九流之中,二化爲最。”(78)傅亞庶《劉子校釋》,第521~522頁。然《劉子》對道家學説評價較儒家爲高,既於《九流》中首列道家,又云:“儒教雖非得真之説,然兹教可以導物;道家雖爲達情之論,而違禮復不可以救弊。”以爲道家乃“達情之論”,而儒家爲“非得真之説”,反映出《劉子》以道家爲宗之傾向。但另一方面,《劉子》亦認爲因時移世易,若治國、修身只着重於一家則不能無亂,以爲“道以無爲化世,儒以六藝濟俗。無爲以清虚爲心,六藝以禮教爲訓。若以禮教行於大同,則邪僞萌生;使無爲化於成、康,則氛亂競起。何者?澆淳時異則風化應殊,古今乖舛則政教宜隔”,故《劉子》雖宗道,但其並不反對儒家之禮教,因爲現世與上古形勢不同,世人實不能純以無爲治世,而應以儒家之禮教化民。而且《劉子》之作者所身處的時代並非大同至德之世,故其所主的修身之法亦未單用道家的學説,而是結合儒、道兩端,將儒家的價值觀加入道家修身的内容中,目的是要配合書中所取儒家禮教的思想,此點將詳論於下文。
由於儒、道學説各有作用,又相互爲用,因而《劉子》提出世人當因應修身、治世之需要而取用儒、道兩家思想,故《九流》又云:“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爲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爲是務,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以爲若要管治國家,化俗安民,當采儒家之禮教;如要全身養性,則當取道家之修身學説,明確地提出由“儒道分工”達至“儒道互補”之方法,以在修身、治國兩方面達致成功。當然,儒、道兩家在學説上實有其相通之處,如上文提及《劉子》在論述戒盈、謙下等思想時,並引儒、道文獻以闡釋儒、道會通之理。面對這些儒、道相合的部分,《劉子》固然不用作出調整。然而,當儒、道兩家思想確然發生分歧時,《劉子》則對道家學説作出了嚴格的取捨,以協調儒、道的根本衝突,以免書中所取的兩家之説産生牴觸,使其主張能切實地得到執行。
我們若要了解《劉子》對道家學説取捨之準則,實可結合《九流》對道家學説之評價與書中所取的儒、道學説加以分析。《九流》評道家云:“以空虚爲本,清净爲心,謙抑爲德,卑弱爲行。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見其迹,亭毒萬物不有其功。”(79)傅亞庶《劉子校釋》,第519~520頁。可見《劉子》以爲道家學説之根本在於虚静、卑弱、無爲、退下等處世態度,這些價值觀恰就是上文提及《劉子》在不同篇章所取的道家思想。而《九流》又云:“然而薄者,全棄忠孝,杜絶仁義,專任清虚,欲以爲治也。”(80)同上。反映《劉子》反對道家全棄仁義忠孝,以爲這種主張不能用於治國。考諸不少道家文獻中,都有反仁義之觀點,蒙文通先生就以是否反對仁義作爲標準,區分北方道家和南方道家(81)蒙文通《略論黄老學》,收入《蒙文通文集》卷一,巴蜀書社1987版,第271頁。,他認爲北方道家是主張全棄仁義,如《莊子·知北遊》云:“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82)王叔岷《莊子校詮》,第806頁。以爲“道德”失而有“仁義”。又今本《老子》第十九章更言:“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絶學無憂。”(83)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第136頁。可見《老子》反仁義之思想。當然《老子》本身是否反對仁義,仍需深入研究,因新近出土之郭店《老子》就無“絶仁棄義”之説,而作“絶僞棄慮”,證明先秦之《老子》並不否定仁義。張豐乾以爲今帛書本及今傳本所見或是自漢以後儒道互絀的産物,推測帛書《老子》出現“絶仁棄義”、“絶聖棄仁”之説法是受到《莊子》外雜篇思想之影響。(84)張豐乾《出土文獻與文子公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頁。
由於這些反仁義的觀點,與《劉子》“六藝濟俗”之主張不合,故書中對這些全棄仁義之看法皆一一捨棄,以免與書中所取的儒家仁義之説相違背。《九流》評儒家云:“順陰陽之性,明教化之本,遊心於六藝,留情於五常,厚葬久服,重樂有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85)傅亞庶《劉子校釋》,第520頁。《九流》指出儒家的缺點爲:“然而薄者,流廣文繁,難可窮究也。”可知《劉子》以爲儒家之弊在於文繁,而肯定其六藝、禮樂之作用,故《劉子》雖重儒家之禮教,如《崇學》曰“人學爲禮儀,絲以文藻,而世人榮之”,又《誡盈》曰“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勿履。處壯而能用禮,居謙而能益寡”,然只取其實用易行之部分,捨棄其繁複不知變通之地方,如《隨時》曰“故《易》貴隨時,《禮》尚從俗,適時而行也”,《法術》云“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以言事”。此亦可見書中的内容與《九流》的觀點相一致。可見《劉子》肯定儒家之禮教,並在不同篇章吸收儒家仁義之説,如《思順》云:“夫爲人失,失在於逆。故七緯逆則天象變,五性逆則人行敗。變而不生災,敗而不傷行者,未之有也。”(86)同上,第99頁。《劉子》指出人應順性而行,其所謂“性”就是“忠孝仁義”,故其又云:“故忠孝仁義,德之順也;悖傲無禮,德之逆也。順者福之門,逆者禍之府。由是觀之,逆性之難,順性之易,斷可識矣。”(87)同上,第99~100頁。後文更言:“君子如能忠孝仁義,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88)同上,第100頁。可見《劉子》此篇以爲忠孝仁義等皆是人天生的本性,而實踐仁義忠孝是順性而行的表現。
又如《大質》篇論述人應保持忠義之行,其云:“故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强變者也。士有忠義之性,懷真直之操,不移之質,亦如兹者也。”(89)同上,第359頁。則《大質》亦把忠義看作士之性,實不可奪,而“生苟背道,不以爲利;死必合義,不足爲害。故不趨利而逃害,不忻生而憾死,不可以威脇而變其操,不可以利誘而易其心。”(90)同上。認爲士對忠義的德行當堅守不移。而《言苑》亦云:“忠孝者,百行之寶歟?忠孝不修,雖有他善,則猶玉屑盈匣,不可琢爲珪璋;剉絲滿篋,不可織爲綺綬。雖多,亦奚以爲也。信讓者,百行之順也;誕伐者,百行之悖也。信讓乖禮,迴而成悖;誕伐合義,翻而成順。”(91)同上,第509頁。亦强調忠孝禮義等儒家德行。《慎獨》篇則旨在論述人於獨處之時亦須循禮守常,其云:“善者,行之總,不可斯須離也。若可離,則非善也。人之須善,猶首之須冠,足之待履。首不加冠,是越類也,足不躡履,是夷民也。今處顯而循善,在隱而爲非,是清旦冠履而昏夜倮跣也。”(92)傅亞庶《劉子校釋》,第105頁。以爲人之行善必須持久,亦在闡釋儒家行善之説。以上可見,《劉子》所追求的品德實來源於儒家,故此其需要揚棄道家那些反仁義之觀點。
而上文亦指出,《劉子》對“性”之理解與《荀子》相似,書中更以儒家的德行擴充“性”的内容,故《劉子》所謂的“性”,明顯不是道家“存性保真”之“性”,如《莊子·馬蹄》云:“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93)王叔岷《莊子校詮》,第335頁。可知《莊子》把“仁義”等德行看成“性”以外的東西。而《劉子·防慾》云:“人之稟氣,必有性情。性之所感者,情也。”(94)傅亞庶《劉子校釋》,第10頁。没有明確爲“性”下定義,故《防慾》之重點並非在推演道家對“性”之看法,而是强調物欲對性之影響,以爲“雖襞情卷慾,而不能收,其性敗也”(95)同上,第11頁。,其中所着重的只是道家節減物欲的修養方法,而非道家“反仁義”之内容。而且,對於物欲之防備,儒家的看法與道家是一致的,如《孟子》就主張“養心莫善於寡欲”,故《劉子》在其他篇章,如上述的《思順》《言苑》等篇,即把儒家的德行如忠、孝、仁、義統攝於人性之中,視仁義等爲人性本然所有的品行,並没有與書中所取的道家修身之法形成任何矛盾。進一步説,上述《劉子》所取道家修身之説,同樣可以是人追求儒家德行之手段,以此把儒家德行與道家修身之道調和,使儒、道兩家的學説成爲一個整體。相同的學説結構其實亦見於《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中,如《吕氏·節喪》云:“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96)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第二册,第967、968頁。視親子之間的孝愛爲天性。又《淮南·泰族》云:“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奸。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97)陳廣忠《淮南子斠詮》,第1111頁。認爲教化可導民向善,以啓發其仁義之質。考兩書均多采道家修身之説,然書中所論亦不與上述所取的儒家價值觀相阻,可見《劉子》遠承此兩書的學説結構而無矛盾。
另外,《劉子》對於道家其他消極思想均加以舍棄。如《老子》三章:“不尚賢,使民不争。”又《莊子·天地》云:“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98)王叔岷《莊子校詮》,第458頁。可見老莊皆以爲至德之世不需用賢人輔助。然而《劉子·薦賢》則主張爲政任賢,以爲“國之需賢,譬車之恃輪,猶舟之倚檝也。車摧輪,則無以行;舟無檝,則無以濟;國乏賢,則無以理。”(99)傅亞庶《劉子校釋》,第187頁。故此不取道家反賢之思想。
《劉子》又捨棄道家反學之主張。如《老子》十九章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絶學無憂。”(100)“絶學無憂”四字本在今本《老子》二十章,此從陳鼓應等人之説法,將此四字歸入《老子》十九章。認爲要體道必須要棄絶仁義聖智之學。及《莊子·養生主》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101)王叔岷《莊子校詮》,第99頁。亦反對無止境的學習,認爲此對生命有極大的損害。然這些觀點與《劉子·崇學》《專務》等主張重視學習、專心於學的看法不合,故《劉子》亦不取用其説。然周振甫《〈劉子〉與〈文心雕龍〉思想的差異》一文則以爲《劉子》既取《老子》修身之説,而在《崇學》主張積學,實與《老子》“絶學無懮”之思想産生矛盾(102)周振甫云:“《劉子·清神》:‘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静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這是本於道家的説法,《老子》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四十三章:‘不言之教。’五十六章:‘知者不言。’按照《老子》的説法,十九章稱:‘絶聖棄智,民利百倍。’二十章:‘絶學無憂。’四十八章:‘爲學日益,爲道日損。’那末主張道家的‘不視’、‘不聽’、‘不言’、‘不慮’,就要‘絶學’。可是《劉子》有《崇學》篇,説:‘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老子》認爲‘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劉子》卻要‘因學而鑒道’。《老子》認爲‘絶學無憂’,《劉子》卻認爲‘津言之妙,非學不傳。’原來《劉子》的《崇學》稱:‘故不登峻嶺,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遊六藝,不知智之深。’這是化用《荀子·勸學》中語:‘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這就跟他在《清神》裏講的‘不視’、‘不聽’、‘不言’、‘不慮’矛盾了。‘不視’、‘不聽’怎麽能登峻嶺而知天之高,瞰深谷而知地之厚,‘不言’、‘不慮’怎麽能遊六藝而知智之深。這是雜引道家和儒家之説發生的矛盾。”見周振甫《〈劉子〉與〈文心雕龍〉思想的差異》,第120頁。引者按: 《劉子·清神》云“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静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見於《淮南子》與《文子》,而與《文子》尤合,形容聖人去除心、五官等與外物接觸之途徑,從而保持精神,不受外物之影響。而整篇《清神》之主旨亦强調精神明清之重要,“故神静而心和,心和而形全”,作者雖於此篇多取道家全性之説,然而當中亦有取捨,如周氏所言老子之“絶仁棄義”、“爲學日損”之主張,《劉子》一蓋不取。而《老子》言“絶聖棄智”,是指抛棄聰明智巧,非泛指客觀知識。雖然《劉子·去情》曾出現“棄智以存真”之句,然這個“智”亦是指“智巧”、“僞詐”、“機心”而言,非指學習。《劉子》用《文子》之原因,乃在突出外物對精神之負面影響,以爲“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搴正性,況萬物之衆以拔擢而能清心神哉。”由於外累從五官而入,故保持神明須從節制五官開始。可知《劉子》用《文子》之文,以明全性保身之道,其中並没有吸收《老子》“絶學”之思想。周氏把《劉子·清神》之主張全等同《老子》之思想實可討論。而《崇學》所言“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乃用《尸子》之文,《北堂書鈔》八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七引《尸子》:“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與《劉子》同。此乃《劉子》調和儒、道思想之方法,本來道家以爲認識“道”是靠體悟的,而《劉子》吸收《尸子》之説,以爲認識道之方法乃在學,故强調學之重要性。既然《劉子》没有吸納《老子》“絶學”之説,則其以《尸子》“以學鑒道”之方法,達至儒道互補,亦没有形成任何明顯的矛盾。且“不言”、“不慮”乃就聖人保持精神、防止嗜慾之形象而言,而《劉子》勸學之意在於人具體修性體道而言,亦無牴牾之處。可見《劉子》並非雜引諸子,當中以儒道互補爲其標準,吸取諸子之説。。細考《吕氏春秋》《淮南子》兩書,即可發現不單《劉子》對道家思想有如此的取捨,其實《吕覽》《淮南》亦在吸收道家修養學説的同時,取用儒家重學的主張。如《吕氏春秋·勸學》云:“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103)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第一册,第404、405頁。《尊師》則云:“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104)同上,第422~424頁。可見《吕氏》亦重視學習,以爲不學不能體性,與《劉子·崇學》所謂“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之説法一致。而《淮南·修務》云:“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蹍水也。”(105)陳廣忠《淮南子斠詮》,第1067頁。又《淮南·説山》云:“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106)同上,第886頁。則《淮南》亦取儒家重學之觀點。由此而觀,《劉子》《吕氏》《淮南》三書雖有取用道家修養之説,但同時皆揚棄道家“絶學”之思想,並在其他篇章吸納儒家重學之説,可見“雜家”調和儒道之學以成爲其自身的體系,而周氏之説,實可商榷。
然而,上文亦指出,《劉子》在《韜光》篇吸取《莊子》“無用之用”的思想;但另一方面,《劉子》在《愛民》《從化》《風俗》等篇則在闡釋儒家的政治思想,那麽兩者的取向是否産生矛盾?首先,《九流》已言:“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爲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爲是務,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可見《劉子》認爲我們要因應世態、己身的情況去運用儒、道兩家之説,而非同一時間、面對同一事件采取兩種不同的取向。而且這種“出世”與“入世”之“矛盾”,經常出現在魏晉士人的身上。在魏晉黑暗的政治環境下,當時士人常常充滿疑惑,既想隱退,又欲建立功業,如阮籍本有濟世之志,後因當時政治腐敗,遂有由儒入道之轉向,進而否定儒家虚僞的禮法(107)李健中、高華平《玄學與魏晉社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205頁。。若將《劉子》書中的内容聯繫魏晉名士複雜的心態,或更能體察《劉子》爲何兼融儒家的積極治世之説與道家全身誡盈的思想,其實就是承續魏晉名士這種“出世”與“入世”的“矛盾”,折衷儒道思想而來的(108)梁德華《魏晉玄學與〈劉子〉“儒道互補”思想研究》,《新道學經營管理學報》第二十輯2015年,第63~ 95頁。。蔡忠道《魏晉儒道互補之研究》認爲阮籍這種由儒入道的轉向實可看成魏晉“儒道互補”的另一種形態。(109)蔡忠道《魏晉儒道互補之研究》,文津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頁。若以蔡氏之説作參考,則《劉子》主張兼治儒道,或更能體現“儒道互補”的内涵,因《劉子》以爲必須兼治儒、道才能達到功業、道德兩全的境界,實以“儒道分工”作爲其互補的手段,故此《劉子》同時兼取儒、道“出世”與“入世”的價值取向其實並無牴牾。
總結而言,《劉子》雖對道家極爲推崇,又多取道家修養之説,但與此同時,《劉子》亦肯定儒家禮教之作用,並對儒、道思想進行適當的分工。爲了避免書中所取儒、道兩家學説構成矛盾,《劉子》一方面取用道家全性之説;另一方面又捨棄其中反仁義、反學、反禮教之部分,進而在其他篇章廣泛地吸收儒家重仁義、重學、重禮教等主張,兼有儒道之長而不相牴觸,形成其“儒道互補”的學説結構,以期達至“身名兩全”之境界。
結 論
根據以上所論,可總結爲以下數點:
一、 以上可見,《劉子》對道家學説,如《老子》《莊子》等,多有吸取,又在書中多采《吕氏春秋》《淮南子》中的道家主張,甚至吸收《老子河上公注》“去情”之思想,反映《劉子》重視道家的學術特點。且《劉子》透過對各種的道家文獻重新組合、轉化,在道論、修身、禍福等學説提出了己見,甚至並引儒、道文獻以闡釋兩家相通之理。
二、 本文結合《劉子·九流》對諸子之評價及書中對儒、道兩家學説的整合,認爲《劉子》對道家學説實有其嚴格的取捨,如《劉子》雖有吸收道家修養之説,但其中不取道家反仁義、反學、反賢等主張,以避免與書中其他篇章所取的儒家思想形成牴牾,並主張“儒道分工”,因應不同時勢取用儒、道兩家學説,形成“儒道互補”之學術結構。
三、 周振甫以爲《劉子》思想前後矛盾,並與《文心雕龍》對照,認爲“雜家有兩種,一種是見治理國家需要兼采儒墨名法之説,去掉各家互相抵觸的部分,加以融會貫通。《文心雕龍》兼采儒道佛各家的説法,就是這樣;另一種是‘漫羨而無所歸心’,即采取各家的説法没有一定準則,不免自相矛盾,《劉子》就是這樣。”(110)周振甫《〈劉子〉與〈文心雕龍〉思想的差異》,第119~120頁。又陳志平《劉子研究》認爲“《劉子》並没有將儒、道兩家很好的融合在一起,産生一種新的學説。它看到儒、道的長處和不足,並試圖用一種互補的模式來完善它們,但它没有注意到儒、道並存和融合間的矛盾。”(111)陳志平《劉子研究》,第281頁。然據本文分析,《劉子》對道家學説之綜合實非胡亂雜引,且在整合儒、道兩家學説的過程中有其嚴格的取捨,以免與所取的儒、道家思想形成牴牾,故此本文認爲《劉子》雖爲“雜家”之作,但實非“漫羨無所歸心”一類,而周、陳二氏的説法,實可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