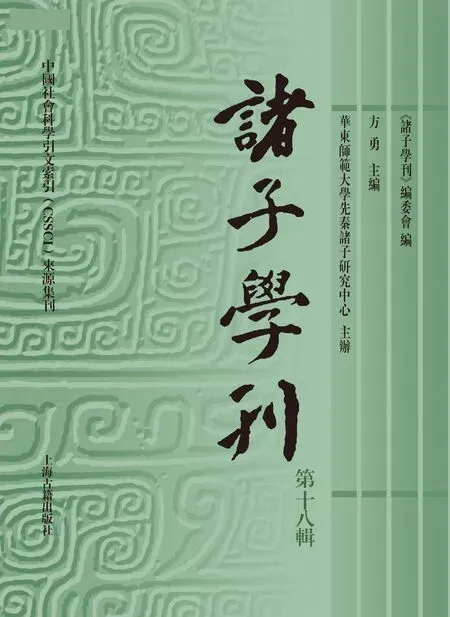“新子學”: 漢學主義的替代者?
[德] 維亞切斯拉夫·維托夫 劉思禾等譯
内容提要 衆所周知,認同研究總是和劃定邊界相關。在西方漢學研究以及中國知識分子關於文化認同的争論中,存在着諸多需要一次又一次借助其他文化中相應領域來標識的研究領域,諸如中國哲學、中國文學、中國歷史等。這種劃定邊界的做法,不僅僅局限於所謂的文化相對主義者。普遍主義者對文化相對主義持批評態度,且提倡世界各種文化現象之間具有平等性原則。他們在反對文化相對主義的看法時,同樣會將他們的看法建立在關鍵的邊界劃分——即他們的學術認同——之上。本文將捍衛如下觀念: 對於任何認同建構的討論,任何劃定邊界的行爲,以及對這種劃界行爲的批評,都可以視作爲一種政治表態。因此,每當這些研究展現出對政治立場的明確否認,或者並未反映出已經介入政治,問題就會經常出現。本文以中國的薩義德《東方主義》研究以及當前中國的國家認同之争爲要點展開討論。
關鍵詞 中國思想史 “新子學” 新諸子研究 漢學主義 東方主義 中國認同
引 言
衆所周知,認同研究總是和劃定邊界相關。在西方漢學研究以及中國知識分子關於文化認同的争論中,存在着諸多需要一次又一次借助其他文化中相應領域來標識的研究領域,諸如中國哲學、中國文學、中國歷史等。這種劃定邊界的做法,不僅僅局限於所謂的文化相對主義者。普遍主義者對文化相對主義持批評態度,且提倡世界各種文化現象之間具有平等性原則。他們在反對文化相對主義的看法時,同樣會將他們的看法建立在關鍵的邊界劃分——即他們的學術認同——之上。
本文捍衛如下觀念: 對於任何認同建構的討論,任何劃定邊界的行爲,以及對這種劃界行爲的批評,都可以視作爲一種政治表態。因此,每當這些研究展現出對政治立場的明確否認,或者並未反映出已經介入政治,問題就會經常出現(2)本文並不追求這樣的觀點,即任何關於中國的學術研究都必然是一種政治聲明。不過,只要政治反映了東西方之間的相互印象,對待文化差異的態度——不管是消極的(此爲普遍主義者的特點),還是積極的,對全球範圍内的東方知識生産而言都依然是重要的觀念背景。故而,本文的主要目的並不是指責漢學家參與到政治中去,而是批判性地展示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即思考國家認同之時把政治視爲麻煩的問題。。本文以中國的薩義德《東方主義》研究以及當前中國的國家認同之争爲要點展開討論。不過,這一問題並不僅僅局限於中國知識分子,如下兩個例證便可以説明。
在梅約翰教授的《失去的靈魂: 當代中國學術話語中的“儒學”》一書中,作者注意到二十世紀晚期以來興起的在其撰寫該書時仍舊處於高峰的“儒學熱”,由此探討了這種現象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認同建構中的作用。一個主要的觀點是,這種現象只屬於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框架,而非政治民族主義。儒學研究的興起據稱並非國家(3)梅約翰《失去的靈魂: 當代中國學術話語中的“儒學”》,哈佛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7頁。策動,這些被稱爲文化民族主義的研究,致力於人民的道德新生,遠離政治民族主義(4)同上,第14頁。關於儒學熱的相反觀點,參見沃納·邁斯納《從十九世紀至今中國對文化和民族認同的尋找》,《中國觀察》2006年第68期;李明輝《當代中國的儒學熱》,拉爾夫·莫里茨、李明輝編輯《儒學: 開端—發展—前景》,萊比錫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而保持着純粹的學術關懷。“然而,最重要的是,將儒學作爲主幹的文化民族主義是一種運動,旨在强化儒家文化作爲建構中國之獨特性與價值性的信仰。”(5)同上,第338頁。梅約翰將自己關於文化和政治民族主義和約翰·哈欽森的觀點相區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民族主義的嬗變: 蓋爾語復興和愛爾蘭民族國家的創建》(倫敦艾倫—昂温出版社1987年版)中,哈欠森認爲這兩種民族主義是包含在政治中的。關於愛爾蘭民族主義的問題,他對愛爾蘭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進行了大量討論,其中包括可以“宣稱戰勝英國的獨立戰争的勝利”等。這種對文化與國家之間不言自明的區分,以及在學術中排除政治的看法,看起來頗有問題。在這種排除下,梅約翰書名中的“學術話語”一詞依福柯的語義就不能得到解釋: 聲稱學術不受權力關係的影響,實際上也反映了——雖然看上去不盡合理——權力的某種意味。
戴卡琳的《傅斯年眼中的哲學、諸子及中國哲學》也許是另外一個例證。文章探討了作爲五四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的傅斯年,並不願意將西方哲學的概念運用在中國傳統思想之上。戴卡琳指出傅斯年身上的一種矛盾,一方面努力追求客觀性,另一方面在處理西方概念與中國傳統思想時評價性、情感化的態度。作者發現,傅斯年的叙述中往往伴隨着某種評價,而這種評價很可能來自當時國家的危急形勢(6)戴卡琳《傅斯年眼中的哲學、諸子及中國哲學》,梅約翰編輯《愛智者: 中國哲學作爲一門學科在二十世紀中國的興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頁。。傅斯年在學術方法上的不一致,被以如下方式解釋:“來自山東的傅斯年,對日本的威脅具有强烈的危機感。在他進行著述時,這種危機感愈發地緊迫。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在這種情形下,很難將學術研究與政治關懷以及民族主義情感相分離。”(7)同上,第298頁。這篇文章認爲,在探討國家認同問題時原則上可以將學術研究與政治關懷相分離。戴卡琳既没有提供任何論證來支撑她的觀點,也没有關注到這一事實: 她自己文章的研究主題——即將哲學概念運用在中國傳統思想上的適用性——絶不是非政治性的問題。自從清朝覆滅後,這一主題已經成爲中西知識分子業已捲入的話語體系的一部分,且受到對如下問題如何認知的支配,即平等 /不平等的全球權力體系以及知識與權力之間關聯的本質。
衆所周知,學術研究與政治關懷之間的關係,也是薩義德《東方主義》這一後殖民主義經典的主題。薩義德解構了作爲西方學術殖民手段的他者——東方知識體系。他表明其研究目的在於警惕“學者與國家過於密切的關係”(8)愛德華·薩義德《東方學》,倫敦企鵝圖書出版社1978年版,第326頁。。换句話説,他呼籲知識分子與一種異化他者以作爲殖民手段的政治保持距離。薩義德並未對下述問題給出明確回答,人文科學是否可能完全放棄政治關懷。雖然他表現出了放棄政治關懷的傾向,而這應視作一種理想主義的態度。不過,他仍舊以一種有説服力的方式顯示出,對於任何涉及跨文化認同與跨文化知識生産的學者來説,批判性地反思他 /她自身與政治的可能關係,以及注意到文化無意識的危險性,有多麽必要。
自九十年代初期以來,在中國知識分子全球化語境中討論自身文化認同時,薩義德的《東方主義》保持着重要的指向作用。然而非常吊詭的是,許多研究非常依賴薩義德的理論,並將他者視作政治對象來看待,同時又非常嚴厲地批判薩義德。這些批評者的一個典型特徵是,他們反對西方學者在各種中國認知上的曲解,同時又嘗試使自己處於中立的立場,以此來克服政治,使之不在場。這種嘗試或是暗示性的(如王銘銘的《西方作爲他者: 論中國“西方學”的譜系與意義》),或是明確的(如顧明棟對漢學主義的各種批判性研究)。本文意圖對這些做法的合理性提出質疑,並通過討論當下中國學術界最重要的學術運動之一“新子學”得出結論。如果説顧明棟强調學者拒斥政治關懷的必要性,並以他的漢學主義論著取代東方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研究,那麽本文的問題便是,當“新子學”的支持者更傾向於認爲拒絶政治是不可能的事,那麽“新子學”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取代漢學主義的新選擇。
一、 從東方主義到西方主義
關於薩義德的早期研究見於1993年第9期《讀書》雜誌上刊發的圓桌會議討論記録,該記録反映了薩義德東方主義在中國被積極地接受。六年之後,《東方主義》被翻譯爲中文(9)這一著作於1999年被香港的王宇根第一次翻譯爲《東方學》(香港三聯書店)。與此同時,在臺灣被王志弘等翻譯爲《東方主義》(臺北立緒文化公司)。。經過《讀書》的這次討論,張寬的“歐美人眼中的‘非我族類’”受到中國學者的特别關注。根據張寬對東方主義的批評(10)張寬《歐美人眼中的“非我族類”》,《讀書》1993年第9期,第5頁。,薩義德著作最嚴重的缺點是没有反映中國的情況。很早之前,西方知識分子對中國的關注充滿了意識形態: 中國在歐洲啓蒙運動時期的理想形象被一種貶損的形象所替代——清末的中國是沉睡的怪物,没有革新能力(11)同上,第6頁。等。在張寬的觀點中,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同樣以重要的方式去建構東方主義,直到他們自我東方主義化而導向西方的標準。在西方人的影響下,他們開始覺察到自己是排外的、自私的、没有邏輯的和不衛生的(12)同上,第7頁。。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薩義德東方主義進行的早期研究中,伴隨着一種被張寬稱之爲西方主義的反話語討論。張寬使用的這一術語,意味着一種錯誤的、歪曲的西方形象,這種形象由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的浮躁、盲目以及非理性的態度所激發出來,出現於二十世紀早期。西方主義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從對西方標準的自我認同,到對西方的整體排斥。作爲一種話語,西方主義被視爲東方主義的翻版。如果不批判性地對待,這二者都視爲危險的。張寬的文章最後呼籲中國知識分子,警惕東方與西方的相互表現造就的政治化(13)兩年後,他又寫了一篇關於東方主義的評論文章試圖解放西方話語霸權殖民的中國學術(西方權勢話語,殖民話語)(張寬《薩伊德的“東方主義”與西方的漢學研究》,《瞭望新聞周刊》1995年第27期,第37頁)。關於早期張寬對薩義德的態度的詳細討論,參見張隆溪《强力的對峙: 從二分法到差異性的中國比較研究》,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193頁。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張寬的思想和理論被摒棄,被認爲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傲慢和自以爲是的自以爲是”(《强力的對峙: 從二分法到差異性的中國比較研究》,第19頁)。張隆溪的專著值得關注,這也反映了薩義德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第一波影響,並在政治上解釋了“民族主義的情緒”(張隆溪《强力的對峙: 從二分法到差異性的中國比較研究》,第190頁)。中國對東方主義的民族主義批評的這種批判態度,由陶東風(2010)隨後進行了論述。。
在張寬一文發表兩年後,陳小眉的《西方主義: 後毛時代中國的反話語理論》一書討論了中國對西方所作的政治工具化的表達。作者區分了毛的官方西方主義,以及一種非官方的西方主義。官方的西方主義主要是第三世界理論,這是黨用來指導中國人民的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而非官方的西方主義據稱與當前的意識形態保持距離。非官方的西方主義以西方文明爲背景,通過對一系列傳統中國身份象徵(例如在《河殤》中的長城、黄河)所作的激烈批判性的展示,成了一種表達政治反對並挑戰黨國的方式。陳小眉把後毛時代的西方主義與五四運動相提並論,並强調後者的矛盾性:
當西方作爲……一種强有力的反儒家文化傳統的論説,西方主義話語可以視作是政治解放。而另一方面,有鑒於五四時期特殊的歷史境況,即以反帝國主義爲其優先考量,對西方的訴求又自相矛盾地顯示出另一面: 西方的父親來征服和殖民“第三世界”的婦女……(14)陳小眉《西方主義: 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反話語理論》,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頁。
陳小眉把中國女性從儒家傳統桎梏中的解放,視作“男性統治女性”話語的典範,在這裏真正女性的聲音根本不在場。她在著作的最後一章主要討論了性别問題,以説明現代中國存在的西方主義之持續性與複雜性(15)同上。。
從對五四時代到二十世紀末的西方主義的考察可以發現一種矛盾的情況,尤其從陳小眉的書中可以看到,作者不斷參考着福柯理論的同時,還討論着與權力關係扭結在一起的西方主義話語(16)同上。。由於後殖民時代的權力關係與20世紀早期的權力關係截然不同,因此談論兩種在知識與權力關係上相應不同的話語會更有意義: 如果五四時期中國在奮發自强,而西化在很大程度上伴隨着西方之爲實際或潛在威脅的形象,那麽後殖民時代的話語中,西方似乎是理論的提供者,西方過去的學術霸權得以揭露,而另一方——在認識上去殖民化——成了被公平而民主對待的主體。
另一本最近出版的關於西方主義的著作,王銘銘的《西方作爲他者——論中國“西方學”的譜系與意義》,也許可以作爲話語多樣性的説明——在諸多話語中陳小眉觀察到連續性。此書從對薩義德的批評入手:
作爲後殖民研究的權威著作,薩義德的東方主義諷刺地將現代西方思想同樣納入到了批評的範圍。當薩義德批判了現代西方知識的權利擴張,他的主張卻自相矛盾地讓我們接受了把西方當作唯一富有想像力和洞察力的主題。(17)王銘銘《西方作爲他者——論中國“西方學”的譜系與意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9頁。
王銘銘將中國對西方的想像譜系從周朝一直追溯到五四時代,最後看到的是與作爲西方的印度和昆侖山傳統相分離。而最新創造出來的現代西方形象是歐美,這個西方作爲真理的新源泉,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允諾之地。與陳小眉相似,王銘銘注意到了這個新完美形象的自相矛盾之處:
然而,西方現在也成了帝國主義的源頭。因此,從西方這裏獲取經典並不意味着能够把東方帶入到“西方的世界”中去。與此相反,只有當這些方法使中國成爲一個孤立的、脱離世界帝國主義體系的孤立國家時,他們才被視爲適用和有價值的。唯有如此,這些經典才能真正發揮作用。(18)王銘銘《西方作爲他者——論中國“西方學”的譜系與意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38頁。
令人震驚的是,王銘銘後殖民研究的系譜方法很大程度上受益於福柯與薩義德,但對二人只有很少的評價,也很少討論到他寫作時的權力關係或者話語。作爲後殖民理論源頭的決定性的西方想像,卻不是王銘銘譜系的組成部分,而對薩義德的直接批評是他在這個議題上發表的少之又少的言論。他没有提到,關於想像的比較對中西方來説絶不是新課題。舉例來説,這個主題是魯迅在《中國小説史略》(1925)中最感興趣的話題。王銘銘和魯迅一樣,拿相同的文獻(諸如《穆天子傳》《山海經》)來與古希臘的材料相比較。王銘銘的研究呈現出與魯迅截然相反的判斷,這一現象顯示出話語的差異性: 當魯迅通過與古希臘相比較而抱怨流傳下來的中國神話太少,並由此聯繫到中國想像的不發達(19)魯迅《中國小説史略》,見於《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頁。,而王銘銘卻觀察到,中國的想像與古希臘文本比較而言,“在‘中國文明’中,人們對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有着更成熟的認識”(20)王銘銘《西方作爲他者——論中國“西方學”的譜系與意義》,第111頁。。王銘銘忽略了與其歷史同路的魯迅,可以解釋爲缺乏對政治的自我意識,或者試圖要去超越政治。無論是哪種情況,政治對於王銘銘的研究而言仍舊是一個大問題——即使隱藏得很好——這一點反映在他對中西文化所作的定性,以及對薩義德理論的批判之上(21)關於王銘銘的書更詳細的討論參見維亞切斯拉夫·維托夫《讀王銘銘〈西方作爲他者——論中國“西方學”的譜系與意義〉》,《華裔學志》2014年第62期。。
對薩義德理論批判的政治意藴是陶東風《警惕中國文學研究中的民族主義傾向》一文的主題。在陶東風看來,張寬以及其他人僅僅把薩義德的理論當作武器(22)陶東風《警惕中國文學研究中的民族主義傾向》,《探索與争鳴》2010年第1期,第46頁。,他們的真正目的不是糾正薩義德或其他後殖民主義理論家,而是要否定五四運動。對此,陶東風以當前中國的文化危機來説明,危機不是由古代傳統的斷裂造成的,而是由魯迅傳統的斷裂造成的(23)同上,第48頁。。通過這些觀點,他强調魯迅的人文主義啓蒙精神,魯迅試圖糾正自身文化中的缺失,以減緩東西方的衝突。這一點在薩義德身上也可以看到,作爲西方的學者的薩義德也試圖糾正西方對東方知識生産的深層缺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的西方主義者們都疏離薩義德的著作,他們没有減少東西方之間的衝突,反而很大程度上强化了這種衝突。掀起這些論辯高潮的是被稱作漢學主義者的批評者,相關學者需要單獨討論。
二、 漢學主義: 永别了,政治
與東方主義的情況類似,漢學主義的概念源自西方,其最初目的是對西方話語主導下的西方有關中國的知識生産作批判性的再評估。漢學主義批評最初的倡導者鮑伯·霍奇和雷金慶,明確地指出福柯和薩義德是他們的著作《中國語言文化的政治學: 讀龍的藝術》(1998)的理論基石。例如,在福柯的意義上使用話語這個概念,其作如下闡釋:
在福柯的意義中,話語是對公共生活中其他領域的社會控制機制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西方的漢學研究就是一個話語霸權的經典案例,它的作用是控制誰有權威言説中國,什麽能够被闡釋和什麽能够被構造。在這套話語結構之下,中國是永遠無法盡知的,永遠無法言表的。事實上,運用福柯的觀點去觀察西方爲自身建構中國的過程也是很有啓發意義的。(24)鮑勃·霍吉、雷金慶《中國語言文化的政治學: 讀龍的藝術》,倫敦勞特利奇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頁。
鮑伯·霍奇和雷金慶將對漢學主義生産起積極作用的人限定在西方學者。這樣,在西方漢學規範的觀照之下,中國僅僅被看作是西方擁有絶對霸權的知識建構領域中的一個對象。由於鮮明的福柯和薩義德的理論背景,這本書被廣泛視作政治批判性著作。可惜的是,這本書對漢學主義只是作了相對簡短的介紹,而没有系統地分析評論。在許多未解的重大問題上,中國知識分子也是漢學生産和東西方之間相應合作機制的參與者。不過,這本書獲得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也激發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漢學研究中政治問題的熱烈討論。
最早專注於漢學主義研究的是周寧的論文《漢學或“漢學主義”》(2004),他的目的在於提醒學術界提防這些危險: 無意識中的漢學主義(25)周寧《漢學或“漢學主義”》,《廈門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第5頁。、學術殖民主義(26)同上,第1頁。、知識與權力的合謀(27)同上,第8頁。。周寧跟隨鮑伯·霍奇和雷金慶,以至於他認爲自己的研究也是政治批判。然而,最主要的區别在於,他認爲不僅僅是西方學者應該爲漢學建構負責,中國知識分子據稱同樣牽涉其中,他們是他首要的警告對象:
西方用中國文明作爲“他者形象”完成自身的文化認同,中國卻從這個“他者形象”中認同自身,漢學叙事既爲中國的現代化展示了某種光輝燦爛的前景,又爲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挖下致命的文化陷阱。西方的文化霸權通過學術話語方式達成。(28)周寧《漢學或“漢學主義”》,《廈門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第12頁。
周寧論文的三個觀點事實上影響了中國後來的漢學主義討論: 一、 在中國自我認同過程中運用源自西方的圖像、理論和規範時的文化不自覺性。二、 漢學主義研究中的客觀性問題,據此意見漢學只是看起來是生産客觀的知識。在有關中國的知識生産的問題上,每個學者都應該對他 /她自己的學科進行反省。三、 確信知識與權力是密不可分、相互聯繫的,學術界有必要意識到自身與政治的糾纏。
所有的這些論點,後來都在漢學主義論争的傑出人物之一顧明棟的著作中得到詳細闡釋。毫不夸張地説,很大程度上因爲他大量的中英文漢學主義論文和近著《漢學主義: 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2013)(29)一年前陳偉文寫的一篇相當短的英文專論——《漢學中的東方主義》(貝塞斯達: 學術出版社2012年版)是對顧明棟的漢學主義批評起重要鼓舞作用的論述。陳偉文没有使用“漢學主義”的名稱,但是他的批評文章的目的明顯和漢學主義相同,那就是把由西方和中國的漢學家們創造的西方概念和理論從中國的相關研究中剔除出去。,這個論題才在中國學者那裏獲得顯著而持續的關注度。儘管顧明棟明顯地受到了周寧的影響,但是在客觀性問題和權力與知識關係問題上,顧明棟展現出明顯不同的態度。
顧明棟認爲,漢學主義是“一種在西方中心主義、認識論、方法論和西方視角指導下的關於中國知識生産的理論,並因中國人和非西方人的參與而異常錯綜複雜的理論”(30)顧明棟《漢學主義: 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倫敦勞特利奇出版社2013年版,第6頁。。在中西漢學研究中認知中國的殖民化是他評論的主旋律。雖然他指出在中國的漢學主義話語中歐洲中心論傾向很突出,他也談到漢學主義研究中有明顯的中國中心論傾向,如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 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31)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 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和石約翰《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32)石約翰《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紐約格林伍德出版社1991年版。這些著作都試圖挑戰西方中心主義的史學研究成見,而堅持一種獨立自主的中國歷史研究。這兩部作品都是當代的漢學研究著作。顧明棟所批判的早期漢學主義研究都是萊布尼茨、沃爾夫、黑格爾、韋伯等討論中國的著作,他們看待中國的視角都是不切實際和批判性的,帶有認知上的主觀性。
正如顧明棟漢學主義著作的標題所表明的,他的評論不僅揭露了漢學主義是薩義德意義上東方主義的變種,而且漢學主義首先是一個替代或批判福柯和薩義德的理論,在這一點上他明顯不同於以前的學者。他如此解釋這種替代的必要性:“我的新觀點是,東方主義和後殖民主義都不能解決純粹的學術問題,因爲它們都强調的是政治批判。準確地説,它們都無法産生公正的學術。”(33)顧明棟《漢學主義: 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第25頁。使自己與後殖民主義研究經典保持距離是他文章的主要議題,例如在論文《後殖民主義的缺憾與漢學主義的替代理論》(34)顧明棟《後殖民理論的缺憾與漢學主義的替代理論》,《浙江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中,他强調他的漢學主義批評是要將漢學從政治和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從而促進客觀且公正的知識生産。又如《“漢學主義”理論與實踐問題再辨析——走向自覺反思、盡可能客觀公正的知識生産》(35)顧明棟《“漢學主義”理論與實踐問題再辨析——走向自覺反思、盡可能客觀公正的知識生産》,《廈門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一文表明,他的評論應當被理解爲反思的理論而不是政治批評。
在顧明棟看來,學術客觀性要通過拒絶政治和意識形態來實現,且首要關注的是全球化語境下的中國文化認同研究。人們可能期待顧明棟的著作提供一些追求學術客觀性的論證,或者至少它們自己是以客觀和公正的態度來闡釋的。不過,顧明棟回避了任何對於認知客觀性的論證,在他的評論著作中遍佈着極度個人化的主觀作風,這與其客觀性的訴求截然相反。例如,在上面提到的顧明棟《“漢學主義”理論與實踐問題再辨析——走向自覺反思、盡可能客觀公正的知識生産》一文中,他只是根據自己的信念,認爲福柯的思想是純破壞性的不能回答知識生産問題,就嚴厲批評福柯的權力與知識理論(36)同上。。同樣令人驚奇的是,爲了支撑這些信念,他引用了同爲漢學主義批評家葉雋的如下抒情性論斷:
“權力”作爲一個學術概念,發展到福柯,已經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黄昏”,因爲它雖然作爲概念工具很好用,但其實有很大問題。因爲它絶對不能抹殺人類對美好人性、社會和諧、情感的嚮往和追求。(37)同上。引用葉雋《亞洲、東方與漢學主義》,《中國圖書評論》2014年第1期,第6頁。
李商隱《登樂遊原》的詩句被用來形象地説明福柯的理論不切實際,這是通過修辭而不是論證去反駁福柯。顧明棟運用修辭手法來探討客觀性和學術非功利性的例子非常多。在另外一些獨特的修辭學方法中,他不斷地運用語義領域中“净化”和“治癒”的意象。這裏有一些來自《漢學主義: 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的例子: 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理論進行着不健康的盲目崇拜”(38)顧明棟《漢學主義: 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第1頁。,顧明棟的工作則是要促成“全球化的健康發展”(39)同上,第10頁。,漢學主義顯現的是“認識論和方法論特徵上的病症”(40)顧明棟《漢學主義: 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第18~19頁。,遭受了“知識分子的詬病”(41)同上,第109頁。,這是一個“對健康的全球化的知識性的阻礙”(42)同上,第96頁。,等等。客觀性問題和文化健康問題具有互補性,這一點如下面所表述的:“漢學主義曾經阻礙了對中國和中華文化的客觀理解和描述,並將繼續成爲文化交流和全球化健康發展的絆腳石。”(43)同上,第18頁。這使得以論證方式來處理問題變得有些多餘。
大量使用“治癒”和“純净”這樣的詞語,可以視爲所有試圖進行整體認知改革的偉大轉型期特性,這對於五四運動來説也是事實。看上去並非巧合的是,顧明棟和東方主義理論家一樣,其評論文章中有大量對五四運動的批評。他認爲五四運動要對盲目崇拜西方規範和西方價值負責,這些最終導致了現代中國牢固樹立了漢學主義話語,使得西方文化優越性這樣的負面觀念快速傳播(44)顧明棟關於五四運動的評論,參見顧明棟《漢學主義: 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第85~94頁。在中國的新的知識結構生産下,語義學領域中的“治癒”和“净化”的作用,參見維托夫2012年的文章。。
顧明棟對漢學主義的評論顯示出許多矛盾的地方。他拒絶政治的告誡帶有只從中華文化中研究中國材料和遠離西方理論的要求(45)顧明棟《語言哲學中的漢學主義》,《東西方哲學》2014年第64期,第712頁。,這也是一種不加掩飾的政治性叙述。他批評薩義德最主要的論據是中國從未被西方完全殖民過(46)顧明棟《漢學主義: 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後殖民主義話語有它自己的缺陷……很明顯的一點是中國從未被西方完全殖民過。”(第3頁),然而他自己卻經常使用中國精神殖民化的意象(47)漢學主義是“非土地殖民”(顧明棟《漢學主義: 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第11頁)、“非暴力殖民”(顧明棟《漢學主義: 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第59頁),是“中國人的自我殖民”,“一種知識殖民的形式”(顧明棟《漢學主義: 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第111頁),等等。,這使他看起來像是中國語境下東方主義的批判者。顧明棟偶爾意識到他矛盾的地方,在某些情況下他稱自己爲烏托邦主義者(48)顧明棟《漢學主義: 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終極目標是擺脱任何形式的政治干擾,看起來可能相當的烏托邦主義……”(第9頁)或者“即使不可能完全將學術從政治中分離出來,實現這個終極目標,我們需要削弱學者的種族意識、强化學術客觀性對於生産和評估中國及西方知識的必要性”(第186頁)。批判顧明棟的客觀性問題和其拒絶在民族身份之下學術研究的政治性,參見趙稀方的論文(趙稀方《評漢學主義》,《福建論壇: 人文社會科學報》2014年第3期,第34頁)。概括來説,趙稀方將顧明棟的觀點視作烏托邦主義。然而,在反對二元對立的問題上,他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折中方案:“顧明棟提倡的非政治性的知識,現實中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應當把它看作是在文化交流過程中建立我們相互間友善邦交的理想觀念。”,然而,這並没有妨礙他堅守自己的選擇,同時繼續忽視他非政治姿態下明顯的政治意味。
三、 “新子學”: 取他山之石
批評東方主義和漢學主義的中國學者都傾向於在研究中國時徹底拒絶西方學術方法。這些學者都有共同之處,西方學術爲他們提供了理論出發點,對於他們構建自己的學術認同十分重要,然而同時矛盾的是,他們認爲西方學術是某種負面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對薩義德和福柯的批評至少解釋爲學者們自我學術認同的否定,這反映了他們自我意識的缺乏。不過,在後現代全球語境中的文化認同建構中,並非所有中國知識分子的討論都走進了方法論上的死胡同。放眼中國當代學術界,有一種重大學術運動值得關注,它在過去四年中在中國各地甚至海外都贏得了支持者——這就是“新子學”,即中國諸子研究的新學派(49)關於“新子學”大量的學術探討及出版物,較好的綜述文章可參考刁生虎、王曉萌《弘揚子學精神,復興文化傳統——“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高教社科動態》2013年第4期)和劉思禾《第二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陝西教育》2015年第7期)。刁、王《弘揚子學精神,復興文化傳統——“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探討了曹礎基《“新子學”懸想》一文,曹文分析了“新子學”這種表達方式在語法上的兩種區别:“新之子學”,關於思想家的新學派,即以新視角看諸子,或是“新子之學”,即新思想家的學派,這種意義下,一些當代的思想家有意識地將自己學術接續古代先哲的遺産,他們也被認爲是“子”。(第 3頁)。“新子學”支持者並没有直接參與到東方主義和漢學主義的論争中,而是懸置上述各類争議,並尋找矛盾性更小的解決辦法。
“新子學”是指古代中國思想學派和學者(老子、孔子、莊子、管子、淮南子等)的復興。80年代改革以來,經濟初步騰飛和文化自覺意識發展相對緩慢,在當前面臨全球化挑戰之時,諸子學在中國文化認同的論争中成爲思想闡釋的新主題,進而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從80年代到2012年——該年方勇教授發表了《“新子學”構想》(50)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第14版。一文,成爲“新子學”的第一份宣言——這段時間中,在各種中國文化認同構建活動中最令人矚目的是所謂的儒學熱(51)關於“儒學熱”,梅約翰《失去的靈魂: 當代中國學術話語中的“儒學”》,第7頁。以及新儒家的主導地位。有鑒於此,“新子學”倡導者提出了學術多元競争的理念,即百家争鳴。
在宣言中,方勇將復興諸子學的必要性歸結爲以下幾點: 自古以來,中國知識的傳遞遵循着兩條路徑,一種是王官之學,它的定位是完全服務政治並以“六經”來界定;另一種是非權威、競争性的諸子之學,它雖與王官學術有直接關聯,但在思維方式上大相徑庭,體現了更多的靈活性和創造性。“新子學”之“子”應當理解爲諸子學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將傳統學術分類中“經”、“史”、“子”、“集”之“子”部類中的内容全部收納,因爲這些内容不一定與原創性的思想相關,而且又包括占卜、陰陽、方技等方面。“新子學”尋求一種新的知識體系: 新諸子學派必須從經典中挑選出有創造性的傑出思想家,並闡發出新的文本批評方式來接近他們。而“新”字强調了重視當代文化認同問題和全球化意識之間的重要聯繫。在當前中國文化認同建構中,“新子學”的研究旨在表明諸子學經典的文化特性:
子學根植於中國文化土壤,其學術理念、思維方式等皆與民族文化精神、語文生態密切關係。對相關學術概念、範疇和體系的建構,本應從中國學術自身的發展實踐中總結、概括、提煉而來。“新子學”即是此理念的實踐。如在思維方式上,諸子百家重智慧,講徹悟,不拘泥於具象,不執着於分析。表述形式上,或對話,或隨筆,或注疏,不拘一格,各唱風流。這些都是存在於特定歷史階段的思維方式和話語風格,本不與西方乃至中國當前的思維話語相類。(52)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第14版。
對於西方哲學術語能否應用到中國傳統上這個中西學界争議了百年的問題,方勇從表述的清晰性、分析的準確性和形式的限制性幾個方面,給出了自己的解釋。他在其他文章中也大多提到這個問題,例如在《“新子學”申論》中指出哲學史不是中國本土的事物,而是一門移植的學科(53)方勇《“新子學”申論》,《探索與争鳴》2013年7月,第74頁。關於中國諸子文本和哲學學科的關係,以及學科的跨文化翻譯的問題,也可參考魏樸和《諸子文學之嬗變: 從孔子到韓非子的早期中國思想》,劍橋,MA /倫敦: 哈佛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是把中國的材料套在西方範本中。在他看來,諸子學從一開始就没有致力於純粹的學術與思想標準(54)方勇《“新子學”申論》,《探索與争鳴》2013年7月,第73頁。,因此他們與西方哲學並不相同。他呼籲讀者遵循原初的話語並運用如音韻、文字訓詁等傳統學術研究方法,切入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研究領域,只有這樣才能認識到中國本土學術的真實面貌(55)同上,第74頁。。
人們可能會有這種感覺,追尋傳統的真實性、原初性、獨特性總會伴隨着對西方學術的排斥,就像批評東方主義和漢學主義的那些學者所表現的那樣。但事實絶非如此,方勇和其他“新子學”探索者一直强調這點。早在2012年的“新子學”宣言中,方勇便指出“以中國解釋中國”不足爲訓。對方勇而言,學者不應忘記吸取使得西方學術變强大的東西,即應該取他山之石。所謂“他山之石”,是個體認同建構辯證發展的一個比喻: 西方不僅只是一種挑戰和威脅,相反,熟悉了西方,熟悉了一個和中國文化一樣獨特的“他者”,這是中國學者成功進行文化自我認知的先決條件。在多元世界中以辯證眼光洞察自己是什麽,一定讓人想到歷史上諸子之間的競争之態,二者可以等同視之。這是方勇《再論“新子學”》(56)方勇《再論“新子學”》,《光明日報》2013年9月9日第15版。一文的關鍵論點。諸子在强調人格獨立、精神自由、學派間平等對話、相互争鳴等方面展現了自身的生命力。方勇爲這些觀察尋求依據,摘引了《漢書·藝文志》的句子:“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57)《漢書·藝文志》,《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46頁。
玄華,“新子學”的另一位倡導者,在《關於“新子學”幾個基本問題的再思考》中致力於相互性認同的建構。他切入該問題時也把當代認同建構中的多元性特徵投射到古代: 在一個多元世界,個體總會面對他者,而且個體發展總伴隨着不斷地自我否定(58)玄華《關於“新子學”幾個基本問題的再思考》,《江淮論壇》2013年第5期,第105頁。。自我否定這一概念可以理解爲自我確證的必要組成部分,這很類似方勇前面所引《漢書》語句所激發的思想。兩者都强調接受差異性對於認同建構至關重要。玄華對差異性的呼唤如下文所示:
“諸子學現象”有一個較爲突出的特點是,其内部組成部分之間存在極大差異,相互詰難,乃至否定,但在客觀形式上卻促成了各自獨特性的確立。在學術文化上,任何諸子個體必須在面對他者,尤其是在面對多元的諸子現象本身時,才確立自身。如孔子正是面對老子、子産、墨子、韓非子等時才確立爲孔子。(59)同上。
東方主義和漢學主義的批評者尋求全面拒絶西方方法論,他們具有的隱性自我否定特質在“新子學”這裏的表述中顯得問題更小,矛盾更少,因爲這成了理論正面探究的明確主題,也因爲否定性或者自我否定會轉向它的對立面。關於客觀性問題看起來也如此: 顧明棟致力於學術客觀性的同時運用了修辭的手段,與此相反,“新子學”倡導者試圖概念性的抓住相同問題,從而在認同建構中提供一種系統論證來支援作爲否定與肯定之統一的客觀性。只有這樣,第二步才訴諸於修辭。並非巧合的是,與顧明棟倡導健康的全球漢學話語一樣,他們將自己的事業界定爲一劑良藥: 方勇談到面對全球化時必須關注“中華民族文化的健康發展”(60)方勇《再論“新子學”》,《光明日報》2013年9月9日第15版。,而玄華在文章中依據觀察總結認爲,“新子學”將成爲幫助中國克服“交錯綜合症”(61)玄華《關於“新子學”幾個基本問題的再思考》,第109頁。的良方。他們之所以和東方主義及漢學主義的批評者一樣都使用“健康”這個修飾語,是因爲他們將自己的事業理解成一種認識論的重建。這就是爲什麽對五四運動的探討也會成爲“新子學”重要議題之一。
方勇2012年的“新子學”宣言就對五四運動不加思考地借用西方術語和概念持明顯的批判態度。在這中間,便是上文提到的哲學和哲學史這類概念,方勇從一開始就試圖與之保持距離。他認爲,與“中國哲學”相對應的替代性術語是中國學術(62)方勇《再論“新子學”》,《光明日報》2013年9月9日第15版。。由於梁啓超、胡適等學者推廣西方術語和方法,人們逐漸喪失了對諸子傳統的理論自覺,並且這一傳統的地位也因之下降,成爲哲學史的附庸(63)方勇《再論“新子學”》,《光明日報》2013年9月9日第15版。。
所以五四運動被視爲一段未經反省的自我異化時期,它没有可能辯證地轉化。這也就是“新子學”理論者爲何將自己視爲是對五四的超越,他們直面它而不是像陳小眉在關於西方主義的著作中將兩種話語簡單地聯繫起來。例如,中國文化曾面臨毁滅性的批判,張洪興對這一階段隱喻地使用了“一百餘年的災難”這種説法(64)張洪興《“新子學”與中國文化芻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3年第6期,第80頁。;還有“新子學”另外一個積極的推動者湯漳平,他慨歎“百年來的中西古今之争”(65)湯漳平《“新子學”與中華文化之重構》,《江淮論壇》2012年第2期,第96頁。。五四運動被認爲是造成這些災難的決定性因素,主要是由於它提倡用西方概念盲目地定義自身文化,並且爲了强國的單一目的而去追隨西方的規範和思想。積極的認同建構没有能够實現,原因就在於自我意識的缺失,以及更關鍵的,在跨文化對照中他者意識的缺失。
“新子學”倡導者主張辯證轉化,反對盲目接受西方認同,但同時,他們又推崇這樣一個觀點,把握好西方認同對於成功建立自身認同非常重要。因此,諸如哲學和哲學史這些他們原來批判地與之保持距離的概念,也可以作爲他山之石來借鑒: 形式的限定,準確的分析,純粹的思維等——把握西方這個他者認同建構中理論性知識的特點,把這些作爲理想的樣式來對照自己經歷的傳統,以促進對自身文化更好的理解。這就是爲什麽“新子學”倡導者對於五四運動的認識同樣具有辯證性: 除了和它公開正面相對,他們同時也將自己放入了與五四相關的譜系之中。因此,玄華稱五四運動爲介乎古典時代和“新子學”時代之間的一個階段(66)玄華《關於“新子學”幾個基本問題的再思考》,第105頁。,而湯漳平在論述中國文化重構的時候,描繪了類似的譜系,並運用“復興”這一主題——這是五四時期最具特徵的主題之一。這也是一塊他山之石(67)在五四時期,復興的概念總是跟歐洲的文藝復興聯繫在一起;西方將當前的生命力歸於西方的相關文化經歷,(中國)對自身思想遺産的復興作爲一種事業就是將它接續起來。關於五四時期復興的概念和論述,可以參考傑羅姆·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 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37)》(劍橋,MA /倫敦: 哈佛大學出版社1970年版)和維托夫2012年的文章。,這將我們專注的焦點引向極爲複雜的認知譜系: 諸子思想的復興不僅意味着在中國和西方之間或者今天和五四之間劃定界限,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今天和古典時代之間劃定界限,要把當前階段作爲一個歷史性的獨特現象。這是玄華文章中最微妙的想法之一,他認爲“新子學”與中國古代諸子學派不同之處在於它在全球語境下的文化他者意識,而諸子則没有意識到這一點(68)玄華《關於“新子學”幾個基本問題的再思考》,第106頁。。因此,當代的文化復興應該被理解爲一種轉化和一種對思想傳統的必要重建,而不僅僅是對它的複製:
諸子學的真正覺醒,應該是醖釀於《諸子學刊》的創刊、《子藏》的推出和中國諸子學會的創立,其真正確立則是到“新子學”命題的提出。所謂諸子學自覺,是指將諸子學作爲整體現象研究,同時將其從經學思維與體系的禁錮中解放出來,真正呈現其自身。(69)玄華《關於“新子學”幾個基本問題的再思考》,第106頁。
意識到當前時代具有歷史獨特性,此時代的話語有别於以往的各類話語,這是“新子學”支持者的共識。同樣地,他們都意識到,討論有關民族認同時總包含着政治性内容。學術界既不是政治上的中立者或者獨立於政治議題之外,也不參與到知識與權力間的合謀中,而是作爲公開討論政治問題的主體。方勇,作爲玄華上述文章中提到的“新子學”運動的發起人,曾經在2012年的“新子學”宣言中明確表達自己的政治態度:
在國勢昌盛,經濟繁榮的今天,全面復興子學的時機已經成熟,“新子學”正以飽滿的姿態蓄勢待發。(70)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第14版。
在這裏,文藝復興的觀念——此爲他山之石——作爲重新恢復民族文化的大計,從五四時代起就成爲中國知識分子熱烈論争的主題。將自己的學術活動看作是國家普遍關注的政治議題的一部分,這也反映在“新子學”的支持者們以他們的規劃呼應2011年10月18日中國共産黨的決議之上(71)張洪興《“新子學”與中國文化芻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3年第6期,第81頁;湯漳平《“新子學”與中華文化之重構》,《江淮論壇》2012年第2期。第95頁。決議發表於《人民日報》2011年10月26日第1、第5版,題名爲《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2011年10月18日中國共産黨第十七届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國共産黨的這一決議肯定了“百花齊放、百家争鳴”(72)中共中央委員會決議的文本摘自其官方網站英文版(http: //www.cctb.net /bygz /wxfy /201111 /t20111117_285296. htm) ,本句見原文第5頁。的重要性,“借鑒和吸收其他國家優秀的文化成果”(73)《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2011年10月18日中國共産黨第十七届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2011): 5。,這是由於認識到中國文化的發展“不完全跟上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74)同上,(2011): 6。,需要“增進對偉大祖國和中華民族的認同”(75)同上,(2011): 10。,“堅持發揚學術民主、藝術民主”(76)同上,(2011): 12。,“發揚五四運動以來的革命文化傳統”(77)《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2011年10月18日中國共産黨第十七届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2011): 12。,“學習外國”(78)同上。,“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必要性(79)同上。。
雖然“新子學”對黨的決議顯示出相當的一致性,但是要完成決議中所規定的任務則複雜得多: 對五四運動的看法、身份建構中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的辯證關係、處理概念——除了哲學以外的概念,所有這些都要求極大的自主性和創造性。只有如此,“新子學”才能處理文化復興問題,並且致力於一種多元的民族認同建構。幸虧這一多元性,對辯證方法的采用,以及將文化發展視作政治問題,“新子學”的擁護者不僅克服了與西方文化那種令人絶望的衝突——這是東方主義和漢學主義批評者的特徵——他們還給其他的“山”提供了有益的“石頭”。除其他之外,“新子學”表明權力和知識的聯結對不同文化間的對話不一定是有害的,只要這種聯結能够被自覺地問題化,並且只要不阻礙所有對話參與者感知各自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