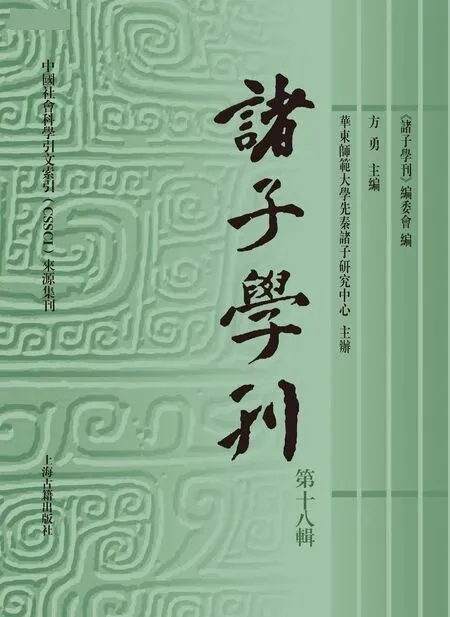開 闔 破 立
——論“新子學”的願與違
(臺灣) 殷善培
内容提要 “新子學”論述有一套嚴謹的方法論反省,先是歸納出歷代“子學現象”,進而由“子學現象”中抽繹出“原創”、“多元”、“平等”、“不尚一統”的“子學精神”,進而以“子學精神”爲導引,整合構建並提出適切的學術走向以供參考。本文以爲“子學現象”本是衰世現象,所謂的“子學精神”或許只是論者美好的嚮往,恐非歷史事實;對“新子學”亟欲去之的兩個框架,本文也有不同意見,認爲“新子學”論者對傳統尊經批判過於嚴苛,而對現今學科本位的教育體制批判又嫌不足;最後並建議以十多年前中國古典文論界所提出的“中國現代學術話語”作爲參考系,思考可能遇到的挑戰。
關鍵詞 新子學 子學精神 衰世現象 通人之學 話語權
一
學術研究因時代的差異、觀念的變革、方法的更迭,甚至意識形態的左右,積累到一定程度時自然會有“改寫”與“新”的呼聲,從孔恩(Thomas Kuhn)的“典範理論”(paradigm)來説,這正是“典範革命”必然的現象(1)孔恩著,王道還譯《科學革命的結構》,臺北遠流出版社2004年版。。春秋戰國“禮壞樂崩”,“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出現先秦諸子的百家争鳴;秦及漢初,法家、黄老迭興;武、宣之後儒學獨盛,諸子學成了“家人言”(2)錢穆《兩漢博士家法》,《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年版。,反映到劉向、劉歆《七略》、班固《漢書·藝文志》目録學的現象就是六藝與諸子的判别(3)《四庫全書總目》云:“自六經以外立説者,皆子書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别而列之,名品乃定。”。此後經學不與諸子并列,後世“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録學,或宗四部,或依違《七略》,唯均不曾撼動以儒家詮釋“六經”的格局,此即所謂經學凌駕史、子之上也。及至有清末造,西力東漸如摧枯拉朽,雖中西體用之争時出,但“典範危機”已無可挽回。光緒廿四年(1898)廢八股,光緒卅一年(1905)廢科舉,一夕由四部成了七科(4)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對此一問題有深入論述。,發生了“典範轉移”,且更從制度層規定了新典範的正當性,從此舊典範似游魂,倉惶間無力面對新局!然而新典範畢竟是徹徹底底的舶來品,自然科學還無所謂,但人文學頓時失去了“話語權”,削足適履,學步蹣跚,更兼以氣運陵夷,學術也成了文化殖民地,學術買辦挾術語横行,百年來徹底喪失了學術主體性。不過對有數千年文化傳統的中國而言,終究不滿足這般邯鄲學步,由剥返復只是時間問題,潛沉既久,各領域檢討反思的聲音就交相迭起了。
“新史學”、“新文學”、“新儒學”、“新道家”、“新墨家”、“新國學”、“新經學”等,乃至各種文化復興運動,此起彼落,從未間斷。近年“新子學”後來居上,短短數年内引發數百篇討論文章,衆聲喧嘩(heteroglossia),成功引領了當代學術史上的熱議及反思。這一現象自是與催生者方勇教授的當仁不讓、捨我其誰的使命感有關,更重要的是“新子學”有相當完整的論述與實踐策略,開闔破立之間,結構佈局嚴密,諸家各種挑戰與詰難其實多不出方勇教授的設想。只是對“新子學”構想與理念,筆者亦和多數學者一樣,有認同也有疑惑,疑義相析,求全責備,希望有助於此一議題更臻完善。
二
方勇教授的“新子學”構思,首先觀察到中國歷史中出現的“子學現象”。所謂“子學現象”,依方勇教授的理解,是指“從晚周‘諸子百家’到清末民初‘新文化運動’時期,其間每有出現的多元性、整體性的學術文化發展現象”,也就是“崇尚人格獨立,精神自由、平等對話、相互争鳴”的現象。方勇教授更進一步指出“子學現象”藴含了“子學精神”,所謂“子學精神”是“原創性的、多元性的”,是“不尚一統而貴多元共生”,是“多元、開放、關注現實”的,而“新子學”便是對“子學精神”的“提煉”、“繼承”與發揚!方勇教授指出“我倡導‘新子學’,不僅意在呼籲革新傳統諸子學的研究方式,更主張從‘子學現象’中提煉出多元、開放、關注現實的‘子學精神’,並以這種精神爲導引,系統整合古今文化精華,構建出符合時代發展的開放性、多元化學術,推動中華民族文化的健康發展”,是“對世界和人的本質的重新理解,它是子學的真正覺醒和子學本質的全新呈現,將爲未來學術文化的走向提供選項”(5)方勇《再論“新子學”》,葉蓓卿編《“新子學”論集》,學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2頁。。然而要推動乃至實踐“新子學”,就要跳脱“兩個框架”的限制,框架之一是傳統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的尊經現象,框架之二是現代學制學科化後的割裂。方勇教授對前一框架要“去尋覓經學觀念籠罩下被遮蔽的東西”,對後一框架則要“重新劃定研究對象,調整研究思路,補上學科框架下剪裁掉的東西”。更具體地説,對前一框架要“要突破傳統四部分類法,把子學作爲真正的學術思想主流去把握,對於納入經學的孔子、孟子等作離經還子的處理,明確區分經學化的儒家與子學化的儒家,重新清理和整體考察歷代子學,尋繹中國學術的内在肌理”。對後一框架要“在古典的語境下摸索古人的問題意識和表達方式”。跳脱框架之後才得以“以返歸自身爲方向,借助釐清古代資源,追尋古人智慧,化解學術研究中的内在衝突”(6)方勇《“新子學”申論》,葉蓓卿編《“新子學”論集》,第37~49頁。,也才能够“與西學建立正向關聯”(7)同上。。
由上述扼要歸納就可知方勇教授對所提出的“新子學”有着相當透徹的認識與反思,所以能從“子學現象”尋繹出“子學精神”,再由“子學精神”深化爲“新子學”的主張。從兩個框架跳脱,一方面破除尊經傳統的制錮,一方面解開西方學科思維對中國傳統的曲解,再以全新的姿態面對西學回應世界。
當然“新子學”延伸的探討並不是如此單向性,“新子學”在消解經學獨尊後更要成爲“國學”的主體;且稱以經學爲主的國學是“舊國學”,以子學爲主體的國學才是“新國學”(8)方勇《“新子學”構想》,葉蓓卿編《“新子學”論集》,第1~11頁。,因爲傳統以經學爲主的國學是以不對等的立場看學術,唯有以子爲主的國學才能平等看待各種學説。其論甚弘,但真的能這樣嗎?
三
先就“子學現象”來看,中國歷史中的“子學現象”是否真的就是“崇尚人格獨立、精神自由、平等對話、相互争鳴”?事實上歷代的“子學現象”幾乎都是王綱解體下的“衰世現象”,先秦時期尚有稷下學宫的加持,“不治而議論”,促成了百家争鳴,孟子的“予豈好辯,予不得已也”就是稷下諸子的寫照;漢末中原板蕩,幸好還有一方净土荆州勉强談論着“新學”;明末諸子反省文化力度强雖强,但聲勢與前相比就稱不上浩大;清末民初言路雖較漢末、明末大開,但和租界地治外法權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子學現象”是否真存在着“人格獨立、平等對話、相互争鳴”的榮景?所謂的“子學現象”會不會只是一種寄意深遠的美好的想象?況且,此刻“新子學”提出的年代不是歷史中子學興盛時期的衰世,而是屈辱百餘年後的再興,理想的“子學現象”應是面對未來期許而非緬懷過去!
因此,從這樣的“子學現象”提煉出的“原創的、多元的”、“不尚一統而貴多元共生”、“多元、開放、關注現實”的“子學精神”,還有討論的餘地。先秦諸子多爲用世、救世之學,本不在乎原創、多元,且所謂“諸子百家”真正有原創性者幾何?“多元”到什麽程度?而所謂“不尚一統”,是“不能也”,還是“不爲也”?我看恐怕不是“不爲也”,而是時遇上的“不能也”吧!至於“關注現實”肯定是有的,所以若有“子學精神”,“時代性”應該是明確的一項,其次或可加入“議題性”,唯有議題明確且“開放”方足能真切地回應時代問題。
方勇教授勾繪出的“新子學”願景是:
“新子學”所提煉出的“子學精神”,是在揚棄經學一元思維和大力高揚子學多元思維的前提下,對世界和人的本質的重新理解,它是子學的真正覺醒和子學本質的全新呈現,將爲未來學術文化的走向提供選項。(9)方勇《再論“新子學”》,葉蓓卿編《“新子學”論集》,第12~22頁。
我們倡導子學復興、諸子會通,主張“新子學”,努力使之成爲“國學”新的中堅力量,非爲發思古之幽情,更不是要回到思想僵化、權威嚴厲的“經學時代”,而是要繼承充滿原創性、多元性的“子學精神”,以發展的眼光梳理過去與現在,從而更好地勾連起未來。(10)方勇《“新子學”構想》,葉蓓卿編《“新子學”論集》,第1~11頁。
簡言之,就是“揚棄”經學、“繼承”子學。若參照方勇教授另一種“照着講”、“接着講”的語詞:
所謂“照着講”,就是要真實地領會古人,探究其精神,理清其脈絡,而不是隨意講解,任意切割。對於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積極借鑒,也要客觀分析,認真吸取。所謂“接着講”,就是保持學術的時代性品質,認真觀察社會,思考未來,把學術研究真正問題化,着重討論根基性的問題,把中國古人的真實洞見引申出來。這些當然是艱苦的工作,“新子學”願意直面中國學術的轉型,嘗試作出自己的解答。
既要“照着講”,又要“揚棄”,是否有内在的衝突?這涉及了兩個框架的問題,且留下節再論。“新子學”的願景引領“新國學”的實踐,令人好奇的是: 這樣的“新子學”理路下,是否還允許有“新儒家”、“新道家”、“新墨家”、“新經學”的存在?若允許各種學説“多元共生”卻不認同這些家派的存在,這種“新子學”只是另一種新獨裁,這自然不是方勇教授所主張的“新子學”;但若“新子學”接受各學派的衆聲喧嘩,若是平等而毫不介入地面對各學派之間争勝的情況,這時的“新子學”不過就是一種“現象”,又如何能在黨同伐異下保持“新子學”維持甚至堅持不尚一統、多元並存的“精神”?可有維繫這種平等自在的方法?若没有維繫平等、自在、多元的方法,“新子學”會不會成了這時代的“新雜家”、“新道家”?雜家以切用爲主,可以不在乎主體性;但道家反思現象,保存價值,會不會轉而出現“新黄老”,成了思想警察?
四
方勇教授對“兩個框架”着墨甚深,尤其是第一個四部分類的框架,方勇教授主張非常明確:
所謂子學之“子”並非傳統目録學“經、史、子、集”之“子”,而應是思想史“諸子百家”之“子”。具體内容上,則應嚴格區分諸子與方技,前者側重思想,後者重在技巧,故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譜録均不在子學之列。由此出發,我們結合歷史經驗與當下新理念,加强諸子學資料的收集整理,將散落在序跋、目録、筆記、史籍、文集等不同地方的資料,辨别整合、聚沙成塔;同時,深入開展諸子文本的整理工作,包括對原有諸子校勘、注釋、輯佚、輯評等的進一步梳理;最終,則以這些豐富的歷史材料爲基礎,綴合成完整的諸子學演進鏈條,清理出清晰的諸子學發展脈絡。依據子學發展完整性,再進一步驗證晚清民國以來將《論語》《孟子》等著作“離經還子”的觀點,復先秦百家争鳴、諸子平等之本來面貌,並重新連接秦漢以後子學的新發展。(11)方勇《“新子學”構想》,葉蓓卿編《“新子學”論集》,第1~11頁。
這一段文字有幾點值得注意:
一是反對從四部分類的“子”來理解“新子學”之“子”。參照方勇教授多篇文章中提到的理由,是因爲“四部分類法中經、子先後的劃分使用的是價值標準,推崇的是所謂‘常道’,而不是依據學術標準講‘學問’”(12)方勇《“新子學”申論》,葉蓓卿編《“新子學”論集》,第37~49頁。,更根本的是四部分類本來就是“尊經”,史、子、集與經不在同等地位,經是本是源,史子集只能是末是流,既然要提倡子學,尊經卑子觀念的四部分類當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只説“新子學”是諸子百家之“子”而不是經史子集之“子”就能與傳統尊經觀念切割乾净?“新子學”反對獨尊經學,但反不反對“史、子、集”的分法?四部分類形成了有主有從的通人之學,與千百年來的價值理念息息相關,“新子學”不也是提倡通人之學以對抗學科化分裂的危機?打破經學獨尊,離經還子,又該如何面對“史、子、集”的分類?況且就算反對尊經,又豈能動摇早已積澱爲文化基因的經學思維?更遑論“史、集”也存在諸如章學誠的“六經皆史”,焦循、阮元對集部的反思,析經還子是否小看了其中的複雜性?
二是嚴格區分諸子與方伎。《七略》《漢書·藝文志》的“諸子”、“數術”、“方伎”在四部分類中的合成“子部”,歷代子部的領域不斷擴大,及至《四庫全書》的子部更可説是集子部之大成囊括了14類,“新子學”着重在學術思想,將着重“技巧”的方技屏除,但道與術、道與藝,愈往古就愈不能分,道家和醫學甚至原始道教難以分割,而墨家去掉了守禦之術就不是完整的墨家,陰陽家與方伎關係更密切,兵家更不可能只在紙上談兵,這些技術類若都去除,“新子學”就只剩理論,只有道而無“術”無“藝”了,這對“子學”是擴大還是限縮?而且,“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譜録”亦都有其傳承與思想,“術數”類更是許多時代知識分子賴以“知命”或消遣的工具,勞思光先生對術數的研究就是一例(13)勞思光著,劉國英編《虚境與希望: 論當代哲學與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若割裂這一部分,不也就陷入了方勇教授極所欲跳脱兩種框架“遮蔽”、“割裂”的迷思嗎?且近來“新子學”論者也開始推展“子商”,若準此,“子商”説法是否也該在摒棄之列?
三是諸子學資料的收集整理。這正由“子藏”工程持續推動中,其價值自不在話下;諸子學資料收集梳理之後,試着清理出諸子學發展脈絡,也就是建構諸子學史,這一企圖當然是想建構出有别於經學傳統的學術史觀,這點當然該做。方勇教授在這方面超邁前賢,令人由衷敬佩。
四是消解經學的權威性,“離經還子”,諸子平等。這點清末以來就已經在做了,也没什麽問題;但方勇教授的“離經還子”可不是單純以諸子視之。爲了跳脱尊經的框架,方勇教授援引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之説:“經學的特點是僵化、停滯,子學的特點是標新立異,生動活潑。”這種粗糙的二分法本非嚴格的學術語言,可怪的是方勇教授似乎非常認同這種講法,甚至説:
經學在四部中占據首要地位,往往並非緣於其自身的學術價值,而是更多地得益於政治力量的支撑,其獨尊地位常常是權力刻意營造的學術假象。我認爲,這才是真實的經、子關係。所謂“新子學”,就是要突破傳統四部分類法,把子學作爲真正的學術思想主流去把握,對於納入經學的孔子、孟子等作離經還子的處理,明確區分經學化的儒家與子學化的儒家,重新清理和整體考察歷代子學,尋繹中國學術的内在肌理。
這段話其實是非常有争議的,反對獨尊經學無妨,提倡“新子學”是學術自由,建構諸子學的宏願亦極可佩,説經學獨尊是由政治力量的支撑,也不算過份,但順此而説經學的獨尊地位是“學術假象”就未免過頭了。儒術獨尊造成的影響已是事實,拉下經學就代表可把子學當學術主流去把握嗎?經學傳統的存在是事實,在經學傳統下出現的注疏學傳統也是事實,這是以往存在的現象,這種存在是無從否定的。“新子學”可以建構屬於“新子學”的詮釋傳統,但不必以取消乃至否定經學傳統的事實爲前提。
相較於對經學獨尊框架的撻伐,方勇教授對現代學制框架的批判火力明顯減緩許多,甚至一開始就提到“國學無法與現代學制抗衡”(14)方勇《“新子學”申論》,葉蓓卿編《“新子學”論集》,第37~49頁。,這當是指所謂的“舊國學”了,但對方興未艾的國學院也不認爲有與現代學制相抗衡可能,以“新國學”主體自期的“新子學”,居然也只是保守地試着“對現代學術分科式研究的修正”,這點筆者較有意見。傳統的四部之學實是通人之學,與現代學術以知識分科爲主的專業本不相侔,現今教育雖然仍是分科教育,但長久以來就不乏史諾(Charles P. Snow, 1905—1980)“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式的反省,之後的科技整合(Interdisciplinarity)、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博雅教育(Liberal Arts)、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呼聲此起彼落,今日大學也漸漸出現以學程(program /concentration /major /course)取代“科系”的嘗試,提倡跨域學習,樹立了從I型人到T型人、π型人的轉型,這固然是因應時代變化,突破科系的局限,但何嘗不是對古典精神的回歸?“新國學”當此之際豈能不思有所興革?宋代性理學的推展雖然與王安石改科考有直接關係,但宋代尤其是南宋的書院蔚爲一時之盛,獨立於官學之外,講會制度爲後世所艷羨,朱子延請陸象山講學白鹿洞書院更是學術史上的動人一幕。書院精神本就是獨立於體制外的抗衡機制,臺灣民間長期存在着講學傳統,宗教及商業背景的講學暫且不論,有志之士推動的講學從未間斷,如“德簡書院”是建築師王鎮華所設立,“日月書院”是作家馬叔禮所創立,這種危微精一、精神薪火相傳,才是寶貴的文化資産。今日的中國已不再是百年前面對西學潰不成軍、毫無招架之力的中國了。近年來中國的留學生日增,各地紛紛增設孔子學院,若要跳脱百年來學科的框架就該以古典“通人”之學的教育理念當“新子學”的“議題”,才算是有主體性且有特色的回應。
五
關於“新子學”如何面向世界,方勇教授的論點不外是將世界等同於西方,例如説“所謂世界性,指的是現代中國的學術必須與西方現代學術處於一個平臺上,能够與其他國家學術相互理解。所謂中國性就是這一學術又必須是帶有中國屬性的,是中國獨特視角、立場、方式下的産物,對於我們自身是必要的,對於其他國家是有價值的”(15)方勇《再論“新子學”》,葉蓓卿編《“新子學”論集》,第12~22頁。,以及“‘新子學’不提倡所謂中西融合的隨意性研究,‘新子學’希望以家族相似的原則處理傳統學術與其他學術體系的關係。所謂家族相似,就是在中國複合多元的學術中找到與其近似的資源,嘗試引入其視角,從而開闊自身的理解。因而我關注現代語境下傳統資源的現代轉化,對各種嘗試工作保持樂觀。”(16)方勇《“新子學”申論》,葉蓓卿編《“新子學”論集》,第37~49頁。這樣的論點在我看來還是太過保守,還是不對等的態度,我們不妨看看中國古典文學理論界對類似問題的思考方式。
四川大學曹順慶在《重建中國文論話語》就提出:“建立屬於我們自己的從而是具有中國文化精神特質的中國現代學術話語系統。它必須是具有中國文化精神特質而又吸收全人類文化成就的新型話語系統。”但要如何建立,曹順慶進一步提及:
中國現代學術話語系統絶不能一蹴而就,一朝即成。因此,我們祇能從一個個帶根本性的具體問題入手,以具體問題爲中介讓中西理論進行對話,在對話過程中凸顯中西理論各自獨特的聲音。而這也就意味着如下三個方面: 其一,我們所選擇的問題必須是國際學術界共同關心並且具有重要理論意義的問題,這樣既能對這些問題的解決起到實質性的推進作用,又可以在言説這些問題時以無可争辯的事實顯示中國傳統學術話語系統的言説能力,從而使中國現代學術話語系統在逐步建立的同時就取得其應有的話語權力。其二,我們必須盡量讓對話各方的聲音得到最爲清晰的呈現,祇有這樣纔能進行最有成效的對話,而不是獨白,或者是壓制某方的聲音使之不能被完全地表達出來並把不屬於它自己的觀點强加給它。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就某一具體問題將中西雙方觀點的具體的歷史面貌清理出來,讓它們以最爲完整的形態參與對話。這一點對於中國傳統理論來説尤其顯得必要,多年來我們比較多地運用西方理論來切割中國傳統文化和學術,往往不是歪曲、忽略事實,就是根本不對中國傳統進行切實的研究,祇是想當然地以爲它應該如何如何。其三,在對話終了,應該就這些具體問題以中國傳統學術話語爲基礎吸收西方理論上精華,融會鑄造出一些基本的理論和看法,並體現在若干核心概念或範疇之上,從而爲建立整個中國現代學術話語系統打下堅實的基礎,作好充分準備。(17)曹順慶《中國古代文論話語》,《緒論: 重建中國文論話語》,四川巴蜀書社2001年版,第2~3頁。
曹順慶提出的理論的“議題性”、“清晰、完整”且“多元對話”這三點和方勇教授的主張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誠所謂英雄所見略同,文學理論受到現代學術知識體系制約和思想領域並無二致,也在努力尋找“話語權”。不過,文論界對此話語的反思已超過十五年了,後期進展似乎不大,關鍵何在?就是十五年來社會文化及國際局勢亦有相當幅度的變異。其間種種,頗值得“新子學”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