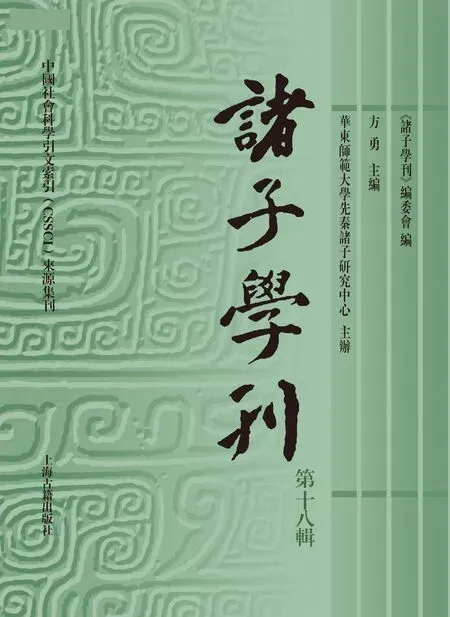淺説“新子學”之實踐
揣松森
内容提要 “新子學”理念提出以來,影響日益深廣,學者們從不同的面向對其内涵進行理論闡釋和廓清,使之更加充實和豐富。我們認爲,“新子學”不僅是一種理念,而且更是一種實踐。經過數年的積澱,對“新子學”之實踐方面的探討就十分必要和迫切。“新子學”上承先秦諸子精神,而先秦諸子皆“務爲治者也”(《論六家要指》),其所追求的是一種天、人和社會的秩序性,這就啓示我們今天的人文研究不能把“人”排除出研究的各個環節,也不能以“天人關係”似或虚無縹緲而棄之不理、置之不論。在理清以上兩點的基礎上,“新子學”之實踐應特别提點出主體性和禮義闡發及禮制建設等,並着重在學術與教育等領域深耕細作,從而積極推動社區乃至社會的建設和完善。在“新子學”理念的引領下,學者們既就各自專長着力用功,又在一些交叉領域、公共領域通力合作,再加上廣泛社會力量的凝聚,那麽不難建設一個心靈有安頓、學術有歸宿、社會有秩序、未來止於善的學術共同體和生活共同體。
關鍵詞 新子學 先秦諸子 先王經典 經世之治 主體性 禮義闡釋 創造性轉化
方勇教授於2012年發表《“新子學”構想》(1)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第14版。一文,正式提出“新子學”理念,引起海内外學者的廣泛關注。隨後,他又相繼發表《再論“新子學”》(2)方勇《再論“新子學”》,《光明日報》2013年9月9日第15版。《“新子學”申論》(3)方勇《“新子學”申論》,《探索與争鳴》2013年第7期,第73~77頁。《三論“新子學”》(4)方勇《三論“新子學”》,《光明日報》2016年3月28日第16版。等文章,對“新子學”的相關問題分别進行闡述;與此同時,相繼召開五次“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者們從不同的面向對“新子學”内涵進行理論闡釋和廓清,使之更加充實和豐富。我們認爲,“新子學”不僅是一種理念,而且更是一種實踐,那麽在已經取得的豐碩成果的基礎上,對“新子學”之實踐面向進行探討就十分必要和迫切。
一、 理清人文學術研究的兩個認識誤區
方勇教授《三論“新子學”》文中説:“傳統文化研究創新首先需要回到中國思想的原點,即先秦時代的諸子學傳統。”(5)方勇《三論“新子學”》,《光明日報》2016年3月28日第16版。即是把先秦諸子學傳統作爲中國思想之原點,而“新子學”則要上溯本原,直承先秦諸子學傳統。先秦諸子各就所見發表學説,其内容雖彼此不一、互有短長,但其歸宿皆“務爲治者也”(《論六家要指》)。我們認爲,“務爲治”是先秦諸子争鳴的基面,也是先秦諸子學最基本的傳統。我們要繼承這一傳統,就應克服當前人文學術研究的兩個認識誤區: 一是爲講科學精神而把“人”排除出研究環節,二是對天人關係問題或以其虚無縹緲而棄之不理、置之不論,或僅作義理闡述,缺乏對天人關係知識基礎的研究。
先談第一個方面的問題。中國古代學術是一種求治的傳統,觀司馬談説諸子“務爲治者也”(《論六家要指》),司馬遷論“六藝於治一也”(《滑稽列傳》),可見該傳統之久遠。所以,中國從來都很重視賢能政治、君子之行,賢者和君子其實集學術與政教爲一體,故而在中國傳統學術當中特别突出“人”的地位。然而近代以來,中國因閉關自守而國運不昌,受到西方列强的極大衝擊,連帶着思想學術也受到西學强勢衝擊。這種衝擊帶來有益的一面是,因借助西方科學方法而使中國傳統學術的某些研究更加精密,比如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對墨經的研究就得益於他西方邏輯學知識的學習。但這種衝擊的弊病也是極大的,早在民國時期,錢穆就曾批評近世史學中的所謂“科學派”(即考訂派)道:
至“考訂派”則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爲局部窄狹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爲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唯尚實證,誇創獲,號客觀,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6)錢穆《國史大綱·引論》,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4頁。
錢先生所批評的現象在當時及其後並未減緩,反而隨着學科體系壁壘的加强和國内高校的市場化,而在20世紀90年代後愈演愈烈。“科學派”的觀點是: 學術研究講求科學性,不能摻雜個人好惡、傾向於其中,以免影響結論的客觀性和科學性。這其實是把學術僅僅當作知識看待,而且表現出對科學方法的迷信。科學是一種方法,也是一種精神,其核心是講求實證和實事求是;而且科學方法的運用在人,科學研究的歸宿亦當在人。舉例來説,朱熹作爲宋代理學家,其學問有自身的追求和傾向性,但這並不妨礙他研究名物制度時運用實證的科學方法和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凱恩斯是近代英國經濟學家和邏輯學家,其研究當然講究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但在其歸宿上他仍可堅持推動充分就業和建立基本福利政策的傾向性。所以,學術研究不能因講方法的科學性,而模糊甚至消解學術研究的歸宿。特别是對人文研究來説,如果把“人”排除出研究的各個環節,就等於放棄了人文研究的傳統,也放棄了人文所以爲人文的根本。試想在科學强勢的今天,若只講知識性的考證、分析而放棄智慧獲得、德行修養、知行合一及終極關懷等不論,那麽人文研究的科學性果真就能與數理研究的科學性相匹敵?很明顯是不可能的。但這並不是人文研究的缺陷,反而正突出了其特質所在——人文研究歸根到底是一種價值性的研究。
再來談天人關係方面問題。人對天人關係的認識,是指導和制約人類行爲的基礎。通過歷史和考古可知,特定人群的特殊習俗和社會組織形式,往往受到他們對天人關係認識的影響;天人關係的認識隨時代而漸漸變化,那麽相應的舊習俗和舊的社會組織形式也會被新的取而代之。即便在科學發達的今天,每一次對宇宙探索的新成果,每一次對生命本原的新認識,都仍直接影響着我們的行爲和思想。天人關係是中國傳統學術探究的主題,也是今人打開中國古代思想寶庫的一把鑰匙。然而,我們當前的人文研究,或者以爲這個問題在科學發達的今天不必再講,或者守着傳統的名詞大發高論,而忽視其知識基礎的研究。比如,對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觀念,有人就覺得這是傳統迷信,以爲這是古人故作高深,以爲在科學發達的今天不必再講這類虚無縹緲的東西,而對其加以否定。可以説,這是一種厚今薄古的態度,實並未理解科學的精神。但也有另外一些人懷着對中國文化的特殊感情,以“天人合一”作爲中國哲學的高明之處而以此自高,動輒就“天人合一”、“重玄”、“齊物”、“逍遥”,但是對中國古代講天人關係時所涉及的天學、星占、律曆、陰陽、五行、養生等知識,以及天神信仰、化生觀念、天生人成、三才之道等並未加以瞭解和研究。那麽,這就是對古代的一種迷信,失卻了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精神。我們認爲,恰當的態度應當是,在瞭解古人知識背景的基礎上,探討古人對天人關係的認識,並梳理出這種認識隨着社會的發展而變化的軌迹;而且,吸收最新的物理學、宇宙學、地理學、考古學及生物分子等生命研究的成果,以新的知識作爲基礎,接續探討天人關係的人文傳統而作出新時代人文研究的闡釋和發展。當然,這涉及交叉學科的知識,處理起來有很大難度,但既然是做研究就要有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就要有終極關懷的追求,就當以謙卑和求是的態度勉力爲之,而不能畏難不進而固步自封。
總之,我們的人文學術研究應克服當前這兩種誤區。“新子學”之實踐,也只有首先克服這兩種誤區,然後才能更好地繼承傳統和轉化創新。
二、 突出主體性和禮義的闡發
“新子學”之實踐,在最廣泛意義的精神追求上,應該突出對人的主體性和禮義的闡發。高揚的主體精神和最廣泛的秩序追求,是先秦諸子學最核心的精神,也是我們當前繼承和轉化諸子學傳統時最應該突出的核心精神。
首先,在繼承和創造性轉化諸子學傳統時,應該突出對人的主體性精神的闡發。先秦諸子高揚的主體精神,是在周初以後日漸濃厚的人文精神的環境下醖釀的結果,是先秦諸子對人之所以爲人這一問題進行思考、反省的升華。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萌發較早,至少在殷周易代之際就開始了。關於這點,看《尚書》等的記載就可以十分明顯地感受到。究其原因,可能主要因爲小邦周取代大邦殷這一現實,使“周初的統治者深感天命的無常,轉而强調自身的德行修養,‘人’的價值和人文精神漸漸受到强調”(7)揣松森《論“新子學”的内涵及其意義——兼談子學與經學之别》,《集美大學學報(哲社版)》,2016年第 3期。。在那之後,雖然不是没有談論天命鬼神者,但多對之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在上層士大夫和知識階層間,逐漸發展出一套從氣和陰陽生化生命乃至萬物的理論和知識,人們對於天人關係的認識也前進了一大步。至孔夫子廣收門徒,有教無類,迅猛地擴大了掌握知識的群體,催化了知識的傳播、碰撞和升華,以至在夫子之後逐漸形成一股辨别德位、探討人性及情欲、定位天人關係的思潮。在這個過程中,人的主體性精神和價值,在先秦諸子身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張揚。這種高揚的主體性精神,不僅表現爲一種對生命價值的自信和追求,而且更體現在他們對“人”之責任的擔當。我們看墨子追求君子爲人,“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莊子·天下》)地爲天下興利除害,就可以知道這種主體性精神之可貴!看宋鈃“周行天下,上説下教”,以“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天下》),就可感受到其情懷之博大!再看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的豪氣,以及“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公孫丑下》)的豪邁,則無不被其主體的自信與擔當所感染。再看《中庸》“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大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及《易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繫辭上》),就可以明白諸子對人之定位的高致和對人之擔當精神的期許。哪怕道家之莊生,也因深感現實生命之痛楚而苦苦爲衆生尋求安頓生命和精神之所在。也許,這就是我們常常能在先秦諸子身上感受到强烈生命感,以及他們爲衆生而不惜勞苦思索、奔波的情懷,並深深爲之感動的原因。其實,這種感觸的背後,我們又何嘗不是碰觸到了自身人性中主體性欲求張揚的部分呢。
時不分古今,地不分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現代社會也是如此,雖然存在着信仰的多樣性,但對人的肯定和對個體尊重已經是一種潮流和共識。這與先秦諸子高揚的主體性之間是共通的。不過,現代社會對個體的尊重有時會顯得有些極端,就是容易造成對主體責任要求的缺位,發展到偏激的程度反而與人文精神有相背離之處。相比之下,先秦諸子傳統下的主體性的張揚,則更加凸顯出其價值和優勢。所以我們以爲,“新子學”在現實實踐上,應該繼承這一傳統,並突出對主體性精神的闡發,從而實現創造性轉化,爲現代社會精神的建設貢獻智慧。
其次,在繼承和創造性轉化諸子學傳統時,應該突出對禮義的闡發。我們這裏所用“禮義”一詞,是從作爲最普遍秩序層面的“禮”之精神的意義上來講的。以往人們對先秦諸子有些誤解,就是好像他們是反傳統的,要衝破甚至抛棄“禮義”;其實,先秦諸子本身是在當時傳統思想的滋潤下成長和發展起來的,而且他們的宗旨也都是要在秩序正日益破壞的情況下,探討和追求秩序回復、重建的可能和路徑。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古人的評述中得到證明。如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説:“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8)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2頁。司馬遷在《滑稽列傳》中説:“孔子曰: 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9)司馬遷《史記·滑稽列傳》,第1154頁。可以看到,先秦諸子與六藝傳統在其歸宿上並無二致,都是追求一種“治”的狀態,也就是都同時追求一種内在和外在的秩序性。另外,我們從先秦諸子的思想發展中也可以看到他們對“禮義”的追求。一者,先秦諸子從内在尋求秩序性。我們知道,孔子當時對德位問題已有較多關注,而他之後的諸子則從人性及天人關係方面探求建立社會秩序的内在根源。《中庸》説“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對從作爲秩序根源的天落到人之内在的性,再落實到現實層面建立秩序的教,有極爲清晰的描述。他們還認爲,在這個過程當中,不管是人自身還是其他萬事萬物,在天地將其生出之後,實際上仍處在尚未完成狀態,其存在狀態的完滿則有待於人在通過修持而完滿自性的基礎上去“成物”。二者,先秦諸子也追求外在禮制的建立,並特别重視“禮義”的闡發。先秦諸子對倫理關係都是承認的,即便如莊子也不得不説“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人間世》)。儒家主張恢復和建立禮制的態度是很明確的,另外儒家先師也極重視對禮義的探討和闡發。道家似乎反對禮制,他們處處提防具體之禮文可能産生的弊病,但他們能從本原上對禮進行反思,實際上也就涉及儒家先師所重的禮義問題。不管是正面立論,還是負面反思,他們對禮義的探討在現實上對禮制的制定都極有價值。
禮制隨時代而發展變化,每個時代都可以根據現實的要求進行禮義的闡發,從而建立適合當時的禮制規範,所謂“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禮記·禮運》)。對禮義的探討,在内在方面與當時對人性及天人關係的認識有莫大關涉。這在當今也是如此。現代社會對於人性及天人關係的看法,隨着生命科學及物理學、生物學的發展而日益加深,這是我們進行禮義闡發的知識基礎。當代對主體價值的肯定和個體的尊重,已經成爲人們的共識,這可以説是我們闡發禮義的一項價值觀基礎。當下,隨着全球交流的加深和加速,不同信仰和價值觀之間的交流和相處模式正在探索和形成之中,這就需要我們以共識的價值觀和知識爲基礎,闡發當代的“禮義”,從而推動一種最基本、最廣泛的内在和外在秩序的摶合和建立。就國内來講,中國正處於文化轉型和發酵創新的時期,要建立一種寬緊適度且在個人與禮制之間達成平衡和良性互動的秩序狀態,首先需要我們闡發新時代的禮義。這就是我們認爲“新子學”之實踐應突出禮義闡發的理由和用意所在。
三、 着重在學術與教育等領域用功
作爲一種理念的“新子學”,其實踐的範圍應當涉及社會的各個領域和方面,但從目前的現實角度考慮,我們認爲“新子學”應該着力用功的地方是在學術與教育領域。因爲一方面,“新子學”在學術和教育領域的力量比較堅實,而且本色當行,最能也最應該在此展示“新子學”所追求的學術研究境界和現代精神風貌;另一方面,當下的學術和教育已經遠非封閉在學院之内的物什,而是已經越來越要走進廣闊的社會,而面向各個層次的文化需求的對象,這片廣闊的天地正是“新子學”發揮其學術與教育功能來傳播時代文化、孕育新思想、培養思想者、引領思想風尚的用武之地。
具體就學術方面來講,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做功夫: 一是,扎扎實實做好傳統文化的闡釋與轉化。闡釋與轉化的基礎是,首先要盡可能地做好基礎文獻的收集和整理,並進而對研究對象做一番歷史的研究,就是盡可能地釋讀文本的原義及其發展、衍變的脈絡。如果這一步工作不做,或做得不够扎實,那麽接下來的闡釋就可能流於牽强附會,而這種無根的研究就無法讓人信服,也不能切實推動學術研究的進程。有了堅實的基礎,闡釋者就可以闡發文本中所藴含的豐富意涵。當然,我們所謂的闡釋並非爲闡釋而闡釋的純粹知識性解説,而是擇取文本中所藴含的古今相通的話題、情感、困境及制度、禮義、評判等進行思考、探討和發揮,作出我們當代人的新看法、新思路、新判斷。在這一點上,我們以爲儒家先師對六藝的解釋經驗就頗值得借鑒。比如,子夏闡釋《春秋》時説:“《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10)陳奇猷《韓非子集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17頁。是從《春秋》中提煉出防微杜漸的歷史經驗。又如,帛書《易傳·昭力》從《周易》中闡發出“卿大夫之義”、“國君之義”、“商夫之義”、“邑餘(長)之義”、“戎夫之義”、“處女之義”等,幾乎囊括了社會所有階層人員所需的思想資源。其他,如王式教授昌邑王《詩》三百篇,而闡發其中忠臣孝子之義以作諫書,董仲舒闡發《春秋》大一統、立元謹始、改制質文、循天之道等義而推動儒術獨尊,也都可不同程度地爲我們提供借鑒。如果説闡釋仍立足於傳統的話,那麽轉化則是着眼於對當下乃至未來的方向做出設定或指引。這就要抓住學術和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進行貫通的思考,取資傳統,因應現實人情,順乎時代潮流,從而提出新問題、新思路和新追求。
二是,力争形成可以奠定新學科基石的典範之作。近代以來,中國引進西方學科體系,時至今日已經造成愈來愈森嚴的學科壁壘,不利於中國學術特别是人文學術的發展。“新子學”的提出,其中有部分原因即是爲應對這種狀況。但是,這種體系已經建立百餘年,其影響已經深入到學術研究的方方面面,可以説已是根深蒂固,再加上這種體系在某些方面也有其合理之處,所以現在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對其全盤否定。對我們來講,現在是對該體系進行糾偏的時候,即對確實不符合中國學術傳統的方面做出反思和調整。在這個問題上,具體成果的典範意義,要遠遠大於單純的理論探討。近年來,中國文學史和小説史的某些研究成果對我們應有所啓發。比如,王齊洲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簡明教程》(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一書,以文體史爲線索進行文學史寫作,就是對以往以朝代爲序來描述文學史狀況的糾偏,爲中國文學史的本土化寫作提供了一個樣板。他的《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一書,則運用發生學的方法,在中國文化和歷史語境下,探討中國文學觀念的發生、發展和演變,也是對遮蔽了中國傳統文學觀念特質的現有學科體系下文學史叙述的突破。其他,如陳平原先生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和學術體系建立的研究(11)陳平原先生著有《中國小説叙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可參考。,吴承學先生關於中國文體學的研究(12)可參見吴承學先生《中國古典文學風格學》(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中國古典文學風格學(修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譚帆和王齊洲兩先生對中國古代小説的研究(13)譚先生這方面成果主要見於專著《中國古代小説文體文法術語考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小説文體發展史》等。王先生這方面成果主要見於專著《稗官與才人: 中國古代小説考論》(嶽麓書社2010年版)及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二十五史〈藝文志〉著録小説資料集解》等。,對文學學科的最新建設和發展都極具示範意義。對“新子學”來講,在該理念的指導下,創作出一部甚至一批具有學科基石意義的成果,將更有力、直接地推動學科體系格局的調整和優化。
三是,以實際行動來改變當前的文風。當前的文風存在着實者過實、虚者過虚的問題,或者學術架子十足而同乎文字遊戲,或者長篇大論但言而無物,較少雅俗適中、親切平易、富於生氣的文字。這一方面是受學科體系和評價體系的不良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學風不够踏實、不接地氣所致。“新子學”在這方面,首先要做的就是追求學術研究中“人”的回歸。我們樂見研究者自身的個性、特質等投入到學術研究中,也樂於探求研究對象思想中所獨有的氣質特徵、精神風貌,這樣學術研究才能注入生氣,才具有生活氣息,而不只是乾巴巴的文字或知識。其次,學術研究要深入到研究對象的生活情景、知識背景、時代場景等進行細部觀照,這樣研究對象的面目才能越來越清晰,因而也越來越具有親切感。相反,若總是在現有的粗線條框架下觀照對象,就只能人云亦云,而永遠無法與對象進行親切的對話,無法發現他們新的樣貌和形態,也無法形成新的學術增長點。此外,在現有資源的基礎上,盡可能地聯合相關力量,争取把學術研究做得大氣、做得從容,不急於更不輕於發論著述,從而扭轉現有評價體系對文風的不良影響。
具體就教育方面來講,首先要明確教育的目標。“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棟樑之材並非一日所能生成。以培植參天大樹的耐心和功夫,培養真正具有氣魄和擔當的大才,這是目標之一。其二,探索一套新的教育模式,這種模式有利於培育思想領袖及綜合型研究人才。我國現有教育體制存在種種弊病,嚴重阻礙人才的培養和發展,國人對此有目共睹;然而,這種體制似乎又有存在下去的理由。所以,在體制外開拓出一條培養人才的模式或機制,就可以發揮其對現有體制的某些補充甚至替代功能。其三,争取能够承擔孕育新思潮的源地和輻射中心的角色定位和社會擔當。這既需要大志宏願,也需要包容的心態,以及長期的追尋、探討、碰撞和醖釀。現在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不管是從國内政治、經濟環境看,還是從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進程看,如果有這樣的宏願和時代擔當的話,應該説是恰逢其時。
其次,開展教育要面向廣闊的社會。這既是指教育面向對象廣泛,教育形式多樣,以不同層次的教育滿足廣大人民群衆的不同需求,又是指教育要以人爲中心,突出人的教育,强調人的參與,追求人的提升。隨着社會生活的發展,人民群衆對文化教育的需求越來越迫切,也越來越廣泛,國學熱、讀經熱等很可以反映國人對於文化的需求和期許。國學教育越來越熱,但是從事教育的機構品質參差不齊,産生不少弊端和消極影響;但在這個過程當中,也爲傳統文化教育、傳播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比如,據程度高低和需求不同分類進行教育;在教育過程中注意進行思想的現代轉化;讀書與養成教育相結合;探究性的學習和教育;以讀書會的形式開展教育,教學相長;承擔文化培訓功能;編寫系統的適用不同層次人群需求的教材;利用現代傳媒,製作有聲讀物和教育視頻;與文化企業相配合,形成教育、出版、傳播的配套模式,等等。這些經驗對我們都有借鑒意義。對“新子學”來説,一方面要編寫突出該理念的不同層次的文化讀本,製作各種類型的文化傳播載體;另一方面要拔選優秀人才,維持一定規模的高端教育班組。這項工作牽涉面很大,需要統合各方力量和各種資源,並進行統籌佈局,根據現有條件而各有側重,這樣才能全方位地推進開展。
最後,建立集研究和教育爲一體的平臺。這樣的平臺,既可包括活動基地等物理場所,又可包括刊物、出版發行單位、文化機構等推廣陣地,還應包括人員的組織形式。活動基地提供一個日常活動的場所,也是一個可以作爲教育示範的基地。刊物、出版發行單位、文化機構等,一方面是一個表達“新子學”理念及教育理念、教育心得的陣地,另一方面也是把“新子學”的新進展、新成果及時有效地進行推介的媒介。最重要的,是要把相關人員通過各種可能的形式組織起來,作爲一個社團、協會或者學會等,可以有統籌、有商量、有協作,就能群策群力,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這樣的話,不管是開展研究工作,還是開展教育活動,這種强大的合力就能産生巨大的效能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