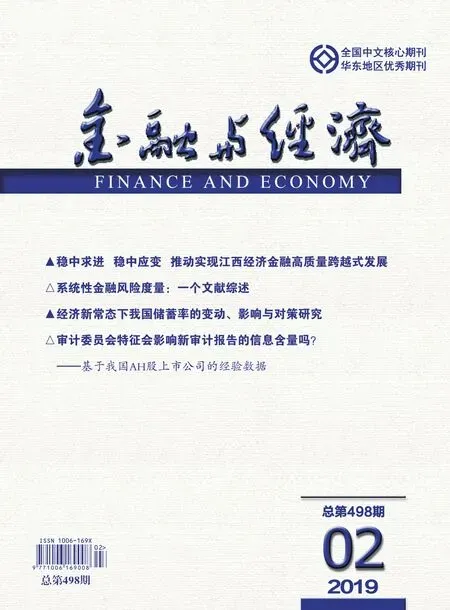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一个文献综述
■杜冠德,胡志浩
一、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金融体系造成了严重冲击和破坏,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众多经济体陷入衰退困境,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得到广泛实施,但多年来效果微弱,复苏乏力,金融危机已然使世界经济付出了巨大代价。
根据历史经验,金融危机所导致的通缩型大衰退一般程度较深,恢复时间较长。金融危机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直至爆发的结果,由于金融机构共同的风险敞口或存在业务关联,系统性风险会造成大范围的影响和扩散,威胁金融稳定。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事前,美联储对次级债务风险做出了严重误判,认为其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风险。但事实上,美国的主要金融机构都大量持有次级债务相关的MBS等有毒资产,金融体系为经济的虚假繁荣承担着巨大风险。
金融危机后,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受到了高度重视。有效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要求能够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准确的动态评估。IMF-FSB-BIS(2016)联合报告指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时间和横截面(结构性)两个维度。其中:时间维度是指金融体系风险随时间积累而产生的脆弱性,主要包括信贷总量和资产价格过度增长等宏观脆弱性、家庭和公司信贷增长等部门脆弱性以及金融部门期限和外币错配累积的脆弱性;横截面维度是指金融体系内部的相互关联性及相关的风险分布所产生的脆弱性,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包括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间的关联性风险以及某一机构倒闭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
近年来,学者们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度量方法进行了大量探索,国内也相继涌现出一系列的综述文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对现存的各种度量方法进行分类和介绍。
系统性风险度量的目的是能够及时发现风险,从而采取宏观审慎政策处置风险,进而防范危机。而现有文献中尚缺乏从这一根本目标出发,对系统性风险测度进行较为深入的解读和准确的概括。也正是基于这一角度,我们才能对现存测度方法的不足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明确未来研究的着力点。因此,本文根据学术文献对系统性风险界定的不同,将测度方法主要分为三类,即测度(单个)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所承担的整体风险,测度经济部门的债务风险和部门间的风险传导以及测度银行间同业拆借关联所导致的银行体系脆弱性。
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所承担的整体风险
次贷危机爆发后,作为全球最大保险公司的美国国际集团(AIG,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因持有大量与次级债务相关的衍生品而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为避免AIG破产对金融体系造成大范围的冲击,美联储对其实施了紧急救助,减少了危机的扩散。其后,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因未能获得救助而破产,由此引发了持有其大量票据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MFs)面临危机,并迅速蔓延至整个MMFs部门(Allen et al.,2009)。这些经验和教训表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对于维护金融稳定举足轻重。目前的主要测度方法正是基于这一角度,对单个金融机构所承担的系统性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四类方法:
(一)CoVaR与Co-Risk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Adrian&Brunnermeier(2016)提出的△CoVaR是最具代表性的系统性风险测度。该测度基于风险管理中最为常用的VaR,将其推广到单个金融机构处于某一状态时整个金融体系的条件在险价值(CoVaR),并以该金融机构处于危机或正常状态下的CoVaR之差作为其所承担的系统性风险度量(相对于个体风险承担)。
除了上述对横截面维度的风险度量,Adrian&Brunnermeier(2016)还基于CoVaR对时间维度即顺周期性进行了讨论。他们将公司特性和宏观指标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建立了CoVaR的预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前瞻性的系统性风险测度Forward-△CoVaR(即未来△CoVaR的预测值)和当前的△CoVaR具有很强的负相关性,从而揭示了系统性风险的顺周期性。然而,CoVaR还只是度量尾部依赖性的一种统计方法,并不能刻画因果关系,也不能揭示金融机构所承担的系统性风险的具体机制,因而对于宏观审慎管理的作用存在局限性。
Chan-Lau et al.(2009)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条件(分布)度量方法,称为Co-Risk模型。他们基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CDS日度价差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研究一个机构的信用风险状况对另一个机构信用风险的影响。该模型建立了“条件Co-Risk测度”:首先计算一个金融机构的条件CDS价差(即在另一个金融机构CDS价差处于95%分位数的条件下),然后计算条件CDS价差相对该机构非条件下的95%分位数价差的变化,并将其作为机构间信用风险关联性的度量指标。
(二)SES与SRISK
Acharya et al.(2017)提 出 的 SES(Systemic Expected Shortfall)测度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将整个金融系统资本不足时(将总资本充足率低于某一比例定义为系统性危机)某一单个银行的预期资本短缺定义为该银行的SES,并将其作为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同时,将金融体系的权益资本视为单个机构资本的组合,用MES(Marginal Expected Shortfall)表示某一单个银行对金融系统ES(Expected Shortfall)的边际贡献。他们的理论模型表明,单个金融机构的SES与该机构的杠杆率和MES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故而可用后者对该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贡献(SES)进行分析和预测。在文中,他们选取的SES代理变量有三种:危机期间压力测试所评估的资本短缺、危机期间的股票收益率和CDS价差。而且,在一年中市场收益率最低的5%天数内,将银行股票的平均收益率作为其MES。实证结果表明,根据次贷危机前1年的数据估计的银行杠杆率和MES,能够预测该银行在危机期间的SES实现值。
这为度量和预测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提供了一种新方法,但该方法在理论上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SES的定义是金融危机中单个金融机构的资本短缺,其数值大小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其对金融体系稳定可能带来的影响,但该机构的资本损失也有可能是其他机构风险溢出的结果,即仍然是微观意义上的风险。因此,SES测度不能揭示风险的来源及风险发生的先后顺序等系统性风险机制。其次,理论模型对SES与杠杆率、MES存在密切关系的论证是基于SES的上述定义,文中采用的后两种代理变量(股票收益率、CDS价差)有些缺乏理论基础。第三,SES是一种事后测度,对于未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该方法的使用将受到制约。
“A到VP”格式中的“到”不是可有可无的。关于“到”的意义和作用,前文已做了专门讨论。它在“A到VP”格式的意义和结构上都承载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单独看A和VP都不能理解它们的整体含义,不能根据表面意义得出整个格式的意义,“A到VP”是“A”“到”“VP”意义的整合与融合,它已经成为语言表达的固定格式。没有“到”的连接,整个结构就不完整、不自足,表义也不连贯或有偏差,谓词性VP对A的描述和补足就不能产生作用。例如:
Brownless&Engle(2017)对MES和SES做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了SRISK(Systemic Risk Indices)测度①“Volatility,Correlation and Tails for Systemic Risk Measurement”为其工作论文版本。:将市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收益率低于-10%的情况下,某一金融机构的预期资本短缺定义为该机构在当前时刻的SRISK,并将其作为测度单个机构对系统性风险贡献的一种动态指标(有别于SES静态测度)。同时,将某一金融机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股权预期收益率(在市场收益率低于-10%的条件下)定义为该机构当前的LRMES(Long-Run MES)。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容易得到SRISK是公司规模、杠杆率和LRMES的函数。这一测度方法克服了SES事后观测的不足,并且能够动态评估。但根据定义,SRISK度量的是整个金融体系发生危机时(风险已全面扩散的情况下)某一机构的损失,而不是单个机构对整个系统造成的风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在整个市场中举足轻重,市场收益率的崩溃实际上表示SIFIs处于危机状态,故而SRISK测度反映的其实是公司规模的大小,而不能揭示金融风险机制。关于SRISK测度的探讨也可参见Acharya et al.,(2012)。
(三)DIP
另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系统性风险测度是Huang et al.(2009)提出的 DIP(Distress Insurance Premium)。他们将银行系统大规模信用违约视为系统性风险(文中设定的阈值为银行部门债务组合的违约损失达到其总债务规模的15%及以上),计算系统性风险爆发时银行部门所造成的预期损失的当前价值,即DIP②文中选取了十几家重要的银行作为研究样本。。
具体来说,他们首先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利用CDS价差计算单个银行的风险中性违约概率③因为要计算现值即无套利价格,故而要计算以无风险利率折现后的风险中性期望。,然后基于股票价格预测银行资产未来收益的相关性,并将其作为对银行违约相关性的估计。基于这两个要素所计算的DIP是一种前瞻性的动态测度。Huang et al.,(2012)对DIP做了进一步发展,将单个银行对DIP的边际贡献作为该银行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并且能够在时间和横截面两个维度进行度量。
(四)Shapley Value
Tarashev et al.(2009)将 合 作 博 弈 论 中 的Shapley值④Shapley(1953)提出了一种度量每位参与者对团队贡献的方法:计算每位参与者对所有可能的子团队边际贡献的平均值,即Shapley Value。概念应用于系统性风险分析,度量单个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即度量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Shapley值是一种一般性的分配原理,基于这一原理对系统性风险分配依赖于具体的风险测度。他们选择ES(Expected Shortfall,预期损失)作为系统性风险测度,对选定的20家大型跨国金融机构,运用Shapley值方法分析违约概率、规模和对共同风险的敞口等因素对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的影响。
Tarashev et al.,(2016)对度量金融机构(银行)系统重要性的Shapley值方法做了进一步研究,建立了严格的理论基础,并对相关实证结果给出了理论证明。
以上四大类方法主要是基于SIFIs的股票收益率进行风险度量。此外,也有学者尝试运用股票期权数据进行分析,例如Malz(2013)使用的方法包括以下两个步骤:
1.基于期权数据估计金融部门股票组合收益率的概率分布。首先,基于G-SIBs(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的股票期权价格等数据,估计股票未来收益率的概率分布。然后,用单个股票和股票指数的隐含波动率,估计股票收益率的相关系数。最后,基于股票收益率分布和相关系数,运用正态Copula模型估计股票收益率的联合分布,进而得到金融部门股票组合的概率分布。
2.基于金融部门股票组合的收益率分布计算系统性风险指标。首先,计算金融部门股票组合在未来3个月内遭受大幅损失(例如25%的市值损失)的概率。其次,计算金融部门股票组合收益率尾部分布(后5%)的平均损失。最后,在某一金融机构遭受损失的条件下计算前两种测度,即“条件系统性风险指标”。
三、经济部门的债务风险及部门间风险传导
与聚焦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测度方法不同的是,CCA(Contingent Claims Analysis)模型是基于经济部门的结构模型,通过计算部门的风险债务暴露、违约概率、危机距离等风险指标,分析各部门的信用风险以及部门间基于资产负债表关联的风险传导,并将其作为对系统性风险的度量。
CCA是Merton(1973)所提出的分析方法,即假设总资产的市场价值服从Itô随机过程,则可以运用期权定价的方法对公司的权益、债务的市场价值进行计算和分析。其中,权益资本可以视为以总资产为标的、债务额为敲定价格的看涨期权。类似地,公司未来的资本短缺,即总资产相对于总债务的差额可以视为总资产的看跌期权。
后来的学者们对CCA方法进行了拓展,将其应用于系统性风险分析和度量。例如,Lehar(2005)基于CCA方法,研究了银行系统的风险度量。他将银行体系的风险定义为银行监管者投资组合的风险,利用看跌期权定价原理计算单个银行预期资本短缺的现值,并利用股票市场信息估计银行资产之间的动态关联,从而对银行体系的风险进行评估。Gray et al.(2007)将CCA模型框架进行了拓展,使其能够适用于主权资产负债表,从而能够对主权信用风险和相关政策进行量化分析。Gray et al.(2007)基于CCA方法,提出了一个度量系统性风险的新框架:将一个经济体的各个部门视为相互关联的由资产、负债和担保所构成的投资组合,运用风险调整的资产负债表进行风险分析。这一方法比传统方法能够更好地刻画风险逐渐积累后突然爆发的非线性特征,以及对资产负债错配的影响进行量化,并且更加便于通过数值模拟和压力测试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效应进行评估。Gray et al.(2008)对基于CCA的主权信用风险模型做了进一步发展,建立了一个分析公共部门债务可持续性的新框架。这一方法克服了传统方法在度量风险暴露、违约概率和信用利差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能够进行相关政策分析。Gray&Jobst(2010)建立了“系统性 CCA”(Systemic CCA)的新框架,基于市场信息计算预期损失,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度量,并将该方法应用于政府隐性债务分析。Jobst&Gray(2013)基于“系统性CCA”框架,通过估计金融机构的联合预期损失,对系统性的偿付能力风险进行度量和分析。Gray et al.(2013)将 CCA 和 GVAR(Global Vector Autoregression)方法相结合,分析银行、政府、公司等部门间的风险传导。通过对校准后的模型进行银行风险和主权风险的冲击模拟,分析风险溢出效应,并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进行评估。Gray(2014)基于CCA分析了房地产价格和住房抵押贷款风险向银行部门的传导,以及银行部门的风险向政府部门及实体经济的传导,并将这一分析框架应用于爱尔兰。
CCA模型的主要不足在于,其依赖于总资产服从几何布朗运动的基本假设①即Black-Scholes模型中对标的股票价格过程的假设,漂移和波动率均为常数。,并继而得到部门的权益和债务,故而与事实存在较大的偏离。
四、银行间同业拆借关联所导致的银行体系脆弱性
大量文献基于网络模型研究银行间同业拆借关联所导致的银行体系脆弱性。Allen&Gale(2000)是金融网络模型的奠基性文献。他们对银行间信用关联和风险传染建模,论证了银行系统信用关联的完全结构(Complete Interconnection)比非完全结构在面临外部流动性冲击时更加稳定。Eisenberg&Noe(2001)在一定条件下证明了银行间信用关联网络存在唯一的“清算支付向量”,并建立了一个基本算法(“Fictitious Sequential Default”Algorithm),分析银行违约风险的传染过程。Cifuentes et al.(2005)主要分析了资产抛售与资产减值相互作用所导致的银行系统风险传染。Degryse&Nguyen(2007)发现完全结构的银行间网络比“多货币中心”(Multiple-Money-Center)网络结构更加稳健。Gai et al.(2011)的研究表明,银行间网络结构的复杂性和集中度增加会放大银行系统的脆弱性。Cont et al.(2013)运用“传染指数”(Contagion Index)度量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并对银行网络中的传染风险进行分析。Glasserman&Young(2015)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金融网络模型分析的新思路,即建立单个金融机构特性(资产规模、杠杆率和关联性)与网络中传染放大效应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并不依赖于网络拓扑结构。
五、其他测度方法
(一)宏观指标与宏观指数
用一组宏观指标或其合成的宏观指数来度量金融体系的总体风险状况,这类方法可以统称为“金融状况指数”(Financial Conditions Indexes)。
例如:Frankel&Rose(1996)、Sachs et al.(1996)对发生货币危机的主要经济基本面因素进行了研究;Kaminsky et al.(1998)建立了货币危机预警系统;Illing&Liu(2006)、Morales&Estrada(2010)、Cardarelli et al.(2011)、Brave&Butters(2012)、Carlson et al.(2014)建 立 了“ 金 融 压 力 指 数 ”(Financial Stress Indexes)。此外,Brunnermeier et al.(2014)建立了“流动性错配指数”(Liquidity Mismatch Index)。
(二)主成分分析与格兰杰因果网络
Billio et al.(2012)基于主成分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建立了两类度量金融机构关联性和系统性风险的指标。他们在美国的银行、证券交易商、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四类金融机构中分别选取最大的25家,并基于其股票月度收益率(或对冲基金的月度收益率)进行统计分析。
首先,将样本机构股票收益率的“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正交分解,从而可以将收益率表示为主成分的线性组合。将金融系统的总风险定义为主成分方差之和。选定前几个解释力最强的主成分,将它们的方差之和与总风险的比值作为金融系统关联性的(动态)指标。这是因为当金融系统关联性增强时,选定的前几个主成分对总波动的解释比例增加。同时,金融系统关联性增强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系统性风险水平上升。另外,也可以计算单个机构对总风险的贡献。
接下来,他们对机构的股票收益率序列互相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从而建立“格兰杰因果网络”,并基于该网络提出了度量关联性的5个指标:格兰杰因果度(Degree of Granger Causality)、关联数目(Number of Connections)、部门条件关联(Sectorconditional Connections)、紧密度(Closeness)、特征向量中心性(Eigenvector Centrality)。
六、主要结论
本文对主要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方法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回顾。测度(单个)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所承担的系统性风险仍是目前的主流方法,但这类方法度量的是危机爆发后扩散阶段的风险,并不能揭示系统性风险在机制上的来源,故而对于采取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的作用有限。
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雷曼兄弟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对其金融体系稳定性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危机爆发前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看似都保持着稳健运行,并无危机征兆,但事实上它们乃至美国金融体系已经积累了巨大风险。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这些大型金融机构所暴露出来的巨大流动性缺口,会迅速表现为整个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崩溃。从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先后顺序看,比大型机构破产所引发的连锁效应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实力强大、举足轻重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为什么会集体同时遭受规模如此庞大的损失以致破产?这一风险从何积累而来?事实上,这就是系统性风险,即相当数量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因大规模卷入资产价格泡沫而面临危机,从而危及金融体系稳定。
总之,系统性风险是金融体系或多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所面临的共同风险因素,这些风险因素及其潜在影响是系统性风险分析和度量的核心。在当前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时期,对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影子银行体系等主要的系统性风险因素及其潜在影响进行准确的动态评估,是系统性风险度量对于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意义所在,其目标在于能够及时采取宏观审慎政策,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从经济部门看,房地产价格和住房抵押贷款风险向银行体系传导,继而由银行体系向实体经济和政府部门传导,是危机的重要传导路径。因此,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和银行体系的稳健,是宏观稳定的重要前提。此外,几年前的“钱荒”事件充分暴露了银行间同业拆借的复杂关联可能导致的流动性危机,故而对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流动性风险监测也是维护金融稳定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