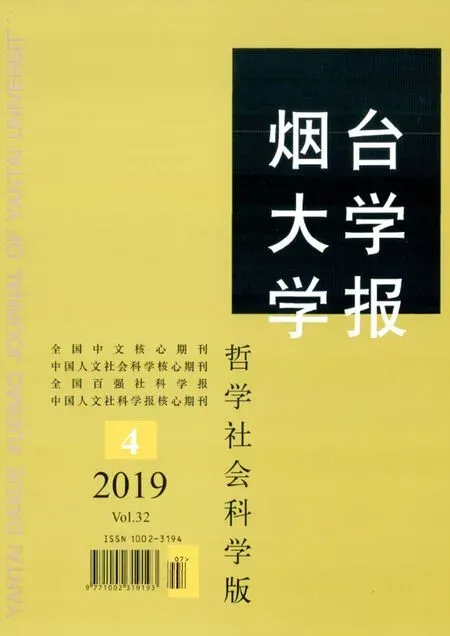构建汉语语篇学的基础和原则
丁金国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一、关于“语篇”
“语篇”作为语言学的一个特定概念,中国原来没有,是从英语“discourse”(话语)和“text”(篇章)转译而来。在英语中,通常认为“discourse”为口头讲的话语,而“text”则被释为“书面语”。英美习惯用discourse来概括二者;欧陆则更多用Text(德)、тeкcтa(俄)、texte(法)。国人最早介绍语篇理论的是王福祥(1981)、廖秋忠(1981)、黄宏煦(1982)。1988年黄国文正式以“语篇”(test)命名,出版了《语篇分析概要》(EssentialsofTextAnalysis)专著。此后,陆续有任绍曾(1991)、胡壮麟(1994)、彭宣维(2000)、朱永生(2001)、张德禄(2003)、徐琚(2007)等具有功能语言学背景的学者,均用“语篇”对译discourse 或text。在“语篇”一语开始流行之时,“话语”与“篇章”仍在使用。与语篇并存的,除话语和篇章外,还有会话、文本、本文、辞章、文章、文辞、言语、表述等。如此众多似是而非的概念,用哪个好?自然需要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我们认为从西文“化”出来的“语篇”,来概括篇章和话语现象较为合适。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从西文化来,但不一定能化回去。近日笔者就遇到了化回的尴尬,是用discourse还是用text犯了踌躇。汉语用“语篇”来囊括“篇章”和“话语”,而英语却没有一个可将discourse与text二者兼而容之的词。在英语里,除了discourse和text外,近似概念还有utterance、dialogue、monologue、conversation、writing、essay、article等,但这些因其原有使用域已约定俗成,难以接受新的语义挂靠,只能依习惯在discourse、text中择一。
语篇是以特定母语为根基,以特定文化为沃壤萌生、成长、发展而来,由此也就决定了任何语篇从其发生始就带着特定母语文化的基因而存在。所以,语篇研究的伊始,就面临着语言观的选择。固然各语言间,在本质特征、构成要素、系统结构及语用功能有相似性的一面,然由于各语言间生存环境、文化母体的差异,从而决定了各自异质性的一面。异质性的差异对于语篇研究是本质性的,对于语言运用和语文实践来讲,研究语篇的异质性尤为重要。中国外语学界于上世纪70年代末,将西方刚出现的“语篇、话语”研究,以“新兴学科”引入,经几十年的转译、仿拟与消化,“语篇”与“话语”这两个概念,高频出现在语言类刊物上。由1981年“1”的篇量,逐年增加,进入新世纪后每年则以三位数的速度激增。仅2000-2017十七年间,以语篇、话语为题的著述,竟达四万余篇、部,远高于当年生成语法进入国门时的热度。值得深思的是:学界的热情与社会语文实践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什么会出现此种局面?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语言观问题没解决。引入者自觉不自觉地将印欧语的语篇理论作为范式来观察汉语的语篇事实,从而造成“两张皮”的深层隔膜。
我们认为,所谓语篇,就是人们使用言语进行交际的过程和结果。这个界定有两个注视点:一是“构组言语”。言语潜隐的是个动态的过程,是具有历时性、个体性特征的连续话语;一是“过程和结果”。过程和结果所提示的是:一切语篇的生成都是从动态到静态衍化而成。动、静的显性标记是开头、结尾。语篇可以是长篇巨制,也可以是一个句子,甚至是一个字。如“冲!”只此简单的一个词,由于有“!”的伴随(实际上提示的语境),立即显示出其“针对性”“言有所为”的话语作用。而语言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词、一个句子,则无此功能。因为任何词、句子都无现实语境作为其存在的根据,其语义解释的不确定性,也就无所谓头、尾边界。语篇的外显形态,有口头、书面及网络形式,上述学界所称的“话语”、“篇章”、“文本”、“辞章”、“文章”、“文辞”、“言语”等一切言语形式均可收纳进来。可见,语篇不是语言单位,实际上是个交际单位。
现引入的语篇理论,是在印欧语的母胎中孕育、在印欧语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对其理论范畴、内在结构、语言事实的阐释,莫不以西语为宗。哲人洪堡特、萨丕尔等的语言哲学已提示我们:观察一种语言应站在该语言赖以生长的文化基点上进行考察。洪、萨二氏的论述,对我们的启示是: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言观,每个言语社群认识世界的差异是由语言的不同所使然。印欧语的语篇研究是建立在有丰富形态变化(尤其是拉丁系和斯拉夫系诸语言)的屈折语基础之上。单向、单维、定向线性的屈折意识,天然地控制着人们在言语表达时追求与语句变化统一性的努力,推进其言语表述上的逻辑顺序:内在抽象语义与外在形式结构,关联并置,从而造成逻辑严谨,确认性强等特点;而汉语则以形音义为一体的立体多维结构,从而形成汉语社群的人们在言语表达时注重整体和谐,语篇的题旨情趣与客观规律要一致,而外在的言语表达,则应与题旨情境相协调,即刘勰所言“心与理合”“辞共心密”,从而达到“外文绮交,内义脉注”。国人的这种空间思维逻辑,具有多维、多向、形象与抽象相结合的思维特征,诱导出以“心”为轴的聚敛表征,完全异于西语的那种必须凭借外在形式来完成内在语义连贯,一切都围绕题旨转。本文立足于异质语言观来展开我们的论题,考察汉语语篇现象的种种表现,摸索构建汉语语篇语言学的途径。
二、国人的语篇研究
对语篇现象的思考与探索,应该说是中国的强项,从汉一直到当代,从未间断过对语篇的研究。早在王充(公元27-约97)的《论衡》里,就有“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有章句也,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注]转引自郑奠、谭全基编:《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4-45页。。王充对语篇的论析是从大到小,逐次切分,然后再由小到大,递次组合。“经”指上古的一种语类,是由具体“篇”所组成。“篇”由章、句构成,章、句由文字构成。文字是个意义单位,因有“意”,方可用来组成句子。数个句子联结而成章,“数”者,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数句成章,另一个意思是“规则”。既然每个句子都有意义,各句的联结是要按照组合规则联结而成章。章成篇的条件是,必须接受“体”的调控或约束,方有资格成为篇。王充的寥寥数语就将语篇的内在结构勾勒清楚,其科学性已为两千年后今天的研究所证实。尤其是对“章有体以成篇”的强调,将“体”提到语篇构成决定性的地位,是“语体为先”学说的权舆。王充的语篇论,在中国语篇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逮及六朝,经曹丕、陆机的阐发,汉语语篇论的轮廓初露端倪;尾随的挚虞则提精取粹,梳理出我国古代第一部语篇文章学专著《文章流别志论》。《志论》以体为纲,论述了各体文章的特征、性质、源流和发展变化,与之配套的还有四十一卷的《文章流别集》,以佐理论参证。[注]所憾这两部书均已亡佚,我们只能从相关著作的引录中看到部分佚文的片断。到齐梁,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刘氏系统地总结了此前的语篇研究的理论精粹,将散玉碎珠串联起来,提出了系统的本体论、写作论和阅读论。自此以降,历朝均有语篇论经典问世。唐有刘知几《史通》,宋有陈骙《文则》、谢昉得《文章轨范》、李涂《文章精义》、吕祖谦《古文关键》,元有倪士毅《作文要诀》、王构《修辞鉴衡》,洎明清有方以智《文章薪火》、唐彪《读书作文谱》、刘大櫆《读书偶记》、章炳麟《国故论衡》、刘师培《文说》和《论谋篇之术》、刘熙载《艺概》等,都是极重要的语篇典籍。历经两千多年磨砺,汉语的语篇研究始终沿着汉魏诸贤所奠定的理论轨辙行进下来,在培养一代代文笔大家的同时,传递着中华语篇文典精髓。
由魏晋迄当代,一千八百多年的语篇研究,可概括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是魏晋至清末,其语篇形态表现是:一是以语类为准绳的文选编撰,萧统的《昭明文选》首开端。《文选》以典雅、厚重为准则,以诗文为重点,将周至梁七百年间诗文精粹收进文集,开创了文选编撰的先河。为补《昭明文选》之不足,清代曾国藩在对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增补基础上,编纂了《经史百家杂钞》,连同此前的《古文观止》(吴楚材、吴调侯)等遂成为后世学子的古文津逮。二是以诗文点评批注为形式,承载着著述者对有关语篇的理论阐述。发端于《诗品》(钟嵘),昌盛于宋元明清各类“话”及语类、书简,散布着汉语语篇的吉光片羽。三是与语篇相关的专论,遗响后世者六朝有曹丕、陆机、刘勰、钟嵘辈,唐宋有皎然、司空图、朱熹、陈骙、严羽等,元明清还有王若虚、吴讷、徐师曾、王世贞、袁枚、姚鼐、刘熙载、王国维诸贤。
第二时段是民初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其形态表现是:随着泰西语篇思想理路的输入、文言与白话地位的置换、社会语用方式的嬗变,语篇研究的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除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和《修辞学发凡》为代表的系统理论外,还出现了以表达方式为轴心的各级语文课本的编撰。民国时期的国学翘楚,几乎都有与语篇学相关的著述,先后有来裕恂(1906)、刘师培(1907)、蔡元培(1916)、梁启超(1913)、陈望道(1922)、叶圣陶(1924)、龚自知(1925)、胡怀琛(1925)、夏丏尊(1926)、刘咸炘(1929)、傅东华(1934)、蒋伯潜、蒋祖怡(1942)、吕叔湘(1944)、郭绍虞(1946)等。他们著述的共同点是:立足于汉语特质,从语文教育的实际出发,系统地讲述和阐释汉语语篇的阅读、写作和欣赏机理,其理论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语文教育服务。上述语文大家不仅有著述于茅庐,执教于讲堂,还编撰了贴近汉语实际的各级语文教材,有的甚至至今仍是语文课堂上的范本。语文课本的共同特点是:以文体为纲,统摄讲述和例文;以表达方式为骨架,串联各级语脉逐次递升;以典范的古今华章为范本,浸染学子心智为目的。
第三个时段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降。如果说“文革”前还有些语篇研究,“文革”中停滞十年,研究无从谈起,然国民的言语运用却从未停止,只不过是在毫无约束的情境下行进。就社会整体语文形态而言,有人喊“语文危机”,有人批“中文退化”。面对“英语围剿”“网络施虐”语文品位的下降,国民语言素养整体水平呈下降征兆。最早觉察到汉语颓势的是终生致力于语文研究和语文教育的张志公。志公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就积极倡导篇章教学,和者有张寿康等先贤。他们着力倡导继承传统,呼喊建立“汉语篇章学”。然刚刚起步,就受到“惟洋是从”大潮冲击,涓涓细流终于敌不过“国际接轨”的巨浪而败下阵来。一时间“主位与述位”、“指称与回指”、“语篇的衔接与连贯”等话题成为硕博论文的首选,占据了理论语场的主阵地。“语篇”新学经几十年的转译、仿拟与消化,引进时期有《语篇分析概要》(黄国文,1988)、《语篇的衔接与连贯》(胡壮麟,1994)等,新世纪出现了“国产”的语篇学著作,有:《汉语篇章语言学》(郑贵友,2002)、《现代汉语语篇研究》(聂仁发,2009)、《现代汉语篇章语言学》(徐赳赳,2010)等,三部著作都冠以“汉语”或“现代汉语”。经披览发现,所有这些汉文著述,虽标冠“汉语”,然最缺略的恰恰是汉语篇的灵魂,与国人几千年来执术驭篇的传统与语用现实相悖。其共同特点是:既缺题旨立意论证,也无语类、表达论说,更少韵律情境撰述,受到汉语文社会冷淡,实属情理之中。为什么会出现此种尴尬局面?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语言观问题没解决,引入者并未接受西语语法进入中国百年遭遇的教训,仍以印欧语的语篇理论作为范式,妄图匡正汉语的语篇事实。值得欣慰的是,最近在检索高校基础写作教学大纲时,发现几乎所有的大纲,都将五种表达方式和常用语类置放在中心位置。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回归,值得翘首以盼。
三、《文心雕龙》的奠基作用
从上述对汉语语篇研究“史”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几千年来的汉语语篇研究,从未间断过;然具有体系性、理论性、且集前贤研究之精华,具跨时空特征的著作,还没有一部超过《文心雕龙》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心雕龙》为汉语语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之所以能成为开山奠基作,就在于它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且这个体系既符合彼时的语文事实,又可跨越时空,为华夏一千多年来的语文实践活动服务。
《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梁间,在唐宋前学界并未投以青眼,既无评注,也无刊本梓行。窃以为这可能与刘勰以骈体行文有关,因为彼时,正是唐宋古文大家独占鳌头的年代,骈文再优秀,也无地盘可容纳。历元迄明清,由于学术环境的变化,随着《文心雕龙》的各种刊本梓行,校勘、注释、点评等研究相继出现。到了二十世纪,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西方文艺思想的输入,尤其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学界从美学、文学理论等角度开始对其作深度研究;下半叶虽偶有从文章学、修辞学等文化视点观察《文心雕龙》,但重彩浓墨依然在美学、文艺学。至于所谓文章学研究,只在部分著述的字里行间提到,就语篇学意义上来看《文心雕龙》,五十篇中,除《序志》作为全书例序,《时序》作为汉语语篇发生、演变、发展史外,其余四十八篇可分两类,一是语篇类型论,共有二十篇,从《明诗》到《书记》(严格讲《辨骚》和《正纬》亦应属于语类论);这样余下的二十有八,均属于语篇从生成到接受理解的全过程。
语类论各章的行文顺序大致是:概念诠释、特征、基本功能、运行语境、产生渊源流变、代表著作及作者、风格特征、写作要领等。从语篇学角度看,《原道》、《征圣》和《宗经》三篇,是专讲立意,即“题旨”,从《神思》到《才略》是从表达者的角度来揭示语篇的生成过程及其要求,《知音》是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在接受过程中的认知结构。《程器》是讲语篇生成者和解读者的人格修养问题。《体性》、《风骨》、《定势》是专门研究语体风格。
从今天的视角来检视《文心雕龙》到底是部什么性质的书?笔者认为它并非是纯然的一部文学批评或美学的书。理由是:文体论二十篇再加上《辨骚》,共二十有一,是语篇类型研究,纯粹“文学”的只有辨骚、明诗、乐府、诠赋四篇,其余“诸子”、“史传”、“论说”非文学性自不待言。其他像有韵文《赞颂》、《祝盟》和无韵文《诏策》、《檄移》等,均属应用文。现代语篇学所要描写的内容,它不仅融涵其中,而且比当代中外语篇研究更丰富、全面。综观整体,应该说《文心雕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语篇学的著作绝非夸张。这里将《文心雕龙》所论具有普遍性的逻辑意义,归纳为八个范畴:题旨、语类、情境、语脉、声律、修辞、接受、风格。
(1)题旨 即语篇的主旨、主题、旨意、旨趣、趣旨、目的、动因、内容等。“题旨”最早见于冯梦龙《警世通言》,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正式列为语篇的构成范畴。《文心雕龙》开篇就亮出“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的题旨。题旨在《文心雕龙》中,多以“情”“思”“志”“意”“道”的形式出现。
(2)语类 语类论是《文心雕龙》的核心,是枢纽,五十篇中,二十一篇是分门别类谈论各体语类。他在《熔裁》篇里,特别提出制篇三准则:“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位体”即为题旨置厝于一个合适的位置,与特定语类相适应。“体”即现代的语体、体裁、文类、体式、文体或体制。全书从语类角度说“体”,初略计之有一百四十七处。
(3)情境 刘勰未提及,然这并非意味着刘氏昧于对情境的认识。他在《神思》篇中强调“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物者”,外界客观存在的物质、人文环境。“神与物游”即语篇的题旨情趣与外在客观情境相适应。《文心雕龙》中,“物”共出现48次。
(4)语脉 即语篇结构,集中论述有《章句》、《熔裁》和《附会》诸篇。《章句》是从微观入手,依据情理、韵律,逐次铺开,“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以达:“外文绮交,内义脉注”。《熔裁》阐述的是语篇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认为“首尾圆合,条贯统序”。《附会》着重讲统摄语篇整体的是义脉,“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
(5)声律 即韵律,《文心雕龙》设有《声律》专篇,揭示语篇声律的内涵和渊源,认为“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精神)枢机,吐纳律吕(韵律),唇吻而已。”
(6)修辞 《文心雕龙》既是汉语语篇学开山,也是修辞学的鼻祖。如《夸饰》《丽辞》《事类》《比兴》《隐秀》等篇,就是专讲夸张、对偶、引用、比喻和委婉等辞格。各种组句成篇、润饰辞采、抒情达意的方法与原则,在各篇之中都不同程度地显现。
(7)接受 刘勰首倡,先于德国姚斯(H. R. Jauss,1967)的接受论[注]理论界誉为“前沿”的接受理论,公认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德国姚斯(H. R. Jauss)所提出。其要点是:作品的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要在读者阅读中实现,而实现过程即是作品获得生命力和最后完成的过程。读者在此过程中是主动的,是推动文学创作的动力;文学的接受活动,不仅受作品的性质制约,也受读者制约。姚斯的接受论发表一年后,1968年法国学者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问世,认为文本产生之时就是作者消亡之刻。接受理论被巴特推到极致。一千四百余年。刘氏在《知音》篇中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身。”并指出:妨碍“知音”的障碍:一是世俗陋习“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二是“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建言接受者应“务先博观”“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接受者应“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刘勰所论切中“接受论”的要害,今天依然放射着理论的光芒。
(8)风格 刘勰是汉语风格论的奠基人,《体性》《风骨》《定势》三篇是语体风格论的轴心。《体性》集中论述风格的发生,以及语篇主体个性要素对风格发生的能动作用。《定势》所定就是循体成势,重在对风格形成的客观要素的剖析。《风骨》意在强调“辞意”的作用。风格之所以得以形成,全在语篇的语义结构的主导作用。风骨是一切风格所具有的一种“含量”。刘勰加意赞誉的阳刚类,诸如雄健、旷达、典雅、遒劲、壮丽、挺拔等气清骨峻的风格,其风骨含量就高;相对繁缛、新奇、轻靡、显附、远奥等,其风骨含量自然就低。
这八个范畴之所以称其为开山奠基,就在于它植根于母语,所总结的理论是前贤经验的提纯;对历代语文生活都具有建言树德、扶雅立正的功能。需要说明的是,刘勰没抽绎出“表达”系统,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意识到表达手段的存在,如其对语篇类型的划分,其中就蕴含着表达方式的标准。如《论说》、《谐隐》等篇章的区分。
四、西人的语篇研究
语篇这一概念孕育于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和演讲术,历经中世纪语法、修辞、逻辑的哺育和文艺复兴的洗礼,到二十世纪,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斯(Harris,1952)的《话语分析》,始将语言研究从微观单位语素延伸到宏观单位语篇,从语法分析中离析出话语分析。发育成长于印欧语文化语境中的语篇理论,其理论范畴、内在结构、语言事实的阐释,莫不以西语为宗。印欧语的语篇研究是建立在有丰富形态变化(尤其是拉丁系和斯拉夫系诸语言)的屈折语基础之上的,单向、单维、定向线性的屈折意识,天然地控制着人们在言语表达时追求与语句变化统一性的努力,推进其言语表述上的逻辑顺序:内在抽象语义与外在形式结构关联并置,从而造成逻辑严谨、确认性强等特点。故而西人在研究语篇时,以语法结构为主轴,再自然不过。然跳出语法窠臼,我们从语言哲学角度来透视语篇,则是另一番情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L.Austin)195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以“论言有所为”为题作了系列讲座(共十二讲),系统地阐述了其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言之发”,需完成三件事:言有所述,言有所为,言有所果。据此可推导出:语篇即在特定交际语境下发生“言有所述,言有所为”追求“言有所果”的言语事件。从言语行为出发来定义语篇,不仅有语境伴随,还伴有言语过程中言者和受者互动环节,这较之仅笼统地表述是“语义问题”更深刻得多。它将韩礼德的“语场”、“语旨”和“语式”的内涵尽收囊中。
海姆斯(D.Hymes)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对言语事件的构成要素作了提炼。于1962年的《言语行为的文化学阐释》(TheEthnographyofSpeaking)中,在论及言语行为单位时,海姆斯认为任何一个言语事件,至少由16个要素构成,他将这16个要素归并为八类:背景(situation)、参与者(participants)、目的(ends)、行为顺序(act of sequence)、格调(key)、语式(instrumentality)、准则(norms)、体裁(genre)。为便于记忆,从各个英语词开头字母缩略为英语词——SPEAKING。海姆斯论证的特点是按照言语事件发生的顺序逐次推进。始于背景(情境),终于体裁(语类)。其中“目的”即题旨,“行文顺序”和“准则”可视为对语脉的述说,格调对应风格,语式指述说过程的媒介,参与者与情境有相关性,与系统功能理论的“人际功能”相当。这样我们可以将其整合为:题旨、情境、语脉、风格、语类、参与者、媒介。如果说海姆斯的分类有些琐碎,那么韩礼德和哈桑(1976)在论及语篇功能时,提出的语篇三大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却又过于概括。概念功能涵盖了语篇发生的情境、题旨及目的等,人际功能包括表达者和接受者,以及交际中发生的表情、语气等实际变项,语篇功能指使用语言联体成篇,即刘勰“执术驭篇”之谓,包括体类、风格形态的形成。
伯格兰德(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Dressler)1981年问世的《语篇语言学导论》(IntroductiontoTextLinguistics),一改此前的语篇观,将语篇置入社会网络,融汇语言学、语体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及认知科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进行观察,着重从言语交际来描写语篇的构成要素及特征,因而被誉为新派语篇语言学的标志性著作,代表了西方语篇学的前沿水平。该文认为:凡是语篇都必须满足如下七个条件方符合语篇性(textuality),即:衔接(cohesion)、连贯(coherence)、目的性(intentiona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信息性(informativity)、情境性(situationality)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衔接、连贯可转释为语脉或结构,目的性即题旨,信息性指语篇所述话题内容的新颖度而言。伯、德依据接受者已知还是未知的程度,将信息性分为三个级别。第一级的可预见性较高,信息性偏低;第三级可预见性较低,信息性则偏高;第二级处于中位,可依据情境作高低调整。信息性的适切度,由表达者意图和接受者期待决定。可接受性即“得体性”,得体与否取决于接受者主观态度,是接受者对语篇的题旨、体类、话题内容以及风格形态的满意度而言。如汉武帝元鼎年间,让最高司法官张汤拟定疏奏,由于不合御意,两次均被驳回。可见为文论语,可接受性的提出极为重要。互文性[注]该词系克里斯蒂娃所创,英译为“intertextuality”,其前缀“inter-”为相互之间之义,与词干“textual”加后缀“-ity”复合而成。是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J.Kristeva)在阐释苏俄巴赫金(М.М.бaхтинг)的“对话理论”时,从中推导出来:“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是在语篇构组的过程中,表达主体为强化其意念语篇的语势,进而引入已存历史语篇的过程和结果。
上述七项产生于交际,缺少任何一项都不成其为交际单位。伯德二氏所言,固然在理,然在实际操作上,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如“可接受性”自然是表达者希望接受者接受,但表达与接受之间的差距、障碍等各种要素很多。A认为可以接受,然而B却认为不可接受。此类交际事件很多,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况且“语篇”是历时性产物,此时可以接受,而彼时就难以接受。“信息性”与可接受性一样,作者认为信息量是高度,而有的接受者却认为是中度的,甚至是低度的。尽管言之凿凿,实际上理论破绽还是不少。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该理论是在印欧语的母胎中孕育、在印欧语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对其理论范畴、内在结构、语言事实的阐释,莫不以西语为宗。
尽管该文与汉语有诸多不洽,但仍对我们有诸多启迪,至少有如下四点:
(1)语篇制作固然要体现表达者的主观态度,以决定信息的含量和侧重面,然而接受者的背景知识、话语环境等不能不进入言语交际活动中,否则,真成了“对牛弹琴”。
(2)“情境性”的提示,对汉语学界来说极端重要,在我们的传统中,情景的地位一向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上世纪中期后,伦敦学派的情景思想才开始受到重视,才进入我们的学科体系,发展到今天,凡是涉及人文事实,不将其置入特定情景思考,一切等于零。
(3)“互文性”尽管源自文艺哲学,由法国学者巴特、克利斯蒂娃等所创立,但其影响力却不能忽视,其对诸多学科的解释力都很强,但互文性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来解释和观察具体语言事实,确有点“大材小用”。
(4)从伯德二氏的体系中,我们再次认识到中、西的差异,不仅是结构性的差异,而是体系性的差异。凡源自西论(包括苏俄),其基本思路是:立足于描写语言学的形式原则,沿着语法分析的方法演化出——语篇是超句现象。将语篇界定为“超句统一体”,或“句子以上的语言单位”、“许多语句在应用中的组合”、“内容相关的句子的连贯排列”、“大于句子的任何叙述语”。尽管所论各有千秋,然都在超句语法漩涡中打转转。形式界定的最大缺陷是:疏略了语境和语用者在语篇构成中的主导作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由于语义学、语用学及认知科学的带动,语篇研究的视野开始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开始审视语义问题。
五、汉语语篇学的逻辑体系
我们之所以倡导建立汉语语篇学的逻辑体系,就在于这个体系不因时空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在逻辑上凡是言语事件(语篇),其内部构成都必须有的要素,缺其中任何一项,都不称其为语篇,参照以上中西各主要理论,我们这里总括为六:题旨、情境、结构(脉络)、表达、体性(语体风格)、节律。这六个要素在语篇中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题旨是“帅”,由它统领其余。
(1)题旨 即语篇的主旨、主题、旨意、旨趣、趣旨、目的、动因、内容等。在“题旨”命题出现前,古人多用“志”、“道”和“意”,“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洎南北朝,范晔提出:“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狱中与诸甥姪书》)逮宋,周敦颐又提出“文以载道”(《通书·文辞》)。唐杜牧、金元王若虚都曾力主语篇需“以意为主”,一直到清王夫之则正式将这一原则确立下来,“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姜斋诗话》)。《文心雕龙》开篇就亮出“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的主旨,在《原道》《征圣》《宗经》帅旗导引下,展开了语类论、写作论、阅读论的论述。五四以降,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在语文教育的语篇教学中,在坚持“以意为主”谋篇原则的同时,又凸显情境、结构、表达等要素。1932年问世的《修辞学发凡》(陈望道),在“引言”中列专节论述“情境和题旨”,并将“题旨情境”视为语篇的第一要义。然在印欧语的语篇理论中,其所强调的首位不是意义而是形式。韩礼德(1994)认为,“没有语法的语篇分析根本不是语篇分析”。即使新学派领军人物伯格兰德和德雷斯勒,其所强调的语篇构成的七个要素,形式衔接仍排在第一位。
(2)情境(context) 即与题旨同现共存的场境和文化背景,是学界熟悉且运用自如的概念。在传统的语篇研究领域,先贤并未对其专门研究,既没有情境的概念,也没有语境的命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先哲无语境意识。刘勰强调语篇应“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圣》),制篇造语要适情应境,随时变通。苏东坡在其“文论”中,几十次的反复论说“随物赋形”。随物者即语境,赋形则是随语境的变化,而制作与之相谐的语篇。情境对语篇的制约是全面的、绝对的。不仅制约着语篇的意义、语脉运行轨迹,对语体、风格也有制约。在言语交际中,情境的制约是全方位的,不仅制约着表达者,也制约着接受者。如李密的《陈情表》。其呈递和批复程序清晰地显示出这种双向制约过程。李密(224—287年)幼年丧父,母改嫁,由祖母抚养成人。曾仕蜀汉尚书郎。蜀汉亡,晋武帝司马炎多次征召他入朝供职,但均被其以“祖母年迈多病而辞”。作为亡蜀宿臣,面对切峻诏书,却逋慢坚辞,杀身之祸影随,此为李密的语境。司马炎的语境是:面对亡国之俘,竟不识抬举,屡犯御令,不杀难立皇威,然虑及曾许诺朝野,以“孝”治国。而李密所陈,婉转凄恻,孝情笃厚,故不得不适应李密的语境,准其所奏。可见,面对同一语篇,表达者与接受者的语境迥然,且随时都在变化,直接影响着对语篇语义的解读。故结论是:没有情境就没有语篇。
(3)语脉 语脉即贯穿于语篇始终的流动性语义潜势。语脉这一概念是地道土生,最早由宋范季随提出,他认为凡论语著文,都应“从首至尾,语脉连属”[注]转引自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0页。。与语脉相近的概念,有义脉(刘勰)、意脉(宋李涂、吴可)、文脉(元杨载)等。明胡应麟在论及识读语篇时说:“凡读古人文字,务须平心易气,熟参上下语脉,得其立言本意乃可。”[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丹铅新录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0页。可见胡氏的语脉,与文脉同义,而与立言本意的意脉相区别。复旦汪涌豪先生在其《范畴论》中也曾断言:“未发之前,上下连贯之旨为‘意脉’;已发之后,前后统属之词为‘语脉’。”[注]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第260页。我们认为,依据“已发”“未发”来确定语脉与意脉的界限欠准确,意脉与语脉一样都出现在语篇的现场,只是其出现方式有别。语脉是凭借有标记的物质形式,来显现其存在。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其未发前的语意,《序志》已讲清:扬经抑邪。已发语篇的语脉,五十篇已清晰显示,是未发意脉的现实化。如果说二者有区别,其区别点就在“意在语先”。语脉受制于意脉,意脉对于语篇来讲具有唯一性。与西论比较,语脉与“连贯”最为贴近,它涵括了“衔接”与“连贯”的全部意义。
与语脉紧密相连的是“结构”,不同的语脉由不同的结构链所组成。“结构”一语东土虽古已有之,但近代以前从未用于诗文话语的构造方式。作为语篇的构造方式内涵,应是从西文structure转译而来。宋吕祖谦在《古文关键》中提出:“有形者纲目,无形者血脉”,强调纲目的关键是:首尾相应、铺叙次第、开合抑扬,有经纬相通,一脉过接。及元,杨载在《诗法家数》中,将吕氏的“有形纲目”演化为:起、承、转、合。洎清,刘熙载在《艺概》中将“起承转合”推而广之到一切语篇。“结构”实际上是言语事件的运行轨迹,线性潜隐形式的物质化。
(4)表达 即语篇话语的表达方式,也是一个普遍性范畴,任何语言概莫能外。表达作为语篇理论,萌芽于魏晋,成形于唐宋。宋真德秀在《文章正宗》中梳理汉语语篇时,所立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门。“议论”、“叙事”作为理论范畴正式被提出,显示了真氏理论上的自觉。洎清,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开篇就是“论说类”,近尾有“杂记类”,实为近世的“记叙、说明类”。曾国藩嗣承惜抱轩,于《经史百家杂钞》里,明标“论著之属”、“奏议之属”、“叙记之属”。论著、奏议为议论,“叙记”即“记叙”,其“告语门”中的四类(诏令、奏议、书牍、哀祭)均属“说明”。上世纪初始,由于受日本修辞学和西方修辞思想影响,先后有汤振常(1905)、蔡元培(1916)、陈望道(1922)、叶圣陶(1924),都论述过言语表达。逮及1940年代,蒋伯潜、蒋祖怡在《体裁与风格》(1941)中整理为议论、说明、记叙、描写和抒情五种。[注]详见蒋伯潜、蒋祖怡:《体裁与风格》,上海:世界书局,1941年。蒋氏父子的归类,对于汉语语篇的表达研究,具有定型作用,自此以降,无论在文选编纂,或是语文教材的编写,或是写作教学,都无不以蒋氏的分类为范,直至今天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仍以此为宗。[注]详见丁金国:《语篇的表达系统》,《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5)体性 “体性”最早由刘勰提出,《文心雕龙》通行本第二十七篇即为《体性》。“体性”实际上是个复合概念,“体”者,存在于言语社群集体意识中的言语体式;“性”者,指表达者个体在言语活动中所显现出来的由个体性情所决定的语篇风格。故而“体性”涵括了语体和风格,将其仅释为风格之意,显然失之偏颇。“体”最早用以论文说语是曹丕。《典论·论文》认为“文非一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进而确认“体有万殊”,其原因是客观世界“物无一量”(《文赋》)。可见,这种“体”不为个体所左右,是一种客观的为言语社群所公认的体裁,即语类。由体裁决定风格的命题,到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中,将“体”所对应的风格作了系统化整理,单独抽出来创建为汉语风格论体系: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并作了正负相对的处理: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体性》篇中所显现的风格是由个体的才、气、学、习主观要素所决定的,故另设《定势》篇,专论由体裁、语辞和韵律等客观要素所决定的“体势”。可见,两篇中的“体”实际上是一个存在于言语社群的一类语篇所显示出来的“气势”、格调。这种气势格调所凝结的是:个体与社群,客观与主观,语体与风格的精髓。刘勰以降,历代学者在研习刘氏理论的同时,或阐发,或增补。历史进入现代后,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专立章节阐释语文体式,将语体与风格兼而容之进行阐释,并将各体之间关系以图显示。时至今日,这个体系仍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语体学、语用学、美学、文学批评,以及相关的语文教育和语文实践。
(6)节律性 所谓节律,即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周期性显隐交替的现象。就语篇而言,语流中出现的由音高、音强、音长和音色组合的抑扬顿挫、高低起伏规律性的流动称为节律性。节律性在语篇中具有表情、表意和表态的功能。节律与声律、韵律、节奏及超音质音位、非线性特征等称谓,应是同一所指,但囿于学科和个人语用习惯,出现各取所需也实属自然。
对于语篇中的节律性,先哲在三千多年前,即已发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礼记·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及至现当代,学界对汉语节律的研究,已由感悟式转为科学化,先贤刘复、赵元任、罗常培等做出了重要贡献。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汉语节律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成绩卓著者有林焘、吴宗济、曹剑芬、林茂灿、吴洁敏、冯胜利、吴为善、王洪君等,笔者正是在当代节律学的启迪下提出节律性特征。有鉴于语言的民族性,各语言的节律在语篇中的作用和地位迥然,这是由节律的内核,即节律的支撑点所决定的。如英语的支撑点,经过西方学者近百年探索,发现决定其语流节奏的支撑点非音长,而真正起区别作用的是音高——重音。这一重要发现也直接影响着汉语的韵律研究。一个时期以来,“重音决定论”深刻地影响着汉语节律研究的视野。罗念生、闻一多、徐志摩等力主重音论,王力、林庚、启功、何其芳等在研究诗词韵律单位时,从平仄律中引发出“顿”“逗”“半逗”等单位,认为“顿”是汉语节律的基础,两个停顿之间则由“延连”来连接。吴洁敏(1989)对“顿”“逗”及“延连”作了整合处理,提出以“停延”替代上述概念,并力主停延是汉语节律的基础。刘现强(2007)在对英汉语“节奏支点”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停延是汉语节律的支点”的论断。之所以将停延作为节律的支撑点,是因为其对汉语有区别功能,停延对英语则无。如设“/”为小停延、“//”为停延、“#”为大停延,对鲁藜(1938)的《泥土》加以标注:
老 是/把 自己//当作 珍珠# 就 时时 有//被 埋没 的/痛苦#
把 自己//当作 泥土 吧# 让 众人//把你 踩成/一条 道路#
如果把该语篇中的停延全撤掉,这就意味着由不同时长所显示的各音节间的边界全消失,其结果是该语篇形同自然之声。
西论中的“可接受性”、“信息性”、“互文性”和“对话性”,四个概念的共通意义是超越主体,强调外在要素对语篇的制约,因而,我们认为是哲学意义上的提纯。作为普遍性范畴,在实践中难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