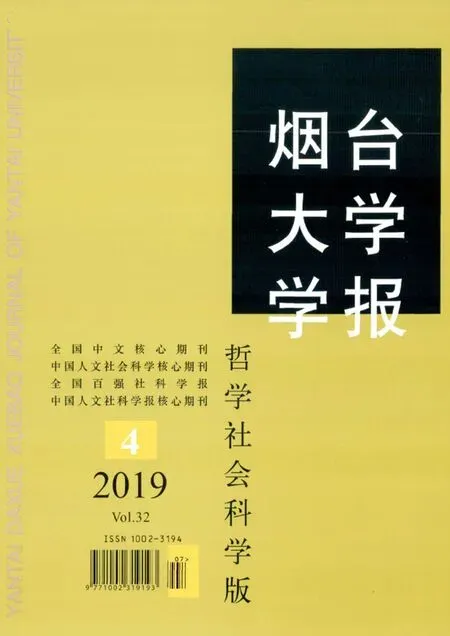“她江湖”文学场与新媒体时代的“女性向”方式
孙桂荣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女性向”最初来源于日本漫画,意为“面向女性的”、“针对女性的”,是一种将女性定位为主要受众(读者/观众)群体的文化类型,目前中国学界的研究以针对特定类型化文本的个案研究为主,而对由女性网络社群的“她江湖”文学场之整合性、语境性研究还不多见。本文旨在从以网络文化为代表的“女性向”文学场(“她江湖”)的建构角度讨论新媒体时代的“女性向”方式及其女性主义的可能性问题,重点探究“女性向”阅读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其对传统女性写作与女性阅读带来哪些层面的冲击,以及在新世纪以来的新媒体文学中是如何具体展开的。
一、“看/被看”的文化尴尬与女性阅读“异托邦”
“女性向”叙事以女性为目标读者,而非写作内容上的女性生活或写作者的女性性别,这是符合叙事学意义上的女性写作概念的,像沃霍尔曾言,“男性写作与女性写作文本的差异毕竟不在于所谓的内容,而在于他们的讲述方式、话语的特征(感伤的、反讽的或是科学的等)”转引自孙桂芝:《罗宾·沃霍尔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56页。。这与传统上从“女性写的”或“写女性的”角度来界定女性写作的思路大相径庭,但符合从受众感受层面言说的“女性向”原则。“女性向”并不拘泥于“谁叙述”层面的叙述人、叙述视点等传统叙事学关注的范畴,而主要是在“谁阅读”层面的受众构成、传播渠道、接受方式、感受认知等层面发言。对于“女性向”叙事而言,最重要的是建构一种相对女性化的阅读接受机制,其性别意义在于破解了私人化写作时期“看”与“被看”的文化尴尬。
从一定程度上说,“女性向”叙事首先是一种新媒体技术催生的大众文化,是新世纪以来文学分众化传播的结果,似乎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关注的纯文学领域中私人化写作浪潮没有太多关联。但事实上,它摒弃男性为主体的大众化阅读市场,衍生出了以女性为主体的“我阅读”理念,对1990年代“看”与“被看”的女性写作难题有一定的缓解、破释作用。在私人化叙事遭受热议的年代,女性本色的身体写作往往被文化市场上以男性读者为主体的阅读机制所误读。即使是卫慧、棉棉这样几乎成了负面性指涉的写作者,也有研究者在索解其文本后发现,“在‘为谁写作’问题上,她们是有明确的选择的,她们将自己的读者限定在同胞姊妹(未被男性阅读所整合的)以及具有女性同情心的男性读者身上”[注]金惠敏:《超前的女性写作与滞后的女性阅读——关于卫慧与棉棉的小说及其争议》,《中国女性文化》2001年第2期。。不过,大众阅读市场从来没有理会这种“小众化”的读者设置,旋即以奇观化的目光来窥视这些文本,将其阐释为情色化的女性文艺,这便造成了金惠敏所言的“超前的女性写作与滞后的女性阅读”之间的矛盾。或许卫慧、棉棉是否将读者设置成了“小众化”读者是有争议的,但这种本色的女性写作只有在“小众化”读者范畴(即“女性向”空间)中才能真正被阅读、接受的思路却值得学界注意。
如何理解这种“小众化”、“女性向”阅读机制的现实可能性呢?为了更充分地阐释这种小众化“女性向”阅读机制与以男性为中心的大众化市场机制的联系与区别,笔者在这里力图联系女性主义批评史上、对男性中心逻格斯进行解构与颠覆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加以对比说明。克里斯蒂娃、西苏、伊瑞格瑞的名字对中国女性学界来说并不陌生,表面看来,她们的理论言说同本文所述“女性向”文化并无关联,但事实上,其以“重建女性文明”相号召的主张与以女性受众为核心的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某种逻辑的一致性,只不过她们更多是将语言和文本当作颠覆父权制的主战场。正如女性主义学者宋素凤所言,“伊瑞格瑞与西苏的方法是诉诸女性,释放阴性能量,克里斯蒂娃则是期许一个性别符码不再具有文化位置意义的社会”[注]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2页。。无论是伊瑞格瑞的“女人话”、埃莱娜·西苏的阴性书写/身体写作,还是克里斯蒂娃改写拉康镜像说的符号态理论,都将语言、文本放置于女性解放的中心位置,而非只将其视为某种解放的工具和手段。这种文本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反抗被另一些女性学者认为精英气、经院色彩太明显,现实建设性不足。像丽塔·菲尔斯基认为,所谓的“阴性书写”基本上是一种“反写实主义的文本性美学观”,并对其所表征的女性解放之途进一步解释道:
从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文学文本的政治价值,只能由它们在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对妇女权益所具有的社会功效来决定;而不是靠演绎那些背离文学生产与接受的社会状况,把文本区分为“男性”与“女性”、“颠覆”与“反动”的抽象文学理论。[注]丽塔·菲尔斯基语,见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第152-153页。
无独有偶,这种基于文本社会历史功能的女性批评在中国学界也有一定呈现。像针对1990年代将男性塑造得较为恶俗,以“边缘”、“逃离”相号召对男权社会进行反抗的私人化叙事,有学者指出这种情形是将写作本身视为一种“姿态性”的女性反叛,一种与现实空间的社会问题相对隔膜的“纸上的女性主义”,“可以把男性写得非常丑陋、卑鄙,可以一千次一万次地诅咒男权文化,却损伤不了男权文化半点皮毛”[注]薛毅:《浮出历史地表之后》,《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这种悖论也让女性写作陷入了文本与语言学意义上的“超前的女性写作”之境,文化市场里的男性中心则进一步加剧了其接受语境上的“滞后的女性阅读”情态,而让女性批评陷入二难境地的“看”与“被看”的矛盾也就在这里得以体现。
如何避免仅从美学与符号学意义上建构女性写作伦理是问题的关键,小众化“女性向”文学场的必要性就是从这个层面而言的。按照布迪厄的说法,文学并不是单一的文本,而是存在各类文学场中,所谓“场”(Field)就是一个由拥有不同权力(或资本)的团体或个人,按照他们占据的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对这些权力(或资本)的占有,“也意味着对这个场的特殊利润的控制”,文学场便是这样一个“遵循文学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注]皮埃尔·布迪厄:《场的逻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以文学场理论反观女性写作上述问题,会更加凸显将作品传播、接受纳入观照范畴的“女性向”视域的必要性,即需要一个遵循女性阅读“自身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的出现与壮大,才能有效化解“女性化写作”旋即被大众文化市场中“男性化阅读”窥视、误用、改写的尴尬。
当然,在私人化写作只能通过大众市场机制才能公开化、公众化的1990年代,这种“女性向”文学场的完整性建构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女性从“被看”到“看”的转换需要相应的社会基础,既有文化心理层面的,也有物质技术层面的要求。因为在整个社会的性别机制还是男权文化的前提下,要建构一方“女性向”天地并不容易,但并不是没有一点可能性。早在1967年福柯就曾放言,“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明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些真实的场所、有效的场所,它们被书写入社会体制自身内,它们是一种反位所的场所,它们是被实际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些场所中,真实的位所,所有能在文化内被发现的其他真实的位所被同时表征出来,被抗议并且被颠倒;这些场所是外在于所有的场所的,尽管它们实际上是局部化的”[注]转引自邵燕君:《从乌托邦到异托邦——网络文学“爽文学观”对精英文学观的“他者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8期。。这种场所被福柯称之为“异托邦”(Heterotopias),以有别于作为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想象性空间的乌托邦。“异托邦”并非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有之乡,在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都具备的情景下,是能够在一定时空中发生的。按照沙茨的秩序仪式/融合仪式理论,文化社群所面对的外在威胁与内在冲突矛盾是可以通过一种具有仪式感的媒介方式加以解决的[注]桂琳:《宣泄仪式:类型电影视野下的冯小刚喜剧电影研究》,《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对于本文论述的“女性向”叙事而言,新世纪以来新媒体技术的发达便为此提供了一定条件。
二、“她江湖”文学场的建构
布迪厄认为文学场域本质上是关系网的建构,就是从社会大集体下分离独立出来的小集体,并且这个小集体内部充满着复杂性与斗争性,而复杂性与斗争性的来源则是文化权利的争夺。“女性向”文学场意味着女性在这场性别文化角逐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冲破男权文化的重重包围,一种堪称“她江湖”的女性为中心的文学机制的形成与壮大。这在新媒体文学的“女生频道”类中体现得最明显。像红袖添香、潇湘书院、起点女生网等原创文学网站已被研究者从写作者、阅读者、评论者、组织者、衍生产品策划者等各层面阐释为几乎都是女性从业者构成的“朋友圈”,其“不仅产生了自己的文坛‘领袖’、评论家、策划人、活动组织者,还发展出了许多周边衍生活动:插图、配乐、制作MV、广播剧、cosplay等”,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目前虽然已有部分商业资本的介入,但总体来说“大部分的劳动并无酬薪,只以同好社群的形式来维系——观念和趣味的共享、以及社群成员间的感情支持”[注]徐艳蕊:《网络女性写作的生产与生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滋生琼瑶、岑凯伦大众化言情小说的文化社群,在这种相对封闭的虚拟女性空间中,才可能发展出一种屏蔽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男性目光的女性阅读视点,以与本色的女性叙述视点相对接,并形成“女性向”叙述声音的可能性。
首先是该场域内女性作者、读者、评论跟帖者等在数量上的庞大,足以生发出某种“女性向”力量。当前我国的网络文学用户整体上是以男性群体为主的,而在晋江文学城、红袖添香、潇湘书院等大型原创网站上,女性用户数量却远远超过男性,还有一些综合文学网站中的女生频道都是“女性向”叙事的主要领地。女性以“创作者”、“读者”的身份群居于网络社区中,会形成某种集体化的、靠个人难以达到的不可小觑的声势或力量,在此意义上,将网络称为滋养她们话语发声的体制土壤并不过分。“女性向”文学场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女性将现实生活里日常经验的累积以及个人生命情感体验借助网络平台以文本的形式表达出来,是其最主要的动力所在。由于女性在社会历史中经常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女性向”文化是一种久被压抑、遮蔽的所在,其在印刷媒介时代并非不存在,而是因为没有有效的激发机制残存于孤立的个体女性心中或无意识深处,无法浮出叙述地表,更不用说形成某种影响社会的力量了。“她江湖”文学场的建构为这一切提供了前提,写作者、阅读者、跟帖点评者、论坛讨论者、衍生产品策划者等大体一致的女性性别,在群体力量的激发下将女性之间朴素的惺惺相惜之情上升为某种男权文化中“同呼吸、共命运”的性别文化。这种性别身份上的大体一致性,使得浪漫的想象、梦幻的表达、唯美的风格、唯爱的情感等女性钟爱的叙事特征有了不是迎合男权文化的消费需求的可能性,因为其是从女性心理出发、表达女性欲望、在女性中讨论、得到女性认可的。女性组成的“朋友圈”能够自足、自为地建构文学场的行为使得女性写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纸媒时代无所不在的男权文化窥视,而这对于女性主体性的形成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网络写作的低准入门槛为“女性向”文学场的形成也提供了一定便利条件。传统纸质出版印刷曾经垄断了文化符号的输入与输出,也一度是男性发挥历史见证者和彰显性别优势的文化场域。女性书写一般与个人经验息息相关,在有着鲜活细腻日常感受的同时却往往是被男性掌控的文学场视为不具有“宏大叙事”特征的风花雪月,抑或无关痛痒的自怨自艾,其受到来自男权社会源源不断的文化符号暴力,自身创作不断被弱化,由于“位卑言轻”往往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即使偶有发声也得不到太多公众关注,更是由此丧失了文化集群的可能性。然而,网络新媒介的出现也意味着新的文学体制、文学场域的诞生,最起码文学场所“把关人”的权力松动了。文学“把关人”既包括杂志社和出版社这些机构及这些机构中一个个的编辑、出版人,也包括能够以自己的推荐和评论影响新人作品发表的知名作家和评论家等。“在文化领域,竞争的利益通常是象征性的,其中包括对权威、声望和认可的争夺”[注]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利——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82页。,文学场所“把关人”把持的文学场难免有一定男权文化的痕迹,处于场内的中心位置,一言不合就给女性写作扣上“狭隘、自恋”等帽子就是鲜明体现,女性写作很难逾越文学场所“把关人”的操控进入主流文学体制,更难以集中形成规模化、自觉化的群体创作,无法掌控自身话语权。新媒体语境则为“女性向”文学场的最终确立提供了有利条件。女性作者操控了小说剧情的发展以及主人公之间的关系,按照心中理想的样子以及爱情范式来着力塑造男人形象;女性“中介人”取代过去的文学“把关人”负责网络文章的推送、运行、监管,使作品朝更加灵活和自由的向度发展,而“中介人”与“把关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其没有像后者那样有体制赋予的权力与明显的权威意识,而只是一个普通的联络人;女性读者的主体性日益彰显,通过直接留言、发帖、续写、改写、创作接龙等各类方式彼此或与作者对话交流。“女性向”文化就是在这些层面浸淫了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更加自由、民主的氛围,这对女性主体性的形成是大有裨益的。
值得注意的是,商业利润因素在新媒体语境中的“女性向”文化运转中并不总是起到决定性作用,无论是女作者、女读者、还是女“中介人”,情感投入的作用远超普通文艺现象。像写出粉丝众多的穿越小说《梦回大清》的作者金子在博客中曾写道:“我是一个面孔和才能都较为普通的女孩,但我拥有各种绚烂多彩的梦,写作就是给我做梦的机会。”[注]金子博客中的自述,http://baike.haosou.com/doc/5428597-5666821.html.穿越小说被精英研究者视为意淫、YY、精神鸦片的“白日梦”,但若细致考究起来,它首先却是女性写作者宣泄自身情感和欲望的场所。像起点女频的资深作者希行(代表作《名门医女》,曾获粉红票榜第一名)在访谈中说:“写网络小说是从2008年开始,在此之前一直喜欢写作,不是写作,应该说是讲故事……偶然的机会看到了第一本网络小说《回明》,当时就震惊了,天下还有这样好玩的故事!顿时一发不可收拾……”[注]转引自徐艳蕊:《网络女性写作的生产与生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作者的这种肺腑之言也验证了新媒体语境中的这种“女性向”叙事在宣泄制作者情绪方面的作用。来自读者层面的回应更加证实了在“她江湖”建构层面“女性向”文学场的巨大影响力。女性粉丝作为“‘过度’的读者”(excessive readers)不仅在数量上有着绝对优势,还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公开参与实现文化符号的挪用和情感上的迁移,从而直接促成了文本意义的再生产。像在耽美社群中对传统经典《三国演义》中刘备与诸葛亮、曹操与关羽之间男男之情的各种文学想象、演绎,就是“腐女”的再创作,其将自身梦想与欲望通过戏仿古人的方式张扬出来,进行肆无忌惮的改写、挪用、恶搞、影射[注]Xiaofei Tian, “Slashing Three Kingdoms: A Case Study in Fan Production on the Chinese Web”,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2015,27,1 (Spring).,这本身就是“女性向”文学场彰显自身“在场”的一种鲜明方式。
三、“她江湖”中的“她叙事”:女性主义的可能性
之所以在“她江湖”文学场中谈论“她叙事”女性主义的可能性,是因为如果仅仅在“她经济”、“她文化”的范畴中论述“女性向”问题,就有可能像“郭敬明现象”昭示的那样把“女性向”演绎成利益驱动下对女性受众中“大多数”的迎合,或者说将有着男权观念的大众商业原则对象化[注]详见孙桂荣、邱桂梅:《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向”叙事——以郭敬明现象为例》,《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期。。俘获“大多数”女性读者/观众,并不等于女性主体欲望的最大限度表达与接受。本色的女性自赏、自视、自伤、自审等女性写作旋即被阅读成窥视女性私人生活细节的“他者”文本,是与受众的性别构成与文化趣味密不可分的,也离不开商业原则的暧昧引导。而由女性作者、读者、评论者、策划者等构成,洋溢着鲜明情感投入(而非仅仅商业原则)的“她江湖”文学场,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这些大众文化语境中的亘古难题。或者说,由女性网络社群提供技术支持的“她江湖”文学场使“女性向”阅读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而也就是在这样的知识语境中,“她叙事”中的女性主义内涵才能成为某种可能,其颠覆了1990年代的女性主义表达,呈现出了某些新世纪女性文学的新症候。
比如身体叙事“看”与“被看”的主体与聚焦对象发生了变化。1990年代私人化写作中常见繁富叙述的美丽灼灼、欲望灼灼的身体美学在新世纪文学中仍有一定市场,其主要就是体现在新媒体文学中的“女性向”叙事,尤其是Boy’s Love(耽美)文类中。但与1990年代私人化写作主要聚焦于女性身体的浓墨重彩铺排不同的是,女性在耽美文本中不在场或只居于次属性角色,但她们却是主要的写作主体和阅读主体,被繁富细致书写的聚焦客体是男性的身体,作为叙述者和阅读者的女性却历史性地承担了“看”(聚焦者)的角色:
柔韧而颀长的颈子,精巧的喉结因了紧张兴奋微微滚动着。宽而秀丽的肩胛,平滑白皙的胸膛……[注]《入川之夜》,http://shugong.maozhumeili.com/wap/mtc.aspx?tid=12914475(posted December 8, 2010).
那白玉一般的双腿被曲起,那身体顺着酒桌向下躺,胸前红蕾凸起,明晃晃地展现出激越的欲色,长发如瀑一般落下,散在青色的石板上,仿若流光。[注]《恨》,http://www.yaochi.me/ebook/23797/36.html.
以上是两段对男性身体的描写,前面一段出自网络小说《入川之夜》,后面一段出自《恨》,两篇小说都是对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恶搞改写之作,描写的都是诸葛亮的身体,均为涉及男男之恋的耽美之作。与私人化写作中感性化、欲望化、细节化身体写作相类似,但与前者多体现为女性身体的自赏、自恋式描写正相反,它们着力铺排的是男性身体之美,乃至带有挑逗气息的男性色相。这两篇小说将诸葛亮塑造为男男之恋中的“受”(uke)角色,凸显其男色之美,与影视界愈演愈烈的“小鲜肉”现象有点类似。如同具有男色美的“小鲜肉”演员在目前的主流影视机制中遭到了各界批评一样,耽美叙事中表征感官化的男性身体书写也往往被主流文学批评诟病为欲望化消费气息。然而,考虑到耽美叙事的“女性向”文学场,在“女性作者为女性读者所讲述”的男性身体写作语境中,我们就会发现其颠覆了1990年代私人化叙事中“看”与“被看”的身体写作模式:一方面保护了女性自己的身体隐私,另一方面又以文化想象的方式意淫男性的身体,释放被男权文化压抑的女性欲望,这在非“女性向”叙事中是很难实现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网络文学用“眉如远黛、眸如春水、唇如凝露”来形容诸葛亮,对其身体书写盗用了很多女性修辞,颠覆了传统上以阳刚、健硕为特征的男性主流审美及其暗含的“男强女弱”蕴涵。非但如此,它们并没有完全类同于对女性身体的描写,“精巧的喉结”、“平滑白皙的胸膛”等均保留了一定程度上的男性生理特征,这进一步突出了其将女性定位于受众群体的“女性向”特征。耽美小说实现了从“强攻弱受”、“强攻强受”,到“美攻强受”的叙事模式的发展[注]肖映萱:《“女性向”网络文学的性别实验——以耽美小说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8期。,体现了女性不但无视男权文化的限制、尽情释放包括欣赏男色在内的自我欲望,而且有将之扩大化与公开化之势,这无疑是以张扬“女性向”文化的方式将体现性别权力翻转的表征,其在非“女性向”文化中亦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这是对1990年代女性主义写作理念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除了身体写作新症候,女穿男、男穿女的性别穿越“女性向”叙事还以投胎转世的方式表达了变性者、双性者、跨性别者等“性少数”人群的雌雄同体(androgyny)理念,其不再纠结于“复数”性别身份的迷惘与困惑等传统文学命题,而是以戏剧性、喜剧性的方式描述现代女性借用男性身体在古代社会政治经济领域有所成就,实现自我价值(如《青莲纪事》),或以变身为女性身体的男主以双性同体的混合气质征服古代人的故事,张扬被男权文化束缚的女性才能与跨性别的自由性、现代性(如《太子妃升职记》)。巴特勒说过:“性别不应该被解释为一种稳定的身份,或是产生各种行动的一个能动的场域;相反地,性别是在时间的过程中建立的一种脆弱的身份,通过风格/程式化的重复行动在一个表面的空间里建制……必须把性别视为一种建构的社会暂时状态(social temporality)的模式。”[注]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84页。性别并非一个经验化和本质主义的所在,而是流动性的社会文化建构,这种在主流社会中较为深奥和复杂的反本质主义性别观念却在《太子妃升职记》等网络穿越小说中以喜剧性与戏剧性的方式展现了出来。
当然,现代传播讲求分众化(customization),即“将传播媒介的服务对象从广泛的整体大众,分化为各具特殊兴趣和利益的群体,这是一种消解同质性神话、认同差异的传播理念”[注]孙桂荣:《新时期期刊出版制度研究》,《小说评论》2012年第5期。,从“女性向”写作需要伴随“女性向”阅读才能实现其释放女性欲望、满足女性心理需求的层面看,“女性向”叙事的文化传播目前更需要的是分众化原则,而不是雅俗共赏、多多益善的大众化市场伦理。《太子妃升职记》网上走红、所改编影视剧却在2016年被迫下架的复杂境遇,也表明“女性向”叙事要想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得社会性别认同还是需要一个磨练的过程的,离开了“‘她’江湖”文学场,“女性向”阅读并不容易取得其应有成效,这也是“变身”类性别穿越小说多被阐释成YY、意淫、消遣性“白日梦”等通俗读本的内在原因。另外,女尊、女强小说则除了部分践行西方女性主义的激进主张[注]像女尊小说《女权王国》中有婴儿全由高科技手段下的人造子宫产生,儿童养育法禁止母亲单独喂养婴儿,国家统一抚育孩子的情节,同激进—自由派女性主义者宣称的“生物性的母亲身份使妇女在身体和心理上都精疲力竭”,期待“能够在人工胎盘上进行体外受孕,由体外的人工培育完全取代自然的妊娠过程”有类似之处。见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5页。外,还改变了叙述人以谦卑姿态刻意迎合受众的吸引型叙述模式,代之以无限张扬、纵恣的女性权威感的表达,在近乎“恶搞”的气息中将父权制颠覆为母权制。像《四十花开:还魂女儿国》以缺钱、缺爱、卑微、普通的女主死后重生来到女儿国,以“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方式获得了权力、地位、才能以及多个男人的爱情,这一戏剧性逆转的故事把“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女性向”诉求发挥到了极致。
可以说,从“我叙述”到“我阅读”,“女性向”叙事呈现出与酷儿(queer)理论结缘的某种性别新质,但没有导向艰深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而是以语言的混搭,戏剧性、喜剧性美学风格、中国传统元素的渗透等,同1990年代以边缘、逃离、幽闭、偏执为关键词的私人化写作拉开了偌大距离。“女性向”文化有张扬、外露的一面,但其是通过新的叙述机制,及新时代中人们对女性利益、欲望有着更高接受度的新的阅读/观影机制的建构达成的,像对于《甄嬛传》《延禧攻略》等后宫文本中我行我素、或借男人达到自己目的的“坏女人”,中国公众认可度在逐渐提高,甚至将其奉为独立自主的“大女主”,这些都体现了社会性别意识在新世纪中国向前发展的一面。如同一个时代的文化书写也模塑了其性别再现一样,“女性向”叙事及其在类型化书写反复出现的过程本身,也成了再造女性主义话语的操演环节,并可能以更符合女性利益的方式,从想象性文化书写逐步推演到日常实践,并进而影响到公众的性别认知。在此层面上,笔者认同“女性向”、“她江湖”等文化的出现可以被视为推动女性解放向前发展的正向力量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