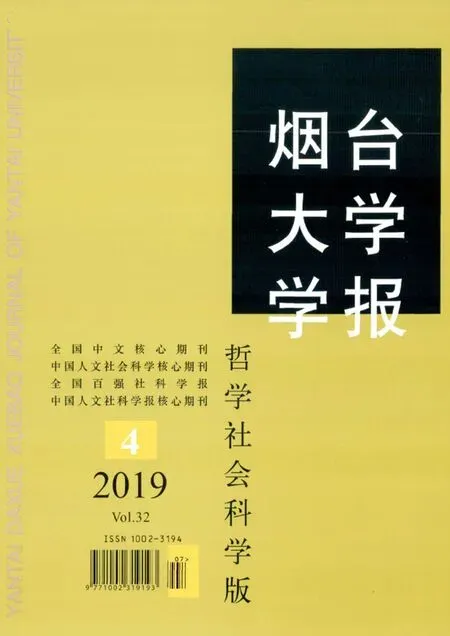清代永定河及东西淀争地矛盾的环境和社会因素
王培华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水、土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有土斯有财。山泽水土,人民衣食之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所以,古代中国不乏争地争水矛盾。清初,直隶永定河淀区,八旗王公贵族和庄头、汉民多占种偷垦河淀淤地滩地,种植麦、稻和蓝靛等。在以往对清代华北西北争地争水矛盾的研究中,发现争水矛盾的主体比较简单,无外乎县与县之间、上下游之间、渠道之间、农户之间等。王培华:《元明清华北西北水利三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但从未有一个地区,其争地主体,像清代永定河下游河淀区这样复杂。旗民争夺河淀地淤地,至少产生了八种类型的争地纠纷:八旗庄头与汉民之间、旗丁与民户之间、八旗庄头侵占官地、八旗王公与官府之间、八旗王公与民户之间、八旗侍卫护卫与民户之间、民户之间、乡绅豪强与官府之间等。王培华:《清代直隶河淀区争地矛盾的类型和特点》,《河北学刊》2018年第5期。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直隶永定河淀区产生这么多类型的争地矛盾?以往学术界对永定河下游和西淀的研究,较少涉及当时争夺淤地淀地问题,遑论争地纠纷的原因探讨。[注]参见陈茂山:《清代乾隆年间华北水旱灾害及减灾备荒措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编:《水利史论文集(第一辑)——纪念姚汉源先生八十华诞》,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4年;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吴文涛:《历史上治理永定河的环境效应》,《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4期;王玮璿:《清代永定河的滩地占耕问题》,东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笔者从气候和政治经济等方面入手,探讨争地问题。研究发现,17世纪到18世纪晚期海河流域进入偏旱时期,使得河道淤积,淀泊涸出,出现新的可耕地。但18世纪气候变化不足以完全解释这个问题,根本原因还是清初直隶八旗贵族的圈地,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变迁,如拨补地、民户租种旗地、直隶州县旗民杂处、八旗王公的强横、州县吏役把持地方词讼、永定河水利工程占地等。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助于人们了解清代八旗圈地对直隶地区社会稳定和人地关系的影响。
一、16—19世纪直隶河淀区沧海变桑田
造成清代直隶永定河淀区争夺淤地、淀地纠纷的大背景,就是16—19世纪,直隶永定河下游及东西淀,经历了自然环境的变迁。自明隆庆到清乾隆年间,从总趋势说,海河流域(包括永定河流域)经历了由多水到干旱的变化,正所谓沧海变桑田。[注]王培华:《清代永定河流域的沧桑之变》,《河北学刊》2017年第5期。而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6世纪中后期到17世纪初(明隆庆元年至万历四十八年,1567—1620年),海河流域,包括永定河流域中下游多水。气候干湿变化研究显示,1560—1620年(明嘉靖三十九年到万历四十八年)华北东部,出现偏涝峰值。[注]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28、332页。1567—1574年(明隆庆元年到万历二年),海河流域出现连续的涝年,其中有6年特大涝。[注]汤仲鑫:《海河流域旱涝冷暖史料分析》,北京:气象出版社,1989年,第31页。桑田变水乡泽国,农民实有耕地数量变少。万历十年(1582)东安知县阮宗道所修《东安县志》说:“东安田亩之数不减于昔,而可耕之地实缩于旧”,“今民田册有一顷之额,实无二三十亩之数”。[注]阮宗道修,杨廷选、邵鸣岐纂:《东安县志》卷二九《附》,明天启刻本。农民在册田亩少于实际可耕地数量,有多种因素:华北东部气候湿润偏涝,东安地势低洼;皇室占地;浑河河道变迁,水势盛大,许多村庄被淹没,平地水深丈余,农民耕地减少。地方志编者追问:“九河泛涨,民何从而耕?租何从而办?”[注]阮宗道修,杨廷选、邵鸣岐纂:《东安县志》卷二《田亩庄田补遗》,明天启刻本。总之,16世纪中后期华北东部偏涝,直隶永定河淀区水势盛大,东安、武清等地,由于水涝较多,淹没桑田,耕地明显减少。
第二阶段,17世纪到18世纪晚期,海河流域进入偏旱时期。[注]汤仲鑫:《海河流域旱涝冷暖史料分析》,第30页。1615—1720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到清康熙五十八年)华北进入旱灾多发期,[注]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第328、332页。1640年(崇祯十三年),直隶九河俱旱,白洋淀竭。[注]汤仲鑫:《海河流域旱涝冷暖史料分析》,第30页。1677—1684年(康熙十六年到二十三年)有两年特旱。永定河卢沟桥水志显示,1766—1777年间(乾隆三十一年到四十二年),永定河12年中有5年为枯水期,即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1767(乾隆三十二年)、1772(乾隆三十七年)、1776—1777(乾隆四十一—四十二年),永定河处于枯水期。[注]潘威、萧凌波、闫芳芳:《1766年以来永定河径流量与太平洋年代际振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期。清宫档案《晴雨录》(康熙二十四年到光绪三十年,1724—1904)是世界上最早、标准统一的系统天气观测资料之一,记录全国各州县逐日阴晴雨雪状况,其中北京晴雨录资料保存完整。根据北京的晴雨录(1724年以来)资料显示:18世纪中期,存在降水较少的时期。[注]张德二:《北京清代晴雨录降水记录的再研究》,《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1期。1724—1742年(雍正二年到乾隆七年)降水偏多,1743—1782年(乾隆八年到乾隆四十七年)、1821—1871年(道光元年到同治十年)降水较少。[注]兰宇、郝志新、郑景云:《1724年以来北京地区雨季逐月降水序列的重建与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1期。
17世纪到18世纪晚期,海河流域气候的干湿变化,具有从多水向少水变化的特点。在时人对海河流域从水多到水少状况的描述中,也有同样的认识。乾隆二十七年(1762),工部侍郎范时纪奏请,饬直隶州县于低洼之处疏浚种稻。乾隆谕旨:“此不过偶以近来一二年间,雨水稍多,竟似此等地亩,素成积潦之区。殊不知,现在情形,乃北省所偶遇。设遇冬春之交,晴霁日久,便成陆壤。盖物土宜者,南北燥湿,不能不从其性。即如附近昆明湖一带地方,试种稻田,水泉最便,而蓄泄旺减不时,灌溉已难徧给,傥将洼地尽令改作秧田,当雨水过多,即可藉以潴用。而雨泽一歉,又将何以救旱?从前近京议修水利营田,未尝不再三经画,始终未收实济,可见地利不能强同。”[注]方观承:《覆奏酌办水利疏》,见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一百八《工政十四》,光绪十二年(1886)思补楼重校本。可见,乾隆帝认为直隶以干旱气候为主,水多只是一时偶然现象,而干旱才是常态。乾隆三十七年(1772)裘曰修奏验收永定河工程一折,并陈近水居民与水争地之弊:“淀泊利在宽深,其旁间有淤地,不过水小时,偶然涸出,水至仍当让之于水,方足以畅荡漾,而资潴畜,非若江海沙洲东坍西涨,听民循例报垦者可比。”[注]《清文献通考》卷九《田赋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乾隆帝肯定裘曰修所奏,认为永定河流域水小为偶然,此时海河流域已经由干旱转向水多了,但承接前期水少干旱的状况,农民仍习惯于占垦河淀淤地。18世纪中期永定河下游淤积成陆,可能与降水减少有关。上述清人的说法,以及当代气候干湿变化研究的成果都显示,17世纪到18世纪,海河流域气候的转干,大致与永定河淀区边缘的淤积成平壤、涸出成陆地一致,即主要因素是气候变干旱,结果是河淀淤地得以形成。自雍正四年到乾隆后期,永定河河道变迁和淤积,使一些地方淤积成陆,东淀、西淀(白洋淀),水乡泽国变为桑田沃土,水域面积缩小,有些水边淤积成平壤,或偶尔涸出成陆地,形成可耕地。因此可以说,17世纪到18世纪晚期,气候转干,使直隶永定河淀区部分边缘变为平壤,形成大量可耕地。这些可耕地,成为各方觊觎的对象。[注]王培华:《清代永定河下游的蚕桑之变》,《河北学刊》2017年第5期。
第三阶段,19世纪,海河流域包括永定河流域,已经又由水少转向水多,1700—1799年(康熙三十九年到嘉庆四年)海河流域有8年特涝,1800—1899年(嘉庆五年到光绪二十五年)海河流域有11年特涝。[注]汤仲鑫:《海河流域旱涝冷暖史料分析》,第30页。卢沟桥水志研究显示,1784—1895年(乾隆四十九年到光绪二十一年),永定河有32年丰水期,其中1881—1895年(光绪七年至光绪二十一年)更是一个连续15年的丰水期;只有1848—1853年(道光二十八年到咸丰二年)连续6年的枯水期。19世纪整体趋势是多水涝。嘉庆六年(1801),海河流域大水,永定河处于丰水期,“值河溢被水。次岁旱蝗,沧、静、间均优免正赋,独未及青。亟向大吏条分缕析,慷慨请命,遂得入告邀恩。”[注]徐宗亮: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四十《传二·宦绩二·沈联芳》,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本。沈联芳为天津府青县知县,他向知府和总督请求赈济,他写道:“今则惟求除害矣。”[注]沈联芳:《邦畿水利集说》卷四,清钞本。沈联芳此文当作于嘉庆六年(1801)。[注]王培华:《元明清华北西北水利三论》,第240页。嘉庆六年大水,改变了人们对海河流域水旱规律性的认识。道光四年(1824)潘锡恩指出:“囊者,十年之中,忧旱者居其三四。患涝者偶然耳。自嘉庆六年(1801)以来,约计十年之中,涝者无虑三四。”[注]潘锡恩:《畿辅水利四案·附录》,道光三年(1823)刻本。此言嘉庆到道光直隶水涝要占30%—40%。[注]潘锡恩:《畿辅水利四案·附录》,道光三年刻本。这就是说,19世纪以来直隶水涝居多,当时人们仍然继续占垦占种河淀淤地,不过是承续以前干旱时的行为定势而已。所以,光绪八年(1882)时李鸿章等要求清理东淀,排水除害的迫切性远远超过兴修水利的迫切性。总之,清代永定河淀区的争夺淤地等,有自然环境变化的因素。
二、永定河淀区的争地矛盾及原因
直隶永定河淀区争地矛盾,有政治经济因素,包括八旗圈地、拨补地、旗民杂处、八旗王公势力强大、吏役把持地方等。
其一,清初发生八旗圈地事件,国家在边远地方给农民拨补地,直隶民户租种旗人地亩,将有收获,招致旗人和其他农户觊觎,引起争竞。
清初,京畿地区经历残酷的政治变迁,八旗贵族圈占京畿膏腴近地,许多民户失去土地和房屋,国家给予他们拨补地,但多为偏远州县的荒地、薄地、屯地。固安、永安、霸州、武清、永清、沧州、东安、高阳、庆都、漷县、新城县,膏腴之田多被圈占,拨补地多在南皮、静海、乐陵、庆云、交河、蠡县、灵寿、行唐、深泽、曲阳、新乐、祁州、故城、山东德州等地,甚至山海关以外,多系无主的屯地、荒地和薄地。农户往返种地麻烦,因此,由当地人佃耕,地租由当地代收。拨补地的地租,很少全额上交,造成有拨补之名,无拨补之实。农民失地后,赋税不减。直隶被圈占州县的农民,为生存计,租种八旗的土地,或者占种耕垦河滩地、淤地、淀地,种植茭芦、豆麦、高粱、小麦、水稻、蓝靛等。种植有秋,这就成为八旗王公庄头或其他农户觊觎的对象,引发争竞、纠纷。
直隶被圈占州县农民失地的情况,究竟怎样?以武清县为例,武清县民小地三亩,合大地一亩。武清县原额实在民大地2625顷94亩,圈丈地、投充地和船地共占地2585顷,到乾隆二年(1737)时实存民地40顷93亩,实存民地只占原额的1.5%;额外宫边地3014顷86亩,除去圈丈投充地、船地,拨补宛平地623顷,乾隆二年时实存339顷38亩,实存只占11%。原额实在马房地2438顷46亩,除去圈丈地1107顷63亩,船地788顷,乾隆二年时实存马房地542顷83亩,实存只占原来的22%。[注]吴翀修,曹涵、赵晃纂:乾隆《武清县志》卷二《田赋》,乾隆七年(1742)刻本。总之,各类土地的实存数量,都远远少于原额,有的只有原额的1.5%。无地何以为生?无地何以完税?正如前文引《东安县志》所说:“田亩之数不减于昔,而可耕之地实缩于旧。今民田册有一顷之额,实无二三十亩之数。”[注]阮宗道修,杨廷选、邵鸣岐纂:《东安县志》卷二九,天启刻本。无地或少地的现象时有发生,但税粮不变。此为明末东安县的情况。清代,由于八旗圈占直隶膏腴地亩,农民少地的情况更加严重。
国家在偏远地方给民户拨补地,那么拨补地是否能正常收租?农民能不能去拨补地耕种?民户安土重迁,一般不肯离乡前往拨补地,而是继续在本乡租种旗地。他们不能亲自耕种、收获拨补地亩,于是政府委托拨补地州县代收,而租户耍赖,少交租粮,甚至抗租不交,这样直隶农民租入减少。仍以武清县为例,顺治二年(1645),圈丈武清近城地三万二千四百八十八晌,计二千二百七十四顷十六亩,分给旗人。顺治四年(1647),将德州正、左二卫四十八屯及抛荒之民地,补还民人,谓之拨补。其粮仍于德州正、左二卫征解,其地或租或种,听民自便。经知县萧芳,钦差里书尚文举、张宠、王桂芳、李继茂带同各业主,赴德州正、左二卫,查认文卷、册籍,两处俱存。本县之民,既望升合以资养赡,而屯卫、佃丁,又恃土著而欺流移,抗租交控,胶葛不休。遂至有拨补之名无拨补之实。”康熙三十年(1691),直隶巡抚郭世隆,为缓解小民争端,定为官征官解,但康熙帝竟然不知有此事。后来九卿会议,制订处分条例,各行遵守,永杜分争。武清县共获得拨补德州正、左二卫屯边等地686顷88多亩。除有些士民自行耕种、收租外,每岁计官征官解租银975两8分8厘。[注]吴翀修,曹涵、赵晃纂:《武清县志》卷二《附拨补》,乾隆七年刻本。在郭世隆制订官征官解前,地租银不能完全足额征收。永清县的拨补地亩在德州、恩县、静海等处,因此租银或税粮就在当地征收。永清县“新收拨补地亩:顺治四年奉部文拨补德州、恩县二处官地,并静海县无主荒地,共三千四百二十二顷四十六亩”[注]周震荣修,章学诚纂:《永清县志》卷十,乾隆刻本。。后来这些拨补地亩从本县开除,退还彼处输粮。也就是说,有些民户拨补地距离较远,民户不能到远处去耕种,由当地人租种,并于康熙三十年才定为官征官解。
有些农户的拨补地在附近州县,就前往拨补地耕种,如永清县贾家的拨补地在天津静海。永清“贾氏有先业,为旗庄圈占,官给静海荒地百二十顷,名拨补地。地滨海潮远,不可种,而官租输纳,岁以为常”。乾隆四十二年(1777),永清贾家,卖出在静海县的拨补地,贾澎“以负租重,不可胜,乃出四百余金,始得除,地隶他人户贯,诸伯仲后裔,由是免追呼忧”。即永清县贾家,在静海耕种拨补地至少100多年。除拨补地,永清农户,也在静海新垦荒地,这类荒地,六年后都起科交租。从顺治十七年(1660)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这类荒地约三百六七十顷。后来永清县“列入开除”,改为在静海缴纳官租。[注]周震荣修,章学诚纂:《永清县志》卷十,乾隆刻本。也就是说,静海县既有永清县民户的拨补地,又有永清农户开垦起科的官荒地,还有旗地、马厂分布。各种地亩,交错存在,发生旗民争夺河滩地、淤地事,也就不足为奇。当永清贾家卖出在静海的拨补地后,贾家何以为生?贾氏“遗产数顷,为永定河冲溃,日食无资,因赁种旗地,躬自课耕”[注]周震荣修,章学诚纂:《永清县志》卷二十一《诸贾二张刘梁列传第六》,乾隆刻本。。
在农户租种旗人地亩时,失去土地的农户,往往私垦河淤地、淀地,一旦种麦有收,就招致八旗官员或旗丁和庄头的觊觎,其他农户也眼红,往往发生纠纷。以安新县为例,西淀位于安新境内,康熙二十七年(1688)、二十八年(1689),高以永为安州知州、兼摄安新县事,“州中皆八旗庄屯,民田仅十之一二,又皆沮洳斥卤,在畿辅为最贫。……八旗圈占安州民田,向拨补深泽、安平二邑地土以偿民,而地仍二邑人佃种,属其邑令代征租,给发安州人。佃户黠者每激怒邑令。当各为其民。盛气争胜,藉此得行其短少租额之阴谋。安州人苦之。”因拨补地地租收入减少,安州民户迫不得已,就多私垦淀地,“州东有白洋淀,众水所会,旱则涸而为地。民种麦其间,所收倍他地。旧额,每亩官征三升,以备赈。是年淀地麦茂,旗丁驻保定者,恃统兵官显贵谋夺之,指为民占马厂地,讦于巡抚,下令清理。”[注]陈鼎:《留溪外传》卷七《廉能部·高户部传》,康熙三十七年自刻本。万斯同:《石园文集》卷八《循吏高公传》,民国四明丛书本。旗丁指认农民偶尔种麦的淀地为马厂地,是旗丁与农户争夺淀地的常用手段。高以永认为,“此固淀也,偶涸而为平地。今指为马厂,他日水溢,地不可得,而按籍复索马厂,势必指他地实之,是民害无已也。力持之,民得刈麦。争者必欲得之,百计媒蘗。巡抚谓亲临丈量,则彼此心服。丈地有期矣。忽霖雨连日,所争地仍成巨浸。前言验而事得寝。”[注]陈鼎:《留溪外传》卷七《廉能部·高户部传》,康熙三十七年(1698)自刻本。农民耕种偶尔涸出的淀地,保定旗丁就来争夺。高以永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升户部江南司员外郎,所以保定旗丁与民户争地,当发生于康熙三十一年前。此案说明,争地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八旗圈占土地,使当地农户地少,远处拨补地有名无实,农户耕占偶尔涸出的淀地,又遭到旗丁的觊觎,于是发生纠纷。再以涞水县为例:“涞水地经圈占,小民多无寸土,惟赖租种旗地。例于上年纳租,次年种地。虽遇凶年,不敢欠颗粒。盖依此为生,惟恐失之。故有租种至数十年者,积妇子之血汗勤劬,致成沃壤,殆与世业无异。乃近有奸民,垂涎肥地,辄钻刺旗下家人,议增租数,往往夺此与彼。”[注]甘汝来:《甘庄恪公全集》卷十六,乾隆赐福堂刻本。奸民投靠旗人,争夺民户租种的旗地,引起纠纷。另外,畿辅拨补地亩,岁有更易。[注]朱彝尊:《曝书亭集》卷第七十七《赵吉士墓志铭》,四部丛刊景康熙本。在更易变换中,难免发生新的纠纷。
其二,被圈州县,旗人与民户交错杂处,且畿辅靠近京师,八旗王公势力强大,增加了治理难度。
河淀区的农户,为维持生计,私垦河淀淤地、河滩地。而八旗旗庄本来有旗地,农民种植有收,八旗王公、庄头又来争夺,导致争夺淤地、滩地纠纷。直隶九府内,广平、大名二府远处京南,无旗庄坐落。其余七府所辖,有旗庄坐落者,共计七十七州县卫,广袤约二千余里,其间旗民杂处,贤愚不等。根据册报,一州一县之内,有旗庄一二处,也有至百余处者。即一村一庄,有二三旗分之人居住者。亦只有地亩坐落,无旗人居住者。又有此州县旗庄虽多,而界址实与别府州县地相辐辏者。故淀区的情况相当复杂。州县,无约束旗人之责,仅理事同知一员,又难稽查周遍。若分旗分府,官员难以办理。[注]《八旗通志》卷六十三《土田志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直隶“旗民杂处,旗人以强凌弱,势力相加,谨朴良民,常被欺压,相习于强悍之风”。雍正四年(1726)分直隶为九府为三路,派员巡查。[注]王先谦:《东华录》“雍正四年六月己巳”条,光绪十年(1884)长沙王氏刻本。直隶地方“旗民杂处,猾吏舞文,太监戚属,散处州县,兼皇庄、王公等庄屯,全在其间”,地方官往往掣肘。[注]王先谦:《东华录》“雍正四年八月庚申”条。雍正八年(1730),户部根据旗庄多寡,地方远近,约三百里以内,设立一路,共设立八路。其中顺天府固安、东安、永清、霸州、保定、文安、大城,河间府任邱,保定府新安、安州、高阳十一州县为京南路,在地方上设立屯目、乡长等。[注]《八旗通志》卷六十三《土田志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乡长一名,专供督率农务交粮,并稽查逃盗、赌博等事。“旗人杂处,强豪梗法,当事莫敢谁何。”[注]陈梦雷:《松鹤山房诗文集》卷九《代送王峨园计部入都序》,康熙铜活字印本。旗民杂处,官府每每担心庄头把持地方事务,而确有庄头不服官府统驭,武断乡曲,鱼肉小民,甚且庄头下又有壮丁,如投充、雇工、拉车、放马之辈,原非旗人,尽行假冒。州县不能究诘一概,法不能施,稍或抵牾,旗人立时嫁祸州县。有的庄头捏造栽赃,有的庄头在公堂起哄,有的庄头凌辱州县官员,欺负民户。[注]宋荦:《西陂类稿》卷三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不仅庄头、壮丁欺压百姓,其家属亦如此。“直隶地方旗民杂处,庄头、壮丁多系带地投充之人。当日投充之时,一家只报一名,其余兄弟叔侄尚系民籍,皆朦胧影射,不纳丁徭,数传而后,子孙繁衍,支派难稽,是以有不旗不民之人,隐避差役,窝留奸匪,吏治不清,多由于此。”[注]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四《清查旗民疏》,敦和堂刻本。旗庄、旗丁及其家属,欺压普通民户,互争田土之事,时有发生。雍正六年(1728)清查直隶旗地时,“以直属旗民杂处,有互争田土之事,议令内务府、宗人府、八旗都统,将旗庄圈、赏、投充各项地,核明坐落四至,造具清册,一送户部,一送直隶总督,照式造册、钤印,发各州县收贮,如有旗民互争田土,即据册察勘审结。其带地投充人户,或有隐漏地亩,令一并清察。”[注]《清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其三,直隶被圈地州县与拨补地州县行政区划不尽相同,州县官既受八旗王公贵族的掣肘,又有书吏把持地方,同样增加治理难度。
本来各省都有布政使、按察使总理钱谷刑名。京畿直隶于户部,[注]李绂:《穆堂类稿》初稿卷三十一《畿辅通志序·代王布政》,道光十一年(1831)奉国堂刻本。不设布政使和按察使,有八道员各管一府。圈地州县,以邻县地拨补,退出者分还各州县,不尽系一道管属,彼此牵混难稽。至提解犯人,隔界推诿,会审参差。[注]《八旗通志》卷一百九十五《人物志七十五·金世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旗圈地、拨补地、退还地,名目繁多,这就使治理难度增加。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对直隶总督李维钧说:“畿甸之内,旗民杂处,向日所在,旗人暴橫,小民受累,地方官虽知之,莫敢谁何。”而汉官处理旗民争地等问题,既要避讳“旗汉冰炭之形迹”,又要“畏惧王公勋戚之评论”。[注]王先谦:《东华录》“雍正二年六月”条。所以,旗民争地之事,处理起来不那么容易。同时,直隶州县官员受制于书吏,雍正帝说:“直隶书吏积弊,凡新官到任,一切文卷悉行藏匿。州县官因限期严迫,急而求之,方始取出。由是堕其术中,以后事件,皆任其把持,为害甚大。”[注]王先谦:《东华录》“雍正四年八月庚申”条。可见,在争地纠纷处理中,不乏八旗贵族的掣肘和地方州县书吏的把持之害。
其四,因水利工程等占地,直隶被圈州县农民耕地更为减少,政府拨补河滩淤地,使争夺在所难免。
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金门闸附近修引河,“占用旗民地亩有限,应即于附近河滩淤地内,照数拨补”。[注]陈琮:《永定河志》卷十六《乾隆二十四年九月直隶总督方观奏》,清钞本。武清县土地的减少,有历次开挖永定河、筐儿港引河等所占地亩,有建造先农坛占地,还有皇后、公主食邑,未央宫、慈宁宫、乾清宫、庆陵、新庆备边地、景皇庄等,都占用不少土地。水利工程占地,官府即于附近河滩淤地内拨补,因此发生争夺在所难免。永清县境内,永定河河道占地,也有拨补地,“龙王庙东首,《拨补河滩地碑记》一通,雍正十年壬子立。又堤内断石碣一通,雍正五年丁未立。又留养局前《拨补各村地亩碑记》一通,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立。”[注]周震荣、章学诚:乾隆《永清县志》卷六《疆界》,乾隆四十四年(1779)刻本。据这些碑记记载,当时河淤地亩的拨补,以及河淤地的变化非常复杂,发生争端在所难免。
综上,17世纪中期以后,直隶的环境变化,尤其是降水偏少,使淤地淀地耕种成为可能,而八旗贵族圈占直隶膏腴肥地,虽有拨补地,但拨补地多在远处,使得直隶民户失去土地,但产去税存,所谓“田亩之数不减于昔,而可耕之地实缩于旧”,“今民田册有一顷之额,实无二三十亩之数”,农民依旧需要交纳租银,并未因地的减少而减额。
直隶永定河淀区争夺河淤地滩地的矛盾,十分复杂。其一,社会因素很复杂。有时一件争地纠纷的产生,不是一种原因,而是多种因素纠缠在一起。其二,涉事人员成分复杂。有时不是一类人员,而是多种人员参与到争夺纠纷中,这就使争地矛盾复杂而激烈。其三,直隶地方州县处理任何问题,不仅受到直隶省、保定府或顺天府的制约,也受到八旗、内务府等多种制度和因素的制约。其四,州县处理土田互争案件,还受制于州县吏役的制约。直隶争地纠纷案件的解决,有时长达几十年。
这种种因素,使直隶争夺滩地淤地矛盾纠纷复杂难解。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直隶总督方观承奏:“直隶河滩淤地,例许附近贫民认种输租,每户不得过三十亩之限,所以防隐占、杜兼并也。永定河旧下口一带,及南北两岸淤出地亩,向为地棍影射、胥役串通,往往占种多项,贫民不沾实惠。并有旗庄人等,冒认老圈业地,纷纷争控。”[注]陈琮:《永定河志》卷十六《乾隆二十三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清钞本。在争夺永定河下口一带及南北两岸淤出地亩时,有地棍、胥役、旗庄等多种势力参与。这种复杂的争夺资源纠纷,在其他地区很少见。即使在直隶南部的滏阳河流域,争水矛盾也主要表现为上下游之间的争夺,如邯郸与永年等各县争水。[注]王培华:《清代滏阳河流域水资源的管理、分配与利用》,《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在河西走廊,争水矛盾发生于上下游各县之间,一县内各渠坝之间,或者农户之间。[注]王培华:《元明清华北西北水利三论》,第60页。在新疆伊犁,兵屯、旗屯、回屯之间有争夺,但是其主要形式,还是不同屯田形式间的水土纠纷[注]王培华:《清代伊犁屯田的水利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不像直隶这样,水土纠纷,掺杂了很多政治的和满族八旗王公贵族的成分。
三、争地矛盾的性质和危害
水、土都是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源,直隶各方开发河滩地、淀地、淤地,种植小麦、蓝靛,建盖房屋等,其实质不仅是八旗王公贵族、地方豪强乡绅和民众与国家争夺水利和土地资源,也不仅是农户与农户之间的争夺土地,还是近水居民与水争地,即人类经济活动和居住生活侵占河流蓄水区和入海通道,这无疑严重影响河道畅通。在这过程中,官府贪图赋税利益,官修、民修各种堤防保护纳粮地亩,又造成蓄水区进一步缩小,入海通道进一步受阻,造成水淹村庄,积潦为灾。即占垦、升科、筑埝等活动,使永定河下游积涝成灾。经济发展和村民居住,严重地侵害河淀蓄水和河道行洪的能力,造成多种争夺滩地淤地的纠纷,也造成了环境的变化。对于居民与水争地,清代帝王和臣工都有深刻认识。乾隆三十四年(1769),天津道陈宏谋说:“淀池多淤一尺,则直省受水之咽喉即多一尺之阻。所以,自雍正三年淤平胜芳淀以后,各河水患,年多一年,数年之后,淀池淤满,西南诸水无处容受,则直隶水患更不可言。”[注]李祖陶:《国朝文录续编·培远堂文录》,同治刻本。淀池淤积,导致入海受阻,各河水患年年发生。乾隆三十七年(1772)六月,裘曰修奏称:“直省之弊,近水居民与水争地。如两河之外,所有淀泊,本以潴水。乃水退一尺,则占耕一尺之地。既报升科,则呈请筑埝。有司见不及远,遽为详报上司,又以纳粮地亩,自当防护。……堤埝一立,水从缺口而入,漫滋既满,被淹更甚。及水退之时,不能仍从缺口而出,遂致久淹不退,积潦为灾,多由自致。而愚民无知,仍以筑堤为爱,遂日曲防重遏,甚有横截上流,俾无去路者。”[注]陈琮:《永定河志》卷十七《乾隆三十七年六月裘曰修奏》,清钞本。水退一尺,占耕一尺,甚至得寸进尺,影响河道运行。乾隆四十七年(1782),胡季堂奏称:“河滩地亩尽,皆耕种麦苗,并多居民村落,一遇水发之时,势必筑围、打坝,填塞日多。是河身多一村庄,即水势少一分容纳。”[注]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戊子”条,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永定河志》卷十八列为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嘉庆十四年(1809),永定河道王念孙说,河淀农民占垦淤地,“不查,则种地而隐粮;经讼,则升科以免罪。历任州县不思水道之有妨,且图征收之日扩。增一分有粮之地,占一分蓄水之区。统计易沧而桑者,爰止千顷,无怪一经盛涨,宣泄为难。”[注]王念孙:《王石臞先生遗文》卷一《查勘新旧唐河潴龙河并东西淀应浚情形禀稿》,民国十四年(1925)高邮王氏遗书本。陈宏谋、裘曰修、胡季堂、王念孙等都揭示出,占垦耕种、建盖房屋、经济发展和村民居住严重侵害河淀蓄水和河道行洪的能力。
光绪八年(1882)正月,李鸿章奏称:“东淀本甚宽广,东西一百四五十里,南北六七十里,系为大清等河尾闾蓄泄之区,关系至重。……乃附近乡民,逐渐侵种,百数十年来,竟已占去淀地大半,现存不及三分之一。臣往来津沽,亲见丛芦密苇,弥望无涯,不特难容多水,即淀中旧有河道,因而淤垫,重烦官款挑挖。该淀既节节壅滞,上游各河遂泛滥为灾,动关全局。及今不治,再阅数十年,将东淀胥为平陆矣。”[注]《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十三《清理东淀折》,民国景金陵原刊本。此言绝非危言耸听。光绪二十九年(1903)袁世凯奏称:“同治年间,西淀淀地逐渐涸出,州民私种淀地。”[注]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卷一百八十一“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乙亥”条,袁世凯奏“安州之新安乡白洋淀”条,宣统元年(1909)上海集成图书公司本。于是把西淀涸出淀地,招民佃种收租。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封禁之地,终于在环境变化和清末新政中开禁,国家禁令更未能阻止18世纪新增人口对土地的渴望。总之,政治制度变迁、自然环境变迁叠加在一起,使直隶永定河下游积涝成灾。海河流域的洪涝问题,完全是经济行为、税收政策导致河流内涝、入海不畅。尽管从乾隆皇帝到历任直隶总督、历任永定河道、清河河道等,都反对直隶永定河淀区旗民占垦淤地、淀地、滩地,并采取措施,但最终都不能阻止私耕占垦淤地现象的发生。
综上,清代直隶永定河淀区争水争地矛盾中,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争地主体,仅气候的变化之由并不足以完全解释这个问题,根本原因乃是清初直隶八旗贵族的圈地,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制度变迁,如拨补地、民户租种旗地、直隶州县旗民杂处、八旗王公的强横、州县吏役把持地方词讼、永定河水利工程占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