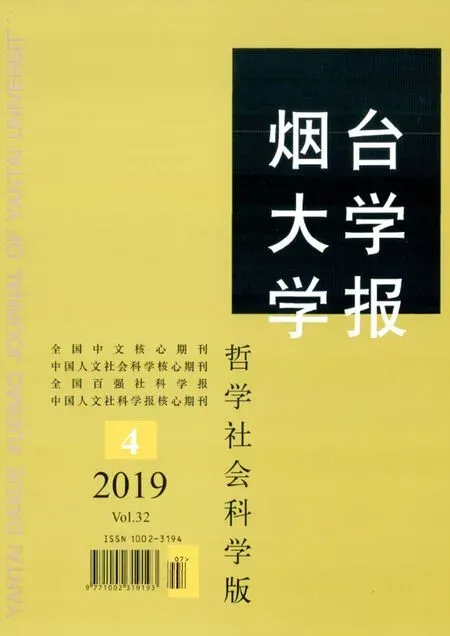汉代纪行赋中天气的表达和意义
丁 涵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珠海 519082)
纪行文学是作者以实际连贯的行程为主轴,记述沿途的风土人情、历史典故并穿插评议时政的一大文学门类,远源在《诗经》《楚辞》中涉及行旅的篇章。自两汉之交迄至东汉末年,赋充当了中国纪行文学发轫期的唯一载体。降及魏晋南北朝,纪行文学又以赋、诗颉颃并进的形式方滋未艾、渐臻繁荣。纪行赋最为人称引的地方莫过于其“因地及史”“即景抒情”的书写体制,王琳:《简论汉魏六朝的纪行赋》,《文史哲》1990年第5期;赵逵夫主编:《历代赋评注2:汉代卷》,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383页。比如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尝曰:“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15页。,业已注意到这篇见存最早的纪行赋侧重捃摭经史以使事用典的特性;《古文苑》中本赋的序言“之官,经历故晋之域,感今思古”章樵注:《古文苑》卷二,载孙星衍辑:《岱南阁丛书》,民国十三年博古斋景印刻本,第11页a。,也意识到作者将行踪所历的丰厚文化积淀转化为悲凉历史情怀的纪行笔法,由此带来的错综古今的沧桑感和化虚为实的现实感,于浴贤:《六朝赋述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页庶几成为论者对纪行赋的基本印象。殊不知这两种美感的形成,还有来自赋家运用细腻、密集、微妙的笔触塑造的行程中天气形象的参与。这些天气多带着一层悲戚底色、以多愁面貌出现在这些汉代的纪行赋中,既是当时气候条件恶化的结果,也是文字背后文学隐喻的要求。汉代纪行赋具备这种可信度与审美性契合无间的优势,使得其研究不但有助于获悉特定历史时期的天气状况,而且还裨益于理解“天气”在中国早期文学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天气的描述
人们对与天气息息相关的气象、气候、物候的敏感古已有之。譬如气象,古人通过观察这些“大气中所发生的一切物理(化学)现象和过程”,[注]周淑贞主编:《气象学与气候学(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页。总结出了相关经验。《小雅·信南山》(“上天同云,雨雪雰雰”)、《鄘风·蝃蝀》(“朝隮于西,崇朝其雨”)、《鄘风·定之方中》(“灵雨既零”)、《卫风·伯兮》(“其雨其雨,杲杲日出”)、《小雅·角弓》(“雨雪瀌瀌,见晛曰消。……雨雪浮浮,见晛曰流”)等分别用只言片语,粗线条地勾勒了下雪前、下雨前、及时雨、日出、冰雪融消之容。
再如,古人也勤于观察气候——这个“某一地区气候系统的全部成分在任一特定时段内的平均统计特征”[注]William L. Gates, “The Influence of the Ocean on Climate (Scientific Lecture at the 28th Section of the ECWMO),” WMO Bulletin, vol. 2758, no. 3 (July 1977), pp.168-169.,以及受其影响的生物反应——物候。[注]刘敏、方如康主编:《现代地理科学词典》,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99页。《小雅·四月》云:“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注]朱熹著:《诗集传》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49页。隐约归纳出气候和物候在节律上的呼应。其周期性和稳定性一旦被遵循,则便利于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安排。《豳风·七月》一篇所言“以时系事”皆农桑稼穑之事,也即朱熹《诗集传》所说的:“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昆虫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注]朱熹著:《诗集传》卷八,第93页。
到了《楚辞》中,节候、物色变化的规律一般紧扣着感时伤世的情感基调。《文心雕龙·辨骚》篇曰:“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注]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一,第162页。观览楚骚文辞便可见时令变迁。《九辩》一文捕捉到了四季中最萧飒的时节中最动人的境头: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廪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沉藏。……霜露惨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济。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将至。……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怅而自悲。四时递来而卒岁兮,阴阳不可与俪偕。[注]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2-192页。
春夏秋冬四季更替给读者最直观的感受则是变与不变的轮回:或者节同时异,或者物是人非。此篇又将秋天草木零落、霜露俱下、寒风侵肌、阴雨不绝的凄怨物象呈露得淋漓尽致。鲁迅先生置评道:“凄怨之情,实为独绝。”[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5页。这种凄怨之情还可从草木的荣枯引申到人世的盛衰,宋代朱熹在《楚辞集注》里精辟地批语道:“秋者,一岁之运盛极而衰,肃杀寒凉,阴气用事,草木零落,百物凋悴之时,有似叔世危邦,主昏政乱,贤智屏绌,奸凶得志,民贫财匮,不复振起之象。”[注]朱熹撰,蒋立甫校点:《楚辞集注》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6页。时序轮替、岁月更换中的韶光易逝之感或可诠释为哀时叹世之慨,因而饶有隐喻艺术的感染力。
至若天气,则与气象、气候和物候或多或少地交叉联系,但区别是天气特指在较短的时间尺度和确定的地域范围内各种大气状态和大气现象的综合。[注]周淑贞主编:《气象学与气候学(第三版)》,第1页。《诗经》中的天气描述通常发挥着取譬引类、触物起情的功能。与天气相关的字眼屡被用来提摄全诗,如《小雅·正月》云“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注]朱熹著:《诗集传》卷一一,第129页。《邶风·谷风》云“习习谷风,以阴以雨”。[注]朱熹著:《诗集传》卷二,第21页。循环复沓以导引下文者也不乏其例,如《小雅·谷风》云“习习谷风,维风及雨”、“习习谷风,维风及颓”、“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注]朱熹著:《诗集传》卷一二,第146页。《邶风·终风》云“终风且暴”、“终风且霾”、“终风且曀,不日有曀”、“曀曀其阴,虺虺其雷”,《邶风·北风》云“北风其凉,雨雪其雱”、“北风其喈,雨雪其霏”,《小雅·蓼莪》云“南山烈烈,飘风发发”、“南风律律,飘风弗弗”。[注]朱熹著:《诗集传》卷一二,第147页。凡此种种失节无度的极端天气在诗中一语双关,带有人性叵测或政治暴虐的弦外之音。当然,除了人性讽刺和政治怨刺之旨外,还有用作烘托气氛的设词案例,如《召南·殷其雷》云“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殷其雷,在南山之侧”、“殷其雷,在南山之下”,[注]朱熹著:《诗集传》卷一,第11页。《郑风·风雨》云“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潇潇,鸡鸣胶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注]朱熹著:《诗集传》卷四,第54页。都在一唱三叹间着力渲染了电闪雷鸣、风萧雨晦场面中的相思之苦。
相较《诗经》中对天气的简笔粗描,《楚辞》中的眼前即景更为生动隽永。如《九歌·山鬼》云“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注]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81页。《九章·悲回风》云“悲霜雪之俱下兮,听潮水之相击”等,[注]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160-161页。多为专注于脱离现实的内心独白,因此《楚辞》天气描写中幻想的意味要远大于真实。
二、早期纪行文学中的天气
《诗经》《楚辞》中还有少量涉及行旅的篇章,它们中的天气语言与那些天气真实性缺席的诸篇大异其趣。
《诗经》中被视为纪行文学滥觞之一的《豳风·东山》,[注]王允亮:《汉魏六朝纪行赋考论》,《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往复四次在各章开头叠咏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注]朱熹著:《诗集传》卷八,第94-95页。不仅出征的目的地、返回的起始点被反复强调,而且归程中的天气也有迹可循。作者遭逢朦胧细雨,好在久戍还家,终究是喜胜于悲。这一“以哀景写乐意”的天气表现手法不唯见诸此诗,《诗经》中另一首“行役征旅”诗《小雅·采薇》,[注]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0页。有一诗句据说曾被谢玄推尊之至,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注]刘义庆撰,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校笺》卷上《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28页。王夫之亦有妙论曰:“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注]王夫之著,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卷一《诗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页。就此诗而言,这种情境反衬的落脚点或许仍在“以哀景写乐”。细味忆昔从征时,倒是杨柳依依、春风拂面;如今归来,却是漫天飞雪、背影孤独,征人劫后余生的悲欣交集的心路历历可辨。与其异曲同工的还有《小雅·出车》云“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注]朱熹著:《诗集传》卷九,第107页。同样点染了往返的时气差异:之前出发时,正值夏初禾苗青青;而今凯旋日,已是隆冬雨雪载途。天气虽不理想,但能够从九死一生的沙场上回返,就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楚辞》中的《远游》和《涉江》被清人孙梅、近人刘师培视为纪行文学先河,孙梅曰:“《西征》《北征》叙事纪游,发挥景物,《涉江》《远游》之殊致也。”[注]孙梅:《四六丛话》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刘师培曰:“《西征》《北征》,叙事记游,出于《涉江》《远游》者也。”[注]刘师培:《论文杂记·概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6页。其情况需分而述之。《远游》重在蹈虚避实地陈述天空遨游:
恐天时之代序兮,耀灵晔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沦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遥兮,永历年而无成。……重曰:……顺凯风以从游兮,至南巢而壹息。……舒并节以驰骛兮,逴绝垠乎寒门。轶迅风于清源兮,从颛顼乎增冰。[注]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165-174页。
一番精神探索之后,作者担心天时代谢,旭日西沉。适值微霜席卷,芳草凋零。百无聊赖下他再度翱翔,先乘着南风随之飘荡,游至南巢稍作休息,之后信马由缰到达天边北极的寒门,超越疾风迈往寒风源头,追随颛顼攀援层层厚冰……此般经营四荒、周流八漠之举盖非舟车足力之能及,无非是神游而已。《远游》的纪行多据间接材料以虚拟悬想,模拟《离骚》的痕迹略见一斑,连带着此中的天气也披上了抽象、失真的色彩。
较之《远游》,《九章》习惯上更被接受为反映屈原放逐的系列作品。[注]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曰:“屈原放于江南之壄,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见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120-121页。后世如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明王夫之《楚辞通释》、清刘梦鹏《屈子章句》、今人汤炳正《屈赋新探九章时地管见》和《楚辞今注》等皆主此说。近人黄侃看出刘歆之后的纪行作品“皆自《遂初》出”,而“彼(刘歆《遂初赋》)又本《九章》。”[注]黄侃平点,黄焯编次:《文选平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7页。其间的《涉江》一篇更是翔实屡述了屈原从今武昌地区展开的一段沿沅水而上的辗转足印:[注]清人胡文英曰:“《涉江》篇,由今湖北至湖南途中所作,若后人述征纪行之作也。”见胡文英:《屈骚指掌》卷三,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19页。
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注]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129-130页。
明人汪瑗《楚辞集解》曰:“此篇言己行义之高洁,哀浊世而莫我知也。欲将渡湘沅,入林之密,入山之深,宁甘愁苦以终身,而终不能变心以从俗,故以《涉江》名之,盖谓将涉江而远去耳。”[注]汪瑗撰,董洪利点校:《楚辞集解》,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2页。此题解已明晰点出入林、入山之行的氛围是“愁苦”为主的。其确切作年虽无从知晓,但进行时季是秋冬当无疑。作者从鄂州泽畔迎着凌冽寒风水陆兼程,过常德、辰溪而入溆浦,愁看山高蔽日、雨锁烟迷,怅望雪珠纷飞、雾霭沉沉。钱锺书评点道:“开后世诗文写景法门。”[注]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12-613页。实际上这段对沅水流域山川风貌的铺叙不单大开诗文写景法门,而且对诗文纪行也别有意义,它在保留真实感的基础上,凭借愁云惨雾、凄风苦雨等天气构成的凄美哀景以展露幽独哀志。《文心雕龙·辨骚》云“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注]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一,第156页。此之谓也。
比照纪行文学的《诗》《骚》二源,首先,需肯定《诗经》中行役征旅诗篇对纪行文学的肇端之功,虽然后世注家对个中内容存有分歧,但这几首诗中纪行的各个要素大都无所不赅,且较为完整连贯地交代了行程的经过,相对《诗》《骚》中非纪行诗文的天气处理手法更进一竿。其次,《楚辞》中放逐流寓的篇章,无论在外在形态还是内容肌理上,对后世纪行赋之烙印均比《诗经》中的行役征旅诗来得更为显著深远。随行的险恶天气被作者投入更多目光,并渐具与艰苦的跋涉处境、消极的个人心境或动荡的社会环境相配合的表达雏形,至此纪行赋已是呼之欲出。
三、两汉纪行赋中的恶劣天气
相比散见在《诗经》、《楚辞》中的征行诗文以寥寥数语以少总多、点到即止地白描天气,两汉的纪行赋细腻、真切、集中、立体地刻画着风云变色、河山动容,其牵涉的天气又多在恶劣的范畴,“如雷电、冰雹、大雾、沙(尘)暴、暴雨、台风等”。[注]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785页。
刘歆(前50-23)作于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末的《遂初赋》,[注]对此学者持不同意见,如:刘跃进认为约作于建平三年(前4),见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98页;彭春艳认为作于太初元将元年(前5)十至十二月,见彭春艳:《刘歆〈遂初赋〉〈甘泉宫赋〉作年新考》,《兰台世界》2014年第29期;徐华则认为应在建平二、三年(前5-前4)之间,见徐华:《刘歆〈遂初赋〉的创作背景与赋史价值》,《文学遗产》2013年第3期。笔者更倾向于陆侃如建平元年(前6)的推测,首先陆氏认为《汉书·楚元王传》透露刘歆此年从事了如“改名为秀,上《山海经》,请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又作《移太常博士书》”等诸多活动,其次他又据刘歆《遂初赋》中“守五原之烽燧”句和刘歆《上山海经表》中“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句认为“从官衔上知道不能作于本年以后,从改名秀上知道也不能作于本年以前。”故系于此年,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9页。承载着他历经河内、晋国故地、五原的北徙足迹以及与之相随的见闻感想。在甫抵终点前的重镇——临沃(汉五原郡县名,今内蒙古包头西)之后,他似乎有意在蹊隧险绝、人迹罕至之地驻足,用“遥思”和“垂意”两个动作来遐想过往和洞察周遭:
济临沃而遥思兮,垂意兮边都。野萧条以寥廓兮,陵谷错以盘纡。飘寂寥以荒睗兮,沙埃起之杳冥。回风育其飘忽兮,回飐飐之泠泠。薄涸冻之凝滞兮,茀溪谷之清凉。漂积雪之皑皑兮,涉凝露之隆霜。扬雹霰之复陆兮,慨原泉之凌阴。激流澌之漻泪兮,窥九渊之潜淋。凄怆以惨怛兮,慽风漻以冽寒。兽望浪以穴窜兮,鸟胁翼之浚浚。山萧瑟以鹍鸣兮,树林坏而哇吟。地坼裂而愤忽急兮,石捌破之岩岩。天烈烈以历高兮,廖窻以枭牢。雁邕邕以迟迟兮,野鹳鸣而嘈嘈。望亭隧之皦皦兮,飞旗帜之翩翩。回百里之无家兮,路修远之绵绵。[注]此赋的正文今可见最早载于《艺文类聚》,见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二七《人部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90页。《岱南阁丛书》所收《古文苑》中的此赋版本略为不同,较前者,其序言更长且正文更为完整,章樵注:《古文苑》卷二,第13页a-b。
当他步入临沃,映入眼帘的是一派清冷肃杀之景: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只见朔风回旋,沙尘蔽日;河川封冻,雹霰覆野。然后他又察觉到了静中有动的迹象和音响:江河解冻导致的冰块激撞,气旋穿过引起的风声哀切,加之树摇叶落、山崩石裂、哀鸿翩翻、军旗飘卷……一切绘影绘声,宛在目前。其中百兽伏窜、群鸟悲啼的这幅画面,还为后世的王粲名作《登楼赋》中“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一段所本。[注]王粲:《登楼赋》,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一一《游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91页。此地距他赴任的五原郡治所已然不远,征程的高峰却与天气的急转直下和心情的跌落谷底形成鲜明反差。
班彪(3-54)的《北征赋》作于改朝换代频仍的公元25年岁尾,[注]《资治通鉴》载:“九月,赤眉入长安,更始单骑走”,又“十二月……三辅苦赤眉暴虐,皆怜更始……隗嚣归天水,复招聚其众……三辅士大夫避乱者多归嚣,嚣倾身引接,为布衣交……安陵班彪之属为宾客。”见《资治通鉴》卷四○,光武帝建武元年九月、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3册,第1283、1288页。《后汉书·隗嚣公孙述传》亦有类似记载。龚克昌据以上资料考定班彪于建武元年十二月北附隗嚣。见龚克昌、苏瑞隆评注:《全汉赋评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3-354页。记叙了从长安途经周秦故地、再西北向至天水的行迹。在迫近安定郡城(今宁夏固原)的高平县时,天气骤然变得严酷异常:
齐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猋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鸡鸣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悢以伤怀。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揽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阴曀之不阳兮,嗟久失其平度。[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九《纪行上》,第429-430页。
登陟高平环顾和远眺这片被浩瀚无际的银色雪海裹束下的塞北荒漠,四周风水激荡,云雾迷蒙;天边鸿雁南翔,鹍鸡啁哳。通过登高、环视和极目,不同高度、方位、距离的物色对比更加剧了视觉和听觉的冲击。这位“无家”的“游子”念及故都和故里、万物与生灵,不禁抚剑陨泪、泣涕涟涟。
蔡邕(133-192)作于桓帝延熹二年(159)秋的《述行赋》,笔述了始自陈留出发,游历大梁、中牟、管城、荥阳、成皋,终于偃师的长途奔波。赋中作者对天气的渐变和情绪的潜移更加体物入微。启程伊始,天公便不作美:
余有行于京洛兮,遘淫雨之经时。途屯邅其蹇连兮,潦污滞而为灾。乘马蟠而不进兮,心郁伊而愤思。[注]蔡邕著,林纾选评:《蔡中郎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53页。
淫雨连绵造成积潦成灾,骄马偃蹇更使人心不宁。洛阳渐行渐近,雨势丝毫不曾敛抑:
寻修轨以增举兮,邈悠悠之未央。山风泊以飙涌兮,气懆懆而厉凉。云郁术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渐唐。仆夫疲而劬瘁兮,我马虺隤以玄黄。格莽丘而税驾兮,阴曀曀而不阳。[注]蔡邕著,林纾选评:《蔡中郎集》,第53页。
快马加鞭穿越河洛期间,先是山风汹涌,雾气逼凉;俄而沉云四塞,大雨倾盆。在暗无天日的秋季人困马乏,蔡邕一行止步于土丘之前。随着行程的推进,天气逐步在恶化,他的忧伤也渐次累积:
玄云黯以凝结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败而无轨兮,途泞溺而难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师而释勤。……佇淹留以候霁兮,感忧心之殷殷。并日夜而遥思兮,宵不寐以极晨。候风云之体势兮,天牢湍而无文。弥信宿而后阕兮,思逶迤以东运。见阳光之颢颢兮,怀少弭而有欣。[注]蔡邕著,林纾选评:《蔡中郎集》,第54页。
头上黑云压城,大雨滂沱;脚下污泥浊水,道路梗阻。偃师已距洛阳不远,蔡邕非但没有将抵尽头的欣悦,眼看风雨不测、晴意久无,反而徒增了内心的挣扎纠结。栖迟两日后,他西望长安,发觉云开见日、雨后初霁,情不自禁地转悲为喜。但短暂的欢欣转瞬即逝,当他朝着京洛策马西进,无可奈何的现实致使他再次回肠九转。前前后后,蔡邕情绪的起伏伴随天气的好坏而几经顿挫。
在上述赋作中,仍可发现《诗经》的行役征旅诗关注行程中的天气、《楚辞》的放逐流寓篇重视以哀景写哀情的余影,然而汉代纪行赋在天气描写上愈发浓密、细致、忠实、曲折和多维,天气在全文中不再居于可有可无的次要地位。
四、自然和人文背景
上列汉代纪行赋中天气呈现的共性看似巧合,实则有其必然性。有关天气描写不能跳脱其历史和文化背景。
首先,这些恶劣天气的发生并非凭空杜撰,而是在气候史上有据可依。竺可桢先生在上世纪就曾归结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寒暖交替史大致可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公元初至公元600年这一时段正巧隶属于第二个寒冷期。[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历史学家、气象学家近年进一步考证得出,约在两汉之交,中国的确经历了由暖转寒的气候剧变。[注]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特别是在公元前50年至公元70年这一百二十年区间,事关低温灾异的记录多达二十余起。王莽专政的十年中就有七年曾被严寒侵袭。[注]李廉水等编著:《应对气候变化研究进展报告》,北京:气象出版社,2012年,第254页。刘歆的《遂初赋》和班彪的《北征赋》前后分别作于公元前6年、公元25年的秋冬,又恰逢寒冷期,无怪乎刘歆在赋尾言及在“玄室”的温暖隔绝下虽找到了一丝静谧与自足感(“既邕容以自得兮”),但仍对极度寒冷心有余悸(“唯惕惧于笁寒”)。同理,班彪赋中形容站在旷野面对残年衰景弥漫着的寒心销志也不是无病呻吟。
蔡邕作于公元159年的《述行赋》述及当年雨灾洗礼的遭遇,在文献中更非孤证。《后汉书·桓帝本纪》载录:“(延熹二年)夏,京师雨水。”[注]《后汉书》卷七《桓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2册,第304页。又《后汉书·五行志》侧证:“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余日。是时,大将军梁冀秉政,……其年八月,冀卒伏罪诛灭。”[注]《后汉书·五行志一》,第11册,第3270页。蔡邕又作《霖雨赋》,[注]今只存六句,《艺文类聚》卷二题作曹植《愁霖赋》。严可均案:“张溥等因收入《子建集》,今考《文选》张协《杂诗》注引蔡邕《霖雨赋》云:‘瞻玄云之晻晻兮,听长雨之霖霖。’曹植《美女篇》注引蔡邕《霖雨赋》云:‘中宵夜而叹息。’知此赋在《蔡集》中。”见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六九,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852页上。今余残篇云:“夫何季秋之淫雨兮,既弥日而成霖。瞻玄云之晻晻兮,听长雷之淋淋。”[注]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二《天部下》,第30页。将之与《述行赋》序言“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及正文开首二句“余有行于京洛兮,遘淫雨之经时。途屯邅其蹇连兮,潦污滞而为灾。乘马蟠而不进兮,心郁伊而愤思”对读,说明延熹二年京畿附近的淫雨从夏日一直延续到杪秋,应无疑议。《左传·隐公九年》云“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注]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4页。蔡邕冒着踰月的淫雨在泥泞不堪的道路中前行必然是备尝辛苦。
美国学者康达维指出:“到蔡邕的时代,赋以及整个中国文学在时间、地点和个人观点表达上都有具体化的趋势”,并且“这种具体化的趋势是缓慢发展的,最初主要体现在赋体文学中。而在赋的范围内,这种具体化的绝佳例子则是早期的纪行赋”。[注]David R. Knechtges, “Poetic Travelogue in the Han Fu,” in Proceedings of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89, pp.127-152.趋向具体、写实不惟显现在时间、地点和个人观点方面,天气细节的加入意味着纪行的要素赅备,这也是文学具体化落实的标志之一。
其次,这些恶劣天气的描画超出了单纯的天气记实,进而在隐喻上自成体系。这套体系主要渊源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三种感应:一是人的内心与外界事物的感应;二是天人的感应;三是自然界诸现象的感应。[注]小林正美:《六朝佛教思想研究》,王皓月译,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第22页。
第一种是围绕恶劣天气与个人情感的感应。中国古代文论家历来对天气不甚属意,好在他们对与天气攸关的气候、物候施加于文学的作用还是有所发覆。刘勰《文心雕龙》之《诠赋》篇“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之谓,[注]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二,第304页。已模糊地揭示出“心物交融”的主客互动肌理。其《物色》篇又曰: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注]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一○,第1728-1732页。
秋冬、春夏的气候特点一者使人忧戚,一者使人舒快。此般因物兴感、由感生情、由情见辞的文学生产机制也就应运而生。这亦与钟嵘《诗品》序言中“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的所见略同,[注]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5-20页。都体认到有一个从外在的四季风物、内在的情感刺激再蜕变为文学投射的生发途径。天气本身并没有喜怒哀乐,因人而沾染了纷繁的情感。进入到汉代纪行赋中,耐人寻味的是恶劣天气的出现无一例外地都被安置在行程的最后一站。天气的每况愈下皆对应、预示着情感酝酿的喷薄而出,最终倍添忻戚的抒情效果。
在《遂初赋》抵达五原前的临沃之际,忽然风云突变,河岳异彩。刘歆顿觉满目荒凉和过耳凄厉,前瞻路途漫漫,回眸去国遥远,不由思归怀乡,黯然神伤,在艺术上“颇能收到情景交融的效果”。[注]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8页。
在《北征赋》临近结尾处,班彪在安定附近的高平勒马徐行是整个行程的高潮,当他置身于冰天雪窖、风起云布的高原,残酷的天气景况推动了“进入客观性的‘情感蔓延’”,[注]顾彬:《中国文人的自然观》,马树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0页。为后面放弃冷静克制的姿态并迸发“哀生民之多故”和“嗟久失其平度”的浩叹埋下铺垫,哀景悲情从而若合符契。
在《述行赋》中,雨霾风障、雾沉云暝的天气几乎覆盖了全程。蔡邕起程离陈留、中途过河洛、末了临偃师,天气波动递次剧烈,情感脉络随之由弱至强,以至终于忍无可忍,愤然折返(“爰结踪而回轨兮,复邦族以自绥”)。在随后卒章显志的乱辞中,他援引《小雅·正月》的诗句(“终其永怀,窘阴雨兮”)回顾这一路走来栉风沐雨、涉历险阻,不过远行中断、功亏一篑反而正中其下怀(“言旋言复,我心胥兮”)。
第二种是围绕恶劣天气与黑暗政治的感应。自然气候与政治气候同步的理论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深察名号》、《阴阳义》等篇提出“天人合一”概念之前就初露端倪。先秦典籍《吕氏春秋》中已经对此言之綦详,其《应同》篇曰:
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澡。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注]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卷一三《应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83页。
这段话力图赋予物与物、物与人同类感召的理论基础。《吕氏春秋》又引而伸之曰:“《商箴》云:‘天降灾布祥,并有其职’,以言祸福人或召之也。”以天象为媒介,“天人感应”表现在上天降灾布祥,对人世惩恶扬善。此类观念时至东汉依然有顽强的生命力。安帝朝仆射陈忠针对时下霖雨积时,宦官伯荣又恃宠而骄的局势上疏曰:“臣闻《洪范》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肃,貌伤则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为君上威仪不穆,临莅不严,臣下轻慢,贵倖擅权,阴气盛强,阳不能禁,故为淫雨。”[注]《后汉书》卷四六《陈郭列传》,第6册,第1562页。他阐释雨患所援据的是西汉鸿儒夏侯始昌的《洪范五行传》,其实质又本自《尚书·洪范》对各种征兆的穿凿附会,即阴、晴、暑、寒、风之移变消长皆有定式,任何一种过甚或不及都属恶兆,而恶兆之一即君王狂妄,久雨不止。[注]《尚书·洪范》曰:“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咎征:曰狂,恒雨若。”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86-1187页。刘歆和其父刘向都曾就《洪范五行传》阐扬过天人之际的论说。[注]《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152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及外戚间关系的约31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39条。《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73条,尽管论述的对象不出其父前著范畴,但在接受天命的前提下承认天命会多少以人力为转移。在汉代纪行赋中,天道休咎与人君美恶关联模式也多有阐述。
《遂初赋》序称:
……歆好《左氏春秋》,欲立于学官。时诸儒不听,歆乃移书太常博士,责让深切,为朝廷大臣非疾。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徒五原太守。是时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论议见排摈,志意不得。之官,经历故晋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征事而寄己意。[注]章樵注:《古文苑》卷二,第11页a-b。
序言大多复述了《汉书·楚元王传》的原文,[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67页。显然非刘歆亲笔所写,但也明了地道出了此赋构撰的来龙去脉和题旨语境。起因在于刘歆好《左传》并欲将其列入汉代学官框架内,触怒了儒官耆旧而被排挤出朝。又因其皇室宗亲身份循制不宜担任河内、河东、河南三郡太守,故从出守河内一职迁任五原太守。恰是这次北徙过程,让他在路过晋国故地期间触目伤怀,因而以“感今思古”为展现形式,且以“寄征事叹己意”作结撰目的。后文紧接着一段关于日月星辰分布运行的话语,字里行间蕴藏了影射现实的大量信息,如:“惟太阶之侈阔兮,机衡为之难运。惧魁杓之前后兮,遂隆集于河滨。”[注]章樵注:《古文苑》卷二,第11页a-b。“太阶”为“三台”上下各附的两颗星,[注]上台、中台、下台各二星,相比而斜上,如阶级然,故名。扬雄《长杨赋》曰:“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也。”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九《畋猎下》,第407页。李善注左思《三都赋》引《皇帝泰阶六符经》曰:“泰阶者,天之三阶也。上阶,上星为天子,下星为女主。中阶,上星为诸侯三公,下星为卿大夫。下阶,上星为元士,下星为庶人。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岁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谓太平。”见《文选》卷六《京都下》,第288页。“机、衡”为北斗七星之中的第三、第五颗,“魁、杓”为北斗七星之中的第一至第四、第五至第七颗,它们的紊乱无序或变动不居也隐示了宇宙枢纽对应的中央朝政的失其常道,也即哀帝时期三公专擅威柄、凶恣日积的时弊。全赋在类似政治隐喻的掩饰下诉说着国是日非、世道弥艰的苦衷。仅有一处直陈时政道:“空下时而矔世兮,自命己之取患。”[注]章樵注:《古文苑》卷二,第13页a。作者在奔走间隙转视当下,嗟怨时乖命蹇。接下来行经临沃,时值天寒地冻,雪虐风饕,更在其心头平添了阴影。康达维认为刘歆把北上五原的行程呈示得如此艰难是有暗示自己一波三折的仕途之现实用意的。[注]David R. Knechtges, “Poetic Travelogue in the Han Fu”, pp.127-152.跃然纸上的“非常”的天文景观和气象景观,正是因为产生于非常时期,也就有了充作喻体的合理性。体验了异乎寻常的天气后,作者强作宽解道:“运四时而览阴阳兮,总万物之珍怪。虽穷天地之极变兮,曾何足乎留意。”[注]章樵注:《古文苑》卷二,第14页a。表面上泰然处之,其实正话反说,正透露了他对天人失调的无奈。其愤激之意,情见乎辞。
复举另外两篇作品为例。《北征赋》开篇曰:“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阨灾。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九《纪行上》,第426页。班彪以前路窒塞来暗喻世道壅闭。《后汉书·班彪列传》载:“年二十余,更始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注]《后汉书》卷四○上《班彪列传》,第5册,第1323页。受天下板荡、地方割据的时势所迫,班彪踏上颠沛流离之路。旅途之初,他矛盾地设问:“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九《纪行上》,第426页。旅途之末,他又纠结地自问:“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愬?”[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九《纪行上》,第430页。前后两次他都将沦落天涯的处境归咎于时运不济,却始终维护天命的恒常。但是如影随形的玄云蓊郁、沉阴杳冥的天气,分明凸显了天人皆已失常。唐代吕向在《文选》注里切中要害地指陈道:“言阴曀不见阳景,喻天下昏乱,无明君之道,使失和平之法度。”此与李善的“阴曀,喻昏乱也”的注解不谋而合,[注]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九《纪行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84页下。都析出了惨栗天气中隐晦的政治寓意和现实指涉。
蔡邕《述行赋》中天气之差、行路之难,和时局之乱互为因果,这从其序即显而易见: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郡守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注]蔡邕著,林纾选评:《蔡中郎集》,第52-53页。
时局之乱一则是自矜功伐、飞扬跋扈的外戚梁冀先被徐璜、左悺为首的五个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宦官集团合谋翦除;[注]《后汉书》卷三四《梁统列传》,第5册,第1185-1186页;卷七八《宦官列传》,第9册,第2520页。二则是桓帝为大兴显阳苑而致民不聊生、饿殍横野,白马令李云为此坐直谏诛,[注]《后汉书》卷五七《李云传》,第7册,第1851-1852页。大鸿胪陈蕃也因谏诤获罪。[注]《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第8册,第2161页。此时蔡邕却被宦官强征赴都唤作倡优之用。天气之差与行路之难一是因霖雨逾月;二是因疲病交侵。其后他自述感怀触绪、长歌当哭的缘由,其中“聊弘虑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属词”一句中的“幽情”,源自身世浮沉和天气纷扰两个层面。当他接近走完赴都之旅时,想起权贵、宦官们永无止境的贪腐和傲慢便疾首蹙额起来:
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并集。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駸急。怀伊吕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入。唐虞眇其既远兮,常俗生于积习。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淴。[注]蔡邕著,林纾选评:《蔡中郎集》,第54页。
作者蒿目时艰,大失所望(“观风俗之得失兮,犹纷掌其多违”),遂托病不就。诚如康达维所说:“笼罩他的黑暗并不止缘自坏天气,也象征了那时恶劣的政治气候。”[注]Kang-i Sun, Stephen Owe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vol.1, p.157.蔡邕一上路就举步维艰的深层原因浮出水面,归根结底非惟天灾,亦由人祸。天气的恶劣与政局的恶劣高度重合,促使这篇作品对个人情感的敷陈和对社会政治的怨刺最为激进。[注]Mark Laurent Asselin, A Significant Season: Cai Yong (ca. 133-192) and His Contemporaries, New Haven, Con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10, p.56.
第三种是围绕恶劣天气与自然万象的感应。这主要导源于异类相应的思维。《召南·草虫》云“喓喓草虫,趋趋阜螽”,郑玄笺:“草虫鸣,则阜螽跳跃而从之,异类同类。”[注]毛亨传,郑玄笺:《毛诗》,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汉魏古注十三经附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册,第6页上。初步把握到了不同事物依存相适的原理。南朝梁刘孝标《广绝交论》又言:“客曰:‘夫草虫鸣则阜螽跃,雕虎啸而清风起。故絪缊相感,雾涌云蒸;嘤鸣相召,星流电激。’”李善注曰:“元气相感,雾涌云蒸以相应;鸟鸣相召,星流电激以相从。言感应之远也。”[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五五《论五》,第2365-2366页。李善承认这类感应普遍存在,同时以为天地阴阳之气才是其根本动力。
汉代纪行赋里的天气景象也为自然界的这一表象作了注脚。《遂初赋》中,沙埃、回风、封冻、漂冰、暗流、雪霜、雹霰等天光地景共同营力;鹍鸡、胡雁、野鹳等飞禽走兽对举见意,总之刘歆经目过耳的鄂尔多斯草原是风激电骇、飞沙走石、霜雪盈路、鸟兽哀号之地。《北征赋》中,班彪被怒号的狂风、高翻的激浪、杳杳的云雾、皑皑的积雪所围困,也被啼鸣的大雁、啁哳的鹍鸡所萦绕。《述行赋》中,彤云密布、大雨如注、山风飙涌、寒气逼人的多种气象纷至沓来,与仆夫憔悴、马匹玄黄的诸般回应构成了交集。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谓“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顷灭没,而诗人能结之不散。”[注]黄宗羲:《景州诗集序》,载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册,第15页。汉代纪行赋中的诗化表述不排除夸张、想象、虚拟的艺术成分,但作者抓住了瞬息万变的天气下自然万物的生命律动和相互感知的片刻。
四、余 论
汉代纪行赋中,除去班彪的《冀州赋》(《艺文类聚》卷二八作《游居赋》)因残佚严重而难窥全貌,故暂搁置不论,[注]另有学者认为冯衍的《显志赋》(《初学记》卷六又题为《明志赋》)亦属纪行赋,然其虽夹杂纪行片段,其实无论在内容还是篇幅上,述志才是全赋重心所在,故当划归述志类为宜。《艺文类聚》就将此赋收入“言志”门类中。日本学者中岛千秋将此赋纳入“贤人失志之赋”的系谱中也是言之成理的。见中岛千秋:《賦の成立と展開》,松山:关宏成,1963年,第469-502页。仅有一篇作品不具前述共性,而这则特例恰好证明纪行赋中恶劣天气的表达需要在一定的自然和人文的前提下方可成立。这篇作品即班昭(?-120)的《东征赋》。[注]赋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九《纪行上》,第432-436页。从赋文可知,班昭所述从偃师到荥阳的一段路线与蔡邕《述行赋》中的行止大抵是重迭的,差别惟二人行进方向东西相反而已。为何班昭赋中全然不见风雨晦暝、霜雪迷漫等恶劣天气的踪影?抛开班昭温柔敦厚的自身气质和步趋父业的写作动机(乱曰:“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等因素,[注]此与班彪追模刘歆《遂初赋》主要是出于文学传统上承继的动机要另当别论。李善在注《文选》时提醒读者,《北征赋》其中一些语句是从《遂初赋》衍化而来,从而见得后者影响的铁证。如“涉长路之绵绵兮”对“路脩远而绵绵”、“为强秦乎筑怨”对“剧强秦之暴虐兮”、“迥千里而无家”对“迥百里而无家”、“涉积雪之皑皑”对“漂积雪之皑皑”。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九《纪行上》,第428-429页。还要从其时的天气情形和政治生态说起。赋文起首即云:“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时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九《纪行上》,第432页。永初七年(113)班昭此行的活动区域在今见史料中查无灾害性天气的记载,而在孟春时分择良辰吉日出行,自无风霜雨雪之虞。此外,班昭彼时身处汉安帝朝。安帝虽平庸无为,历史评价不高,但在永初年间,邓太后摄政,朝野差可“内外扶持,无大变故”。[注]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3页。当此之时,班昭陪同儿子东征就任陈留长,[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九《纪行上》注引《大家集》,第432页。并无迫不得已的外界压力。在这两重背景下,《东征赋》对语言的组织和材料的选取明显有别于创作于秋冬季节的衰世(如《遂初》《述行》二赋)和乱世(如《北征赋》)同类作品,[注]李炳海:《汉代文学的情理世界》,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7页。纪行赋中惯用的恶劣天气的描绘与隐喻了不可见,取而代之的是与盎然春意相辉映的、关乎嘉言善行的命辞遣意。[注]孙晶:《汉代辞赋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68页。
括而言之,天气在中国文学中的表达经过了从浮泛抽象到真切具体的漫长演进轨迹,而纪行赋在两汉为其提供了绝佳的书写载体。这些赋作的独到之处是在空间的转换、时间的推移中借助对恶劣天气势态状貌的直接、浓烈、形象的图绘摹写,使贯穿通篇的情感主线也与天色跌宕起伏。非躬亲行旅、身历其境者,不能言之历历如绘如是。风霜雨雪、阴晴晦明被编织进纪行的文本,在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首先,旅程沿线暂付阙如的某些历史时期的气象讯息得以丰富饱满;其次,天气表述不止停留字面的史实,还进入到隐喻的阐释系统中:第一,天气绝非依附在叙述骨干上无关宏旨的例行备录,而是赋客心情的晴雨表。往往在路程的最后一站,天气愈加变得令人不可捉摸、望而却步,行人的忧伤情绪不断地被强化、放大。第二,天气波动和世途坎坷曲尽其妙地联结到了一起,诡谲的天象世界不啻是复杂的人间政治环境之写照。第三,天气映现了气象与万象的交互影响。大自然中,诸种气象之间、气象与生物之间彼此牵动。是故,纪行赋中的天气表达将“天气——心情”、“天气——时局”和“天气——万象”三组隐喻关系熔于一炉。在这两层意义上,天气表达的“实化”和“诗化”互相成就了对方,汉代纪行赋亦可谓是历史性和文学性的合璧。是知风霜雨雪,实文思之奥府;纪行述志,抑亦天气之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