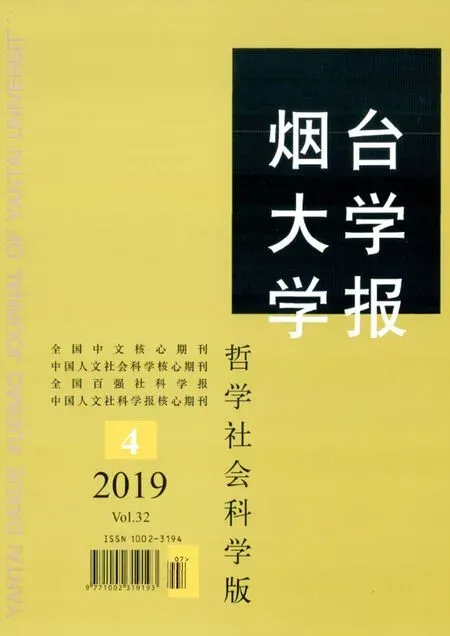显现之维
——对“文”范畴的考察
李光柱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引 言
在儒家文化体系中,“文”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也是一种人格理想,同时也是一套完整的文化理想。比如,《论语·八佾》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5页。《论语·公冶长》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8页。,《礼记·檀弓下》有“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8页。《论语·子张》甚至有“小人之文”:“小人之过也必文”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6页。。子贡也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9页。探究“文”的含义对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逸周书·谥法解》关于“文”列举了以下内容:“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78页。《国语·周语下》有“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注]韦昭:《国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3页。诸多文献以类似的方式罗列了“文”所要求的各种德行,后人在此基础上又不断增益,但以例证或枚举法只能无限切近,却无法到达“文”的真正含义。因此,有必要以哲学的方法对“文何以为文”做出考察。
一、《论语》中的“文”“质”之辨
《论语·颜渊》有卫国大夫棘子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关于这段对话的语境,《论语正义》认为:“夫子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棘子成或闻其语,妄以君子但当尚质,不必用文。”[注]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93页。朱熹《论语集注》认为:“夫棘子成矫当时之弊,固失之过;而子贡矫子成之弊,又无本末轻重之差,胥失之矣。”[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28页。《论语正义》又认为:“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是文、质皆所宜用,其轻重等也。”[注]刘宝楠:《论语正义》,第493页。但文与质谁轻谁重似乎并非本段谈话的要点,子贡解释的其实是文的功能问题,并且潜在地否定了将二者在同一语义层面横向对比的可行性。子贡认为,文是使质得以显现的东西。倘若文不能使质得以显现,则虎豹之皮与犬羊之皮无法区分。虎豹之皮与犬羊之皮各自凭借纹理得到显现。这里强调的不是虎豹、犬羊谁贵谁贱,而是各自的“显现”—— “文”就是“显现”,而“显现”是产生秩序的前提。因此,这里的“文”首先是一种存在论,而不是价值论,这里不妨借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它指向的是“存在者之存在”。“文”由此就具有了接近“现象学”的意味:“凡是如存在者就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展示存在者,我们都称之为现象学。”[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1页。“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2页。而具体到君子“何以文为”而言,就是一种对“此在”(人/君子)这一特殊的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规定。这应该看作中国古代哲学以“君子论”形态呈现的“人本主义”哲学。
《雍也》篇提出“文质彬彬”。“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彬彬”,《论语正义》解作“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强调 “用中”之意。[注]刘宝楠:《论语正义》,第333页。朱熹解作“犹班班,物相杂而均适之貌”,亦是用中之意,又引杨时观点“然则与其史也,宁野”,有扬“质”抑“文”之意,与其在《颜渊》篇中的解释一致。[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6页。而事实上,倘若以“文”的功能观之,从这里所营造的“文”与“质”的张力感来看,“彬彬”在此处更宜解作一种动态的规定:“文”与“质”始终共时态存在,并且,“文”总是保持为对“质”的本真呈现。这就揭示了作为“此在”的“君子”对自己存在状态的领会,也即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对自身的“存在之领会”(生存)问题:“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的规定。”[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4页。
作为君子理想人格的“文”,聚焦于君子对于自身存在状态的领会和理想状态的实现,并且扩及自身与天地万物(存在者)的关系,这在《易经》中得到最生动的表达。《易传·文言传》以象取譬:“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这是“文明”一词较早的出处。《文言传》认为“乾”道代表了君子四德:元、亨、利、贞。“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可以说,“乾”对应的正是君子理想人格中“文”的维度:而“坤”则对应“质”的维度:“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
二、《国语》中的山川之守
《国语·鲁语下》中有《孔丘论大骨》篇,记载了一段精彩的外交言辞。吴王夫差伐越获得一节很大的骨头,之后,吴王派使者来与鲁国重修旧好。夫差让使者向孔子请教大骨的来历,并叮嘱使者不要告诉孔子这是他要问的。但孔子直言不讳,对使者说,这是“防风氏”的骨头:“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使者又追问什么是“神”,孔子说:“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使者又问防风氏所守为何,孔子说:“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在这段言辞中,孔子以渊博的知识,借题发挥,揭示了鲁国、吴国的政治渊源,重申了古老的政治传统。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以一种“转喻”策略将“山川”与“社稷”并置,点明了先王传统对“王”的规定:山川之守。
孔子的这一言辞对应于前《展禽论祭爰居非政之宜》篇。展禽对作为先王传统的“山川之守”阐述得更加系统全面:
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注]韦昭:《国语注》,第74页。
如果说,王的责任是守护山川,那么我们就能够更直观地理解包括《国语》在内的典籍中频繁出现的有关山川崩坏的言辞,以《周语》为例,在《邵公谏厉王弭谤》篇中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注]韦昭:《国语注》,第5页。;在《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中有“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注]韦昭:《国语注》,第45页。;在《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篇中有:“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污也,其竭也无日矣。”[注]韦昭:《国语注》,第52页。诸如此类,其他诸《语》中也不胜枚举。这些言辞强调的是一种疏通和敞开的品格以及对壅塞封闭的警惕,语带虔敬,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并非实然只是譬喻。
《文心雕龙》对“文”的精神与“山川”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释。上文提到的《逸周书·谥法解》中所说的“经纬天地曰文”应属于一种共相的定义,而其后的枚举则属于殊相,似乎所有美好的德行都可以纳入“文”的范畴。刘勰关于“文”的论述真正逻辑清晰地阐明了“山川”与“人文”在何种维度上是可以统一的。《原道》开篇说: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地理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注]张国庆、涂光社:《〈文心雕龙〉集校、集释、直译》(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页。
刘勰在这里指认了三个层次的“文”:自然之文、言之文、道之文,它们统一于“文德”,而所谓“文德”就是天地万物各自文理的显现。
海德格尔曾辨析希腊语“逻各斯”(“话语”,希腊语:λγοδ)的含义,认为逻各斯是“有所展示的话语”:“λγοδ的‘真在’亦即αληθευειν说的是:在λεγειυ(说)这种αποφαιυεσθαι(有所展示)中,把话题所及的存在者从其掩蔽状态中拿出来,让人把它当作去除掩蔽的(αληθεζ)东西来看,也就是说,揭示话题所及的存在者。”[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9页。正是在一种类似“逻各斯”的意义上,刘勰对“文”的论述才跃迁至道的层面,在显现和去蔽的意义上将一种宇宙论与伦理学统一起来。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海德格尔提出“大地”与“世界”对举,作为存在的遮蔽之维与显现之维。它们之间的“争执”也就是真理的发生。海氏说:“大地是一切涌现者返身隐匿之所,并且是作为这样一种把一切涌现者返身隐匿起来的涌现。”[注]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4页。“确立一个世界和建立一个大地,乃是作品之作品存在的两个基本特征。”[注]海德格尔:《林中路》,第29页。“世界建基于大地之上,大地穿过世界而涌现出来。”[注]海德格尔:《林中路》,第30页。“世界立身于大地,在这种立身中,世界试图超升于大地,世界不能容忍任何锁闭,因为它是自行公开的东西。但大地是庇护者,它总是倾向于把世界摄入它自身并扣留在它自身之中。”[注]海德格尔:《林中路》,第30页。海德格尔在文中是以自然物——器具——艺术为真理生成的线索。[注]陈聪:《器具如何作为艺术作品——兼论海德格尔与杜尚的比较》,《艺术探索》2007第2期。而在刘勰那里,以一种更加广义的“创作论”范式,日月星辰、山川鸟兽等自然之文,对于创作者(人)及他所创作的一切而言也就成为“大地”,也即存在的遮蔽之维;人为天地之心,以言立文,照亮万物,乃是 “大地”—“世界”之建立,也即存在的显现之维;而“道”之文就是存在的澄明状态,也就是真理的“生发”(Geschehnis),被置于天地这一宏大“艺术品”之中。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有“世界之肉”的提法。“肉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不是实体”[注]杨大春:《从“形象整体”到“世界之肉”——梅洛-庞蒂对柏格森自然观的创造性读解与借鉴》,《哲学研究》2008年第12期。,它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存在,人的身体和语言意识都是世界之肉演化的产物,而“世界环绕着我,而不是面对着我”[注]张文初:《将身体借给世界——读梅洛-庞蒂〈眼与心〉》,《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5期。,世界是经验和知觉的对象,而不是认识和观察的对象,“我们作为自然人置身于自身和事物之中,置身于自身和他人之中,以至于通过某种交织,我们变成了他人,我们变成了世界。”这种描述与刘勰对“文”的论述十分契合。在“肉”的意义上,人与世界万物是统一的。因此,“文”同时意味着一种认识和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哲学。人的活动乃是“世界之肉”的演化、生成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的交往同时也是自然的一种自我显现。人并不是超绝孤立的主体,因此人的活动尺度不能偏离其内在自然的尺度,否则就会使自然陷入壅塞和封闭的状态。以此返观“山川之守”,它强调的正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共同实现。
三、《尚书》中的光明崇拜
在先秦政治哲学话语中,“文”的显现表现为“德”。《尚书》中有“明德”的提法。有历史学者认为,殷商与周王朝关于“德”的观念是迥然不同的。殷商所谓的德是垄断性的、封闭的,在殷商的血亲—巫术共同体之外,人兽无别,皆是猎物。为了对抗殷商毫无人道的德性狩猎战争,周人在西方提出了一套新的德性法则(“明德”),打破了殷商王族对天命德性的封闭垄断经营,将殷商血亲之外的世界纳入了德性秩序,构建了一个开放性的封建体系。[注]刘仲敬:《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页。从诸如《西伯戡黎》、《微子》之类的《商书》篇章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商王朝末期统治者关于独享天命的话语,然而这到底是传统抑或只是王朝末期的特殊情况,似乎还缺乏充分的证据。但是从一些文本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出周人对“明德”在现实政治中的功能的强调,如《梓材》篇有“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注]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83页。。
需要注意的是,周人的“明德”观念乃是以一种“光明崇拜”方式得到表达的。《泰誓》篇有:“呜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四土。”[注]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第202页。《洛诰》中,周成王对周公说:“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注]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第300页。,周公不敢居功,答谢道:“王命予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注]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第302页。《君奭》篇中,周公对召公说:“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注]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第321页。“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注]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第329页。《顾命》篇中,周成王说:“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注]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第371页成王逝世,太史对即位的康王说:“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汝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注]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第376-377页。周平王时有《文侯之命》,追溯先王事迹曰:“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闻在下;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注]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第412页。
作为一种普遍观念的光明崇拜可能是十分古老的,姜昆武在《光明崇拜及其在封建政治中的遗痕与作用》一文中对此作了系统的考察。[注]姜昆武:《光明崇拜及其在封建政治中的遗痕与作用》,《浙江学刊》1988年第5期。我们这里关注的问题是:光明崇拜如何在特定的政治事务中得到表达并从中诞生一种政治哲学。周人明德观念的强化可能与周王朝“受命于天”的神话有关。在这个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神话中,“天命”是以一个壮观的天象明确地显示出来的。《竹书纪年·帝辛》云:“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有赤乌集于周社。”[注]张玉春:《〈竹书纪年〉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7页。《墨子·非攻下》云:“赤鸟衔圭,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注]孙诒让:《墨子闲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51-152页。《吕氏春秋·应同》云:“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注]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9页。美国学者班大为认为,这描述的实际上是发生于公元前1059年5月底的一次五大行星会聚的天文现象:
木星、土星和火星三星在巨蟹座(即舆鬼)聚会,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加入了水星和金星……这一切发生在距离太阳足够远(21°或更远的地方),在西安所在的纬度五月末至少十四天的时间里,日落后一小时左右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若干天里,五星聚一定压过了它周围的任何天象,特别是在巨蟹座这群不明亮的恒星背景上(+4度或更暗)。[注]班大为:《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徐凤先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大赤乌降于岐山时口中衔的作为王权象征的玉或叫圭无疑是指当晚五星形成的像刀片一样斜挂的形状……这就是展示给文王的著名的洛书……敦促他去夺取王位。我们不敢肯定在商代的星占学中这一块特殊的天区是否已经与周人联系起来。然而我们能够肯定,从这时开始,不仅是被称作鹑火的这块天区,而且还有红色、夏季、上升的太阳一定被与周民族的崛起紧密联系起来。[注]班大为:《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第28页。
在我看来,同样值得提出的是,我们认识到了关于天命以及包括凤凰在内的神灵显现的传统——这些观念所蕴含的“皇天可鉴”的思想对于商周期间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心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很可能起源于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天象。[注]班大为:《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第59页。
在班氏的描述里,周王朝克商的漫长过程是与天象的运行保持高度一致的。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从这种对天命合法性的事件性关注中如何诞生了一种政治哲学。比如,《史记·周本纪》描述了周武王盟津退兵的一次“意外事件”:
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注]司马迁:《史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天象在当时可能是无法预料的,即便如此,诸侯的意志并未动摇。然而关键在于,武王选择遵循天象的指示退兵。这一决定无疑冷却了八百诸侯冲决一切、改天换地的激情。由此,伐商行动不再是一次渎神行动。这暗示了一种政治哲学理念。
在《北极简史:附“帝”字的起源》一文中,班氏考察了商周至上神“帝”的宇宙论起源,认为“帝”字是起自殷商时代对北天极区域一种特定星象的象形化,实际上是一种定向方法,关系到商周王朝如何确定正北方向以使政治事物在根本上与北天极保持一致,后来成为了对至上神的称呼。[注]班大为:《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第349-356页。然而,在周人那里,我们看到了一次与至上神的谈判。在《金縢》中,现实世界的君王被认为必须舍弃他对现实政治的责任而去侍奉上帝。这涉及到对“王何以为王”这一关键问题的裁决。而周公却借助“王有疾”的这个关键时刻,通过一个仪式,费尽心思地借助“三王”之灵与至上神“帝”达成了一个“新约”,从而确立起一种现世的政治哲学:“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注]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第238页。
上面《尚书》引文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周公与成王、周公与召公的对话中,周公不敢将这种“光明崇拜”用在自己身上,他认为自己只是传递光明的一个中介,从而确立了“先王”与“光明”之间的专属联系。夏含夷曾在《周公居东新说——兼论〈召诰〉、〈君奭〉著作背景和意旨》一文中提问:为何周公的名字极少见于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典籍中?夏含夷给出的解释是:周公与召公的政治分歧导致周公的隐退和式微。[注]夏含夷:《古史异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06-319页。然而,从上文我们征引的对话内容来看,周公主观上试图将所有的政治成绩都归功于文王、武王的明德,这样做的客观后果就是削弱了周公自己的存在感。因此,在一个“光明崇拜”的政治氛围中,周公之名或许并非被人为地抹去了,而是自然而然地消失在了先王的光明之中。作为光明的介质,他消失得越彻底,就越能证明明德的炽盛,也就越能证明他自己的透明无瑕。同样地,唯有当先王明德的火光衰弱的时刻,才能再次显现出周公的身影。而《国语》开篇讲的是“穆王将征犬戎”,正是这样的一个时刻。
于是我们看到,祭公谋父马上提到了“周文公之《颂》”(《周颂·时迈》):“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然后详细追忆了先王传统:“……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欢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注]韦昭:《国语注》,第1页。徐元诰《国语集解》认为应作“至于文王、武王”,理由是“周人叙述祖德,未有称武王而不及文王者”,并认为自“商王帝辛”以下才是专言武王事迹,并以后来的《史记》文本作为印证。[注]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页。而事实上,考虑到祭公谋父这段发言的目的是为了规劝周穆王的军事行动,周武王事迹应当处于发言的落脚点位置,这点应是没有疑问的,至于应从何处开始叙述武王事迹,以及是否一定要“文王、武王”并称甚或先称文王后称武王,没有确实的证据实在无法断言。本文更倾向忠实于所见文本,将祭公谋父此处的单称武王看作是他言辞策略的一部分:祭公谋父实际上在这里刻意调节了透镜的焦距,把光源的焦点落在了以“武”著称的周武王那里。而这一略显突兀的言辞策略也恰恰证明了光明的衰弱。个中意味,正如《论语·八佾》中孔子说“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并非真的是说《武》本身“未尽善”——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在鲁观《武》舞时就说“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所谓“尽善”与“未尽善”,要看是追溯往昔还是指涉现实,是为发言者的言辞策略服务的。再比如,在《史记·乐书》(又见《礼记·乐记》)中,关于《武》舞的演出程序在一开始“备戒之久”的问题,孔子就给出了一种“尽美又尽善”的解读。周大夫宾牟贾与孔子一起观看《武》的歌舞表演,在一番印证之后,宾牟贾问孔子:“夫《武》之备戒之久矣,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注]司马迁:《史记》,第408页。于是,孔子追述先王事迹,为这种节奏上的延宕填充—缝合上了丰富的伦理意义(“周道四达,礼乐交通”),从而将乐舞中美与善两个维度的张力化解于无形。而祭公谋父的言辞策略与孔子恰恰相反,其目的是为了凸显两个维度的张力,正如当孔子在另一个时刻说“未尽善”的时候指涉的乃是现实政治伦理维度的缺失。就指涉现实而言,正是光明的衰弱导致美与善的分离,而随着美—善张力的重新凸显,现实政治的伦理维度才重新得到关注。
因此,在现实政治中,对光明的崇拜事实上已经演化成为一种伦理维度的政治关切,因而是一种政治的再生产。于是我们看到,在周幽王的浩劫即将到来之前,《国语》将这个“光明崇拜”的神话转移到了南方的楚国。在《史伯为桓公论兴衰》篇中,史伯称赞楚国的祖先祝融“天明地德,光照四海”,“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注]韦昭:《国语注》,第240页。从楚国后来的发展史来看,当中原诸侯纷纷摒弃周王朝的礼法的时候,楚国却开始大力吸收中原制度,从而造成了历史的错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国语》会在后半部分将楚国事迹纳入周礼的话语范式加以叙述。但在它们(《楚语》以及《吴语》、《越语》)的差异性中,我们也注意到先秦政治哲人试图再建一种开放性的政治话语的努力。
四、“文”与“恭”
相较于《尚书》文本的“文”,《国语》通篇贯穿了一个“恭”的理念。“文”与“恭”恰如本体和它的投影,勾勒出当时政治哲人所追求的理想的轮廓,指引人们努力在晦暗的现实中搜寻光明的碎片。
由于《国语》的起始语境是承《尚书》而下的,所以作为《国语》核心理念的“恭”在《周语》起始部分就得到了显著的提示。《周语上》这样叙述周宣王伐鲁故事:
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王立戏。……鲁候归而卒。及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鲁,立孝公,诸侯从是而不睦。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樊穆仲曰:“鲁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对曰:“肃恭明神而敬事耈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王曰:“然则能训治其民矣。”乃命鲁孝公于夷宫。[注]徐元诰:《国语集解》,第22-23页。
这里作者在叙事完结之后又将周宣王立孝公的理由单独拿出来讲,似乎意在强调周宣王试图对自己的行为(废长立幼)做出补救,对照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方式可以看得更加显明:
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其君伯御,而问鲁公子能道顺诸侯者,以为鲁后。樊穆仲曰:“鲁懿公弟称,肃恭明神,敬事耈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固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宣王曰:“然,能训治其民矣。”乃立称于夷宫,是为孝公。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注]司马迁:《史记》,第481页。
然而这里存在叙事上的歧义:周宣王立孝公似乎不仅仅是为了安定鲁国,更是为了“导训(道顺)诸侯”,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司马迁的叙事顺序,周宣王的主观意图与其实际效果之间就形成了反讽。而《周语》则试图通过一种言辞策略促使我们超越反讽而去关注更有价值的部分:鲁侯之孝/恭。在樊穆仲或者《周语》作者看来,鲁侯之恭恰恰是周宣王所缺失的品德。“恭”(或“孝”)本质上是一种消极和保守的品德,然而面对先王传统的日渐崩溃,也只有“恭”能够守先待后。但是,如果始终没有一种积极的德行发挥作用,那么“恭”也终将难逃落入反讽之境的命运。于是我们看到,恰恰是在《鲁语》部分,对“恭”的阐释达到极致并终于落入反讽的境地。
陈桐生认为,《鲁语》文风大体与《周语》相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周、鲁拥有共同的政治资源——礼乐文化,并且敏锐地注意到《鲁语》在言辞的礼乐程度上甚于《周语》。[注]陈桐生:《〈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鲁语》一开篇就令人惊讶地看到了鲁庄公的“独恭”。在长勺之战前,曹刿指责鲁庄公临时抱佛脚,临战以赐,一身独恭,不务民本,而在曹刿的步步逼问下,鲁庄公最后谈到了“情”的问题:“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注]韦昭:《国语注》,第67页。《礼记·大学》中有类似的表述:“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并强调“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页。,所以“情”以“民”为本。“情”有四种含义:感情,情绪;爱情;实情、情况、情态;志向、意志。[注]《古汉语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3年,第748页。传统的解释在此处将“情”释为案件的实情,如朱熹认为:“圣人能使无实之人不敢尽其虚诞之辞”,“故讼不待听而自无也。”[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页。但这种解释存在问题。“情”在这里与“智”对举,指的不是客观意义上的“实情”,而是主体主观情感上的“真实”,也就是“真诚”。关于曹刿与鲁庄公的这一对话,《左传·庄公十年》记叙如下:“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注]李梦生:《左传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可见这里的“情”与“忠”的含义有关。《周语下》在《单襄公论晋周将得晋国》篇评价姬周(晋悼公)时有“言忠必及意”,韦昭注“出自心意为忠”,又说姬周“其行也文,……忠,文之实也”,[注]韦昭:《国语注》,第42页。可见所谓的“忠”也是指一种主体的品质。若一一考察“情”在《国语》全篇其他地方的用法,《晋语一》有“好其色,必授之情”,[注]韦昭:《国语注》,第121页。《晋语二》有“君子不去情”、“死不迁情”、“守情说父”,[注]韦昭:《国语注》,第132页。“偕出偕入难,聚居异情恶”,[注]韦昭:《国语注》,第135页。《晋语五》有“夫貌,情之华也”、“身为情,成于中”,[注]韦昭:《国语注》,第183页。《吴语》有“句践愿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无阿孤,孤将以举大事”。[注]韦昭:《国语注》,第289页。这几处的“情”都首先是指一种主体意义上的“真情实意”。这种解释也更符合鲁庄公与曹刿对话的逻辑:虽然不能凭借智慧断明每件案情,但主观情感上一定是为民着想。然而从《鲁语上》后文所叙述的关于鲁庄公的事迹来看,鲁庄公是个善于狡辩的角色,所以这里鲁庄公之谈“情”是可疑的。然而曹刿还是对之表示肯定,并以劝诫的语气补充了后面的内容:“是则可矣。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鲁语上》以包括鲁庄公在内的一系列类似的故事意在表明,所谓的“恭”、“孝”、“情”在鲁国政治中已经沦为一种言辞的游戏,尤其是臧文仲无底线的“言辞外交”,更是受到了展禽的直接批评:“若为小而崇,以怒大国,使加己乱,乱在前矣,辞其何益?”[注]韦昭:《国语注》,第71页。当“恭”仅仅表现为一种修辞策略的时候,也就变成了一种反讽。《鲁语下》则借一组对照性的文本直接嘲笑了鲁国政治中的“恭”。在《子服惠伯从季平子如晋》篇中,子服惠伯在与晋国的一次外交中展示了“恭”的最后尊严,[注]韦昭:《国语注》,第91页。然而到了子服惠伯之孙子服景伯那里,“恭”在现实中丧失了最后的尊严:“齐闾丘来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注]韦昭:《国语注》,第99页。子服景伯对“恭”的解释受到了闵马父的嘲笑。闵马父追述先王对“恭”的解释,并引周恭王、楚恭王事迹作为“恭”的底线,认为至少要过而能改才称得上“恭”,而有过失(“陷”)本身绝称不上“恭”。正是在这一反讽的笑声中,伴随着孔子的“金刚怒目”(《孔丘非难季康子以田赋》),《鲁语》结束了它的叙述,迎来了《齐语》以及其后的所谓“霸术”的时代。然而若就此放弃掉“恭”这条线索,那就会导致对“霸术”的严重误解。
《齐语》基本以管仲和齐桓公的对话贯穿全篇,但仍然存在一个基本的叙事框架,那就是齐桓公的流浪—归国故事,纵然这一故事框架要到《晋语》才完全展开,让我们看到了更加丰富的细节,得到了更加清晰线索。《齐语》与《晋语》主题统一性的证据出现在《晋语四》的齐姜言辞中。重耳适齐,在齐一年而桓公卒,诸侯叛齐,齐姜以“管仲之教”传授于重耳[注]韦昭:《国语注》,第155-156页。——管仲与重耳的隔空对话完成了主题的传递。正是在《晋语》中,通过公子申生故事和重耳的流浪—归国故事,一种全新的行动理念(“信仁”)被大张旗鼓地提出,并一扫“恭”的阴霾。
《晋语》始于对“曲沃代翼”的一个孤立场景的描述(《武公伐翼止栾共子无死》),[注]韦昭:《国语注》,第116页。这里同样点到了“恭”(共)。这样的开篇方式事实上终结了传统政治语境下无意义的争论,由此整个《晋语》故事直指那个根本性的问题:王何以为王。作为第一叙事单元的晋献公故事,以骊姬之谗和太子申生故事作为叙事主线。太子申生之死完美诠释了“恭”的现实处境:行动的无能。申生死后谥为“共君”(恭君),韦昭注曰:既过能改曰恭。这与《逸周书·谥法解》是一致的。但从太子申生死前的言辞来看,他并不为自己的死感到悔恨,而是呼吁有识之士能够有所行动。[注]韦昭:《国语注》,第133页。所以这里的“既过能改”并非仅仅局限于个人的品行。正是申生诉诸现实之“恭”启动了后面公子夷吾(晋惠公)和公子重耳(晋文公)的行动。
夷吾与重耳的行动准则完全是对立的。夷吾信奉的是“亡人无狷洁,狷洁不行”,而重耳信奉的是“亡人无亲,信仁以为亲”。[注]韦昭:《国语注》,第141页。在申生故事中,优施/骊姬曾经曲解和割裂“仁”的内涵,从而决定性地导致晋献公对申生的不信任:“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注]韦昭:《国语注》,第127页。而重耳的“信仁以为亲”则重新将“爱亲”与“利国”统一起来。《周语上》内史兴品评重耳时说:“仁所以行也”[注]韦昭:《国语注》,第19页。,《周语下》有“仁,文之爱也”[注]韦昭:《国语注》,第43页。,韦昭注曰:仁者,文之慈爱。而夷吾的“无狷洁”则注定他要失败。“无狷洁”恰恰意味着对“恭”的违背。而重耳则凭借信行仁道,最终实现了“文”的复返,成为晋文公。试对比《晋语四》的《文公称霸》篇[注]韦昭:《国语注》,第180页。与《鲁语上》的《曹刿论战》篇,行文何其相似,但却完全是另一种境界。
晋文公之“霸”最终实现的是对先王传统之“文”的复返。这一从“恭”到“文”的复返,拓展了先王传统的内涵,触及了某种根本性的政治哲学理念,从而表明了“文”并非纯然是一种精神化的世界理念,而是现实的自我实现。人格之“文”与政治之“文”统一于对“王”的现实规定,正如佩特森所言:“成为福人需要阳刚的、帝王般的德性。福祉并不意味着具体的事物、生活和美德都消融于涅槃,有福并不超越时空。相反,福祉是积极地占有某些东西,比如占有整个地土。”[注]佩特森:《面向终末的美德:罗马书讲疏》,谷裕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0页。
五、结语:文与自由
“山川之守”是先王传统的内容,“光明崇拜”是先王传统的形式。不断探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造就了“文”的政治理想。它的核心要义乃是一种关于存在的政治哲学,强调政治作为一种“显现之维”彰显了社会与自然共同实现的存在方式,彰显了人与天地万物作为存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乃是真、善、美的统一,是大光明境界,是一切存在者随着存在之维的不断拓展和交织而达到显现的历程。
“文”表现在个体身上,集中体现为一种自我实现的人格理想。《论语·子张》篇中,子夏说:“小人之过也必文”[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6页。,所谓“不贤者识其小者”[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9页。,“小人之文”未必是一件坏事——不至于像孟子说的“自暴自弃”[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63页。,仍然有向仁向义敞开的可能。而“君子之文”强调不断地内外兼修,旨在达到“诚”的境界。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更也人皆仰之。”[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78页。《礼记·大学》篇形容那种完全敞开的光明境界曰:“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页。正如在政治事务中明德的普照最终彰显天地万物的存在,“诚”也同样如此:“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达到极致,无可增益,由此实现所谓“诚于中,形于外”的境界。“诚”作为对本真性的规定,即是“文质彬彬”。
《礼记·中庸》篇更强调“诚”的外化:“诚者非自成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5页。这就将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伦理性地统一起来。所谓“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4页。,自我潜能的开发最终要达到至高的政治理想:天地万物价值的显现。因为人是天地万物的一员,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在存在论意义上是统一的,统一于真理的澄明,统一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即是马克思劳动实践论意义上的自由:“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2页。由此,“文”最终追求的是包括此在在内的所有存在者的真理得到显现的伦理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