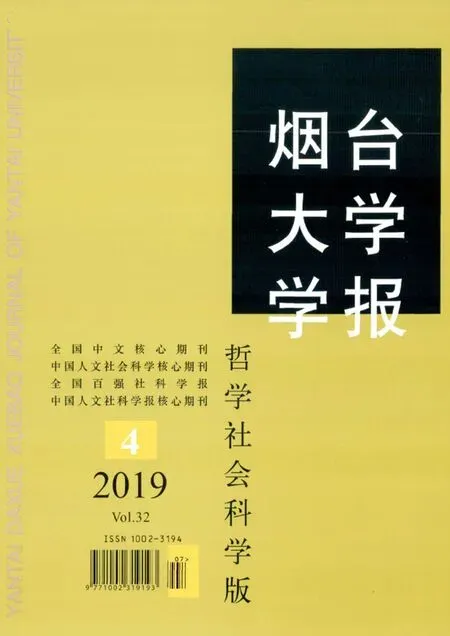论明代捐赈的“尚义”观念及其实践
向 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2488)
捐赈是历来荒政中筹集救济资源的重要方式,无论是来自民间的自发主动,还是出于官府的动员劝分,在备荒、赈济当中都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宋室南迁以后,劝募富民出钱粟的救荒之法,曾经从辅助性、补充性的措施发展为“官府赈灾不可或缺而备受依赖的主要措施”李华瑞:《北宋荒政的发展与变化》,《文史哲》2010年第6期。,其中“酬以官爵”、“赐以金币”等劝募形式在金元时期遵照循行,至有冗滥之讥。明朝前期以官仓发赈为主,“永乐之赈多出仓库之羡,宣德之赈间劝富民之财”钱薇:《赈济议》,《承启堂稿》卷十,《海石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62页。。自明宣宗以后,劝募民间捐赈的情况也逐渐增多,在吸取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劝捐形式——“旌义”,即对捐粮助赈的富民,依捐额高低,分别给予义民称号(敕书、建坊)、立石、表门等奖励,辅以羊酒慰劳、免除数年徭役的优待,景泰以后又增添了授以冠带、散衔等待遇。与前代相比,明朝劝分的成就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旌义”的形式,使劝募民众捐赈的财政行为同时具有了旌表“尚义”、表励风俗的道德奖劝意义。
自正统初年以来,迄万历时期,明朝捐赈产生的义民数额庞大,影响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府州县,但因为受到旌表的捐赈者多为庶民富室,在传统的史料如明实录、政典、文集方志等记载中常显得简短零散,给深入研究这一群体的政治心态及行为方式带来了诸多困难。旌义事例后期的变化中牵涉到授予散官,亦曾被笼统纳入广义的捐纳中讨论,但对于旌义作为政治决策,兼具怎样的道德内涵、反映了明代皇权政治的何种特点等问题,目前的研究尚付阙如。[注]主要研究成果:佐藤学梳理了旌表义民制度的创行情况,见《明代“义民”旌表制度考——创行期正统年间を为中心に》,《明代史研究》1985年第3期;赵克生指出旌表义民是一种道德奖劝,是明代劝分相比前代的特色,见《义民旌表:明代荒政中的奖劝之法》,《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伍跃将旌表义民纳入明代的捐纳研究中,认为成名的渴望是富民选择旌义的基本原因,见《关于明代捐纳制度的几点思考》,《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2-68页;陈业新研究了包括旌义在内的劝分方式在凤阳府的施行情况,见《明代国家的劝分政策与民间捐输——以凤阳府为对象》,《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方志远指出不同地区民众对明朝政府的“国家认同”程度影响了他们对待旌义的态度,见《“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间赈灾助饷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以上各位学者关于旌义的内涵及性质的重要讨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助益。近年来,随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不可移动文物的调查结果逐渐公布,明朝捐赈义民的家族牌坊、墓碑、族谱等新出资料积累渐多,为结合传统史料探讨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将江西新发现的义民族谱、碑刻资料与实录、方志、文集中的记载相互补充印证,尝试以江西、南直隶、浙江、福建等地的义民个案为基础,分析明代捐赈中“尚义”观念的内涵,揭示民众关于“义”的社会道德实践如何影响了明代的政治事例运作,以求正于方家。
一
刘世教曾在《荒箸略》中指出:“赈之所自出有三,曰朝廷、曰有司、曰富家巨室。”朝廷之“大赍”与地方官府的“所蓄”用来赈济“亦当有限,势必有所不逮”,因此富家巨室与赈务成败的休戚利害最为相关。[注]刘世教:《荒箸略》,《救荒全书(及其他七种)》,《丛书集成初编》第96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页。这种看法代表了自宋代以来劝募富民捐赈者的共识,真正的困扰是采用何种方式劝募才能获得富家巨室的响应,达到既“恤贫”又“安富”的目的。如葛麟所言:“荒者,乱之端也,民至于乱,其祸尚可言哉!然禁乱民必先安饥民,安饥民必先劝义民。夫义民曷以劝乎?”[注]葛麟:《救荒刍言》,《葛中翰遗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1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71页。按照葛麟的说法,能应“劝”而捐赈的富家巨室,已经当得起“义民”之誉。在向富民募粟的各种途径当中,相比率之以法、临之以势或者诱之以利,能感之以德的“劝义民”才最符合儒家为政的理想,在荒政中实现“劝尚义”,对于倡导良俗、鼓舞民心方面的社会意义并不亚于济贫扶困。在明人看来,“劝尚义”当然也最为困难,一经实践就会不免发出“尚义之民可以德感,难以势加”[注]钟化民:《赈豫纪略·劝尚义》,《丛书集成初编》第966册,第4页。、“民之好义由感不由劫”[注]吕坤:《积贮仓庾》,《实政录·民务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64册,第376页。这样的感慨。
与前代相比,明朝对于“劝义民”尤为重视,正统初年“旌表义民”的事例也是在财政纾困与鼓舞道义的双重意图下开始推行的。时任内阁首辅的杨士奇在为江西吉水县义民曾希恭所建勅书阁撰记时写道:
洪惟圣天子体天之心、法天之道以覆育天下,夙夜孳孳,虑或有一物之失所者。或遭岁饥,抚循赈恤之使旁午道路,于是四方之民咸知圣志所向,争趋奉承,发廪倾帑以助济给,如已当然。盖前此所未见者,岂非上之仁有以感之乎!夫仁义礼智之心不间乎贵贱上下,皆均有之,惟在上者躬行以率之耳,《传》所谓“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于是有司奏:出谷济民者悉赐勅奖劳,旌其义而复之,而劝赏著于令甲。[注]杨士奇:《敕书阁记》(曾希恭),《东里续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372页。
这段记载的突出之处,在于将赈饥劝募的政治过程描绘成了君仁臣义的道德感应,凸显出君主权力所依据的道义性基础,肯定捐赈富民获得的政治表扬是来源于他们具备“义”的美德、足当旌表的资格。这种“立意”在旌表义民的文献中非常有代表性,得到了同时在朝的部院监寺大臣,如大学士马愉、王英、吏部尚书王直、国子监祭酒胡俨、陈敬宗、翰林学士周叙、陈循等多人的赞同唱和。以“尚义”、“好义”之德来解释旌表义民的捐赈之举,不仅体现在许多为义民所建的纪念性建筑(如御书楼、皆荣楼、敕书阁、玺书阁、承恩堂、恩荣堂、惇义堂、旌义堂、乐义堂、重荣堂等)撰写的“记”中,也频繁地出现在明朝南北各地义民的行状、传、送序和墓志铭当中。
如果只从道德角度出发来解释政治选择,似有“形象塑造”之嫌,与地方社会习俗殊异、价值多元的实际情况显然不尽相符,对此笔者曾撰专文分析,此不赘述。[注]向静:《感仁兴义、树立风声:明代正统年间义民形象的塑造》,《北大史学》第19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值得注意的是,给予捐赈者的旌表过程,如行人赍敕、羊酒花红、诣阙谢恩、赐宴光禄,这些被视为“近世所未曾有之宠荣”[注]黄养正:《送义民李信夫还瑞安序》,乾隆《瑞安县志》卷九《艺文·风化类》,清刻本,第七页a。的政治待遇,以及在普通民众中造成的效应,如树坊建阁、玺书供奉、名卿题表这些令“族姻乡党群聚瞻望,莫不举首加额、忻谢感动”[注]杨士奇:《恩荣堂记》,《东里续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371页。的动人声势,综合来看的确体现出了朝野之间对于“尚义”、“好义”之德的激劝和嘉重,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捐赈者不可能获得隆重的政治表扬与社会承认。这也提醒我们,即使“尚义”、“好义”事实上并不是被旌表的义民所能普遍具备的道德品质,也不能涵括全部的捐赈动因,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它的存在,或者说忽视它对朝政的重要性、对民众的感召力,这也是使明代劝分极富特色的关键所在。此亦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即捐赈者为何可能受“尚义”、“好义”的观念驱动,“义德”这样的道德动因是否具有真实可信的社会基础。
如果细绎旌表者“好义”的文献,可以发现其中呈现的“义德”至少具有三种侧重各有不同的内涵。
二
一种“义德”的内涵侧重于君民之义。现存可见最早的义民敕书,是正统二年(1437)九月初七日颁给南直隶淮安府海州义民段兴的,敕书中明确表达对义民的期待是“允蹈忠厚,表励乡俗,用副朝廷褒奖之意”[注]隆庆《海州志》卷九,《恩典志·敕直隶淮安府海州民段兴》,《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第五页。。所谓“忠厚”,强调了民对君所怀有的忠诚笃厚之义。这种忠诚笃厚,不是强调捐赈者个体的美德,而是形容他在“君民”关系中完成自己的政治角色的能力、实现这种政治联系的程度,具体表现为君若待民以仁,民则会仰体君心,以义报仁,如《大学》所言“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因此,这一层面的“义”侧重政治道德中的君民关系,能够体现这种关系的义民事例很多。
江西吉安府永新县民贺祈年,在捐谷前曾与其弟引年商议:“今天子虑民或艰食而豫为之防,吾其可不奉诏!”贺孟琏称捐赈时“吾只承德意,知出谷而已,岂敢徼此名哉!”新淦县义民何用高说:“吾奉承天子仁民之意而已。”吉水县义民萧文志曰:“今天子一意养民,必欲使之皆足给而无失所者,盖所谓如天之仁也,吾可不加勉!”平阳县义民柳靖,闻知劝分时,欣然曰:“吾民所以安生乐业而幸有余积者,上之赐也。今圣心惓惓,思患而预防之,将使斯民无不得其所,此天地之心也,其可负哉!”[注]王直:《敕书阁记》(贺祈年),《敕书阁记》(贺孟琏),《恩荣堂记》(何用高),《敕书阁记》(萧文志),《抑庵文后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册,第308、314、312、311页。《柳氏旌义敕书碑阴记》,《抑庵文后集》卷二,上引书第346页。南直隶淮安府义民罗振,除了捐谷千二百石赈饥外,“凡于出赀奉公,率以当为然,恒自谓‘吾民之职也’。”[注]杨士奇:《罗氏旌义堂记》,《东里续集》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436页。苏州府长洲县民丁宗,称输粟是因为“受朝廷恩,乐温饱,幸藉此图报,敢搏一官乎!”[注]方凤:《丁翁夫妇合葬墓志铭》,《改亭存稿》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3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3页。浙江处州府缙云县民赵贯,闻知劝民出粟赈饥,曰:“天子轸念民艰,吾辈坐视饥饿,岂不负上心耶!”[注]光绪《缙云县志》卷九《人物·义行》,清光绪二年(1876)刊本,第六页a。这些义民所谈的捐赈动因是他们体察到了君主的“仁民之意”,出于对朝廷德政的感激,也出于臣民完成政治义务的自觉,所谓“其可不奉诏”、“吾可不加勉”、“幸藉此图报”、“不负上心”、“吾民之职”,在此处体现的是传统君臣政治关系中的道德责任。
不难想象,这种政治道德的纽带比具体的行政关系更难建立,也不容易令人确信。除了曾经有过朝觐经历的粮长或耆老,大多数村民终身不出乡野,要能增进他们对君民之义的切身感受,除了学校与典籍教育的途径,往往有赖于地方官员的施政效果,尤其是看能否达到感化民众、顺其心意的程度。宣德五年(1430),于谦受命巡抚河南、山西,“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即具疏言之”。他接触到的“父老”,是在基层社会中颇有影响力号召力的代表人物,他们帮助于谦深入了解地方政事的症结脉络,提出兴利除弊的建议措施,也会从于谦的回应来判断朝廷是否支持地方民生,“(谦)一岁凡数上。小有水旱,辄上闻……朝上夕报可”[注]《明史》卷一七○《于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543-4544页。。透过于谦的虚衷与实政,民众对于君主和朝廷的感受就有可能变得真切踏实起来。正统五、六年间(1440-1441)在于谦的晓谕动员下,河南、山西受旌表的捐赈义民超过300人。宣德五年,赵新与于谦一道,受命巡抚江西。赵新出身富室,曾在江南岁旱时发家粟赒饥,对富家捐赈的心理较为了解,他提出的旌表劝分措施颇得人心。[注]商辂:《吏部尚书赵公挽诗序》,《商文毅公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5册,第62页。正统五年,薛希琏受命巡按江西,他到任之后,“以便宜惩奸弊,变通成法,宽猛得宜,民惠赖之”[注]彭时:《资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书丽水薛公希琏神道碑》,《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卷四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02册,第496页。,解决了江西官场中的不少沉疴痼疾,在赵、薛二人的共同努力下,正统间江西捐赈义民亦超过200人。李乐曾经指出,地方官的作为会直接影响民众捐赈体国的程度:“若平日有一团实心实政及民,即大荒穷民,必不为乱,劝民出粟,十必有四五应之,此可以理推者,非臆说也。”[注]李乐:《见闻杂记》卷二,第七九条,《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4页。有了实心实政,民众就不会“此心先与他隔绝”,这是履行君民之义的情感基础,地方官员在这样的基础上诚意劝募,即使再悭吝的民众也可能被激发出政治道德的义务感和荣誉感,一如正统年间吉水县知县柯暹的感叹:“人心靡常,顾所遇何如耳。”[注]柯暹:《永新修学纪序》,《东冈集》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册,第533页。
三
捐赈者“好义”的第二层涵义,是强调积而能散、能与众共财的品行。这种品行之所以被称为“义”,来源可以追溯到儒家经典中对“礼”的规定。《论语·学而》记载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在孔子看来,富者“无骄”之所以不若“好礼”可贵,是因为前者提出的只是近于底线的道德标准,而后者强调了一种积极行动的道德义务,相比“无骄”来说要求更高一些。那富者何以是“好礼”的呢?《礼记·曲礼》指出“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能将积累的财富散施给别人,这是富人“好礼”的表现,是志于道德的积极作为。对于“礼”与“义”的关系,自春秋以来,便有“义以出礼”的阐释。《礼记·礼运》中说:“礼也者,义之实也。……为礼不本于义,犹如耕而弗种。”《礼记·郊特牲》称:“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这表明“义”作为“礼”的观念性基础,合于“礼”的行为一定符合义。[注]桓占伟:《义以出礼,义以生利,允义明德——论“义”在春秋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地位》,《文史哲》2015年第1期。积而能散的富民,能够“好礼”,是因为他们具备了“义”的观念与精神。
南宋以来,在民间“以义为名”的各种俗称当中,就体现了上述思想在民众中的影响。洪迈《容斋随笔》卷八中指出:“人物以义为名,其别最多”,其中“与众共之曰义,义仓、义社、义田、义役、义井之类是也”。南宋嘉泰《会稽志》记载说,当时“与众共之曰义”的观念在宗族事务、民间互助活动中颇为常见:“今世俗置产以给族人曰义庄,置学以教乡曲子弟曰义学,设浆于道以饮行旅曰义浆,辟地以丛冢以藏暴骨曰义冢。……近时州县众力共给役曰义役,皆与众同之意。”[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151册,第334页。这里提到的“与众共之”、“与众同之”表达了与“积而能散”同样的内涵,都指将私人的财富无偿地用于对他人(不拘于血缘关系)有利的各种用途当中。
根据这样的观念,称捐赈者为“义民”,是指他们对待家财积而能散,储粟能“与众共之”,做到“富而好礼”,怀有“义”的观念与精神。这在各地的民众当中也是被承认的共识。江西赣州府民钟景崇,正统初闻劝分,“公闻命即出谷千二百石输仓济民,谓其子弟曰:‘亏盈谦益者天之道,积而能散者《礼》之言,散财以济民,义也。’”[注]余学夔:《处士钟公景崇墓志铭》,《北轩集》卷九,《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7册,第226页。福建建宁府寿宁县民陈偃素好施予,“值岁歉,朝廷行劝分之政,慨然曰:‘积而能散,吾党事也。’”陈偃觉得自己身为富者,“积而能散”是分内的责任,出粟千石赈济,遂获旌勅,这也是符合“富而好礼”的表现。[注]黎淳:《犀溪陈先生墓志铭》,《黎文僖公文集》卷一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330册,第115页。浙江金华府东阳县民楼震,正统七年(1442)被旌为义民,将所建承恩堂绘图以示后人,称“愿吾世世子孙,其慎毋丧,天下之财与天下共之,啬亦散,不啬亦散也”[注]道光《东阳县志》卷一九《义行》,民国三年(1914)东阳商务石印公司石印本,第二十页b。。山西太原府寿阳县民岳昙,正统间遇岁祲劝分,妻武氏曰:“吾闻多财贵赈施,否则守钱奴耳。矧今明诏涣颁,容可后耶!”岳昙于是出粟二千石,受旌为义民,“人犹荣之”。[注]康熙《寿阳县志》卷七《旌表节妇武氏墓表》,清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第下廿三页。
对待财富采取“与众共之”的态度,以此实现“以义立身”,秉持这种美德的生活,在儒家的价值观念中是能与立功、立言并列不朽的存身之道,而这作为一种个人价值的实现方式,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与现实基础。一方面,随着社会的稳定发展,财富的力量逐渐上升,物质追求日益趋向多元,警惕“逐利自富”对伦理规范、公序良俗的践踏逾越,也成为保护社会存续与公平的必然需求,这种需求落实在个人的价值层面,是鼓励人们在积利的诱惑面前选择“积而能散”、“与众共之”,以义立身。另一方面,许多义民生活在乡村社会当中,在家族、姻亲和朋友之间长期存在互助的传统,人们通过钱财、劳动力、家事、纠纷调解等各方面的互相帮助、彼此扶持,共同度过农业周期中那些不可预见的危机,也能藉此缔结深厚的情谊,形成紧密的社会关系。[注]有关传统乡村生活中互助的形式与作用,参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71页。因此,对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具备“与众共之”“周人之急”这样美德的人,也是在互助时愿意提供切实有力帮助的人,能成为被信任、被尊崇的对象。由此可见,在乡村的生活世界中,对拥有财富的人来说,“行义”并不是某种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在赋役、借贷、救济、礼仪、诉讼、营建等重要领域内的“施予”行为赢得个人声望与成就感的生活方式。嘉靖《广信府志》中记载了上饶县民未仲舒的例子,体现了富民对于这种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自觉选择,“(仲舒)为人沉密有大志,自以身为齐民,不能效诸事功,深耻之,于是奋于为义,思所以立其身。赀既富,乃推所余,置义田以赡族之贫而无养者,立义学以教族之贫而无师者,缙绅难其所为,辄奖扬之。”[注]嘉靖《广信府志》卷一八《人物》,《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45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1071页。未仲舒通过在族内“推所余”、“奋于为义”,实现了“以义立身”的愿望。
在捐赈的义民中,出于总结古人的经验选择“行义”立身、或者将“行义好施”作为家族生存经验的情况并不少见。江西抚州崇仁县民陈本贡,“尝读《国策》,至《冯谖客孟尝》一篇而叹:‘市义之举,为有赀财者所宜效。’故凡有义举,公即为之先。与夫邻里无资藉者,公为给济,有贷而不能偿者,取其券焚之,义声由是日著。”正统间本贡助赈捐粟一千二百石,更被视为“诚勇于为义者”。[注]杨贡:《陈本贡先生尚义传》,载《崇仁浯漳陈氏十三修族谱》,抚州崇仁县相山镇浯漳村陈氏家族收藏,笔者2015年1月在该村考察得见。陈本贡认同冯谖为孟尝君事先筹谋避祸之道,从中得到有财富之人如何自处的启发。在他看来,散财以获美誉的这种“市义”方式越千年之下仍会奏效,于是选择积极地资助贫穷乡人,获得“义声”,捐赈使他得到“勇于为义”的赞誉,更是难得的护持。南昌府新建县民欧阳则安,景泰四年(1453)出粟赈饥,被旌为义民,其后三代銮、深、玺“皆富厚相承,世好施予,依然有则安公之遗风”[注]朱少焀:《处士欧阳西谷公传》,《西山欧阳震昌二公支谱》,南昌新建县石埠乡欧阳村欧阳家族收藏,笔者2015年1月在本村考察得见。,将“好施予”作为保护家族生存延续的传统。龙泉县义民谢汝涵,“(高祖以下至父)皆有隐德,而以诗书行谊世其家。……(汝涵)心之嗜义如饥渴之于饮食,唯恐或后”,曾经在乡间构筑简室,提供免费的居处和食物,“凡民无所庇者使居之,不取僦直,贫无食者与之粟,不责偿,于是人争趋之而归徳焉”。[注]王直:《谢汝涵墓志铭》,《抑庵文后集》卷三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2册,第268页。谢汝涵拥有的财富远远超过一般的乡民,但他和家族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并不是纯粹依据其经济地位,在付出了相当多的资源“与众共之”后,他才拥有了乡人的归心推服。与这种付出相配,“义德”也就不是虚誉了。
四
捐赈者“好义”的第三层涵义,侧重于宋明以来理学涵养实践的道德自觉与自律性。“义”的观念在先秦形成的时期可以追溯到西周,大约到了战国中晚期,在诸子论“义”的思想系统中,“义”的涵义常用来表达一般性的善、正确、正当或恰当,使用非常广泛。[注]先秦时代“义”观念的形成演变与早期政治领域的变革关系相当密切,从西周以来,“义”作为有普遍性、有共识的价值尺度,在社会关系的诸多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春秋至战国的社会转型中,“义”观念在政治的变动、冲突与利益裁夺上原本发挥的制约作用减退,并已落实到个人伦理、价值准则的层面,这使它成为诸子讨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论“义”之说并不限于儒家学者。参见桓占伟:《从宗教神性到政治理性——殷周时期义观念生成的历史考察》,《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4期;《百家争鸣中的共鸣——以战国诸子“义”思想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本文因主要关注宋代以下儒家“义”观念的内涵变化,故此上溯渊流时并未展开。此时在儒学的伦理信条中,“义”作为道德价值的独立内涵也开始形成。[注]陈弱水:《论义三则》,《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儒家的经典从《孟子》开始,“仁义并重”,与“仁”相比,“义”的内涵更多地指向道德的自觉与自律性,强调“义”的德性是一种基于是非善恶的道德区别与道德判断。[注]陈乔见:《羞恶、义与正当——孟子“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详解及其理论内涵》,《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东汉刘熙在《释名·释言语》中释“义”时说:“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这里的“裁制事物”也秉承了做出道德判断并引起行动的意思。
宋代理学兴起之后,对“义”的内涵有了进一步阐发。自北宋的周、邵、张、二程以来,在新的宇宙本体论之下,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哲学思潮,即以心性之学为核心,提出了一套包括认识与实践的修养方法,“义利之辨”的问题尤其受到宋代以来理学家的高度重视。程颢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便是“存义去利”。张栻循此发挥,在讲“义利”时将“义”与“善”等同,义利之分即是天理之公与人欲之私的对立,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中,“义”即是天理,是未加以人为干预的本然之性,是“无所为而然者”[注]张栻:《孟子讲义序》,《南轩集》卷一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7册,第539页。。朱熹对此极为赞赏,称其“扩前圣之所未发”,并在自己的学说中继承、发展了这一见解。他在《四书集注》中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又说:“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何不利之有?……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注]朱熹:《朱子语类》卷二七,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02页。从朱子的论述来看,“义”是天所赋予人的本性,是一种裁制处事是否合于道德、判断伦理规范的实行是否得当的自觉性。据此,程端蒙《性理字训》对理学中“义”的内涵作了一个通俗概括:“无为而为,天理所宜,是之谓谊(义)。”
基于对“义”的这种阐发,循“义”而行成为朱熹以来理学人士涵养实践的重要方法。程颐谈涵养,重点在“持静”,朱子进一步谈到要“敬直其内,义以方外”,“静则察其敬与不敬,动则察其义与不义。……须敬义夹持,循环无端,则内外透彻”。[注]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第216页。这里指出以“义”察“动”,即遇事要能济之以“义”的话,就可以辨明是非,处事得当,自然而然地符契天理、不惑于人欲之私利。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好义”是指依循人的本然之性、随事能体认天理的一种道德自觉与自律性。
上述见解到了明前期仍然是理学中占据主流的看法。方孝孺在阐释“善”与“义”时表达了同样的见解:“夫善者,天之所赋、人之所有者,由乎仁义忠信而行乎家,推之以及乎人,大之于众庶,皆义之宜为尔,岂望其报哉!”[注]方孝孺:《宋氏为善堂记》,《逊志斋集》卷一五,《四部丛刊正编》第7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27页。此后永乐年间,胡广等人奉勅编撰的《四书大全》,成为科举程式的标准读本。是书通过对朱熹集注与宋元明初诸儒训注的取择,亦反映出了当时学界所宗的意旨,其中《论语集注大全》卷四所汇辑的诸儒阐“义”之见,足与方孝孺之说桴鼓相应。
依照理学涵养的方式,严于“义利之辨”、循行“义之宜为”是志于学者的首要之务,也是济民救世的道德践履之途。明初以来,理学发展得到官方支持,学校教育以程朱理学家的经典纂集为主。此外还有地方闻名的理学人士,通过研读宋元以来重要理学家的著作,虽无师承而能“自悟其学”,并在乡间开学授徒,颇有影响。在响应劝分的富民当中,那些素习理学之经籍、或与理学传播渊源较为深厚的捐赈者有可能接触到有关“义”的学术见解,并身体力行。以下兹举出抚州陈氏、吉安萧氏两个家族为例。
在抚州府崇仁县浯漳村,曾旌表义民陈有恒、陈舜民父子。陈氏子弟志于为学,接受理学思想的途径也较为丰富。据《竹溪华阴陈氏族谱》记载,陈家世居崇仁县集峰之南,元代理学家吴澄家族则居于集峰之北,两族地理位置邻近,世通婚姻。陈有恒之父陈本毅所娶吴氏,即吴澄的孙女。吴澄与有恒的高祖筠坡翁交好,曾为其题写墓铭,成为陈氏子孙自勉于学的箴言。这一家族中的成员对理学的兴趣持续时间较长,本毅的族兄弟号仰德者,其仲子与甥曾从罗汝芳听讲,罗汝芳也曾造访其家。[注]《绍筠轩序》、《勅旌尚义民陈公墓志铭》、《前峰仰德序》,载《竹溪华阴陈氏族谱》,抚州崇仁县礼陂乡左坊村陈氏家族收藏,笔者2015年1月在该村考察得见。
从元末明初陈氏家族的学术倾向来看,复卿-本毅-有恒-舜民四代均致力于经学,以儒业自励。复卿自任“儒生分内事”,尝语人曰:“纵使际遇非时,不能尽泽苍生,亦当周恤困乏。”每当官廪不足赈乏时,复卿便出粟以拯救饥民,里中受其饷馈者指不胜屈,亦不责其报,其曰:“吾不欲令若辈再悴经营耳。”元末盗乱,复卿避地宜黄,“假馆授徒”。其子本毅回归旧籍后,率诸子弟,“志于道德”,构南圃书屋,读书计日课程,“学务实得,无畔圣筌”,受到江西致仕官员陈珪的称许,认为他“士志于道德,则所求者大,所见者远。苟道德有所不存,放(其)心而不知求,岂能自得于中,不愿于其外哉”。本毅子有恒,“尝师事征士张希颜、永明令永和詹先生,肆力问学”。有恒子舜民,被誉为“读书穷理人也”,曾自构书斋,名曰“泰斋”,取朱子所倡存诚主敬、养心循理故能安舒不矜、泰而不骄之意。[注]《义士陈公复卿并李孺人行实铭》、《南圃书屋记》、《勅旌尚义民陈公墓志铭》、《泰斋书屋记》,载《竹溪华阴陈氏族谱》。陈有恒在正统六年(1441)以捐赈受旌表为义民,陈舜民在成化四年(1468)因捐赈为义官,他们受家族的教育薰陶而读书穷理、志于道德,如果真正服膺朱子之教,循行“义之宜为”,这与先后捐赈的行为也是十分契合的。
与崇仁陈氏相比,吉安府吉水县义民萧文志家族对捐赈的理解或能直接昭显理学思想之影响。萧氏与罗伦的家族世有联姻,文志在正统间欲出谷二千石,以疾卒未果,幼子东钺不避艰险,竭力尽心以成之,当朝廷遣官追旌文志为义士时,东钺感激而叹曰:“义者,人所禀之天理也,今父以义承恩命褒宠,为后人者当善继之。”东钺将捐赈之“义”视为“天理”,且为人“修身慎行,非义不苟处;与人言笑,非义不苟合”,显见其在日常修养中十分重视循义而行。在文志的孙辈中,萧琼、萧魁二人,都出粟应备荒诏,旌为义官;萧赞,习书经为岁贡,授任湖广应山县儒学训导,曾摘编一书,名为《儒家备览》,以勉后学。文志与长子东铉、长孙征济先后经理义仓,邑人艾凤翔称赞他们“三代尚义”,且征济为人“是非坦然明白,取与不苟,惟义是从”。对于萧文志家族捐赈、建义仓的行为,邑人罗通认为原因在于“虽其处富而不吝,要亦学问之功不可诬也”[注]《虎溪萧氏双节堂记》(罗伦)、《处士东钺行状》(李同仁),《故隐君竹斋萧先生墓铭》(罗通)、《义仓记》(艾凤翔),载《虎溪萧氏十一修宗谱》,吉安吉水县文昌乡虎溪村萧氏家族收藏,笔者2015年1月在该村考察得见。。
在留下的有关其他捐赈者记载当中,家族子弟多与理学家交游、或本人受理学思想影响而行“义之当为”者亦不乏人。如《明英宗实录》正统六年(1441)十月所旌义民徐国(以排行称让三),[注]《明英宗实录》卷八四,正统六年十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1683页。世居江西抚州金溪县大耿村。在金溪当地,徐氏是与理学传播关系较深的大族。自宋元以来历代子弟先后从学陆九龄、陆九渊、吴澄等人,入明以后,每代子弟均致力经史,或私淑于官学训导,或教授乡里,所习以程朱为宗。徐国之祖徐渊,从临川葛元哲受书经,父徐熹“好读父梅轩遗书”,伯徐大宽“与友生宾客讲论道义,终日而不厌”;徐国本人“锐志于学”,捐赈千石旌为义民,并自宣德以来积谷万斛,建义庄,环庄数十里乡人皆仰赖之,人称“义庄先生”,有“生财制事一出于义”之誉,[注]《士徐公东皋先生墓志铭》(徐琼)、《贫乐斋记》(万蕴辉)、《贫乐斋后记》(徐琼)、《旌义民徐公邦任墓志铭》(刘俨),《送徐显道还金溪序》(林瀚),载《大耿徐氏族谱》,江西抚州金溪县合市镇大耿村徐氏家族收藏,笔者2015年1月在该村考察得见。可以说是践行“义之当为”的人物。
金溪浒湾镇捐赈义民车贞所属的车氏家族,则与吴与弼过从甚密,并深受影响。元末明初,车氏家族的车宝、车福兄弟主理族务,担任粮长。车宝从五河教谕李子亮,“得朱子《性理吟》,家学传习”。《性理吟》对性理之学的阐述浅易,很适合作为“家学”的启蒙读物教育子弟。此后车氏族人对理学的了解逐渐深入,先后从本地进士何自学、江胜等人游学,到车福的孙辈时,师事吴与弼的人数最多、时间最长,车福一房遂成为吴氏之学在金溪传播的中坚。
正统七年(1442),车福的长子车贞,输米二千石助赈,旌为义民,景泰四年(1453)再次捐粟助赈,获授冠带,吴与弼也在这一年首访车家,“为书‘尚义堂’、‘读书楼’,并题《石泉手卷》”。此前,车福这一房支已有多名子弟师事吴与弼,如车福第四子车用广的次子车亨,幼子车绍祖(号石泉)的长子车泰来、三子车宏道等。吴与弼的到访,一来为表彰车福、车贞、车绍祖这一支的义行,二来也是与车氏的子弟聚会讲学,如谱中《举林记》所载:“吴康斋先生与生徙[徒]会社于兹,族中先型多出其门,扁(匾)其楼曰‘读书’。”天顺二年(1458),吴与弼再次到访,车贞“宾吴处士与弼于尚义堂,论文赋诗,请序世谱”。车泰来师事吴与弼多年,“学得其传”,成为吴在金溪最重要的弟子。泰来之弟泰平的长子车玑、长孙车民范,先后以尚义输粟、好善赈乏,获授朝廷与郡邑的冠带。[注]《四六公松竹梅房世系全图》、《明故春谷先生慄二公墓志铭》,载《举林车氏十修族谱》,江西抚州金溪县浒湾镇黄坊村车氏家族收藏,笔者2015年9月在该村考察得见。有关车氏家族与吴与弼的关系,还可参见张艺曦:《明及清初地方小读书人的社集活动:以江西金溪为例》,载《“十六-十八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刊),台湾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编,2018年6月。在上述过程中,吴与弼的讲学与车福这一房支的学问行谊相结合,吴氏对理学意旨的阐发也通过地方家族的子弟行为、政治选择而引起周遭民众的关注,这有助于将理学中“义”的抽象内蕴落实到世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化民成俗的重要途径。
从以上所举数例来看,捐赈富民对于“义”的认识会受到明代理学发展的影响。张栻、朱熹以及宋、元、明初诸儒对于“义利之辨”的深入剖析,通过学校教育、经籍流传、私人讲学等方式进入了民众对于道德生活的观念当中,尤其通过家族内部的代际传承、姻戚往来和师友脉络,循行“义之宜为”可能成为几代族人所奉行的道德涵养方式,形成明晰可辨的“尚义”传统。个人在这种传统的浸润下实践“无为而为”的义行,可以说是理学推行以德化民的理想模式,对这个层面上“好义”内涵的阐发也只有在理学的思想语境中才能获得充分的理解。王直在任礼部尚书期间,应邀为不少义民的家族作记,他曾从理学思想的角度解释民众捐赈之“义”,并认为对这种“义”的旌表正体现了朝廷对理学的提倡、民众对理学的信仰,如给吉水义民胡有初的墓表中写道:“义者,天之所赋、人之所同得者也,推而行之,岂以为名哉!然而名必归之者,上之人所以劝天下之为义者也。”[注]王直:《义民胡有初墓表》,《抑庵文后集》卷二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2册,第99页。
五
综上,我们讨论了捐赈行为可能出于“好义”,即捐赈者受“义德”的内驱而响应劝分的三个层面。从我们的分析来看,无论这种道德因素的内涵是认可、完成君仁民义的政治义务,还是侧重自身伦理修养的德行实践,或者只是积而能散、与众共之的处世之道,它们的存在都有相当清晰的现实基础与历史脉络,由此推论,民众在面对劝分时确实可能受到“尚义”、“好义”的观念驱动,从而选择捐赈。
再回到本文开始所提出的问题上,在深入研究明代民众选择捐赈的政治心态和行为方面,本文对道德发挥作用的分析只是迈出了一小步,但也由此揭示出了旌义事例据以推行的具体道德内涵。这提醒我们进一步关注明代皇权政治的道义性基础,在以行政理性的角度研究政治运作之外,还应当充分考虑社会道德观念的作用和影响。
在有关捐赈者“好义”的记载当中,民众所认可的道德选择很少强调出于个人的“天赋”或者“自然”的过程,而是更多地追溯到政治的或社会的环境“建构”当中。“义”所代表的价值追求本身含有“正当性”的前提,这使得对“义”的德性理解与实践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政治观念与社会需求,无论是社会发展作用于个人、家族义利观念的变化,还是朝廷、官员、理学人士对旌义源自道德动因的鼓舞宣扬,都构成了这种“建构”的组成部分,并产生积极的相互作用。当研究“尚义”观念如何在民众当中变动于内、形诸于外的时候,我们发现,对于“义”这样的普遍道德观念的重视,通过旌表“尚义”来争取对于社会道德规范的“话语权”与“主导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代皇权政治的道义性基础,亦是其得以运行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