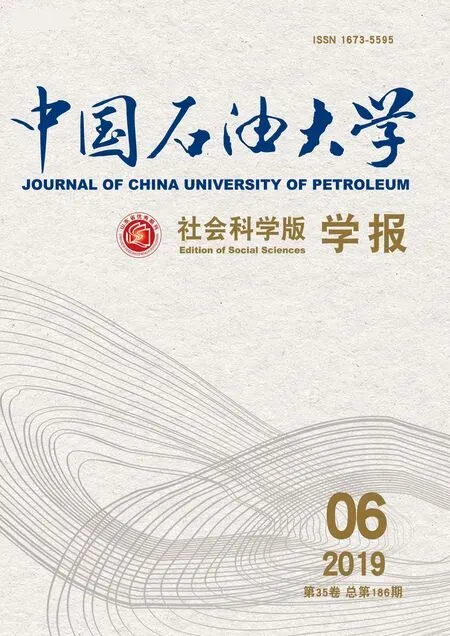“五四”的回声与询唤的“主体”:陈凯歌电影中的女性困境
孙 祖 欣
(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艺术部,江苏 南京 260000)
陈凯歌在电影中展示了丰富的女性形象:从传统文化压抑下的翠巧,到“巾帼不让须眉”的赵女,再到网络暴力和资本裹挟中的叶蓝秋,每一个女性形象都传递了时代的精神。性别斗争从来不囿于男女之间,它背后往往有权力、文化、政治和资本的参与,因此,对这些女性形象的梳理和解读,离不开对其背后的文化脉络和权力动机的拆解。陈凯歌早期电影中女性形象可以追溯至“五四”启蒙精神,而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又反映出民族主义对于个体的询唤以及资本主义对女性自由的颠覆。
一、“五四”启蒙思想的传承与女性意识的觉醒
陈凯歌早期电影塑造了诸多现代、独立的女性形象,散发着现代启蒙思想的光辉。这些形象并不仅仅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诞生于西方思潮对于现当代中国的影响之中。
20世纪之前的中国女性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生活中心很难离开家庭(以父亲或丈夫为主导)。“自周兴以来,一切折衷于礼,以礼对原始习俗进行梳理、改造。礼讲究男女有别……而妇女的从属身份不但被礼确认为两性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在宗法家族组织下被制度化。”[1]“先秦性别角色的模式成为此后两千年中国社会男女性别角色的基本模式,它开启了一种男尊女卑的社会角色定式。”[2]93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中,如果没有“五四”精神的爆发和西方启蒙思想的引入,中国男尊女卑的社会角色定式将难以在短短一百年间自发地演化出独立自主的女性成长脉络。
17世纪,西方发起启蒙运动,强调理性、自由、平等、科学以及个人主义。中国在20世纪的启蒙运动,通过引入西方启蒙思想,将现代性带入了这个古老帝国,向西方学习的传统滥觞于“洋务运动”,发展于“五四运动”,并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传承。
“五四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急于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西方哲学与思想被适时地引入。“1919—1924 年,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先后有五位国际著名学者应邀来华讲学: 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和泰戈尔……每位学者的影响自有不同,但作为整体,却构成了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景观。”[3]在这些引入的思想中,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中国传统集权和封建思想的对立面,成为显学。“对个人主义精神的宣扬将女性树立独立人格提上了历史日程。”[4]女性的权利与独立开始进入公众视野,许多作家开始创作大量反映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现实小说,探讨女性的生存状况。“五四及1920 年代女性写作,是中国女性以‘人’和‘女人’的反叛性姿态参与反封建的历史进程,书写女性的觉醒与成长……批判礼教罪恶和封建婚姻,关注弃妇命运;追求自由婚恋、大胆表露性爱,探求婚内主体情欲;反抗社会压抑的女同性恋准同性恋书写。”[5]尽管从社会启蒙的视角来看,“五四运动”并未取得成功,但女性解放和独立的观念却成功地进入人们(至少是知识界)的视野。
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其(80 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上承 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下启90年代,成为当代中国的又一个‘五四’。”[6]中国第五代导演于20世纪8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用自己的影像和镜头,从多个方面传递和发扬了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现代启蒙精神,为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烙下了深刻的印记”[7]。“第五代导演的早期电影无疑就具有现代启蒙性的基本特征,个人的‘发现’、传统意识的颠覆、现代化的渴望以及对于未来中国的期冀几乎是所有电影的精神内涵。”[8]如陈凯歌的《孩子王》(1987年),便是一个传统文化对个性压抑的寓言。
因此,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是在西方思潮影响和国内新文化启蒙下形成的。陈凯歌早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是“五四“启蒙精神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回声、一场回放。
《黄土地》(1984年)运用了典型的性别压迫下女性抗争的“五四”叙事。在马克思主义性别观中,性别压迫往往被化约为阶级压迫,但是,《黄土地》绕开了这种马克思主义性别观,呼应了向封建礼教抗争的“五四”传统:电影女主人公翠巧遭受的是来自传统文化、而非上层阶级的压迫。“女人不该简单地被视作被男性压迫的无辜受害者:在男人和女人的共同积极参与下,可辨识的性别歧视实践被合理化、维持、续存,并被确认到社会和文化的理念当中。”[9]即不应该狭隘地定义为男性群体将自己置于中心对女性实行剥削和压迫。
共产党员顾青从延安来收集乡间民歌,在陕北的黄土地上,翠巧的命运渐渐在顾青以及观众面前展开。顾青甫一到达村庄,便见证了一场婚礼:婚礼现场14岁的新娘表情木讷,毫无幸福感。看过婚礼的翠巧也表现出了绝望与恐惧的情绪,却也无法逃脱父亲给她安排的同样命运:被迫嫁给一个笨拙、丑陋的老男人。电影中,翠巧用民歌哭诉自己悲惨的命运。她唱到:
六月里黄河冰不化,扭着我成亲是我大,五谷里数不过豌豆圆,人里头数不过女儿可怜,女儿可怜女儿哟。天上的沙鸽对对飞,不想我的那亲娘再想谁。
悲情涌动在歌词里。在《黄土地》中,翠巧和其他女性并未被视作独立的个体,而是家庭的财产。在一场戏中,当翠巧快乐地挑水回家时,她看到了屋里的媒婆,以及床上的聘礼。她的婚礼是一场买卖,礼金用来下葬母亲和给弟弟娶亲。父亲没有出现在镜头里,但他冷漠的声音宣告了翠巧的命运:
你娘这回闭上眼了,为这事儿,爹打过你。家家女子都是这条路,我看着,你的命能比你姐好。女婿家是好人家,就是岁数大点,大点好,老成,实受。再说,你定的是娃娃亲,定金一半发送了你娘,一半给你弟弟凑数定婆姨了。
实际上父权既是等级社会和文化的一个内核,又是其一个显著表现。“传统上,父权赋予了父亲对于妻妾和子女的包含家暴、虐待、以及谋杀和交易的近乎全部的所有权。”[10]25抱持着这样的保守观念,父亲驳斥顾青的自由婚恋观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场夜间对话里,顾青说,在中国南方,女性可以自由恋爱,不需要通过媒婆也不需要聘礼交换。这番描述使翠巧父亲大为震惊:“那女子们就那么不值钱?”为驳斥顾青,翠巧父亲不断强调:“咱庄稼人有规矩,咱庄稼人有规矩!”继而叫停了这场对话,因为在旧父权的规则下,实在难以通过理性和逻辑为这种偏执和错误的信仰来辩护。支撑旧父权的内核实质上便是传统文化中专制、反现代、非理性的那一部分。
但通过顾青,翠巧的个体性与独立意识开始觉醒。顾青的出现在翠巧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了一种不同以往的、积极的、充满希望的性别可能性。翠巧向顾青了解军队生活的细节、男女的关系,甚至请求入伍。虽然她的请求一开始被顾青拒绝,但是不再向包办婚姻妥协的火种已经被点燃。不幸的是,结局中翠巧虽然从一个村子里的压迫中挣脱,却最终没能逃脱被黄河——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吞没的命运,翠巧的“五四”式女性自觉的星星之火被旧父权连同精神和肉体一起消灭。但她的觉醒恰恰反照出了传统文化中的旧父权的腐朽,也正是通过这种对父权的批判,女性的独立逐渐化入“五四”以后发展起来的正统性别论述之中。
尽管陈凯歌曾在采访中自称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11],但他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中的那些个性独立和反抗传统的女性形象却是以“五四”精神为源头的,而非孕育于20 世纪60—70 年代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女性主义于1980年代传入国内,但其影响首先集中在“纯介绍性研究、建设中国女性主义文论、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作为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作品”[12]等文艺批评领域,对电影创作的影响也仅仅触及到了部分女性导演和她们具有先锋性质的实践。而此时陈凯歌的创作主题多“注重人性的启蒙,关注生活在浓郁的中国气息和特有的文化禁锢下人的挣扎与渴望,展现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束缚”[13],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依旧要在本土的文化启蒙中寻找源头。
二、旧父权的衰落与女性的崛起
女性主义起源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女性追求与男性同等政治、劳动、经济权利的社会运动,早期的女性主义理论聚焦于研究父权、父权的起源以及它的运作机制,寻找性别不平等的背后动因,认为父权是导致性别不平等的根源。陈凯歌的电影即对压抑女性的传统文化进行了详实的描写。
以现代的眼光回顾旧父权,会发现它显而易见的肮脏面目,而且其维系自身的理由不堪一击。《风月》(1996年)中的如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种压迫,但最终也在父权的一波波反扑中湮没。根据旧父权的种种“约定俗成”,女人被禁止于许多领域之外。相应地,一系列规训与惩罚也伴随这些禁忌产生。
电影《风月》开头,一群官员聚首于庞府,等待皇帝退位的消息,另一边女主角如意则在祠堂里玩耍。当退位的消息抵达,所有大臣脱帽下跪,哭天抢地。下一个镜头庞老爷严厉斥责随从和如意:“放肆! 是谁让女子进祠堂? 皇上下了龙椅也不可以,不可以!”“妇女不仅在生理特殊时期被隔离,而且由此而来的妇女不吉成为将妇女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一个宗教性理由,几乎一切重要活动都存在妇女禁忌。”[2]215尽管新建立的共和国宣布了封建制度的消亡,等级制和父权却在传统文化的掩护下继续存在。
电影中,庞老爷去世,如意哥哥残疾,如意以女性身份继承了家业。表面上,如意成为了庞府的新领袖,背后里,族中长老却尽力破坏女性领导,找来远方亲戚端午服侍如意,希望通过端午掌控她。料理后事时,如意决定遣散老爷生前的姨太太,理由是“不是说女人连祠堂都不能进吗,留着她们有什么用”。族中长老坚决反对并大声哭号:“庞家没有男人啦!”后来当端午表达了他对如意的爱和服侍如意的决心后,同样的哀嚎再次发生。在这些情节的安排中,旧的父权与女性的崛起针锋相对,并一直纠缠到电影结尾,如意瘫痪,端午掌门。
这里指称旧的父权,并非意味着存在着时序上的两种父权,而是将传统文化中那种显而易见的、毫无掩饰地将女性视为下等人和附属物的思维统称为旧的父权。在“五四运动”中,女性主义暴露了女性和年轻男性的恶劣生存和文化环境,对旧父权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使之至少表面上失去了支配性别关系的正当性。
《荆轲刺秦王》(1999年)同样展现了一位现代独立女性形象。电影改编自《史记·刺客列传》,塑造了赵女这个全新的角色。为实现更宏大的政治野心,秦王嬴政入侵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在这一过程中,他面临着诸多阻碍,刺秦便是一系列阻碍的一次集中爆发。在这个男人与男人、国家与国家博弈的过程中,赵女的角色举足轻重。生于赵国,赵女曾与青年嬴政有过一段浪漫的爱情。当嬴政继位成为秦王后,赵女背井离乡来到秦国,成为嬴政的妾。但是,宫廷里的生活却无法驱散她的孤独和忧郁。作为一名独立的女性,赵女拒绝在绝望里继续沉沦,她反抗命运,并决定去秦返赵。当嬴政问她为何要离开,她回答:
你是每天都到大厨房来看我,你以为这样就是对我好了,你知道我都在想什么,我要过什么样的日子?你不知道。在宫里,我见人就要笑,不笑要皱眉,走路要低头,说话要小声。我是个摆设,是个木偶。我想放声大哭,想大声讲话,我不想对每个人都好,我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可我已经过了很久了,我要走了。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赵女显然不是一位两千多年前的女性,而是一位“五四”式的、追求自我的新女性。这位新女性还拥有强烈的爱国情操和人文情怀:在了解到嬴政统一六国的雄心和实现永久和平的愿望后,赵女甘愿以间谍的身份潜入燕国,促成太子丹刺杀秦王,创造秦兵入燕的借口。从这里开始,赵女的行为在男人的世界里创造出一条可见的、有意义的女性轨迹。
顽固的父权制主宰了两千年中华文化里的性别关系。在20世纪,面对女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风潮,作为一种落伍的观念,旧父权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尽头。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权从文化和习俗中彻底消失了,它消失的仅仅是旧式的面貌。伴随着女性的崛起和女性权利的获得,父权虽然从旧文化体系中撤出,但却隐藏到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当中,新的父权诞生。
三、新父权的诞生与被询唤的女性主体
旧父权和新父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共享同样的性别等级秩序内核,在旧父权衰落之后,这一内核掩藏到新的社会关系之下,浮现出新的父权模式。“作为一种习惯,父权制成功地以一种社会常量的形态深深地根植于所有政治、社会或者经济模式之下。”[10]33新父权寄生在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下,借助这种社会生态的掩饰,它询唤出女性的“主体”,为其服务。
民族主义是新父权的首个藏身之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中源远流长,积累了深厚的民族认同基础,以至于隐藏于它之下的父权,都获得了一种力量,能够将解放的新女性再次询唤为为其服务的“主体”。
尽管民族国家的概念在19世纪后期才在中国出现,但是长久以来,中国精英阶级却常常有着强烈的共同体身份认同。这一共同体并非建立在地理国家之上,而是建立在文化和“礼”的一致认识之上。“夷夏之辨”的概念形成于先秦,“从三代到秦汉,华夏文明随着中原统治区域的不断拓展而向四周扩散,诸多夷狄戎蛮与偏远落后之邦在接受华夏族的典章制度、礼乐文化以及社会组织后,逐渐认同而融入其中。”[14]受“夷夏之辨”的影响,中国精英阶层经历的是一种文化优越感。“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中国是由一种共享的书面语、古典文学经典、官僚传统、共同历史、遍布帝国的教育机构以及一套在政治和社会层面规定精英行为的价值系统定义而成。即便国家解体,这种文化统一意识依旧长存。而当面临拥有不同传统的蛮族入侵时,这种共同文化的力量就变得尤为明显。”[15]即是说,一旦被夷狄侵略,文化认同和自尊就会遭遇强烈挫折,相应地,一种民族主义或忠君主义便在精英阶层被广泛地唤起。
鸦片战争,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要思潮,现代国家意识取代传统的“夷夏”观逐渐形成。帝国主义侵略和救亡图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两个主题。民族主义最终超越自由主义和忠君主义,并成为之后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
由于民族主义拥有如此广泛的社会根基和深远的历史脉络,联合并隐藏在民族主义之下是新父权保全自身的策略。虽然表面上父权不再强迫女性在两性关系里一味地履行义务,但是新父权却以民族主义的名义来询唤女性。关于询唤,阿尔都塞认为,不同于(强制性)国家机器依靠强制手段来发挥作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首先会借助于意识形态方式来发挥作用,“意识形态是以一种在个体中‘招募’主体(它招募所有个体)或把个体‘改造’成主体(它改造所有个体)的方式并运用非常准确的操作‘产生效果’或‘发挥功能作用’的”[16],这种操作就是询唤。《荆轲刺秦王》中,表面上赵女是一个拥有主体性的女性典范,但这样的主体却是被父权以民族主义的名义询唤出来的。电影中,为了留下赵女,嬴政向她解释自己的政治宏图:
五百五十年了,原来的几百个诸侯国哪里去了,现在只剩下七个。小国想要变成大国,大国想要吞并小国,五百五十年战争不停止,百姓好像活在水火中,只要六国还在,战争还不会停止,天下就永不得安宁,百姓就永不得安宁。六国注定要灭的,不能改,谁也不能改。
这场激情演说感动了赵女,使她自愿充当间谍。她的牺牲看起来是自发的,但却是被民族主义掩盖下的父权招募而来的。因此,在叙事中赵女的主体性本质上是被动和客体的。换句话说,她成为被“询唤”的主体。“这种‘询唤’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刺激—接受’的过程,而是一种‘教化’和‘暗示’的过程。‘询唤’不可能直接造就‘主体’,必须通过‘个体’自身的‘认识’和‘认同’,才能产生对自我形象的确认,进而形成一种想象性的关联,使每个社会个体同社会整体结成紧密的关系。”[17]伪装成犯人、潜入赵国、接触荆轲……赵女完成了对自己身体和灵魂的“改造”,完成了“询唤”发出后的一系列主体确认动作。然而电影后段还是揭露了民族主义掩饰下的父权的虚伪:嬴政对赵国的入侵是一场连儿童都不放过的大屠杀,他入侵赵国的真正目的是复仇。现实粉碎了赵女的天真,摧毁了她个体牺牲的意义。相较于在旧父权下被迫履行义务,女人更愿意在民族主义的号召下放弃自由,做出牺牲,留下“女性独立”的一纸空文。
在《妖猫传》(2017年)里,陈凯歌将杨贵妃塑造成大唐气象的代表,所有盛世的极乐,都收纳在她的绝世容颜里,而在民族主义的招募之下,杨贵妃也明白自身的意义,“强盛时,她是帝国的象征,危难时,大唐将不再需要她”。在马嵬驿兵变中,为了皇帝的安危和大唐的延续,她主动“牺牲”,但在真相揭开之际,观众却发现她主体性的“牺牲”,仅仅是男人阴险策划的一场谋杀。在民族国家大义的询唤之下,女性看似走出一条进取之路,在这条路上,她们主动、承担,但背后却是父权的设计和诱导,女性的自由选择在一开始便是虚构和充满欺骗的。
除了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也弥漫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滥觞于20世纪60—70年代,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退潮,资本、父权和女权都有了新的变化。戴锦华指出:“20 世纪 60 年代,整个世界曾经有过批判和反叛的逻辑,同时也是质疑父权和动摇父权的逻辑。今天,父亲归来,父权重建,它以爱的名义重新获得一种掌控。”[18]与戴锦华的论述类似,N·弗雷泽在分析第二波女性主义时指出,在进入新自由主义阶段,女性主义却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女仆,例如,资本主义通过精心阐述女性进步和性别正义为女性创造出一个虚构,为资本主义授予一个道德伦理的光环,而在这种虚构之下,女性寻求打破职业天花板、提升个人收入和个体解放的过程,都化约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引擎。[19]“就资本主义经济强调利润动机、阶级结构、殖民战争、种族歧视等方面而言,资本主义基本上仍然是父权制的。”[20]相较于民族主义,资本主义更具侵略性,也更肆无忌惮。缺乏有效的监管,资本主义野蛮生长,将其他意识形态如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公平、正义等统统挤入角落。不止如此,跟消费主义捆绑在一起的资本主义还在主流社会里赢得名声:商界的成功意味着近乎全方位的成功。在私人领域,资本主义调整着家庭关系,确保资本在家庭关系中的基础地位,稳固“供给—依赖”的二元模式。在公共领域,资本主义物化和客体化女人,并将其视作市场战争的战利品。资本的泛滥带来父权的无所不在,也最终导致女性的无处可逃。
在中国当代电影中,父权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并不少见,而且观众也已习以为常。基于网络暴力的现实,《搜索》(2012年)展示了资本主义父权结构在当代中国的霸权。
电影中,一个小事件在媒体炒作和网络暴力的裹挟下无限放大,并将来自不同阶层的5位女性卷入其中。女主角叶蓝秋是一位美丽的秘书,在诊断出晚期癌症后,她倍感绝望。绝望中,她无礼地拒绝在公交车上为一位老人让座。一名实习记者用手机记录下这个事件,并在晚间新闻中播放。最终,事件不断发酵,改写了5位女性的命运。在这一过程中,叶蓝秋的老板、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商业精英沈流舒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沈流舒与这5名女性的互动中,电影揭示了资本主义掩盖下父权的主导力量。
首先,女人被物化为男性事业成功的装饰品,在资本领域,女性的个体价值被转换为一种资本价值。电影开始,沈流舒在第二秘书唐晓华面前评价叶蓝秋姣好的身材,唐晓华回应说:“您要是(把她)带出去啊,不更让所有的老板都羡慕您了吗。”在这里,叶蓝秋的美貌是沈流舒事业的装饰,就如同首饰之于妇女,豪车之于商人。在另一场商业签约仪式上,沈流舒要求妻子莫小渝一同参加。尽管莫小渝怀疑丈夫与人有染,甚至发生争吵,但她还是在宴会上展现出支持、深爱丈夫的好妻子形象。沈流舒跟合作伙伴说这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而当莫小渝私下里指出这并非结婚纪念日时,沈流舒傲慢地回答,“我说哪天就是哪天”。最后,这场恩爱秀被拍下并发布在报纸上,成为提升企业公共形象的公关事件。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莫小渝在签约仪式中的现身,并非出于妻子和女性的身份,而是源自其个体所拥有的为沈流舒企业扫除雾霾、提升形象的资本功能。
其次,男人可以通过资本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维持自己的主导权。在私下,尽管莫小渝怀疑沈流舒与秘书有染,但是沈流舒完全拒绝解释和澄清。讽刺的是,沈流舒关心的并非事实的澄清,而是莫小渝居然向他的男性气概发起挑战。而后,沈流舒停掉了莫小渝的信用卡以示惩罚,甚至拒绝莫小渝的离婚诉求,他说,“敢跟我提离婚,离婚得我说离才行”。在公共领域,沈流舒通过操纵商业来摧毁陈若兮的新闻事业,以报复她在新闻报道中对自己企业声誉带来的损害。面对沈流舒的资本主义父权,莫小渝和陈若兮即便联合起来也无力抵抗。
通过资本的修饰,父权能够明目张胆地表现其霸权,使得男人与女人都默认并接受女性在男性成功面前的装饰功能。而且,在一个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社会里,即便电影结尾暗示了莫小渝离开沈流舒并追求自由,但是鲁迅提出的“娜拉出走以后”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四、结论
陈凯歌并非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女性议题并不是他创作的中心,然而不论是他关注的社会文化,还是历史命运,却都有女性主动参与或被动卷入的身影。在导演创作题材和体裁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随之变迁,而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透露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30多年的身份变化。受启蒙思想的影响,陈凯歌早期电影展现了摆脱封建压迫追求独立的女性形象,呼应了“五四”时代的启蒙精神。随着启蒙的逐渐深入和女性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女性主义批判使得寄生在传统文化上的旧的父权制失去寄生的土壤,在现代性面前其逻辑脆弱得不堪一击。但1980年代末期启蒙退潮以后,女性主体地位又面临父权秩序与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结合的双重挤压,父权借助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庇护,迅疾消解了女性一度争取的独立空间,并轻而易举地将女性询唤为新的为其服务的“主体”,带来了女性自由的新困境。
将视野拓展到世界范围,伴随着社会关系与科学技术的深刻变革,国外女性主义在新世纪重新出现社会运动和文化实践两条腿走路的现象,文化实践领域的银幕影像所探讨的女性议题不断翻新,对多元性别、新的婚姻形态、抗议性暴力、女性个体欲望、解放后的女性迷茫等新内容的探讨也已经走出学术的书斋,在银幕中呈现出色彩纷呈的图景。陈凯歌30多年的电影实践为我国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记录和注脚,展现出其盘旋上升的成长路径。时至今日,相较于国外女性主义电影近20年的灿烂和多样,在国内以女性为主题和欲望表达对象的电影仍然处于少数,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名导演和新导演的电影创作进行研究仍有巨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