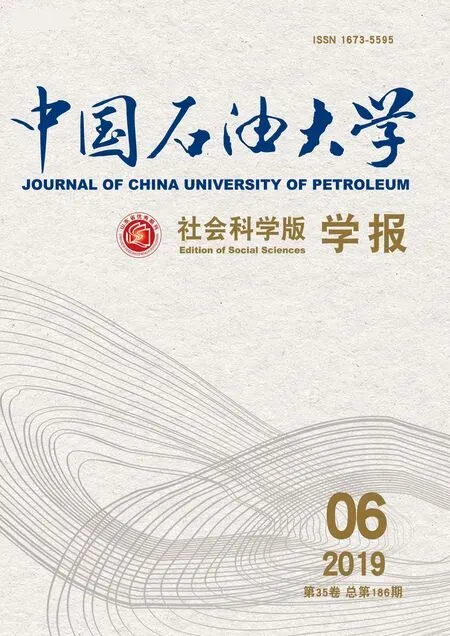好古与忠信:先秦儒者子张与申祥的威仪从政论
石 超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子张,名曰颛孙师,是先秦“子张之儒”的创立者,他仪表堂堂,志在从政,是孔门后期弟子中个性极其张扬的一位。他的一句豪言将这种性格展现无遗:“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论语·子张》)显然,在子张看来,君子之修养若仅停留于“执德”“信道”的层次,还远远达不到他所追求的理想从政人格标准。因为,“有所得而守之太狭则德孤,有所闻而信之不笃则道废”[1]188,这样的人,对于现实世界来说,“不能为损益”[2],“不足为轻重”[1]188,发展到极端,正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3]之流。程树德《论语集释》引《反身录》对此论述得更加透彻,其文曰:“执德是持,守坚定宏,则扩所未扩。信道是心,孚意契笃,则始终如一。既宏且笃,方足以任重致远,做天地间大补益之事,为天地间有关系之人。若不宏不毅,则至道不凝,碌碌一生,无补于世。世有此人,如九牛增一毛,不见其益。世无此人,如九牛去一毛,不见其损。何足为轻重乎?”[4]1302可见,仅仅做到“执德”“信道”,但“碌碌一生”之人,恰如九牛之一毛,其对于现世的事务无所增益。而子张的志向,恰恰在于“做天地间大补益之事,为天地间有关系之人”。对于他来说,“执德”“信道”只是起点,最终目标乃是成就现实的政治事功。而事功的实现,最有效的途径必然是积极投身于实际的政治事务。与此相关,对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政者展现于外的威仪修养的重视,正是子张治学的务外取向之具体体现。
一、禹行舜趋:重视《尚书》、践迹古圣威仪
子张及其后学对于历史及其经验教训非常重视。《论语·为政》篇载子张曾以十分开阔的历史视野向孔子发问道:“十世可知也?”在他看来,“圣人垂教以为天下之经,将俟之百世,而非但为一时补偏救弊之术”[4]131,故而关心“十世”以后的礼仪制度可否预先知道。很显然,他所期望的是一个肯定的回答。果然,孔子不仅以“虽百世,可知也”作为回应,更以著名的“三代损益”之历史事实做论据,对于子张的问题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可见,“历史”对于子张来说,不仅是已经发生的事件之总和,更是儒家之“道”指向未来、并在其中具体落实与展开的经验与凭证。
子张重视历史,便自然会对已经故去的杰出人物之生平事迹感兴趣。《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子张曾以令尹子文、崔子、陈文子三人为贤而三问孔子“仁矣乎”。不仅如此,他对古代圣王的威仪行状,更是欣然向往,这一点集中体现于他对《尚书》的兴趣之中。《论语》一书中唯一一处涉及孔子与弟子讨论《尚书》的语录,即是由子张引出。《宪问》篇载子张之问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答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尚书大传·周传》中有对此更为详细的记载,尤其是对于高宗“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听”的具体行止的记录,正是子张对于古圣先王之“威仪”向往的具体体现。不仅如此,《尚书大传》中还有更多涉及子张围绕《尚书》请教孔子的材料,且这些材料亦与尧舜等圣人事迹直接相关,例如《尚书大传·唐传》篇载“孔子对子张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明显是对《尚书》中所记载的尧以二女“妻舜”,而舜“不告而娶”之事迹的讨论。又如《尚书大传·周传》篇载子张赞叹“尧舜之王”曰:“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则?教诚而爱深也。”则是对圣王治理天下“一人不刑”之“威仪”的歆羡。此外,子张与《尚书》的密切关系,还可从《孔丛子·论书》与《刑论》两篇中的相关记载得到补充证明。综上可知,子张对于《尚书》的兴趣,并不仅仅停留于对普通历史知识的了解(1)关注历史、重视《尚书》不仅是子张一人的思想特色,其子申祥亦不逊之。《孔丛子·居卫》篇载申祥与子思讨论周代先王的事迹,或可看作是其对子张为学特色的继承与发扬。,而是更加注重其中所记载的历代圣王之“威仪”。(2)准确理解和把握“威仪”一词在古典文献中的意义,可参见石超发表于《暨南学报》2017年第10期的《品貌与人格:〈诗经〉“威仪”政治话语研究》。
子张效法古人“威仪”之方法,亦是从模仿、复制古人之礼仪、礼容,甚至书中所载圣人形躯之动静作为起点的。这一点,在《论语·先进》篇“子张问善人之道”章中有充分体现,孔子对此问的回应是“不践迹,亦不入于室”,提点子张“当践迹乃能入圣人之室”[4]786。但对于这句话的具体内涵的诠释,历代解说颇为模糊,其关键在于“践迹”一词何解,《集解》引孔安国释“践”为“循”,释“迹”为“旧迹”,皇侃所疏与之相同,而朱熹《集注》则引“程子”之言将“循其旧迹”引申发挥为“循途守辙”[4]785。但笔者认为,将“迹”之外延扩大为“途辙”的同时,亦不应忘记“迹”字之本义。许慎《说文解字》载“迹,步处也”,段玉裁注曰“夫迹,履之所出”[5]。由此,“践迹”可解为“践履圣人的脚印”,也就是让子张对文献中所记录的“善人”一举一动都要亦步亦趋,甚至连其如何留下“途辙”与脚印的方式都要模仿。而荀子以“禹行而舜趋”(《荀子·非十二子》)一语对其大加批判,其理论的根据即是抓住了子张之儒“礼容实践”[6-8]这一特点。然而必须澄清的是,学界历来认为荀子是在批评子张本人,但荀子并未直呼子张之名,而是称“子张氏之贱儒”(《荀子·非十二子》),由此来看,荀子的矛头应是指向那些与自己同时代的子张学派之后学末流[9]。这是因为那些距离子张相去上百年的后人,大概丢失了理论思维的能力,对于先师的遗言进行了极端教条化、表面化、庸俗化的理解,将“践迹”的全部意蕴局限于其字面意义,并将其落实于日常的行动之中。其实,孔子的用意显然不限于此,而应是教诲子张通过模仿圣人的“威仪”,进而感知圣人之用心,“践迹”只是手段,“践其所以迹”才是目标。当然,这些子张后学对于实践圣人之“迹”的极端强调,亦可从侧面反映出子张本人对于古圣先王之威仪修养的深切关注。总之,从《论语》和《尚书大传》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在子张之儒与早期《尚书》学之间存有某种密切的联系。
子张重视历史与古代圣王之容止,并非仅仅是要在效法古代圣王的前言往行的基础上返古、复古,而是要以其所体现的指向未来的儒家之“道”为鹄的。顺此思路,再看《论语·尧曰》篇,作为今本《论语》的最后一篇十分简短,仅仅三章,其中唯一出现的孔门弟子即是子张,而且首章依次提到的尧、舜、禹、汤(3)按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由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的《论语集释》,本章“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句中的“履”字,为商汤之名。、武王(4)按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由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本章自“周有大赉”以下,朱熹《集注》以为“述武王事”也。等圣人,皆为《尚书》中的核心人物,与子张重视《尚书》的历史情结若合符契。有学者推论,在《论语》的成书过程中,《尧曰》一篇当为子张之儒所提供。[10]99-137我们或许还可以进一步将提供者锁定于子张之子申祥。首先来看该篇第一章:“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又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其中,“躬”与“执其中”两处用语体现了子张及其后学极端重视礼容、威仪对于身体之呈现与运作之规训。而《尧曰》中所载圣人以己身“承天之数”、以己身“赎民之罪”,正是子张之儒落实“摄威仪”之修身取向的最终理论根源,亦是对前文所论“践迹入室”的具体体现。
更有趣的是,“执其中”一语亦在《孟子》一书中以“执中”的形式出现过,其主张者被孟子称为“子莫”,与之相提并论的有杨朱与墨翟,争论的焦点则在于三者对待身体的不同方式:杨朱珍爱身体,走向极端,竟“一毛不拔”;墨翟轻身重利,若能“利天下”,则不惜“摩顶放踵”;子莫则不偏不倚,恰“执”二者之“中”。对于前二者,孟子持彻底的批判态度;而对于子莫,则曰“执中为近之”,乃是有所保留地接受,由此可知,子莫当属儒家者流。关于子莫,可参考《说苑·修文》中提到的“颛孙子莫”。向宗鲁《说苑校证》曰:“颛孙子莫即《孟子·尽心上》篇所云‘子莫执中’者。”[11]子莫以颛孙为氏,当与子张(颛孙师)关系密切,而据钱穆先生所称“颛孙合言为申”,推断子莫当为儒家文献中经常被当作子张之子的“申祥(详)”,其本名应为颛孙祥(详),而“子莫”则是他的字[12]。以下是《说苑·修文》中与子莫相关的文献之全文:
公孟子高见颛孙子莫曰:“敢问君子之礼何如?”颛孙子莫曰:“去而外厉,与而内色胜,(与)(5)“与”字为笔者根据文意补充。所引原文为:“去而外厉,与而内色,胜而心自取之。”断句似有误,笔者倾向于将其断为“去而外厉,与而内色胜,(与)而心自取之”,理由有三:后文“色胜”一词连用,故此处不应断开,此其一;其二,“外厉”“内色胜”“心自取”恰可构成引文中子莫所谓当“去”之“三者”;而此“三者”又可与《忠信之道》中“忠人弗作,信人弗为”之“三者”一一对应,此其三。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见后文。而心自取之。去此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厉者必内折,色胜而心自取之者必为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闻识博而辞不争,知虑微达而能不愚。”
可见,此处颛孙子莫对于“君子之礼”的论述,亦落实于君子修养之身体威仪面相,正可解释前文孟子所谓的子莫那种“执中”身体观。其中所谓“外厉、内色胜、心自取”,三者皆非君子威仪所应有者,故应“去”之。而曾子所谓“德行成而容不知,闻识博而辞不争,知虑微达而能不愚”,正是对颛孙子莫教人“去此三者”而“执中”的身体规训与威仪修养方式的高度肯定。
综上,从子张对古圣先贤之“威仪”的重视,到《尧曰》篇的圣人之“躬”与“允执其中”,再到《孟子·尽心上》篇的“子莫执中”,最后到《说苑·修文》篇的去“外厉”、去“内色胜”、去“心自取”,其间所具有的明显且连贯的历时性演变与内在一致性,均是以对古圣先王之“威仪”的效仿为前提而落实于身体的君子修养论。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子张之儒作为孔子殁后的一大儒学支派,其为学特色即在于重视历史,尤其是《尚书》中所描述的圣人之“威仪”,而其具体的为学取径,则是努力效法古之圣贤,既包括外在容仪的呈现,也包括身体动姿的运作,并以此作为对孔子“不践迹,亦不入于室”的“善人之道”的身体力行。
二、忠信仁义:《成之闻之》《忠信之道》《唐虞之道》
虽然极力效仿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圣人“威仪”是子张之儒的治学特色,但是在这种外在模仿背后,我们隐约看到一种非常深刻的从政理念。遗憾的是,由于文献不足之故,再加上荀子等后儒极力夸大子张后学末流“务外”而“无本”的缺陷,甚至径自斥之为“贱儒”的做法,致使后人忽略了子张之儒更为深刻的理论思考,并最终使之湮没。
“郭店楚简”的出土,使得子张之儒被重新认识与再评价成为可能。据王博先生分析,在这批文献当中,《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性自命出》《尊德义》与《六德》诸篇之著作权均应归入子张之儒的名下。[10]170-189尤其是《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两篇,在笔者看来其属子张之儒当为不易之论,而《成之闻之》一篇,亦与子张之儒渊源颇深[13]。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即是其在行文过程中对于《尚书》文句的反复征引(6)据200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李零所著的《郭店楚简校读记》可知,《成之闻之》引用《尚书》之处依次如下:(1)《大禹》曰,“余兹宅天心”何?(2)《君奭》曰,“襄我二人,毋有合在音”何? “槁木三年,不必为邦旗”何?(3)《(讠吕)命》曰,“允师济德”[何]?(4)《君奭》曰:“唯冒丕单称德”何?(5)《康诰》曰“不还不戛,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何?,这与子张、申祥对于历史、《尚书》的重视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除此之外,《成之闻之》所论皆为从政者应该如何克己修身进而如何安民治国之“身体-政治”问题,这显然是子张之儒对于孔子“政者,正也”的君子威仪正身观之继承与展开。换言之,子张之儒对于君子威仪修养之重视,并非仅仅停留于对古圣先王之外在形迹的盲目崇拜与机械模仿上,而是有着现实的政治事功之指向。换言之,从政者唯有以身作则,方能“导民”向善,即所谓“上苟身服之,民必有甚焉者”“上苟倡之,则民鲜不从矣”。具体而言即为“君袀冕而立于阼,一宫之人不胜其敬。君衰绖而处位,一宫之人不胜其哀。君冠胄带甲而立于军,一军之人不胜其勇”[14]121。这段论述也正是对于《论语·颜渊》篇中“君子德风”“小人德草”之比喻的具体阐发,而君子之德之所以能使“草上之风必偃”,关键即在于其“有信”。对此,《成之闻之》篇载文曰:
君子之于言也,非从末流者之贵,穷源反本者之贵……故君子所复之不多,所求之不远,窃反诸己而可以知人。是故欲人之爱己也,则必先爱人;欲人之敬己也,则必先敬人……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行不信则命不从,信不著则言不乐。民不从上之命,不信其言,而能念德者,未之有也。故君子之莅民也,身服善以先之,敬慎以守之,其所在者入矣。民孰弗从?形于中,发于色,其诚也固矣,民孰弗信?是以上之恒务,在信于众……信于众之可以济德也。[14]121-122
显然,子张之儒之所以重视“发于色”的君子人格之威仪呈现,正是因为它能够直接体现君子“形于中”的“诚”与“信”。而以“信”作为“莅民”者从政之本的理念,亦是子张得之于孔子,并由子张之儒发扬光大。《论语·阳货》篇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得到的回答是“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即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其对于“信”的解释——“信则人任焉”——显然是针对子张的气质特点与其为学志向而专从莅民、从政的角度进行立论的。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条语录本身就是由子张之儒“润色”,“甚至傅益”[15]。虽然“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所教诲的对象乃是全部孔门弟子,并非专为子张而发,但子张对其中的忠、信特别重视,亦是不争的事实。在《论语》中,“忠信”作为固定搭配,共见四次,而其中两次是针对子张而发,这样的概率绝非出于偶然: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子罕》)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
子张问崇德……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
前两条为孔子自述,后两条则子张问、孔子述,子张为唯一受者,这很有可能是由子张之儒提供并最终被写进《论语》。由此,亦可见子张之儒对于“忠信”的极端重视。而前引《成之闻之》的内容,则可看作是对这种“忠信”之理论主张的演绎与铺陈。
子张之儒重视“忠信”的特点及其对于“忠信”的独特理解应该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因为“忠信”虽为儒家通义之一,但其在儒家理论中的品级并不突出。这一点,在孔子思想中有所体现。《论语·子路》篇载孔子之言:“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阳货》又曰:“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显然,在孔子那里,“信”作为一个道德条目,并没有什么突出的优势。而后来的孟子,明确继承且放大了孔子的这一看法。《孟子·离娄下》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尽心下》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在孟子“善—信—美—大—圣—神”之君子人格修养梯次中,“信”德明显地处于一个较低的品级。
与孔、孟不同,子张之儒将“忠信”之德的理论品级提拔到了罕见的高度,他们以“忠信”配“天地”,大有视其为君子修养之本的意味。这一点在“郭店楚简”《忠信之道》一篇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述:“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是故古之所以行乎蛮貊(7)此二字简文较为难辨,今从王博引赵建伟作“蛮貊”。见王博《中国儒学史·先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76页。者,如此也。”[14]100其中“古之所以行乎蛮貊者,如此也”一句,显然是本之于《论语》“子张问行”章,是对孔子“言忠信,行笃敬”之教的引申发挥,这为我们将其划归于子张之儒所著,又提供了一条文献学的支撑证据。而其中“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基)也”的中心思想极具代表性。考察该篇文献前文所论,亦是对所谓“主忠信”“言忠信”之旨的铺陈与发挥,请再看该篇第三节:
口惠而实弗从,君子弗言尔;心[疏而貌](8)此三字原文脱落,根据李零校读补。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00页。亲,君子弗申尔;故行而争悦民,君子弗由也。三者,忠人弗作,信人弗为也。[14]100
其论“君子”所“弗言”“弗申”“弗由”之“三者”,恰可与前引《说苑·修文》载颛孙子莫(申祥)所谓“君子之礼”有“三去”相互呼应。具体讲,去“外厉”,对应着君子“弗言”之“口惠而实弗从”;去“内色胜”,对应着君子“弗申”之“心疏而貌亲”;去“心自取”,对应着君子“弗由”之“故行而争悦民”。这不仅可以进一步证明该篇文献属于子张之儒所作,甚至更可以推断其与申祥本人有关联。而且,这篇文章对于“忠信”的阐发,在先秦文献中独树一帜。其以“忠”为“仁之实”,“信”为“义之基”的讲法,显然与孟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之安排完全不同,且二者所述“信”与“义”之本末关系恰好对调。与孟子相比,《忠信之道》已然是将“忠信”放在了比“仁义”更具根本性的地位。更甚者,在《忠信之道》的作者看来,“忠信”乃与“天地”齐,即所谓“至忠如土”,“地也”;“至信如时”,“天也”。具体讲,“大忠”,“不说而足养”,其德似“地”;“大信”,“不期而可遇”,其德似“天”。这样的安排似乎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其所适用的修养主体正是那些为人臣者之“威仪”。一方面,人臣之上有人君,面对人君,其“威仪之则”以“忠”为主,恰如“地”之在下,“不讹不孚”“化物不伐”“久而不渝”,能使“百工不楛,而人养皆足”;另一方面,人臣之下有百姓,面对百姓,其“威仪之则”以“信”为主,恰如“天”之在上,“不欺弗知”“毕至不结”“陶而睹常”,能使“群物皆成,而百善皆立”。“君子如此”,方能使民“亲信”,而“不忘生,不倍死”。[14]100
可见,子张之儒对于“忠信”的高度推崇,与其重视事功、积极从政的为学理念一以贯之,其理想人格同时具备对上“忠”与对下“信”之双重面向。而在儒家所推崇的上古圣人之中能以一人之身同时做到至“忠”、至“信”者,也许只有虞舜。恰巧,在“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名为《唐虞之道》的文献正是以虞舜作为核心人物,而与《忠信之道》构成“姊妹篇”,它们不仅竹简形制完全统一,就连抄写字体亦无差别,李零即认为二者可能“抄于同一卷”[14]100;而且两篇之间的各种一致性又与同时出土的其他各组文献明显不同,这就更能说明“它们的来源可能相同,或者原本出于同样的作者(9)如果《忠信之道》与申祥关系密切,那么《唐虞之道》势必与之同然。”[10]173;从思想内容之方面来看,两篇文献之间亦存在互相发明、前后呼应的关系,如:《忠信之道》曰“其言尔信,故亶(禅)而可受也”,这显然是针对虞舜接受唐尧禅让之历史记载而言的;《忠信之道》曰“信,义之期(基)也”,《唐虞之道》则曰“禅,义之至也”,[14]95亦即“义之期(基)”为“信”,及其“至”也,具体表现为“禅”,正是以“信”德作为禅让的前提,而禅让则为“信”德之实践。显然,《唐虞之道》花费大量篇幅描写、赞美虞舜之形迹、德行,正是为了印证《忠信之道》篇对于“忠信”之德的反复褒扬。而《唐虞之道》对于虞舜之德的赞美,集中于“极仁之至,利天下而弗(自)利也”一句,概括地说,即是“禅而不传”。具体的做法(“尧舜之行”),则是“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孝之施,爱天下之民”,“孝,仁之冕也”;“尊贤故禅”,“禅之传,世亡隐德”,“禅,义之至也”。圣人者,“必正其身”以仁义,“然后正世”,“六帝兴于古,皆由此也”。仁与义不可偏废,若“爱亲忘贤”,则“仁而未义也”;若“尊贤遗亲”,则“义而未仁也”。[14]95
由此可见,在子张之儒的理论架构中,“禅而不传”的根据在于“爱亲”之“仁”与“尊贤”之“义”,而“仁义”的实质内容,又最终归结、落实于“忠信”。
三、正言必行:子张之儒的为学特色及其原因分析
综上所述,“郭店楚简”中的《成之闻之》《忠信之道》《唐虞之道》均可能属子张之儒的作品,而三篇文献之共同点,则在于对子张“修身(摄威仪)以从政”之治学理念的铺陈,其理论上的创新,则在于特别拔高“忠信”之德,并阐发了“忠信“在从政者修养中的特殊地位。而三篇文献在共同阐发子张之为学宗旨时,各有侧重、各有分工:《忠信之道》是以一种形而上的思考方式对从政者所应具备的“忠信”之德进行讨论;《成之闻之》则是将其落实于具体的政事环境中加以展开和说明;《唐虞之道》则通过突出虞舜在古圣先王中上事唐尧、下禅夏禹的特殊历史地位,将从政者所应具备的理想人格加以落实,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理想模型。由此,我们清楚地体察到,正是子张之儒对于构造从政理论的兴趣以及其积极投身现实政治的特质,才使其能够在孔子殁后异军突起,并保持其影响以至战国末世。
而子张之儒与儒家内部其他派别的最大不同,即在于其将“忠信”看得比“仁义”更为重要和根本,这一方面根源于其以政治哲学的进路发展儒学的特质;另一方面也是对时代潮流所提出的现实要求之积极适应。这两方面的原因其实可以归结于一事,即是以申祥为代表的子张之儒所普遍具有的实际身份。《孟子·公孙丑下》载:“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朱熹《集注》曰:“二子义不苟容,非有贤者在其君之左右维持调护之,则亦不能安其身矣。”[1]249杨伯峻《译注》将其翻译为:“如果泄柳、申详没有人在鲁缪公身边,也就不能使自己安心。”[16]可见,以申祥为代表的这一批子张之儒,曾经积极活动于鲁国的朝堂之上,且与国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在《孔丛子·居卫》《抗志》两篇文献的材料中亦能得到支持,而王博则进一步将这种联系落实为申祥“在鲁穆公的朝廷中服务”,其身份则是“臣子”[10]167。
辨明了申祥作为人臣的身份,可以加深我们对子张之儒“摄威仪”“主忠信”之治学特色的理解。显然,与周游列国而终不能得君行道的孔子、孟子不同,子张之儒作为人臣,在提出、建构理论之时,必然会受到更多现实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对于广义上的儒家理论亦必须有所侧重与选择。因此,子张之儒才不得不采取了将“忠信”凌驾于“仁义”之上,并将仁孝、尊贤、亲亲之儒家通义导向“爱天下之民”而主忠信的轨道之上。这也难怪很多学者倾向于将子张之儒的主张类比于墨家的“兼爱”“尚贤”等,甚至还有学者将《唐虞之道》划归墨家(10)值得说明的是,这种以子张之儒近于墨家的观点并非近世之说,而是古已有之。例如,据郭沫若分析,《荀子·儒效》篇载“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即是针对子张之儒而给予的批评。见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29页。《庄子·盗跖》篇作者借子张之口称赞仲尼、墨子曰:“仲尼、墨翟,穷为匹夫,今谓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则变容易色称不足者,士诚贵也。”亦可说明在《盗跖》篇的作者心目中,子张之儒与墨子亦具有某种相似性,由此来看,对于二者关系的深入考察将是另一项值得深入的课题。,这些观点虽偏颇却亦有其道理。
至此,我们对于子张学派的两位最重要先儒之思想作出了较为详备的介绍与分析。在本文的最后,似乎有必要对他们的思想特色作出更为精练的概括。笔者以为,《庄子·盗跖》篇“子张问于满苟得”章,以寓言形式旨在批驳子张之儒的材料中,却以最为精练的方式概括了其治学之大纲。请看其文所载“子张”之言:
盍不为行?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义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则夫士之为行,不可一日不为乎……子不为行,即将疏戚无伦,贵贱无义,长幼无序;五纪六位,将何以为别乎?
本段文献以“行”发端,其所对应的正是前文所引《论语·卫灵公》篇中的“子张问行”章,而与“行”相涉之“信”“任”“利”“名”“义”以及“六位”等概念,无一不是本文所提到的子张之儒的文献所极端重视者,可见《庄子·盗跖》的作者对于子张之儒的思想、作风颇有了解,若非亲眼所见或深有研究者不能及此。不仅如此,该篇作者更能直指子张之儒的核心思想,并且给予颇为深刻的批判与辛辣的讽刺,其文曰:
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祸也;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鲍子立干,申子自埋,廉之害也;孔子不见母,匡子不见父,义之失也。此上世之所传,下世之所语,以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离其患也。
此文以高度凝练的排比修辞再次提到了“忠”“信”“廉”“义”以及“正其言必其行”等概念,不仅与本文所论若合符契,而且再次印证了《忠信之道》等三篇“郭店楚简”中的文献当属子张之儒。显然,《庄子·盗跖》这篇文献虽是批判,但对于子张之儒的核心主张之把握,不可不谓精到。
总之,在《庄子·盗跖》篇“子张问于满苟得”章之作者看来,子张之儒极度崇尚“忠”“信”之德,落实于行动,则要求学者“正言必行”。唯有贯彻此“行”,才能博得上下之“信”,进而出仕“任”职;相反,若违反此“行”,必将导致“疏戚无伦”“贵贱无义”“长幼无序”。而后者不仅损害“行者”个人之“利”益与“名”声(11)对于令名之追求,乃为儒学之通义,这一点在孔子的思想中即有鲜明的体现,如《论语·里仁》篇:“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卫灵公》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更会导致国家、社会“五纪六位无以为别”之严重后果,进而破坏天下之大“利”,引发天下之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