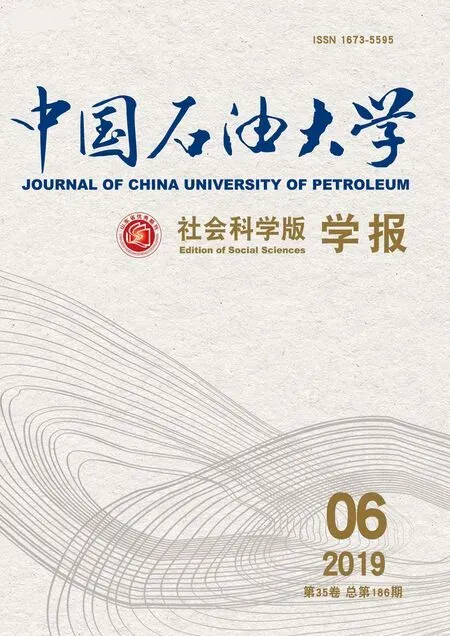世界政治话语转型视阈下“社会”的理论角色演变
张 会 芸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确定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之分在传统社会中并未出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原本混合一体。近代以来,随着社会从政治国家概念中渐次离析出来,政治学研究的国家—社会二元分析路径才逐步定型。在此前提下,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不能仅理解为国家这一政治实体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自主性过程,它同样也是与现代国家相对应的社会不断发展与演化的过程。国家与社会间的冲突、妥协甚至相互包容的关系是贯穿现代政治研究进程的主线之一,也构成了政治学理论的基本面向。本文梳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学领域中“社会”的理论角色演化,自“社会”这一面向出发更清晰地把握世界政治秩序的起伏与政治话语的转型,也期望对我国当前政治改革实践有所裨益。
一、自由民主秩序扩张视阈下的“社会”角色:反国家主义的公民社会
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自由民主秩序以强势的胜利姿态向非西方国家渗透与扩张,席卷全球的非民主制度向民主制度的政治转型拉开了序幕。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将这场始于1974 年葡萄牙军事政变的全球民主化运动视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1]而关注全球政治发展的拉瑞·达尔蒙德(Larry Diamond)也断言这个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段应被视为现代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民主躁动时期。这场民主躁动是西方自由民主秩序全球扩张的表现,也正是在这场民主躁动中,“公民社会”理论复兴。[2]促成公民社会复兴的直接原因就是处在民主化浪潮中的东欧与苏联国家为摆脱斯大林“万能国家”政治模式而发起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公民社会”理论在一系列运动中承载着反国家主义的积极理想,表达了自下而上地创建非国家主导之独立生活方式的愿景。
公民社会理论建基于西方政治学对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认知判断与学术传统。17至19世纪,欧洲各国不同的学术传统为公民社会理论提供了精神内核与外在形式。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认为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是政府成立的逻辑起点,自然状态下的个人首先签订社会契约,达成遵从多数人意见行事的规则共识,进而依据多数人意见将权力委托给政府。在洛克的表述中,公民社会与虚拟的自然状态成两元对立,与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国家(Commonwealth)等在概念上基本同义。政府作为公民社会的核心特征,改变了自然状态下的人人为政与潜在的战争威胁。如同洛克,17、18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们笔下的“公民社会”等同于国家,与当前的理解存在一定差距,但他们关心个人权利的保护,同时主张一种对政府形成潜在威胁的个体群集——“社会”——的先在性,这种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国家—社会二元分立的政治分析框架及当代“公民社会”的精神内核。[3]19世纪源于英语世界的“公民社会”概念传到德国,“公民社会”概念开始与“国家”概念分离,并被赋予了新的意涵。在黑格尔笔下,市民社会(1)该节中笔者交替使用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德文“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译为“市民社会”已较为固定,英文对应“civil society”。在中文语境中,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存在细微的区分,前者突出“公民”的政治权利与自主意识,在政治学领域更为常见。概念的进一步清晰化可参见姜涌《德语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及其在现代的汇合》(《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由非道德的因果律支配,在伦理层面表现为不自足的状态;黑格尔寄希望于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补其不足,换言之,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国家是市民社会奔赴的目标。到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与“国家”进一步分化,市民社会在时间维度上为人类社会特定的发展阶段,具体则指私人的物质交往关系,指与政治领域对应的存在的私人活动领域。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政治国家终将统一于市民社会,实现人类解放。“市民社会”理论的德国传统与当代多数公民社会研究者的基本价值取向不同,然而当今理论界关于公民社会与政治领域的界分却从中获益。18、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则以“社会制约权力”的切实内容填充了当前“公民社会”的内涵,如孟德斯鸿指出在君主政体中,贵族群体和社会团体的存在会制衡君主权力、维护社会自由;托克维尔则在此基础上表明拥有自主权的多元社会对国家压倒性的强制权力产生制衡作用,独立的报刊及出版物、自由的政治结社以及普遍的乡镇自治组织等能够抗衡国家对社会的过度侵占,维持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
当前公民社会理论的代表性学者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人致力于探寻良善制度和积极公民相统一的理想公民社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17世纪以来公民社会理论的一种融汇和创新。复兴的公民社会理论以自由民主秩序为基本倡导,大致以个体权利与政治权力二元对立为基础格局。在这个理论格局中,公民社会是在权利与权力、个体与国家的对立中形成的中间概念。公民社会理论阐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公民社会的根本旨趣在于保障或增进其个体成员的利益或价值;其次,国家之外存在个体的集群——社会,国家以整体秩序的稳定为首要目标,而社会则将保护个体利益作为第一目标,两者间存在冲突的必然性;再次,国家为了维持秩序会对社会进行渗透和控制,社会则为捍卫自主空间扮演着对抗国家强权的激进角色,两者呈现为充满对抗色彩的动态交锋。正如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言,复兴后的“公民社会”是一个与国家相对的比较性概念,它独立于国家并部分对立于国家。公民社会,从底线意义来看,在国家与个体之间设立了一面屏障,使公民社会内成员的个体利益免受或少受国家权力的直接侵害;从积极意义来看,也可被视为个体与国家间进行信息交流和传输的传送带,活跃有效的公民社会形成对个体利益的凝聚性表达,并使其进入政治系统的运作过程。
作为公民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公民”是与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思想深入人心相伴随的,是与现代国家的发展相伴而生的。公民社会理论在处理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抗关系时分离出具有公共性与私人性双重身份的“个体”,在受保护的个体权利与受牵制的政治权力间抽离出“公民”这一概念以承载个体的公共性(包括政治性),个体成为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人。[4]公民对政治的参与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对个体私人领域的保护程度。民主转型与民主发展多被认为需要理性公民加以支撑,理性公民应能有效表达自身的利益和要求,维护自身的自由和权利,进而平衡国家权力的强势。当所有公民能够自由、平等、有效地参与政治时,政府的责任性与回应性就最高,对个体私人领域的侵犯也降至最低。近年来,西方学者关注公民及公民身份的研究,公民身份(citizenship)更“成为西方社会科学讨论的主要新领域”,[5]他们强调公民应保持相当的政治兴趣与政治参与热情,具备如协商、游说、辩论等政治技能,同时主张公民应具备较强的公民意识和公民风范,并内化为态度、气质、性格及行为习惯。公民社会则承载着公民培育及公民联合的关键责任。
然而,政治学领域中围绕反国家主义、亲个人主义衍伸而成的公民社会理论潜存着逻辑困境。民族国家的建构本身是政治现代化的关键标志之一,个体被剥离出自然的、传统的关系网络(如等级、血缘、宗教等关系),并安置于“国家”这一政治实体中,成为平等之“国民”(nationals)。然而,脱离自然社群的“国民”与主权在民等观念捆绑,内含着更具普遍性的特质——平等的权利与义务,驱使个人走向自由、民主、法治观念,铸成“公民”(citizens)的身份认同。本质上而言,公民与现代民族国家同气连枝、相伴而生,但它拥有现代民族国家难以吞噬消化的权利硬核,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内,公民社会理论本意在于提防国家强权以保护弱势的个体,潜存着消解国家界限、冲破国民身份的嫌疑。更进一步而言,公民社会理论以个人主义为本位,所谓“个人”是典型的抽象假设,是普遍主义的原子式个人,这种个人主义倾向将普遍性、抽象性的个人自由置于共同体之上。基于此,西方政治学在惯常的理解中将公民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视为个人对国家所要求的首要正当权利,而个人对社会与他人的责任以及社群规范对个体的约束力却被后置。换言之,对个人平等权利的强调还可能使得公民社会的“社会”角色存在被自我消解的风险。既消解理论对手(消解国家)又自我消解(消解社会)的内置困境潜在地推动西方政治学领域中“社会”的理论角色认知悄然调整。
二、自由民主秩序内顾视阈下的“社会”角色:反个人主义的社会资本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其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意识形态争论很大程度上被搁置,西方对自由民主秩序的乐观主义态度一时间在学术界弥漫,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提出“历史终结”的断言。西方自由民主秩序在既自满又保守的心理状态下内顾自身,对“社会”理解呈现出与公民社会理论的激进对抗色彩全然不同的温和与柔性特质。
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现代化进程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相对紧凑的社群生活,强调个性的科技发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日常生活,使得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倾向进一步加剧,重塑社会凝聚力成为学术界新的理论诉求。20世纪80年代末,桑德尔、麦金泰尔、沃尔泽等代表的社群主义理论强调社群共同利益,反对个人主义的过度发展。某种意义上,稍晚些的社会资本与社群主义一样是个人主义的主导范式式微的替代物,社会资本研究也被称为“新社群主义”(Neo-communitarianism),其核心理念在于弥补当今社会中个体过度关照私人生活的倾向,但社会资本于实证研究上的突出表现是作为政治哲学的社群主义无法比拟的,它顺应美国乃至全球政治科学研究的大势所趋,基于数据直观呈现的社会生活凋敝图景因其非同寻常的时代契合性一经提出便获得广泛共鸣,导致“社会资本”从学术研究蔓延至政策辩论与大众视野中。
与前述趋势同时段,部分也因为“历史终结”的乐观情绪,西方政治学研究的话语接力也在进行。在“民主”成为政治共识的基础上,政治学研究出现了由“主义导向”到“问题导向”的一系列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其研究重心从制度的选择与确立悄然走向制度的运转与效率问题,当然这种研究的话语接力也影响了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以“治理”(governance)为代表的知识话语将这种趋势体现无疑,更引导了政治学界的理论重组。此前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多以政治体制的建构或政治秩序的稳定作为分析对象,侧重分析民主制度的构建与合法性证成;新兴的“治理”研究尽管缺乏统一的认知,(2)治理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罗伯特·罗茨(Robert Rhodes)详细列举了六种关于治理的不同定义。这六种定义是:(1)作为最小国家的管理活动的治理,指国家削减公共开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2)作为公司管理的治理,指指导、控制和监督企业运行的组织体制;(3)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指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4)作为善治的治理,指的是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5)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指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6)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6]但相比既有的政治学理论,研究重点发生了明显转向:政治与行政二分建构的理论空间趋于融合,“效率主义”这一行政学的价值标准被引入政治学的研究视野,政治学领域的规范研究开始强调民主与效率相结合,于技术上亲和管理主义。[7]在政治学的知识话语从“制度”向“治理”转向之际,制度构建导向下的公民社会理论所塑造的“社会”角色具备鲜明的反国家主义色彩,针对体制运作的效率而言自然解释力不足。某种程度上而言,社会资本概念正像是为了弥补既有的公民社会理论解释政治运作效率的不足而引入政治学的。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为代表的研究者顺应学术发展潮流将“社会资本”一词从经济学引入政治学,其原因更多是受到该词内在的功能主义的诱惑。此后,政治学领域的社会资本研究者们尝试把社会资本打造为一个政治绩效的解释性概念,以此修补甚至超越既有“社会”角色理解的解释局限。在此基础上,社会资本的运作逻辑不在于重回以国家—社会二元对立为底色的政治系统论,而是迎合政治学知识话语的“治理”转向,提出了突破集体行动困境的政治绩效解释机制。
社会资本属于“本质上具有争议性的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8]学界很难达成较高的共识。借用芬尼·亚当(Frane Adam)以及博鲁特·阮赛维可(Borut Roncevic)在梳理社会资本概念乱象时的研究态度,隐身于社会资本多元“表象”背后的“基因”要素才可真正认定为社会资本。当前政治学界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多有差异,但多数研究以粗略的A+B形式指称社会资本,即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主要由主客观两种要素构成,一为客观的社会网络和组织, 二为主观的社会信任与互惠规范,本意指称相对高频的社会生活与较为融洽的社会氛围。由此而言,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理论均力图展示一种对社会秩序的道德理想,但两者的理论指向全然不同。公民社会理论以个人主义为本位,是在与强大国家权力的对抗语境中逐步成型并成熟的理论,它强调的是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所谓个体的消极自由为最高价值。换言之,公民社会理论需要一个与外在国家暴虐权力对立的立场作为思考问题的先在设置。然而,在民主制度成型并成熟的背景下,或曰“利维坦”被成功驯化时,公民社会与其对抗的国家实体间关系逐渐趋于缓和,强调个人主义至上的公民与公民间粘合度也随之降低。公民社会研究复兴近20载后,社会资本以新面目出现于政治阐释中并吸引了学术界的众多目光,正是接力般地关注到有别于既往公民社会研究的理论盲区。
具体而言,社会资本理论所针锋相对的理论敌手中没有“国家主义”。区别于20世纪70年代末东欧国家体制改革与全球民主化浪潮对公民社会研究复兴的理论需求,社会资本理论进入政治学领域的理论背景或前提就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稳定与巩固。如戴特林德·斯托利(Dietlind Stolle)所言,“公民社会”兴起于反国家主义浪潮之中,而社会资本在反个人主义的浪潮中诞生。[9]作为社会资本的概念之父,罗伯特·帕特南最负盛名的著作《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便带着浓重的怀旧愁绪,浪漫化了过去时代的社会想象,并以此批判过度个人主义造成的社会散沙状态。社会资本理论也是在认清个人主义的种种问题后,才尝试引导人们走出家门投入更多的社交与公共生活。如果说公民社会要塑造一种政治意涵上的参与型公民,那么社会资本理论在内部效应上弥补了公民社会理论相对弱化的道德与伦理的含义,着意强调塑造“社会人”。因反个人主义的基本立场,社会资本理论的历史厚度与哲学深度(3)国内学者黎珍从政治哲学视角细致解读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与平等、自由、正义、和谐等多重政治哲学原则相互照应,对此笔者不能认同。社会资本理论在过去20年的时间中迅速崛起,与时代的理论需求紧密结合,它恰恰缺少相应的哲学深度,而黎珍的研究存在过度解读的嫌疑。 参见黎珍《正义与和谐——政治哲学视野中的社会资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多来自于法、德的社会学传统。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心灵习性”、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关于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阐述、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关于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等多被视为社会资本的智识来源,相关引述多重合于社会学界关于“共同体(community)”一词的演进史叙说。社会资本理论力图证实信任、宽容、合作、团结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是重要的,其相对于既有的公民社会理论而言,社会资本理论的创新性之处在于以托克维尔所谓的“心灵习性”或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的“社会气质”(ethos)[10]填补了公民社会脆弱的伦理观,或如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所言,逆转了公民社会的空洞化。[11]社会资本在此意义上被视为公民社会的粘合剂、道德伦理软件或者文化柔和剂,它体现出公民社会理论中未被重视的一面,并使其进入了学术主流话语。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政治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理解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公民社会研究对国家—社会此强彼弱甚至针锋相对的固有分析进路。不同于公民社会理论对政治权力的提防,社会资本理论忧心过度私人化造就的社会行动陷阱与政府管理困境,更关照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社会团结等民情的培育,形成了社会强则国家强的双赢阐释。可以说,社会资本的宏观政治效用研究是马克思·韦伯关于宗教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命题的回声,其思维方式需要实现从社会学领域到政治学领域的转换。目前,社会资本被认为多体现在那些将家庭、朋友、邻里、工作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中,家庭聚餐、拜访亲友、打牌娱乐、邻里互访等非正式的社交形式均被视为社会资本的体现,这些带有明显“去政治化”(depoliticalised)特质的元素如何影响政府运作及政治绩效仍是政治学领域中社会资本研究亟待解决之事,社会资本理论以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为核心的经济逻辑能否完成在宏观政治领域的套用,成为社会资本在政治学界推进的关键难题。[12]从另一侧面讲,政治学领域中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却是对17世纪以来国家—社会二元对立之分析模式的反叛,也是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政治系统论的反叛,这种反叛使原先治理主体(国家)与治理客体(社会)间界限分明的关系被打乱,使得治理者与被治理者间的边界模糊化,政府成为被包裹在社会氛围中的虚化形象。西方学术界在对自由民主秩序过分自信与自满的情绪支配下反而淡化了对民主政治程序与制度建设的关注度,在效率主义的支配下开拓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解的新视角,间接影响了非西方国家的研究取向。
三、自由民主秩序退守视阈下的“社会”角色:反多元文化主义的国民社会
近年来,自由民主秩序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2010年左右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效应外溢,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政权相继更迭,然而,这场被誉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并未促成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巩固与发展,而持续的社会动荡与经济衰落逆向带来“伊斯兰国”的兴起。“阿拉伯之春”短时间内变为“阿拉伯之冬”,西方民主秩序遭遇到非西方国家严重的“水土不服”,“民主退潮”[13]的诸多议论声随之蔓延。与之相对,全球化下人口的跨国流动带来广土众民的主权国家内部国族结构的复杂化与社会成员的异质化,根源于不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渊源的族群间冲突频发,甚至演变为恐怖主义。西方各国面临着严峻的国族空心化困境,呈现出国家认同被削弱的治理危机。如果说公民社会理论是自由民主秩序志得意满、向外扩张时的理论表象,那么社会资本可以说是政治学界尤其西方政治学界在此基础上顾影自怜的研究呈现,然而两者在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民主退潮及连锁反应般的国内冲突时却纷纷招架不力。
究其原因,公民社会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虽然对个人主义态度不一,但都对多元文化主义态度友善,而个人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具备亲缘性,甚至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公民社会”作为自由民主秩序强势扩张时期的理论产物,给予了非西方国家人民用以抵抗与推翻独裁政权的理论武器。能以强势姿态冲破国家界限向外渗透的公民社会理论暗含着普遍主义的认知,其对公民身份的界定必然抽离依附于人身的外在文化特性,将其简化为抽象的原子式个人,使之具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特质。需要警惕的是,公民概念一旦压倒国民概念,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价值虚无主义的盛行,社会成员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乃至核心文化认同的立场均会发生动摇。这种动摇本身的理论基因就暗含在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内部。个人主义本位将个体抽象化也平等化,并奉人权、自由与平等为价值链条的至高点。但是,个人主义对个体自由的平等性与至高性认知终会突破同质化的抽象设定而步入现实世界,进而与现实社会成员所属的种族、宗教、阶层、文化等群体特质相联系。这在理论上会进一步催生出更具现实意味的平等与宽容,即文化相对主义及衍生的多元文化主义。简言之,越是宣扬个人主义,越是认同自由与平等,在现实中,便越可能会对不同文化背景与文化立场的个体持宽容态度,以至于认为只要是不同的观点立场就应受到尊重,只要是不同的文化形式就应被认同,甚至接纳各种前现代和反现代的文化类型。在此意义上,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公民身份一方面超越差异建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却潜在地支持异质排斥融合。实质上,多元主义的公民社会必须具备至关重要的存续前提,即被宽容的各种政治和文化要素认同多元格局,若相当份量的坚定一元主义夹杂其中,多元主义的格局本身必然面临随时被打破的风险,社会分裂状态迫在眉睫,对此,近年来世界各国尤其欧美国家内部频发的族际冲突及恐怖主义可见一斑。
社会资本理论对个人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采取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它一方面反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却拥抱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者们提倡个体社会成员有规律地去参加团体与组织生活,打破个人主义造成的社会凋敝。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加入同质性团体(或曰内聚型组织)可能进一步强化小团体意识,形成抱团排外的社会分裂局面。只有加入异质性较强的组织(或曰外联型组织)(4)以罗伯特·帕特南为先锋的社会资本研究者以成员身份的异质性为标准划分组织类型,试图明确能够引导人们形成与“他者”的群际接触,化解多元社会的分裂困局。帕特南从罗斯·吉特与艾维斯·维达尔处借用了外联型(bridging)与内聚型(bonding)组织的说法;戴特林德·斯托利(Dietlind Stolle)与托马斯·罗尚(Thomas Rochon)从组织成分的包容性出发采纳兼容性(inclusive)与排他性(exclusive)组织的区分; 帕梅拉·帕克斯坦(Pamela Paxton)则借由组织成员的异质性程度考虑组织的外联特性,区分出孤立型(isolated)及连接型(connected);与之相似,还有同质型(Homogeneous)与异质型(heterogeneous)组织、内向型(inward-looking)组织与外向型(outward-looking)组织、组内(intra-group)关系与组外(extra-group)关系的说法才可借助社会接触或者群际接触(social contact)培植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更具包容性的交往态度,进而解决多元文化主义造就的社会分裂困境。目前来讲,社会资本理论在这一点上陷入了研究困局,2007年帕特南发表的《合众为一:二十一世纪的多元化与共同体》可被视为社会资本研究的分水岭。该文指出,多元文化的美国社会本质上是以差别性为底色的多元社会,但以差别性立基的小群体抱团的行事规范成为共同体凝聚与团结的关键阻碍,由此帕特南意图重新唤起美国立国之初的“大我”意识——“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号召多元化社会的凝聚力重建。在该文中,帕特南承认在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恐怖主义袭击时而发生的新局势下,借由个体与个体间薄弱的社交接触来解决多元社会的基础认同问题难以奏效,却也未能提出更有效的解决方式。[14]
在主流意识形态及所谓“政治正确”的引导下,西方社会正逐步从阿维沙伊·马加利特(Avishai Margalit)所谓的“宽容社会”跨入“多元社会”,呈现出自我身份认同弱化的危机感。马加利特指出,真正的体面社会(Decent society)中主流文化不应包含组织性、系统性地羞辱次群体的集体表象;宽容社会是以主流价值观立基,只是审慎地默许其他竞争性生活方式存在;多元社会则不仅仅是宽容各类竞争性生活方式,也认可它们的平等地位及重要价值。[15]在全球化浪潮下,人口高速流动、文化相互碰撞,作为强势方的西方国家一直在扮演着向全世界进行文化输出及价值定调的角色,却逐步意识到个人主义内核的脆弱性,以及由此而来自我对核心地位的拱手相让。对此,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从情感地缘政治学角度分析到,美国和欧洲害怕被所谓“政治正确”禁锢,在其他力量崛起过程中逐步失去自我认同与国家身份,呈现为一种怯懦的“恐惧文化”。与之相对,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因为在全球化经济繁荣中被排除在外的现实挫败、过往历史中遭受的种种屈辱,加之持续的宗教冲突,呈现为典型的“羞辱文化”,又进一步外化为“仇恨文化”。[16]这些夹带羞辱与仇恨情感的一元文化移植到多元主义的社会与政治格局中,已经造成了西方社会严重的社会对抗及政治极化现象。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保守主义政治学者批判多元文化主义,在“社会”的理论角色上尝试从“公民社会”回归到“国民社会”。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将“文明冲突”的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指出因为拉美裔移民的涌入与次国家认同的强化,也因为精英人士弥散的世界主义与多元主义情怀,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正在动摇,他认为仅靠意识形态立国是脆弱的,美国应重申历史性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与宗教信仰,重振国家认同。[17]另如,希斯-摩尔(Theiss-Morse)的《谁算美国人:国家认同的边界》则区分出强认同者(Strong identifiers)与弱认同者(Weak identifiers),她以详实的数据分析为基础,指出强认同者往往将“互助”与“忠诚”投向具有共同历史记忆与民族记忆的族内成员,弱认同者仅以宪法或政治认同作为底线标准,在国家认同的强度上偏弱,文化认同才是促进国家认同最本源的共鸣。[18]17世纪以来,政治学的发展主流可以说是一部“驯化利维坦”的历史,然而,“驯化利维坦”的学术史走到今天似乎已趋向极致。近年来,国家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国家信念(national creed)、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等晋升为政治学界的研究热词,如何找回国家认同与社会团结成为政治学研究中更为迫切的理论关注点。这些研究超越国家—社会二元分立的分析框架,尝试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重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构社会结构与政治运作的一体化理解。以反国家主义为主轴的公民社会理论、以反个人主义为主轴的社会资本理论均无法有效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与社会分裂,自由民主秩序退守视阈下的“社会”理论角色已尝试抛开国家—社会的二元对抗性,甚至自公民社会理论背后的普遍主义立场退回到特殊主义的国家立场,着重自国家认同的视角寻回国民特性,以逆全球化之势找回一个社会的凝聚力。换言之,反国家主义、反个人主义已成政治话语的前置阶段,支持社会的多元文化主义格局还是逆向强调社会的同化主义趋向成为各国国家治理需要抉择的新问题。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在国内理论界传播并为众学者簇拥,以公民社会理论为表象的国家—社会二元思维模式甚至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话语逻辑。近年来,西方社会资本理论以大热之势来袭,亦为国内学术界采纳用以本土化分析与研究。这些理论作为舶来品根植于厚重的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如果将其从所诞生的母体中剥离,在异质的东方文化与制度背景中从事相关问题的思考,必然需要对其有更深入的洞察。尤其是当下以反多元文化主义为基调的保守型国民社会的理解转向,更需要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目前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竞争性和冲突性显著增强,仅在贸易失衡的框架内思考这场贸易战将无法洞悉美国积淀多年、层次更深的价值焦虑与文明恐慌,而后者可能让贸易战在持续时间、波及范围及激烈程度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状态。对此,我们不仅需要严正立场、自我捍卫,更需最大限度地把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之所思所想,做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并以此为基寻求最佳解决方案,真正实现美美与共。本文梳理西方政治学知识话语转型视阈下“社会”的理论角色演变,从反国家主义的“公民社会”到反个人主义的“社会资本”,再到反多元文化主义的“国民社会”,可以看出西方尤其欧美自由民主秩序从扩张到退守的时代变化,亦可看出西方国家对其内核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从肯定到怀疑甚至自保的多次态度转变。 未来中国调整与西方国家间的关系应该敏锐地注意到此点,推动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有效对话,最终实现习近平倡导的“以文明交流谋和平,以文明对话促发展”。[19]
——以《文化偏至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