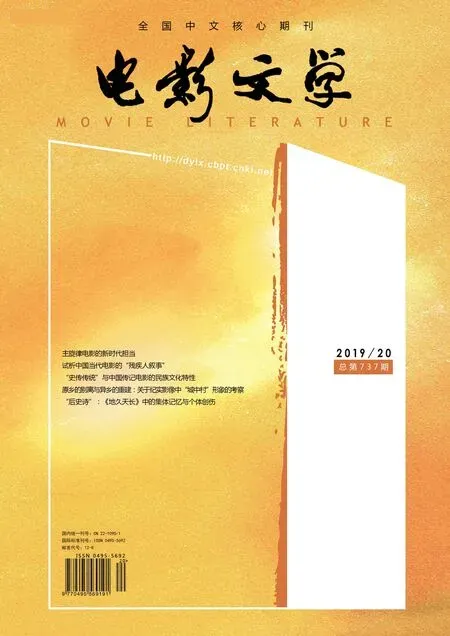从女性主义看《白蛇:缘起》的叙事困境
姜 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2019年1月,追光动画和华纳兄弟共同制作的动画电影《白蛇:缘起》在国内首映,上映38天后,票房达到4.4亿,豆瓣评分7.9分,猫眼评分9.3分,成绩喜人。这部影片是追光动画耗时3年精心打造的力作,虽然也有美国华纳兄弟的参与,主要创意与制作还是由追光完成,可谓地地道道的国产动画。影片采用CG动画技术,将表现真实再现的三维CG技术与中国水墨画的写意追求相结合,有较大的技术突破。此外,场景还原、人物造型方面,影片将中国风元素与现代时尚相融合,受到青年粉丝的大力追捧,网络评价《白蛇:缘起》是“国漫的再崛起”。抛开技术层面,《白蛇:缘起》在故事叙述上,是一次旧瓶装新酒的改编尝试。影片以“缘起”为入口,摆脱了白蛇故事的经典叙事模式,通过阿宣(前世许仙)不断救起白蛇而两人相恋的基本构思,为后世白蛇报恩构建逻辑支持。然而,摆脱了经典叙事之后,影片又陷入了创新叙事的讲述困境。白蛇故事经过千年的世代累积、文人创作,已经由一个妖怪故事雏形演变为以男女爱情为核心话题的传说故事,这其中关于爱情的追问、女性的定位是《白蛇:缘起》难以摆脱的潜在话题。如果从性别视角进一步追问影片对白蛇故事的创新叙述,我们能够发现男女主人公陷入爱情理念的符号化危机,也因此可以找到影片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一、白蛇:由女妖到女人的递变
白蛇故事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学界目前认为其传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太平广记》所辑唐代《博异志》中的《李黄》篇,已经涉及男子、白蛇女妖、魅惑等元素。更完备的文本记载,是明中期洪楩所编《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西湖三塔记》和明末冯梦龙所辑《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两个话本的背景均是南宋临安西湖,大体梗概均是白蛇女妖魅惑男子,与之结为夫妻,后被法师镇于石塔中。其中《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在妖怪故事的胚胎之上,带有当时的市井气息,基本奠定了后世白蛇故事的雏形:男子名叫许宣,是药材铺伙计,与白蛇在西湖船上相遇,借伞还伞之后结成夫妻。虽然屡屡给许宣带来祸事,但是白娘子终究只是想和许宣做夫妻,并“不曾害人”。从明中叶到清末,白蛇故事还出现了评弹、戏曲、皮影等系列演绎形式,故事情节不断丰富。其中清雍正、乾隆时期,黄图珌的《雷峰塔传奇》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基础上,将白蛇故事改为传奇,以白蛇被镇压在雷峰塔下为结局。黄本之后,梨园中有人续了“描真”“产子”“炼塔”“祭塔”等情节,白蛇角色逐渐向“人”靠拢。此后,乾隆时期方成培对梨园续本加以润色增补,增加了“端阳惊变”“仙山盗草”“水漫金山”等剧目。20世纪50年代,田汉在白蛇旧戏的基础上编写了新版京剧《白蛇传》,奠定了现代白蛇京剧及影视剧的叙事基础。田汉将白娘子取名白素贞,称其为“蛇仙”,将其与许仙的姻缘归为白蛇“报恩”。白素贞在剧中是期待爱情的少女、帮助丈夫的贤妻、爱怜幼子的慈母,许仙则一方面对白蛇确有真情,另一方面又轻信法海,最后向妻子下跪认错。从中唐到近代,整个白蛇故事的演化过程,是白娘子由妖到人的递变过程,清中叶以后,白蛇故事基本从早期的捉妖猎奇模式逐步成为融入爱情、解放、自由等诸多元素的伦理爱情剧。白蛇故事每一个时代的演进,体现着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潮和妇女观,“得益于现实社会中妇女地位的提高,白蛇从审美理想的高度完成了艺术形象质的升华”[1]。
最早以影视形象讲述白蛇故事的,是1926年上海天一电影公司出品,邵醉翁导演、胡蝶主演的电影《义妖白蛇传》。此外,国内的白蛇电影还有1939年由杨小仲导演、华新影片公司出品的《白蛇传》(又名《荒塔沉冤》)。1962年,香港邵氏制片厂出品,由岳枫导演、林黛主演的京剧电影《白蛇传》。198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傅超武导演、李炳淑主演的京剧电影《白蛇传》。1982年台湾第一影业机构出品、林青霞主演的《真白蛇传》电影,1992年赵雅芝主演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其中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堪称历代白蛇故事的集大成者。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杨小仲导演的《白蛇传》将白娘子从蛇妖传说中抽离,她成为了一个被污蔑成蛇妖的女性,影片主要表达反父权、反封建的意识。可见,白蛇故事,虽经过千年演变,其精神内核始终与女性问题有着难以割裂的联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内白蛇电影又有新的发展,尤其体现在对剧中人物的深度塑造、剧情改写以及画面制作方面。1993年徐克导演,王祖贤、张曼玉主演的电影《青蛇》,以李碧华的小说《青蛇》为蓝本,将青蛇设计为与白蛇并重的人物,法海也不再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僧侣,对男女之爱以外的同性友情、人性、“情为何物”等问题提出更深层次思考。2011年,程小东导演,李连杰、黄圣依、蔡卓妍主演的电影《白蛇传说》,水漫金山一幕,画面堪比好莱坞大片,其中白蛇形象融入了现代都市女性果敢、历练的性格元素,小青发展出与能忍的爱情,法海最终被白蛇与许仙的爱情感动。
二、缘起:女性期待与叙事突破
2019年,动画电影《白蛇:缘起》的出现,堪称白蛇故事在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突破。抛开动画电影制作形式所带来的传统电影难以媲美的魔幻特效、山水画面等视觉震撼,影片以白蛇故事的“缘起”为叙事入口,极大程度摆脱了这个千年累积的民间故事对后世改编作品的控制力。
首先,影片某种程度反映了新时代的女性期待,对许仙与白蛇关系进行了叙事调整。导演黄家康称“好奇白素贞为什么那么义无反顾地爱一个人,所以就很想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情”。[2]传统白蛇故事,白蛇与许仙之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3]的爱情,白蛇更多是主动方、付出方,许仙则是感情的被动接受者,他听信法海所言后,感情有所游移。《白蛇:缘起》则从前世缘起切入,更多强调男方对女方的付出在先,于是白蛇和许仙的关系由女方主导叙事转为男方主导叙事。影片中小白一出场不再是经典文本中对爱情充满向往的少女,而是失去记忆对人处处提防的略显冷漠的女子。相反,阿宣则表现出善良、阳光、热情的性格特质,与经典文本中许仙的文弱、安静、被动形成鲜明对照。整部影片,阿宣在捕蛇村的瀑布边、古塔降妖阵、国师阵法等地多次舍命救白蛇,最后甚至因此失去生命,换得了白蛇坚贞不渝的爱情。传统白蛇文本,更多是白蛇努力将自己化为人,试图拥有人的形体和精神,向作为人的许仙靠近。电影《青蛇》中,法海见白蛇水中产子,惊呼“她已经是人了”,对自己镇压白蛇产生一丝犹疑。而《缘起》中,阿宣把自己变成妖,跨越人妖界限,向小白靠近。这样的叙事安排,更多注入了现代女性关于爱情的某种期待。玛丽·安·多恩在《电影与装扮:一种关于女性观众的理论》中指出“对女性观众而言,就是存在图像的一种过度在场——她本人即是图像。由于这种关系的封闭性,女性观众的欲望才能被描述为一种自恋——女性的观看要求一种成为(a becoming)”[4]。影片上映后,不少女性观众表示,这样的爱情令人十分感动。观众的观影期待,尤其是女性观众的期待,是影片叙事调整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动因。
其次,影片在“缘起”的逻辑前提下,对传统叙事元素进行了删、增、改的再组合,将白蛇从妻子、母亲的从属角色中解放出来。第一,影片删除了历代白蛇故事中白娘子帮助许仙开药铺、盗仙草救夫、生子等经典叙事元素,男女主人公一出场是两个没有爱情的独立个体,从而避开了白蛇作为妻子与母亲角色的叙述。第二,电影增加了独特的创新元素。柳州捕蛇,本是中唐柳宗元的散文《捕蛇者说》中的一个背景,编剧将其嫁接为许仙和白娘子爱情的前世源头,对传统文本中许仙前世救白蛇的情节进行了新的扩充,丰富了白蛇对许仙的爱恋条件。第三,影片改动了传统文本中旧符号的叙述功能。从电影符号学的角度看,电影是“用影像表达的一种语言符号的系统”,这些符号包括“场面调度、蒙太奇、摄影、照明、构图、音响”[5]等电影元素,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作为符号系统的电影。白蛇头上的金钗在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中是许仙与白娘子的重要定情信物,它的作用是推动两人爱情发展。而在《白蛇:缘起》里,“钗”首先是一个法器,小白一出场是担负使命的独立女性,并非为爱情而生。此外“钗”还成为整个叙事结构的勾连,小白将阿宣的魂魄锁在钗中,又通过珠钗回忆起500年前和阿宣的过往,小白通过珠钗误吸小道法力变成巨蟒,又因“钗”而最终刺死国师,“钗”还连接了关于宝青坊的相关叙述。
最后,影片叙事融入了伴随女性问题而来的对自由、人性的深层追问。首先,对自由的争取。经典白蛇故事中,白蛇与法海的斗法、天地规矩与人妖恋爱的矛盾,始终隐含一个自由与解放的问题。《白蛇:缘起》更明确地点明了“自由”的主题。小白几次对阿宣提到“不想做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暗示自己不想担负行刺国师的重任,以及不能违背天地规矩与人相恋。阿宣则表示“就算人生命数有定,也要活得自在”,他和小白驭伞腾空,认为这是庄子的“逍遥游”。当小白变成一条巨蟒,他依然表示八荒四海总有容身之所。其次,对人性本质的深层追问。白蛇故事的演变历程,从妖怪害人到白蛇拥有更多属人品质,始终存在一个人高于妖的叙事秩序。电影《青蛇》中,法海见到人间百态,对人与妖的区别就提出“人?妖?”的质疑。《缘起》中,人不再拥有传统故事中绝对的优势地位,狐妖称人“浑浑噩噩”,小青认为“人不过是再狡猾不过的骗子强盗”,阿宣自己也承认“人间多是长了两只脚的恶人”,对人性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思考。
三、符号男女:缘起叙事的瓶颈
《白蛇:缘起》从“缘起”角度切入,避开了世代累积文本的故事窠臼,体现了制作团队在电影叙事层面的巧妙创新,加上画面、音乐、对白设计等因素,确实可称“国漫的再崛起”。不过,如果用国际一流水准来衡量,《白蛇:缘起》依然有其提升的空间。
“缘起”作为开端、起因、条件来理解,最初来自佛家典籍。《维摩诘经·佛国品》所谓“深入缘起,断诸邪见”。赖永海解释“缘”为“一切事物和现象所依赖的原因和条件”,解释“起”为“依条件而生起”,“缘起”则“意谓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处在普遍的因果联系之中,都依一定的条件而生起”。[6]由此可见,影片的一个基本诉求,即找到后世白蛇故事中“白素贞坚贞不渝爱许仙的理由,找到他们爱情的起点”。[2]这里有一个潜在逻辑:后世白蛇为许仙赴汤蹈火的爱情,并不是没有缘由和条件的。这是《白蛇:缘起》相对前代白蛇故事的一个逻辑胜利,某种程度亦是当下中国女性意识朦胧觉醒的产物。然而,当我们再用同样的逻辑来问《白蛇:缘起》,是什么理由让阿宣能够不顾自身性命几次救素不相识的小白,甚至为了与她相恋甘愿做一只天要杀、地要杀、人要杀、道士也要杀的最弱的小妖,影片似乎就要陷入难以自洽的叙事困境。
这样的叙事困境,尤其表现在男女主人公各自的符号化呈现上。
首先,白蛇的被动、柔弱让本该作为第一主人公的女性形象成为男性凝视的载体。英国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一文中,以20世纪70年代好莱坞电影为分析对象,指出好莱坞电影将女性作为供男性达成观赏快感的一种符号,指出影片背后女性自身的主体性的缺乏,她指出“女人的含义就是性的差别”,“电影为女人的被看开阔了通往奇观的途径”。[7]劳拉的观点被后世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普遍运用,因为它所揭示的看与被看的问题,广泛存在于各种电影叙事之中,揭示了一种普遍的男权话语。《白蛇:缘起》删除了历代白蛇故事中的经典叙事元素,就需要几乎重构一个全新的女主人公。影片似乎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然而,新的白蛇形象作为女性的主体性,几乎同于劳拉所说的“缺乏”。整部影片,有数次白蛇晕倒被人抱起的镜头。影片开头,小白在深潭中突破功力失败晕倒,被小青抱起,影片过程中又因触碰珠钗、刺杀蟒蛇、搏斗蛇母等情况先后晕倒,被阿宣抱起。
小白虽然会法术,某种程度也可以担负制敌任务,但是关键时刻,她只需要晕倒,就足以配合不会法术的阿宣演出一幕一幕“英雄救美”的故事,就如劳拉·穆尔维引勃德波埃蒂舍所言“正是她使他那样做的,而女人自身却丝毫不重要”。[7]女性的“缺乏”背后,又被摄像机所构建的自足的女性美所填充,最终成为男性凝视的载体。影片试图打破传统爱情模式中男子因女子容貌而产生爱情的模式。当小青问到“如今姐姐变成了这个吓人模样,你还喜欢她吗”,阿宣没有正面回答,但是却用行动表示,哪怕小白变成一条巨蟒,依然对她不离不弃。然而,电影依然重点突出了小白的价值——美:镜头多处特写小白身形曼妙,一袭长裙,发髻后的白色绸带仙气飘飘。此外,亦可从旁人叙述视角见出小白的美。她被阿宣救起后,村民议论“那姑娘长得多好看”。小道士来捕蛇村抓小白,称“美人,我们又见面了”。小青称小白修得“诱人身形,精致容颜”,认为阿宣“不过是喜欢我姐姐的美貌罢了”。尤其是佛塔之中,大受感动的小白主动褪下衣裙,在银幕上献身,与起初羞涩、戒备的形象有鲜明的反差,这背后可见影片满足银幕前观众凝视欲望的动机,正如劳拉所谓“女人作为影像,是为了男人——观看的主动控制者的视线和享受而展示的”。[7]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出《白蛇:缘起》在叙事精神上试图突破,又终究陷入了男性主导思维。
其次,多次无条件拯救白蛇的阿宣亦带有男性符号特点。影片某种程度试图突破男性角色的刻板印象,打破了中国传统爱情故事诸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霍小玉传》《莺莺传》里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模式,然而又滑入了另一种英雄救美的男性话语。阿宣是不会法术的凡人,成妖之后也是一个“最弱最小”的妖,并非传统模式的盖世英雄,但是他往往宣称要保护小白,并在关键时刻多次救起会法术的小白,又俨然成了盖世英雄。这种男性救赎模式与迪士尼早期动画所改编的民间故事电影颇相似,例如《白雪公主》(1937)、《灰姑娘》(1950)、《睡美人》(1959)。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总结“在歌谣和故事里,我们看到,年轻男人为了追求女人而离家出走,甘冒风险。他杀死巨龙,与巨人搏斗,而她则被锁在塔楼中”。[8]然而,经历过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的理论洗礼,新一代的迪士尼动画在叙事模式上已经发生了某些改变。例如《怪物史莱克》(2001)、《冰雪奇缘》(2013)、《疯狂动物城》(2016),男性不再是救赎女性的英雄,女主人公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以及实现自我的能力。此外,设计阿宣成为救世英雄也并非完全不可取,但是英雄人物也可有凡夫懦弱、胆小、害怕的一面,否则易走向符号化的扁平。美国大片中的英雄拯救模式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主流叙事模式,英雄主人公除了无畏、勇敢、责任以外依然有平凡人的特点,甚至他一开始只是人生失意的普通人,如《钢铁侠》(2008)、《复仇者联盟》(2012)、《毒液:致命守护者》(2018),等等。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张启忠在《〈白蛇:缘起〉:唯类与文化底蕴的互生与壮阔》一文中曾指出《白蛇:缘起》“角色性格和心理,过于单调,以至于角色的动机都是导演的直线设定,缺乏因缘际会的张力、变化与递进”。[9]“直线设定”的背后,即是被影片叙事所驱使的符号化人物。
四、归因分析及解决策略
如果我们从文化生成的角度,更深入地挖掘《白蛇:缘起》在女性主义视角下叙事困境的形成原因,大概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首先,经典文本的叙事控制。白蛇故事经过世代累积创作,作为第一主人公的白蛇已经具备了男权话语之下的楷模女性形象,她以爱情为第一追求,美丽大方、温柔贤淑,是丈夫的得力内助。将爱情视为最高人生追求的白蛇,与中国传统爱情故事中的崔莺莺、杜丽娘、祝英台等女性形象都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改写这样一个男性话语中的经典女性人物,势必受到强烈的文本控制。相较而言,未被捧上神坛的青蛇,在后世文本中呈现出比白蛇更大的改编空间。徐克导演的《青蛇》,以李碧华的《青蛇》为底本拍摄,整部电影中,青蛇呈现出全知视角,她引诱许仙、法海,并不信任所谓的人间爱情,打破了白蛇一心要做贤妻良母的女性人生轨迹。李碧华的《青蛇》所承载的女性意识并不借白蛇来表达,小说中的白蛇依然是一个在爱情里“变得很低很低”的传统女性,由此也可以反观传统故事对经典女性形象的叙事控制。
其次,中国传统爱情故事“缘起”的叙事虚弱。《白蛇:缘起》在叙事、画面构图、人物造型上充分运用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元素,本身是值得提倡的。影片片尾曲融入了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插曲曲风,歌词“匆匆美梦奈何天,爱到深处了无怨”仿照了《牡丹亭》中《游园惊梦》一节中的《皂罗袍》唱词“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片尾以长卷水墨画的形式呈现出白蛇故事的多处场景,如夫妻洞房、保安堂、雷峰塔等,如同一幅动态的《清明上河图》,将传统文化元素进行了现代性的再创造。然而,传统文化并不能统统解决现代问题,要在传统爱情文本中寻找“缘起”叙事因素,则容易陷入暧昧不清的逻辑虚弱。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这个取向几乎是中国传统爱情故事的共有特性。《西厢记》《牡丹亭》《金瓶梅》等经典文本中的爱情情节,男女主人公均是初次见面即陷入不可自拔的爱情,女主人公瞬间就可以具备对爱情的绝对忠贞。
最后,当下中国女性问题的复杂性。第一,中国女性的解放运动具有先天的依赖性。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由妇女主动自下而上争取权利不同,中国女性的解放从一开始就附着在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历史进程中。当下,由于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政府出台一系列法律、政策保护妇女的权益,此外中国女性主义的相关理念更多来自西方世界的输入,这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中国女性主义发展的内驱动力。第二,当今中国女性解放道路出现价值寻求困境。戴锦华指出当下中国女性地位及社会关于女性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倒退。[10]民间乃至思想界,依然有不少声音认为,女性的天然属性是妻子、母亲,一个再优秀的女性,婚姻爱情不顺即是最大的不幸。职场中不少优秀女性最终会选择放下自我追求回归家庭。李碧华《青蛇》中的白蛇,拥有千年法力,却甘心为一个平凡的许仙过尘世的生活,“他会哄我……于是我便听从他的话……只要我稍微降低自己”。[11]《白蛇:缘起》里的小白,功力应该远高于不会法术的阿宣,却屡屡要在阿宣面前晕倒以得到他的保护。第三,当下中国对女性问题的众声喧哗。由于媒介手段的丰富,当下也存在不少自媒体的声音表达女性意识诉求,例如咪蒙的公众号,诉求男性对女性的无条件关爱,获得众多女性粉丝狂欢式的追捧。然而,这种女性天然就该得到男性无条件关爱(类似阿宣爱上小白后就该无条件为她付出一切)的观点是否可行以及可能,受媒体影响的大众意识来不及进行深入思考。
作为一部电影,《白蛇:缘起》或许承担不了那么多文化创新或者价值引导的使命,但是中国电影要想真正走向甚至引领世界,就必须探索电影背后所要传递的价值问题。李小江指出中国女性主义面对传统文化应持“清理”的态度,这个“清理”就是某种程度摆脱女性主义在文化谱系中“批判者”和“啄木鸟”的形象,是一个从破到立的过程。那么,《白蛇:缘起》要想改写经典文本,树立新时期的新白蛇形象,构建新时代思潮下的男女两性关系,仅仅搬运或重组传统文化因子,显然是不够的。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白蛇:缘起》,如果影片能够在叙事与制作技巧的背后彰显出全球化的普世性别观,塑造真正的独立、解放、实现自我、可以爱人又被人爱的男人和女人,那它将真正成为国际电影界的领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