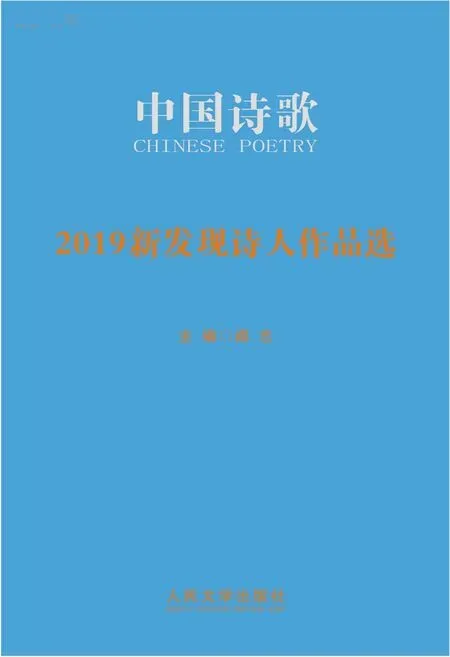杨泽西的诗
空麦秆
我第一次如此细致地观察
一根根被镰刀割断的麦秆
这片和我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麦
它的伤口尚留有疼痛的记忆
现在它站立在故乡的麦田里
有一些哀伤
它曾经在头顶高举的麦子
它引以为傲、赖以生存的麦子
已经堆在了粮仓里
和它没有了任何关系
只留下它中空的身体裸露在空气里
这无用而又脆弱的存在
多数时刻,我写诗
让自己置于一间密室里
如同暂时割断与生活连接的血管
当一首诗完成之后
我将继续回到身体的囚笼
我一次次返乡,夜夜反思和写作
究竟是为了把这中空的身体填满
还是为了给这空,腾出更大的空间?
纸上:引蛇出洞
因为无风
纸张恢复成了一面湖水的镜子
你坐在窗前开始读纸上的涟漪
你的影子任由纸底的一尾鱼垂钓
整个下午你都在一张空白的纸上
吞吐鱼刺的诱饵
无数的词语卡在喉咙的深处
你有点难受
甚至想把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吐在纸上
直到夜晚
你看到远处的湖面上摇曳着一束细小的渔火
就像一条蛇吐出的信子
突然夜的皮肤被咬破
伤口处渗出一股一股的光
听水滴
夜里十一点
失眠使我的听觉更加灵敏
我能听到遥远的街道上酒瓶摔碎的声音
男人女人哭泣的声音
流浪歌手歌唱的声音
一阵拔尖的刹车声撕咬公路的声音
更远的地方,我能听到
工地里砖头坠落到地面上碎裂的声音
火车驶过铁轨尖叫的声音
甚至再遥远一点
我能听到故乡的鸡鸣和狗吠
这所有的声音现在都汇集在了一滴滴水里
通过我床头旁没拧紧的水龙头
慢慢滴落下来
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像个病人
那细微的声音
一滴一滴地流进我的血管里
直到午夜我才成为一瓶药水
把那自己重新输进夜的体内
牧雪记
没有绿色,便用文字刮骨头上的青苔
把思想调到零度以下,在纸上下一场雪
在黑夜里引出,身体里沉睡已久的羊
而身体之外,大雪早已封山
屠夫在火炉上烤化最后一片雪
几乎所有人都把羊皮穿在了身上
只有少数人仍固执地摊开一张羊皮卷
让大雪落在上面,用黑色的文字
复活一只只死去的羊
危险是:当所有人都一致认定
大雪是这世间唯一的羊、唯一的一张羊皮
雪地里太阳的反光便成了一把锋利的刀子
多么可怕:当你走到城市的边缘走到无人区
黑暗里突然射出一道强光,像扔出一根长绳
你成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牧雪的人,唯一的羊
捉迷藏
我们躲进门后、草垛和水缸里
越是黑暗的地方,我们越是选择隐蔽于此
任凭伙伴们一次次寻找和惊吓
任凭他们一再呼喊我们的名字
——假装以自信的口吻叫道
“出来吧,我看到你的影子了”
我们仍旧屏息不动,直到对方真的投降
我们才带着胜利者的笑容缓缓地走出来
成年后,我们继续着这种游戏
我们借助身体躲在不同的场合、面孔下
被不同的人叫出不同的称呼和名字
有时我们会因为紧张而表现迟钝
不知道对方叫的是谁
直到夜里,所有的人都散去
我们才脱掉外套,站在镜子前
轻声地对自己说——
“出来吧,我看到你的影子了”
这时候,它早已消失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