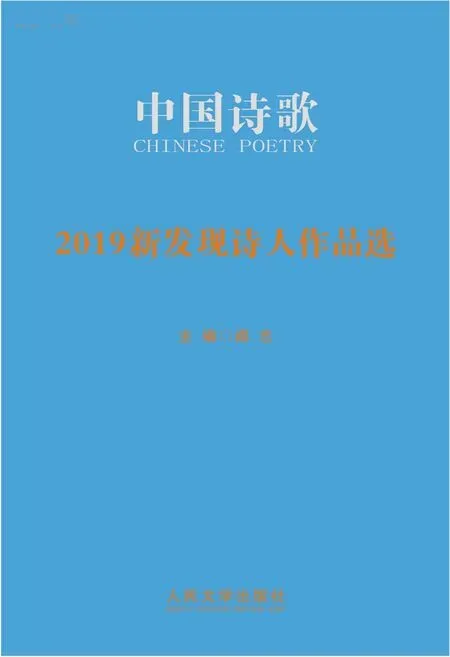路攸宁的诗
遥遥东去
沿襄渝线,火车驶出山川起伏的巴山
黄昏卷入这次远行,渐次垂下的暖黄色光芒
成为流淌和收敛的部分
列车的轻微晃动反复惊醒艰难入睡的旅客
就像这次远去,睡眠和清醒都
十分仓促而又,无需交代
相邻而坐的人相互谈论起故乡、异地、工作
和生活中无数的厌倦和流离
浅尝辄止,不作深入的叙述
车窗外,有积雪成川,有遥遥东去的风
跋涉千万里。倾注而下的夜色
映出了人间辽阔苍茫的白
谅解
雨季到来之前的毗河,还来不及涌出内心的澎湃
河岸的水草截取了初春的底色,布满了绿意
一些辽阔的风声掩入沉寂的河水之下
先于我们早些年,信口说出的志向
生活的馈赠和剥夺,抵消了大多数的悲喜
这两端的平衡,无数次地修剪着参差的枝叶
我们向时间抵押了戾气、顽固、反骨和逆鳞
群山罗列的迷阵,反复撞入年少的途中
尘粒从光线的涌动中,翻身而过
诸多莽撞都获得了谅解和宽恕
我们临河而坐,分食一份蟹黄豆花
绵绵不绝——致钟钟
投奔远方的日子挨到了尽头。你谈及“归”
一个延迟的喻意和一场陌生的仪式
雨水和暖意指认你的南方——巴蜀之地
辽阔的成都平原布满了秋日的冷雨
木芙蓉涌向秋天,也涌向了悬空的窗口
我不会对你提及更深远的季节,和彻骨感受
薄雾四溢,滴答的雨声在夜色中破裂
我们在遥隔千里的地方,无限接近于疲倦的深夜
此后,晨光被温柔打开
你将拥来北国的温凉和仆仆风尘
从锦州南到成都东
那些途经而过的山川,都是你久别重逢的故乡
寥寥无几
小酒坊里,马爷爷还在酿造浓郁的苞谷酒
黄葛树穿过凛冽的年代,耸立在老街的边沿
小河流洗净了旧日的浑浊。人们依次衰老
在冬寒夏热的交替中,熟悉了命运的轮廓
族里的孩子已经拥有新颖的玩具
不再重复我童年时代的纸飞机游戏
大伯偶尔行径异常,众口铄金
人们指认他患上了精神病
但这偏远之地的沉疴,却无人过问
诸多逝去之物被我们遗忘。时间的筛网
终将为我们截住无数沮丧的粗粝
“往事应声恍惚”,秋日迟迟
多年后,我回到这里,认领了它的破败
片段
白炽灯光截断了窗外的沉寂夜色
细小的飞蛾,扑向光的源头
窗外的虫声不绝于耳。只是那一瞬的扭动
流水从水龙头倾泻而下,像是找到了密闭
而孤独的出口。它们喧哗
在不断退后、不断逃遁的时间里
身前的镜子表露出亲水性特质
吻上了几粒飞溅的水花
体内的涌动,和隐匿的幻想
近似于夜的沦陷,近似于无物
也是在这样的时刻,她在被风吹过的洗漱台上
刷洗一双发黄的旧款小白鞋
纪念日
每一岁都在向我们奔来。低垂的黄昏
卷曲的枯叶,坠落的雨点
一一呼应着我们生命的纵深
四十五年前,你还是一个幼小的婴孩。而我
不曾被你拥有
后来,你获得了一个柔软的幼婴。并且
拥有了她今生的爱、叛逃、和依赖
心脏是不会碎的,妈妈,它顽固且隐蔽
它延伸的脉络,是我重回你腹中的路径
这些年,我们互相消磨,互相深爱
仿若这满腔热忱、孤勇
是因为你的存在,也因为我的被爱
现如今,我已然宽恕了青春期残留的痘印
但是妈妈,我无法宽恕你赐予我的
人世间漫长的跋涉
就如同我无法宽恕二十二年前
伴随我的降生
竭力撕咬过你的凶兽,疼痛
失去
失去你之后,远山和时间都变得空旷
我已经不再喂养野蛮的小鹿,作为喜爱过你的佐证
日光被悬铃木切割成散乱的碎片
阴影和白斑险象环生,重新坠落下来
我剪掉了分叉的枝丫,它已经为你剔除
笃定的花朵。卷曲的枯叶咬合疼痛
来年,干枯的末端会衔来初春的嫩叶
那些新生的枝节,将不再向你延伸
炉边岁月长
我曾见过七十多岁的祖父,坐在炉火旁
一边翻弄生活的琐碎,一边细数过往
像故事里的说书人,但无需扇子和醒木
瘦弱的猫蜷缩在他的脚边
打盹。倦意朦胧,似乎一生都睡不够
公社化运动时期,他做船夫,给钢铁厂运送铁矿石
那条他曾数次往返的河流
自巴山深处涌出,蜿蜒而下
人世的苦雨,尽入腹中
后来,他做公社识字班的老师,也做木匠
几经流离,如水上飘蓬
但他最终也无力逃脱祖祖辈辈躬耕的命运
和祖母结婚之后,他回到家里
开始了余生属于一个农民的生活
很多片段他都无法清晰复述
如同丢失至珍的孩子
静坐在光阴里——怅然若失
山里雪大,轻易就覆满枝头
住在小巷
我们住在相隔不远的地方
共同分享巷子里昏黄的路灯光
我们从未打过招呼
抑或尝试用眼神交流
有时候,我们朝着相同的地方走去
一前一后。有时候,我们背向而行
我在诗里记录他的生活,或者说
——窥探他的孤独
清晨,他推着装有不同水果的小车到街口
午时回家,以清简饭食果腹,再推车到街口
夜晚,在街灯深沉行人零星时回到家里
如此反复,生命中仍旧有大片的空隙
无法被填满。我深夜归来
他在门前剥开一颗颗新摘的核桃
我匆匆走开,和往常一样
核桃与夜色坚硬,只有内心柔软
逃离
无人与你对谈,遥想数百年后肉身寄予何处?
荒山毁于无物,覆雨之间,云雾竞相空明
星河寥落,你眼底存有扑朔皎洁的光
这充斥无垠与浩瀚的时代,也因往日的顽习
滋生多余的疼痛与风湿。若干年后
凛冽的风将湖面吹皱,雨水继续重复更迭的命运
卷轴与书册洞穿隔岸的灯火,于明灭处喋喋不休
你奔跑,在游标卡尺上读出精准的记忆
那些不断在你身后追逐的呼吸声
像是跌宕起伏的海浪,也企图将你淹没
反思
这是我们共同的罪愆
不必陈列纸上
也不必标记符号
事物本身就在陈述一切
更多时候
潜入最深处的
不是海洋生物,而是
一切为我们所构造的表达
质疑,控诉,欢呼
我们对语言有着天生的驾驭能力
我们言及身与物,包括敏感词汇
一切像是早有预谋
在既定的场景里
我们成为犯罪的人
也成为遭受苦难的人
逃亡的人。最后
我们竭力证明自己是
无辜的人
我们标榜智慧
但也必须承认愚昧
比如,在曾经的一次交易中
我们用鱼,交换了等量的沙子
误少年
你不必向我提起那些光亮,我裹挟暗夜的影子
摇摇晃晃,踩碎了脚下的每一寸恍惚
我们各有秋天,不必相互分享
时间会把叶落和飘雪的日子错开
为我们的错过,让出路径
此后我们独自返回,并在沿途置放睡眠
“你我山前没相见,山后别相逢。”
至于悲伤,不过转瞬即逝,不过历久弥新
误入
一条误入人世的河流,避开所有的目光
从掩映的沟壑间逃走
没有惊动岸边的顽石与水草
低处腐烂的树叶不再分享下一个春天
一场预料之中的雨水,会清洗一切
关于荣枯的规律和与人相处的学问
都会有人教给你,但在那之前
你必须要先学会分辨河流的清澈与浑浊。并且
去理解世间万物的美意
把宽容与慈悲给予未知的一切
岁月老
路过一场大雪之后,两鬓就白了
活到七十岁,他不再敏感
一座荒草重生的坟头
死后,他也将沿着枯草落叶的足迹
选择湿润的泥土
磨难与伤痛
终于落荒而逃,在身后
破裂成无力的尘粒
七十年,庄稼和锄头都放下了
被抽干的身体像一棵苍老的槐树
他依旧每日沐雨饮露
但不再是为了去重逢春天
流动的,沉淀的,丢失的,遗忘的
都一一遁入静默。仍然要衣衫整洁
在院子里,淘洗正午的阳光
起风了
缝隙里,携带秘密的风——悄无声息
点亮的烛台远了。
四月的巴山,拼命翻腾着绿
这里雨水充足,庄稼疯长
那只慵懒的灰猫,在夜里走失
想象落空,透明的光在林间彷徨。
我试着理解疼痛,试着去拥抱一朵
在春天承受苦难的花。带刺的植物,藏进角落。
隐匿的通衢,在月光下,流淌着温热的血液
群山静止,视线沿着山脉的走向
追寻遥远的光芒。只有水土,害怕流失。
起风了,乡径掩没在尘草之间
我爱这里的草木,胜过爱远古的太阳
胜过爱洁白的月光。
民风拙朴的穷乡僻壤,蜷缩一隅的老屋
生命和温柔,都有了归宿。
无人问津河流的去向
滚落山梁的乱石,一一遁入河谷。
夜色渐臻浓郁,选择沉默的事物
一边聆听时间和风声,一边等待黎明。
生命倔强,露水滑落,一只云雀轻易就爱上了天空。
破土的生命,学会了饮水,也学会了淳朴的方言
起风了,万物努力生长。
万物此都寂
山光,潭影,清瘦的修竹密布
幽僻的红壤小径向竹林深处探寻
我们拾级而上,苔痕在低处爬行
飞瀑从崖间坠落,悬挂的竹节
投下满目的苍翠。竹丛掩映的古寺
用哀婉的嗓音,反复唱着渡海的佛音
骤然降临的冷意,不断在我们周遭汇聚
这微启的寒凉,穿透禅房与人心
小半日里,尘归尘,浑浊归于浑浊
喧嚣的人潮依旧喧嚣
夜幕悄然垂下,灯影寥落
竹海和迷雾在我们身后奔袭
工业时代的汽车闯入再溜走
我们俗世的肉身,也未曾在此山中
遗落多余的、疲倦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