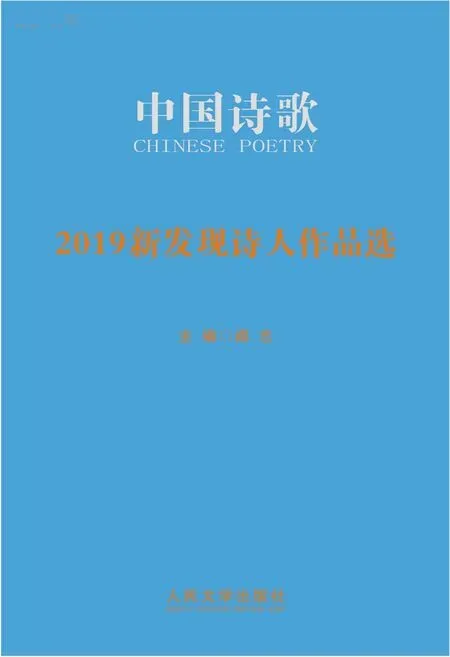醒洱的诗
风景之末
1
已然忘记,何时置身此地
天空低矮,秩序简明
但仍需步入事物内部
一个草草写就的废园
是否能带来新奇的触觉?
沿着这条路,依旧是荷塘
硕大而肥厚,欢快的脉络重复
朝各个向度增殖的绿
洁净的细梗将其递向湖岸
弯折或低垂之态
暗银色叶腹,悬临幽深的波澜
湖水青绿,而天灰暗
鹳掠过水面,翅羽执掌气流的力矩
低空滑翔,负荷疾行
我们惊叹于这精微艺术的赋形之美
逗留于顽石,扬起黑色的喙
和失眠的细腿
“我们不走回头路。”
熟稔的东西从不能使人充盈
进入丛林深处
一些灌木枝杈挑衅着我们
而蕨类的暗绿给予安慰
横向生长,极低而宽阔
顶端渐变血红,它内陷的风暴
涌出,但不能舒展
沿叶脉折叠自我,以封藏柔嫩的屈辱
它与生俱来的债务。哦,女性!
总在夜晚变得陌生
依盛夏之权威
存活,蔓延
此地:一个幽闭空间的宗教
2
步入此地的纯粹智力
月之领土的干冷气候
灌木尖锐而猩红,封藏在小巧的篱笆中
精微结构的拉力控制
使柱蕊竭力伸长,它惊呼的喉舌增殖
花瓣避让,反向折叠
白头鹎停留,凝视复飞离
鳞块裹挟的树体,灰至深褐色
警戒断面的明黄,仿拟光之牙齿
使新绿磨损
松果坠饰呈卵形,规律性崩裂
圆瓣递进填补空隙
重复,变奏的绿交响,和柱状新枝上幽微的刺
它的羽翼平展,斜向上式蔓延
被旋切成平顶,低矮近于荒草
远处飞蓬,在疏于管理的湖岸
是由于摄取了水的狂暴和凛冽,
所以变得高挑而笔直?
叶脉上季节搏动
脚下的血管纠缠
是蒺藜深埋的叛乱
此地,无主的历史
荒芜铺排的秩序
为新的广延统摄
3
向前,是凌乱的松树
积尘使脖颈微垂
并压弯躯干和颀长的脊柱
松针紧锁浓绿,向内的刺
聚成疼痛的骨节,它的新绿生成
这敏锐者的生产,灼热中不断磨损
月季开始衰败,丰盈渡至褶皱
褪作枯朽的黄
黑心菊微笑,高举中心的巨眼
我步入一股甜腻的腐味儿
既非月季也非黑心菊
是梧桐花无数癌变的喇叭
堆积在发黑的枝干
柔软的淡紫花瓣上
稠密的霉斑,向内排布
而狭长的花柱向外探出,呼叫
被柔软的绒毛裹挟
坠入潮湿的沉默中
而树依旧高耸
太阳为石壁刻入影子,漆黑而坚硬的割线
其强力,其持久
将悲伤埋入律法
横亘于此地的空气
与历史
夏日妆台
把所有迟来的触摸相加便得到你的形状。
你低着头,拼贴罪业的发票。
把所有迟来的触摸砍除便露出无你的星空。
空空的蓝,你的粉盘。
镜中升起的双眼,被黑色的时针划分。
私语与红烛,收纳在底部抽屉。
众光容纳平凡的形体,欢爱如广泛的性,
浮动裙裾般的树冠。
你的耳饰一长串儿,翡翠的位序
种植,种植在耳垂,美的领域
须以迷途释义。不忍但我折返,
那些陌生的干冷的反光。
一些尖叫的树叶被重新组织。
双手裁剪的路径,跟随花枝,针线拼接着邻域。
天空晴朗地收缩着,有限的事物,
正在开发持续的冰冷。
钟表微笑,证件在铁盒里,周转黎明。
事件还没有新的主人。
晚风将树叶击散,
声音介入了秩序。
疯马
疯马逐月,月不予应答
月于荒野,疯马不止
一些喃喃细语声吹过灌木
那些怀望的眼睛疯马拒绝
疯马逐月 月于荒野
月摇晃,它罪恶的金黄
摇落夏日,那未经测量的盛大阴影
或阴影的阴影,筑世界于洪水的暴怒与滞留
疯马逐月 月于荒野
于时代的罪业诸峰
它的梦魇已被宽恕:
每一事件都源自内部闪电的碎裂
疯马领会月之意念,但无以承载
匀了三分杀意予我
季节
终究,我们失败了。
是因为你的懒惰和自私
还是因为我的冷漠和多疑?
这质询激荡冬日的晴空,
澄澈、辽远,如你的注视。
在这个以呼吸取暖的寒冷村落,
我们诞于贫穷等待疯狂信仰宿命
如果诉说?我们拒绝诉说。
如果哭泣?我们拒绝哭泣。
为了焦渴的良心。
惧怕,讥笑和私语,我们小心地藏起。
看冰风中栾树枯萎的果荚如风铃触碰,
大山雀机警的椭圆形眼睛旋即没入丛林。
我们也是,如此机警,
如此努力地,小心地,不陷入孤绝。
面对笨拙和矫饰,
一贯致以嘲讽和鄙弃。
恰如它对我们的鄙视,滑溜如体制:
失败者,
曾渴求艺术,
一头栽入痛苦的经验。
低音的震颤,在我们的手心共鸣。
还有什么能从苦痛中涌出使得一切得到报偿?
又为什么自此一切叩问都得不到回答?
仿佛苦痛就是世界的极限之极限?
以致语言只能成为其描述?
我们也再不能借此拥抱?
而夜空的细语带来安慰,
积云的身体教导柔软
传授迟钝和化妆术,
使我们具备阴影之美以便与世界和解
并获得有形的,紧实的欢悦,
以对抗血液中古老的敌意
飞机划过,留下逃逸的痕迹。
它的白色滞留。
它的时间正涌来。
因为迟钝,疼痛并未使我们驯顺。
因为记忆,仍旧坚信爱之创造。
或许一切早已注定,我们的历史也早已写就。
我能看到它的重现:
栾树的黄花散落成泥,
温热的雨水流过身体,
就像灵魂的柔软滑过,就像温柔的欺骗,
孔雀在叫喊,激越的经验
在生命中溢出。
捕获装置
阴天,她习惯在傍晚观望天空
以图书大厦的避雷针参照
它灰冷、渺远、真实
适于回应一个虔诚者的敬畏之心
真正的知识是悲伤
而她已足够勇敢,以疼痛来体验
她的习惯:以各种角度
注视自己最恐惧的事物
触摸它的肌理,深深潜入它——
来习得生存的规则,计算它的出口
(多数时候幽深得令人迷失)
不断忍耐着,又质疑它的真实
是否能磨砺出澄澈、坚硬的灵魂?
每一次哭泣的疲惫,失控后的灰冷
为何会化为一种怯懦和驯顺?
难道这不会激化施虐者的恶行,
因为他们博学的恫吓?
而此刻她已足够冷静和隐忍
拒斥流泪的安适和快慰
真正的知识乃是悲伤
她仍需注视,驯顺者的敏锐和温柔
如一位遥远的母亲
在夜晚用卫生纸折出玫瑰
藏匿于未流出的泪水
而他们熟稔施虐的艺术
乐于享受哭喊
是因为真正的思考只能以身体完成。
天空从不展示它深邃的认知
直到目不能视,恐惧之物不能再被解析
她会一直深入,因为
一个修行者要勇于面对恐惧
并展示破碎的自我
是因为他们的血并不淌在自己身上
一如她的眼泪并非为自己而流
喜鹊
和他走着,跟在后面
阳光透过拱廊的宽缝晒着我们
并透过我的塑料水瓶留下蓝色的影子
我在说着,幸运和不幸,是否可以互相填补
这样就可以为个人的际遇附上合乎逻辑的注脚
而你说,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就证明我是
不幸的人因为幸福的人从不会想这件事情
我很失落,还是不愿意相信
然而是与不是,只能带来一点儿缥缈的傲慢
孩子们从冰淇淋店走出来,吸溜着口水,发出嘿哈的笑声
这个疑问更加使人恼怒了
“你才二十二岁,根本不该考虑这些。
虽然这是唯一能做的,但它并不能告诉你该做什么。”
然后你便沉默了
一辆辆卡车开过,扬起大片尘土
石灰味儿和土味儿
紧随其后的三轮摩托载着三个漂亮的女孩儿
和她们鲜艳的嘴,映在积灰的玻璃中
想想吧,那些锤炼的词句
是不是使生活更加逼仄了,但词却更加丰盈
可到底该如何自处
滚烫的高压线上,暗含闪电的激流
它黑色的翅羽上幽蓝的浮光
彰显陌生的财富
和浑圆的白色的腹部
整洁,修长的尾羽
使我讶异,想把它赶走
大叫着,挥着手
太高了,它听不见
依旧站在那里
专注地,深沉地,注视着
在闪电上
在死沉的热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