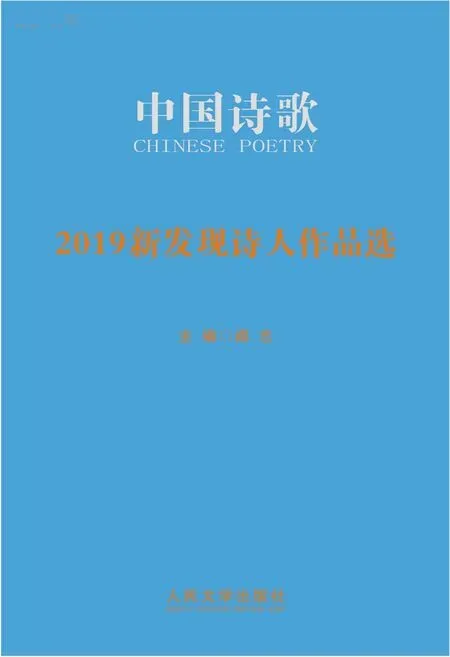葛小明的诗
脊梁
这一生他极其沉默
别人笑话他走路都直不起腰
他没有任何回应,只是
习惯性地捡起秋天的树枝
画一画挺直腰杆时的自己
好多年了
自从生了第三个儿子
他便没把脊梁捋直
沉默惯了,开口成为艰难之事
想想也只在讨论是否立碑时
轻轻说了一个“不”
刀入案板
用力点
多的是硬骨头
难啃
好肉皆在刀斧
触碰不到的地方
狠一点
劈下去便会获得众人的赞美
劈下去便完成了作为刀的使命
欲望尽在刀尖附近凝集
这一刀马上就能解放自己
肉平静地躺着
对即将来临的一切
没有任何表态
挨刀惯了
便不觉疼
案板隐忍很久
终于对刀松了松口
石头是怎样跳下山崖的
你说,石头是怎样跳下山崖的?
一定经历过树的排挤,鸟的奉承,风的肆虐
还有雨水的第三者介入
不知道他们中有没有后悔成为墓碑
立在痛苦的记忆里,难以消磨
你说,替别人清醒是种罪过
那些短暂的名字、用力过度的刀痕
都会被陌生人的悼词一一覆盖
你说,做一个沉默者并不容易
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做一块石头
风声里那么多陷阱,就连落下的雨
也掺杂着来自高处的阳奉阴违
做一块石头太难了,不小心被砌进墙里
必将遭受众人目光的射杀
你说,目光的高度,往往
低于任何一个低头爬行的影子
高傲者自有失,石头同样要闯荡江湖
如果石头被磨成沙子,势必
失去个性,失去姓名
失去所有与血有关的热度
有一部分沙子在柏油路上想起往事
不甘心就这样一辈子
哪怕借助风,再飞一次,重新嘲笑世人
曾经无度搜刮自己的风,此刻异常高大
不求任何人!我愿意清贫一生
石头也曾有过热血豪情
从一道沟滚进另一条壑
你说,起起落落的路上没少被坑
学会圆滑才不会被欺凌
才能在无数场山雨欲来中屹立不倒,才能
伪装成一个少言寡语者,逃避是非
石头是怎样跳下山崖的?
勘察过现场后,他们匆匆抹掉痕迹
这种相遇,或许只有一撇
他们却读懂了你的痛苦与野心
你说,这个世上,太多问题难以解答
真相是无数次敷衍后的沉默
他们在调查过程中
也将会成为石头。
这里有每个人的一生
未来之事难料
你说,石头有了不满,才会敲打山谷
敲打这生生世世缺少回声的山谷
不敢用力了
这辈子许多话忍着没有出口
撞到沙子,就把沙子摁进修辞的末端
让其微弱地发声
既表达了诉求,也不过分生事
撞到大树,就拍一拍他的末须
把那些来自人间的尘土掸去
少几分烟火味,便少了几分危险
人群密集的地方,危险度更高
大树迟早要下山,迟早
要失去一棵树的样子
撞到谄媚者,就接受他
慢慢学会做一个小丑
毕竟有时候也需要粉饰太平
撞到同病相怜的,就挤一挤
拿出多年不敢示人的脆弱
拿出胸膛深处压抑的怒火
一杯老酒,几块石头
围火取暖
邀请夕阳的余晖前来开光
棱角有差别吗?
我只知道所有的苦难相似
遇到采伐者,也会吓得魂不守舍
铁质的器具具有杀伤性
沸腾的血因之冰冷
父辈不止一次提起过
铁是宿敌,冰冷的宿敌
没人的时候,石头也会小声唱歌
唱出委屈
唱出疼痛
唱出对命运的不甘
唱出多年未痊愈的旧伤
唱出一块石头的发家史与沉沦的种种缘由
唱出往事,唱出历史,唱出求不得放不下
唱出风雨密谋已久的蜕化与重生
石头也曾有过青春与年少
一只曾经驻足的蝴蝶,很轻易地夺去了他的爱情
其实,甜言蜜语最可怕
美丽的背影最可怕
他们随后变成金子和宝石
走进博物馆
走进富人的温柔乡
进行新一轮的流亡
善谎者像橘子,甜中带酸
在此之下,许多界限模糊
但是石头是怎样跳下山崖的?
这将一直是个谜
秋后
麻雀反复商量的事
已经被多次
拒绝
谷地里,它们纷纷投降
秋后,天空高了一分
空旷的大地
难以养活接下来的荒芜
更多的鸟进巢
一只只,独挂枝头
他们去向神秘
他们的一生充满了未知
在秋天,不用过分紧张
所有解释不清的事情
都能在一粒米里找到答案
那只喜欢说话的鹦鹉死了
我不敢停下我的笔
我怕再也记不住此刻的场景
我怕没出嘴的话
再没有机会表达
耳朵和笔同样珍贵
毕竟世上能留下的东西太少
那只喜欢说话的鹦鹉死了
终于不用再因为嘴巴活
最后一个尾音,也
“沿着屋顶的方向消失了”
天空那么大,足以安慰整个人间
刀钝
镰刀生锈很久了
麦地里
曾经高高在上的部分
彻底消失
麦子齐头生长
谁也不愿意第一个
站出来。再次地
一些往事就此戛然而止
刈麦者的步子迟缓起来
只有拿刀时生出的风声
越来越急
火柴
冬天的树枝像白骨
一堆堆逼近
残留的东西多为人不齿
月亮就是这样一个可怜虫
清醒,高冷,又不敢出声
你说孩子能看见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深夜里划亮一根火柴的罪过
远远大于在半路安慰一群迷路的人
筷子
好大的欲望
一下子就传染了
这么多人
每只持筷的手
伸出后
便停不下来
筷子的欲望
是从做一棵树开始的
而每一棵树
都曾幻想在巨大的森林里
饱食盛宴
警惕
写一条苍蝇能看懂的标语
简单点,就写:
“不要进来,这里危险”
但愿它们能够学会轻信
轻信扬起的手势真会落下
轻信赞美里藏有致命的毒药
轻信陌生人的善良
轻信趋之若鹜是一种信仰
真的很难,肮脏的事物
拿起与放下都如此轻松
真的很难,谄媚都是陷阱
忍受欺骗才会百毒不侵
真想告诉它们
不要进来,这里危险
毕竟生存不易
毕竟苍蝇也有美丽的时候
大风
目之尽处一片浑浊
草不是原来的草,他们的野心在
更高的地方
沙子是最难驯服的,他们说
草原之上,规规矩矩长久不了
如果是草
就要有戳破天空的长势
如果是沙子
就要学会在诋毁中长成石头
如果是少女
就要懂得处女之身迟早要没的
大风过境,羊群消失
马上之人越来越小
只有多年前撒下的谎在风中若隐若现
月亮投下干净的影子
睡在草原上的时候
从不担心会有蚂蚁爬上来
因为我的欲望全部藏好了
贪婪那么巨大
再多蚂蚁都无法搬运
不能把肮脏的一面暴露在草原上
不能让那些忙碌的蚂蚁空手而归
要睡就睡在草原上
要睡就找一张铺满月光的大床
月亮投下干净的影子
归途明亮异常
蚂蚁在别人的呓语里满载而归
蚕场
蚕场没有明确界限,在鲁东南
一座山,一道梁
一棵枯而未倒的槐树
都有可能成为界限
祖上传下来的东西多数可靠
生产队划分的蚕场
均匀,等量,公正,严谨
说这话时,爷爷比任何时候都严肃
祖上还传下来过质朴,诚实,坚忍和委屈
曾经因为贫穷而落下的泪水
在这富足的山里突然涌现
那里有奶奶的青春,父亲的稚嫩
也有母亲第一次嫁进山时的羞涩
天尚冷,太阳无力温暖大山
父亲披着隔夜的露水准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