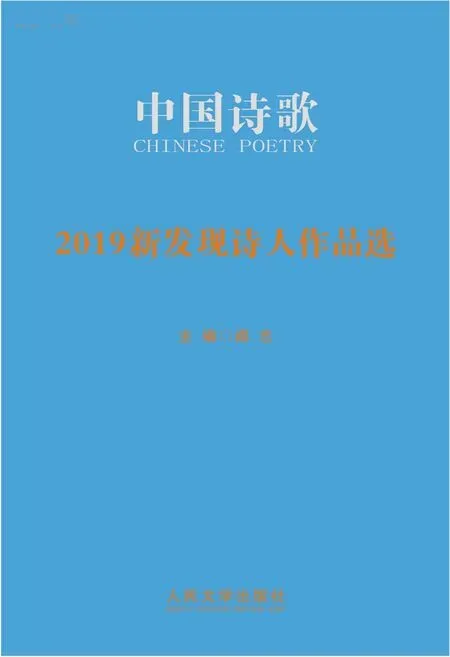邓可君的诗
披上庄稼
我要把庄稼种在身上才能活
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
都要盛装
这样
就没有人敢来脱我的庄稼
没人尝试揭下我的皮
没人敲打我的骨瘦如柴
没人唾弃我的乌漆墨黑
没人知道,我一出生就没有土地
女生节
我的心里空无一物,儿子还小
奶瓶里的硬币吐出泡泡,开出绿色的花
一光年前,我搬动过南天门的影子
在日晷上,歪着一根极度柔软的指针
季节并不扭动,动物们一片和谐
终究有人老去,带着干花和乌云
驾鹤西行时要穿越十三尺高楼,轻踩自家屋顶的黑瓦
我看不到她
入夜时分,点过的纸钱试图减轻寒冷的重量
她驮着一袋冰块儿,把脊骨压得咯咯响
八十五岁
所有热烈的生命在病榻上化为灰烬
乾坤倒转,灵魂很轻
她在盘旋,随时空扭动
性别,年代
她可能成为我儿子
下雨天
朝天门和黄浦江只隔了一扇窗
城池在码头之间流转
心中的人就坐船来往
波浪在舷窗上反复散开
我们坐在一起,像雨脚试探海水深浅
哥哥
海上大雾笼罩
船舷像患了风湿
哪里去找风和日丽
杯壁上残留的眩晕在波浪中越晃越少
临终
我应该抱紧她
抱紧一个孤独衰老的灵魂
趁她还有重量,还有留下来的决心
拉她一把,像鼓励一个蹒跚的婴儿
路是那么远,没有走过的暗夜
苔藓是不是会吃掉连在一起的鞋子
她以跳跃预备飞翔
滑动,竹叶作桨
无论是河流还是天空
都不再眷顾这样一个
因为吃饭而活下来的人
因为睡觉而活下来的人
她曾经多么根本且坚固
如今,大地裂开
包裹她,如一条新鲜的伤口
那个老灵魂已经无法起身
倒下的牙齿把嘴唇砸破
燃烧,碎裂的柴火
春
整个冬天
我都举着黑色
笔墨浸润枯黄
毛边纸生熟不一
这个冬天
写下所有的战书
砚台换了一盏
废纸篓总是倒不干净
有时候,树的影子在周围打圈
一个完整的晴天
我把字写得阳光明媚
仿佛能听见她的笑声
有时候,表盘形状奇特
分秒之间,鸟兽也不知黑白
雨落,躲进罥烟眉画龙点睛的
黑痣、红唇、大花轿
墨汁把冬天炸得通红
我看见了写喜联的姑娘
南方海
你看 爱上浪子的时候
海滩可以把人吞噬
夏日夕阳把美人刷上油漆
让她晾一个晚上
太阳不来
马达轰不走轮胎
东风不来
月亮也不来
天气不准备化妆
船长是个至今都让我误会的谜
误会他暧昧一瞬
那个晚上 灯塔灿若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