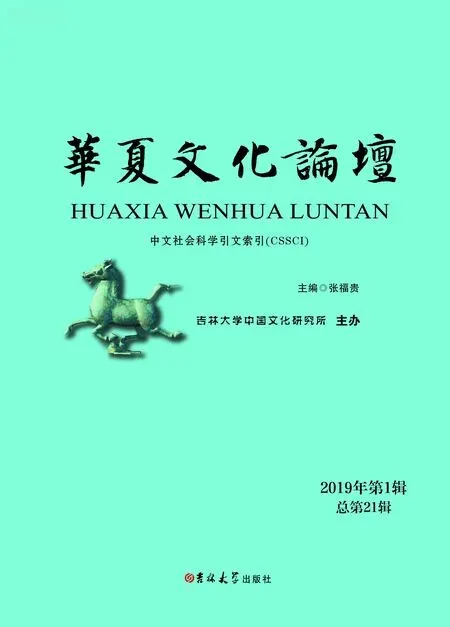作为话语的新闻专业主义:基于历史和逻辑的考量
石谷岩 常 江
【内容提要】本文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出发,通过对美国主流媒体与新媒体机构与其选举政治之间的互动过程的分析,探讨作为“信仰”的新闻专业主义和作为“话语”的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差异。本文进而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内涵进行剖析,进而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式生成本土新闻理论的问题。
一、引 言
作为欧美新闻业普遍遵循的价值规范,新闻专业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受到严肃的学术和政治审视。在美国社会的土壤中,它不仅是新闻生产应该客观、独立、抱有社会责任感的价值伦理标准,也是一种具体的行业实践,代表了权威话语体系对新闻业的规训,并与特定历史条件接合(articulation)。在美国本土,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反思性)研究多从新闻职业的社会学入手,取得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美国式的新闻专业主义成为构筑本土新闻行业专业化的强势话语,并长期为业界、学界相关人士所关切。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本土文化土壤中的内涵、模式、本质、流变,至今尚未形成准确的、可为人们广泛接受的理解。美式新闻专业主义诞生的社会土壤是进步主义和专业主义运动的开展,经济土壤则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并行,以及劳动分工逐渐专业、精细化。新闻专业主义在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社会土壤中得以形成、发展壮大的历史语境,以及这种历史语境所标识的鲜明的“美国性”,往往在中国语境的讨论中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前沿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也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新闻行业的对主流信息生产的垄断地位,进而重新组织了新闻机构的存在形式和运作机制。这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反思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的机会。一方面,若技术的变迁是导致自媒体平台上假新闻横行、“后真相”时代全面到来的重要原因,那么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新闻实践范式,其效力究竟如何体现?另一方面,在新闻行业普遍陷入“失范”危机的情况下,那些呼吁新闻专业主义回归、呼吁新闻教育“专业化”的口号,又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本文即以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新闻业的表现,及其与美国选举政治之间的互动为考察对象,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方式及实践形式进行批判性考察,并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做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符合时代特征和本土旨趣的判断。
二、新闻媒体与美国选举政治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将刊物出版物匿名发表文章称为国家的第三种权力,美国政治体系的设计亦称新闻是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的“第四权”。这是新闻专业主义在学理上的合法性基础。无论何种体制,均认可新闻行业在保障公民权利和监督政府的权力使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一般意义上认为,奉行“新闻专业主义”的新闻媒体是进行专业化新闻生产的独立新闻机构,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和编辑则是与普通民众不同的“专业人士”,两者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前者有能力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专业化的新闻采编工作,因而有“资格”获得后者的授权,为其把关信息。
美国社会学家弗莱德森认为,专业主义代表的是有别于资本和国家权力逻辑的“第三种逻辑”,它强调了自主运行和专业性的价值观。但欧美主流学术理论始终无法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或刻意回避这个问题),那就是:专业的标准究竟由谁制定并为何制定?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专业”即为劳动分工制造合法性的话语,其本身就是维护国家机器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威的工具。专业受到资本和国家力量的双重牵制,其内部凝聚力建立在对“专业化”的生产机制的再生产的保证之上。在特定的时空语境和代表性案例中,新闻专业主义的确发挥着有效的权力制衡作用(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五角大楼泄密案”“水门事件”中的表现);但若着眼于历史的长河,不难发现,新闻专业主义要维护的东西远远超越“监督政府行为”或“揭示社会问题”这样具体的概念范畴,维护国家政策的延续和促进主流意识形态再生产才是专业新闻生产更为重要的任务,哪怕其生产内容及议程设置和新闻专业主义倡导的客观性、理性、独立有所背离,或者和民意有所背离。这一点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体现得格外明显。
回顾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在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角逐中,前者得到了新闻媒体几乎一边倒的支持,而后者则成为绝大多数媒体戏谑、揶揄的对象。尽管美国主流媒体历来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价值立场差异,但是在面对代表着民粹主义力量的唐纳德·特朗普和传统政治精英希拉里·克林顿的竞争时,我们会看到,绝大多数主流媒体几乎统一声音,共同消除异见,一致为维护美国精英政治传统发声。更有甚者,多年来一直试图在党派政治中保持中立的美国《大西洋月刊》在这次大选期间罕见发表社论支持民主党,而众多长期稳定支持共和党的媒体,如《亚利桑那共和报》《圣迭戈联合论坛报》等也纷纷为希拉里·克林顿背书。倒戈的媒体还包括上次支持民主党要分别追溯至1916年和1944年的《辛辛那提问询者报》和《达拉斯晨报》等。在内容生产方面,以全球最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主流大报《纽约时报》为代表——有研究表明,《纽约时报》在对特朗普和希拉里的相关事实报道中存在明显的好恶偏向。在美国,新闻媒体党派化已经不是新鲜事,所有人都知道CNN和福克斯新闻台之间的立场差异,但是绝大多数媒体如此一边倒地偏向某位候选人,甚至造成了特朗普支持者的“沉默的螺旋”效应,的确很难令人看到新闻机构在有意识地履行新闻专业主义对“客观、公正”的要求。
一方面,主流媒体背离专业主义标准,一边倒地维护“最大的意识形态”即美国的精英政治传统;而另一方面,有利于特朗普的各种非专业新闻,以及假新闻,却在网络媒体和自媒体上兴起并获得大量转发。与主流媒体的喜好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以Facebook 为代表的社交网站上,特朗普的支持率一路碾压希拉里·克林顿,他因此被人称为“社交媒体总统”。沃尔特·李普曼曾在《舆论》中提出“拟态环境”的存在,他认为多数人的认知过程的形成都要依赖媒介机构,所以媒介机构创造的“拟态环境”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想法和行为。算法时代的总统大选更具有这样的特征。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分别在各自的阵营中,通过算法过滤机制接触、传播个人想要了解的新闻,形成内卷化的“我群”(in-group)趋势,结果是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各自为政,在“另类空间”中封闭自我,意见和阵营“极化”更为明显,而这一过程明显令特朗普受益。在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媒体是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这是一个支持特朗普的极右新闻网站,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特朗普竞选期间担任该网站的首席执行官,他曾任特朗普竞选团队主管,被人称为“白宫操盘手”。该网站发布了大量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贸易保护主义、白人优越论、反对全球化的内容,成为特朗普竞选的舆论推手。该网站还发布了大量具有一定依据,再加上一定推测性的贬损希拉里·克林顿的“假新闻”,且浏览量极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竞选期间的舆论生态。这样的舆论环境使得公众对媒体逐渐失去信任。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在2016年9月14日发布的民众对媒体信任度调查结果显示,仅32%受调查者表示对媒体充分信任,创历史新低。该年仅有32%的受访者认为大众传播媒体“对新闻的报道全面、准确、公正”,与去年40%的比例相比,降幅达8个百分点。盖洛普公司认为,这可能要归咎于总统选举中各路媒体的表现。
无论是主流媒体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背离,还是新媒体中“假新闻”的频发,都与旨在消解一切真相、反对权威的后现代主义语境无法分离。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业内外人士都在声讨传统媒体违背了新闻从业者们一直奉为职业信仰的新闻专业主义。但实际上,这种“莫名惊诧”实在没有太大必要,因为传统新闻行业在美国本来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因此在维护大资本家与政治精英的权威,防止民粹主义获得胜利的过程中,传统新闻行业选择维护代表精英利益的希拉里·克林顿,弱化其“邮件门”的影响,并攻击特朗普的言论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坚守还是批判
面对逐渐衰落的传统媒体和众声喧哗的媒介生态环境,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态度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坚守或者批判。有人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仍然具有规范新闻实践的重大意义……在人人生产并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信息的‘技术民主'当中,新闻专业主义需要以理性交往模式为‘元传播范本'展开重新阐释,并以之与现实条件相勾连”。还有人指出,“在新闻业承担的内容生产和社会责任的关系中,在信息爆炸与众声喧哗中寻找到独立新闻价值才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关键之所在”,并且提出坚守新闻主义是要坚守新闻客观性,注重社会责任,在信息爆炸和多媒体融合发展中坚守伦理规范。
以上“坚守论者”认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态度应该随着媒介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应充分思考传播技术的变迁对新闻专业主义话语提出的新的时代要求。通过对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这一个案进行话语分析,借用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在 《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
)一书中所使用的 “液态的”概念,陆晔认为新闻业目前正呈现出鲍曼所说的“液化”状态,具体体现为记者群体、新闻职业共同体边界模糊、职业流动性强等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她认为更应该“将新闻专业主义不仅视为有关媒介公共性和记者职业角色的期许,也将其视为以自由表达和公共参与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的话,“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话语实践,依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话语资源,并且具有新的普遍关照 (general relevance)的理论意义”。由此可见,“坚守论”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在媒介融合、信息爆炸的时代更应该肩负起重任,应当将其核心话语贯彻于新式的新闻生产中,并为其赋予抽象的“信仰”角色。而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下,如果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历史性考察,就会发现专业主义的本质并非是信仰,而是一套资本促使新闻业独立于社会政治机构、促使新闻从业者取得“独立的”合法性的政治话语。从这一视角出发,新闻专业主义所面临的危机其实并不主要由前沿技术导致,而源于其服务于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新闻机构的本质。
例如,赵月枝、王维佳等考察了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历史环境和制度因素,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最初是“媒体业主们防范国家干预其资本积累自由和维护私有新闻产业的政治和社会措施”。它能有效地规避国家干预,促进新闻行业的资本原始积累,扩大行业规模。王维佳还认为,19世纪后期资本的集中和产业的垄断促使美国新闻业产业化;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劳动群体从自由劳动转向了工资劳动,对体制的依附相应地增强”,进而提出“要区分市场新闻业的两种参与者:一是作为职业群体化身的新闻记者等劳动力,二是作为资本化身的媒体机构”,由此得出“媒体机构实际上篡夺了职业记者群体的专业主义诉求,变为媒体资本脱离社会控制、独立操控舆论的至关重要的合法性屏障……记者的独立自主实际上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理想和被资本力量随意调用的意识形态”的结论。胡翼青、郑保卫等也持类似的观点。胡翼青认为,从倡导新闻专业主义的美国报业巨头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开始,新闻专业主义就是作为一种管理的意识形态而存在。也许在记者眼中,新闻专业主义是新闻行业的职业信仰,但是对于传媒企业主来说,“一方面它可以尽量减少报道所造成的社会风险和市场风险,尽最大可能不得罪复杂的政治势力和财大气粗的广告主;而另一方面,它又可以约束新闻从业者的个体行为,增加其专业认同度,加强自律与自我审查,使之便于管理”。而郑保卫、李玉洁认为,“新闻专业主义观念所具有的理想主义色彩让人忽视了职业观念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对其所进行的操控和限制,也忽视了新闻机构作为美国社会中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机构的运作过程”。
基于对“坚守说”和“批判说”的理解,本文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更像是社会专业化运动在新闻业的延伸,是科层制管理在新闻行业的应用体现,但被巧妙地包装成了记者应当遵守的职业信仰。在社会机制运转平缓的时候,基本矛盾被掩盖,新闻专业主义有丰沃的对自身存在的社会条件进行再生产的土壤,因而往往可以很好地发挥其效能——监督政府、揭露问题等。但在主体权力结构受到系统性的挑战(如极端民粹主义力量获得角逐国家最高权力的入场券),或社会的变迁的轨迹因某些力量的出现而导致动荡(如前沿传播技术对话语生态和意识形态力量对比的影响),新闻专业主义作为“话语构型”(discursive formation)而非基础价值观的本质就会表露出来,成为被操纵和利用以维护“更大的稳定”的工具。
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媒体表现来看,新闻专业主义其实有着鲜明的功能指向——它不是服务于某一个政党或某一类观点,而是服务于美国制度底盘的稳定性,包括两党政治、精英治国、三权分立等。当这些基本政治原则有被破坏的危险,它所强调的客观和中立都是无从谈起的。美国式新闻专业主义伴随新闻行业的专业化生产而出现,它本身就是劳动分工的必然产物。没有资本的社会化大生产,没有新闻教育、新闻采编、新闻出版和精细化分工协作,没有新闻行业雇佣制度成立,就不会有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从本质上来说,正如甘斯在《什么在决定新闻》中对新闻编辑室的考察一样,在信源的选择、新闻内容的生产方面,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生产机器的国家新闻生产机构会遵循一些有利于权威巩固的“法则”;而作为官方行业标准的新闻专业主义,也是为了巩固掌握了信源、从业者教育资源以及宣发路径的权威地位而诞生的产物。对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严格意义上说,新闻专业主义不过是媒体精英社群的标准和理想,与普罗大众之间还存在脱节甚至是分裂,是媒体精英建构的乌托邦”。
四、余 论
在所谓“后真相”时代的美国,一方面是精英媒体影响力的衰落,传统媒体纷纷倒戈一方,新闻政党化显露无遗;另一方面则是新媒体平台上假新闻层出不穷,造成了类似“气泡过滤”“回声室”等舆论和态度极化现象。这为我们反思新闻专业主义的本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来,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一直在下降,究其根本原因,是权贵阶层联合霸占了新闻信息的生产资料,并按照自己的意愿不断对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结构进行再生产的体现。在“二元对立,尊重权威”的现代主义被“多元化消解一切真相”的后现代主义逐渐取代后,公众对宣泄情感的需求大于对事实追问的需求,慢慢不再在乎真相是什么,不再相信传统媒体的报道。公众对专家、学者、媒体的不信任,对精英主导的社会的不满意,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种情况下,不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本质进行反思,并努力超越“专业”的边界,去建立起一种新的行业范式,而一味捍卫作为“信仰”的新闻专业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内卷化”的体现。
新闻专业主义源于美国,是在代议制民主政治、高度发达的海洋法体系、纯粹的商业化大众传播市场、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以及由此兴起广泛的专业化运动等等独特的社会基础上诞生的,它的适用性必然也要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在中国,传统主流媒体在大众传播市场中并未实现纯粹的商业化,且也没有两党制的传统,社会利益、宣传效果是主流媒体的首要考量,这也决定了简单的“挪用”,哪怕只是话语甚至表达层面的“挪用”,都会带来认知混乱的问题。诚然,在20世纪80年代,新闻专业主义曾经是中国新闻业谋求独立发展,脱离政治与社会束缚的理论武器,也在特定历史时期为新闻业专业化程度的提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学术界揭示出的西方新闻主义各类模式,实质上是中国学者站在中国的语境下,对西方主要是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一种描述乃至想象。甚至进而说,在这里展现出更多的是作者们自己关于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寄望与愿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专业主义作为舶来品,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在多数场合,使用者本人并不知其历史条件的情况下便随意使用的概念。在对新闻专业主义话语进行有限、有效借鉴及本土化的过程中,必须时刻警惕“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的问题。
总而言之,“新闻专业主义”虽然是一个在历史中形成的、有着自己独特的政治内涵的概念,但它对于新闻生产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要求,对记者的专业意识的培育,以及它对新闻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考量,的确可以为我们在不同时空语境之下理解新闻业的本质和使命带来有益的启发。但正如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本身是“历史地形成”的一样,我们对于中国新闻业的具体实践及其理论化,也应当是一个基于历史、忠于历史的过程。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制度和文化条件下的人类社会有着不少相通的地方,观念上的相互借鉴甚至相互引用,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让我们的认知还原到准确的历史脉络之下,同时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式生成本土理论,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